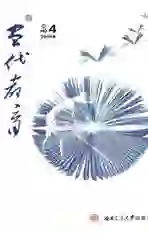他在丛中笑
2017-03-18郭渊
郭渊
2016年4月12日,清明刚过,阳光温暖,春风徐徐,空气中已有了些许谷雨的气息。先生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说“不放心我”,有些东西“还不行”。虽然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却依然一派懵懂,并不明白个中深意。我带着一身未退的寒气来到先生家中,似乎冲破了屋内的温暖。先生万分亲切,接过师母递过来的塑料小凳,拉我坐在他身边,一改往日丁卯话语。先生一会儿关心我的生活,一会儿又畅谈诗歌写作上的心得,说诗歌蕴含的东西很多,虽不可下里巴人,但亦不可阳春白雪。诗言志,可以兴……诗乃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不可无为而作。诗贵含蓄,写性情以真切为要……我暗自心惊,已入耄耋的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艺术事业,为何今日有如此叮咛。春日的暖阳透过窗户射进屋内,仿若薄雾依稀,先生的白发被染成金色,矍烁的眼神中已显暮色。
说毕,拉过我的手,问起了我今年的创作计划是什么?犹豫了片刻,我说:“我想尝试从诗歌的角度切入,创作一部海龙囤的长诗。”话音未落,先生马上说:“好,非常好,诗歌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可以直入主题……”接着,先生马上询问起我是“如何构思,从何着手,表现什么主题?”我想不到,一直处于构思阶段的写作计划居然得到了先生的肯定和贊赏,惶恐中,我大胆说出了自己尚未成熟的想法:“通过杨氏一族的兴衰成败,彰显海龙囤就是一种文明的主题。”听罢,先生稍停顿后说,“这是个大题材,一定要有大结构、大主题,你先写,有些眉目后我来给你把把脉。”
围绕海龙囤,我和先生聊了很久,因先生每周三次透析,怕先生身体支撑不住,不得不起身告辞。临行前,先生叮嘱我回去好好看看《邓小平之歌》长诗的结构和主题,同时注意诗歌的语言和节奏。一定要强迫自己读一些长诗,如《波尔塔瓦》等描写战争的经典长诗,一定要我读。
我似乎被这场气氛诡异的谈话吓到了,胸中开始哽咽;我似乎嗅到了房中苍老的气息。十六年的授业恩情,使我与先生的情分早已超越了师徒,不是父子,胜似父子。我郑重地应允了,心中却有泪水在冲动,先生已有垂老之象,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心力十足的刚毅教授了。现在想来,那应该是一位老人对往生的预感。
2016年10月19,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因一夜失眠,我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了,暮秋的清晨有着丝丝凉意,我感觉病了,胸中压抑,有一口气凝驻着,呼不去。睡眠一向很好的我,竟然如此莫名其妙的失眠?毫无来由,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上班不在状态的我,临到午饭时间,打开手机,一刷朋友圈,突然,一条信息被无形放大,瞬间占满了手机显示屏,也瞬间屏蔽了我的整个大脑。先生走了!就在今天凌晨。我随即赶往景云山殡仪馆,先生已躺在太平间了……泪眼迷蒙,无语凝噎。我想起半个月前因修改《千年播州——海龙囤·1600》长诗,先生和我促膝长谈的午后,竟会是我最后的惦念。昔日儒雅慈祥的先生,现已沉睡,只见冰冷的遗体。抽丝般的痛,将心头的肉撕来扯去,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深入骨髓的痛。
两周后的今天,贵阳下起了绵绵秋雨,天公也为恩师送行,有着和泪湿衣衫的人们一样的心情,先生就在如此收获和时节中安详地走了。
连日来,辗转反侧。一想到恩师已沉睡大地深处,而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胸中的压抑之感越来越沉重。我明白,我是真的病了,这种病源于恩师的逝去,胸中有着解脱不了的悲闷之气,这种病叫做感念。先生十六年的教诲情形,在脑海中愈加清晰,那些已封存多年的画面一瞬间都释放了出来,就这样变成了不断反刍的记忆……
与先生初识是在2000年的秋天。我就读于贵阳师专美术系二年级。高中就开始习作诗歌的我,一直希望在学校能找一个老师指导写作。进校后就不停地向师哥师姐打听学校这方面的“高手”,当得知中文系有一个叫王蔚桦的老师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时,我兴奋不已,但先生已退休。
怎么办?我一边通过学校微机室面对学生开放的机会打印诗稿存盘,一边通过中文系的同学想办法打听怎么样才能与王蔚桦老师见上一面,以便当面请教。当我打印完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作的200余首诗稿后,看到学校挂出了“热烈庆祝第十五个教师节”的横幅我想机会来了,因为老师虽退休,但学校庆祝教师节的活动,老师肯定会出席。
于是,教师节当天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着请老乡帮忙打印的厚厚一叠诗稿,向中文系教师办公室走去。当我敲开虚掩的门后,王蔚桦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先自报家门后,便把近年来创作的诗稿交给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批评和指导。先生一边上下打量着我这个无名的“毛头小子”,一边接过诗稿后翻了翻道:“一个学美术的,居然喜欢文学这‘劳什子,回头我给你看看。”
没想到,王蔚桦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高高在上的、抽象的,我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和先生产生此种联系,自己的冒昧拜访没有打扰先生,反而受到了先生的热情接待。在中文系老师办公室的初次见面,先生的气度与德行,不但打消了我的不安,还见识了先生的学者风范,感受到了先生的和蔼可亲。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终于见到了先生,且先生应允了;担心的是,先生那么忙,真会抽时间看完自己的诗稿吗?自己的诗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会得到先生的肯定和认可吗?我怀着即惊喜又矛盾的心情,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一天上午,电话铃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先生慈祥的声音:“你的诗作我全看完了,清新雅致,有陌生感,建议选出百首左右编成一本诗集,我给你写个序言,争取在毕业前出版,我想办法帮你在贵阳找个工作。”
挂完电话后,我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人肯定了。至于在贵阳找份工作,对于我这个来自大山的农村孩子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带着美好的憧憬,接连失眠了好几个夜晚。接下来的日子,一边在先生的指导下选编诗稿,一边与出版社联系。然而,自费出版需要7000多元钱,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要拿出这数目的一笔钱很是困难。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带着我到贵阳市文联“化缘”,获得了2000元的赞助费。
事隔多年,先生才跟我说起,就为了这2000元的赞助费,几经周折。相关领导嘴上答应没问题,可到具体的操作上,这个领导说管不了这事,那个领导说这事得谁谁说了算,就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在先生多次沟通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便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市文联的相关领导,电话那边答应说马上就办,可之后就是不见落实。一气之下,先生在一个清晨,趁大家都还没出门上班的间隙,直接跑到领导家,把一肚子的火憋成了“咚咚咚”的擂门声。领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急事,来的什么人,竟有这么大胆。过了许久,门终于打开了,看到穿着一身睡衣和一脸睡意的领导,先生大声嚷到:“某某某,我不是为了我的事情,我是为了贵阳市文学事业的发展来找你。”不容分说,领导被这突入其来的一幕吓白了脸,只好答应说:“马上落实!马上落实!”。
经过几番周折,我的第一本诗集《六月没有主题》终于在2001年12月份出版了,先生为我写了《胸中田园别有情》的序言。诗集出版后,先生还将我的诗歌推荐给《贵阳师专报》副刊整版发表,还积极协调学校宣传部和校团委共同给诗集做了一个首发式。事后,先生叮嘱我要戒骄戒躁,要苦读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中外诗歌中的经典作品,以自律自策。
先生為我做的这些,怕影响到我的学业,都不让我有丝毫察觉,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先生的举动令我颇为感动,我也懂得了何为“师德”,何为“大家风范”。我明白先生的名字依旧“高高在上”,但却不再“抽象”。先生的精神影响我至今,不仅是在写作上,更重要的是在做人上,影响我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写作,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那个夏天,在与先生相交的短暂的时日里,先生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洗去了我的年少轻狂,洗去了我的浮躁。每当想起,我浑身就会有一种无穷的力量。
大学毕业后,本来属于定向生的我,因为诗集的出版,在先生的帮助下,破除了定向,却意味着我可以像其他统招生一样,不用回到原藉工作,如两年之内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学校才将档案打回原藉。在得知这一些况后,先生把我介绍到《法制生活报·汽车与安全周刊》编辑部,当上了一名临时记者。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学美术的我,除了在观察事物的方法上略占一点优势外,在新闻采访、技巧、方法、写作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均无法与学新闻的“正规军”相比。为此,先生一边鼓励安慰我,一边给我制定了学习计划。有机会到先生家里拜访时,先生还将书柜上有关新闻的书籍赠予我,给我讲述如何策划新闻主题,采访中如何对新闻细节进行捕捉等关于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技巧。除了平时的写作外,先生还要求我尽可能地将欠缺的新闻基本功补起来,同时阅读大量的中外经典诗歌作品。
当了近一年的临时记者,先生看到我为了生存在外奔波的艰辛和疲惫,感觉到了我对新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想法,此后不久,也就是2003年6月,把我举荐到了乌当区委的机关报《新天报》社,当上了一名真正的记者,有了正规编制,彻底解决我了的后顾之忧,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写作中。正是先生的这种直接的帮助和鼓励,才使我有毅力和恒心在坎坷的文学之路上不停地跋涉。
之后多年,先生成了我的“写作督导”,经常在写作中提出一些建议,指导我准确把握、分析不同题材难以把握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也使我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了更多的捷径。多年后,我才由衷地体会到了先生的这份辛劳。
2016年6月,我的长诗《千年播州——海龙囤·1600》初稿完稿,因第一次写长诗,时空跨度大,众多历史细节与历史事件难以驾驭,结构也难以把握,于是和先生约好,在先生不去医院透析的时间求助于先生。此时的先生,捧着厚厚的书稿,却不停地在找放大镜,小倍放大镜不行又换成高倍放大镜,书稿都几乎与眼睛贴在了一起,但还是无法看清楚字迹。先生因各种并发症,晚年不得不通过每周一、三、五透析来维持,视力也快速下滑,近于失明,虽茶几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放大镜,仍无济于事。坐在一旁的我,沉默良久以后,终于想出了一个笨办法,我说:“王老师,干脆我来读,您来听,您觉得有‘卡壳的地方你就喊停。”就这样,我把书名、每一个章节及每一个小标题都读出来给先生听,当我刚读完书名“海龙囤”时,立即被先生叫停,先生说:“不妙,何不用‘遗恨海龙囤作为书名”,接着先生说出了他的理由:“平播之战本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多少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战争席卷,一个王朝就这样因这场战争而加速灭亡,用‘遗恨海龙囤更好”。读到第一章标题“播州”时,马上又被先生叫停,何不用“播州,播州”,加重语气……就这样,一个上午就这样结束了。临走时,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长诗,开头要提炼几句经典的比喻,彰显出叫人担心的人情味,吸引读者;作为史诗,要考虑历史的复杂性和丰沛的细节……”
就这样,在先生的指导下,长诗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几易其稿,由最初的6000余行改到了现在8000行。可惜先生等不到这部长诗的出版面世,这也是一种“遗恨”。
每次从先生家离去,离开先生的那一霎那,我都百感交集,眼泪不由自地主夺眶而出。学艺多年,先生为我付出诸多心力我无法偿还,只希望能拿得出像样的作品来回报先生,能给先生带来些许慰藉。每次,我都会发现先生的眼睛也湿润了,于是更加坚定了我的意志,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因为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汗水与努力。这部长诗在浓浓的师生情中开始,在浓浓的师生情中完稿,可以说是成功的。对此,先生的内心定是无比喜悦,而我的心里则是充满幸福而又极为复杂的。因为,这成功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无不是先生在我艺术道路由稚嫩逐步趋向成熟的过程中所倾注的心血,无不渗透着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殷切期望。
我想,如果认识先生十六载来我有所成绩的话,倒不如说我前进的每一步都有先生的汗水与鼓励伴随左右。我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幸运地遇到了先生。是他给我信心、为我导航、赐我智慧、教我做人……
送走先生的那天,贵阳的天气由连日的阴雨突然变晴,仿佛阳光都在为先生一路行。安葬先生的龙归园,山清水秀,想必每年春天,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绽放时,先生一定会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