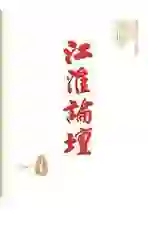MEGA工程从创立到1990年的历史及其意蕴
2017-03-14罗尔夫·黑克尔
摘要:本文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工程即MEGA工程自1924年梁赞诺夫创立至1990年的历史演变。贯穿MEGA工程的是一对历史的张力:虽然MEGA是东德和苏共时期的工程,但它同斯大林式的执政党教义的关系并不稳定。本文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影响MEGA的政治压力,以及1989年后剧变期的重大问题;考察了版本内容在这些历史时期的范围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政治因素和编辑因素;着重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柏林和莫斯科的关系,及其对版本编辑的影响;指出了1989年之后国际学界对MEGA的支持;最后探讨了MEGA的出版在国际学界的反响。
关键词: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历史;意蕴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009-003
MEGA的編辑工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存在一对张力:虽然MEGA是东德和解体前的苏联共产党时期的工程,但MEGA从来就不是苏共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斯大林式的严格的执政党教义的关系并不稳定。这怎么理解?我们可以在MEGA工程本身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以全集的形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的想法可追溯到1911年。在筹备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时,奥地利和德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一起考虑如何进行这种全集的编辑工作,达成的一致意见被称为“维也纳编辑计划”。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有其背景的出版社的财力有限,这一项目最终失败了。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命运就和政党路线的迫切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维也纳编辑计划”的缔造者是大卫·梁赞诺夫。这位俄国思想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卡尔·考茨基保持着最好的联系。多年来,梁赞诺夫通过研究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的档案资料,已经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历史,他最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
1917年的“十月革命”及之后的列宁政权,给了梁赞诺夫另一个机会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工作。1921年,列宁委托梁赞诺夫在莫斯科成立和主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3年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委托他编纂MEGA,或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梁赞诺夫从流亡维也纳时期就熟识的卡尔·格伦伯格当时在主持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梁赞诺夫的指导下,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密切合作,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意,开始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编目和拍照工作。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这项工作的是孟什维克的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他曾被驱逐出俄国,“尼古拉耶夫斯基收集品”现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此外,梁赞诺夫在他的研究院同事中,有一些非俄籍专家,他们既活跃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中,又是德国、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地的记者。这些非俄籍专家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其中包括梁赞诺夫负责MEGA的助理厄内斯特·科索贝尔。1927年,MEGA第一卷问世了。
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合伙人,曾经是孟什维克的艾萨克·鲁宾被监禁,受此牵连,梁赞诺夫在1931年年初也“退休”了。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主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后,编辑工作中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MEGA以及梁赞诺夫的国际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斯大林的眼中钉,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更不得不顺从地为苏共的宣传目的服务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直属于苏共中央。它导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烈攻击,这体现在《资本论》全三卷的新的普及版中。这个新版本直接针对考茨基版。然而,它也导致了马克思一些家庭信件的首次出版,包括攻击社会民主党的信件,之前据说被梁赞诺夫一直保密。
当然,MEGA第一版在许多方面呈现了它的优点:它遵循国际编辑实践的标准,力求文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包括单个文本的不同变化,等等。但是,编辑也存在问题。文本的安排有待统一,拼写、年表、日期和注释有待按照现代标准加以规范。直到1941年,MEGA的13卷问世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MEGA扩大至80卷的计划在编辑人员中流传。另外,他们想增加一个第四部分,以全文出版摘录和笔记。虽然在1936年中期的公审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初始成员在“节约”的名义下被解雇了,但研究院又发生了一次清洗。这次清洗之后,研究院不再有外籍专家。1938年年底,新的编辑工作所需的文件被封存入档案,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编辑工作被允许继续下去,它的两个部分在1939年和1941年被首次发表。
1936年年初,根据斯大林的直接命令,布哈林赴巴黎和哥本哈根,意在获得全部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但行动失败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手中获取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后来在对布哈林的公审中,这次失败成为对他的一个主要指控:他被控与孟什维克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同谋。布哈林被公审,之后,梁赞诺夫在1938年被处决,MEGA的编辑人员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们或丧命于斯大林的劳改营,或被处决。之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对这些事件三缄其口,即使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也是这样:这个话题在整个东方阵营中完全成为禁忌。
历史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库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的新篇章,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利用苏联对东德的占领,从普鲁士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以及其他来源中,征用必要的文件,内容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德国工人运动史。它还成功获取了恩格斯家族档案的原始文献。
20世纪50年代早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俄文第二版的编辑工作在莫斯科启动。这个新的俄文第二版成为1956—1968年德文版的基础,之后也是许多其他国家版本的基础,英文版全集就是其中之一。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最初不得不严格按照莫斯科设定的方向来开展自身工作,这是因为莫斯科控制必要的文件,并不是柏林研究所请求的全部资料实际都能获得。一些特定著作的出版又总是出问题。因此,一些马克思的文本被排除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著作之外,例如,关于俄国秘密外交和波兰问题的手稿。还有一些不符合苏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被从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著作中移除,仅在之后作为补充卷发表,《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例子,它也被称为《1844年手稿》。
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只能缓慢推进自己的研究。当条件具备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的想法重新浮出水面。筹备出版全新MEGA的首次尝试始于苏共1956年“二十大”之后,但到了1964年之后该工作才有了具体形式。很明显:1.旧MEGA无以为继,2.新版编辑工作要在莫斯科和柏林同时进行,3.党管编辑工作的传统将保持不变。
柏林和莫斯科的研究机构在以互信精神开始协作之前费了一些周折。最终,双边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比他们各自的领导,甚至比各自党的领导人更好地理解了手头的任务。例如,工作人员比院长或党的领导人更了解MEGA工程的文献范围。如果不放弃编纂的全面性原则,MEGA至少会有130卷,对这一点,编辑人员自己早已知晓。后来这一计划被一项更稳妥的100卷出版計划所替代。
统一化的编辑准则得到重视。在1972年出版的测试卷中,这些准则以及四个计划出版部分的组织,得到公开讨论。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使得编辑工作更加精确,在此过程中又进一步产生了编辑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最终要靠补充准则来解决。然而总的来说,这些准则符合国际编辑学的标准。在这方面,在新MEGA中强调以下原则尤其重要:
1.绝对完整性(包括摘录、笔记本,以及第三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
2.严格保持按时间顺序排列;
3.精确复制原始文本(包括保持当时的拼写);
4.单个文本的变化的最新表现;
5.范围广泛的注释。
建立这些原则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些原则的贯彻需要面对相当大的阻力,尤其是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尤其是当这些原则同苏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直接矛盾时。历史考证注释版的复杂内容使苏共领导层很难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找到理论支持。与此相关,也应提到第一和第四部分的分卷没有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另一个原因较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分卷的排列顺序是由当时的编写队伍决定的。然而,尽快编纂最重要最知名的作品也很重要,包括以前未发表的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一卷。
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界对MEGA的反响直到1989年都是不同的。一方面,他们对存在一个完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欢迎;另一方面,他们对用某种历史考证的方法编辑出来的文本,对首次出版的手稿和摘录,持犹豫怀疑态度。MEGA并没有迎合当时的宣传路线或意识形态。它被视为一个学术版,并没有促使党内理论家重新考虑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
例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争论——也就是说,他们在理念上是否与对方一致——参照《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的手稿(MEGA II / 4.2,柏林,1992)和恩格斯的版本(MEGA II / 15,柏林,2004),在1989年之前不可能不引起巨大争议。这两个文本的比较肯定会使当时对马克思的“正统的”或教条的解释者高兴不起来。MEGA的完整性原则揭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如何描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理念。例如,他们对所谓“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当然,在其他方面,在两位思想家的这些差异之间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应该的,就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相同的。MEGA用可靠的文献支持来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在彻底清理旧的教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1989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到了1989年,MEGA工作人员有150人的规模,他们分布在柏林和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以及在柏林、哈雷、莱比锡、耶拿和爱尔福特的大学中。在MEGA编辑人员的通力合作和辛勤努力下,每年可出版3~5卷MEGA。到1991年5月,共有45卷出版。我们不应忘记,个人电脑在1987年第一次进入我们的生活,在此之前,文本的排版印刷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
大部分工作人员对于从事如此重要版本的编辑工作肯定是骄傲的,虽然不能否认一点,即他们被看作是为政党服务的,MEGA被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尽管他们编辑的是历史考证版,因此也必定会产生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的成果,但某种双重意识却一直萦绕心头。他们在篇目介绍、一些注释、主题索引、人名索引中,首先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稳定作用。注意到这些细节的人也会承认MEGA编辑工作在独立批判方面是有进展的。
自1975年首次出版以来,MEGA在德国以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在美国反响不强、无人订购,但在日本,1990年之前售出了800套。在有些国家,MEGA很快实现了一个主要目的,出现了以前未发表手稿的译本,例如,《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被译为俄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日语和其他语言。MEGA的编辑人员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参加关于马克思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主办方既有共产党组织也有大学和学术机构。国际范围的辩论和对编辑问题的建议,都对此版MEGA的发行产生了影响,例如,就影响到了手稿的排列顺序。
直到198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一直被视为打上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需要的烙印。随着东德的解体,MEGA的编辑人员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满足读者对学术版MEGA的需要。编辑人员呼吁一部更加学术化的版本,同样也是包含着更广泛国际合作的版本。因此,MEGA应被视为一个历史考证版这件事,在当时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在今天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也不能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就应当被如此对待。从这一点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编辑的历史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本文为罗尔夫·黑克尔教授2015年10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经作者同意发表)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