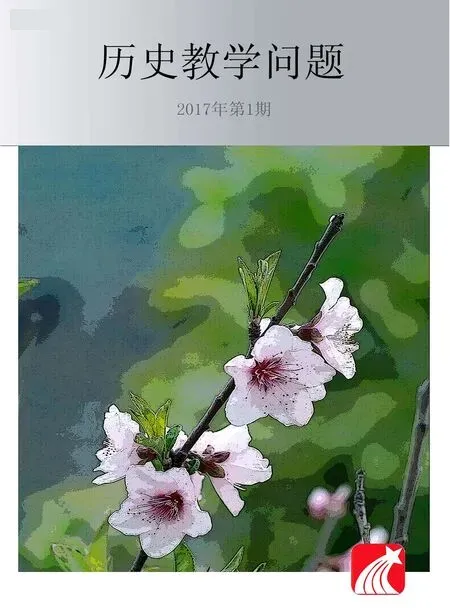古代晚期基督教社会犹太人的法律地位
——基于罗马法的考察
2017-03-12疏会玲
疏会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古代晚期基督教社会犹太人的法律地位
——基于罗马法的考察
疏会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罗马法是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世界犹太人法律地位的重要原始文献。尤其在5-6世纪法典化时期编纂完成的《塞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宗教实践以及社会活动设置了统一规范。从其中的涉犹法令可见:犹太人在享受罗马法保护的同时,日益沦为帝国的下等公民;犹太教维持合法宗教的地位,但也受到诸多限制。犹太人这一矛盾性法律地位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法传统和基督教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罗马法;犹太人;古代晚期;下等公民;合法宗教
古代晚期,①“古代晚期”的概念最早见于布克哈特的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853年)。2001年,由彼得·布朗参与主编的《阐释古代晚期》,宣告“古代晚期”作为一个专门历史分期的存在。目前学界对古代晚期的分期始末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主流观点认为其历史时段狭义上是从公元3世纪至7世纪,广义上则上至1世纪中期,下至8世纪初。参见李隆国《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陈志强:《古代晚期研究:早期拜占庭研究的超越》,《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犹太人是以罗马-拜占庭帝国为代表的基督教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主要通过成文律法来实现。法典化时期完成的《塞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犹太人政治地位、宗教实践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出规制,集中反映了犹太群体的法律地位,成为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社会犹太人生存状况、社会参与等诸多问题的首要法律文献。自上世纪初,史学界就展开了罗马法与犹太人关系的相关研究,②主要研究成果有: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Amnon Linder ed.,The Jews in the Legal Source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John Tolan,Nicholas de Lange eds.,Jews in Early Christian Law:Byzantium and the Latin West,6th-11th Centuries,Belgium:Brepols Publishers,2014.Alfredo Mordechai Rabello,The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Legal Problems,from Herod to Justinian,Aldershot:Ashgate,2000.Solomon Grayzel,“The Jews and Roman Law”,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Vol.59,No.2,Oct.,1968,pp.93-117.Catherine Brewer,“The Status of the Jews in Roman Legislation:The Reign of Justinian 527-565 CE”,European Judaism,Volume 38,No.2,Autumn 2005,pp.127-139.国内方面,参见汪中砥:《中世纪早期西欧犹太人地位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但大多倾向于强调罗马法对犹太群体的限制,对相关法令与反犹主义的渊源关注有余,而对其中的保护措施以及犹太人的矛盾性法律地位研究不足。本文借助罗马法典中涉及犹太人问题的有关法令和后世研究成果,分析古代晚期犹太人的公民权、社会地位以及犹太教生存与发展等问题,以利于后续研究的开展。
一、罗马法及其文本中的犹太人
体系庞杂的罗马法在5-6世纪开始系统汇编与整理,这一法典化过程建立在西罗马时期的零散律例、东西罗马并立阶段的有关法令以及拜占庭帝国早期的成文法典基础上,大体涵盖律例(decreta)、应答(rescripta)、一般法(lex generalis)以及授令(mandata)等内容,①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p.17,p.61,p.57,p.57.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法典是《塞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塞奥多西法典》由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8-450年)颁布,于439年初生效。近一个世纪后,十卷本的《查士丁尼法典》问世,在此基础上,法学家又先后完成五十卷本的《法学汇编》以及四卷本的《法学总论》。到查士丁尼统治末期,法学家将534年以后颁布的法令收录入《新律》。至此,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罗马民法大全》的编辑工作最终完成,为帝国理顺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罗马法的划分方式多样:根据所调整的不同对象可划分为公法与私法;根据适用范围可划分为自然法、市民法和万民法;按照权利主体、客体和私权保护又可划分为人法、物法、诉讼法,等等。犹太群体在中古早期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社会参与十分广泛,犹太问题因而涉及私法、万民法、人法、物法以及诉讼法等众多司法领域。
迄今为人所知的罗马法中涉及犹太人问题的法律文本约有百余条,《塞奥多西法典》和《罗马民法大全》是涉犹法令的主要出处。总共十六卷本的《塞奥多西法典》中有不少于六十五条法令是针对宗教异端的,②西里尔·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陈志强,武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其中,明确包含犹太群体的大约四十五条,并且主要集中在最后一卷。《罗马民法大全》中也有近四十条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法令分散在《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编》以及《新律》当中。需指出的是,这些涉犹法令中超过一半的文本直接来自《塞奥多西法典》,其余则来自塞奥多西二世的第二部新律、戴克里先时期先后编纂的私人法典《格里高利法典》和《赫尔摩根尼法典》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零散律例和行政档案。③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p.17,p.61,p.57,p.57.
罗马-拜占庭帝国在由拉丁文化转向以希腊文化为主导之前,拉丁语长期是帝国的官方语言,法典化以前的罗马法以及拜占庭帝国早期的法令多用拉丁文书写,因此,罗马法文本中对犹太人、犹太教甚至是犹太法的称谓一般为拉丁语形式。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犹太人通常被称为人民(gens)、种族(natio)、民众(populus)以及犹太人(Iudaeus)等。④Ralph W.Mathisen,“The Citizenship and 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oman Law during late Antiquity(CA. 300-540CE)”,John Tolan,Nicholas de Lange eds.,Jews in Early Christian Law:Byzantium and the Latin West,6th-11th Centuries,Belgium:Brepols Publishers,2014,p.36.以及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59.拉丁语“Iudaeus”意为“Judaean”,即“来自犹地亚地区的人”,该词和希腊语近义词“Ε β ρ α ι ο ι”在词源学上与希伯来语中犹太人的称谓“/Yehudi”、“/Yehudim”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出表示犹太人的其他词汇。⑤关于犹太人称谓的词源学考察,参见宋立宏:《谁是“犹太人”——关于Ioudaios的札记》,《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后期罗马法文献中也有一些表示犹太人的少数词汇或词组带有政治含义,比较典型的如“alieni Romano imperio”,表示犹太人对罗马-拜占庭人而言是外来者,因此,该词组在一定程度上暗含后者对犹太人的敌对之意。⑥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p.17,p.61,p.57,p.57.
古代晚期的犹太人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宗教属性居于首位,基于此,罗马法文本常常也利用表示犹太教的词汇来指代犹太人,具有代表性的是“宗教-迷信(religio-superstitio)”这一矛盾的组合词汇。古典拉丁语“religio”通常表达不带价值判断的客观态度;而“superstitio”主要表示与罗马宗教不同或敌对的宗教,体现话语者消极的价值立场。在5世纪以前的法律文献中,“宗教”和“迷信”两个词都用于指代犹太人。416年后,一般情况下,前者仅指代基督教,后者用于指称犹太人。⑦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p.17,p.61,p.57,p.57.此后的立法者更加强调两个词的对立,在描绘改宗的犹太人时,甚至直截了当地称其“摆脱了‘superstitio’,进入基督教世界”;罗马帝国西部皇帝瓦伦提利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年)上台伊始就公开强调,禁止任何“superstition”腐蚀帝国的宗教正统派(即基督徒),⑧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9,p.17,p.61,p.57,p.57.前者既指当时仍一息尚存的多神教势力,也包括犹太教。不仅如此,在指称犹太教时,罗马法文本还借助大量名词和形容词来表达并强化立法者的态度,诸如“畸形(deformitas)”、“邪恶(perversity)”、“可憎的(execrable)”、“穷凶极恶的(nefarious)”等词汇就明显带有消极含义,突出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价值观上的对立。①关于罗马法对犹太教的不同称谓,参见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p.55-61.此外,“宗派(secta)”是另一个用于指代犹太教的词汇,该词最初表示一种哲学派别,宗教内涵相对淡化。罗马帝国西部皇帝洪诺留(Honorius,395-423年)在5世纪初开始用其指代包括犹太教徒在内的非基督教徒,此后,罗马法文献中所使用的“secta”一词就进一步带有了宗教异端的色彩。
罗马法本身就有法(ius)和法律(lex)的区别,前者是将社会结构本身用法律术语加以表述的体系,后者是以协议形式确定的并且具有权威性的实在规范。②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随着罗马帝国向外发展,不再隅于意大利本土后,其法律体系也随之更加具有包容性,不仅传统的市民法(ius civile)适用帝国公民,其他法律体系也得到罗马法认可。古罗马学者尤文纳尔(Juvenal)在1世纪末就曾提到犹太法律体系“ius Iudaicum”享有和罗马市民法同样的地位。③RalphW.Mathisen,“TheCitizenshipandLegalStatusofJewsinRomanLawduringlateAntiquity(CA. 300-540CE)”,p.38.4世纪以后,罗马法文本中常见诸如“lex Iudaica”,“Iudaicus ritus”,“I-udarorum”等众多由法和犹太组合、变异形成的语汇,这些均是罗马法律文献对犹太法的称谓。古代晚期的罗马法总体上尊重犹太法学家以及犹太民族独特的法律体系,在涉及犹太人问题时,由罗马法、基督教法和犹太法组成的律法体系经常共同发挥效用,但三种体系在处理涉犹案件时的作用力是递减的。犹太法在超越犹太社团内部事务的实践中较为脆弱,其权威性因罗马法和基督教法的存在而被弱化,尤其在当事双方中有非犹太人的法律纠纷中,后两者享有绝对的优先权。④具体请参见Ralph W.Mathisen,“The Citizenship and 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oman Law during late Antiquity(CA. 300-540CE)”,pp.37-41.
二、犹太人公民身份与地位
古代晚期的犹太人是罗马帝国公民,其公民身份的获得始于西部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198-217年)在212年颁布的《卡拉卡拉敕令》,法学界一般称此敕令为《安托尼亚那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na)。作为主要管理和协调罗马人和外邦人(peregrini)之间关系的万民法,该敕令将罗马的公民权赋予了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帝国男性自由民,事实上将行省的居民提升到与罗马城居民同等的地位,其中就包括犹太人。《卡拉卡拉敕令》的出台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因素的影响,即卡拉卡拉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助公民群体规模的人为扩大来实现帝国税收的快速增长,以应对正在四处蔓延的3世纪经济危机,然而,该敕令却在事实上成为犹太人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法律来源,在犹太民族史上具有深远的政治和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罗马法中蕴涵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法律观念,具有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的价值,正如中世纪史家伯恩斯对罗马法的权威代表——《罗马民法大全》所作的评价:
“《罗马民法大全》就像《圣经》一样,乃是一个巨大的材料库,可以从中引出各种不同的原则和格言……法典通篇都一致地强调法律的道德特性,把法律看作‘善良和公正的科学’,强调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旨在赋予每一个人其应有的权力……”⑤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350年至1450年)》(上),程志敏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页。
这种立法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立法原则和理念同样贯彻在帝国处理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对犹太人相关权益的尊重和保护:尊重犹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社团生活的传统;允许犹太人遵守安息日和其他犹太节日;承认犹太法庭的存在以及维护其在特定形势下的权力;保护犹太商人的经贸活动,等等。以罗马法对犹太人经济权益的保障为例,396年,一条来自帝国东部的立法就允许犹太人为自己所售的商品预定价格。⑥Ralph W.Mathisen,“The Citizenship and 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oman Law during late Antiquity(CA. 300-540CE)”,p.40.而在政府严格把控、限制私人参与的丝绸贸易领域,帝国也对犹太丝绸商的存在报以宽容。例如,被称为“撒母耳之父”的阿巴(Abba)是一位著名学者,但也常常以商人的身份从事贸易,贸易对象正是丝绸。①Ze’ev Safrai and Aren M.Maeir,“(An Epistle Came from the West):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Ties between the Jewish Communities in the Land of Israel and Babylonia during the Talmudic Period”,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Vol.93,No.3/4(Jan.-Apr.,2003),pp.497-531,p.511.在前朝保护法令的基础上,6世纪中期的《罗马民法大全》也明确提出对犹太人公民权益的保护,如鼓励犹太商人从事各种贸易,对其贸易内容、贸易方式和价格实施保护性监管,甚至规定非犹太人不得对犹太人所售卖的商品货物讨价还价。②Andrew Sharf,Byzantine Jewry: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1,p.21.亦有法律规定,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私有财产的犹太人,一般会得到其财产损失的至少两倍赔偿。③Michael Avi-Yonah,The Jews under Roman and Byzantine Rul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lestine from the Bar Kokhba War to the Arab Conquest,Jerusalem:The Hebrew University,1984,p.248.在基督教迅速发展,与犹太教之间冲突增多的古代晚期,立法者也有意扩大对犹太群体的人身保护。塞奥多西一世就曾在393年立法保护犹太人免于攻击者的暴力袭击;塞奥多西二世上台以后,于420年重申该法令;《查士丁尼法典》中也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责任保护犹太群体不遭受基督徒和其他群体的攻击。④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p.64,86.
5世纪初,罗马法进入法典化时期,针对犹太人的保护性立法开始减少,代之以日益增多的歧视性立法和限制性禁令。随着罗马法撤销犹太人此前所享受的特权、驱除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犹太人、增加对犹太人的限制,后者的公民地位显著下降,在事实上沦为帝国的“下等”公民。尼古拉斯·兰格就曾评价道:“……犹太人二等公民的地位……确立的基础根植于……基督教皇帝的立法中,并在随后的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得到迅速发展。”⑤Nicholas De Lange,“Hebraism and Hellenism:The Case of Byzantine Jewry,”Poetics Today,Vol.19,No.1(Spring 1998),p.132.本-萨松在其《犹太民族史》中更为详细地阐明了这一观点:查士丁尼在527年上台后……5世纪开始出台的律法现在被重申,同时,加重对违反法律的犹太人的惩罚,而对犹太人财产被盗的赔偿在下降。……一些涉及保护犹太人权利以及犹太教地位的法律被删略,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歧视犹太人以及强化犹太教下等地位的新法令。⑥H.H.Ben-Sasson,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6,p.359.
多神教罗马时期的统治者曾给予犹太人众多特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免除犹太宗教领袖在市政委员会(Curiae)中任职的义务以及允许犹太族长制度(Patriarchate)的存在。由古老的区议会(Comitia Curiata)发展而来的市政委员会是罗马帝国的地方政治单位,具有管理市政,为市民提供服务的职能。多神教罗马帝国时期,政府没有硬性要求犹太人在该机构中服务,但321年后,任职于市政委员会开始作为一种义务,强加给犹太人。383年,塞奥多西一世刚上台不久,即宣布此前免除“宗教犹太人”(指犹太教拉比)在市政机构任职义务的法律无效。⑦Michael Avi-Yonah,The Jews under Roman and Byzantine Rul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lestine from the Bar Kokhba War to the Arab Conquest,p.216.399年,更进一步规定,所有犹太人都需履行该项义务。⑧Robert Bonfil ed.,Jews in Byzantium:Dialectics of Minority and Majority Cultures,Leiden:Brill,2012,p.166.
此外,犹太人丧失特权更为突出的例子体现在犹太流亡政权的消亡上。2世纪上半叶,哈德良平毁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犹太族长制作为一种流亡性质的自治政权,在组织、重建犹太社团内部的同时,代表犹太群体处理与罗马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统治者认可。《塞奥多西法典》明确保护犹太族长的权力,并规定,当犹太族长已经决定驱逐某犹太社团成员后,帝国法官不得撤销这一判决。⑨Clyde Pharr trans.,The Theodosian Cod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469,p.468.然而,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和对独一权威的强调,统治者对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犹太自治政权的存在越来越难以容忍。尤其流散各地的犹太社团普遍尊崇这一制度,并自愿向族长捐献财物或缴纳税金,该举动往往间接昭示了犹太族长吸纳财富的能力,导致后者与行省政府产生利益冲突。为转移财富的流向,罗马帝国甚至直接立法,要求犹太族长将收入上缴国库。⑩Clyde Pharr trans.,The Theodosian Cod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469,p.468.更为严重的是,425年,塞奥多西二世借时任族长迦玛列六世(GamlielⅥ,400-425年)死后无子嗣的契机,宣布不再任命新族长,在事实上废除了延续数个世纪的犹太流亡政权,犹太群体在罗马-拜占庭帝国行省制的框架内享受自治的特权宣告终结。
统治者通过罗马法逐步将犹太人驱逐出军、政、法系统同样是犹太人身份地位下降的重要体现。5世纪初,帝国军队开始驱逐服役的犹太士兵,418年,洪诺留颁布首个将犹太人全面驱逐出中央机构的法令后,到425年,行政系统和军政系统都不再接收犹太人。①Andrew Sharf,Byzantine Jewry: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p.21.527年4-7月间,查士丁尼再次重申一条禁止犹太人在公共机构中任职的法令。②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356,pp.77,371.与此同时,犹太人在涉法领域的权威也日益丧失。415年,塞奥多西二世禁止犹太族长处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案子;而《罗马民法大全》规定并重申拒绝接受犹太人针对正统基督徒所出具的证词。③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356,pp.77,371.这些禁令不仅是对犹太人的公开歧视,更是对犹太人享有和基督徒同等地位的明确否认。此类立法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对上述罗马法平等公正原则的侵蚀:即犹太人在法律层面不具备凌驾于基督徒之上的权威。④Ralph W.Mathisen,“The Citizenship and 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oman Law during late Antiquity(CA. 300-540CE)”,p.42,p.40.
古代晚期的税收制度是一个包含经济因素的政治问题。罗马帝国从公元70年开始征收犹太特殊税(fiscus Iudaicus),拟征对象为所有3-70岁之间的犹太人;第二种针对犹太人的税赋“aparchai”几乎在同时征收,并一直持续到4世纪。⑤Robert Bonfil ed.,Jews in Byzantium:Dialectics of Minority and Majority Cultures,p.156,pp.214-215.人头税也是犹太人向帝国缴纳的税种之一,自苇斯巴芗时代开始征收;后来的有关资料也表明罗马-拜占庭政府仍然对犹太人征收特殊的人头税,例如,《金皇冠》(Aurum Coronarium)中就记载有5世纪初犹太人需向国库上缴集体税的内容。⑥Robert Bonfil ed.,Jews in Byzantium:Dialectics of Minority and Majority Cultures,p.156,pp.214-215.客观而论,犹太人口规模有限,其所上缴的赋税对帝国财政的影响力并不显著,然而,剥离经济因素后,犹太税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表征,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并强化了犹太人“他者”的身份,及其作为帝国下等公民的特殊地位。
三、犹太教地位及其演变
犹太教在古代晚期拥有“合法宗教”(religio licita)的地位,该词最早由基督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50-220年)在3世纪初使用。⑦Solomon Grayzel,“The Jews and Roman Law”,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Vol.59,No.2,Oct.,1968,pp. 93-117,p.95.基督教在4世纪后期上升为国教后,该词不再用于指称犹太教,但后者的存在仍然具有合法性。事实上,罗马法对犹太教合法宗教地位的明确规定只有一条,一般认为是由塞奥多西一世在393年所公开宣称的:“犹太教不被任何律法所禁止(Jusaeorum sectam nulla lege prohibitam satis constat)”。⑧Clyde Pharr trans.,The Theodosian Code,p.468.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法律条文使用的是双重否定的特殊句型,其背后的用意因此显得意味深长。学界对这种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这表明塞奥多西是受制于此前的罗马法传统才被迫承认犹太教这一合法地位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双重否定能够起到一般否定句和肯定句所不具备的表达功能,罗马法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肯定,并进一步强调对犹太教的合法地位的认可。姑且不论统治者颁行该条法令的真正意图,它至少为犹太教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依据。不仅罗马法承认并允许犹太教以合法宗教的身份存在,早期基督教社会也很少公开否认犹太教的合法性,而是将犹太教置于基督教真理性和最终胜利的“鲜活见证”的特殊地位。⑨“见证说”(Testimonium)最早由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强调由于犹太人是弑神者而必须降低犹太人的地位,但他们也是基督教的“真理见证者”,因此要予以适当保护。
得益于罗马法传统的延续以及基督教“见证说”的传衍,犹太教在很多方面受到帝国保护,如犹太社团可以建造会堂,守安息日,庆祝自己的节日,延续割礼传统等。继4世纪初罗马法对犹太人各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后,412年,西部法律重申犹太人可以按自己的习俗生活的权利,并规定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官方休息日,允许犹太人在安息日不被强行召集参加任何公共或私人的诉讼会议。⑩Ralph W.Mathisen,“The Citizenship and Legal Status of Jews in Roman Law during late Antiquity(CA. 300-540CE)”,p.42,p.40.同样是在5世纪初,塞奥多西二世也公开立法保护犹太教会堂,并承认犹太人的宗教节日。此后,《查士丁尼法典》沿用《塞奥多西法典》中的规定,宣布犹太会堂是合法的祈祷场所,保护其免受暴力和亵渎的破坏,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查士丁尼也始终承认犹太教存在和犹太人按照传统进行宗教实践的合法性。①Catherine Brewer,“The Status of the Jews in Roman Legislation:The Reign of Justinian 527-565 CE”,European Judaism,Volume 38,No.2,Autumn 2005,pp.127-139,p.135.
在保护犹太教的同时,罗马法对犹太教的规定中体现更多的是隔离和限制。罗马法本身并无特别限制不同种族间接触和融合的传统,阻止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交往的力量主要来自基督教会。强调两大宗教间的差异、推行两教隔离的思想则主要受到基督教父的影响,早期神学家在护教过程中树立了犹太人有罪的负面形象。例如,奥利金(Origen)就曾指出:“……犹太人……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阴谋杀害了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尼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更是对犹太人痛加斥责,称他们“谋害上帝,暗杀先知,是憎恨上帝的反叛者……魔鬼的同伙和耳目,毒蛇的同类,世界上所有美好事物的敌人”。②Leon Poliakov,History of Anti-semitism,New York:Schocken,1974,pp.23-25.圣奥古斯丁也在《反犹太人》一书中对犹太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正是基于犹太人不可饶恕的罪责和自身的恶劣品性,基督教始终反对两教接触,并试图在各个领域推行隔离政策,如,禁止所有基督徒与犹太人一起斋戒、庆祝节日,接受犹太人的礼物;禁止基督徒给多神教神殿或犹太教会堂供应膏油,或在犹太人的宗教节日点油灯。随着基督教化进程的发展,教会推行更加广泛的社会隔离,如691年召开的基督教五六次大公会议(Quinisext Council)就规定:基督徒不可与犹太人接触、联系,不可在生病时找他们,不可吃他们开的药,也不可与他们共浴……。③Robert Bonfil ed.,Jews in Byzantium:Dialectics of Minority and Majority Cultures,p.200.此外,禁止与基督徒通婚也是犹太人遭遇歧视和限制的重要内容。多神教罗马皇帝并不反对通婚,但基督教化皇帝则认为基督徒与犹太人的通婚等同于通奸,理应受严厉惩罚。早在388年,塞奥多西一世就颁令禁止基督徒与犹太人通婚,428年的一条法令也规定罗马人的婚姻应该发生在“两个地位平等的人之间”,④Clyde Pharr trans.,The Theodosian Code,p.70.这种平等不仅涵盖物质经济、权势地位等一般性条件,更重要的是应达到宗教信仰的一致。
不仅如此,罗马法还通过控制犹太教会堂和犹太教信众的规模达到剥蚀犹太教合法地位和削弱犹太教影响力的目的。犹太教遭遇生存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犹太会堂的存在危机。第二圣殿毁灭后,会堂在犹太社团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罗马民法大全》中却规定不能兴建新的犹太会堂,而对原有的会堂进行维护和修缮也不合法,假如犹太社团成员执意冒险兴建和维修,会堂建筑就会被充公为教堂并辅以罚款。有资料显示,530-531年,外约旦(Transjordan)地区的格拉萨(Gerasa)会堂曾被改建成基督教堂。⑤Nicholas De Lange,“Jews in the Age of Justinian,”in Michael Maas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401-426,p.406.545年,查士丁尼颁布一条新法令,禁止犹太会堂占用基督教会机构的用地,⑥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p.398-402.为基督教变相挤占犹太教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削弱犹太教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减少犹太教徒的规模和扩大基督徒的数量上,而改宗历来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限制基督徒和多神教徒皈依犹太教。基督徒改宗犹太教,被视为“比死亡更让人悲哀,比谋杀更残忍”,堕入犹太之道的基督徒也就此背负对罗马帝国的叛国罪。基督教会与教父都力图以各种方式阻止基督教徒改宗犹太教。其二,吸引犹太教徒改宗基督教,同时保护改宗为基督教徒的犹太人不受犹太教徒的攻击。鼓励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被基督徒视为神圣的职责,早期传教士不遗余力推动犹太人改宗,且成效显著。根据学者推测,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4世纪末期,数量增长到50%;5世纪晚期则达到90%。⑦西里尔·曼戈主编:《牛津拜占庭史》,第154页。对于改宗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基督教立法者也颁布相关法令,保护这一改宗群体。
古代晚期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仍然是以奴隶占有作为生产关系主导要素的社会。罗马法继续承认奴隶制,但是规定教俗各界应释放奴隶,改善奴隶的地位,奴隶不再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不具有法律地位的“人”。对异教徒持有、买卖、迫害基督徒奴隶的规定最早可追溯至君士坦丁于329年颁布的法令。①涉及基督徒奴隶的法令众多,参见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p.82-84.此后,罗马法中普遍禁止犹太人拥有基督徒奴隶,君士坦丁的这一法令分别在335年、339年、384年、415年以不同形式和说法出现;《塞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的第9章甚至直接以“禁止犹太人持有基督徒奴隶”为标题,其下的5个条目全部是涉及这一问题的详细规定;②Clyde Pharr trans.,The Theodosian Code,pp.470-471.查士丁尼上台后又曾在法典中两次加以重申。在禁止持有基督徒奴隶外,有关法令还要求无条件释放改宗基督教的非犹太奴隶,且不对犹太奴隶主进行任何补偿,即使犹太主人自己改宗基督教后也无权再追回已释奴。534年,查士丁尼还进一步强调各地的基督教主教和世俗官员有责任保护犹太奴隶主所拥有的基督徒奴隶的权益。罗马法如此频繁地限制犹太奴隶主的所有权,显然是认为犹太人不具有超越基督徒的法律权威,而从宗教角度出发,这种规定也顺应了基督教化进程中降低犹太教地位的要求。
正是基于罗马法日益限制犹太教生存发展权的事实,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自巴尔·科赫巴起义后犹太人享有宗教自由提出质疑。③具体的质疑性观点参见Solomon Grayzel,“The Jews and Roman Law”,p.94.基督教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很快剥蚀了犹太教享受罗马法保护的基础,动摇了其作为合法宗教的地位。尤其在7世纪上半叶的近东危机期间,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强制要求帝国境内所有犹太人接受洗礼,改宗为基督徒,在事实上推翻了犹太教存在的合法性。至此,犹太教在中古早期作为“religio licita”的地位在形式上荡然无存。
四、结语
古代晚期完成法典化过程的罗马法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规范体系,从中既可以看到罗马法的基本原则,也能发现基督教会法规和神学政治的存在。罗马法本质上是一种人意法而非神意法,是世俗法而非宗教法,因而通常扮演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监护人”,基于其公平正义的立法原则和传统对后者予以保护。此外,帝国的政治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都离不开犹太人自身所具有超越周围民族的政治管理才能、法律智慧以及经济实力,对主流社会的这种有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犹太人的相关权益。另一方面,基督教在4世纪上升为罗马国教后开始限制、排挤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犹太人,要求后者让位于基督教权威,保持低层次的社会参与。如查士丁尼535年收复北非地区后曾出台法令,规定犹太人和异教徒只要满足于“还活着”就够了。④Amnon Linder,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lation,p.66.尽管犹太教的生存发展权遭遇限制,但罗马法中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在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宗教反犹和20世纪的种族反犹主义,其出发点更多的是通过贬低犹太人的存在价值来抬高正统基督徒的身份和地位,通过削弱犹太教势力为基督教提供发展空间。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尽管罗马法是帝国实行政府管理、调整社会关系的律法工具,但总体而言,古代晚期的皇权对罗马法的实践效率是有限的,不仅存在诏令、条例在下达过程中因官员渎职而失去效力的情况,有些法律法规的适用性也会由于具体行省的差异而受到影响,正因如此,不少涉及犹太人的隔离、限制法令很难付诸实施。如哈德良将犹太人逐出耶路撒冷后,后者仍然可以通过贿赂官员前往圣殿旧址。又如据考古资料表明,在查士丁尼禁止建造犹太教会堂的区域,到6世纪末仍然有新会堂出现。⑤Catherine Brewer,“The Status of the Jews in Roman Legislation:The Reign of Justinian 527-565CE”,p.131.这些史例有力地证实了,虽然古代晚期基督教世界犹太人的法律地位普遍开始下降,但犹太社团的整体生存状况并未显著恶化:社团内部组织有序;《塔木德》编纂完成,宗教文化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对外社会、经济交往密切;与基督徒民众和政府之间频繁互动。简言之,罗马法为犹太群体设置了众多限制性规范,但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犹太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责任编辑:孟钟捷)
疏会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