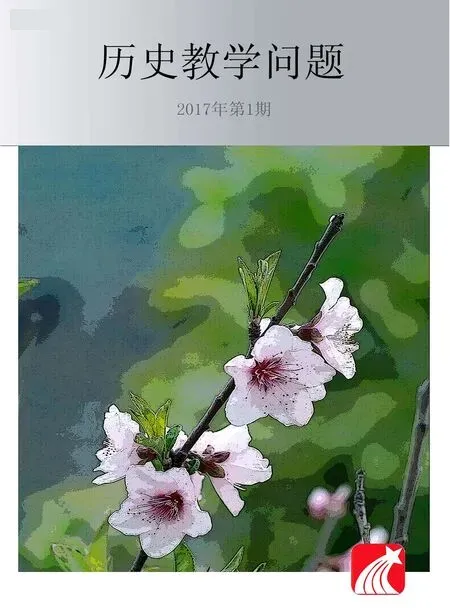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是否关乎“拯救文明”?
2017-03-12王三义
王三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是否关乎“拯救文明”?
王三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战争,由于英国诗人拜伦的热心援助和亲临希腊,变成一个醒目的事件。事实上,希腊人寻求独立一事,恰恰抓住了奥斯曼帝国衰弱的大好时机;独立战争的胜利,并非由于希腊起义军的强大,而是欧洲大国直接干预的结果。英、法、俄三国派军打败奥斯曼政府和埃及的军队,其出发点是各自的利益盘算,而非“与希腊人的文化情感”,更与拜伦之援助不是一回事。欧洲大国“帮助”希腊人脱离奥斯曼帝国一事,实质并不关乎“拯救文明”。
希腊;奥斯曼帝国;独立战争;“拯救文明”
希腊独立是19世纪国际政治的大事件。从革命史的角度,人们一般称之为“希腊独立运动”、“希腊民族解放斗争”或“希腊革命”,视之为奥斯曼帝国境内少数民族成功脱离帝国的样板。希腊人要求独立并于1821年掀起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本来与英国诗人拜伦(Lord George Gordon Byron)没有直接关系,但拜伦满怀热情地声援希腊起义军。支持希腊独立的英国人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集了一笔援助款,拜伦带着这些援助款去了希腊前线。此时希腊起义军势单力薄,渴望得到“欧洲同胞”的帮助。拜伦亲赴硝烟弥漫的希腊,这一举动的意义,超出拜伦从伦敦带来的援助款之价值。拜伦到希腊不久便因劳碌并感风寒而病倒了。1824年4月,他在迈索隆吉翁城病逝。这位诗人虽未扛枪上阵,但确实如后来的“拜伦简历”中所说,“为希腊独立献出了宝贵生命”。拜伦热心支持希腊独立这件事,后来得到反复阐释。一个基本的论调是:欧洲文明有着共同源头(古希腊文明),欧洲人从感情上与希腊人是“亲近”的,拜伦援助希腊,正体现了这种文化与情感上的“联系”。由此,论者引申为:以拜伦为代表的英国人支援希腊独立运动,是“文明同源”的欧洲人帮助同胞摆脱土耳其人野蛮落后统治之举。
事情是不是这样呢?这牵涉到欧洲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问题似乎变得复杂了。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看法呈现两个极端:要么认为土耳其人会带来威胁,甚至恐怖;要么认为土耳其人是“欧洲病夫”。典型著作如阿斯里·西拉克曼《从“世界的恐怖”到“欧洲病夫”:16-19世纪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及其社会的观念》,①Asli Cirakman,From the“Terror of the World”to the“Sick Man of Europe”:European Images of Ottoman Empire and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02.查理·斯瓦洛《欧洲病夫——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1789-1923年》。②Charles Swallow,The Sick Man of Europe,The Ottoman Empire to Turkish Republic:1789—1923,London:Ernest Benn Limited,1973.至于讨论拜伦援助希腊体现了欧洲国家之间文化及情感联系的书籍,不仅有希腊史著作,例如约翰·马弗罗戈达托《现代希腊史,1800-1931年》、③John Mavrogordato,Modern Greece,A Chronicle and A Survey,1800-1931,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31.理查·克罗格《现代希腊简史》、④Richard Clogg,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约翰·克里奥珀罗斯《现代希腊:1821年以来的历史》、①John S.Koliopoulos,Modern Greece,A History since 1821,Oxford:Wiley-Blackwell,2010.p.16.托拉斯·加兰特《现代希腊》等,②Thomas W.Gallant,Modern Greece,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6.还有不胜枚举的文学作品。欧洲人不吝笔墨地为这件事添枝加叶,以至于留给后世读者的印象实质与史实不符。
其实,只要弄清楚两个层面的问题,就足以揭示真相:第一,希腊人要摆脱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为什么不迟不早,非要等到19世纪20年代初?第二,英、法、俄为什么要帮助希腊而打击奥斯曼帝国?与“文化情感”究竟有没有关系?客观而言,英、法、俄三国出兵并打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联军,帮助希腊人摆脱了土耳其人统治,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就包含着丰富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一、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理由
既然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理由应该是希腊人遭受了异族土耳其人的压迫。现代希腊史也如此描述:希腊人在政治上没有获得与土耳其人平等的地位;希腊商人和作坊主、船主既要向奥斯曼政府缴纳赋税,也遭受地方管理者的敲诈勒索,生命和财产并无保障;在希腊农村,人均土地少,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农民占有耕地极少,生活艰难。
然而事实上,在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中,希腊人的地位相对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希腊人信仰东正教,土耳其人征服后并未强迫希腊人改宗伊斯兰教。在“米勒特”制下,每个宗教社团或米勒特享有文化和法律上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作为管理内部事务的自治体,每个米勒特选择自己的领袖,得到素丹的认可和祝福。素丹要保护这些基督教和犹太教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这些臣民有义务向奥斯曼政府交纳人头税,而不必服兵役。③Mehrdad Kia,Daily Life in the Ottoman Empire,Oxford:The Greenwood Press,2011,pp.111-112.希腊东正教的主教不仅负责希腊东正教徒的事务,还取代保加利亚主教、塞尔维亚等巴尔干民族的教会的主教,代替他们行使米勒特制度下的总负责人之职权。希腊的高级教士和世俗社区领导人的社会地位较高,甚至拥有较大的权力。
从经济方面来说,17至18世纪希腊本土的手工业发展较快,制造业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希腊产品行销于奥斯曼帝国各地,也远销国外。希腊商人利用他们在航海方面的优势,支配着奥斯曼帝国的海洋运输和贸易。在帝国的许多港口城镇,商业交易由希腊代理人控制。④Res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p.28,p.28.一些希腊人经商、当船主,不仅与威尼斯等商业城市有联系,也在俄国、奥地利、法国有自己的商站。在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等城市的制造业中,希腊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主导作用。⑤John Mavrogordato,Modern Greece,A Chronicle and A Survey,1800-1931,p.1.此外,伊斯坦布尔的银行家主要是希腊人。一部分希腊人进入政府,从事外交工作或管理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很多富裕的希腊商人定居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萨洛尼卡等大城市,过着优裕的生活。希腊人还支配着东正教主教的职位。⑥Res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p.28,p.28.在米勒特制下,希腊人在教育、文化方面也有一定自由,他们保留着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传统,与西欧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也未中断。客观地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生活稳定。
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理由,更多是观念上的。比如,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不是同一个民族,没理由长期被土耳其人统治;土耳其统治者给希腊臣民增加了不少义务,却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希腊当年是土耳其人用武力征服的,希腊人与土耳其人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土耳其人是占据欧洲土地的外来者,他们应当放弃这些欧洲领土;希腊人有权利重返继承古典希腊遗产的欧洲民族大家庭”。⑦John S.Koliopoulos,Modern Greece,A History since 1821,Oxford:Wiley-Blackwell,2010.p.16.
换言之,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不满,并非经受了比其他民族更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真实的情况是,希腊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认为他们应当独立,而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生活是“不正常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革命的观念,自由、平等思想,通过信件、演讲等方式在全希腊传播。一部分希腊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改变生存状态。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希腊人看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可能性。在希腊人知识分子中,阿达莫提奥·科莱斯(Adamantios Koraes)、布尔加莱(Boulga rê s)等人在希腊地区颇有影响力。尤其科莱斯,他是一位学者、政治思想家,致力于复兴希腊语言,出版古典希腊著作等活动,也对建立希腊国家充满渴望。科莱斯提出了发展希腊教育、制定宪法、建立代议制政府等主张。①John Mavrogordato,Modern Greece,A Chronicle and A Survey,1800-1931,pp.8-11,p.19.希腊地区建立的组织,多数是文化团体。“友谊社”(1814年)便是第一个明确追求政治目标的组织。它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来推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解放祖国”的愿望。但“友谊社”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成分复杂,有商人、医生、教师、律师、学生、行省贵族、教士等;握有武器的人也是以匪帮为主,还有为数不多的农民和手工艺人。②Richard Clogg,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p.49,p.52.可以说,希腊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到19世纪初民族主义形成一股力量,但这股力量还不强大。
希腊人的反抗活动始于1821年3月。先是秘密团体“友谊社”成员发动起义,领导人是亚历山大·伊普昔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当时只有一支大约5000人(一说4500人)的起义军,号称“神圣军团”,完全没有战斗经验。③Nicholas Doumanis,A History of Greece,London:Plagrave Macmillan,2010,p.171.首次起义没有得到当地民众支持,归附者不多,很快就遭遇到奥斯曼军队的镇压(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伊普昔兰提斯逃往奥地利控制的地区,被捕,死于1828年)。④Richard Clogg,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p.49,p.52.这年4月,其他政治团体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者在佩特雷城的圣乔治广场宣誓,成立“革命指挥部”。此后两个多月里,有一些城市响应。1822年1月27日,起义者在埃皮达罗斯(Epidauros)召开了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不久,宪法公布,人们选举亚历山大·马弗罗戈达托为总统,但这位“总统”在希腊没有多少威信,仅仅在希腊西部的阿卡纳尼亚有一些影响力。⑤John Mavrogordato,Modern Greece,A Chronicle and A Survey,1800-1931,pp.8-11,p.19.起义军在取得一些胜利后,内部出现分裂。不过奥斯曼帝国的旧军队战斗力也不强,希腊起义军控制的范围才逐步扩大。奥斯曼素丹求助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825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率军队进攻希腊,很快攻占大片希腊土地。希腊起义军无法抵挡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军队,到1826年夏,“革命之火几乎被扑灭”。在此情况下,希腊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求助于欧洲大国。
二、希腊独立运动的时机选择
希腊人之所以要起来反抗,就是看到奥斯曼帝国政治腐败,地方势力形成割据。
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内部腐败,表现在多方面:首先,素丹软弱昏聩,执政能力低下。17-18世纪的众多素丹中,有的沉湎酒色,有的生性懦弱,有的甚至精神失常。这些素质不高、能力不济而又贪图享乐的人物“君临天下”,还要给穆斯林臣民树立榜样(素丹也是哈里发),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政治腐败,纲纪废弛。当最高统治者软弱、昏聩、腐化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各种机构的大小官员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甚至卖官鬻爵,出现严重腐败。上层腐败很快蔓延到整个帝国统治阶级,宫廷阴谋和帝国政治腐败层出不穷,造成政治不稳定。民族和宗教矛盾引发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使得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一般通史都介绍过奥斯曼素丹的暴政和多次宫廷政变。
在大帝国的管理中,常见问题是17-18世纪地方割据势力逐步形成和壮大。巴尔干领土上的一些王公、总督和地方官员不再忠于素丹,而转变为独立或半独立的最高长官。西亚、北非地区的封建主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有不少成为独立、半独立的王国。⑥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4-47.到18世纪后期,北非、巴尔干半岛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奥斯曼政府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很微弱,有些地方首领只是名义上服从朝廷权威而已。埃及、两河流域由当地马穆路克封建主所控制,北非马格里布属地事实上已经独立。
希腊人看到,奥斯曼帝国四分五裂,此时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确实是有利的时机。关键是,善于打仗的土耳其人已经没有战斗力了,17-18世纪政治腐败也渗透到军队中,从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军官晋升,到征兵制度、军事训练,整体出现严重问题。帝国的军队从保家卫国、忠于素丹的力量,蜕变成危害国家安全、挟持素丹的力量。加尼沙里军队管理混乱,战斗力极差,远不是欧洲军队的对手,以致屡次败于俄国、奥地利和威尼斯军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看来,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武器不先进、军队战斗力不强,所以他们致力于缩减封建军队,通过引进现代火炮,进行欧式训练等办法,来改革军队、提高战斗力,如塞利姆三世改革“加尼沙里军”和“西帕希”骑兵,同时建立“新正规军”,在士兵选拔和培训、军官任用和考核、军队组织和管理的制度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还建立军事学校以培养人才。但塞利姆三世被废黜,军事改革的成果有限。马哈茂德二世担心军队叛乱,不敢把改革延伸到军事领域。正因如此,尽管希腊起义力量分散,但起义军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奥斯曼帝国正规军——他们就是那些加尼沙里为主的旧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正好帝国境内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反抗活动,素丹分兵平叛,顾此失彼。
希腊起义军第一次选择的时机,恰好是爱奥尼亚的阿利帕夏掀起反对马哈茂德二世素丹的“叛乱”。阿利帕夏巧妙地玩弄强权政治的把戏,镇压了所有反对派,巩固了他对希腊大陆的统治。由于阿利帕夏暴露了自己的野心,1820年马哈茂德二世决定派兵打击,这才给亚历山大·伊普昔兰提斯领导的“友谊社”成员提供了发动起义的机会。“友谊社”成员与阿利帕夏建立联系,后者与希腊其他武装力量也表示联合。他们的计划是,当奥斯曼政府大军压向爱奥尼亚时,基督教徒在三个地区同时起义策应:一是多瑙河的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二是首都伊斯坦布尔,三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可惜,这些计划不切实际,大都落空了。阿利帕夏不堪一击,在1821年3月中旬就被奥斯曼政府军打败了;伊斯坦布尔起义没有实现;作为这次起义主力军的多瑙河公国也没有得到俄国支持。①Thomas W.Gallant,Modern Greece,p.18.最后还是希腊地区的起义军独立面对奥斯曼帝国大军。在政治上,希腊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位是在全希腊拥有广泛权威的。可见,发动起义的时机是好的,可条件并不成熟,准备也不充分,到1826-1827年,起义军已接近被镇压的边缘。
三、希腊独立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希腊独立战争在欧洲大国帮助下获胜”——在后来的史书中,人们总是从“结果”出发来讲述这一事件。其实,欧洲大国在希腊起义发生后并没有很快关注并准备干预。有些学者说,“欧洲人似乎把希腊人的行动看作是对奥斯曼素丹的反叛,欧洲人对希腊起义不抱任何同情”。②John Mavrogordato,Modern Greece,A Chronicle and A Survey,1800-1931,p.15.这种情况不符合实际。有的学者说,欧洲政治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支持希腊解放斗争,这也与事实不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希腊闹独立,给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出了难题。如果听任希腊革命之火蔓延,有可能引发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如果不支持希腊起义,等于放弃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权或扩展势力的机会。在希腊起义的过程中,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保持观望状态。英国和法国一开始并未重视,也未表示支持希腊的独立运动,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好应该如何做。所以,一开始“关注”希腊起义的只有俄国。
鼓励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本是俄国的策略,而希腊人也曾经把脱离土耳其人统治的愿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然而,希腊起义之初,俄国非但没有表示支持,反而同奥地利、普鲁士一样,从“正统主义”出发来谴责希腊人的起义之举。俄国担心刚刚恢复的正统秩序受到破坏,因此反对任何起义或分离活动。当然,俄国绝不会对希腊起义这一事件视而不见,这毕竟也是削弱奥斯曼帝国的机会。在起义发生的第二个月,奥斯曼帝国军队镇压和屠杀基督教徒,俄国便迅速做出反应,申明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同时希望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
俄国人有行动,英国也不会坐视不管。英国国内确实有不少人同情希腊革命,同情者不仅捐资,甚至奔赴希腊参加战斗。诗人拜伦前往希腊,就是被文学家所反复渲染的事件。有资料显示,英国可能向希腊起义者提供过经济援助,暗中支持过希腊起义军。但是,英国政治家未必真的对希腊起义抱同情态度。1823年3月25日,英国外交官把希腊和土耳其称为“交战双方”,这是把希腊当作一个与奥斯曼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法国最后和英国一起出兵了,但法国政治家的动机则是复杂而隐蔽的。法国不希望埃及力量壮大,其出兵目标是打压埃及,而不是帮助希腊人。当然,法国也不想破坏与奥斯曼政府的“良好关系”。由此可见,英、法、俄三个欧洲大国的政治家们在是否出兵帮助希腊起义军的问题上,颇费思虑。
1824年1月,俄国提出一个解决希腊问题的方案,其要点是:把希腊地区分为三个公国,东部希腊由色萨利、维奥提亚和阿提卡组成,西部希腊由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组成,南部希腊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组成。③J.M.Wagstaff,Greece: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1820-1994,Atlas and Documents,London:Archive Editions,2002, pp.55-56.三个希腊公国继续向奥斯曼政府纳贡,但奥斯曼素丹不能干涉希腊公国的内政;希腊人则有权使用自己的国旗,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奥斯曼政府限制。这个秘密方案在5月份向外界透露后,奥斯曼政府和希腊起义者都提出了强烈抗议。1826年4月,英俄两国签订了《彼得堡议定书》。在议定书中,英国支持希腊自治,但希腊仍应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向奥斯曼政府纳税,并由素丹任命自治领导人。①Thomas W.Gallant,Modern Greece,p.25,p.26,p.28.这一“调解”方案,旨在让希腊变成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国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不赞成这项协定草案。他认为希腊要么完全独立,要么完全屈服,不应该有这样一种折中方案。②John Mavrogordato,Modern Greece,A Chronicle and A Survey,1800-1931,p.22.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军队此时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拒不同意给予希腊自治权。就在欧洲列强各怀自己的盘算在谈判桌前商量对策的几年里,希腊人与奥斯曼政府军及埃及军队的战争艰苦卓绝,被围困的城市弹尽粮绝,希腊独立运动明显陷入困境,一部分起义者转入游击战。以1827年夏季的形势看,希腊起义眼看就要失败了。
正在此时,欧洲大国终于采取了行动。法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不愿看到英俄联合控制黎凡特地区),于1827年7月6日与英、俄一起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该条约敦促停战,使1826年的议定书生效,并承诺由欧洲强国保护希腊,并派遣联合舰队维护和平。③Thomas W.Gallant,Modern Greece,p.25,p.26,p.28.条约还提出希腊和土耳其两个民族分离的原则与“和解”的方式。8月16日,《伦敦条约》送往奥斯曼政府,这等同于英、法、俄三国向奥斯曼政府发出通牒。结果,素丹拒绝停战。9月初,英、法、俄三国正式出兵,切断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联军的运输线。10月20日,英、法、俄的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战役中,打败了奥斯曼政府的军队和埃及的海军舰队。奥、埃海军共64艘舰艇参战,至少29艘被击沉,损失惨重。纳瓦力诺战役之后,埃及军队撤离,法国军队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俄国军队跨过多瑙河,挺进奥斯曼帝国领土。
1828年4月26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经过一年多的交战,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俄国军队直逼伊斯坦布尔。英法两国不愿看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被俄国占领,也不愿看到希腊被置于俄国沙皇的保护之下,于是急忙采取行动,阻止俄军前进,并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希腊事务”。7月2日,英、法、俄在伦敦召开会议,就希腊领土边界等问题进行了实质性协商。④J.M.Wagstaff,Greece: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1820-1994,Atlas and Documents,p.66.8月,俄国军队移师奥斯曼帝国首都附近。奥斯曼政府被迫求和。9月14日,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埃迪尔纳条约》。根据条约,希腊取得独立,但在10年内每年向奥斯曼政府缴纳150万金币的贡赋;条约还划定了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线。
就在奥斯曼军队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处于劣势时,希腊军队乘机反攻。1829年5月14日,希腊人收复了迈索隆吉翁,9月,希腊军队大败奥斯曼帝国军队。至1831年1月,奥斯曼帝国军队撤出北希腊。希腊独立战争至此取得胜利。
不过,建立希腊国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根据1830年2月3日英、法、俄签订的《伦敦议定书》,希腊完全取得独立,4月奥斯曼政府接受这份议定书。⑤Sina Akᶊin,Dexter H.Mursaloslu,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London:Hurst&Company, 2000,pp.24-25.《伦敦议定书》规定:“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政治、行政管理、贸易等方面享有完全独立的权利。”然而,希腊正式独立后局势不稳。1831年10月9日,总统卡普迪斯特里被暗杀。英、法、俄三国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为希腊君主,却引发希腊局势的波动,利奥波德不久遇刺身亡。1832年5月7日,英、法、俄三国与巴伐利亚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选择巴伐利亚的奥托亲王接受希腊王位。奥托于1832年成为希腊统治者,称奥托一世(1832-1862年在位)。换言之,《埃迪尔纳条约》、《伦敦议定书》、《君士坦丁堡协定》共同确立了希腊在列强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地位。1829-1832年的几个条约(或协定)划定了希腊边界,建立希腊政府。⑥Thomas W.Gallant,Modern Greece,p.25,p.26,p.28.
事实表明,希腊人仅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取得武装斗争胜利,欧洲大国的干涉和插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有了一个常见的说法:“在英、法、俄等国的帮助下最终建立了希腊王国”。由此,希腊政治成为欧洲政治的一部分。希腊王国的君主是巴伐利亚人,法国人充当希腊的军事顾问,英国人指导希腊政府的管理。卡普迪斯特里感叹:“希腊的命运掌握在上帝和欧洲大国的手里。”希腊政治实际上成为欧洲政治的一部分,但它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领土和边界纠葛直到奥斯曼帝国瓦解都未曾得到完全解决。
显然,希腊的独立是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大国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开端。乘希腊独立运动之机,俄国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并获得很大利益,强化了它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海峡的优势,并由此加剧了它与英、法、奥地利等国的矛盾。40多年之后,欧洲强国围绕“近东危机”的斗争,比这一次更为激烈,矛盾更为错综复杂。干预希腊问题成为欧洲大国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成功范例”,以至于后来巴尔干半岛上寻求独立的民族,欧洲大国总要主动加以“担保”或“保护”。①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by G á bor á goston,Bruce Nasters,Facts on File,New York,2009,p.242.支持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之举,实质表明欧洲大国在近东的争夺升温。巴尔干地区从此成为大国争夺的场所,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也逐步加剧。
四、结论
以上分析可知,希腊人寻求独立是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文化、教育等行业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不低。土耳其人没有摧毁希腊宗教和文化,也没有压迫和剥削希腊人。正因如此,希腊人寻求独立,不存在摆脱“野蛮统治”的问题,也不存在希腊所承载之文明亟待“拯救”的问题。希腊人在19世纪20年代要求独立,一是受法国自由、平等思想和革命观念的影响,二是看准了时机。希腊人的胜利来之不易,现代希腊史颂扬希腊人民在独立运动中的英勇精神,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胜利从根本上而言只能算特殊情况下的“侥幸取胜”。
历史事实是清楚的:英、法、俄三国派军攻打奥斯曼政府和埃及的军队,并不是出于“与希腊人的文化情感”,和拜伦的援助也不是一回事。英国和其他大国出兵帮助希腊,实则出于各自利益的盘算。换个角度而言,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英国人把全世界当作自己表演的舞台。出兵打击奥斯曼政府和埃及舰队,只能算是英国对外战争中的小插曲,不值得大惊小怪。法国和俄国把东地中海当作争夺目标,奥斯曼帝国的每次战争,几乎都有法国人和俄国人的身影,他们打击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军队(客观上帮助了希腊起义军),也不关乎“文化情感”。“希腊反抗土耳其”之所以引起西方人的兴趣,是因为“好事者”容易把“土耳其人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和“欧洲文明失落”联系起来;与此相应,“欧洲大国帮助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似乎从逻辑上就成了“拯救欧洲文明”了。这属于文学意义上的联想,与历史事实存在着较大差距,我们不必当真。
(责任编辑:孟钟捷)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