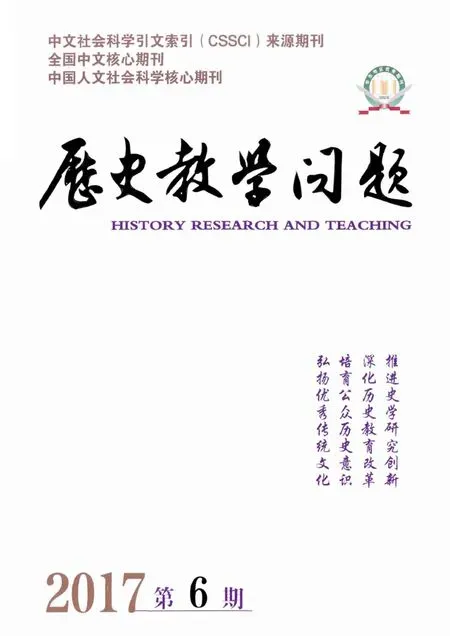日本江户古学派的“尊孟”与“非孟”论
2017-03-12董灏智
董灏智
虽然确切时间仍有争议,但据考证,《孟子》至少在公元9世纪时已传入日本。因为,在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孟子》赫然在内。然而,《孟子》在日本的流行却是在江户时代,这与朱子学的盛行有着重要的关联。但不久,江户古学派率先对朱子学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其中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古学思想最具代表性。重要的是,仁斋与徂徕虽对朱子学皆持批判态度,但对于朱子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孟子及《孟子》一书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前者极为推崇,后者则极力批判。同为古学派学者,为何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观点?透过古学派的“尊孟”与“非孟”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域外的《孟子》诠释特色。
一、伊藤仁斋的“尊孟”论
作为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形成与对朱子学的“反动”有着密切关联。他围绕着中国舶来的朱子学,先后发生过“崇朱”“疑朱”和“反朱”的学问取向,最终转向了古学。①董灏智:《伊藤仁斋的古学思想形成脉络探析》,《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3期。重要的是,无论是在“问道朱子学”期间,还是转向古学期间,孟子和《孟子》一书在仁斋视域内都占有着重要位置。
在仁斋的“道统论”中,孔子与孟子被提升至无以复加的地位,而对于语孟二书,他更视为“天下万书”的准绳与标尺。同时,他还将二者置于“六经”之上,认为:“语孟犹设权衡尺度,以待天下之轻重长短也。六经犹画也,语孟犹画法也。知画法而后可通画理,不知画法而能晓画理者,未之有也……故通语孟二书,而后可以读六经,否则虽读六经,茫无津涯,琐琐训诂,不足以发明六经也。”②伊藤仁斋:《语孟字义·总论四经》,收入《伊藤仁斋·伊藤东涯》(日本思想大系33),岩波书店,1971年,第160页。所以说,《孟子》在仁斋的学术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斋将其与《论语》视为一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语孟体系”。
回顾仁斋的学术历程,自36岁“开悟”以后,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重新注解《孟子》,几经反复,才完成对《孟子》的新解,可见对《孟子》用功力度非凡。关键是,仁斋对《孟子》认识不同于中国儒者。宋儒最为看重的“心性论”,在仁斋的视域之内却并非重点,他认为宋儒的说法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实是以佛老之学曲解圣人之作。一般认为,“性善论”是《孟子》的重要内容,经宋儒的发挥,更是重中之重。但是,仁斋却特别指出“性善论”并非《孟子》的核心。他在《语孟字义·性》中专门批判了宋儒的“性二元论”,并反复强调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万世论“性”之根本准则,孟子以孔子为宗,二者应无太大区别,但宋儒却以孟子之说为“本然之性”,孔子的言论为“气质之性”,将二者割裂开来。对此,仁斋解释道:“盖孟子之学,本无未发已发之说……孟子所谓性善者,即与夫子性相近之旨无异,益彰彰矣。”①伊藤仁斋:《语孟字义·性》,第134-135页。这意味着,宋儒所提的“性二元论”违背了孟子之学的本旨,至于《孟子》中“性善论”,仁斋论道:“孟子之时,世衰道微,而功利之说,沦入骨髓。不唯不知仁义之为美,而自视甚卑,以为不能行仁义,故特倡性善之说,亦必称尧舜以实之,而曰道一而已矣。”②伊藤仁斋:《孟子古义》,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孟子部一),东京:东洋图书刊行会,1926年,第96页。同时,仁斋更进一步说道:“孟子之学,以仁义为其宗旨,而又倡性善之说者,盖为自暴自弃者而发,明己性之可以行仁义也。自暴其身者,礼义不足行,自弃其身者,仁义不能行,此天下之通患也……故性善之论,专为自暴自弃者而发,非徒论其理也。”③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149页,第2-3页,第68页,第7页,第69页。也就是说,孟子之世,邪说暴行充斥天下,十人十意,不知仁义为人道之极,故孟子提出“性善”之说是为那些不知人人皆可行仁义之德的人所发,进而指出扩充仁义之德的必要性。
那么,在仁斋的古学视域内,《孟子》的核心是什么?在《孟子古义·叙由》中,仁斋反复陈述“孟子之学”的核心为“仁义”与“王道”:“以仁义为本,而王道为要”,“以王道为主,以仁义为宗”,“以仁义为宗,以王道为主”。④伊藤仁斋:《孟子古义·叙由》,第1-3页。在《孟子古义》的开篇,仁斋言道:“仁义二字,乃王道之体要,而七篇之旨,皆莫不自此绎焉……所以孟子为惠王发之,以此章为一书之首,有旨哉。”⑤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149页,第2-3页,第68页,第7页,第69页。显然,“求仁义”是“行王道”的前提与关键。在孟子生活的那个众人言“利”的战国时代,梁惠王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则以“仁义”对之,劝君王由“仁义”而行“王道”,即由“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斋完全赞同孟子的说法,说道:“不忍人之政,即所谓仁政是也。有不忍人之心,而无不忍人之政,谓之徒善,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虽治天下,亦无难为者矣。运掌上,谓甚易也。”⑥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149页,第2-3页,第68页,第7页,第69页。从中可知,仁斋的认识与孟子的“王道论”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对君主而言,仅有“不忍人之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在于能否“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孟子·梁惠王》篇中的大部分内容不离“推行王道”的措施。其中,仁斋与孟子相似,极为推崇“与民偕乐”“崇尚节俭”“制民之产”等内容,认为能否实行这些措施恰是验证君王是否推行“王道”的关键。尤其是《梁惠王》中规划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等“制民之产”的措施,仁斋更视其间包含了“王道之本”与“王道之要”,说道:“详论王道,本末兼该,最为明白,学者信能熟读焉,则其于王道,犹指诸掌。”⑦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149页,第2-3页,第68页,第7页,第69页。因此,此章内容在《孟子》中先后出现两次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仁斋还指出宋儒将《孟子》的“仁义礼智”理解为“性”的谬论。在仁斋的古学视域内,“仁义礼智”四者皆是“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这种差别的缘由在于宋儒解“四端”之端为“绪”,即“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版,中华书局,2006年,第238页。而仁斋则以“本”释“端”,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仁义礼智之本,能扩而充之,则成仁义礼智之德”。⑨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149页,第2-3页,第68页,第7页,第69页。宋儒不深考于此,以致谬以千里。所以,仁斋认为,人有“四端之心”,即性之所有。人人具足,不待外求。犹如四体之具于自身,如果扩而充大,则能成仁义礼智之德。是故,仁斋言道:“求仁义,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以功利邪说为之害。所谓性善者,明仁义之有于己也。浩然之气者,明仁义之功用也。存心者,存此也。养性者,养此也。尽心者,尽此也。求放心者,求此也,皆莫非所以求仁义也,故孟子之学,莫要于求仁义,而求仁义,莫先于扩充四端之心,可谓一本矣,非若诸子泛论错说,而无所本也。”⑩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纲领》,第3页。这意味着,《孟子》中的“性善”“浩然之 气”“存心”“养性”“尽心”“求放心”等心性论内容,皆与“仁义”等道德有着重要关联。“仁义”为道德的大端,万善的总脑,至于“礼智”二者,则皆从此而出。于是,《孟子》强调扩充人所固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进而成就“仁义礼智”之德,此为仁斋不同于宋儒的关键之处。
在日本古学派中,仁斋对孟子和《孟子》书是最为推崇的,尤其是在其“语孟一体”的视域内。由于仁斋对《孟子》的解读是围绕着批判朱子学者对《孟子》的误读而展开的,所以,他作《孟子古义》的目的与《论语古义》一样,皆是“尽废宋儒注脚,重解语孟二书”,恢复“二书”的本来面目。在《语孟字义》中,仁斋与宋儒采用相同的方式,从字义入手,入室操戈,针对《孟子》中的天道、天命、道、理、德、仁义礼智、心、性、四端之心、情、良知良能、权、圣贤、君子小人、王霸等关键词进行了重新解读,将宋儒赋予其中的理气性命、明镜止水、冲漠无朕、体用一源、心体性体等论说全部解构,认为宋儒的这些说法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实是以佛老之学曲解圣人之作。即便如此,仁斋作《孟子古义》也绝不是简单地恢复《孟子》书的原意,其中仍不时地折射出“古义学”的特色,由此凸显出其“尊孟论”的独特之处。
二、荻生徂徕的“非孟”论
与仁斋的“尊孟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学派之集大成者荻生徂徕的“非孟论”。在徂徕的古文辞学视域内,“道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为其“道论”核心。由《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组成、且早于“四书”的“六经”,才是“先王之道”“圣人之道”的重要载体。这是徂徕与仁斋的根本不同之处,恰是在这一脉络下,徂徕提出了“非孟”的思想取向。表面上看,徂徕的古学主要批判对象为宋儒与仁斋,但实际上徂徕却将矛头直指孟子及《孟子》书,认为,宋儒与仁斋之谬误的源头实则源于孟子及其思想学说。
在徂徕的视域下,宋儒与仁斋的重要失误皆在于不知“古文辞”之故,仁斋因不懂“文字”有“和汉”之异,以致出现了以“和语”视“华文”的局面,此乃仁斋之失,而宋儒却不知汉文有“古今”之别,而以“今言”视“古言”,其失误自然难免。因此,徂徕反复强调,中国古代典籍——“六经”既为“先王之道”的载体,更是“古文辞”的重要载体,其他皆有后人增补、损益的成分。
在《辨道》中,徂徕明确指出“道”的意涵,即先王所制作的“礼乐刑政”,而非其他。然而,其中能被称为“先王”或“圣人”的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人,因为他们皆有“制作礼乐政教”且“安天下”的事功。至于孔子,虽无制作之功,但因其在礼崩乐坏的年代绍述“先王之道”,并以作“六经”的方式使“先王之道”流传于后世,因此,也被徂徕视为“圣人”。徂徕还把“孔子之道”等同于“先王之道”。他说:“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孔子平生欲为东周,其教育弟子,使各成其材,将以用之也,及其终不得位,而修六经以传之,六经即先王之道也……”①荻生徂徕:《辨道》,收入《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36),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第200页。然而,由于孔子殁后儒分为八,又值诸子百家争鸣之际,思孟等孔子后学为捍卫孔子之道始与百家争衡,却将“先王之道”“孔子之道”降低为“儒家者流”,“观夫子思作中庸,与老氏抗者也,老氏谓圣人之道伪矣,故率性之谓道,以明吾道之非伪,是以其言终归于诚焉……至于孟子性善,亦子思之流也……立言一偏,毫釐千里,后世心学,胚胎于此……吁嗟,先王之道,降为儒家者流,斯有荀孟,则复有朱陆,朱陆不已,复树一党,益分益争,益繁益小,岂不悲乎?”②荻生徂徕:《辨道》,第200页。所以,在这一脉络下,徂徕率先解构了宋儒所赋予孟子的圣人地位。
徂徕极力批判“孔孟之称,不伦殊甚”,③荻生徂徕:《蘐园九笔》,收入《日本儒林丛书》第七卷,东京:凤出版株式会社,1978年,第187页。因为“先王之道”至孔子便戛然而止,孟子既不属于“七十子”范围,又相距孔子时代之远,既无“制礼作乐”的事功,也未能像孔子那样绍述“先王之道”,实难与孔子并称。然而,宋儒与仁斋却提出“孔孟并称”“孔孟一体”的主张,这在徂徕看来,实是“后王骄其贵”“后儒骄其圣”之举,由此徂徕否定孟子的圣人地位,并斩断“孔孟并称”之说。重要的是,“语孟一体”的说法也被徂徕所解构。在宋儒及仁斋的思想体系内,《论语》与《孟子》并称,即便是仁斋强烈批判宋儒的“四书”经典结构,但至少还是认同“语孟”经典结构。然而,在徂徕的视域内,《论语》和《孟子》并称,也是不伦殊甚。他认为,《论语》是唯一能与“六经”比肩的著作,而对于《论语》的性质,徂徕说:“孔子生于周末,不得其位,退与门人修先王之道,论而定之,学者录而传之,六经传与记是已。其绪言无所系属者,辑为此书,谓之语者,裁然耳。”④荻生徂徕:《论语征·序》,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论语部五),东京:东洋图书刊行会,1926年,第1页。所谓“绪言”,即“已发而未尽的言论”,这意味着,《论语》是“六经”的“已发而未尽”的言论。但是,《孟子》一书绝不可与《论语》比肩。孟子虽为维护圣人的地位而奋起与老氏之徒抗争,但其结果却是将“先王之道”简单化为“儒家之道”,故《孟子》一书不传“先王之道”,徒以“议论”“强辩”为主,试图欲以服人,背离了圣人之道。对此,徂徕言道:“孟子则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也,是战国游说之事,非教人之道矣。予故曰,思孟者与外人争者也,后儒辄欲以其与外人争者言施诸学者,可谓不知类已。”①荻生徂徕:《辨道》,第205页。
考察徂徕的著作,其晚年注释《孟子》的《孟子识》一书,虽只注释了《梁惠王上》及《梁惠王下》前四节(止于“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一段),据此将之与徂徕的著作结合来看,便可知徂徕“非孟”之关键在于《孟子》不言“礼乐制作”的事功而徒称“仁义礼智”。如前所述,“先王之道为安天下之道”是徂徕思想的核心,而“先王之道”的主旨不离“制礼作乐”,其主要内容为“四教六艺”,“四教”即“诗书礼乐”,“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然而,《孟子》却以“仁义礼智”与“四端之心”相连,由此提出“性善说”的理论基础,而这与徂徕以礼乐(礼义)为核心的“道论”格格不入。在古文辞学视域内,徂徕对“仁义礼智”皆有新解,认为四者皆离不开“先王之道”“先王之礼”,如“义”字,徂徕以“先王之义”解之,他说:“义,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盖先王之立礼,其为教亦周矣哉……先王既以其千差万别者,制以为礼,学者犹传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谓礼之义也,而其以空言传者,是所谓义也,故礼义皆自古传之,岂非先王之义乎!”②荻生徂徕:《辨名·义》,收入《荻生徂徠》(日本思想大系36),第220页。也就是说,只有将“礼义”合称,才是“先王之礼”“先王之义”,至于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朱熹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仁斋道“为其所当为,而不为其所不当为,之谓义”等言论,是皆不知“义”为“先王之义”、以安民为本,徒取诸“臆”以为“义”,宋儒的“义理”之说,也是不知“义”之本义。关键的是,在徂徕看来,这些谬论虽源自于后儒对孟子“裁割断制之说”,但如果《孟子》一书本身没有问题的话,恐怕后世也不会有这么多误读。所以,徂徕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孟子》。其中,徂徕与孟子的根本分歧在于“礼乐”与“仁义”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毫无疑问的是,徂徕是以“礼乐”为主、“仁义”次之,以“礼乐”为道、“仁义”为德,进而解构了孟子“仁义礼智”并称。同样,以“四端之心”为根基的性善之说,也是徂徕非议的重要命题。徂徕以“六经”来释“性”,认为:“性者,生之质也。”③荻生徂徕:《辨名·性情才》,第240页,第240页。它无善无恶,对人来说,智、愚、贤、不肖之差别,全是后天的修养而成,习善则善,习恶则恶,是故,孟子好“性善”,荀子言“性恶”,各执一端,皆有所失,是故,徂徕对《孟子》核心的“心性论”是持批判态度。
不止如此,徂徕还认为《孟子》中“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实为“妄说”。这在徂徕看来无异于“人人皆可成为圣人”,但徂徕认定的圣人只有先王七人外加孔子一人,他们因有制作或传承之功而被称为圣人,圣人岂是常人所能企及的?孟子妄称“人人可为圣人”,实是侮辱圣人之道,而宋儒、仁斋不察孟子的“议论”之言,故陷入歧途。“宋儒不循圣人之教,而妄意求为圣人,又不知先王之教之妙,乃取诸其臆,造作持敬穷理扩天理去人欲种种工夫,遂以立其本然气质之说耳。仁斋先生活物死物之说,诚千岁之卓识也,祇未知先王之教,区区守孟子争辩之言,以为学问之法,故其言终未明鬯者,岂不惜乎!”④荻生徂徕:《辨名·性情才》,第240页,第240页。但宋儒、仁斋之谬误的根源皆在于《孟子》,这一逻辑的展开脉络,构成徂徕“非孟”论的重要一环。
三、古学派的“汤武放伐论”
“汤武放伐论”是后世儒者诠释与研究《孟子》难以越过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史上,孟子成为圣人及《孟子》一书“升格”为经书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直至理学兴起之后,二者的地位才发生了改观。即便如此,仍有明太祖罢孟子配享而作《孟子节文》之事。究其原因,《孟子》书中凸显的“民贵君轻”“汤武放伐”以及“劝诸侯行王道”的“革命论”倾向,加剧了君臣关系的紧张性,并可能为后世“乱臣贼子”的犯上作乱埋下伏笔。所以,《孟子》一书即使成为儒学经典,也难以消除其对统治阶层的隐患。
上田秋成在《雨夜物语·白峰》中记载道:“汉土典籍、经典、史策、诗文等无一不曾传入本朝,唯有《孟子》一书至今未传到日本。”⑤上田秋成:《雨夜物语》,收入永井一孝校:《上田秋成集》,东京:有朋堂书店,1926年,第219页。桂川中良在《桂林漫录·孟子》中引用这一传闻:“《孟子》为忌讳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自古有传闻,若有船自唐土载该书而来,必颠覆。然此书若无恙舶到,亦不为朝廷所用。”①桂川中良:《桂林漫录》,收入《日本随笔大成》第一期(2),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年,第293页。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其它江户时代的著作中。然据考证,这一说法最初源自中国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中:“倭奴亦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辄覆溺。’此亦一奇事也。”②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6页。很显然,从日本孟学史来看,这一传闻纯属无稽之谈,但其中却折射出“汤武放伐论”在日本社会所造成的紧张性。由于《孟子》中对“汤武放伐论”的肯定,必然会冲击日本“万世一系”的政治体系,以至于在江户后期竟流传着“《孟子》难以传入日本”的传说。
然而,对于古学派的《孟子》诠释中,“汤武放伐论”虽是难以绕开的话题,但却与《孟子》会造成日本社会的紧张性关联不大。在仁斋的视域内,他对《孟子》的“汤武放伐论”是持肯定态度的。其言道:“孟子论征伐,每必引汤武明之,及其疑于弑君也,乃曰闻诸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盖明汤武之举,仁之至,义之尽,而非弑也……道也者,天下之公共,人心之所同然,众心之所归,道之所存也……夫天下非一汤武也,向使桀纣自悛其恶,则汤武不必征诛,若其恶如故,则天下皆为汤武,不在彼则在此,不在此必在彼……故汤武之放伐,天下放伐之也,非汤武放伐之也,天下之公共,而人心之所同然,于是可见矣!”③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35页,第36页,第14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8页。这意味着,仁斋率先否认了“汤武弑君”的说法,反复强调“汤武放伐”并不是汤武二人的“放伐”,而是天下的“放伐”。言外之意,桀纣的暴行已激起了天下之人的愤怒,即使汤武不实行“放伐”之举,也会有人做“放伐”之事。因此,仁斋驳斥了宋儒以“汤武放伐”为“权”的说法——“宋儒以汤武放伐为权,亦非也。天下之同然之谓道,一时之从宜之谓权。汤武放伐,即道也,不可谓之权也”。④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35页,第36页,第14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8页。对于“权”和“道”,仁斋称“权”为“称锤”,即“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夫称锤之为物,所以随珩之斤两,或前或却,定其轻重者也,故权字取称锤之义”。⑤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35页,第36页,第14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8页。要而言之,“权”即“变”也,强调变通。“道”则与之不同,它是人伦日用当行之路,是万世不易的准则,不可因时因事而随意变通,“道者……非待教而后有,亦非矫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于四方八隅,遐诹之陋,蛮貊之蠢,莫不自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亦莫不有亲义别叙信之道,万世之上若此,万世之下亦若此”。⑥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35页,第36页,第14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8页。所以,仁斋指出,桀纣与子婴、隋炀帝一样,属于暴君,其被“放伐”“杀戮”的结局是“道”的结果——“盖以合于天下之所同欲也,唯汤武不狥己之私情,而能从天下之所同然,故谓之道”。⑦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35页,第36页,第14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8页。虽然,仁斋称“汤武放伐”为“天下放伐”,但其旨归却是“人心向背”,其言道:“欲知天命,当观人心。欲得人心,当施仁政。”⑧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第35页,第36页,第149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8页。故他极力反对“乱臣贼子”假借“天道”“天命”来行“放伐”之事,即使仁斋赞许“孟子劝诸侯行王道”的做法,他在最后也说道:“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王者之心,而孟子所谓王道者如此,若不然,而曰:‘天命已改,遽废天子’,以为庶人,已自抗然,敢居天子位,是篡也,王者不为。”⑨伊藤仁斋:《孟子劝诸侯行王道论》,收入《古学先生诗文集》,载《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一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85年,第51页。
然而,徂徕对“汤武放伐论”的认识却与仁斋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是在批判仁斋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论。在徂徕的“道”论视域内,“道”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道”自圣人所出,汤武二人既属圣人,所以,汤武实行“放伐”之举正是“圣人之道”的体现,其言道:“夫道者,圣人所建也。圣人所以建道之心则在仁。汤武圣人也,汤武放伐,应天顺民,仁也。五伦者,道之通于上下者也,以为尽乎道者,非也。夫道者,圣人所建也,则圣人重于道,岂得执达道以非汤武乎?是孟子之意也。”⑩荻生徂徕:《孟子识》,收入板仓胜明辑:《甘雨亭丛书》(四),江戸:安中造士馆藏,嘉永6年(1853),第14页。重要的是,“圣人之道”以“敬天”为本,故汤武的“放伐”就是依据“天命”而行之,完全符合圣人之道,其言道:“汤武奉天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谓一夫纣者,以明民之所弃即天之所命也,非恶纣之恶也,祇好辨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于敬天之义,则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谓禘之说也。”⑪荻生徂徕:《论语征》,第306页。也就是说,汤武的放伐之举与桀纣的善恶无关,亦与民心的向背无关,完全是“奉天命而行之”。由于孟子“好辩”,“言辞激烈”而未知“先王之道”的内涵,再加上“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的坠落,故孟子只能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求天命的改与未改,误解了汤武放伐论——“孟子生其时,欲以口舌胜之,遂有诛一夫纣之说,汤武岂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谓我道之祖,务欲分疏其为圣人,是其过尔。后世有论汤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汉儒以为权,仁斋以为道,皆僭妄已”。①荻生徂徕:《论语征》,第193页。也就是说,不只孟子如此,仁斋以“汤武放伐为道”的说法也是有问题,徂徕对此持批判态度,指出:“若仁斋以汤武放伐为道,既非矣。然其既以放伐为道,则孟子劝齐梁君王,亦何所讳也!乃其言曰,孟子所谓王者,本以德称之,而不必以居天子位为王也。齐梁之君,苟能行仁政而得天下之心焉,则虽为诸侯,皆可以称为王者也。因引文王为证妄哉!是回护之言也。孟子何啻引文王,亦引汤武,而仁斋何乃举一而隐二,非回护而何?”②荻生徂徕:《孟子识》,第15页。这意味着,徂徕视仁斋的说法为回护之言,一方面,仁斋称“汤武放伐”为道,一方面,仁斋又赞同“诸侯行王道”且“不必以居天子位为王”,显然是悖论,所以,徂徕驳斥道:“汤武放伐,圣人之事也。圣人者道之所出,故古无论汤武者,后世儒者傲然自高,以圣智自处,妄意谓道先天地生,故有是妄说,岂不僭乎!”③荻生徂徕:《辨名·经权》,第253页。
由上可知,仁斋与徂徕对“汤武放伐论”的认识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二人对“汤武放伐”皆是持肯定态度,他们都未意识到《孟子》的“汤武放伐论”会对日本社会产生冲击,完全是从古学思想的脉络中新解“汤武放伐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孟子》新诠。
结 语
仁斋与徂徕在古学视域内赋予了《孟子》新解,但因二人对古学的认识程度不同,导致了二人不同的“道”论。仁斋以“道为人伦日用之道”解《孟子》,故《孟子》与《论语》并称。而徂徕则以“道为圣人之道、安天下之道”解《孟子》,因此《孟子》难以与《论语》并肩,被徂徕移出了圣人的经典著作。透过仁斋与徂徕的《孟子》新诠,可看出宋儒赋予《孟子》的新解以及《孟子》自身的“心性论”完全被二人解构,凸显了江户古学派的务实主义特质。
虽然,仁斋与徂徕对“汤武放伐论”皆持肯定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汤武放伐论”必然会冲击到德川幕府,即使在当时尚未凸显,但在江户中后期之后“汤武放伐论”所造成的紧张性却日渐明显,引起了后儒的批判,这与当时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所以,诚如黄俊杰所言:“《孟子》这部经典在德川时代日本思想史上,常发挥某种思想的温度计的作用,许多儒者的思想立场乃至政治态度,都可以从他们对孟子学的解释而窥其消息。”④黄俊杰:《伊藤仁斋对孟子学的解释:内容、性质与涵义》,《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修订版),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第85-86页。因而,从日本视域下考察《孟子》诠释,不只凸显出《孟子》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对《孟子》的深入研究将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