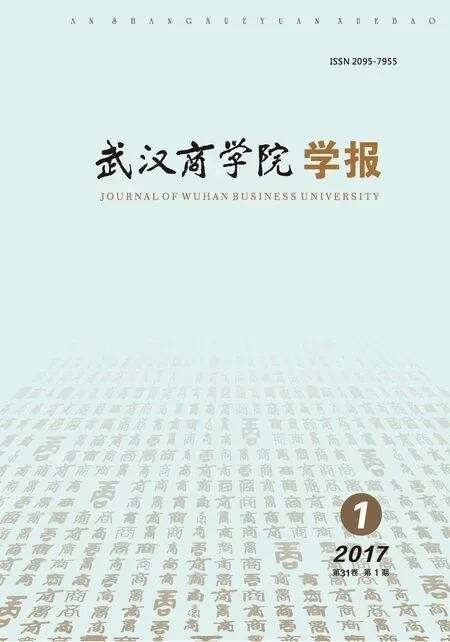现代化视域下的晚清湖北江汉关研究
2017-03-12常城
常城
现代化视域下的晚清湖北江汉关研究
常城
(新乡学院,河南新乡453000)
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开关。江汉关的筹建,标志着列强控制下的近代海关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经济力量楔入湖北地方,从而导致传统的双边关系演变为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江汉关独立于传统机制的完整框架之外,是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直接产物,表征为领导权力的半殖民化、管理机制的现代化和业务职能的多元化。作为现代化的产物,这一新型的海关税收机构反过来成为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催化剂,加速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同时,江汉关亦具有明显的半殖民性和侵略性,逐渐沦为外国经济压榨中国的利器。
江汉关;晚清;现代化;湖北
1862年1月1日,历经清廷中央、海关总税务司和湖北地方几年时间的角逐博弈,湖北汉口江汉关正式筹建完成。[1]江汉关的创办,是晚清汉口开埠后湖北商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方利益均衡博弈的契合点。作为一个新型的海关税收机构,江汉关对湖北近代历史,特别是晚清湖北的现代化历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江汉关本身即是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产物之一,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近代特征,表征着晚清湖北现代化的肇始与初步发展;另一方面,江汉关对晚清湖北现代化产生了典型的双重作用,既促进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亦扭曲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发展轨迹。
一、均衡与博弈:江汉关筹建始末
江汉关的创设,首先缘于汉口港的开埠。五口通商后,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并非期望中的快速增长,各口岸相继出现货物积压、贸易停滞、价格跌落等市场萧条现象。列强对华贸易受阻,归咎于商业贸易被严格地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除非我们从事买卖的范围能扩展到我们现在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去,我们对华贸易永远也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2]。
为了增加通商口岸,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两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九省通衢且位于长江中游的传统商业名镇汉口,成为西方列强的必然选择。1858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静,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商出进货物通商之区。”[3]
1861年3月7日,英商上海宝顺行行主韦伯、英国官员威利司、通事官曾学时和杨光谦及随从人员近五十人乘英国火轮船抵达汉口,与时任湖广总督官文商定汉口通商相关事宜,后又委托李大桂代觅栈房一所,岁付房主租银400两,杨光谦和部分随从留驻。同年3月11日,英国参赞官巴夏礼率三百多英兵乘四艘火轮船至汉口,会同汉阳府县等于汉口下街尾、杨林口上下勘定地基界址,并与湖北藩司衙门和湖北布政使唐训方签订签订《英国汉口租地原约》,“并议再有他国到楚,须在英行以下择地盖栈,不得上占正街。”[4]而此次交涉,“是为英人立汉口市埠之始。嗣后,通商之国踵至,而汉口遂为中外交涉之一大关键,接武上海矣。”[5]
汉口虽然开埠,但并未立即创建海关。
英国领事官巴夏礼与湖广总督官文商洽汉口开埠之时指出没有必要设立汉口海关,“货物出口入口,课税俱在上海、镇江完纳,九江、汉口概不征收”[6]。其实,当时情形之下,清军正与太平军鏖战正酣,“长江贼匪,出没无常,商贩走私,难于查拿,固宜于总处支纳,以免偷漏”[7],创办海关条件确实不够成熟。随之签订的《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便明确规定,“自镇江以上、汉口以下沿途任便起货、下货,不用请给准单,不用随纳税饷。俟回镇江,遵照前章办理。”[8]对于《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所颁行的条款,总税务司赫德亦有合理解释,“若照暂定章程,在上海征纳税饷,旋在镇江以上,汉口以下,准商任便起货下货。镇江以上,即作为上海内口,无庸设虚立之关。如此办理,一面于税务不至偷漏减少;一面可免待贼如官之关系。以上两般办法,若照新设三关征收税饷,则经费虚糜,而奸商易于偷漏,实于中国税饷银大有碍;若照新定章程办理,实于中国有益而无损。”[9]
汉口开埠而不设海关,固然是战时客观情形所致,但也因此带来了诸多弊端。
首先,增加了关税管理的问题,“半载以来,洋商往返贸易,凡有洋货进口售卖内地,内货出口贩运外洋者,因自发逆上犯,汉口巨商大买,迁移一空,所到洋货皆于汉口以货易货,并不教进口货物清单,亦不报出口货物数目,以致毫无稽查。”[10]。同时,出于促进合法贸易的需要,英国领事馆准许英、美商人悬挂本国国旗于租借而来的货船之上,但由于缺乏海关监管,此项措施肆无忌惮地被西方走私者利用,其“悬挂英国国旗以逃避本地关卡课税……又伪装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11],从而走私之风日炽。
不设海关亦使湖北地方财政税收日趋拮据,这是湖北地方政府不能容忍的关键。清末迫于战事与时局,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松动,地方督抚的财权空前膨胀。地方财权的重要基础是厘金,而关税管理上的漏洞严重影响了地方厘金的收入,“内地商船借插英旗影射偷漏,甚至将违禁货物如钢铁、米粮等类装载下船,内地商人分赴湖南、湖北购买茶叶等货物,动称洋商雇伙,抗不完纳厘金。”[12]
总之,长江通商贸易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引发地方督抚的严重不满,湖广总督官文曾多次请奏汉口设置海关,后又联合江西巡抚毓科针对赫德所奏之《长江一带商论》进行反驳。官文指出:“汉口为九省通衢,行运甚广,百货丛集。其中茶叶、大黄、桐油等货,尤为出口大宗,奸商倚托影射,甚至将停运之货接济贼匪,违禁之物潜行夹带。自汉口至镇江,途径千余里,其中处处可以私售,汉口既无盘验,上海镇江无凭稽查。若经由长江出口,则上海亦无从查知,不特税课竟归无著,抑且将来流弊无穷。”[13]官文还特别强调,在长江新开之汉口、九江设关征税,添设监督,赶建衙署,方为解决长江通商问题的关键。
从清廷的角度来看,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未平息,长江中下游流域很多地区依然动荡不安,汉口建关收税缺乏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同时,汉口建关收税,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地方督抚的财权,势必会更加削弱本已江河日下的中央集权。另外,总税司赫德的反对意见也并非子虚乌有,当时情形之下在汉口设立海关也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和诸多弊端。但经过权衡甄别,特别是鉴于太平天国军屡次攻打两湖地区,为防止地方财政亏空引起军事实力虚弱而被重新占领,并且安抚地方督抚,清廷将《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修改为《长江通商各口暂行章程》,并于1861年11月11日最终批准同意官文所奏请之《汉口设关收纳洋税折》。
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建立,大关设于夏口县汉口河街,即汉口镇英国租界花楼外滨江。
然而,江汉关设立之初,各方利益依然无法协调。
原因在于江汉关虽然设立,但只能征收子口税和稽查走私,“长江应收进出口正税及土货复进口税,现今均在上海完纳,应请伤下江苏巡抚将上海代收长江各税,每届三月一结之期,分别解往湖北、江西二省,以济军晌。”[14]
“每届三月一结之期,分别解往湖北、江西二省,以济军晌”,中央虽如此打算设计,地方政府却不能如是执行。1862年5月,湖北候补道张曜孙奉官文之命赴沪催提代征款项,与江海关方面发生了激烈争执。张曜孙要求返鄂省的款项既包括长江进出口正税还有土货进长江的半税。而江汉关则认为:“洋货向无一货两税之例,既完海关进口税,即不能再完长江进口税。上海关代征货税,只有长江运来土货应完汉口、九江出口正税,及由上海运入长江复进口半税两项,其由上海运入长江洋货,历系遵照条约,以洋人在先到海关纳税为定,海关给发免照,其他海关并不再征,因此,江海关委无代征其他海关长江进口正税之说,长江进口正税一项不应列入返还之数。”[15]
即使只返还土货出口正税,苏省亦搪塞敷衍,屡屡诘难。[16]最后干脆声称:“此项代征之税,本应随时解还。惟上海贼氛环逼,堵剿吃紧,已将该款尽数提充本省饷需。”[17]
现款不能提取,湖北则要求抵代拨协军饷。但是,江海关依然不允,“查湖北、江西两省以应归之税,划应解之款,苏省本无诱卸但此项税银,在当时有不能不拨动之苦况,现在又有不能即行弥补之情形”,“请将划拨前两项银两,另行改拨,以济要需。”[18]
对此,湖广总督官文继续奏请清廷,语言尖锐,直指要害:“盖其中有专为上海计,而未为三口计者,有专为洋商获益计,而不为内地税饷计者。照章办理,则长江无可立之关,无可征之税,并无可查之货。”[19]在该奏折中,官文也再次吐露地方财政的困绌,甚至借两湖战事吃紧威胁清廷,“频年两湖、安徽血战之师,久已望饷若渴,以为江汉开征之后,饷需无虞匮乏,得以尽力东征;迄今关税尚未议定,即收子口税,而不抵厘金之一二成。求盈反绌,皆由上海之未能洞悉长江情形,为十二款、五款章程所限故也。”[20]
迫于地方压力,清廷最终又废除《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厘定《长江通商统共章程》。至1863年1月1日始,江汉关正式征收正税。
透过以上种种可以窥视,江汉关的创办不仅是晚清汉口开埠后湖北商贸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多方利益博弈的产物。多方利益博弈中,除了传统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海关总署开始作为一个新兴力量强势楔入,“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上,围绕财权分割和财源争夺,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和近代海关三者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21],以往中央与地方的双边关系,演变成三角关系。
二、初步现代化:一个新型的海关税收机构
柯文把19世纪的中国历史分成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三个不同层带。最外层带,“包括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人侵略的回应,或者是入侵产生的后果。这一层带包括的现象颇为繁杂,例如通商口岸,近代兵工厂与船坞,像王韬一类的报人,基督教徒,像总理衙门和海关这类机构,向外国派遣中国学生与使节等”[22]。
江汉关完全按照西方的管理模式移植而来,独立于传统机制的完整框架之外,是典型的最外层带,其本身即为晚清湖北现代化的直接产物。作为一个新型海关税收机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呈现出领导权力的半殖民化、管理机制的现代化和业务职能的多元化三方面特征。
(一)领导体制的半殖民化
江汉关实行双轨权力领导体制,即清廷任命,地方官监理的海关监督与总税务司直接派驻的外籍税务司共同承担对中国海关的监督管理权。江汉关第一任海关监督为湖北分巡道汉黄德道郑兰,第一人税务司为狄妥玛。缘于汉黄德道监理江汉关,其衙署由黄州府迁至汉口镇。
海关监督名义上是海关机构的第一负责人,但并不真正地干涉关务,甚至变成徒有虚名的傀儡。由英籍总税务司赫德任命的外籍税务司反仆为主,俨然成了江汉关的主人。江汉关海关监督和外籍税务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畸形关系,并且“这种畸形的关系,随着列强侵华形势的加剧而激化”。[23]
从大环境来看,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海关始终处于一种半殖民化的状态,“是一个以英员为主,先后有23个国家和地区人员参加的国际官厅;其格局与各国实力,在华势力的涨消息息相关,在某些地方,还往往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相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列强势力范围色彩。”[24]至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海关总数49处,海关职员20000名,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海关网络。[25]
具体到江汉关,从1862年汉口正式设立江汉关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半个世纪中,税务司一职全部有外国人担任(含署理和代理),其中英国占18人,美国占2人、法国占2人、德国占1人。[26]江汉关的领导权基本上被牢牢地掌握在英籍税务司手中,它所制定的协定税则将华洋商品置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税率上显示了有利于华商的强烈倾向性,不仅不能起到现代海关保护民族经济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责任与使命,相反成为西方国家掠夺中国内陆资源和倾销其工业商品的利器。另外,近代海关一开始就与清政府的赔款、外债发生某种特殊关系,江汉关所征收之关税除了一小部分留为本省所用外,大部分交付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汉关逐渐沦为外国压榨湖北的有效工具。
(二)管理机制的现代化
江汉关的的管理机制完全采用近代西方模式,拥有独立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征税系统,与原归户部管辖的四海关分别形成两套迥异的榷关制度。其高效快捷的工作效率与廉洁自律的运营机制与湖北传统税收机构的混乱、腐败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比。
机构设置方面,江汉关由税务司负责,税务司下设副总税务司、帮办。根据工作性质分内勤与外勤,内勤设秘书、税务、总务、会计等,外勤设验估、监察、缉私、江务、港务等。无论内勤与外勤,高级职员均由外籍人员充任,中国人只担任文书、杂役之类低级岗位。
税收管理方面,江汉关实行严格地税收征收和保管制度,将税款之征收、储存、汇寄予以分割,征与管之间相互制约又统为一体,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以往税收征管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弊端。所征收的税款,“向按西历纪年每足三个月为一结,详情奏报征收各项税钞数目一次,年凡四结。动支款项四结一报,仍造具四柱清册逐款开列,以昭明晰”[27]。
江汉关的人事制度也是其管理机制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江汉关根据海关总税务司仿效西方制定的人事制度,将包括职级管理、官员选拔录用、福利奖惩办法等一系列较科学的人事制度,实施于海关实际人事管理之中,对保障江汉关机构运行及最大限度地发挥关员的工作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28]
(三)、业务职能的多元化
作为一个初步现代化的新型海关税收机构,江汉关业务职能呈多元化特征,不仅全面承担海关业务职能,如关税征收、货物稽查、货运管理、海关贸易统计等,还履行了其他非海关业务职能,如港务建设、航道整治、气象测候、报关行管理等。
1、海关业务职能
关税征收:江汉关开关之初只能征收子口税,1863年1月1日正式征收海关正税。税源主要包括正税、半税、子口税、船钞、三联单罚款、罚款、洋药进口正税、红茶补厘、火油池捐、护照费、小轮船牌照费、船牌费。[29]
货物稽查与走私缉拿:江汉关具体负责缉稽查货物的工作人员为总插子手、插子手、验货员、巡役等。总插子手和插子手共19人,为外籍人员;验货员一等7人,二等5人,可由中国人担任。税务司和总插子手各配备专用巡船一艘,所有巡船均挂“江汉关巡查”字样。为了严行稽查,江汉关在广济武穴设总卡。对于走私者一经发现,均按章程严肃处理。
货运管理:江汉关监管之初即订立专章条款,对轮船停靠地点、货物申报程序、货物起卸与存储等货运管理事宜有明确详细的规定。
海关贸易统计:江汉关税务司即在总税务司的监督和指导下,照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统计方法,撰写并保留了大量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为其后汉口,乃至整个湖北社会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信息。
2、非海关业务职能
港务建设:管理汉口港务,对汉口港船只停泊界限、移泊、载运军火、油类及易燃物品,船舶管理、航道保护等都有详细规定。
航道整治:1866年筹划汉口航道,先后在长江中下游设置灯船、浮筒、标桩等;1906年设置九江设巡江司,专司测量水道、设置水尺,引发航船布告、水道水量通告,检查沿江标志事宜。
引水监督:1869年总税务司颁布《引水总章》,明确规定引水监督权归海关。
气象测候:1869年始江汉关开始办理气象测候业务。
邮政代理:1866年,江汉关开始兼营邮政业务,至1908年之前,汉口邮政方才完全脱离海关。江汉一直关监理汉口邮政业务,邮务长之职由江汉关外籍人员兼任。
检疫服务:1902年汉口关制定检疫规则,对汉口进出口货物进行检疫。
报关行管理:随着外贸的繁荣发展,报关行应势产生,江汉关则负责报关行的注册与管理。
三、硬币的两面:江汉关对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作用
江汉关不仅是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发展产生典型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江汉关促进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具体表现在四点:之一、江汉关的成立规范了晚清湖北的贸易秩序。汉口开埠后至江汉关建立之前,湖北境内贸易关税管理混乱,甚至外国人都承认,来往长江的外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些无原则和无品行的人,事实上也就是些不法之徒,他们不但把条例和章程一概置之度外,而且把中国人看成是可由他们任性劫掠的”[30]。而江汉关的创办革除了旧式海关名目繁多的关税摊派,有效地防止了敲诈勒索、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等弊端,保证了健康正常的税收秩序,也因此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为晚清湖北的崛起做出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之二、江汉关的的创建,是汉口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至清末的最后几年,“汉口年贸易额达1亿3,000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现今已成清国第二要港,几欲摩上海之垒。鉴于此,机敏的观察者言:汉口乃东方芝加哥。”[31]江汉关为汉口由传统国内商业“四大聚”之一涅槃为近代国际扬名的“东方之芝加哥”提供了历史契机。之三、江汉关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海关行政机构,但实际上还履行了部分港口和城市建设的公共服务职能。海关的近代化设施,“使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些近代化气象。”[32]其直接或者间接地建设了一批近代市政基础设施,一定程度改变了汉口的城市风貌、空间结构等,有效地加速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堪称汉口由传统市镇一变而为近代通商口岸的崭新商业标志”[33]。之四、江汉关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完全采用近代西方模式,是湖北地区税收行政管理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近代转型的先驱,为晚清湖北现代化其他各项事业提供了制度借鉴和学习典范。
另一方面,江汉关亦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发展。
晚清无地方财政之名,却有地方财政之实。晚清湖北现代化的进展,与湖北地方财政的多寡息息相关。
诚然,江汉关拟定出新的税收项目,改变了以往税收结构过于单一的状况,增加了税收总额,使江汉关获得持续稳定税收来源。1863年到1885那年,江汉关的税收总额一般都在100-200万海关两左右,1886年至1911年的大多数年份总额都超过200万两。[34]但是,江汉关的充沛税收绝大多数都纳入中央财政体系,它对晚清湖北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支持过少。自1863年至1910年,江汉关税收中,省用项下共5957888库平两,仅占税收总额的6.5﹪,而江汉关本身的运转成本即达11471067库平两,占税收总额的12.5﹪。江汉关税收的省用项下,只是全部税额的极少部分,甚至还仅仅是关用项下的一半左右。[35]
近代海关的诞生,首先是西方在华列强意志的产物,但清政府很快加入了自己的意图,“由于海关在晚清财政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本身统一、有序、高效的管理制度,海关征税范围和权力的扩大不但为帮助清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提供了不断增加的税收,而且还不断使部分原中央政府已基本失控的财源和财权通过海关重新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的控制下。”[36]江汉关的设立和开征正税虽是在湖广总督官文的力荐之下完成,然而,自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之后,随着洋关制度体系的形成,江汉关迅速沦为列强与中央政府实现自身意图的有效工具。中央财政透过江汉关确保了税款流入国库,但对于湖北地方而言,无疑彼长此消。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纷争,便在一定程度上经由海关与地方当局对征税权的争夺表现出来。例如,1873年至1874年,湖北厘金总额的严重下滑,即是由江汉关开征子口税造成。[37]厘金是晚清湖北各项现代化事业得以展布的重要资金来源,从这一点来看,江汉关对晚清湖北现代化的发展确实不利。
最后必须还要指出,江汉关虽然是晚清湖北现代化的产物,并且反过来推动了晚清湖北现代化的进展,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是由西方强力促成,甚至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的延伸,因此在其倍加渲染的近代性的表象之外,丝毫也掩饰不了它的殖民性。”[38]随着晚清政事的败坏和民族危机的加重,江汉关的税收大部分交付海关总税务司署用作偿还外债和赔款,成为外国经济压榨中国的工具。同时,江汉关虽然规范了湖北近代的贸易秩序,创办了现代的关税管理体制,但由于操控于外国人之手及受到关税协定的制约,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掠夺中国内陆资源和倾销其工业商品的利器。另外,江汉关的势力远远溢出海关之外,渗透到湖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诸多领域亦对晚清湖北的现代化产生消极作用。
[1]在清代官方文献中,“海关”的指谓一般是指常、洋两关的合称,如果再细加分别的话,则将常关、大关、旧关、老关、土关、内关归为一个范畴,新关、洋关归为另一个范畴。而在税务司系统的文献中,一般即将洋关直接称为“海关”。
[2]“曼彻斯特市商会议事录”,1849-1858年卷,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97页。
[4]《官文奏英国官商到汉查看地势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9页。
[5]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
[6]《官文奏英国官商到汉查看地势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90页。
[7]《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恭亲王奏》,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1页。
[8]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6页。
[9]赫德:《长江一带商论》,文庆等编《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1页。
[10]宝鋆编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110-111页。
[11]迪安:《中国与英国的商业外交》,第54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12]宝鋆编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111页。
[13]《钦差大臣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奏英美在汉通商各事又俄船办事来汉折》,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75页
[14]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15]《李鸿章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奏》,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朝)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16]具体参见《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代征长江洋税急难筹解折》,《李鸿章全集》(1),奏稿,卷1,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5页;《沈葆祯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奏》,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朝)第一册,北京大学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98页。
[17]《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代征长江洋税急难筹解折》,《李鸿章全集》(1),奏稿,卷1,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18]《李鸿章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奏》,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朝)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67-670页。
[19]宝鋆编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342页
[20]宝鋆编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344页。
[21]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2](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页。
[2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24]文松:《近代海关洋员人数变迁及分布管窥》,《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25]中国海关:《新关题名录》,海关总税务司造册处,1910年。
[26]数据来源自孙修福编译《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199页。
[27]张仲炘等:《湖北通志·志五十·经政八·榷税》,武昌省长公署,民国十年,第13页。
[28]彭建、李笙清:《浅论江汉关的人事管理制度》,《武汉文博》2013年第4期。
[29]参见张仲炘等:《湖北通志·志五十·经政八·榷税》,武昌省长公署,民国十年,第13页。
[30]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庆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202页。
[31](日)水野幸吉:《中国中部的事情:汉口·译者的话》,武德庆译,武汉出版社,2014年,第1页。
[3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33]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0页。
[34]参见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表(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第340-346页。
[35]数据来源于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表(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第340-346页。
[36]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7]参见洪均:《厘金与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
[38]陈勇:“晚清海关税政研究:以征存奏拨制度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年。
责任编校:饶敏
A Study of Jianghanguan Custom in Hubeiof Late Qing Dynasty from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
CHANG Cheng
(Xinxiang 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0,China)
Jianghanguan custom was officially open forbusiness on January 1st,1862.Its construction indicated contemporary customs controlled by foreign powers wedged in Hubeias an emerging politicaland economic force.As a result,the traditional bilateralrelation evolved into a complex trilateralrelation.Jianghanguan custom,as a direct productof Hubei's modernization,was independentofthe whole framework ofthe traditionalmechanism,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its half-colonized leadership,modernized managementsystem and multiple business functions.This new duty-collecting agency,as a modernization product,also turned into the catalystof Hubeimoderniz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accelerating Hubei's modernization pace in late Qing dynasty.Butwith its half-colony and invasion nature,itgradually became a toolofforeign economic entities to exploitChina.
Jianghanguan;late Qing Dynasty;modernization;Hubei
K251
A
2095-7955(2017)01-0048-06
2017-01-18
常城(1987—),河南新乡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