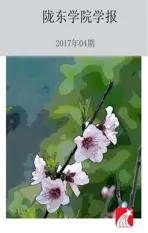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
2017-03-12漆调兰曹应梅
漆调兰,曹应梅
(陇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
漆调兰,曹应梅
(陇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众说纷纭,对其发展演变进程的详细考证和梳理语焉不详。鉴于此厘清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进程是深入研究本论争的关键,有助于更好地揭示论争的现实价值,有助于深刻理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文章以文艺界的反响程度为界,把这一进程分为开启、发展与高潮、继续发展到走向尾声三个阶段,为进一步开展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提供帮助。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民族形式”论争; 发展进程
围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由于一度被认为是文艺界的争论,因此,研究大都限制在文学史和文艺界领域,未能引起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和深度挖掘。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历史上著名的科玄论战和社会性质论战,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规模、议题和影响要逊色很多。但是论争双方涉及到的议题在今看来意义也非同寻常,具有很深的现实价值。正如李泽厚指出:“如果能获得对历史和现实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它的成就和缺陷,也许能使五四的交响乐章重新奏起。”[1]因此,要更好地揭示论争的现实价值,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史和文艺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更需要从党史的角度,对这一论战的发展演变进程进行详细考证和系统梳理,这是深化本论争研究的关键问题。只有这样,方能从错综复杂的文艺论争中厘清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方能正确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引领这场论争的导向作用。同时,能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历史借鉴和有益启发。
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发展进程,众说纷纭。由于处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由于地域性的差异;由于对“民族形式”理解的不同;参加论战的文艺家们关于论争的发起时间和思想内容看法不一,呈现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繁荣景象。
第一,不同地区的论争参与人对开启时间界定不同。如延安的陈伯达、柯仲平和艾思奇等人一致认为,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上的讲话是他们发文的起源。而国统区的参与者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信息传播所致,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如光未然在1940年4月21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座谈会上认为,“民族形式的提出眼看快要一年了,最先是旧形式的利用问题,后来才发展成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2]在他看来,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是由文艺大众化本身发展而来的,具体时间也就是1939年初。而作为当时主持座谈会的主席罗荪,开门见山首先承认了共产党在延安很早提出“民族形式”新命题的事实,同时也指出了国统区重庆论争的刚刚开始。他指出问题“虽然早在一年前就提出来了,但在重庆展开讨论,还是最近不久的事情”[2]。并希望通过召开座谈会,来深入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作为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的李泽厚,认为此次论战主要表现在“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1]。而此书胡风写于1940 年10 月14日晚上,在附记中提到“‘民族形式’问题底被提出,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罢,实际上引起了争论,也已经过了半年以上的时间”[2]。可见,无论是研究胡风的李泽厚,还是在胡风本人看来,论争主要指的是1940年4月开始的“中心源泉”论争。
总之,由于在抗战特殊时期,国统区文艺界人士不可能很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党提出“民族形式”新命题的具体时间,更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共产党的政治意图。因此,国统区的参与者关于论争的开始时间认识都是模糊的,他们说的发起时间,也一般认为是从各自所在地区为开启标志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论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第二,研究者们对论争时间的界定更是纷繁复杂。从目前史料显示,如中文系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室编写的《民族形式讨论纪略》认为,是从1939年到1943年7月;(韩国)金会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形式论争”有关资料目录》则是从1937年的“旧形式利用讨论”开始编写直到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目前收集资料较全的《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中得知,论争时间认为集中从1939年到1942年。当然,后期论争其实也在继续,但不是很集中。还有期刊论文,如最早的刘泰隆认为,“‘民族形式’论争不应当认为到1939年才展开,同时,解放区也不只在延安开展了讨论。”[3]戴少瑶则认为,“论争的时间应该是1939年至1941年”[4]。后来,袁盛勇则提出了“它从193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甚至更后”[5]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石凤珍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较为全面,她对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梳理[6]。总之,以上研究为我们后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基础。
综合以上史料及其研究,笔者认为,以思想文化界的反响程度为界,将时间界定为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发生的集中阶段更具典型性与合理性,即从1938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民族形式”为标志,到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结束点。
一、开启(1938.10——1940年初)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初,是本次论争的开启阶段。为何将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作为开启的标志?为何将此时间段界定为开启阶段?依据有三:
第一,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民族形式”命题。当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民族形式”新命题后,首先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当时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晋察冀边区的《边区文化》等,均相继发表了柯仲平、陈伯达、艾思奇、萧三、罗思、杨松、劳夫、何其芳等人的文章。他们从各个角度肯定了文艺“民族形式问题”提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试图正确阐释“民族形式”的内涵;同时,同文艺上长期进行的“旧形式利用问题”进行了区分,并就“民族形式”与新文艺和旧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正如有学者指出:“大多数讨论者都是以学习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理论为指导,结合文艺界的创作实践,阐述自己对‘民族形式’的认识并努力提出建设性的意见。”[7]
第二,此阶段论争中的各项议题分歧逐渐鲜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延安作为发起地,关于论争的各项议题意见一致。其实不然,仔细研读文本,在如何正确“利用旧形式”;如何正确评价新文艺;如何界定“民族形式”的内涵;各位撰文者中分歧逐渐鲜明。如陈伯达过分强调“旧形式”的主张就是一例,为以后的论争埋下了伏笔。他曾指出:“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就不能拨开广大老百姓年代久远所习惯的民族形式。”[2]这就为后来向林冰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周扬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稍有不同,他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承认旧形式利用的同时,高度肯定了新文艺在历史上的贡献,认为新文艺与大众是“一步步接近的趋向”[2],提出了民族形式之建立的路子就是现实主义,被毛泽东评为“写的很好,必有大影响”[8]。可见,陈伯达、艾思奇与周扬之间在如何看待“旧形式利用”等问题上歧义已很明显。
第三,全国各地的论争拉开了序幕。例如重庆陪都文化界以柳湜1939年4月《论中国化》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他在文中不惜笔墨用了大量篇幅引用毛泽东《论新阶段》的讲话,并指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从而,引起了广大国统区文化界人士对“中国化”思想和“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如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文艺阵地》上发表黄绳《当前文艺运动的一个考察》和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西线文艺》上发表魏伯《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文学月报》上发表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戈茅《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召开了有莫宝鉴、艾芜、鲁彦等人参加的“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座谈会。在香港地区,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召开了座谈会,开辟“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专栏。黄药眠、 杜埃、宗珏、 黄绳、袁水拍等人纷纷著文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人方面以毛起鵕为代表,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反对“民族形式”的口号,并未针对“民族形式”展开全面批判。再者,国民党当局发文甚少。
毋庸讳言,由于当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尤其是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不会被国统区的文艺界人士很快了解,论争一时间不可能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这也是历史的真相。正如茅盾于1940年7月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时指出:“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方才看到的”[2]。具体指的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他的启发,从而写下了《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但像茅盾这样能够从延安地区直接获得关于‘民族形式’口号方面的信息的毕竟是少数,国统区的许多文艺界人士基本上都是在关于‘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激辩中,才对这次论争有所了解。”[9]因此,论战拉开的时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一面也是必然的。总之,以上论争还未形成高潮,仅仅处于开起阶段。因此,将1938年10月到1940年初界定为本次论争的开启阶段,也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正当“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方兴未艾之时,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提出了“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既强调“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又反对“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指出应当“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0]。对于正在开展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又一次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推动了问题讨论的深入。
二、发展到高潮(1940.1—1940.6)
从1940年初到1940年6月,将本次论争界定为从发展走向高潮的阶段,其原因有二:
第一,相比于第一阶段,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延安地区的周扬、张闻天、茅盾和陈伯达等人较之国统区更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在如何评价新文艺等一系列问题方面显得更为成熟,对国统区的影响较大。正如胡风非常赞同周扬“新文艺无论在发生上,在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上,我认为都不但不是与大众相远离,而正是与之相接近的”的观点,指出“这正是非常正确的理解。”[2]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毛泽东《论新阶段》讲话,但是开始的引用,很明显是从讲话中而来,并且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毛泽东“民族形式”内涵的界定“对于一切工作者的能动精神的鼓励”[2]很有启发。
第二,从发文数量和参与人数来看,论争围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在重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将论争推向了高潮。“中心源泉”问题是由向林冰(赵纪彬)首次提出,并连续发文十多篇来阐述自己的见解,认为“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民间形式运用的归宿”,而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只应置于副次的地位”[2]。此种观点引起以葛一虹为代表一方的激烈反对,葛一虹批评向林冰一方“由于认识的错误,终于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2]这是典型的“新的国粹主义”。但葛一虹却又无视旧形式中的精华和新文学本身存在的缺点,一方面对旧形式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继续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艰苦斗争的道路”,是“我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2]。总之,围绕“旧形式运用”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功过等中心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要么过分强调“旧形式的运用”,否定五四新文艺的成果;要么过分强调五四新文艺的成果而否定“旧形式的运用”,将此次论争推向了高潮。
当然,高潮阶段的不足也很明显,那就是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态度;不是一笔抹杀,就是十全十美,无视它本身存在的弱点。而且,纠缠于所谓“中心源泉”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族形式本身的深入探讨。为此,罗荪和潘梓年分别召开了座谈会,来总结论争的不足。正如以群指出:“自从民族形式提出,到现在为止,一直停留在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问题上了,现在应该把这一问题向前拉一步,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讨论”[2]。这为高潮过后论战的继续发展留下了可讨论的空间。
三、继续发展到走向尾声(1940.7—1942.5)
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2年5月,也就是到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前,界定为从继续发展走向尾声阶段,原因有四:
第一,延安文艺界的小争论从未间断,论争更趋复杂化。在延安文艺界,围绕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等问题的小论争一直存在。诸如“鲁艺”与民众剧团之间关于普及与提高的争论;以丁玲、王实味一方的暴露与以周扬、周立波和何其芳等主张光明的一方的争论;宗派主义的问题等等,都可看作是“文艺民族形式论争”议题范围内的小论争。同时,论争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如王实味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将他与陈伯达的分歧进一步深化;而且又一次引发了国统区的论争,防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民族形式的再提起》,对王实味的文章进行了批评。
第二,一系列高质量文章的诞生。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以及胡风《论民族形式底提出和争点》等人的文章,对论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总结与思考。如茅盾对向林冰“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驳,并提出了“民间形式中的某些部分(不是民间形式的某一种,而是指若干形式中的某些小部分),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可以作为建立民族形式的参考,或作为民族形式的滋养料之一”[2]的观点。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2]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一文对前期的论争做了总结,认为前期的论争“仅仅只抓住了一个‘形式’,完全忘掉了或者抽掉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11]因此,胡风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通过科学的世界观所理解的民族的现实。”换言之,“对象是民族的现实,方法是现实主义。”[11]基于如此认识,他对“民族形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民族形式’,不能是独立发展的形式,而是反映了民族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11]总之,他们在论争继续发展的讨论中,深化了对“民族形式”的认识,认为民间形式可以作为养料;但是“民族形式”必须反映民族的现实,不能仅就形式谈形式。
第三,以田间和左唯央为代表的论争在晋察冀边区掀起的热烈讨论。田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仍然是彻底反驳向林冰“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说,同时,更加深刻地批评“大后方一部分人一做起‘通俗运动’或‘通俗化’,便毫不考虑地举起‘旧形式’”[2]的事实,认为这是符合向林冰论调的做法。针对田间的观点,左唯央提出了异议,认为“以为利用旧形式就是‘近似’‘倾向’和‘符合’向林冰和‘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调,而企图以与向林冰同等的罪名粉碎之,则未免过于武断,自己走错了路。”[2]。可见,左唯央支持周扬的观点,反对田间不利用旧形式的观点。从本质观点上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田间和左唯央之间的继续论争,与前期要不要“利用旧形式”的分歧有关。
第四,国民党的文化人围绕论争进行了集中攻击。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国民党的文化人没有对此次论争明确表态的话,这一时期有孙伏园、郑学稼、唯明、严明对此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与挑战。国民党文化人严重挑战“民族形式”的论争,显然是国统区论争进入到了尾声时期。这是因为在国统区,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文学月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新蜀报》等报刊,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所以他们极力毁谤。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国民党文化人以及论争中的各种错误思想以有力的回击,正确引导了文艺运动的发展走向。同时,也标志着大规模的论争走向了尾声。
四、结语
谈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展演变进程,共约三年多的时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程,从1938年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民族形式”新命题并做了内涵界定,随即引起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作为开起;到1940年前半年围绕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的激烈讨论,使论争从发展走向了高潮;从1940年后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2年上半年,是论争的继续发展到走向尾声阶段。根据文艺界人士的反响程度,对这一论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更好地体现了“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是一次文艺界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文艺的实践活动,凸显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为深入研究“文艺民族形式论争”以及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88,76.
[2]徐迺翔主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06,205,392,5,131,297,389,254,158,183,182,272,347,265,451,457.
[3]刘泰隆.试谈“民族形式”论争的评价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1):37-53.
[4]戴少瑶.“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1-17.
[5]袁盛勇.“民族形式”论争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J].宁夏大学学报,2003,25(5):49-54.
[6]石凤珍.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75 (3):45-50.
[7]廖超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977.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59.
[9]罗维斯.民国视野下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区域特征[J].新文学评论,2013(1):121-130.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11]胡风.胡风评论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4:257.
【责任编辑 朱世广】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yle” in 1930s and 1940s’ Literature and Art
QI Tiao- lan,CAO Ying- mei
(School of Marxism,Longdong University,Qingyang 745000,Gansu)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yle” in 1930s and 1940s’ literature and art.There isn’t any clear hint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argument.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yle” in 1930s and 1940s’ literature and art is the key points of this paper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vealing of the real value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The paper divides the course into proposition,development and peak three parts which continues to the further study on the “National Style” argu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1930s and 1940s;“National Style”;development
D23;I209
A
1674- 1730(2017)04- 0063- 04
2016- 12- 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研究》(13BKS017);甘肃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法治与德治融通的大学生管理方式研究》 (GS[2015]GHB0939)
漆调兰(1983—),女,甘肃天水人,讲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