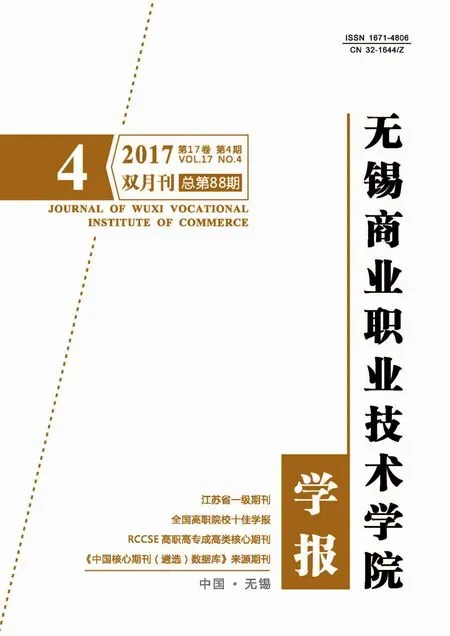从影响的焦虑看第三代诗对朦胧诗的超越
2017-03-11孙元元
孙元元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文史哲研究】
从影响的焦虑看第三代诗对朦胧诗的超越
孙元元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哈尔滨,15008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朦胧诗以启蒙、反思、诘问的姿态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和历史价值,对稍迟于其出现的第三代诗而言,它是当之无愧的前驱。根据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这一诗歌理论,第三代诗作为迟来者对朦胧诗产生焦虑便成为一种必然。对此,第三代诗采取“克里纳门”“苔瑟拉”和“魔鬼化”三种“修正比”进行超越,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却建立起一套独有的诗学观念,成功实现了超越。
朦胧诗;第三代诗;影响的焦虑;超越
美国诗歌理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著作《影响的焦虑》中提到:“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开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诗的历史。”[1]5而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则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誓死不休挑战的诗坛主将们”[1]5。可见,前代诗人对迟来诗人投下巨大阴影,并引起他们寻求超越的焦虑心理和切实行动。对此,布鲁姆运用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和尼采的超人意志论,将迟来诗人试图超越前代诗人所采取的诗歌手段归结为六种“修正比”,即“克里纳门”或诗的误读、“苔瑟拉”或续完和对偶、“克诺西斯”或重复和不连续、“魔鬼化”或逆崇高、“阿斯克西斯”或净化和唯我主义、“阿波弗里达斯”或死者的回归。其影响深远,应用广泛,为诗歌批评开辟了新的维度。根据这一理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浮出历史地表的朦胧诗在一片毁誉参半的评价声中以诘问、反思、启蒙的姿态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成为新时期诗坛上最令人瞩目的新星,对稍迟于其出现的第三代诗而言,它是当之无愧的前驱。因而,第三代诗对朦胧诗产生焦虑便成为一种必然,而第三代诗在诗歌理念、精神向度和审美内涵等方面完全迥异于朦胧诗的追求,体现了它超越的意图。
一、“克里纳门”:时代的转向
根据布鲁姆的阐释,“克里纳门”原指物理学中可能使宇宙产生某种变化的原子的偏移,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意味着迟来诗人偏移他的前驱而采取的矫正行为,即“前驱的诗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应沿着新诗作运行的方向偏移”[1]14。第三代诗便是对朦胧诗发展方向的偏移,这是它在焦虑心理驱使下的自觉追求,也是时代转向这一外因起作用的结果。借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观点,“认识虽是主体以其认识结构对外物进行同化,但客体也反作用于主体,随着对外物认识的发展,人的认识结构也继续重组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2],可见外部环境对认识的影响。
以北岛、芒克、食指、多多、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是十年动乱的亲历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无疑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他们被极权话语欺骗,多参与过“上山下乡”运动,经历了“革命式求索—命运式感伤—自我分裂式质疑、嘲弄、反叛或者逃逸—人道主义批判”[3]四种生命体验流程,是政治斗争中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但在当时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人人自危成为一种常态,他们虽有质疑却不敢公然反抗,只能将一腔苦闷、不满和抱负寄托于“地下诗歌”创作,表现出一种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高屋建瓴的精英意识和重开民智的启蒙姿态。在本质上,朦胧诗依然是一种宏大叙事,与政治话语的紧密缠绕是其明显的特点。服从于这种内容和情绪宣泄的需要,雄辩、诘问、抒情、宣告等艺术手法是朦胧诗常见的形式,表现为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自觉承续。如“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等诗句都是通过激情澎湃的宣誓口吻来表达诗人们的政治理想。它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填补了“文革”时期的文学空白,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真实面目和最高成就;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它的先锋姿态对亟待思想解放的历史转折时代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或者说,它是诗歌在那个特殊年代呈现出的必然形态,是“方向端正不偏不倚”[1]14的。而与朦胧诗的发生语境不同,第三代诗兴起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时,商业化大潮席卷一切,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进程加快,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有所滑落,读者的文学想象也相应发生变化。此外,以韩东、于坚、李亚伟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多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十分模糊,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而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对“纯文学”“纯诗”的追求成为文学界的趋势之一。这种追求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既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长久被政治话语束缚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文学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存在状态成为新的关注点。于是,第三代诗应运而生。从表面上看它是新生事物对传统秩序的反叛和决裂,但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时代精神和文化选择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谢冕先生认为,诗歌“在所有的文学艺术样式中最先、最丰富也最全面地保留了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情感的投影”[4],所以第三代诗人喊出“Pass北岛”“打倒舒婷”等激进口号和对平民立场、世俗关怀及日常话语等诗歌品格的追求并不突兀,是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使然。如“他天天骑一辆旧‘来玲’/在烟囱冒烟的时候/来上班”(于坚《罗家生》)、“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于坚《尚义街六号》)等诗都是对日常场景的描摹,与朦胧诗的宏大叙事相比,有着鲜明的个人化叙事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代诗否定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它“恰恰是在吸饱了北岛们的汁液后,渐渐羽毛丰满别具一格的”[5],只不过时代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诗歌想象理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偏移”。所以,第三代诗是借着时代转向的“东风”完成了对朦胧诗的“偏移”,使当代诗歌沿着新的方向继续发展。
二、“苔瑟拉”:对“人”的续完
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五十到七十年代的诗歌多是政治抒情诗,有着鲜明的写实和叙事倾向,文学的社会功能达到极致。与此相应,诗人多以阶级和社会集团代言人的身份进行创作,独立的情感、意志和思考被压抑,在泛政治化的艺术追求中泯灭了个性,失真、浮夸、单调成为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随着“文化大革命”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和批判的“灰皮书”“黄皮书”等内部读物流落到青年学生手中,这些禁书中的人道主义光芒照亮了他们被政治话语遮蔽的精神角落,“催化了他们的精神核裂变”[6],使他们告别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在多难却充实的精神漫游中回归到“人”本身。作为这些青年学生中的一员,蛰伏于地下的朦胧诗人从极权话语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抛弃了五十到七十年代诗歌服务于政治的艺术追求,以独立思考的方式进行创作,将“人”视为世界的主体,将自己视为“人”的价值的发现者和追求者,在诗歌中真实地表达着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如北岛的“我不相信”(《回答》)和食指的“相信未来”(《相信未来》)都是将自己化身为真理的发现者,率先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和希冀;舒婷的《致橡树》借木棉树的口吻表达了对理想爱情的渴望,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形象随之诞生;芒克的诗歌《雪地上的夜》将夜晚比作狰狞凶狠的狗,暗指那个吃人的黑暗时代,但“我”在它的面前没有畏惧,而是“愤怒地朝它走去”,呵斥它“从这里滚开”,塑造了一个勇敢无畏的抗争者形象。总之,朦胧诗重新发现和宣扬了“人”的价值,是对“五四”精神的断代衔接,有着划时代意义。
毫无疑问,朦胧诗对“人”的发现及其带来的意义成为第三代诗的焦虑。对此,第三代诗采取了“苔瑟拉”的方式进行超越。根据布鲁姆的阐释,“苔瑟拉”即“续完和对偶”,“是一种以逆向对照的方式对前驱的续完,虽保留前驱诗的词语,但使它们别具他义,仿佛前驱走得还不够远”[1]15。朦胧诗虽然重新发现了“人”,但这种发现却并不彻底。或者说,朦胧诗自觉为一种被压抑的政治话语代言,在“人”身上赋予了太多的理想和期望,是被抽象化和本质化了的“人”。如舒婷在《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运用数节排比句式,在抒情主人公“我”身上赋予了“老水车”“矿灯”“花朵”“胚芽”“笑涡”“起跑线”等众多意象,淹没了“我”的本来面目,使“我”不堪重负;而且希望祖国“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取得“富饶”“荣光”和“自由”,强烈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使“我”仅作为表达理想的代言人而存在,并无更多本体特征。再如杨炼的《大雁塔》,将“我”化身为大雁塔,诉说着历史沧桑和时代创痛,也是对“人”的抽象化表现。而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这种被抽象、拔高和负担了太多使命的“人”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说朦胧诗是对五十到七十年代诗歌的松绑,那么第三代诗则将诗歌从为政治话语服务的囹圄中彻底解救出来,使诗歌真正拥有了“纯文学”的品格。和朦胧诗一样,第三代诗也表现“人”,但却“别具他义”[1]15,使“人”真正回到人本身,以此证实“前驱走得还不够远”[1]15。它卸下“人”身上沉重的理想枷锁和道德镣铐,也抛弃了将客观事物“人化”的冲动,它客观真实地表现“人”,还原“人”的本来面目和“人”的日常生活,是对朦胧诗中的“人”的续完。如于坚《尚义街六号》中的老吴、于坚、老卡、朱小羊、李勃、费嘉等人和《作品第52号》中那个“屁股上拴串钥匙/裤袋里装枚图章”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真实再现,他们从云遮雾罩的理想和使命中走出来,庸碌而平凡地生活着,拥有了人间的烟火气,是真实可感的。吕德安的诗《父亲和我》描绘了“我”和父亲在雨中漫步的场景,“我们”因为长久生活在一起的缘故,虽然“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但彼此心中却都“怀着难言的恩情”,表现出最为质朴也最为温暖的人间亲情,使潜藏在“人”心中最细腻柔软的情思分毫毕现。李亚伟的《酒聊》则写在酒精的作用下,“我”的身体产生了一系列生理反应,如“我想离开自己/我顺着自己的骨头往下滑”等等;同时还有精神上的恍惚和错觉,“我是喝掉什么啦/长江以南/已然空空如也”,一个立体感十足的醉汉形象随之诞生,表现了“人”在醉酒之后的真实感受。可见,第三代诗中的“人”或平凡或粗俗,或温情或癫狂,但正是这种世俗化特征使“人”的最本真形态呈现出来,是对“人”的深度发现和挖掘,以“逆向对照的方式”[1]15对朦胧诗中抽象的“人”进行续完,实现了超越的意图。
三、“魔鬼化”:消解崇高
罗振亚先生认为:“面对‘第三代’诗歌的现状,我们无法不承认,寄居在传统诗歌中几千年的崇高感业已被残酷地消解了。”[7]这种消解崇高的叙事策略正是布鲁姆提出的六种“修正比”中的一种——“魔鬼化”,是“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1]15,“它把前驱得来不易的一切胜利交回到‘魔鬼化’世界,从而削弱前驱者的人性光芒”[1]111。
首先,从创作动机来看,朦胧诗人认为生活并不完美,现实是残缺的,他们希望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建构一个理想世界,以弥合生活的裂隙。基于这种艺术理想,崇高与优美自然成为朦胧诗的美学追求。如“但愿我和你怀着同样的心情/去把道路上的黑暗清除干净”(芒克《十月的献诗》),“理想之钟在沼地后面敲响/夜那么柔和/让我同我的诗行随我继续跋涉吧”(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等诗都表现出诗人们崇高的民族使命感和对真理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而第三代诗人则直面现实的不完美,正视生活的淡然凡俗,他们乐在其中,使诗歌呈现出一种与朦胧诗的崇高美截然相反的俗美特征。如“混一天/脚丫气味不佳不必不安/明天也许时来运转/可以用扑克牌试试/最悲哀的是这一脸疙瘩/脸蛋像一座青春的公墓”(丁当《临睡前的一点忧思》)就表现出一种对生活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懒散态度,朦胧诗中光芒万丈的远大理想早已在“不佳”的“脚丫气味”中化为乌有。
其次,在朦胧诗中被神化了的人或事也在第三代诗中被打回原形。如父亲和母亲在朦胧诗中多是高大伟岸和纯洁无私的神一样的存在,这使“我”不敢“惊动”他们的“安眠”(舒婷《呵,母亲》)。而在第三代诗中,“我”和父亲可以平等地“并肩走着”(吕德安《父亲和我》),将高高在上有着规训意味的父亲和母亲的形象还原为凡人。在李亚伟的《中文系》一诗中,本应严肃刻板的教授变成了“屈原的秘书”“李白的随从”,骑着自己“嘀嘀咕咕吐出的气泡”在中文系这条河流上“撒网”或者“巡逻”;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拥有许多忠于他的“寡妇和三姨太”。类似的诗歌还有尚仲敏的《卡尔·马克思》、程军的《赠卢梭》、梁晓明的《读鲁迅书》等,都是运用戏谑和调侃的方式将人们尊崇的偶像做淡化处理,使他们拥有了人情味和生命活力,消解了朦胧诗中那些扁形人物的崇高性。第三代诗还对朦胧诗中崇高的爱情等人类情感做淡化处理。如于坚的《给小杏的诗》,“小杏/在人群中/我找了你好多年/那是多么孤独的日子/我像人们赞赏的那样生活/作为一个男子汉/昂首挺胸/对一切满不在乎/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能拉开窗帘/对着寒冷的星星/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分/有时候/我真想惨叫”,通过对自我的无情解剖,表现出世俗爱情残酷的一面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被动、无助和妥协,构成对以舒婷《致橡树》为代表的朦胧诗中的理想爱情的消解。
再次,与朦胧诗通过意象来内敛含蓄地表情达意不同,第三代诗中的意象只是意象本身,没有更多的附加意义。最常被拿来对比的是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杨炼将大雁塔“人化”,使它以一个孤独崇高的思考者形象出现,通过它的视角和口吻表达自己对时代和历史的观照,而韩东认为大雁塔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物,人们能做的只是“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除此之外不能知道更多。此外还有“大海”“土地”“太阳”等在朦胧诗中被讴歌、赞美的意象也在第三代诗中被完全颠覆,如“你见过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韩东《你见过大海》),大海不再是被讴歌和赞美的对象,也不是诗人们实现理想、考验意志的搏击场,大海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物,甚至还有着骇人的一面,消解了朦胧诗中“大海”的崇高形象。杨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中的“沙漠”“纸牌”以及“纸牌”之间的排列顺序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是为存在而存在。第三代诗对意象的客观呈现正如布罗茨基在《蝴蝶》一诗中描绘的那样,“写出的一行行诗句/毫无意义”[8],然而这正是它超越朦胧诗的一种手段——以无意义消解意义。
最后,第三代诗还从形式上消解崇高。幽默、俏皮、不严肃、无厘头是第三代诗的显见特点,在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山民》、孟浪的《牺牲》等诗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而这种风格又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他们标举“诗歌从语言开始”[9],“诗到语言为止”[10],使诗歌写作“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11],将诗歌还原为纯粹的文字游戏,并进一步将其俚俗化,如“我顺着自己的骨头往下滑/觉得真他妈有些轻松”(李亚伟《酒聊》),“南京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上海王寅呼南斯拉夫同志们太他妈的能说会道了”(夏宁《他们》)等诗都是以污秽、粗鄙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平民精神和对世俗生活的由衷热爱,消解了朦胧诗庄重、严肃、崇高的语言风格。在诗行的排列上,第三代诗也煞费苦心。如“从屋子里走出来的人/像一根根被抛弃/火/柴/太炎热了——它说/需要/一种恬/静”(杨黎《中午》)就是故意将句子截断,纵向拉长,通过蹩脚和陌生化的外在形式消解了中规中矩、整齐排列的朦胧诗行。
四、结语
第三代诗通过对前驱朦胧诗的“克里纳门”“苔瑟拉”和“魔鬼化”运作,成功地建立起一套独有的美学观念、文化模式和诗歌走向,其表达方式平和亲切、贴近人性,其表现内容通俗但不庸俗,更本质地接近了生活的真实状态,更彻底地还原和表现了“人”,呈现出洗尽铅华的诗歌本色,也使读者从云遮雾罩含混多义的“朦胧”氛围中解脱出来,在一览无余的诗歌风景中畅快呼吸,产生共鸣。虽然它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如对语言的过度崇拜淡化了诗歌应有的表意性和表情性,使诗歌情感冷漠、诗意苍白以及误入形式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等,但总体而言,它对朦胧诗的突围是成功的,它使诗歌的艺术范式和精神向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乃至今天中国文学的走向,不仅实现了超越的意图,也确立了自己相对于其后出现的诗歌流派的前驱地位,使它们也产生了影响的焦虑。
[1]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皮亚杰.发生认识论[M].范祖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
[3]张志国.中国新诗传统与朦胧诗的起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222-234.
[4]阎月君,等.朦胧诗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2.
[5]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57.
[6]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5.
[7]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3.
[8]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M].王希苏,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260.
[9]尚仲敏.内心的言语[M]//非非年鉴.成都:中国非非主义诗歌实验室,1989:10.
[10]韩东.自传与诗见[N].诗歌报,1988-07-06(04).
[11]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M].黄正东,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15.
(编辑:张雪梅)
Anxiety of Influence—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ry’s Transcendence over Misty Poetry
SUN Yuan-y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1970s and the early 1980s,misty poetry obtained its legal status and historic value by means of enlightenment,introspection and interrogation,which is the genuine vanguard as far as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ry is concerned.According to Harold Bloom’s theory of anxiety of influence,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s as successors would certainly have anxiety about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their precursors.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ry,by adopting the three revisionary ratios—Clinamen,Tessera and Daemonization,surpassed its predecessors’poems and constructed its unique poetic theory though it paid a price.
misty poetry;The Third Generation Poetry;anxiety of influence
I 106.2
A
1671-4806(2017)04-0098-04
2017-03-23
孙元元(1992—),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