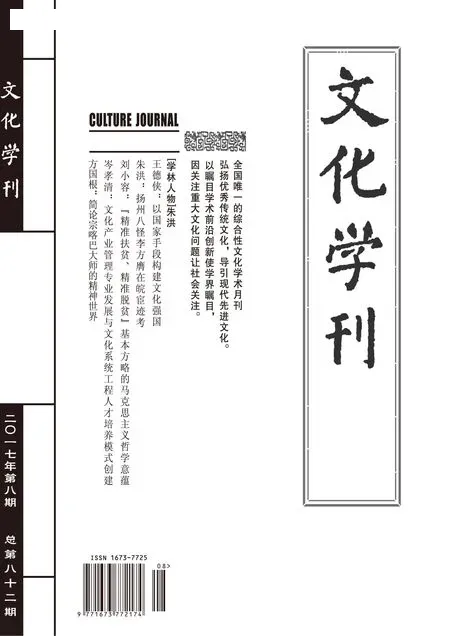唐五代敦煌寺院仓司研究
2017-03-11谢慧娴
谢慧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文史论苑】
唐五代敦煌寺院仓司研究
谢慧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唐五代时期,寺院经济高度繁荣,财力雄厚的寺院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渊源于佛教教义以“供养三宝”的“仓”的职能逐渐拓展,成为寺院的财产出纳机构和面向社会的借贷机构。“仓司”作为“仓”的执掌机构,设置了分工明确的僧职,逐年轮换,并受到全寺僧众的监管。仓司进行的放贷活动,展现出宗教与世俗交织的复杂性。
唐五代;敦煌;仓司;寺院经济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寺院逐渐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结合,这不仅体现在脱胎于封建官僚体系的僧官制度上,也表现在寺院通过占有土地和控制农民,发展起了独特的寺院经济模式。佛教寺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寄生于政治权利和民众信仰之间的供养体系。而“仓”作为这一体系重要的一环,其职能亦随着寺院经济的触角逐步扩张。从最初存放什货杂物的仓房变为管理寺院收纳和民间借贷的中枢机构,“仓”的职能扩展反映了佛教寺院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谋求世俗利益的过程。唐五代时期,“仓”的经营管理逐渐制度化,“仓司”作为仓的执掌机构,不仅管理仓的出纳,也作为寺院的财产管理机构,直接从事经济活动。
一、仓司的设置和职能
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财力雄厚,建立起仓库对寺院财产和粮食进行统一管理。都司在灵图寺设置“都司仓”[1],并通过都司仓进行放贷活动。本文探讨的“仓司”是各寺院下属的对仓库进行管理以及进行相关经济活动的机构。分析现存的敦煌文献得知,至少永安寺、净土寺、报恩寺、灵图寺、金光明寺等寺院设置了仓司。而且,一个寺院如果有多个仓库,那它就有可能存在多个仓司。如P.4694《年代不明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以及S.1519《某寺入破历》中记载某寺有“南仓司”;P.2032号背《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记载净土寺有“西仓司”。
P.3223《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责勘状》[2]记载了永安寺仓司执仓绍建与法律愿庆借贷寺仓谷麦发生的冲突,是帮助我们了解仓司职责及管理人员的重要史料。郝春文先生根据文书的第22行“提招余者,皆例无分”,认为仓司执掌寺院的提招僧物,并进一步判断仓司又被称为常住仓司或招提司,而且沙州寺院应该都有仓司或招提司。[3]实际上,虽然仓司也是常住仓司,但仓司与提招司并不能完全等同。佛典中对常住僧物与招提僧物有着严格的区分,《大宝积经》中称:“常住僧物不应与招提僧物共杂,招提僧物不应与常住僧物共杂。”[4]而且据S.1600(1)《庚申年十二月十一日至癸亥年灵修寺招提司典座愿真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稿残卷》第5行载:“施及官仓佛食、阇梨手上领入、常住仓顿设料”[5],表明常住仓是灵修寺提招司的收入来源之一,说明招提司与常住仓司并非同一机构。
仓司主要管理寺院仓库的粮食并经营相关的出纳、借贷活动。谷麦、豆、黄麻等都是仓司的主要管理对象。P.3223第15行“仓内谷麦”可知,永安寺仓司管理的主要是寺院仓内的谷麦等粮食。S.4701《庚子年(公元940年)十二月十四日报恩寺前后执仓法进惠文愿盈等算会分付回残斛斗凭》中也着重记载了仓司中麦、豆、粟、黄麻等粮食的情况。据此可知,寺院仓库的粮食管理是仓司的工作重心。然而P.3223中还说道:“年年被徒众便将,还时折入干货”,即寺院僧徒从仓司中借谷麦,归还时则常常以“干货”按一定比率进行折算归还入仓,“干货”即布、绢等织物[6],所以除了管理粮食外,仓司还管理着一定数量的布、绢等织物。值得注意的是,仓司并不仅仅是负责寺院仓库粮食的存储,P.3223《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责勘状》中记载的“昨有法律智光依仓便麦子”和“官中税麦之时,过在仓司”,说明仓司还进行粮食借贷活动,并负责向都司或者官府纳粮。
仓司的管理者一般是被称为“执仓”“把僧人”或“执物僧”的职事僧。P.3223中的老宿绍建称自己为仓司“执仓”,是永安寺仓司的负责人。S.4701号文书第2行“先执仓常住仓司法律法进、法律惠文等八人所主持斛斗”,文书后有“执物僧”愿盈等八人押[7],与前文常住仓司的八位执仓相对应。这样看来,“执物僧”为“执仓”的异称或俗称,是仓司中担任相同职务的管理者。由于仓司管理的物品种类较多,对于仓内较重要或数量较多的物品可能会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如“执黄麻人”就是专门管理仓内黄麻的人员,“把麦人”就是专门管理仓内麦子的人员。
仓司管理者为一年一轮换,上届职事僧和下届职事僧之间可进行交接工作。P.3290《己亥年(939年)十二月二日某寺算会分付黄麻凭》载:“先执黄麻人法律惠兴、寺主定昌、都师戒宁三人手下主持人换油黄麻,除破外,合回残黄麻肆拾伍硕贰斗伍升壹合,并分付与后执仓黄麻人徐僧正、寺主李定昌、都师善清三人身上讫。一一诣实,后算为凭。”[8]文书中记载的是仓司中新旧“执黄麻人”之间的轮换。其过程大致为:统计旧执黄麻人任期满后的黄麻数量—进行交接—新任职事僧画押确认交接工作完成。S.4701号文书在确认先执仓任期满后所剩的麦、粟、豆和黄麻数量后,还记到,“惠兴等三人身上欠黄麻三硕二斗二升”“善清等三人身上欠黄麻两硕三斗五升”,此记录即为P.3290中新旧两任“执黄麻人”的债务,那么此时应该是“旧执黄麻人”已经任满之时。从时间上来看,P.3290号文书的算会时间为公元939年12月,S.4701号文书的算会时间为公元940年12月,时间相差整一年。另外,S.4701号文书第3行“从去庚子年正月一日入算后”说明当届执仓是从去年(庚子年)开始担任仓司的工作,到年底与下一任执仓交接工作。种种材料证明,仓司的轮换制度是每年通过算会进行新旧任职事僧的交接,实行一年一轮换的制度。
二、寺院仓司的放贷活动
寺院或僧尼的出贷行为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出现[9],到了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的借贷更加活跃,在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寺院仓司的放贷行为已屡见不鲜。都司仓以寺户和寺院为放贷对象[10],而寺院仓司放贷对象的构成则显得相当复杂,不仅有寺院僧尼、寺户、普通百姓,甚至还有官员,以普通百姓为主要群体。对P.3234背、S.5873背+8567缀合、S.6452(4)、S.6452(6)几件仓司便物历所载的借贷人信息进行统计,发现其中百姓有112人之多,占总人数的84%。但是,通过分析现存的文书发现,这些在仓司进行借贷的百姓具有明显的特点。
P.3234背《甲辰年(公元944年)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第46-50行:“张儒通便黄麻贰斗,至秋叁斗。(押)王都头外甥;米里久便黄麻叁斗,至秋肆斗伍勝。(押)米胡男;行者张建子便黄麻陸斗,至秋玖斗。(押)住在慶子禅师院;安擖便黄麻贰斗,至秋叁斗。(舍在寺前);邓定子便豆肆斗,至秋陸斗。(押)骆驼官男。”借贷者“押”之后的备注常常是借贷者的住址、有名望的亲属或担保人。这是仓司为了确认借贷者偿还能力的常见方式,或者说是仓司对借贷者的一种实际约束手段。不能给予仓司信任感的人一般不能得到寺院的借贷支持。相比起因土地牵绊而较易受约束的农民,工作地飘忽不定的工匠一般不是寺院仓司的借贷对象。在出便人名单中,借贷者为工匠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例。据P.3234背载,71名借贷者仅有“史都料”[11]一名工匠得到了寺院的借贷;S.6452(4)《壬午年(公元982年)正月四日诸人于净土寺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共四十名左右的借贷者,其中也仅有一名“皮匠”和一名“金银匠”借贷成功。
总览敦煌文献中的寺院仓司便物历,以及入破历算会,粟和麦无疑是出现得最为频繁的物品,其次为豆、黄麻*敦煌文书中的黄麻多指黄麻籽,用途为榨油,经常以“斗”和“升”作为其计量单位。和油,都是百姓维持生活必不可少的。从借贷时间来看,百姓向仓司借贷的时间并不固定,主要集中在二月。二月正是粮食相对短缺的时候[12],而且百姓还有可能面临官府的临时抽征[13],生活异常困难。仓司对百姓实行的借贷活动能够及时地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
从放贷利息上看,仓司放贷最高收取50%(二月借八月还)的利息,最低为10%。由净土寺仓司的借贷活动来看,公元944年以50%的利息放贷,参照其他寺院仓司的放贷情况,50%的利息应该是当时各寺院仓司通行的利息标准。到了公元982年,净土寺的放贷利息降低为30%,说明仓司借贷的利息呈逐渐降低的趋势。换算为月息,寺院仓司放贷的最高月息为8%,最低不足2%。
唐五代敦煌的借贷利息存在官民两套系统[14],相比起民间私人借贷,寺院仓司的借贷利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较低且稳定;而相比官方粮仓放贷,寺院仓司的借贷又显得更有效率且储备充足。民间借贷利息与官方规定的借贷利息有着较大出入。民间私人借贷往往可以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如粮食供需状况等因素来决定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利息通常由贷方决定,借方缺乏主动权,于是高利贷大行其道。北图收字43号背《唐天复九年(909)十二月二日杜通信便粟麦契》中有“粟两硕,至于秋四硕”的记载,由此可知利息为100%。当然,100%的利息借贷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私人借贷利息,因为利息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贷方自由决定。有时民间私人借贷利息甚至可达“数倍之息”,“利贷一斗而偿四斗”[15]“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16]等情况屡见不鲜。
9至10世纪的敦煌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7],对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再加上战事频繁,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政府专门设置用来赈济百姓的义仓似乎并没有发挥其功能。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工部尚书孙平上书建议“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18],用于救荒赈贷的义仓由此正式建立。唐代义仓在太宗、玄宗、文宗三朝的灾荒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但义仓粟在后来逐渐赋税化,演变成了地子,不但没有为百姓解决困难,反而成了一种沉重的赋税负担。敦煌文献中未见义仓对民众赈济的相关内容,更多记载的是正仓的借贷活动[20]。S.247V《辛巳年(981年)十月三日勘算州司仓公糜解斗前后主持者交过分付状(稿)》是研究官方正仓借贷活动的重要文书。这件文书是归义军时期州司仓前后两任负责人的交接手续,文书中第7-8行“利麦贰拾玖硕肆斗壹升叁合陆勺捌硅粟壹伯叁拾叁硕贰斗肆升伍合”,其中的“利”字就说明了州司仓进行有息放贷的活动,但文书中并没有说明正仓的放贷利息。按照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杂令》中“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的规定[21],暂且认为此处放贷的月息不超过6%。
官方粮仓放贷更大的问题在于储备不足及效率低下。S.5945《丁亥年(公元987年?)长史米定兴于显德寺仓借回造麦历》中长史米定兴连续两次向寺仓借贷100硕和19硕,应是官府向寺院借贷用以周转,由此可知官仓的储备还不如某些寺院仓库的丰富。另一方面,“官吏漠视民情,赈贷缓不济急,所给减于所需,甚或惜而不肯与。”[22]种种原因,使得百姓有时不得不选择向民间私人借高利贷或向寺院借贷。
利用寺院三宝物进行放贷,并将其获利物用于供养三宝符合佛教内律的规定,因此寺院仓司的放贷行为是佛教内律允许的。仓司的放贷行为是寺院高利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寺院牟利不少,相较于官方放贷和民间私人放贷,寺院仓司放贷活动凭借其稳定性、高效性和丰富的粮食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救济了普通百姓。
三、结语
根据敦煌文书中的记载不难看出,佛教寺院在中古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一方面被赋予一定经济能力的寺院分担了政府在慈善救济方面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寺院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不仅有自己的收支体系,而且还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正如谢和耐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承认,如果中国经济的一般形式在5-10世纪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归于佛教。”[23]作为寺院财货收支的中枢机构,“仓”,以及它的主管机构“仓司”,无疑是佛教寺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通过梳理仓司的经济行为特别是放贷情况可知,一方面佛教寺院通过放贷活动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寺院也通过借贷活动行使着一定的社会义务,展现出了宗教与世俗的复杂性。
[1]田德新.敦煌寺院中的都头[J].敦煌学辑刊,1996,(2):123-127.
[2]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310.
[3][6]郝春文.P.3223《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责勘状》及相关问题考[A].郝春文敦煌学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9-90.93.
[4]菩提流志,编译.大宝积经(第113卷)[M].上海:上海佛学书局,2004.382.
[5][7][8]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527.400.346.
[9]魏收.魏书(第11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7.3041.
[10]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5.59.
[11][14][22]罗彤华.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3.237.155.
[12]董诰.全唐文(第2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4.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72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4.
[15]董诰.全唐文(第86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904.
[16]李昉.太平广记(第43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23.
[17]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33.
[18]魏征.隋书(第2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7.684.
[19][20]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47.
[21]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430.
[23]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M].耿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7.
【责任编辑:周丹】
K242;K24
A
1673-7725(2017)08-0231-04
2017-06-05
谢慧娴(1993-),女,重庆人,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