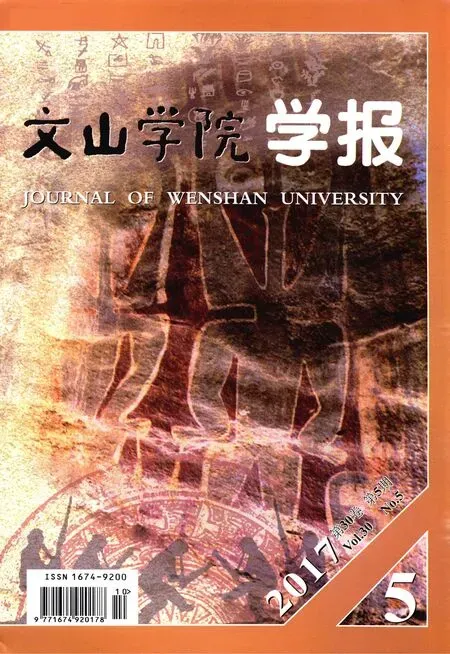浅论“性情渐隐”
2017-03-11孟娟
孟 娟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浅论“性情渐隐”
孟 娟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评刘宋诗歌的发展状况,谓“诗至刘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认为诗歌发展至刘宋时期,在“性情”方面呈渐隐趋势。以“性情”一词论诗,始于《诗大序》,诗歌创作中的“性情”,主要侧重于诗歌的情感表达方面,不过从《诗大序》到南朝诗歌,“性情”的含义也是有所变化、日渐丰富的。通过对“性情”含义的演变过程作简单梳理,从含义和原因两个方面对刘宋诗歌的“性情渐隐”进行探究。
性情;性情渐隐;含义;原因
一、“性情渐隐”的含义
《诗大序》曰:“……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1]在这里,诗歌“吟咏情性”的作用是“风其上”,当时的诗歌只是政治附属品,所谓的“情性”仅仅指对“人伦之废”和“刑政之苛”的感伤。钟嵘在《诗品序》开端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2。文学发展到南朝,已经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诗歌的作用自然也不再是为政治服务,这里的“性情”显然和《诗大序》中的“情性”有着不一样的含义,指的是人自然产生的情感。故而“性情”一词,从《诗大序》到《诗品序》,其含义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最早对“性情”一词作出释义的是东汉班固《白虎通》一书,把“性情”释为一个人的本性和其所持有的情感。书中设立《情性》篇专论“性情”,《情性》篇载:“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六情者,何谓也?喜怒哀乐爱恶谓六情。”[3]在这里,“性情”一词是被割裂的,“性”被释为“仁义礼智信”,即古代所谓“五常”,也即一个人的本性;“情”被释为“喜怒哀乐爱恶”,即人所正常拥有的情感。这是人们对“性情”一词最初的认识。
到刘宋时,“性情”一词含义有所发展,具体又是指人的自然天性,如《世说新语·轻诋》篇载:“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4]这里所谓“情性自得”,即“纵心调畅”,高士必可以做到“纵心调畅”,即高士都是“情性自得”的,反之,则是“束于教”。这里的“情性”是特指与受教条约束相对的人的自然本性,显然更强调“情性”中的“性”字。
到齐梁,“性情”一词的使用更加频繁,含义也更加丰富,有指人的自然天性,也有指人的正常情感和个性。钟嵘而外,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批评谢灵运山水诗“典正可采,酷不入情”[5],认为其诗没有表现真情。沈约评竹林七贤认为:“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悦当年,萧散怀抱,非五人之与,其谁与哉?”[6]在沈约看来,“情性”指的是人的自然天性,风流器度则是情性的外在表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7]65显然,这里的情性延续了《白虎通》对“性情”的释义,指的是人的自然天性和其所持有的正常情感。对于齐梁论诗所出现的“情性”说,阎采平在《齐梁诗歌研究》中认为:“诗应该吟咏情性,诗可以陶冶性灵。这种理论(情性论)可以从三个层次或者三种关系上来理解,即诗与诗人的真情,诗与诗人的感觉,诗与诗人的个性。”[8]认为所谓“情性”者,有三层含义:即诗人的真情、感觉和个性。这种看法还是很全面的。
通过以上论述来看,“性情”一词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其含义也是愈加丰富的。《诗大序》中的“性情”所指,只是简单的“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这两种感情是为了政治需要才被承认的,却忽略了人本身所具有的正常情感体验。到东汉,《白虎通》释“性情”为一个人的秉性和其所持有的感情,相对《诗大序》中的“性情”来说,含义丰富了不少。到了南朝,“性情”一词的含义愈加丰富,不但指人的本性,还指人的真情、感觉和个性。这当然与汉末以来人的觉醒不无关系。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七子再到竹林七贤,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需求,发展到南朝,“性情”之含义较以前自然是越来越丰富。
虽然“性情”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多样,然而沈德潜却认为刘宋诗歌创作是“性情渐隐”[9]。对于“性情渐隐”一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性情渐隐”中有个“渐”字,这个字很重要,它表示的是一种程度、一种趋势,“渐隐”并不是全隐,只是说刘宋诗人诗歌中的“性情”较之刘宋以前诗歌中的“性情”,呈现一种“隐”的趋势。其次,沈德潜所谓“性情渐隐”,后面紧跟的是“声色大开”,故而,我们要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看,它所说的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即诗歌发展到刘宋时期,诗歌中的“性情”相对于“声色”大开的局面来说,是“渐隐”的。而在这两种理解中,后一种又尤为重要。
刘宋以前的诗歌创作,在“声色”方面并无多少刻意追求,在“性情”方面,自建安以来,诗歌不再为政治功利服务,诗人们更注重自己情感的表达和怀抱的抒发,因此诗歌创作更注重“性情”方面的追求。到刘宋时期,诗人们的创作相较于“性情”,更关注的却是诗歌的形式技巧方面。如钟嵘对元嘉三大家诗人的评论就能说明这一点,钟嵘评谢诗“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2]9;评颜诗“故尚巧似。体裁绮密。然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字一句,皆致意焉”[2]13;评鲍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2]14-15。钟嵘对三人诗歌都有“尚巧似”的评价,认为三人都喜欢在诗中巧妙形似地描摹风景物象,对谢鲍诗作的批评也着眼在诗歌形式上,认为谢诗“以繁芜为累”,鲍诗用词遣字“不避危仄”,对二人诗作的性情方面,则未做任何评价。至于在后世看来用事过多、雕镂太甚的颜诗,钟嵘反而认为其处处表现出了颜延之的真情实感。显然,钟嵘对几人诗歌的评价更侧重于“声色”方面而非“性情”方面。至于刘宋的其他诗人如谢瞻、袁淑、谢惠连等,钟嵘对他们的诗作更没有任何性情方面的评价。这说明刘宋诗歌更注重“声色”方面的追求,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其性情的表现。
刘宋诗人诗歌创作在“声色”方面的追求,历来多被关注。颜诗的使事用典,谢诗的炼字琢句,都是为人所关注的焦点。即使是鲍照那些因为情感表达丰富而在文学史占领一席之地的乐府诗,在诗歌用词上,也是雕藻淫艳的,如《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用“金卮、玉匣、羽帐、锦衾、龙鳞、丹彩、麝芬、紫烟”等精致华美的词表达一定的象征意义。再如《代白紵曲二首》中也有“红萼、紫芽、灼烁、玉筵”等色彩鲜艳的词语。而后世对鲍诗的评价,也多着眼在诗歌形式上,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鲍照之诗,华而不弱”[10],“华”字是就鲍诗的遣词造句而言,“不弱”是指鲍诗的气格,当包含性情方面。方东树《昭昧詹言》评鲍诗:“明远虽以俊逸有气为独妙,而字字炼,步步留,以涩为厚,无一步滑。”[11]所关注的也是鲍诗的炼字遣词方面。
由上可见,在刘宋整个诗歌创作大环境下,相比于“性情”的抒发,诗人们更注重对诗歌“声色”的追求,二者是相对的状态。刘宋诗歌较刘宋之前的诗歌创作,固然在“性情”方面呈现“隐”的趋势,更主要的是刘宋诗人对诗歌“声色”的追求超过了对“性情”表达的关注,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沈德潜论刘宋诗是“性情渐隐”了。
二、“性情渐隐”的原因
建安文学“主缘情”的抒情传统一路发展下来,至刘宋时期,诗歌创作呈现的是“性情渐隐”的状况。诗人们的创作不再以情感表达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对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是刘宋诗坛对诗歌的“声色”方面日渐重视。与此前诗歌相比,刘宋诗人更注重对诗歌形式的追求,这直接导致了对诗歌“性情”表达方面的日益忽视。用刘勰的话说,刘宋诗歌整体创作特点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7]67。这种对诗歌形式的刻意追求,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性情”表达的,比如颜延之的诗。《宋书》本传称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12]1891,可是后世诗话家对颜诗多持批评态度,就是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也更关注谢诗和鲍诗,对颜诗多是一笔带过的介绍。究其原因,主要是相比于“性情”的表达,颜诗更注重对“声色”的追求。据《诗品》记载,汤惠休评谢灵运与颜延之的诗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2]13-14《南史·颜延之传》也借鲍照之口说颜诗是“铺锦列绣,雕馈满眼”[13]。颜诗不只是辞藻华丽、精雕细刻,其最大的特点是用典,“颜延之确为中国诗史上以用典著称的第一人”[14]。正因为注重对诗歌形式的追求,反而忽略了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考察颜延之的诗歌创作,会发现,除《五君咏》《秋胡行》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抒情诗篇。再比如谢灵运和鲍照的山水诗,虽有一定的情感表达,但一眼看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于诗歌创作形式的追求,如鲍照的《登庐山诗二首》其一:“访世失隐沦,从山异灵士。明发振云冠,升峤远栖趾。高岑隔半天,长崖断千里。氛雾承星辰,潭壑洞江汜。崭绝类虎牙,巑岏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韬树必千祀。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瑶波逐穴开,霞石触峰起。回互非一形,参差悉相似。倾听凤管宾,缅望钓龙子。松桂盈膝前,如何秽城市?”[15]1282-1283这首诗除前四句和后两句,中间全是对偶组成,句式严谨,甚至在用词上也是别出心裁,力求新奇。而前四句是交代登山的原因和时间,真正算得上抒情的也就最后两句。可见,对诗歌创作形式的重视,一定程度上让人忽略了个体情感的表达。
其次,由于受东晋以来玄言诗的影响,刘宋诗人们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多注重对玄理的阐发,而往往忽略了“性情”的表达。正如刘勰在《时序》篇中所指出的,建安诗歌主缘情、重个性的特点,一路发展下来,到西晋,呈现的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7]674的状态,虽然创作主流仍然是表现作者的真实感情,但已经开始有诗人以玄理入诗,如傅玄《两仪诗》、张华《赠挚仲洽诗》等。到了东晋,以玄理入诗的创作现象更为普遍,并且由此招致了后来一些诗评家的批判。比如刘勰在《明诗》篇中所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7]67,又在《时序》篇中批判其时文学创作是“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7]675。钟嵘也批评这时的诗歌创作风气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2]2可见玄言诗是这时诗歌创作的主流,并且为人所诟病。东晋诗坛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发展到刘宋,即使像刘勰在《明诗》篇中所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7]67,可是任何一种创作思潮不是说退就退的,必然还会对后来产生影响,否则谢灵运的山水诗就不会“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16]了。对于谢诗中的玄言成分,后世诗评家们褒贬不一,清人黄子云认为其是“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17];潘德舆却直言不喜灵运诗,并批评说“谢客诗芜累寡情处甚多”[18],和萧子显所评“酷不入情”看法差不多。显然,刘宋诗歌创作在“性情”表达方面呈“渐隐”趋势,和玄言诗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其实,不止是谢灵运的诗,其他刘宋诗人的诗中也或多或少有玄理的成分。比如鲍照,虽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对谢诗的“玄言尾巴”作了改革,但也有一些诗篇没有完全革除玄言的习气,如其《白云诗》曰:“情高不恋俗,厌世乐寻仙。炼金宿明馆,屑玉止瑶渊。”[15]1301即化用了《庄子》之典,《庄子·天地》篇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19]又如其《在江陵叹年伤老诗》:“五难未易夷,三命戒渊抱。方瞳起松髓,頳发疑桂脑。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15]1304葛洪《抱朴子内篇》曰:“若令吾眼有方瞳,耳出长顶……”[20]而老子曾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21]鲍照用“方瞳”典和“大患”典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暮年已至的忧虑。再如曾得谢灵运盛赞的谢惠连,其《陇西行》曰:“运有荣枯,道有舒屈。潜保黄裳,显服朱黻。”[15]1189显然也含有一定的玄理成分。虽然玄言诗发展到刘宋已经衰歇下去,然而,其对刘宋诗人的影响依然存在,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不自觉地会带上玄理成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诗歌创作中“性情”的表达的。
最后,刘宋诗歌“性情渐隐”,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刘宋王朝政治复杂,士庶争权、皇室内斗,造成人人自危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对诗歌创作的“性情渐隐”产生了间接影响。刘宋政权是由寒门庶族所建立,在文帝刘义隆后由治转乱。刘宋政权短短几十年中,受皇室内斗牵连而死的文士有袁淑、范晔、傅亮、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王僧绰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诗人们的创作自然不敢抒发一些真“性情”,除表达羁旅愁思、向往归隐这些无关政治之情外,对现实的不满之情则不可随意抒发,比如谢灵运,为其引来杀身之祸的正是那首充满愤懑的“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15]1185。谢灵运自诩高才,《宋书》本传说他“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12]1743,可是刘宋皇室只需要他的才能作为装点,却不会让他享有过去士族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故而沈约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12]1753。然而这样的“愤愤”之情在谢灵运的诗中却并不多见,其山水诗多是以表现自己隐逸情怀结尾的。试看几例:“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诗》)[15]1162“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慽。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诗》)[15]1167“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诗》)[15]1160很显然,谢灵运山水诗的结尾既有以养生抱朴自慰的,也有表现出诗人对隐居生活向往的,却很少有表现其“愤愤”之情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和他自身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士庶之争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身份本就敏感,自是不敢再触怒当权者。所以说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诗人真“性情”的抒发。
由上可见,刘宋诗歌“性情渐隐”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其时诗人更注重对诗歌“声色”方面的追求,这直接导致对诗歌“性情”表达的忽视。此外,造成刘宋诗歌“性情渐隐”的状况与玄言诗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故而,后世评刘宋诗歌“性情渐隐” 是有一定道理的。
[1]郑玄笺,孔颖达.毛诗注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4-15.
[2]钟嵘.诗品[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陈立.白虎通疏证(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381-382.
[4]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4:730.
[5]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6]沈约.七贤论[M]//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13.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8]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08.
[9]沈德潜.说诗晬语笺注[M].王宏林.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28.
[10]陈师道.后山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2:313.
[11]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65.
[1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881.
[14]谌东颷.颜延之研究[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03.
[1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7.
[17]黄子云.野鸿诗的·第77则[M]//丁福保.辑.清诗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96.
[1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M].朱德慈.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28.
[19]庄子.庄子[M].孙通海.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122.
[20]葛洪.抱朴子内篇[M].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98.
[21]老子.道德经注释[M].蒋门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54.
(责任编辑 王光斌)
A Study of “Temperament Faded Away Gradually”
MENG Juan
(School of Humanity, 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Temperament faded away gradually but it got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rhythm and the flowery language when poetry developed into Liu Song Dynasty.” Said by Shen Deqian in Talk on the Poetry. He thought it faded away gradually in the poetic temperamental aspect in Liu Song Period. The book talked on the poetry with the “temperament” firstly in Preface of the Poetry.“Temperament” mainly means the aspect of the expression of feelings in the poetry. But the meaning of the “Temperament”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rich from the Preface of the Poetry to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mperament” and study “Temperament Faded away Gradually” of the Liu Song Poetry from the meaning and the reason.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faded away gradually; meaning; reason
I207.22
A
1674 - 9200(2017)05 - 0070 - 04
2017 - 03 -08
孟娟,女,安徽六安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