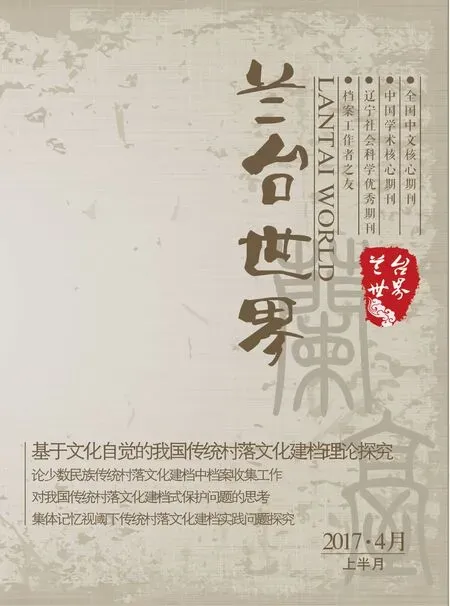《别录》成书时间之探究
2017-03-11李佳宇
李佳宇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150025)
《别录》成书时间之探究
李佳宇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150025)
西汉刘向受诏主持中央藏书的整理工作,为各书写定叙录,而这些叙录被另编一书成为《别录》,时间应该在郑玄之前的东汉时期,原因有三:一者,距刘向时代最近的《汉书》并未提到《别录》一书;二者,阮孝绪《七录序》关于《别录》的叙述存在疑点;三者,《别录》一书在郑玄时才见录于文献典籍。
刘向 刘歆 《别录》 成书时间
西汉刘向负责整理、校雠图书,每完成一部书便为其写定内容提要即叙录,简述校雠经过、条列该书篇目、介绍相关内容,并上奏国君,这些叙录后被编成《别录》。一般认为《别录》成于刘向之手,是他对自己所奏叙录的另外抄录编订,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由于原书早已亡佚,前人文献记载较少且较为模糊,所以只能从只言片语去揆度。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和对众学者观点的分析,推测《别录》成书于郑玄(127—200)之前的东汉时期,当时人对刘向所奏各书叙录进行搜集汇编,作者仍属刘向。
一、《汉书》未提《别录》一书
查考距刘向时代最近的史书记载,便是东汉初班固的《汉书》。刘向、班固分别生活于西汉末期和东汉初期,从刘向校书到班固著书,两人相隔不到百年,且都入皇家校书部,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班固拜为兰台令史,受诏修史,有足够的机会接触丰富的资源,所以《汉书》中关于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及其著述的记载是十分重要的参考。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依《汉书》写成,且相关内容不多,故无可取处。
《汉书·成帝纪》:“(河平)三年(前26)……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1]310
《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2]799-800
以上史料记载刘向等人受诏分工校书,每完成一部书,刘向便列出该书篇目、简述相关指意,并呈国君御览。前辈学者对《别录》进行辑佚,如《晏子》八篇、《孙卿新书》三十二篇,则可与《汉书》此处所载互相佐证。查考《汉书》关于刘向校书与撰写叙录的内容,其只提“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便再无多言,《别录》未见著录。
根据《汉书·楚元王传》与《汉书·艺文志》,刘向主要负责领校中央五经秘书,工于经传、诸子、诗赋,校得《乐记》三十二篇,编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作《说老子》四篇、赋三十三篇。在班固的《汉书》中,这些出于刘向之手的书籍都有记载,对《别录》这部综合刘向十九年校书成果的书籍却只字不提,实失合理。即使中间经历王莽之乱书籍散失,对如此大部头且可以成为《艺文志》重要参考的书籍,班固怎能轻易失察。
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续未竟事业、完成校书整理工作,写成《七略》。这里关于刘歆撰写《七略》所依据的内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汉书·艺文志》“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1928-1966
刘歆是“总群书”而奏《七略》,由此可见,完成《七略》所依据的是多数量、多种类的“群书”,而不是在《别录》一书基础上的简化。但这“群书”应该是经过刘向、刘歆整理分类过的,也应该包括刘向写过的叙录。《汉书》中刘歆生活时代(直至王莽地皇四年)的相关记载也没有提过《别录》一书,可见刘歆也可能未曾编过《别录》。王莽地皇四年(23)之后,更始帝过渡,时间便进入东汉,那么《别录》的成书则该从东汉开始考虑。
姚名达先生曾指出:《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3]39。
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有《晏子》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昧死上”[4]8、《孙卿新书》三十二篇“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4]9,结合《汉书》记载,可知刘向受诏校书,为每书编写条目指意,并且奏上供皇帝御览,各书叙录是分散开的。刘向故后,其子刘歆继续校勘整理书籍,“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里总的是“群书”,而不是《别录》一书,可见刘歆是在众叙录的基础上加以删撮而成《七略》的。据刘向时间较近的史料只能分析到此程度,因为其中并无“别录”二字的提及,所以不能贸然说《七略》依据的是《别录》,更不能简单地从书名及内容的繁简上确定成书先后,只能说《七略》依据的是刘向为各书做的叙录。
程千帆先生认为《别录》成书于《七略》之后:向之叙奏群书,其事未竟,故死后一年,歆犹有《上山海经表》。是在向生前,实无集众录以成《别录》之可能也。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以为,相传二十卷,殆子骏奏进七略之初勒成之,……当时似未尝奏御者也。然据余前所考证,歆主校书之事,多不过一年有半。在此期间,其工作一则叙奏向所未及诸书(《上山海经表》可证),二则造作《七略》,能否再有余闲,更勒《别录》,是难言也[5]7-8。
程千帆先生指出,刘向校书工作还未完成就已辞世,他实无集众录另成《别录》的可能性。“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刘向校书事业未竟而没有编成《别录》的可能,《汉书》也未述《别录》,两者正可互佐。而刘歆的图书工作,只进行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间校余书、写叙录、奏《七略》,如果再加上编成相传二十卷的《别录》,这样的工作量,以当时的条件未必能成。就算用于《七略》的参考,对众录也无须再行编写,直接集中起来利用即可,省时省力。当时的文化工作是服务于皇权的,著书立说都会有所奏御,刘歆《七略》这部群书目录之作也是呈国君御览的。刘向的叙录已完成可随时供皇帝观览,再将众叙录编成《别录》,实无必要。
姚名达、张涤华两位先生则认为《别录》的撰辑,也能随得随编,随时可以成书,即刘向可以一边校书一边写叙录,一边再将叙录另抄别集,就如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已进呈,校订却仍在继续[6]5。姚、张两先生所言,是质疑刘向辞世而未成《别录》的观点,但若果真刘向别集众录另成一书,应该有自己的成书意图、体例安排、内容取舍以及凡例式的陈述,怎么还会原封不动地将“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这样的语句再誊抄在自己的书中呢?
余嘉锡先生疑:《七略》既成,时人始就群书钞取其录,附入歆书,以省两读,但必在王莽未败,书未散失以前,其主名则不可考矣[7]2284。
余嘉锡先生认为是王莽未败、书未散失之前有人将刘向叙录抄取附入《七略》,编者不明。按照余嘉锡先生的想法来考虑,若是附入《七略》之中,则《别录》还是未正式成书,它不是独立的本子,也没有命名,只是《七略》的附录。按照西汉的图书制度,未经批准允许,中央图书不得外借、抄录,一般人是没有权利进入藏书处的;当时能够接近中央图书的人,多是负责图书工作的有才学的臣子,他们也没有将叙录另编成书的理由和权力,史书更无所载。而更始短暂,政局动荡、秩序混乱,谁能有暇编书?想来应该是后人见到刘向所写叙录,视其重要,恐其疏失,才重新编成一书,体例很可能一遵《七略》。
综合以上分析,推断《别录》在刘向、刘歆时期还未成书,那么关于《别录》的成书时间则该从东汉开始考虑。
二、对《七录序》中“时又别集众录”的解读
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序》,提到了《别录》的成书信息。首先是关于刘向、刘歆受诏校书的记述,《七录序》:“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8]112
这一部分指出书籍散佚背景下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史实,与班固《汉书》所述大致相同,只是《汉书》的“每一书已”在此变成了“每一篇已”,但其实都是指每完成一部书的叙录,便上奏国君。同样,刘歆嗣其父业,总“群篇”而奏《七略》,这里没有提到刘向编成《别录》。
接着《七录序》提到了《别录》一书:“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8]112
这一部分主要讲《七略》、《别录》这两部代表目录学成就的书籍。首先可以明确结论的,便是在阮孝绪时《别录》已经成书,其内容就是刘向所写的叙录。刘向校书并为每书写定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并同本书一齐奏上,之后这些叙录就另外综合于一本书上,即成《别录》。对《别录》的成书情况,关键就在于“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这句话。
吕绍虞先生等人将“时”理解为“当时”、“同时”,即刘向同时又将叙录另抄别集变成《别录》一书。但也有人认为“时”当理解为“时人”,或近于或远于刘向时代,是别人而非刘向编订成的《别录》。显然这里的记载是有些模糊的,一个“时”字可以有多种解读,阮氏也没有明确说明“时又别集众录”具体在何时,只是告诉我们刘向的叙录不再分散于各部书中,它们被编入一部名为《别录》的书籍中。“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可指《别录》,也可指各叙录,而若指各叙录,则与《汉书》“总群书”、《七录序》“总括群篇”更为贴近。
阮孝绪生活的时代距离汉代起码有五个世纪之久,期间关于《别录》的记载就很少,而且《别录》的内容也可能已经不是完整的了,他对《别录》的书籍信息不一定是确知的。所以,虽然阮氏的《七录序》为我们了解《别录》提供了难得的信息,但仍不能作为确信无疑的依据,不能就此认定《别录》是刘向成书。
三、文献中关于《别录》的较早提及
就今天所能查考的史料来看,首先提到《别录》一书的,是东汉末年郑玄的《三礼目录》。而把刘向和《别录》联系在一起的,是稍晚于郑玄的应劭《风俗通义》。
郑玄《三礼目录》《仪礼目录·士冠礼第一》:“童子任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仕于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积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为十。冠礼于五礼属嘉礼,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9]77
《文选》“左太冲魏都斌”李善注辑得佚文:“《风俗通义》曰,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10]106
郑玄的《三礼目录》具体指出《别录》对《礼》书中各方面内容的分类处理,这是比较早的明确提到《别录》的史料,《别录》的书名正式出现。之后应劭《风俗通义》直接将刘向以作者的身份与《别录》联系在了一起,时间在东汉末年。东汉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刘向的叙录被汇编成书、命名为《别录》,这是十分可能的。《别录》的内容本是刘向所作,应劭在引用其内容时称为“刘向《别录》”,也不失合理。
结束西汉末年的混乱,进入东汉,政局稳定,国家藏书开始逐渐恢复。统治者提倡图书收集,设立了专门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如辟雍、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处,还创置了主持图书事业的机构——秘书监,足见东汉图书管理事业之盛;除了中央藏书,政府还允许私人藏书,如班固、蔡邕、郑玄等。在这样的环境中,东汉时人很可能将所见到的刘向叙录另编成书,并与《七略》相参照。只是《东观汉记》散佚甚多,而《后汉书》作者范晔为南朝宋人,距东汉时代久远,且经历频繁的时局更迭,要厘清各书的情况并不容易,同时《后汉书》也没有设《艺文志》,所以无法详细了解《别录》的编成情况。后人因为书中内容而提“刘向《别录》”,加上南朝梁阮孝绪含糊的表达,甚至隋、唐史志目录直接题“刘向撰”,使人以为成书者就是刘向,以致误解与混乱。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后人习读汉以后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某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11]269指出了《隋志》题“某人撰”带来的问题。
综上所述,《汉书》、《汉纪》并没有对《别录》的记载,直到东汉末年郑玄、应劭的论著才有提及,而依《七录序》判断《别录》成书信息尚有疑点,各学者对刘向、刘歆成书《别录》的推论又不易圆通,最终认为《别录》成书于郑玄之前的东汉时期,由于内容确属刘向所作,所以《别录》作者仍归于刘向。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永瑢,纪昀,陆锡熊,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M].上海:开明书店,1936.
[5]程会昌.目录学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39.
[6]张涤华.《别录》的作者及其撰辑的时期——《别录》考索之一[J].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1).
[7]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8]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黄奭.黄氏逸书考:第114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10]萧统,李善.文选: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G256
A
2016-12-16
李佳宇,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