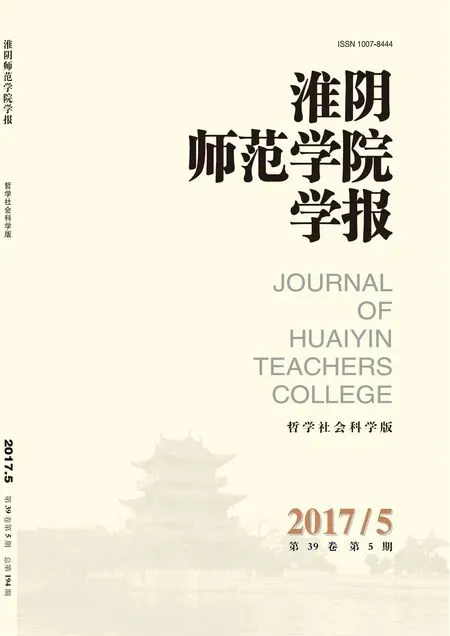读书的两重境界
——追忆父亲宁可的读书生涯
2017-03-11宁欣
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现当代学人研究】
读书的两重境界
——追忆父亲宁可的读书生涯
宁 欣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宁欣作为一直陪伴在父亲宁可身边的女儿,通过亲身经历和日常观察,娓娓道来嗜书如痴的父亲,在“读经”与“读诗”的两重境界中历经坎坷却悠然前行。其间,抗日战争的烽火,南开学堂的艰辛,“文革”的禁锢,都没有阻挡宁可对书的热爱与珍惜。孜孜以求的读书生涯,将宁可带入学术的殿堂,使他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思维缜密,也影响到他的三个女儿,与书为伴,学业有成。
宁可;生平;阅读
读书其实有“读经”与“读诗”两种平行的境界。“读经”需要去领会和钻研,正如大家津津乐道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三境”,比喻做学问的依次递进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三境”说描述了读经挣扎、奋斗、顿悟的心路历程。“读诗”如果也可以分成三重境界,用三句诗甚为贴切,即,“纵使晴明无雨色,如云深处亦沾衣”,此第一境也;“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此第二境也;“轻舟已过万重山”,此第三境也,描述了读书破万卷后的超脱与飘逸,别有天地。父亲读书,恰如在“读经”与“读诗”两种境界中交替行走。
父亲读书如痴,不带任何功利性色彩,读书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曾经专门撰文记述他少年读书时的颠痴之状,文章的名字就叫“读书七痼癖”[1]。所谓“七痼癖”,一谓乱看,二是抢看,三是偷看,四是快看,五是反复看,六是不求甚解,七是纸上谈兵。在中学,就被一些同学喻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包,无所不能。[2]
正可谓:读书无关学问,只是爱好,但读书却能读出学问,是为不谬;读书能映射出人生品质,实为心得。
一
(一)未英胡同时代。
第一阶段是在我幼年时候。我最早有印象的家是位于北京宣武门内顺城街的未英胡同2号,一个典型的旧式大院落,当然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住满各色居民的大杂院。这条胡同是清代皇家喂鹰的场所,取谐音名为“未英胡同”。未英胡同的大宅院不少,很多名人都与其结下因缘。著名鸳鸯蝴蝶派的领军人物张恨水,就曾经租住在50号院,拥有三进五十多间房子。我们住的2号院,是首都师大前身北京师范学院的家属宿舍,据说是吴三桂父亲的宅子,但似乎也不可考了。我们家最早是住在正院西北角的套间,未英胡同二号的18号,里外各一间,外边的廊子作为厨房,安放炉子等杂物。我们一家住在里间,外间不大,但现在想起来,住的人可不少。有姥姥、姥爷,在北京上小学的五姨、小姨。舅舅被打成右派后,舅妈又将表姐表哥送来,于是,外屋常住人口四人,周末人口六人。再加上有可能会来探亲的二人,就要住八口人了。但似乎也都挤下了。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有什么书房,也不记得家里有书架。父亲在师院有一间宿舍,又是图书馆馆长,看书自然有地方。
(二)“维也纳圈椅”时代。
在“大跃进”的尾声,北京师范学院大搞基本建设也进入了高潮,幼儿园对面的家属大楼从挖地基到盖成,速度很快,我们的父母和师院的教师职工很多人参加了义务劳动,大概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集中搬运挖地基挖出来的土和石头等。楼盖成后,我们搬到首都师大的14号楼四单元32号,屋子宽敞了,父亲终于有了独立使用的书房,他从旧货市场买了一个介乎墨绿和浅绿之间的大书桌,两侧各三个抽屉,四根很有艺术特点的桌腿,两把被他称为“维也纳式”的圈椅。那个桌子是否也是维也纳的造型,不得而知,但它们伴随他度过了此后的大半生。书房是三室一厅靠南的单独一间,十四五平方米,靠东的一侧墙放置了几个书柜。当时不多的书都有了安身之所。我们家的书逐渐增加,但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父亲主要是淘书,淘那些地摊或旧书店里的便宜书。买回书来,都会在扉页上写明购买的时间,并签名,这个习惯从上大学起,一直保留。我整理藏书时,发现最早的是20世纪30年代买的书。父亲淘来的书,一是没有大部头,二是没有真正的好版本,都是便宜、实用的,显然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三)包上报纸皮的“封资修”——“文革”时代。
“文革”时,“书荒”对父亲是最大的灾难。不仅抄家把绝大部分“封资修”的书籍都抄走,图书馆也封闭了,满世界不是“红宝书”,就是大字报,或者是由“战斗队”发展成的各种“兵团”组织印刷的“小报”,父亲一直保存着他收集的小报和当时的大报。记得抄家后劫余的书,有全套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选集1—4卷,有革命战争回忆录系列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若干本《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还有侥幸没被抄走的外国小说,包上报纸皮,放在书架的最下面。父亲反复阅读这些保留下的书,通读了马列经典著作,毛选看了若干遍。除了经典大部头,其他的书都成了我们阅读的对象,看得津津有味。父亲还通过“关系”潜入尚未完全封闭的图书馆看书。后来图书馆的部分书籍可供借出“批判”,但极为有限。父亲借了英文版的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和《三个火枪手》等,我们后来才看到中文版《三个火枪手》,记得是竖排繁体,译名是《三剑客》。白天,我们出去疯玩和看大字报,父亲则在家看英文经典小说,晚上,几家都属于“黑帮”家的小孩,聚在我们家,听父亲讲这些世界名著。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醉如痴,恰似沐浴到温暖的阳光。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姐妹三人从小就是“小书迷”,尤其是我,只要有书看,真可以“废寝忘食”。如火如荼的“文革”时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奔赴广阔天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锻炼“一颗红心”。寒冬,由于没有柴火,室内温度达到摄氏零下40度,我们睡觉时都全副武装地戴上帽子、围巾、手套,但只要有书看,我的“一颗红心”就在兴奋地跳动,我的周身热血就在不断沸腾。为了借到一本书,我甚至可以顶着迷漫的风雪走几十里路。黑龙江兵团给我的最深感受不是挥汗如雨,不是千里冰封,不是疲惫的身躯,不是简陋的条件,而是缺书、少书的遗憾。一本从家里带来的书,往往因为有可能是“禁书”而包上封皮,在全团爱看书的战友之间流传。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讲书、读书,大一点,他给我们借书。我从东北兵团回来探亲,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图书馆为我借书,我几乎用一天三本的速度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囫囵吞枣,一目十行,丝毫不敢懈怠,东北还有一屋子的知青战友等着我在工余时间给她们讲故事呢。恢复高考后,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很多专业问题会向父亲请教,他的讲解很少,经常是给我开出一串书单,让我去阅读。
(四)老年时代——书与眼睛的博弈。
晚年时,父亲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情看书,经济不是问题了,家里的书架和书柜也空前地增加了。15个书柜,8个书架,其中有4个顶天立地的铁书架,如果搬走这些书架的话,大概可谓“家徒四壁”了。父亲年轻时就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镜片越来越厚,圈数越来越多,再加上老年黄斑性病变,但这都阻止不了他对读书的渴求,如何解决看得见的问题,就成为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
解决的方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发挥放大镜的作用。在他的建议下和通过我的积极努力,陆续配置了多种型号的放大镜,有可以戴在头上的,有放在手边的,有大圆镜,有小圆镜,有带小灯泡的,有类似军用的,足足七八种。林林总总的放大镜陪伴着他,和他酷爱的书,一直到走进天堂。即便是因白内障做手术,术后,医生规定的禁用眼睛的期限还未到,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看书。
第二种途径,是在为他打印稿件时,将字号放大,刚开始小四就可以,慢慢加大到四号、小三、三号,最后是二号大字。稿子总是处于不断打磨和修改中,经常看见他的眼睛快要与桌面亲密接触,将改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转给我,我就又投入“辨字”的战斗中。最后,我终于决定不再给他看修改稿,否则会“此稿绵绵无绝期”了。晚年,学术方面,他主要是将多年研究的成果汇总和提炼,即后来成书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我负责录入打字,虽然字迹小而乱,我仍然以最大的毅力和最饱满的热情不懈地录入。在撰写过程中,他戴着高度老花镜加上搁在手边的放大镜,几乎贴在桌面上查阅一摞一摞书的背影,似乎仍在眼前。
二
父亲读书的种类和范围非常广泛。他在重庆南开中学时,数学常因无暇顾及而不及格,因内务不整还受到过留校察看的处分,但在同学中,因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而知名度很高。电视台采访他的挚友——晚年的汤一介先生,问到他的同学中,最聪明的是谁,他毫不犹豫地答道“黎先智”(父亲原名)。
父亲写文章,视野开阔,大开大合,注意从长时段观察和研究历史。田余庆先生既是他大学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曾经调侃说:“我顶多管五百年,你能管五千年。”所谓父亲的研究“能管五千年”,得益于书读得广而杂。他每次写作,都会参考很多书,如果家里没有,就到图书馆借,由保姆拎着一个大书包,多的话,就拉上一个老人买菜用的小拖车,拉去一批看完的,又拉回一批准备看的。隔段时间,就会换一批。
他常看的书籍主要有几类:一是专业书籍,但所看书籍并不限于历史学,天文、地理、兵器、哲学、建筑(除了理工科过于专业的书籍),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几乎无所不看。当然详略有别。尤其涉及地名和路线,他都要对照着地图核实,对历代战争的战役、行军路线图(包括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世界发生的主要战争)都烂熟于心。因此,他写的文章涉及领域广,跨越时段长,都是依靠广泛和深入的阅读打下的基础。
二是新书。他很注意新的学术成果。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了,刘北成老师新翻译了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一本书,我回家问了父亲这方面的问题,他当时没有专门接触过,很快,就借阅了福柯及与福柯有关的书,充实了自己这方面的欠缺。再说起来,已经头头是道,确实了解得很深入了,而非皮毛。
三是杂书、闲书。读书不仅是他的需要,也是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因此,阅读范围广而杂。不仅戏剧、诗歌、散文、杂文这类传统而“正点”的书籍,家中还有成套的武侠小说,流行的盗墓小说、悬疑小说、穿越小说、文玩鉴宝小说、官场小说、侦探小说、网络小说、历史小说,搜揽无遗。这类杂书我也非常喜欢,但似乎阅读的速度和能用来阅读的时间都受到限制,于是选择捷径,先向父亲咨询,他会详细介绍各种书的内容和可看度,我便直奔“主题”,只选择他推荐的“精华”,去粗取精,省去枝蔓。
父亲晚年疾病缠身,曾调侃自己各项机能逐渐衰弱,主要零件基本仅存一半功能,初谓“四半堂”(眼、耳、牙、脑),继改“五半堂”(再加肺),最后定为“六半堂”。但始终不变的是,仍然手不释卷。
父亲读书虽然一目十行,但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对书中的人物、细节娓娓道来,对重点书籍和需要核对的数据及资料,仍然反复阅读,悉心核对,读书无暇日,笔耕不辍。父亲并非述而不作,2003年发生脑梗后,开始陆续整理书稿和撰写回忆性的文章,尤其是每次住院,他都抓紧时间撰写,除了带一箱子书,就是带一沓稿纸。陆续撰写的书稿有上百万字。
三
在什么地方找书,找到他所需要的书,是他一生的乐趣。当然也是讲究战略战术的。
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学期间,穷学生,没有钱买书,找书看的方式基本是借和蹭两种。只要看到同学拿到一本有意思的书(多半是小说),就要一把抢过去看,不免时而引起争执,也不免涎皮赖脸地终于达成协议,或者先睹为快,剋时归还,或者挤进去看一段时间再还回去。一般是看一夜,第二天一早还书。抢到一本书就背着人看,唯恐被抓,总要找一个人少的阴暗角落或者黄昏时刻,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以致才小学四年级就成了近视眼。由于乱看抢看和偷看,免不了就要快看,拼命地赶时间。父亲在中学时,到了星期天,带上两个烧饼,跑到街上书店里站着看书,一直到快天黑灯亮了才回来吃晚饭。看书速度之快让见到的人惊讶,一天下来,粗略计算一气看了五本翻译小说,以页码计,平均一小时200页,而且这是从头到尾看的,风景描写和心理分析也不放过。遇到一本有兴趣的书,如能长久拥有,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回看,仔细品味。[1]
上学和工作以后,经常利用图书馆,在闭馆期间,也不甘寂寞,会与一二好友翻窗进入封闭的藏书室看书。“文革”时,图书馆基本封闭,但制度又未严格执行,父亲就利用机会钻进图书馆看书。
“文革”期间,在劳改队无书可看,恰巧原膳食科科长是“牛鬼蛇神”组(劳改队别称)组长,父亲在他屋里发现几本食谱,翻看后,从此对各种食谱产生了兴趣,虽然始终没有实践,但却常作为谈资,说起各地美食的种类、特色及烹调方式,头头是道,不料,竟然得了一个“美食家”的称号。“文革”以后,被推荐为文化大辞典膳食篇的撰稿人,推荐者的原话是“某人不但会吃而且懂吃,编此书既责无旁贷也将胜任愉快”云云,父亲愕然,逊辞推谢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书籍越来越丰富,除了光顾各种书店,父亲亦成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流动和相对固定书摊的“常客”。书摊上可以搜寻到书店和图书馆里不易看到的各类书籍,题材广泛,热点图书上市快,价钱便宜。我们家方圆数里(晚年步行所至)卖书的都认识他,常常为他这个老顾客打折。而父亲对这些书摊的动向也极为熟悉,对摊位、出摊时间、售书内容都了如指掌。为躲避城管,书摊经常变动位置,父亲仍然能顺利找到。如果“风声”较紧,书摊几日不见踪迹,父亲恍然若失,出去散步似乎失去了最重要的“目标”。报刊亭林林总总的报刊在我的印象中说得好听是琳琅满目,说得准确点是花花绿绿,五花八门,档次高的不多,但父亲仍然每次路过,每次驻足,细细浏览一番,重点翻阅几册,或许买上几本。有段时间他没有订《兵器知识》和《舰船知识》,就专门在发行后的日子里到书摊购买。晚年因身体原因,不能走长路,每日散步距离受到限制,由保姆陪护出去遛弯,保姆扶着他,他拄着拐棍,缓慢而行,回来一问,总是会遛到书摊,有时候为了找到书摊,需要走很远的路,来回步行的距离往往超出我对他承受力的估计。在只能靠轮椅出行的日子里,由保姆推着轮椅逛书摊、找书摊仍然是他每日的“日常”。
父亲不善闲谈,也不爱闲谈,与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人的交流话题,大多以书为主题。与老朋友尤其是老同学的聚会,除了回忆旧事,谈书、谈音乐、谈诗词始终是重要的内容。他们热情洋溢、神采飞扬,似乎回到“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的青春时代。
四
父亲对书的喜欢,不仅仅表现在爱看书,还表现在他对书的珍惜。年轻时,钱少,买的书大部分薄而旧,很可能是地摊或书店里的打折处理货,但每本都得来不易,他不仅能一一道明来源,还在书的扉页上写明购书的时间、地点和他的签名——黎先智(到解放区后才改用今名),有一些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早好像是1936年。每本书包括小学课本、中学课本的纸质、封面、内容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流年碎忆》中记述的1937年在长沙及1938年冬在贵阳时,奶奶特地为父亲买的书,其中“一本是中国分省地图,一本是世界分国地图,武昌亚新舆地学社出版,欧阳忞编绘,彩色道林纸硬面精装,中间有文字说明,那山脉都画成了毛毛虫形状。我和弟弟整天捧读,报纸来了对着报纸查看,吃饭时摊开看,居然得到了不少地理知识。那年考初中,地理出题是一幅暗射地图,要求考生注明全国二十八行省二地方五直辖市的方位名称。我大概答了个八九不离十,考上了”。
后来,我想看某本书时,往往要拆开书皮才能看到“真身”,当然父亲并不会受到书皮的限制,每本包好书皮的书他都一清二楚。
对家里书籍的码放,他都有严格的章法,并且根据陆续补充的书籍而不断调整。对每类书中的某一本放在什么地方,都有规矩。晚年时,经常住院,看书仍然是少不了的日常功课。住院时,除了随身衣物,就是满满一箱书,还要陆续写出准备看的书单,于是我就担负起书籍搬运工的任务。他会指示我,某本书在哪个书架的哪一层的哪一侧,我按图索骥,很快就能找到。2013年11月住进空军总院,距离他走完最后的人生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仍然不时地嘱咐我回家在某某书架的某个地方取书带给他。
对家里书籍、刊物和文档的保存,也一丝不苟。原则是不抛弃,不放弃,但求永远拥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订阅的杂志,如《新华月报》*《新华月报》创刊于1949年,1950年改由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主办。1979年,《新华月报》析为文献版和文摘版。文摘版后改作《新华文摘》,文献版仍名《新华月报》,性质为“纯”文献的时政、综合性刊物。《新建设》*《新建设》杂志1949年9月创刊,由学术界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主办。它的前身是《中国建设》半月刊,曾被国民党查封。等,达到上千册,一直保留,按年代顺序打捆。几十年过去,落满了灰尘,我多次表示是否可以“处理掉”,都没有获得首肯。一直随着我们从14号楼的四单元34号搬到二单元的18号,再搬到21号楼的302,静静落位在大铁书架的顶上,伴随着我们全家走了一程又一程。常常有人来借书,他就用一个笔记本记下书名和借阅者,以免流散的书籍漂泊不归。
20世纪90年代以后,纸质文本的传播与网络结合,有很多文件、材料、信息来自网络,他把别人转给他的各种打印的文字材料都分类装在大档案袋里,列好目录,写清内容,一一保存。他看过的光盘,也都一一装进大档案袋,写明存入的目录,摆放在固定位置。
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父亲保留了一大纸箱子的“文革”时期的资料,大多是当年红卫兵编印的各种火药味极浓的“小报”、传单,悲痛之余也不禁莞尔一笑,回想起令人“热血沸腾”的“疯狂时代”,父亲阅读这些小报的感受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在缺书、少书的年代里,这些小报使他不仅能了解全国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的各派观点和各地动向,也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运动过后,他并没有对之弃若敝屣。
父亲去世后,我们将他遗留下的书籍分成几类,一部分我们希望保留的,一部分赠送给他的学生,一部分捐赠给图书馆。虽然没有什么珍本、孤本,但我们希望这些伴随了他大半生的书发挥“余热”,继续带给阅读它们的人们温暖和愉悦。
五
对待书的态度也反映出父亲对待人生的态度:珍惜友情,珍惜名誉,对待学问一丝不苟。
对喜欢的书反复阅读,对撰写的文章,反复修改,精雕细琢。何芳川老师*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我的博士生导师何兹全先生的爱子。曾多次对我提到他在北大上学时,父亲曾在某次开会中间打电话,大概是和编辑部的编辑谈到他已经交付的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潇洒和从容的神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母亲去世后,我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自然成了他的“学术秘书”。父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影响颇深,主要研究范围基本可以划分为五大领域: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他晚年的研究依然如此,并且循序渐进地进行归纳和总结,使得自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序列,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对于我,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他的文稿录入和打印出来,供他修改。他的字内敛而娟秀,晚年则因眼睛和手感,字迹细密而纠结,我辨认起来十分吃力。打印稿交给他后,他仍然不断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摊开查阅的各种书籍,拿着放大镜几乎趴在桌上辨认书上的文字。再回到我这里的文稿两侧空白处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文稿上的符号也丰富而曲折,有删节号、插入符号等,有时另附一张纸贴在旁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我担心“此稿绵绵无绝期”,不再将文稿给他,才告一段落。因为很多研究在经济史领域,他还手绘了一些把复杂流程简单化的示意图,如“封建经济结构运转表”,以显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运转的动态模式。表分为两半,中间由粗线隔开,表左是农村,表右是城市。各部分分红黑两色,红色代表商品经济和同商品有关的东西;黑色代表非商品性的活动和非商品性的东西。红黑两色套框及双色线条,代表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因素的混合,箭头则指向产品、物资、货币及劳力的流向。表的左半表示农业,左半上方,显示农村人口,左半中侧显示农业经济(包括与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左半下方显示农村。这也就是当今所谓的“三农”。右半上方显示城市人口,右半中侧为城市手工业,右半下方为城市。中间粗线一带方框显示商业和市场。用各种箭头和彼此交错的关系,体现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处于平稳的和循环的周转中,但仍不时有断裂曲折、停滞和倒退,而总的趋势则是在发展和进步,呈现一种螺旋形上升的态势。[3]通过观察和分析这个表,他想探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这种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来自何方;它是一直循环下去,不会有突破,还是会有一个终点,最终破茧而出。给自己和研究者提出了如何破解一直困扰学术界的“李约瑟难题”的难题。
我们姐妹三人都是在小学未毕业时遭遇“文革”,但也都继承了父母酷爱读书的基因,一路读书,分别获得历史学、生理学和化学博士学位,母亲戏称我们为“三剑客”,如今我们天各一方,但读书、谈书是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当然,我们也有自知之明,虽然遗传了父亲爱好读书的基因,但远远没有达到他的境界。
父亲到晚年更多地处于“读诗”的状态。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默写李商隐的诗句,应该是萦绕心中最后的咏唱,婉约、敏感,带着淡淡的忧伤。
父亲早早就立下遗嘱,对所住的房屋,对家人,对晚年依次照顾他起居的三位保姆,都有交代,唯独对视为最珍贵的上万册书和几千本刊物,不著一词。似乎是心之所系,不忍别离。
在骨灰安葬时,我们姐妹三人按照父亲的遗愿,将先他而去的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骨灰合在一起,喻示着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在骨灰盒旁放置了钢笔、眼镜、放大镜、光盘、纸等,都是他晚年须臾不可或缺的物品。天堂不缺好书,相信父亲在天堂仍然遨游在无涯的书海。
[1] 宁可.流年碎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宁可.读书七痼癖——我的读书生活之一[J].博览群书,2006(5).
[3] 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8.
责任编辑:仇海燕
K092
:A
:1007-8444(2017)05-0478-06
:2017-03-24
宁欣,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