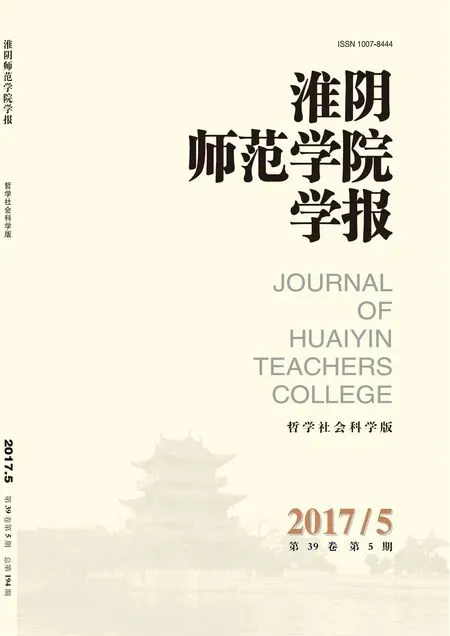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调整主要制约因素探析
2017-03-11张秋生
张秋生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国际关系研究】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调整主要制约因素探析
张秋生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顺应时代变化潮流,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摒弃实施已久的“白澳政策”,使亚洲移民得以大规模地进入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亚裔移民特别是华裔移民人数占移民比重不断上升,澳大利亚移民构成、类型以及移民特性都发生变化。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不断调整,国家利益始终是基本的决定因素,移民政治、经济因素和外交考量是分析其移民政策变化的三个重要维度。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国家利益;制约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在“增加人口、否则灭亡”的口号下,制定并实施了规模宏大的移民计划。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每年人口净增2%,其中1%来自移民。在澳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世界各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澳洲。战后来澳移民主要是以英国人为主体的白裔移民,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开始摒弃实施已久的“白澳政策”,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亚洲移民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澳大利亚。90年代中期以后,亚裔移民特别华裔移民人数逐年增加,占澳大利亚移民比重不断上升,澳大利亚的移民构成、类型以及移民特性都逐步发生新的变化。移民政策多年来一直不断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受到移民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外交政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影响移民政策调整的政治因素
移民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由澳大利亚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作为一个西方民主制国家,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其国内政治体制、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以及外交政策等政治因素的制约。
(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决策者——移民与边境管理局。
澳大利亚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移民政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通常,联邦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和计划时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出台政策,确定年度各类移民的计划人数。
联邦政府辖下的移民与边境管理局(二战后,该机构多次变更名称,简称“移民局”或“移民部”)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移民计划。移民与边境管理局力图成为一个“按照规章制度决策的机构”,尽量避免在决策过程中受政治、种族和媒体等外力的干涉。它认为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否,取决于他们是否普遍认为这个机构管理良好、公平公正。移民与边境管理局注重有关移民及其对澳洲社会影响的调查。这些社会调查全面、深入,主要涉及技术移民、国际移民趋势、移民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城市问题、移民政策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市场的多元文化性、定居和语言服务,以及开放和平等、移民教育和社会公正、少数民族青年问题、向外移民、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例如,按照移民、多元文化和人口调查计划(BIMPR),澳大利亚连续多年对移民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提供了有关移民人口数量、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数据。1996年起,移民、多元文化和原住民事务部(DIMIA)每年开展一次广泛的社区咨询活动。此外,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和劳工市场普查,为移民局制定移民计划提供统计数据。
移民局制定年度移民计划时,还要听取其他机构的建议。移民局设立了一系列专门的咨询机构。例如,国家人口委员会(the National Population Council)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主要咨询机构。1989年,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成立移民研究局(the Bureau of Immigration Research),主要负责“对澳大利亚移民问题进行客观、专业的分析,为政府未来移民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1]13。时任移民、多元文化和原住民事务部部长格里·汉德在向内阁提供年度移民计划前,直接向该局咨询澳大利亚每年接纳各类移民的具体建议。移民局在决策过程中,采取“全体政府管移民”的方式,注重听取其他涉及移民事务的政府机构的意见,诸如教育、科学与技术部、家庭与社区服务部以及就业与劳资关系部等。移民局还咨询各种移民资源中心的意见,例如,少数民族社区委员会等社区群体会集中反映选区的意见,澳大利亚调查协会(ARC)资助的一些大学移民研究中心也参与决策咨询。
(二)澳大利亚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博弈。
亚裔移民是澳大利亚两党关注的焦点问题。两党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移民接纳的规模和移民的构成上。[1]iii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亚裔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移民对澳大利亚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逐渐成为澳大利亚政坛关注的主要议题。1972—1975年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政府因为接纳移民数量问题,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大批越南船民问题上,受到内外夹击。工党内部出现分歧,形成左中右三派:左派主张实行限制自由移民政策,反对政府大规模接收越南难民;中右派则支持一定规模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反对党趁机抨击政府言行不一和移民政策的矛盾性,认为工党政府一方面放弃“白澳政策”,实行无肤色、种族、国籍差异的反对歧视移民政策,另一方面却又排斥、限制越南难民进入澳大利亚,煽动民众反对移民的情绪。反对党借此向惠特拉姆政府施加压力。当外交部部长威尔西建议降低越南难民准入标准时,惠特拉姆表示反对,原因“可能是害怕引起政治上对其政府的敌意”[2]。最终,惠特拉姆政府将接受越南难民的数量,从上台之初计划人数的140 000人下降至1975年的50 000人,而实际上只接纳了1 000名越南难民。学者维维安妮在她的研究中指出,惠特拉姆此举的主要动机是避免新的情绪化的反共产主义者大规模进入澳大利亚,引起澳大利亚政治派系的注意,并借机向政府发难。[3]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实施扩张性移民计划,澳大利亚移民人数总体保持稳定增长。1984年3月17日,杰弗里·布雷尼(Jeoffrey Blainey)教授在1 000名听众面前发表讲话。他使用“傲慢”和“感觉迟钝”两个词形容当时的移民政策:“亚洲移民的步伐现在比公众舆论走得更快……澳大利亚人似乎憎恨大量引进的越南人和其他东南亚人,这些人获得工作的机会很少,他们是靠纳税人的钱维持生活,尽管他们本身没有过错。澳大利亚在宽容中取得的卓越成果以及在本世纪的最后1/3时间里慢慢建立起来的理解,正被当今的政府所危害。”[4]443布雷尼批评扩张性移民政策,建议减少亚洲移民人数,主张实施反对亚裔移民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他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移民问题,尤其是关于亚洲移民数量问题的“布雷尼辩论”。工党政府在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认为移民尤其拥有技术和创业经历的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坚持增加移民的立场。1985年5月,移民部长斯图尔特·韦斯特宣布增加独立类移民(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人数,改变之前公布的移民计划,以回应布雷尼辩论[1]131。
然而,反亚裔移民的呼声没有停止。1988年7月31日,时任反对党领袖的约翰·霍华德提出“一个澳大利亚”的口号,声称多元文化主义使澳大利亚面临“确认文化”的问题,移民政策必须“把澳大利亚放在首位”,公开限制亚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随后,一项反对以种族挑选移民的政策提议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反对党的3名成员不支持霍华德。前移民部长伊安·麦克魁尔、移民委员联合会成员菲利普·罗道科和南澳的斯蒂尔·侯与工党政府一起投票反对,他们甚至想确立一项永久性的政策,即保证种族永远不能成为挑选移民的标准。霍华德的反亚裔移民立场更加顽固。国会议员戈瑞米·埃文斯试图让亚洲人重新恢复信心,但霍华德指责埃文斯是向亚洲邻居“拜倒和道歉”。他在1988年11月15日的《悉尼先驱晨报》上说:“这是对我们国家主权的一种侮辱。我发现,如果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在海外向其他国家道歉的话,那是非常庸俗和贬低自己的。”两天后,同一家报纸在首要新闻中报道了澳大利亚移民咨询协会会长吉姆·戴维的讲话。他说:“商务移民计划被反亚辩论破坏了:仅在3—6个月前,澳大利亚在吸引商务移民方面是领导者,现在被加拿大和新西兰取代了。每人携带50万澳元移民澳洲的1 000人的总数已经有所下降。”一年前,在韩国汉城的讨论会上,他曾对三四百名打算向澳大利亚商务移民的人发表谈话。而他刚刚从一个讨论会上回来,该讨论会只吸引了15—20人。[4]445此外,在华人和其他亚洲移民非常关注的家庭团聚移民方面,霍华德和费兹杰拉德博士也都主张削减一半。[4]445连政府土著事务部秘书查尔斯·帕金斯在1987年1月也认为,“有太多的亚洲人进入了澳大利亚”,他“要求颁布一项不定期的禁令”来限制亚洲移民入境。[4]446
(三)压力集团在澳大利亚移民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压力集团主要包括一些企业集团、代表特定种族背景的社区群体、难民与寻求避难者以及利害相关的公众。在澳大利亚有许多重要的压力集团,如澳大利亚工商业联合会、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退役军人联盟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压力集团在改变移民政策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工商界是最重要的压力集团。他们从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住房、教育和建筑行业。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巨大的影响力,通过政治选举、舆论引导等方式对澳大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实施扩张性移民计划。最具代表性的是代表澳大利亚工商界利益的澳大利亚工商业联合会。该组织强调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认为移民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消费市场,刺激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的人口不仅增加消费需求而且还刺激生产”[5]。霍华德政府执政期间,总体上实行的是扩张性移民计划,澳大利亚政府移民计划人数保持稳定增长,但一些议员和政客对此仍不满足。2006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的居民住宅开发商、澳洲顶级地产品牌梅里顿(Meriton)的创始人哈里·特里古波夫,在一次采访中要求“大规模增加移民”,力争到2050年澳大利亚总人口达到1.5亿人。他说:“国家公园应该让位于住房建设……移民可以带动澳大利亚住房和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些地方进行建设,以繁荣澳大利亚住房市场。”[6]在他看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依赖住房市场,而住房市场基于澳大利亚人口的增长。鉴于住房市场的繁荣以及社会问题的出现,特里古波夫的言论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引进移民还可以大大减少培训工人的成本。澳大利亚工商业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特森指出,澳大利亚许多雇主不愿意对工人进行3—4年的培训,因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直接引进外国技术移民,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而不用负担培训开支,迅速增强企业活力。[7]
另一个重要压力集团是工会。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ACTU)在移民问题上的作用十分重要,对工党政府的影响很大。澳洲全国总工会是工党执政的选举基础,也是工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移民政策和计划制定过程中,澳洲全国总工会都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例如,在1992—1993年度的移民计划意见咨询中,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移民情况迥然不同”,因为国际人口迁移人数越来越多,澳大利亚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企业走向国际,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需要国际背景,澳大利亚需要的不仅是永久性移民,也需要短期类移民。该组织认为,亚洲移民,无论是永久性移民还是短期类移民人数都在增加,澳大利亚应该重视这一变化并调整移民选择标准,不应基于种族、宗教、民族、性别、语言或年龄等因素,歧视移民申请者,并建议政府制定短期类移民计划。[8]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重视短期类移民的意见被此后上台的霍华德政府采纳。澳大利亚全国总工会还积极派代表参与政府各种移民咨询机构的调查,以期做出有利于工会的决策。例如,以菲茨杰拉德为首的移民调查委员会中,工会移民问题专家阿兰·马西森(Alan Matheson)就是重要一员,在《菲茨杰拉德报告》形成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战后澳大利亚实施扩张性移民计划起,澳全国总工会主席或秘书长一直是政府移民咨询机构重要组成人员。[9]
其他利益团体,如澳大利亚少数民族社群委员会联盟(FECCA)、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RCA),则从人权、道德等角度考虑,认为人口稀少、社会富裕的澳大利亚应继续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要求政府增加家庭团聚类和人道主义移民的数量。比勒尔曾写道,澳大利亚移民选择政策主要的政治性压力集团是各种各样的少数种族团体以及支持它们的知识群体。[10]比勒尔的话不免过分夸大少数种族利益团体在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种族团体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总之,澳大利亚压力集团对政府移民政策和移民计划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有学者甚至认为,澳大利亚移民计划是由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利益决定的。[1]ix
(四)公众舆论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影响。
公众舆论不能决定移民政策,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决策。特别在移民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时,决策者往往不得不认真考虑民众舆情。
公众舆论关注移民人数问题。自二战后澳大利亚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起,移民数量显著增长,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移民问题。聚居在主要城市的移民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移民过多并聚居在几个主要大城市中,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当地环境、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利用压力相应增大。
澳大利亚人口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研究所(Australians for an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Population and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iologists)专家认为,大规模移民是造成环境恶化、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澳大利亚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土地、森林以及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过度开发的威胁;当代澳大利亚人有责任为下一代提供至少像这代人享用的干净的、多样的以及高产的自然环境,而大规模移民有可能使澳大利亚主要农业基地诸如墨累—达令盆地加剧水污染以及土地沙化。[11]3611965年成立的澳大利亚环境基金会,受到联邦政府及其他团体的支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该基金会主要由一些科学家组成,其成员弗兰克·芬纳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柯廷学院的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他号召澳大利亚环境基金会继续关注移民对“澳大利亚人口、环境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等产生的影响”,并声称,“我们已经知道立即削减移民数量的合理性以及采取人道主义措施将会降低自然资源的利用率”[12]。
移民对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人口特别集中,60%的人口居住在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其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20世纪80年代,超过80%的移民居住在澳大利亚5个主要大城市。[11]362移民主要前往各州大城市(主要集中于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墨尔本、悉尼等地)。工党的霍克、基廷政府已经意识到澳大利亚人口过于集中的弊端。霍华德政府推行SSRM移民计划,试图吸引移民迁往澳大利亚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促进边远地区开发,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平衡人口分布格局,缓解移民对大城市造成的压力。然而,该计划实施数年,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移居澳大利亚的永久性移民超过50万人。其中,每10名移民中有7人在澳大利亚东部地区的新南威尔士州(28.9%)、维多利亚州(26.9%)以及昆士兰州(15.9%)。移民仍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尤其以悉尼和墨尔本居多(85.4%)[13]。
移民影响着公共生活和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一方面,移民增加了人口数量,他们需要居所,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及其家人,他们的孩子需要教育、必要的健康医疗和其他的社会服务。经济低迷时期,这些基本需求加剧了人们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另一方面,移民也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带来了稀缺的技术和知识。他们积极开展贸易,创办企业,不仅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丰富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多样性。著名学者简·马丁认为,“移民的存在”几乎影响澳大利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3。
然而,在种族主义煽动下,一些媒体片面渲染移民问题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澳洲民众开始排斥移民,反对扩张性移民计划。尤其在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时,一些民众反对外来移民的呼声更高。他们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认为现行的移民政策接纳了过多的移民,尤其家庭团聚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他们认为,这些移民不仅贫穷、无技能,而且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差异巨大,增加了澳大利亚社会的负担,使移民与当地社会冲突日益加剧[11]363。1996年全国大选后,《澳大利亚选举研究》(the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AES)就选民“为何参加选举”等一系列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约2/3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移民过多,一定程度上反对扩张性移民计划[14]。受此影响,1996年霍华德政府上台后,开始有计划地减少家庭团聚移民和人道主义移民的数量。
如今,移民问题已成为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热门话题。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以引进技术移民为主。民意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大选后认为澳大利亚引进移民数量“太多”的人数已达53%,而2004年、2007年大选后,这一数据分别是30%和46%。2012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大约有45.7%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移民计划人数。总之,国内民众的反移民呼声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平衡各方利益集团,实行松紧适度的移民政策。一位加拿大的观察家曾指出,在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认为公众舆论在移民问题和难民政策上普遍倾向自由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15]。
二、影响移民政策调整的经济因素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包括华裔在内的外来移民为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移民。同时,经济的发展又推动政府不断调整移民政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开始转型,经济因素在移民计划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不断调整其移民政策,以适应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需求。
(一)澳大利亚经济的转型。
历史上,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支柱主要为农业和采矿业。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农业、交通运输以及矿业得到较快发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农业和采矿业仍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80%以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铁、镍、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发现,促进了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制造业和以出口为目的的采矿业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60年代末,制造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20世纪80年代前,澳大利亚政府重视生产初级产品,对本国制造业实行高关税的保护政策,以扶持、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1983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推行改革,重点发展服务业,商品与服务业出口增长迅速。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3.0%,上升至80年代的3.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知识经济兴起,澳大利亚开始由生产、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转变。产业结构逐渐发生改变,传统产业部门如农业、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由1970年的55%上升至1997年的68%[16],从业人员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2—1983年度的73%上升至1996—1997年度的80%。
进入21世纪,服务业形成全方位发展的新格局,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澳大利亚非常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一些与高科技密切相关的高附加值产业部门,如计算机信息、电子通讯、金融等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电讯行业为例,1992年,澳大利亚仅有一家由政府持有百分之百股权的澳大利亚海外电信公司(Telstra),独家经营各类国内及国际电信业务。目前除了Telstra,还有Optus、Vodafeng以及其他多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2000年,澳大利亚电信通讯工业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2001年市场总收入达369.9亿澳元,从业人员达10万余人。澳大利亚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发生重要变化。
(二)澳大利亚经济转型对移民政策的影响。
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广袤、人口稀少的国家。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约有700万人。政府深刻地意识到,人口不足不但影响国家安全,还严重制约经济重建与社会发展,为此制定了规模宏大的移民计划,主动吸纳甚至到海外招揽移民。由于缺乏经济增长所必要的人口基数,而工业生产、社会建设以及矿产资源开发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当时的移民政策没有强调移民的技能以及职业背景因素,大量非技术移民涌入澳洲。亚洲移民大量涌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40%的移民来自亚洲[17]。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开始新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改变,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对专业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下降。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当代“经济增长强调知识经济中人力资本因素的重要性”,国家间的竞争逐渐转化为对人才的争夺[18]。澳大利亚移民政策选择标准遵循经济理性主义的原则,开始重视移民的技能、教育背景以及创业能力等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先后执政的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重视商业移民计划,增加商业移民计划人数,加快签证审批程序,目的是吸收拥有雄厚资本和创业技能的高素质移民。1991年,澳大利亚议会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罪犯也通过商业移民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商业移民签证存在潜在的漏洞,有可能被不法分子滥用。为此,政府立即着手改革商业移民计划,修改商业移民准则,更加注重移民的技术能力和创业能力,对资本数额的要求则有所降低[1]135。此后,澳大利亚的商业移民计划不断完善。
1988年出台的《菲茨杰拉德报告》建议,从长远发展看,澳大利亚年度移民计划人数应增加至150 000人,移民接纳的重点是增加技术类移民,减少家庭团聚类移民。该报告强调技术类移民重要性、忽视家庭团聚类移民的做法,招致少数种族媒体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支持者的强烈批评,并将霍克政府推至危险境地[19]。菲茨杰拉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经济因素应该成为移民选择标准的核心考量因素,那样民众才能相信移民计划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目前没有歧视的、以家庭团聚类移民为主的移民政策是不合时宜的。他指出,增加“有技能的、有企业家精神的以及年轻的移民”,有助于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
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经济转型加速,连续多年维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良性发展,对技术移民和商业移民的需求日益增加。2002年,澳大利亚人口研究所举办了人口峰会,认为技术工人短缺将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希望政府增加技术移民的引进数量。会议还特别强调了矿业蓬勃发展对专业技术工人需求的迫切性。澳大利亚是为数不多的“资源供给型发达国家”之一,资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正经历着历史上第五次矿业繁荣。这一传统产业对澳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仍然很大。因此,矿业繁荣也是霍华德政府调整移民政策的重要原因。
此外,本土技术工人大量外流加剧了技术工人短缺局面。据统计,1975—1995年间,本土居民每年大约有20 000—30 000人永久性地移民海外。1995年以来,这一人数不断增高。2007年,高达75 000人[20]65。本土技术工人大量外流,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彼特·麦克唐纳和杰里米·坦普尔指出:“向海外移民的澳大利亚人主要是医生、各类科学家、工程师、IT技术师以及从事市场营销和贸易的专业人员,从澳大利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20]65
霍华德政府意识到技术工人短缺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制约,连续多次改革移民政策,将移民导向由家庭团聚类移民转向技术类移民。霍华德政府执政的10年间,澳大利亚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就业率增加了20%,尤其技术和专业岗位就业率迅速增加。例如,管理者的数量增加了约46%,专家类人数增加了37%,助理专家类人数增加了39%。[21]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澳大利亚加快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之前十多年作为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的矿业投资逐步缩减。澳大利亚政府不断改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金融创新和新兴产业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陆克文—吉拉德政府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其重大举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深化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改革。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霾,将永久技术移民计划由“供给—导向”型转变成“需求—驱动”型:引进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雇主和地方政府担保类技术移民;修改技术移民职业清单;改革技术移民的选择模式,由自由申请制改为选择邀请制。吉拉德政府于2012年引入新的技术移民技术甄选系统“Skill Select”,彻底改变了过去只要达到技术移民评分标准即可移民的规定,目的在于确保澳大利亚获得最紧缺且最具职业前景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另一方面,陆克文—吉拉德政府又将商业技术移民政策改革提上议事日程。陆克文政府于2010年4月宣布调整商业技术移民政策,重点要求增加申请商业技术移民的个人净资产额度,并提高商业技术移民在企业中的所有权比重。2012年7月,吉拉德政府继续深化商业技术移民改革,建立新的商业创新与投资计划,引进新的技术移民选择机制以及创建重要投资人签证机制,目的是吸引海外资本投资澳洲,刺激澳洲经济的持续发展。总之,经济环境的变化在移民政策上的反映,主要体现在重视移民技术能力和创业投资能力等方面,在澳大利亚总体移民计划中,技术类移民的比重日益增大。
三、影响移民政策调整的外交因素
国际移民是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流动[22]。移民的跨国迁移不仅与移民个人相关,而且必然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国外交政策变化不仅影响国际移民流向、规模和性质,还会对本国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移民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以东亚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快速崛起,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推动了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政策的出台,其移民政策与计划逐渐放宽,以华裔移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亚裔移民人数不断增加。
(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转变。
作为历史上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最早的白人移民是英国流放犯。1788年,英国菲利普船长率领的第一批流放犯到达悉尼,建立了早期殖民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与发展,澳大利亚逐渐形成了以白种人为主体、以歧视有色种族为核心内涵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并不见诸具体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官方文件也很少出现这一词汇,然而,它却是澳大利亚自建国以来长期贯彻施行的基本国策,深刻地影响着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白澳政策”是一种非常狭隘的种族主义。在移民政策上主要表现为,严格限制有色人种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后,进入的移民几乎全是欧洲人,其中英伦三岛的占绝大多数。在外交关系上,以传统的种族文化观维系了对英国的依附性,长期制约着澳大利亚摆脱英国控制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严重影响了澳同亚洲等东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形成了自我封闭和对英国的长期依附,延缓了澳大利亚向多元文化国家发展的进程[23]。
20世纪70年代以来,鉴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尤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经济加速发展,澳大利亚开始放弃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由“背对亚洲”逐渐向“面向亚洲”转变。8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7%,APEC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50%,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66%。受到日本经济起飞和随后“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崛起的影响,澳大利亚将对外贸易重心逐渐从欧美转向亚太。整个70年代,澳大利亚65%的出口产品销往亚太地区,进口产品也有55%来自亚太地区[24]。1972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是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政策形成中的重大事件。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仅1973—1974年度的中澳贸易额就超过2亿美元,比建交当年度增长100%。在整个80年代,亚洲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地区,对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几乎占其出口总值的一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6年霍华德联合政府执政以来,澳大利亚进一步“面向亚洲”,在加强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同时,还积极参与亚太事务。新的联合政府虽然没有放弃与欧美国家传统的友好关系,但强调发展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1996年4月出访印尼、新加坡、泰国前夕宣称:“进一步加强与亚洲的联系是澳大利亚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显然,在“亚洲世纪”里,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对象将进一步由欧美转向亚洲。澳大利亚对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显著增长。对亚洲出口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量的比例由1988—1989年度的53.6%上升至2008—2009年度的68.7%,而同期对欧洲出口比例从19%下降至12.9%,对北美出口比例则由11.9%下降至8.6%。[25]
陆克文于2007年底接任总理后,将澳大利亚外交首要任务确定为参与亚洲事务。他指出,“亚洲世纪”是正在发生的鲜活现实。已保持30多年持续增长的亚洲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未来亚洲经济仍将继续增长,这与北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必将重塑国际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惠及亚洲及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26]
陆克文认为,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正加速向亚洲转移,澳大利亚需要有充分准备。2008年,他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倡议。陆克文政府(2007—2010)将全面融入亚太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27]。2012年10月,澳大利亚发表《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表明“融入亚洲”已成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发展战略。澳大利亚政府还相继出台了《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强大与安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白皮书》等相关文件,全面部署“融入亚洲”战略[28]。
(二)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转变对移民政策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在世界进步潮流和国内改革派的推动下,特别是其移民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澳大利亚开始抛弃“白澳政策”,转而实行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强调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文化并存和共同发展。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移民部长阿尔·格拉斯比指出,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澳大利亚,人们都属于某个种族,都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但在澳大利亚以外地区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着血缘相近的根。弗雷泽自由党政府更明确地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允许并鼓励人们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都应当容忍相互间的差异。同时,越来越多的澳洲民众承认,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澳大利亚建设多元文化国家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来自亚洲等地的有色种族移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面向亚洲”促使澳大利亚更加重视同亚洲各国的关系。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为了能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跟迅速发展的亚洲融为一体,澳大利亚开始放宽移民政策,大规模地接纳亚裔移民。早在1966年3月9日,澳大利亚总理霍特就指出,排斥有色人种的移民政策与澳大利亚同亚洲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29]。惠特拉姆上台后强调,“澳大利亚应每年从亚洲国家吸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的移民”[30]。据统计,1976年澳大利亚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亚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执政的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都标榜在亚洲移民政策上体现出公正、宽容和稳定。这一时期,赴澳亚裔移民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在多元文化政策影响下得到了妥善的安置。1996年3月,霍华德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后表示,将继续保持亚洲移民政策的稳定性。新政府外交部部长唐纳在1996年的演讲中,对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所作贡献表示感谢,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促进澳大利亚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社会宽容[31]。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外交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呈现出急剧升温的态势。澳大利亚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移民人数正在迅速增长,占澳大利亚人口的比例也不断上升。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亚洲出生的移民人数翻了一番,从103万上升至201万。其中,中国出生的在澳居民人数从14.8万增加到38万。印度出生的在澳居民人数从9.6万增加至34万[32]。亚裔人口占澳大利亚总人口比重不断攀升,1947年为0.3%,1981年为2.5%,2000年为5.5%,2010年大致为10%。2012年中国超越英国,成为澳洲最大永久移民来源国。2013年澳大利亚的亚裔移民人数逾200万,第一次成为澳洲最大的洲际移民群体。进一步吸纳亚洲移民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如基廷总理所述:“澳大利亚的未来属于亚洲……我们所有的国家利益,不论是政治、经济、战略还是文化利益,都前所未有地汇聚在一个地方——亚洲。”[33]
移民大量进入澳洲必然或多或少带来负面问题,但是,由于亚洲移民迄今为止从未超过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0%,所谓“亚洲化”显然是不可能的。21世纪以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在持续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水乳交融,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未来亚澳关系的深化产生着特殊影响,他们在澳洲社会已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不可能倒退的了。
[1] Jupp J,Kabala M.The Politics of Australian Immigration[M].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93.
[2] Cameron C.China,Communism and Coca-Cola[M].Melbourne:Hill of Content,1980:230.
[3] Viviani N.The Long Journey:Vietnam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M].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4:64-65.
[4] 艾瑞克·罗斯.澳大利亚华人史:1888—1995[M].张威,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5] Betts K,Gilding M.The Growth Lobby and 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J].People and Place,2006,14(4):46-47.
[6] Clennell A.Triguboff: Let’s Trade Trees for Homes[N].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2006-10-11(3).
[7] Bita N.Employers Court Skilled Retirees to Fill Jobs Vacuum[N].The Australian,1998-03-14(3).
[8] 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Submission on the Immigration Program,1992-93[R].Melbourne:ACTU, 1992.
[9] Storer D,Matheson A.Migrant Workers and Unions in a Multicultural Australia[J].Social Alternatives,1983,3(3):42.
[10] Birrell R.A New Era in Australian Migration Policy[J].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4,18(1):68.
[11] Jones H.The New Global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Policy Options for Australia in the 1990s[J].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1992,24(4):361.
[12] Fenner F J.“The Environment”,in How Many Australians?[M].Sydney:AIPS,Angus & Robertson,1971:58.
[13] DIBP.Migration to Australia’s States and Territories 2012-13,2014[EB/OL].[2017-01-10].http://www.immi.gov.au/media/publications/statistics/immigration-update/migration-australia-state-territories-2012-13.pdf.
[14] Betts K.Patriotism,Immigration and the 1996 Australian Election[J].People and Place,1996,4(4):27.
[15] Hawkins F.Critical Years in Immigration:Canada and Australia Compared[M].Kensington: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1989:248.
[16] 魏嵩寿,许梅恋.经济全球化中的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趋势[J].南洋问题研究,2001(3).
[17] Vasta E.Centre on Migration,Policy and Socie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9.
[18] Hugo G.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J].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2006,23(2):116.
[19] Birrell R,Betts K.The FitzGerald Report on Immigration Policy:Origins and Implications[J].The Australian Quarterly,1988,60(3):261-274.
[20] Markus A,Jupp J,McDonald P.Australia’s Immigration Revolution[M].NSW:Allen & Unwin,2009.
[21] Birrell B,Rapson V.Clearing the Myths Away:Higher Education’s Place in Meeting Workforce Demands[M].Melbourne:Monash University,Centre for Population and Urban Research,2006:12.
[22]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24.
[23] 刘樊德.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24.
[24] 沈仲棻.澳大利亚经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50.
[25] 许善品.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进程(1972—2012年)[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150.
[26] 澳大利亚想演“东成西就”[N/OL].(2012-08-29)[2017-01-08].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08/29/content_1104726.htm.
[27] Firth S.Austral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NSW:Allen & Unwin,2011:332.
[28] 王光厚,原野.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战略浅析[J].太平洋学报,2013(9):97.
[29] 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90.
[30] Whitlam G.The Whitlam Government:1972-1975[M].Melbourne:Viking,1985:493.
[31] 亚历山大·唐纳.澳大利亚和亚洲:展望未来——1996年4月11日对悉尼“外国记者协会”的演讲[M]//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40-241.
[32] 亚裔移民成澳大利亚最大移民群体[EB/OL].(2013-06-03)[2017-02-04]http://www.xkb.com.au/html/news/.
[33] 保罗·基廷.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M].郎平,钱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6-17.
责任编辑:杨春龙
K611.54
:A
:1007-8444(2017)05-0460-09
:2017-07-01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20世纪70年代—2013)”(11BRK002)。
张秋生,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与华侨华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