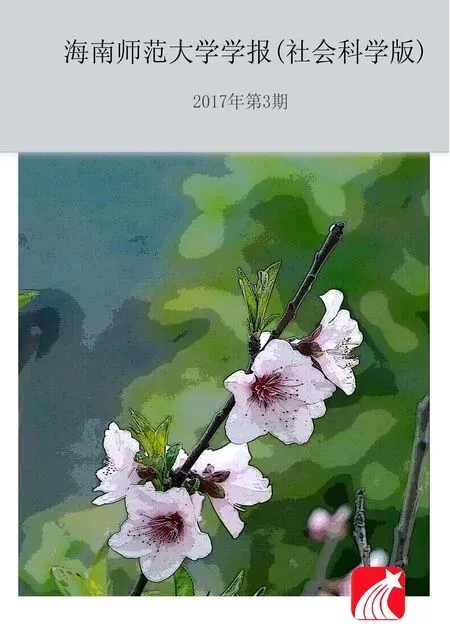论《世说新语》的传记文体
2017-03-11夏德靠
夏德靠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论《世说新语》的传记文体
夏德靠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世说新语》延续《国语》以来的语类文献传统,其实属于一部史传文献,在文体方面呈现显著的传记特质。具体表现为:其一,《世说新语》同一类目之下汇辑性质相似的人物行为及相关事迹,实际上近于正史列传体的类传或合传;其二,《世说新语》存在个人传记,《世说新语》每一门往往将同一个人的资料编撰在一起,这相当于一个人的传记,或者一个人的事迹散布于《世说新语》各门类,将这些事迹聚敛在一起,其实也是一篇传记;其三,《世说新语》还存在家族传记,一是某一特定门类出现家族传记,二是几个门类的资料合在一起形成家族传记。
《世说新语》;类传;个体传记;家族传记
学界历来将《世说新语》视为小说,其实该书无论是编撰还是文体,均延续了《国语》以来的语类文献传统,因此在本质上属于一部史传文献,其文体呈现出显著的传记特质。由于门类的设置,《世说新语》在编撰上就必然采取“以类相从”的方式,亦即按照门类的要求,将经过整理的相关资料系于某一门类之下。因此,《世说新语》的传记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一门类相关资料的传记性,二是不同门类之间的传记性。
一
“传”与“记”原本为两种解经文体。《说文》云:“传,遽也。”段玉裁《注》谓:“辵部曰:‘遽,传也。’与此为互训,此二篆之本义也。《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玉藻》‘士曰传遽之臣’,《注》云:‘传遽,以车马给使者也。’《左传》《国语》皆曰‘以传召伯宗’,《注》皆云:‘传,驿也。’汉有置传、驰传、乘传之不同。按传者如今之驿马,驿必有舍,故曰传舍。又文书亦谓之传,《司关》注云:‘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是也。’引伸传遽之义。则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而传注、流传皆是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7页。可见“传”原指驿递之车马,由于邮递是将信息由一个地方转达到另一个地方,这就与注释传意之行为类似,因而就有了传注的意思。早期用于阐释“经”的“传”,以《春秋》三传最为典型。关于“记”,《说文》:“记,疋也。”段《注》:“疋各本作疏,今正。疋部曰:‘一曰疋,记也。’此疋记二字转注也。疋今字作疏,谓分疏而识之也。《广雅》曰:‘注纪疏记学栞志识也。’按晋唐人作註记字,注从言不从水,不与传注字同。”*[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95页。由此可知,“记”有分疏之意。《汉志》礼类著录《记》百三十一篇,张舜徽先生指出:“古人解礼之文概称为记。《汉志》著录记百三十一篇,皆七十子后学者解礼之文也。”又说:“记之大用,在于解经。”*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强调“记”之解经特别是解礼的功用。
“传记”连词最早大约见于《史记·三代世表》:“《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2页。此处的“传记”,陈兰村先生以为“指解说经典的文字,或泛指书籍”*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一个发展着的文类》,《浙江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这个判断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他又强调说:“表示记载一人生平始终的文体,则至迟在南朝开始。如沈约《宋书·裴松之传》载:‘奉命作《三国志注》,即鸠集传记,增广异文。’此处‘传记’一词始有史料的意义,包括人物传记在内。但应该注意,‘传’、‘传记’的含义从唐宋直至清代还具有含混性,并非专指今天所说的传记文学。”*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一个发展着的文类》,《浙江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古人对于“传记”确实是有争议的,但传记文学的存在与“传记”用以指称这种文学,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案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31页。这就是说,传记的内部存在记人之“传”与记事之“记”的差异,亦即传记有记人与记事两种形态。可是,章学诚对于传记又提出不同的认识:“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章氏并不否认传记有记人与记事的分别,而是否认“传”为记人而“记”为记事的说法。也就是说,章学诚“视‘传记’为同义反复的结合词,指称一种记人或述事的文体,而不是指称‘记人’与‘述事’两种文类”*陈志扬:《传统传记理论的终结:章学诚传记理论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章学诚还指出: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于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于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40页。
对于“传”而言,有一种看法以为生人不当立传,章学诚批驳这种观点,他指出,“传”其实有列传体与传经体之分,列传体叙述一个人的生平,而传经体只叙述一件事。按照这种区分,章学诚与四库馆臣之间有关“传记”的看法之间也绝不是不能相容的,所谓列传体与传经体的说法与馆臣将“传记”分为“叙一人之始末”与“叙一事之始末”是类同的。
二
上面有关“传记”的看法对于把握《世说新语》的传记性质是很有帮助的,可是我们在此并不打算从“记人”与“述事”的角度切入,而是主要从《世说新语》的重要特征即门类的角度来解析其传记性。
首先,就《世说新语》门类来看,这些类目的设置很多是针对人物性格及行为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同一类目之下汇辑性质相似的人物行为及相关事迹,这实际上近于正史列传体的类传或合传。也就是说,《世说新语》三十六门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三十六篇传记。此处试举几例,比如《栖逸》篇,这一门共收录十七条材料,现摘录数条: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廞得笺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67页。
孔车骑少有嘉遁意,年四十余,始应安东命。未仕宦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谓有道术,为生立庙。今犹有孔郎庙。*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69页。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苻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訏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70-771页。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75-776页。
读这些条目,显然与《晋书·隐逸传》没有什么差别,特别是《晋书·隐逸传》还收录了《刘驎之传》:
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驎之固辞不受。冲尝到其家,驎之于树条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闻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后方还,拂短褐与冲言话。父使驎之于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辞曰:“若使从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驎之虽冠冕之族,信仪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侯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其仁爱隐恻若此。卒以寿终。*[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33-1634页。
本传载录刘驎之四件事,而《栖逸》篇只载录两件,这两件事与本传类似,可是却叙述存在差异,尤其是桓冲之事。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
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驎之方条桑,谓冲:“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驎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浊酒菹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斥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妪疾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71页。
不难发现,《晋书》的记载与邓粲《晋纪》接近。余嘉锡先生据王隐《晋书》的记载,指出“粲所纪驎之事,乃亲所见闻,皆实录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73页。,那么,《栖逸》篇所记刘驎之与桓冲之事当是刘义庆别有所据。尽管如此,《晋书·刘驎之传》与刘义庆《栖逸》篇所记刘驎之在书法上是相近的。同时依据上面所引资料的对比,《栖逸》篇视为一篇《隐逸传》也未尝不可。
又如《贤媛》篇,共收录三十二则资料,它们的组合其实就是一篇《列女传》,比如本篇载录“王武子为妹求兵家子”条,此条也见于《晋书·列女传》:
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父徽,黄门郎。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既适浑,生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谓浑中弟沦也。琰女亦有才淑,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帏中察之,既而谓济曰:“绯衣者非汝所拔乎?”济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其人数年果亡。琰明鉴远识,皆此类也。*[唐]房玄龄等:《晋书》,第1675页。
这里叙述钟氏两件事,划线部分即是描述“王武子为妹求兵家子”之事,对比《贤媛》篇,二者叙述是相近的。至于钟氏的另一件事,也见于《世说新语》,《晋书》将它们合编在一起,便构成《晋书·列女传》有关钟氏的传记。《晋书·列女传》还为陶侃的母亲湛氏立传,其文曰: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资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鄱阳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时大雪,湛氏乃彻所卧亲荐,自锉给其马,又密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逵闻之,叹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显。*[唐]房玄龄等:《晋书》,第1676页。
陶母款待范逵之事又见载于《贤媛》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卓、顾荣诸人,大获美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11页。
两者叙述虽然有着差异,《晋书》简而《贤媛》篇繁,后者可补足前者,但基本事态是一致的。依据这些例证,可知《晋书·列女传》的书法与《贤媛》篇大抵近似,并且有些传主及其事迹也同于《贤媛》篇,因此,将《贤媛》篇视为一篇列女传记是符合实际的。
再来看《排调》篇这个例证。早期社会尽管已经出现谐隐现象,但文献对于优语的记载并不多见,即使有所记载,也往往偏于国政家事一面。司马迁撰写《滑稽列传》,说明这种传统已经引起史家的关注,但就其载录而言,仍然是强调实用性的特征。到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虽然没有专门设立《滑稽列传》,但《东方朔传》其实可以视为一篇“滑稽列传”。在这篇传记中,班固没有忽略东方朔“直言切谏”的一面,但也花了相当篇幅描述东方朔的“诙笑”,这种“诙笑”更多的具有娱乐的特色。也正是到班固这儿,优语的娱乐性开始凸显出来。其实,早期社会中不是缺乏这种娱乐性,而是这种娱乐性被有意地忽视,从而造成缺失的错觉。由于班固的示范作用,优语的娱乐性就被赋予某种正当性,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也就出现在世人面前,邯郸淳的《笑林》就是显著例证。《排调》收录六十五则材料,比如: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29页。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39页。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46页。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50页。
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砂砾在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53页。
这些条目载录的纯粹是一些可资捧腹的笑料,比如第一条,晋元帝皇子出生,于是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恩时说此事自己并无功劳,却受此厚赏。元帝笑着说这件事怎么能让你有功劳呢?像这些的玩笑在日常是经常遇到的,一般并无大的教益,纯粹只是让人笑乐。然而联系此前的《滑稽列传》《东方朔传》来看,《排调》也可以说是一篇“滑稽列传”。
三
三十六门通常是依据人物的行为来设置的,这样,每一门便是特定某一类人物行为的聚合,这种聚合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载录每一类人的类传。这是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的。《世说新语》的传记特质,除了这种门类形式所形成的传记之外,事实上还存在其它形态的传记,这又可以从个人或家族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来看个人性质的传记。分析起来,《世说新语》的个体传记其实又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在特定的每一门内,一种是贯穿好几门。《世说新语》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在对每一门材料的辑录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每一门内材料的辑录上。在每一门内,性质类近的资料、特别是同一个人的资料往往会编撰在一起,比如《德行篇》的第10至13则都是关于华歆的: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 :“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4-17页。
这四条资料被安排在一起,实际上相当于华歆的一篇小传记。又如《文学》篇第1至3则是关于郑玄的: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23-228页。
又如《捷悟》篇第1至4则是关于杨修的:
杨德祖为魏公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提“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 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魏武征袁本初,治装,余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并谓不堪用,正令烧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椑楯,而未显其言。驰使问主簿杨德祖。应声答之,与帝心同。众伏其辩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82-686页。
当然,这四则曹操均在其中,视为曹操的小传记也未尝不可。又如《贤媛》篇第6至8则是关于许允妇的: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如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倾之,允至。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钟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89-793页。
第一条记载许允妇新婚如何留住许允,第二条描述许允妇如何使许允免却魏明帝的责罚,第三条记载许允被晋景王诛杀之后,许允妇如何保全儿子。合这三条观之,许允妇贤惠的形象就呈现出来了。又《术解》篇第5至8则是关于郭璞的:
陈述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所言。
晋明帝解占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帝问:“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问耳。”
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其诗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磊磊三坟,唯母与昆。”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30-833页。
这四条载录郭璞作为术士其预见的神奇。
以上列举数例,可以看到在《世说新语》有的门类中,刘义庆将某一具体人物的若干事迹编连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传记的特征。不过,从语类文献传统来看,《世说新语》的这种特征并不意外。《国语》早已出现类似的文体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当然,就《世说新语》个体传记而言,还需注意另一种情况,即跨门类的个体传记。这种传记的特征在于,一个人的事迹散布于《世说新语》各门类,倘若将这些事迹聚敛在一起,就相当于一篇传记。比如王衍(夷甫):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0页。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38页。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38页。
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39页。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遂相与为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45页。
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16-417页。
王夷甫与裴景声志好不同。景声恶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诣王,肆言极骂,要王答己,欲以分谤。王不为动色,徐曰:“白眼儿遂作。”*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20页。
王夷甫长裴公四岁,不与相知。时共集一处,皆当时名士,谓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计!”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20页。
晋宣武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 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构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60-461页。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62页。
人问王夷甫:“山巨源义理何如?是谁辈?”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3页。
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5页。
王夷甫语乐令:“名士无多人,故当容平子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页。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间夷甫、澄见语:‘卿知处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论;处明亲疏无知之者,吾常以卿言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试。顷来始乃有称者。’展常人正自患知之使过,不知使负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31页。
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99页。
王夷甫云:“闾丘冲优于满奋、郝隆。此三人并是高才,冲最先达。”*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03页。
王夷甫以王东海比乐令,故王中郎作《碑》云:“当时标榜,为乐广之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04页。
王夷甫妇郭泰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侠,犹汉之楼护,郭氏惮之。夷甫骤谏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卿不可。”郭氏为之小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57页。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疾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58页。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18页。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19页。
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08-809页。
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42-943页。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懔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979页。
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厷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徙!”*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14页。
据粗略统计,《世说新语》有关王衍的记载共二十五条,其事迹散见于《言语》《文学》《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容止》《贤媛》《排调》《轻诋》《黜免》诸篇。透过这些条目,王衍清谈大家的形象得到比较清晰地呈现,他在当时的地位、影响及人们对他的观感也得到较好描述,而这一切,实际上又构成王衍的传记。事实也确实如此,《晋书·王衍传》载: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兒!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为平北将军,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时报。衍年十四,时在京师,造仆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祜名德贵重,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众咸异之。……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樏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也。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唐]房玄龄等:《晋书》,第813-815页。
《晋书》在撰写王衍传记时,有些事迹显然与《世说新语》相同,如划线部分。这不但说明《世说新语》有关王衍的书写成为《晋书》本传的来源,同时也意味着《世说新语》这些材料的传记特质。当然,存在这种状况其实并不意外,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相关内容时就取材于《国语》《论语》,其中《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更是如此,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载: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67页。
这段颜回的传记,其基本材料来自《论语》: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杨伯峻:《论语译注》,第55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杨伯峻:《论语译注》,第59页。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8页。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3页。
《论语》大约有十九条有关颜回的记载,《史记》有关颜回的传记除一条资料之外,余者均来自《论语》。可见语类文献不但本身具有传记的特质,同时也成为正史传记的文献来源。
四
《世说新语》还存在家族传记。与个体传记一样,《世说新语》的家族传记也有两种形态:一是某一特定门类出现家族传记,二是几个门类的资料合在一起形成家族传记。先来看第一种情形。《言语》篇有四则是关于孔融家族的: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 :“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 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6-76页。
前三条即第3至5则,第四条即第8则。在这四条中,有两则是直接关于孔融的,有两则是关于他的儿子的,这可以视为父子二代的小传记。又如《任诞》篇选录11条有关阮籍及其家族的材料: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 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53-864页。
上面的记载主要以阮籍为主,但围绕他而述及其嫂、其弟、其子等事迹,其实就是一篇家族文献,家族传记。在《世说新语》某一门类中,像孔融、阮籍这样汇辑某一家族材料的现象还存在。其实,《世说新语》的家族传记更多的是分散式的,即某一家族的材料散布在好些门类中。比如贾充,其事迹见于《政事》《方正》《贤媛》《惑溺》诸篇:
贾充初定律令,与羊祜共咨太傅郑冲。冲曰:“皋陶严明之旨,非仆暗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润。”冲乃粗下意。*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01页。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40-341页。
贾充前妇,是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后遇赦得还,充先已娶郭配女,武帝特听置左右夫人。李氏别住外,不肯还充舍。郭氏语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仪,多将侍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语充,充曰:“语卿道何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02页。
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祔葬,遂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05页。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76页。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78-1079页。
将这些地方的资料聚合起来,大致构成一篇以贾充为主的家族传记。范子烨先生在讨论《世说新语》的编者时谈到氏族谱系问题,指出彭城刘氏见于《世说》的有五位,琅琊王氏一族约有八十人,谢氏一族有二十人,吴郡陆氏家族有十位,这些其实均形成家族传记。当然,《世说新语》涉及的家族远不止这些,其家族传记自然也就很多。
这里有必要就语类文献中的家族传记做一些说明。家族文献其实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一组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这组礼器共27件,包括盂、壶、鬲、匜、盘、盉、鼎7个器种,其中除盂以外的26件器物均属同一人即“逑”所作器。逑盘铭文叙述单氏世系,提到的单公为单氏第一代,属于文王、武王时期,公叔为成王时期,新室仲为康王时期,惠仲猛父属昭王、穆王时期,零伯属恭王、懿王时期,亚祖懿仲属孝王、夷王时期,皇考恭叔为厉王时期,逑本人则属于宣王时代。*董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4期。通过逑盘铭文的记载,为单逑及这些器物提供比较清晰的家族背景,实际上可视为同一家族文献。到班固撰写《汉书》时,特别注重家族史的叙述,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这些传记中的传主都不是一个人,而是叙述几代人的事迹。到魏晋时代,更是出现大量的家史文献。语类文献中往往存在家族文献,《国语·周语》选录有七条单氏家族的材料,应该与这里讨论的单氏家族有关联,甚至很可能属于同一家族。其实,《国语》还存在较多的家族文献,比如《鲁语下》从第10条到第17条共八条皆涉及公父文伯之母,其间又多记公父文伯同宗之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之言行,有的学者据此推测“这些脉络清晰、内容集中的材料极有可能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家语,至少来源于最早的家语”*俞志慧:《〈国语〉(周、鲁、郑、楚、晋语)的结构模式及相关问题研究》,《汉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又如《晋语》有关赵简子、范武子、叔向等人的系列材料,很可能就出于他们的“家语”。这些家语文献其实具有家族传记的特征。这些传统显然影响到《世说新语》传记的生成。而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时代别传、家史的撰写非常流行,瞿林东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视野开阔,撰述多途,除记一代皇朝之史外,在民族史、地方史、家族史、人物传、域外史、史论、史注等许多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23-227页。这种撰史风气,特别是家族史、人物传给予《世说新语》的编撰以深刻之影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曾引用经史子集四部著作四百十四种,其中以史部著作二百八十四种为多。而在史部著作中有杂传一百四十三种,占史部著作半数以上。而杂史之中却有别传八十九种,又都是《隋书·经籍志》所没有著录的。……除此之外,并引用其他的杂传,如郡书、家传、类传、志异作品五十四种。……所以编辑魏晋人物逸闻轶事的《世说新语》,不单纯是文学作品。而且刘孝标的注释更引用了大批当时的史料,因此其所具的史料价值是可以肯定的。同时,《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人物,分别在不同的正史中出现,不论怎样他们都该属于历史人物,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趣与情感的发抒,也该属于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说明《世说新语》和这个时代的历史关系”*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3-124页。。这样,《世说新语》传记文体之形成就并不显得意外。
(责任编辑:晏 洁)
The Biography Style ofShiShuoXinYu
XIA De-k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genre literature tradition sinceGuoYu(StateBiography),ShiShuoXinYuis a document of history biography, for it contains distinctive biography traits in its style, as is manifest as follows: firstly, under one entry are grouped characters of similar nature and their deeds, which is equal to an integrated biography in authentic history; secondly, there are biographies of persons, that is, data of an individual are often collected and arranged under one entry, which is roughly approximate to the biography of a person, or in other words, tales of an individual, though narrated in various entries, can be pieced together, which is virtually a biography; thirdly, in the book can also be found family biographies, which are presented in two forms—one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amily biography in one certain entry, and the other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family biograph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e data in various entries.
ShiShuoXinYu; biography genres; the biography of individuals; the biography of families
2016-10-12
夏德靠(1974-),男,湖南溆浦人,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I206.2
A
1674-5310(2017)03-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