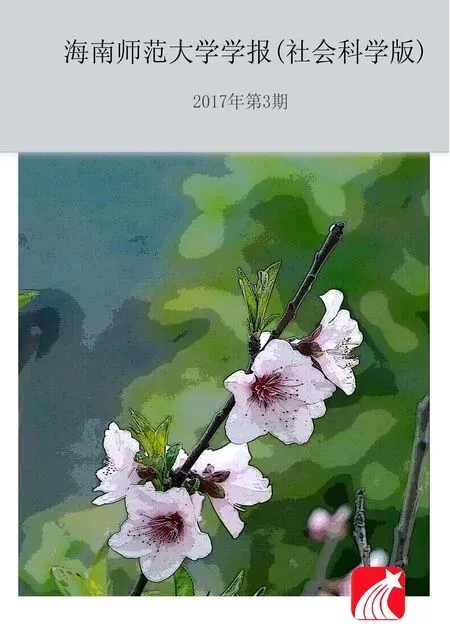林庚新格律诗论的语言结构
2017-03-11赵黎明
赵黎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林庚新格律诗论的语言结构
赵黎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林庚是将古典文学研究与新诗形式探索进行有机结合的诗论家,其所提出的“半逗律论”、“节奏音组论”、“普遍形式论”等,便是此种“沟通新旧文学”的重要收获。无疑,这些成果丰富了新诗理论,对新诗文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以乐诗为标准对待新诗节奏、以字本位为预设建设“普遍形式”、以唐诗趣味为规范处理“语言诗化”——这种以古典规范为语言结构的新格律论,不仅存在古与今、新与旧的巨大错位,而且有着逻辑与历史分裂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执着于“古典性”与“民族性”的诗学理论,天然具有固守传统和拒斥外援的倾向。因此,对这类新古典主义新诗理论要有一个清醒的、辨证的认识。
林庚;新格律诗论;语言结构
林庚(1910-2006)是现代著名诗人,也是独树一帜的文学史家,其对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是新诗形式探索与文学史研究的自觉结合:要以文学史上的现象“说明文坛上普遍的问题”*林庚:《自序》,《中国文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这种“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不仅受到先辈学者朱自清的嘉许,还为后世学者屡屡称道,袁行霈先生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用着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袁行霈:《总序》,林庚:《中国文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葛晓音先生也总结道,林庚的主要贡献,一方面有意识地在创作中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一方面在文学史研究中发现“民族形式”的演变规律,以为新诗形式的殷鉴。*葛晓音:《前言》,《林庚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林庚晚年也如此夫子自道,谓其古典文学研究与历代同业者的不同在于:“我写文学史着眼点却是在未来,是为新文学服务的。”*林庚:《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他强调自己研究古典诗歌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为中国新诗找到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
在林庚的诗学视野里,中国诗歌经历了从四言到五七言乃至九、十、十一言的演变趋势,遵循着从“自由”走向“格律”的历史规律,这种理论被称为“新格律论”。新格律论议题广泛、内容丰富,但核心构件无外乎“半逗律论”、“节奏音组论”、“典型诗行论”、“普遍形式论”等几个部分。这些理论的价值当然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其产生语境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易言之,是其据以言说的构成性要素(语言结构)是什么?其有效性的语文前提何在?其对“民族形式”的执着,会产生何种价值取向?等等。
一、“诗乐一体”:林庚“节奏论”的原始构型
在中国古代,诗乐一体是关于诗歌起源的基本常识。这种观念最早源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记·檀弓》《乐记》《毛诗序》等有关言述,都是对此经典的发挥;后世论家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也多是在此基础上的推绎。翻开古人诗话,类似叙述不胜枚举。如宋人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宋〕郑樵:《通志总序》,吴文治:《宋诗话全编(4)》,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474页。明人李东阳以《诗经》为例强调:“诗乐至一也……诗而不可乐,非真诗也。音曰清音,感曰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诗乐之理尽是矣。”*〔明〕蔡复一:《寒河集序》,吴文治:《明诗话全编(7)》,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7318页。清人也以此为据解释各种诗歌现象,黄宗羲说:“原诗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清〕黄宗羲:《乐府广序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页。张泰来则说:“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唐人律诗,亦是乐府也。”*〔清〕张泰来:《钝吟杂录·正俗》,丁福保:《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42页。吴乔直接以《尧典》为据,说明诗与乐的同根关系:“诗乃乐之根本也。乐既变而为元曲,则诗全不关乐事;不关乐事,何以为诗?”*〔清〕 吴乔:《答万季力诗问》,丁福保:《清诗话(上册)》,第33页。当然,古人强调诗乐一体,并不意谓诗即是乐,而是专指“起源于配乐歌唱”,着重于“以字的音乐做组织”的“乐语”。*〔美〕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反映在文字形式上,就是诗歌的节奏韵律。“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页。文笔之分的根据在于韵律节奏的有无,刘勰的观点反映了传统诗学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古典文体家大致认同了这一观点。李东阳说:“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明〕李东阳:《镜川先生诗集序》,吴文治:《明诗话全编(2)》,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1664页。因此,诗歌创作必须遵守文体规范,“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明〕李东阳:《春雨堂稿序》,吴文治:《明诗话全编(2)》,第1670页。。可见,在传统观念中,“节”之于诗,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本体性存在。
在古典诗学系统里认识林氏节奏理论,其“飞跃说”的来龙去脉便会一目了然。林庚认为诗歌所以保留韵脚这一原始器官,不是人们任意添加上去的,而是因为歌舞的天然关系造成的,“歌舞在艺术的原始上乃是孪生的”;韵脚“有规律的隔着一定距离而一次次的出现”,带来的是“舞蹈中鼓板”的效应,这种“均匀的节奏感”对于诗歌语言而言,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的。*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8-219页。在他看来,诗歌节奏就是语言的“飞跃性”,它的来源正是歌舞乐的原始基因。他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这种基因的功能:“接触到这样的节奏就不禁会感染到它的力量而想要跳跃起来;因此它在诗歌上也就有利于语言的飞跃。它的有规律的均匀的起伏,仿佛大海的波浪、人身的脉搏,第一个节拍出现之后就会预期第二个节拍的出现,这预期之感具有一种极为自然的魅力。这预期之感使得下一个诗行的出现,仿佛是在跳板上,欲罢不能,自然也就有利于语言的飞跃。”*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第218-219页。他还将这种节奏的作用,形象地比喻为“欲擒故纵”,并详细分解其功能作用。以分行为例,他说,分了行不免要停一下,这便是“擒”;可是虽然停止却还要再继续下去,这便是“纵”。在他那里,“擒”就是“节”,“纵”便是“奏”,节奏就是由人为的语言动能而造成的跳动飞跃趋势。“‘节’的本义是‘止’是‘制’,‘奏’字的本义是‘进’是‘走’;我们明明是要‘进’要‘走’,却偏偏要‘制止’一下;这样便产生一种自然的趋势,那便是非跳不可!我们平常走路原是连续的,但是在要跳之前,却要故意制止一下;前者便是散文的语言,后者便是诗的语言;诗的语言如果没有跳跃,那么何必多此一个停止呢?节奏将变为毫无意义的了。”*林庚:《诗的语言》,《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33页。这里,他用舞蹈的跳跃、音符的流动来比附文字的运动,这种认识显然打上了传统观念的深刻烙印。
值得注意的是,林庚还认为节奏形式并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经年累月“自然形成”的结果。以四言诗为例,他强调说四言之后,大约经过了两百年,直到楚辞形成一种新的语言节奏;楚辞之后又经过四百多年,一种介乎四言与七言之间的五言形式才告形成;五言之后又经过四百多年自然生长,七言才慢慢成熟。*林庚:《再论新诗的形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38页。在他眼里,一种节奏形式的形成,就像植物生长一样,有发芽、成熟、结果的自然周期,人力固然可以催促生长,但是内在结构是无法改变的,这似乎意味着,语言节奏是内在于诗歌的本体性因素。
既然认定节奏是诗语的内在属性,那么就可以此为准来进行“诗文之辨”了。实际上古人“辨诗”使用的正是这个标准。明代诗学以辨体为擅长,其区分诗与文的标尺,就是有否“声律讽咏”:“诗之体与文异……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明〕李东阳:《沧州诗集序》,吴文治:《明诗话全编(2)》,第1661页。基于这种认识,极端者甚至认为,诗与文是两种不可兼容的文体,“诗与文异体,不可相兼”*〔明〕黄廷鹄:《诗冶序》,吴文治:《明诗话全编(7)》,第7699页。。具有“复古”倾向的章太炎也坚持,诗之有韵,古今无所变:“大抵有韵者为诗,无韵者为文。《尚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云云,可见诗必有韵,方能传达情绪;若无韵亦能传达情绪,则亦不必称之为诗。”*章太炎:《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上海:平民印务局,1924年,第72页。总之,在古典诗学语境里,“音节”的有无乃是区分诗文的关键要素。
林庚诗文之辨的有关理据多是从此脱化而来。他认为,诗歌语言不同于散文语言的关键所在,是有无“节奏”,而在他那里所谓“节奏”无非是一种“起跳的动作”,“散文像一条线似的直走,诗歌是在跳着走,因而有旋律”*林庚:《林庚先生访谈录》,《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56页。。这不是原始乐舞遗痕而何?照这样看来,一旦失去了节奏,诗歌语言势必变成散文语言,诗歌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诗的语言在离开诗的形式时,便必然落于散文的形式。”*林庚:《诗的语言》,《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36页。总起来看,不论是诗歌节奏的本体论,还是由此产生的诗文之辨,林庚的格律理论无不根植于华夏诗学的深层结构,是对“乐诗”传统的一种现代生发。
二、“字本位”:“普遍形式”论的思维基础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在今人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常识,但在中国传统语境,此种定义完全是一种误识。何以如此?这是由传统语文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古文系统里,“言”是言,“文”是文,“言文分离”早成常态。就“言”而论,“言”必就于“文”方能立足;对“文”而言,则必托于“字”才能独立,因此,在这个以字为本位的书写系统里,字才是语文的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申小龙:《汉字人文性反思》,谢冕、吴思敬:《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8页。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学不能称为语言艺术,而应叫做文字艺术。
受这种文字制度制约,古代诗歌在字音、语法、词汇、修辞等方面,均表现出迥异于拼音文字的独特面貌:空间要求均匀对称,时间讲求平仄相依,对单音字的构成要素(特别是音的要素)提出了极高要求,“声调抑扬的现象是古代汉语习惯的一部分,也是古代汉语语言艺术的一个部分”*启功:《诗文声律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页。。这种状况直到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后才得以改观,在“我手写我口”、“言文一致”等口号推动之下,复音词大量涌现,外国语法不断改造,以句群为单位的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代替了以单字为本位的汉语书写系统。因此,文言和白话虽然同用汉语书写,但实际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书写系统,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也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学形式。关于这种区别,傅斯年当时就曾强调指出,他批评各种古典派“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对语言、文字、文学的多重危害:“语言学的概念不和文字学分清楚,语言学永远不能进步;且语、文两事合为一谈,很足以阻止语的文学之发展,这层发展是中国将来文学之生命上极重要的。”*傅斯年:《泛论·语言和文字》,《傅斯年全集(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页。郭绍虞则更为明确地点明:“以前的文学,不论骈文古文,总之都是文字型的文学,不过程度深浅而已。现在的白话文学,才是真的语言型的文学。”*郭绍虞:《语义学与文学》,《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4-345页。因此,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区分,不只表现为思想意境的不同,还有语言文字的差别。
以研究古典文学名家的林庚,何尝不知文字型与语言型文学的区别,他说,“五七言是秦汉以来以至唐代的语言文字最适合的形式,而今天我们的语言文字显然不同了”*林庚:《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45页。;又说,“我们如果还继续写文言诗,那么旧诗词的形式显然还是最相宜的;可是无奈我们今天要写的是白话诗,那么旧诗词的形式显然是不相宜的了”*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第215页。。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他在谈论语言型文学——新诗的形式问题时,仍然有意无意地使用了文字型文学的某些标准。
当然,不能否认,林庚建构新格律诗学的出发点,是为了打通古今壁垒,建立一种古今通用的“普通诗学”。他当然知晓中国诗歌的古今之别,相信文言与白话各有对象,且是一种进化关系;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新诗、旧诗之间必有某种交集,而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形式”,“‘诗’原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诗如果没有形式,诗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林庚:《再论新诗的形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39页。。在他看来,汉语诗歌的共同元素,并非常人所认为的双声、叠韵以及平仄对仗,这些不过是语言上的“讲究”和装饰,“对于诗歌形式来说,这种讲求是附加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对于繁荣诗坛来说,其作用也从来只是从旁的而不是主要的”*林庚:《再谈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82页。。甚至连诗歌的形式都谈不上,“它并非诗的形式,也不足以代替诗的形式”*林庚:《再论新诗的形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39-40页。。那么到底什么是诗的“形式”?什么又是诗的“普遍形式”呢?他认为:“诗的形式的真正的命意,在于在一切语言形式上获取最普遍的形式。”*林庚:《再论新诗的形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39-40页。这里要分两个层次、两道程序:一个是特殊形式,如几言、词牌、曲牌等;一个是普遍形式,它是对特殊形式的再一次萃取。对于这种“普遍形式”,他有过几次理论总结。据他自述,经过从1935到1950年的15年“摸索、创作、体会”,“我所得到关于建立诗行的理论不过两条,一是‘节奏音组’的决定性,二是‘半逗律’的普遍性”*林庚:《从自由诗到九言诗(代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25页。。在另一个场合,他对这两点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加上一条关于节奏点的“典型位置”原理:
一、要寻找掌握生活语言发展中含有的新音组。在今天为适应白话中句式上的变长,便应以四字五字等音组来取代原先五七言中的三字音组;正如历史上三字音组来取代四言诗中的二字音组一样。二、要服从中国民族语言在诗歌形式上普遍遵循的“半逗律”,也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三、要严格要求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如果它或上或下,或高或低,那么这种诗行就还不够典型,也就还不能达于普遍。典型是使诗行富于普遍性的关键问题,正如五言之必须是“二·三”,七言之必须是“四·三”,而不能是“三·二”或“三·四”。*林庚:《〈问路集〉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5页。
这段文字可说是他对“普遍形式”论的简短概括,其一生所有探索都是围绕这样几点展开的。
客观地讲,上述结论不少是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而出的经验之谈,对新诗形式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其大部分经验来自于古诗文字规律,打上文字型文学的深深烙印,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其新诗形式探索的脚步。
首先,关于“普遍形式”。在他眼里,不论新诗还是旧诗,一定遵循着一种普遍规律,即有一个普遍有效的形式。既然是普遍规律,就要遵循“既严格又简单”的一般原则,如“五言诗的形式就是二三,七言诗的形式就是四三”*林庚:《再谈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88-89页。。意思是说,如把五言变成了三二,就不再是五言诗的形式;同理,若将七言变成了三四,也就不再是七言诗的形式。以两句五言诗为例:“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他认为前者(三二)就不是五言诗;再以两句七言诗为例:“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他也认为后者(三四)就不是七言诗。他总结道,这是普遍形式的基本要求,“这是界限分明毫不含糊的”*林庚:《再谈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89页。。事实很明显,他的所谓“普遍”,实际只“普遍”在古典诗词方面,对于现代新诗,他以古诗为例总结的“普遍形式”是否有效,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疑问。
其次,关于“半逗律”的普遍性。何谓“逗”?他认为是一种“类似pause的作用”,亦即语气的停顿,其情形类似于西方的“音步”、古代的“兮”字等。他从中国文字的特点出发,认为中国诗歌建行的规律,是根据字义的划分即句逗作用来进行的,如每行划分为四言、五言、七言,而一行之中又划分为二·二、二·三、四·三等各种制式。在这些制式的诗行中,字义切分之处便是“逗”,它是节奏产生的关键所在。以他的观察,从四言的二·二、五言的二·三,到七言的四·三,古代诗歌语言形式有一种逐渐放长的趋势,每一次放长都是因为“新音组的出现”,进而他预测:“今天的白话诗行必须建立在比三字音组更长些的新音组上,而随着新音组的加长,诗行也就自然的会变得更长些。”*林庚:《再论新诗的形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41-42页。为此,他在创作实践中有意进行了九言(五·四)、十言(五·五)、十一言(六·五)的试验,认为这些诗行都是可行的典型诗行;而通过这些语言实例,他进而推断出“中国诗歌形式从来都遵守着一条规律,那就是让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这样自然就把每一个诗行分为近于均匀的两半;不论诗行的长短如何,这上下两半相差总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第222页。。他总结说,这种“半逗律”就是汉语诗歌普遍的民族形式。显然,这种推断,仍然忽略了古典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把古代语文中的某种规律加以泛化,将“片面的”民族形式认作是汉语诗歌普遍的民族形式。
最后,节奏点位置的绝对性。节奏点就是“半逗律”的“逗”的落脚点,节奏点位置的绝对性是指“逗”“必须严格固定在诗行的绝对位置上”*林庚:《再谈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95页。。在他看来,几字音组的节奏切分,并不可任意而为,每个切点有其固定的位置,排列顺序一旦改变,诗行的性质也随之而变。“五言诗行就只能是‘二·三’而不能是‘三·二’,七言诗行也只能是‘四·三’而不能是‘三·四’,否则就不是典型的五七言诗。因为如果上下一颠倒,字数虽然照样,‘节奏音组’却变了。诗行的性质也就跟着变了。”*林庚:《从自由诗到九言诗(代序)》,《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25-26页。他还以九言诗行为例,认为“五·四”式和“四·五”式节奏完全是不一样的,进而断定九言诗的“五四体”“最接近于民族传统,也最合适于口语的发展”*林庚:《九言诗的“五四体”》,《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47页。。与前述问题一样,林庚总结汉语诗歌节奏点位置的规律,所举诗例仍然局限在律诗绝句古体诗上,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汉诗与古典诗词之间巨大的语言鸿沟。
三、唐诗兴味:林氏“语言诗化”论的人文根基
如所周知,中国诗素以抒情见长,有着悠久的“抒情传统”*这种传统早被学界所注意,如陈世骧就有《中国的抒情传统》(见《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予以专门揭示;王德威先生近年又做进一步发挥,其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三联书店2010年版)在学界引起广泛涟漪,响应之声不绝如缕。。这种传统直可上溯到汉诗的源头:《诗经》多为个人的低吟浅唱,诉说的是“人类日常的焦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楚辞》也不过是楚的悼亡诗,其不同文体如祭歌、颂词等,也是“用韵文写成的激昂慷慨的自我倾诉”。*〔美〕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陈世骧文存》,第1-2页。这种抒情形态不仅塑造了民族文学的心理基座,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类结构。后世诗歌多是沿着这个河床蜿蜒而下,基本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诗学道统是由言志诗学构成的,中国诗学体统则非抒情体莫属,由这种道体合一而构成的抒情文类,是华夏诗学迥异于西方的文体构型。对于这一点,林庚是有清晰认识的,他曾经说过:“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唐诗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76页。他的很多关于诗歌语言的观点都从这一认识开始。
林庚以唐诗研究名家,其“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著名术语,常为学界所津津乐道。他自述“特别喜爱唐诗”,喜爱它“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新鲜有力、富于生气”*林庚:《我为什么特别喜爱唐诗(代序)》,《唐诗综论》,第1页。的生命活力。非常明显,他偏嗜唐型文学,艺术倾向上有一种浓厚的“唐诗趣味”。而唐型诗正是中国抒情诗的最佳标本。作为一种抒情文类,唐诗“吟咏情性”,“一唱三叹”,具有一种血性少年的率真之气;唐诗直抒胸臆,“不假雕饰”,“浑成无迹”,具有清水出芙蓉的天然品格,因此它被历代文人看作抒情诗的正宗。“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88页。严羽所描述的盛唐之诗,实即中国抒情诗的艺术典范。
唐型文学的熏陶,造就了一批偏嗜唐趣的读者,也造成了一种风格改变的难度,宋诗的出现一直受人抵制大概就出于这个原因。“作者当以盛唐为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浑成无迹,此所以为盛唐也。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傍韵,牵强成章,此所以为宋也。”*〔明〕谢榛:《四溟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43页。习惯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人们,对“专重转合,刻意精炼”甚为不满也就顺理成章,历代以正宗自居的诗论家,往往将“才学”、“议论”、“文字”入诗的宋诗,列为“诗家旁门”*〔清〕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丁福保:《清诗话(上册)》,第152页。。
在唐宋之争的脉络里观察林庚,其诗学趣味是颇有意味的,其对唐诗的喜欢,与其说是对一种文学类型的偏爱,不如说是对中国抒情诗“正宗”的坚守。这种趣味尚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诗语类型的选择方面。他喜爱唐诗,就按照唐型文学标准建立诗语,不管这种语言是否也有某些局限;他反对宋诗,就将宋诗语言列为对立面,哪管这种语言某种程度暗含着进步。这种倾向比较典型地反映在其“语言诗化”理论里。
林庚的“语言诗化”论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诗歌语言须从日常生活语言中来,二是要对生活语言进行一番“诗化”处理。而“语言诗化”的程序则是“捕捉日常语言中所难以捕捉到的新鲜感受”*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唐诗综论》,第279页。,并对此种语言进行祛除“概念性”与“逻辑性”的二度处理,从而形成富有感性、形象性与飞跃性的诗歌语言,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包括词汇、句式、语法在内的全方位语言提纯过程。“诗歌语言突破生活语言的逻辑性和概念的过程就是诗化。”*林庚:《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65页。
照着这个标准,他认为唐诗语言就是诗歌语言的典范。首先,唐诗语言来自生活,“唐诗那么好,就因为唐诗的语言就是唐朝人生活里的语言”*林庚:《我们需要“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69页。。其次,唐诗语言有一种“深入浅出”的功夫。在他眼里,唐代诗人“以豪迈的生活信念”,以及对新鲜事物的高度敏感,“吸收着、创造着”富有实感的全新语汇,“使诗歌的语言步入更为深入浅出的天地”*林庚:《唐诗的语言》,《唐诗综论》,第103页。。再次,唐诗语言自然而然,毫无雕琢之痕,“这里既无典故,也无堆砌,既无所谓模拟,也无所谓雕琢。仿佛生活本身就已经是诗了”*林庚:《唐诗的语言》,《唐诗综论》,第103页。。他引用《诗品·序》“直寻说”的名言,强调“诗歌中的形象最好是直接是从事物本身得来”*林庚:《唐诗的语言》,《唐诗综论》,第99页。。尊唐的反面当然就是抑宋,这里所批评的“模拟”、“雕琢”无一不是针对宋诗而来。他认为,宋诗的衰落除了程式化之外,还跟语言的陈旧有关。据他考察,唐后期至宋初,乐府、七绝和长短句中都出现了古白话,但宋诗却对此视而不见,语言上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使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拉开了距离,导致宋诗语言资源枯竭从而最终扼杀了宋诗的生命,“尤其是江西诗派的形成,使因袭古人陈言的风尚牢笼诗坛二百年,诗歌语言乃离生活语言更远,这就进一步扼杀了宋诗的创造力”*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
显然,林庚的“语言诗化”说,是有不可抹煞的诗学价值的。他强调诗歌语言的实感性、新鲜性与飞跃性,反对语言的雕琢、因袭与远离生活,强调对生活语言进行去概念化的诗化处理等,这些睿见不仅是对既往诗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诗发展的警示,具有普遍的镜鉴意义。但是,其在抒情传统的单向道中对诗语规律的总结、在尊唐抑宋的文学趣味中对诗体变化的预测,也确实存在着某种偏狭与失准。这里权以“虚字减少”为例略作说明。
如前所述,林庚的“语言诗化”范围,不仅包括词汇、句式,还包括词法、语法等。在他看来,古代的虚字,如“之”“乎”“者”“也”“矣”“焉”“哉”等,一般只在散文中才出现的,其在诗中的逐渐减少,是一种从散文语言向诗歌语言的过渡,因而也是一种“语言诗化”现象。他认为虚字减少,至少有这样几种诗化功能,第一是使诗句更为“精炼、自由、解放”,“从而远离散文,让诗歌语言更具有生动性,更富于表现力”;*林庚:《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65页。第二是使诗歌语言突破生活语言的逻辑性和概念化,突出诗歌语言的感性因素,促进诗歌语言的飞跃性,“唐诗在诗歌语言上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为语法而有的虚字都可以省略,因为这些虚字都没有什么实感,省略了就更有利于飞跃”*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唐诗综论》,第279页。。他还将这种虚字减少现象“普通化”,认为它不仅适用于古诗,而且适用于新诗,“《诗经》《楚辞》里一般还用得较多,到了五七言古诗里就少了一些,到了近体诗中几乎是不见了;这个情形也很可以供新诗的参考”*林庚:《再谈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91页。。
虚字减少是否意味着诗化趋势?宋诗对诗语的变化,是否就是违背诗化原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作一辨析的。一般人贬抑宋诗,大多出于其喜用故实、以文字为诗以及知性增强等原因,岂知这正是诗歌语言文体的新变。宋人内敛的文化精神,体悟的格物方式,必然会影响到诗学表现,“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清〕翁方纲:《石洲诗话》,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26页。。宋诗超越了专注于即景抒情的唐诗范式,以诗与思、情与理的交融,表现出精细入微、鞭辟入里的知性特点。而在文体和语言上,也打破诗文壁垒、扩大语言界面,突破清澈透底的语言成规,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说,这是对唐诗传统的突破,也是一种诗歌语言的进化。林庚自己也曾指出,普通诗行有一种逐渐加长的趋势,如此看来,虚字的减少可能还不能视为“诗化”的表征,在古典诗语演变中是一种阶段性现象,而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中国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沟通桥梁。*有学者注意到了虚词增加与新诗形式现代化的关系:“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推动了中国传统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功能向叙事与哲理表现的多元路向发展,对理性的强调和叙事的融入,给中国现代诗歌增添了一种理性抒情与知性美感的新趣味。”见王泽龙、钱韧韧:《现代汉语虚词与新诗形式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四、林庚新格律诗论的语用悖论
与现代诗坛上各种古典派一样,林庚的基本策略仍是想在中国文字的基础上做一些翻新的功夫,与其“想在古旧的诗体范围中创造出诗的新生命”*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页。不同的是,林庚新格律论突破了五七言的藩篱,向现代语文大大迈进了一步。但即便如此,他的变革思路仍然拘囿在传统语文的范围之内,借助乐诗古老资源建构新诗节奏、以字思维传统指导新诗“普遍形式”、以唐诗趣味剪裁“语言诗化”,他的诗学思想里面有着古与今、新与旧的巨大错位,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逻辑与历史的内在分裂。这种矛盾最明显地体现在文字型与语言型文学的错位方面。如前所述,他据以挖掘的资源乃是一种文字型文学传统,它“重在文字的技巧,尚对偶,讲声律”*郭绍虞:《〈中诗外形律详说〉序》,《照隅室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4页。,与所欲给予的新诗文体并不在一个语文前提之下。当然,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区别,“我们知道五七言是秦汉以来以至唐代的语言文字最适合的形式,而今天我们的语言文字显然不同了”*林庚:《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45页。;同样也认识到了其与新诗语言的龃龉,“然而同样的五七言,如果用来作为今天新诗的形式,它就会束缚了新诗的内容,因为决定这个形式的诗歌语言乃是基于中古的文言,它已不同于今天白话的诗歌语言”*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第217页。。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执拗地坚持要以“五七言的传统形式”作为未来新诗形式的样板:“它支配了二千年来的诗坛及民间的文艺形式。我们顺着这一个形式的传统它就很容易普遍,离开了这一个传统就难以为大众接受。”*林庚:《新诗的“建行”问题》,《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44页。显然,这种矛盾使他在两种类型文学的变通中左支右绌。
林庚曾说:“我总希望在研究古典文学的时候,为新文学,主要是新诗的发展找到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借助古代的文化遗产丰富我们今天的创作。”*林庚:《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62页。以自己的古典文学擅长为新诗发展寻求资源支持,以“民族形式”遗产作为未来新诗形式的殷鉴,其经世致用的文学研究动机和借古鉴今的文学创作情怀值得嘉许。但问题也可能就出在这里。或许由于专业局限,或许因为对民族形式爱之切,在从事这项贯通古今的宏大工程时,他的眼界不幸常被自己的身影所遮蔽,致使其建构的眼光未能投向自身以外的远方。其语言形式“土壤论”便是最好的说明。关于中外语言关系,他反复强调一个比喻,文化跟自然一样也是一种土壤,土壤是由酸碱性质、矿物成分经年风化而成,不是想变就改变得了的;而语言则是这土壤中具有根性的组成部分,更不能随意加以改变,所以语言的移植是不可能的,“难道还能把土壤一起移过来吗?”*林庚:《我们需要“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75页。
据此,他不相信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在文学特别是在诗歌上面能够相互移植:“‘移植’某种植物要看气候、土壤,而且,并不是什么植物都可以任意移植。这在诗坛上也是一样。诗坛的‘土壤’乃是历史的累积,是语言、文字、文化信仰等根性的东西。”*林庚:《新诗断想:移植和土壤》,《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页。他还进一步阐明,作为文学惟一工具的语言文字,是决定产品形式的最重要因素,工具的形态直接影响着形式的形态,比如欧洲因为先产生了油性颜料,便决定了油画成为绘画中的主要形式;而中国则由于用毛笔直接作画,于是就产生了不用颜料的水墨画形式。文学上也是如此,“欧洲的语言有明确的轻重音,因此就产生了欧洲诗歌‘音步’的形式,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就产生了中国诗歌所特有的‘几言’的形式”*林庚:《导言》,《中国文学简史》,第10页。。
正是由于这种“土壤”信念,他不信西方形式在中国诗行中能够试验成功。也许有人质疑,商籁体在中国不是移植得很成功吗?在他看来,新月派等移植商籁体之所以侥幸成功,那也是得益于共同的土壤,即这个诗体四行一段的排列法,与中国传统诗行有着某种交集;而音步就不同了,英语中的轻重音为音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中文中就没有这个基础,因此他不相信音步能在中国土壤上成活:“汉语却显然缺少这种普遍而明确的轻重音,也没有类似轻重音的长短音。要在这样的土壤上建立所谓的‘音步’,岂不是有如无米之炊吗?”*林庚:《新诗断想:移植和土壤》,《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2页。他还以《湘夫人》中的诗句为例:“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进一步辨析音步的不合国情论:“如果按照音步看来,第一行无妨说是三步,可是,第二、三行却似为两步,第四行又似为四步,这里有什么规律可言呢?……这凌乱如果不归罪于这四句优美的诗行,那就只好归罪于我们强要把西洋诗歌中的音步(或顿数)加之于中国诗行上这样的做法。”*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第222页。注意,为了说明音节的中外之分,他这里举的全是古代诗例,在语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古今错位。
实际上,不论是现代西语,还是现代汉语,口语本位的自由诗中音步或顿的功能,已经由严格的轻重读音演变为宽泛的语气停顿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汉诗与现代西诗在语法、文法方面已经十分接近了。且以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例:
……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
从大的停顿单位上讲,首句后面连续用了8个“在……之后”,这些单元均可视作一个语顿;从音节构成来讲,古诗里的几言限制也不复存在,是一种无规律的杂言交错;而在语言结构方面,它以口语为基干,辅以欧洲语法,其繁复的句式使你辨不出它的中西身份。余光中的《芝加哥》亦是这样:“新大陆的大蜘蛛雄踞在/密网的中央,吞食着天文数字的小昆虫,/且消化之以它的毒液。/而我扑进去,我落入网里——/一只来自亚热带的/难以消化的/金甲虫。/……”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成功的诗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力地瓦解了林庚所反复强调的“民族形式的规律”,即所谓“让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的“半逗律”*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林庚文选》,第222页。。这里的“逗”,不论功能还是性质,究其实不过是一种语气的停顿,大可不必将其神秘化与国粹化。
语言这东西,既是本体的,又是工具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逐渐“一体化”的现代社会,语言融合程度远超人们想象。现代汉语中欧化的因素已经渗入血脉,你再也找不到纯粹的古风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还有加剧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汉语,而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语言新变。只要汉字不灭,现代汉语任其如何组合,都不会改变其中文性质,这一点尽可放心。汉诗自然也是如此。林庚对西方形式高度警惕,形成的原因或许很多,但对民族的、古典的形式过于执着,是不是一个主导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 Language Structure of Lin Geng’s View on New Metrical Poetry
ZHAO L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China)
Lin Geng is a poetic theorist engaged in explor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with new poetic forms, and his ideas like those on “semi-trivial rhythm”, “rhythm groups” and “the universal form”, etc., are vital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surely enriched the theory of new poetry and contributed positively to developing the style of new poetry. Nevertheless, this new metrical theory, which takes the classical norm as its language structure, embraces not only some huge disloca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s well a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but also the risk of division between logic and history. More importantly, this poetic theory persistent in “classicality” and “nationality” is naturally inclined to observe the local tradition and repel the foreign aid.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a sober and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such neo-classicism new poetry theory.
Lin Geng;new metrical poetry; language structure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新诗’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0XJA751006)
2017-01-10
赵黎明(1968-),男,湖北宜城人,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佛山科技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中外诗学和文学语言学研究。
I207.2
A
1674-5310(2017)03-005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