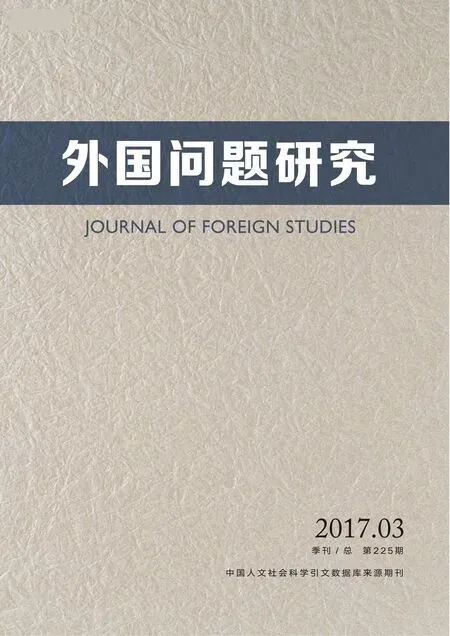论查理曼加冕与拉丁西方-拜占庭之间的政治疏离
2017-03-10朱君杙
朱 君 杙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论查理曼加冕与拉丁西方-拜占庭之间的政治疏离
朱 君 杙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公元800年的查理曼加冕事件对拜占庭皇帝继承古罗马的世界宗主权产生了巨大冲击。自476年至800年,地中海西部世界的政教首脑大多遵奉拜占庭皇帝为名义上的宗主,800年之后,尽管拜占庭皇帝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世界宗主权诉求,但已得不到西方的承认和尊重。所以查理曼加冕事件绝非一幕戏剧或一场宫廷政变,它彻底摧毁了“一个罗马皇帝、一个罗马帝国”的古典文明政治空间,使得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世界实现了政治疏离,从而逐渐形成了对等的政治外交关系。
查理曼;加冕;拜占庭;拉丁西方
查理曼是欧洲历史上杰出的统治者,曾被同时代的诗人称颂为“欧洲之父”。*在拉丁叙事诗《查理大帝与利奥教皇》(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中,查理曼被称颂为“欧洲之父”(pater Europae)。正是凭借他的伟大征服,法兰克王国才从比今天法国还要狭小的地区扩张到原西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他不仅武功赫赫,还大力推广基督教、教育和学术。他在800年圣诞节被教皇加冕为皇帝,此举把日耳曼世界和罗马世界连接了起来,为此后欧洲君王们的帝王野心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潜力。对于查理曼的加冕称帝,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认为此事并无重大意义,“这一拥戴推举纯粹是一幕戏剧而已。其真实意义在于,罗马教皇,这位基督教世界的首脑和基督教世界本身,赋予了查理曼这个帝国;从而使得他成为了这个帝国的捍卫者。同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头衔不同;查理曼这一皇帝头衔中并不具备世俗的意义……它只是宫廷政变的一种类型而已……”*亨利·皮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39页。然而,笔者通过爬梳法兰克和拜占庭的历史文献,发现无论是查理曼本人、还是教皇、乃至与之利益攸关却并未亲见其事的拜占庭皇帝都非常看重罗马皇帝的头衔并围绕查理曼的加冕展开了持久的政治、外交、军事博弈,查理曼的加冕绝非一幕戏剧或一场宫廷政变那么简单,它对中世纪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世界之间的政治关系影响至大,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文明演变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一、历史文献中的查理曼加冕事件
自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古希腊城市拜占庭以来,历代拜占庭皇帝一直以古罗马皇帝的继承人自居,顽固地坚守着他们继承古罗马皇帝的各项权力,其中就包括对于帝国辖域之外地中海世界文明区域宗主权的继承。而800年查理曼的加冕严重侵犯了拜占庭皇帝的这一诉求,自然招致了拜占庭方面的激烈反对,尽管囿于法兰克-加洛林帝国的实力,拜占庭人最终于812年承认了查理曼的皇帝地位,但这种承认并未彻底动摇他们对于世界宗主权诉求的坚守。这一时期,无论是东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文献,还是西方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历史文献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查理曼的加冕事件,但拜占庭方面的记载颇为简略,淡化这一事件影响和意义的用意十分明显。如 “忏悔者”塞奥法尼斯在他的《编年史》801年的年度词条中,仅仅轻描淡写地记下了一句话:该年12月25日,第9小记,法兰克人国王查理被教皇利奥加冕为皇帝。*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p.653.而并未记载教皇为查理曼加冕的热烈场面。相比之下,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记载则较为详实,《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历代教皇传之利奥三世传》都描写了800年12月25日圣彼得大教堂内外所发生的热烈场面。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01年的年度词条写道:
“在最为神圣的圣诞节那天,正当国王在圣彼得大教堂神龛前做完祈祷,站起身来,欲再去参加弥撒之时,教皇利奥将一顶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而后,国王就受到全罗马城民众的欢呼:奥古斯都·查理,由上帝加冕的,伟大而仁慈的罗马人皇帝,万岁、胜利!在民众欢呼之后,教皇为他披戴上了古罗马皇帝样式的冠冕。从此,他的“罗马贵族”(Patricius)之称号被废弃,而改称皇帝和奥古斯都。”*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trans.by Bernhard Walter Scholz,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 p.81.
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之所以把罗马皇帝的冠冕授予查理曼,使地中海西部世界自476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一位罗马皇帝,主要是为了给罗马教会寻找一位新的世俗保护人,以抵御伦巴德人等周边蛮族的侵扰并制服罗马城中的敌对贵族。因为罗马教会原先的保护人拜占庭皇帝为了抵御东部穆斯林阿拉伯人狂飙般的进攻已无暇顾及遥远的罗马教会,而罗马教会与拜占庭皇帝之间因圣像破坏运动产生的嫌隙和裂痕更使这种保护无法实现。不过,此时拜占庭皇位继承方面的新变化也为教皇拥戴查理曼提供了绝佳的借口。797年,拜占庭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太后伊琳娜废黜了儿子君士坦丁六世并取而代之。这在长期奉行《萨利克法典》,排斥女性皇位继承权的西方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据《洛尔施年代记》的记载,教皇利奥三世既是以此为据,方才拥戴查理曼的。
“在该年,教皇利奥因希腊皇帝称号的问题而徘徊踌躇,他已注意到在他旁边出现了一个女性掌权的帝国,这位使徒,全教会神圣的教父利奥,或者还有现存的基督教民众自行提出了(一种计划),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本人应享有皇帝的称号,并且他本人也应占有罗马(城),因凯撒一直习惯于驻跸于此地,并据有遍布意大利亦或高卢,甚至日耳曼尼亚现有的土地。因为万能的上帝早已把他的领地转化成了这些土地,由于这一原因,查理(统治的)正义性应该被人们所注意,凭借上帝的佑助和他那令人称羡的皇帝名号,查理应统治全体的基督徒民众。”*Georg Heinrich Pertz,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vm I: Annales et Chronica Aevi Carolini, Vol.I, München: Impensis Bibliopolii Avlici Hahniani, 1826, p.38.
而据查理曼御用侍臣爱因哈德的记载,查理曼对于教皇的拥戴不仅事先毫不知情,而且非常不喜欢皇帝的称号,“他肯定地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页。一些学者由此认为,查理曼不喜欢教皇的加冕可能是出于对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担忧,因为既然皇帝的称号是由教皇授予的,教皇自然也就享有了废黜皇帝的权力。但有的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如伯恩斯就认为,查理曼加冕称帝是查理曼继承其父祖衣钵,进一步巩固征服成果而利用神权政治的必然归宿,是查理曼内政外交的终极目的,当然是由其一手策划的。*C.Delisle Burns, The First Europe: A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eval Christendom AD 400-800,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1, pp.569,580-581,588-589. 转引自孙宝国:《查理曼加冕历史真相之再思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8期。笔者赞同伯恩斯的观点,因为就当时教皇与查理曼二人之间的情势而论,教皇利奥处于仰人鼻息的依附状态,连自己的人身安全尚且需要查理曼的有力保护,即使他有为查理曼加冕的意图,又岂敢不事先告知后者,至于利用为查理曼加冕的机会,就教权与皇权孰高孰低的问题与之一较长短则更不可能。而从加冕之后,查理曼与拜占庭方面的多次外交交涉中可以推知,查理曼对于皇帝的称号是极为觊觎的,他不仅在加冕之后便派遣了使臣前赴君士坦丁堡交涉,更重要的是,812年,为了换取拜占庭皇帝米凯尔一世对于其皇帝头衔的承认,甚至不惜在领土的问题上做出了妥协,放弃了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沿海的城市统治权。因为获取皇帝的头衔将会抬升查理曼的政治地位,使查理曼成为古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从而名正言顺地统治那些新近征服的,原属西罗马皇帝的土地。故而,800年教皇为查理曼加冕一事,极有可能是查理曼一手策划的,而教皇利奥三世只不过是充当了配合演出的角色罢了。作为查理曼御用侍臣的爱因哈德为了彰显主君的谦卑礼让,自然不会直言查理曼的真实意图,于是,他把教皇推到了前台,塑造成这一事件的发起人和推动者,而查理曼则相应地成为了却之再三、不慕荣利的 “谦恭君子”。相比之下,由远离宫廷,较少牵涉宫廷政治恩怨的佚名修士修撰的《洛尔施年代记》,对于查理曼意图的记载和评论或许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
“查理并不愿意拒绝利奥的恳请,但出于谦卑考虑,这种谦卑是上帝所赞许的,也是教士和全体基督徒所期许的,查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辰那天以向主献祭的方式接受了教皇利奥所提请的皇帝名号。”*Georg Heinrich Pertz,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vm I: Annales et Chronica Aevi Carolini, Volume I, München: Impensis Bibliopolii Avlici Hahniani, 1826, p.38.
爱因哈德也提到了查理曼加冕事件对于拜占庭皇帝的刺激,但他仍然采用回护主君的春秋笔法借机颂扬了查理曼超越拜占庭皇帝的宽容大度。“但是在他接受了尊号以后,却能平心静气地容忍着由此引起的敌视和罗马皇帝(指拜占庭皇帝)的愤怒。他以他的豁达大度克服了他们的敌意,论起胸襟开廓来,他无疑的是远远超过他们的,他常常派使臣到他们那里去,称他们为他的弟兄。”*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30页。的的确确,800年查理曼的加冕,使基督教世界自476年之后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罗马皇帝,从根本上冲击了拜占庭皇帝世界宗主权诉求的理论根基。在中世纪早期,罗马皇帝继承人的身份和皇权神授的思想一直是拜占庭皇帝对整个地中海世界提出宗主权诉求的依据。由于拜占庭皇帝是尘世唯一的罗马皇帝,是由上帝所选立的古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故而,他们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是基督教信仰的监督者和保护人。由此一来,正如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会一样,世界上也应只有一个合法的罗马皇帝和罗马帝国。所有那些曾经属于古罗马帝国辖域(orbis)内的基督教国家,都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永恒和不容置疑的属地。这些思想观念在中世纪的拜占庭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尽管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世界的权力曾一度因蛮族的入侵而动摇,但早期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在为保持它的世界性权力而斗争,查士丁尼大帝更是把这种政策作为拜占庭国家政策的最根本目标并为之征战四方。正因为如此,查理曼的加冕自然被拜占庭皇帝和臣民视为一种篡逆,从而引发了拜占庭与法兰克两国的外交纷争、军事冲突以及拜占庭国内政局的动荡。查理曼加冕后,法兰克与拜占庭即就如何重新确定两国关系的问题展开了双边的外交交涉活动,无论是法兰克,还是拜占庭的历史文献都记载了这些外交活动,但双方的记载却有所不同。拜占庭方面的记载,是查理曼首先向伊琳娜派遣使节的,《塞奥法尼斯编年史》800—801年的年度词条写道:
“该年12月25日,第9小记,法兰克人国王查理被教皇利奥加冕为皇帝。查理曼计划派出一支舰队远征西西里,但后又改变主意,转而决定迎娶伊琳娜,最终他于次年派遣了大使。”*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p.653.
而法兰克方面《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记载,则是由伊琳娜首先向查理曼派遣使节的,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02年的年度词条写道:
“女皇伊琳娜派遣了宫廷侍卫官利奥作为使臣,从君士坦丁堡专程赶来,商谈法兰克人与希腊人之间签订和约的问题。当这位使臣返国时,皇帝随即派遣了亚眠主教杰西(Jesse)、伯爵赫尔姆古德(Helmgaud)作为使臣,前赴君士坦丁堡,同伊琳娜缔结和约。”*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82.
查理曼加冕之后,基督教世界一度出现了两位罗马皇帝同时并立的局面,就当时的国际外交形势而言,无论是伊琳娜,还是查理曼皆有互相协商,以确定两位皇帝之间关系,进而确定并稳固两国外交关系的需求。至于双方史家有关外交往还先后顺序的不同记载,可能是由于两边的史家皆有维护本国君主尊严的意图,因为按照外交惯例,通常先由属邦之君向宗主国的君主致意,继而宗主国君主再向属邦垂恩,这种记载差异充分体现了查理曼加冕后,两国君主在究竟谁为基督教世界最高主宰的问题上所存在的深刻矛盾。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忏悔者”塞奥法尼斯的记载,查理曼曾谋划同拜占庭女皇伊琳娜结婚,以期通过联姻的方式使东、西两个帝国合为一体,重建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从而化解彼此间的矛盾。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上,这种以皇室联姻的方式把两个封建王国合并成一个王国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封建王国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通过伊莎伯拉公主和斐迪南王子的结合,形成了西班牙国家。据“忏悔者”塞奥法尼斯的记载,女皇伊琳娜似乎已准备对该计划予以认可,但该计划受到了大贵族阿提乌斯(A⊇tius)的抵制,因他力图使自己的兄弟获得皇位。*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p.654.在这项计划尚未取得最终结果之前,以长官(logothetes)尼基弗鲁斯为首的贵族集团发动了政变,罢黜了伊琳娜的皇位。802年10月,尼基弗鲁斯和一伙高官显宦,包括特里菲利奥伊兄弟(Triphyllioi brothers)等人在部分皇家近卫军官(officers of the tagmata)的配合下,闯进了宫廷并逮捕了伊琳娜。10月31日凌晨,政变分子抵达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尼基弗鲁斯被大牧首特拉西奥斯(Tarasios)加冕为皇帝。废帝伊琳娜随后被流放至普林基普奥斯(Prinkipos)岛上的塞奥特奥克斯(Theotokos)修道院,后又被遣送至莱斯博斯岛并于803年8月9日崩逝。*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p.655.“忏悔者”塞奥法尼斯在他的《编年史》中虽未明确记载尼基弗鲁斯发动政变是出于反对伊琳娜与查理曼联姻的动机,但从尼基弗鲁斯称帝之后,拜占庭与法兰克外交谈判破裂且兵戎相见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推知尼基弗鲁斯是拒绝承认查理曼配享皇帝头衔的。尽管相关的历史文献并未详细记载伊琳娜统治时期,拜占庭与法兰克外交谈判的具体内容,但伊琳娜同意嫁给查理曼,也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查理曼“罗马皇帝”的地位。因为从查理曼一贯强势的作风来看,他在与伊琳娜联姻后是不可能仅仅充当 “王夫”的角色,甘居幕后的。而且考虑到古代社会“夫主妻从”以及女人“为帝称君”*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里,女性称帝有违男权社会以男性为尊的传统,所以这种现象极为少见,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只有伊琳娜女皇曾使用表示皇帝的阳性名词“奥古斯都”,而西欧中世纪早期则没有一位女性帝王。备受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推知伊琳娜与查理曼婚姻谈判的结果极有可能是:查理曼是统一后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伊琳娜仅仅充当皇后兼副王的次要角色,作为交换,查理曼同意婚后充当伊琳娜的保护人以制服那些觊觎她皇位的臣下。这样的结果自然招致了阿提乌斯、尼基弗鲁斯等拜占庭大贵族的一致反对并最终导致了联姻计划的破产和拜占庭皇位的更迭。
尼基弗鲁斯登基后,拜占庭与法兰克爆发了战争,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记载,“806年,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派遣了一支舰队,在大贵族尼西塔斯(Nicetas)的统领下向达尔马提亚地区发动了进攻,欲重新将该地征服。”*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86.《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虽未明确记载这次战争的胜负,仅记载807年,尼西塔斯同意大利国王丕平签订了一项和约后,便起锚返回了君士坦丁堡。*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p.87-88.不过,从拜占庭并未攻占达尔马提亚地区,并未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角度分析,拜占庭很有可能是这场战争失败的一方。809年,拜占庭又派遣了一支舰队远征达尔马提亚地区,在科马奇乔诺岛外抛锚停泊,同驻守该岛的法兰克军队发生了交战。结果,拜占庭舰队被击败,被迫撤回威尼斯。舰队统帅保罗(Paul)准备同意大利国王丕平谈判,以实现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和平。但他的媾和计划遭到了两位威尼斯公爵维勒里(Willeri)和比奥图斯的反对,他们甚至准备对保罗进行伏击,幸好保罗识破这一诡计,率舰队安全离去。*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89.保罗的这次远征大概是拜占庭帝国最后一次主动向法兰克对抗。自此之后,法兰克方面由守转攻。次年,意大利国王丕平被威尼斯公爵们的诡计所激怒,下令从陆地和海上对威尼斯发起进攻,结果攻占了威尼斯并迫使两位威尼斯公爵臣服。*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91.810年10月,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迫于战败的形势, 向查理曼派遣了使节并签订了合约。查理曼将威尼斯还给了尼基弗鲁斯。*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92.“812年,尼基弗鲁斯在麦西亚(Moesia)行省同保加尔人的战斗中阵亡。他的女婿米凯尔(Michael)登上了皇位,并在君士坦丁堡接见了查理曼先前派来拜见尼基弗鲁斯的使团。米凯尔重新确认了尼斯菲奥鲁斯先前提出的和约。然后派遣了一支使团与法兰克使团同赴亚琛。拜占庭使团在亚琛拜见查理曼时,在一座教堂中,接受了一份经过装裱后的和约,并按照希腊人的习惯,将查理曼称之为‘皇帝’和‘巴塞勒斯’。 他们在返程途经罗马时,在圣彼得大教堂,再次从教皇利奥那里接受了同样的和约或盟约文件。”*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p.94-95.
尼基弗鲁斯登基后,拜占庭与法兰克“由战到和”的历史表明继承了古罗马帝国衣钵的老大帝国拜占庭在军事实力上已不是西方新兴的法兰克-加洛林帝国的对手。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作为战场上获胜的一方,查理曼并没有同时获得名誉和土地两方面的彻底胜利,而是采取了以“土地换名誉”的原则,他在合约中允诺将他征服的威尼斯、伊斯特里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等地归还给拜占庭,而他的交换条件仅仅是要求拜占庭皇帝承认他也有使用“皇帝”一词的权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附加条件。而拜占庭方面对于这种名誉分享的让步可谓心有不甘,在拜占庭与法兰克签订的合约中,查理曼只能使用一种比较拗口的罗马皇帝头衔“统御帝国的罗马人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 gubernans imperium),而不能使用加冕时民众欢呼的“罗马人的皇帝” (Imperator Romanorum)这一头衔,或许是由于查理曼认为“统御帝国的罗马人皇帝”这一头衔过于拗口且不太好听,所以他和他的臣下更喜欢使用“皇帝”、 “奥古斯都”(Imperator Augustus)的头衔,以及“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的国王”的头衔。“罗马人的皇帝”这一头衔仍旧被拜占庭皇帝专属使用,而且自812年之后,历代拜占庭皇帝几乎从未在我称呼中舍弃这一头衔的全称,然而,在此之前,拜占庭皇帝已经习惯于以希腊式的巴塞勒斯的头衔称呼自己。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拜占庭皇帝在法兰克人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放弃了独占罗马皇帝这一头衔的特权,让一位西方的蛮族首领也配享了这一称号,但心有不甘的他们仍旧在头衔的语言文字上竭力维护自己高人一等的尊严,以示他们与蛮族皇帝的区别以及他们是古罗马皇帝合法继承人的正统地位。
二、拜占庭皇帝世界宗主权的历史由来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两大帝国的首脑为了争夺“罗马皇帝”的头衔而不惜一切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拜占庭皇帝在帝国辖域以外的地中海世界孜孜以求地实现一种名义上的统治呢?首先,拜占庭皇帝的世界宗主权诉求是历史继承的结果。罗马从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逐渐发展成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环抱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这一领土疆域上的突出成就使罗马人逐渐形成了罗马帝国的疆域“无远弗界”的思想,认为一个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应该统治所有人类居住的土地并以此把和平赐予所有的民族。在奥古斯都时代,一些罗马作家的文艺作品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例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朱庇特神向维纳斯(Venus)许下诺言,当奥古斯都使大洋环抱他的帝国,他的荣耀与星辰同辉之时,罗马人就将控制辖域内所有的海洋与大地。”*Vergil, Aeneid, 1.287. 转引自Emily Albu, The Medieval Peutinger Map: Imperial Roman Revival in a Germ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5.奥维德在他的《岁时记》(Fasti)中也曾宣称:“罗马城的空间与整个世界的空间同度。”(Romanae spatium est urbis et orbis idem)*Ovid: Fastic, ed. by Thomas Keightley, London: Whittaker, 1848, p.37.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并非唯一的大帝国,在她的东部仍然存在着与之对立的波斯帝国,而且在公元前9年,奥古斯都大帝因为痛感瓦卢斯军团在条顿堡森林中的覆灭而从此放弃了对外扩张的政策,使帝国的疆界就此稳定了下来,尽管如此,罗马人依旧执著地认为罗马帝国无远弗届且永世长存,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都是没有尽头的。即使到了5世纪初,帝国饱受各个蛮族的侵扰,国势已然江河日下,帝国“无远弗届”的思想仍旧未被舍弃。例如,高卢-罗马诗人茹提利乌斯·南马提阿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在其诗歌《论还家》(De Reditu Suo)中就把罗马比喻成世界上最为美丽的女神“罗玛”(Roma),“她把过往的一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城市。”(Urbem fecisti, quod prius orbis erat.)*Rutilius Namatianus, De Reditu Suo, ed. by Aug Wilh Zumptius, Berolini: Sumptibus Ferd. Dümmleri, 1840, p.58.这首诗词形象地说明了罗马灭国无数、凌驾万邦之上的世界性帝国地位。
众所周知,“拜占庭”是近代人编造出来的一个学术用语,并不被我们现在称之为 “拜占庭人”的古人所使用,事实上,历史上的 “拜占庭人”一直有意识地把自己称为 “罗马人”,把他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称为新罗马,把他们的帝国称为罗马帝国。在他们看来,古罗马与拜占庭之间的历史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其间并无明显的断裂。关于古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分期,近代以来的学术界众说纷纭且争讼不断,其中主要的历史分期观点大致有如下三种,一是以324年君士坦丁大帝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世界作为古罗马与拜占庭之间的历史分期;二是以395年狄奥多西大帝崩逝,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离作为历史分期,三是以476年,罗慕路斯的被废作为历史分期。*关于古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分期,参见徐家玲:《拜占庭的历史分期与早期拜占庭》,《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6期。尽管后世学者选取了上述年代,把它们作为重要历史分期的节点并赋予他们以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在这些历史年代中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罗马皇帝传承谱系的一次又一次分分合合罢了,恐怕并未料想到它们会有后世学者所附会叠加的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也不会把它们视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在他们看来,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未使罗马帝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罗马帝国依旧是以前的罗马帝国。例如,被后世学者附会叠加最多的一个历史年代——476年,它被认为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代、中世纪的开端、西欧奴隶制终结和封建制开启的年代……在时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度分裂的罗马帝系又一次实现复合罢了,因为废黜罗慕路斯的日耳曼蛮族将领奥多维克并未自立乾坤,而是派遣使节至君士坦丁堡,希望东罗马皇帝芝诺能够认可他在意大利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仍然是以芝诺的名义实行的。上述历史现象充分表明了古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历史延续性,作为古罗马帝国在中世纪的直接继承者,拜占庭帝国自然也承袭了前者的众多遗产,其中就包括罗马帝国凌驾于万邦之上的世界性帝国的地位。尽管在整个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这种国际地位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但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却被拜占庭人一直坚守至帝国的灭亡。
其次,基督教君权神授的思想为罗马-拜占庭皇帝的世界宗主权诉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基督教产生和发展的早期,由于基督教徒仅仅笃信上帝为唯一的真神,拒不履行神化罗马皇帝的仪式而饱受罗马皇帝的摧残和迫害。这种迫害基督徒的活动从54年尼禄统治时期开始,时断时续的发生,其中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共有10次,直至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后,迫害活动方才终止。面对罗马皇帝的迫害,基督徒以大规模的以身殉道的方式来应对,在这场肉体与灵魂、暴力与精神的较量中,基督教会最终凭借信徒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了胜利者。为了收揽人心、稳固统治,君士坦丁大帝意识到需要对基督教信仰加以改造,使国家和宗教连成一体,以重建对于民众的传统控制力。为此,他在解除基督教信仰禁令的同时,召开了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以皇帝的身份干预教会内部的组织及教义问题。另一方面,尽管教会认为崇拜皇帝的仪式行为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异教的信仰,但为了赢得皇帝的庇护和支持,也不得不对先前公然藐视神化皇帝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此历史背景下,皇权神授的理论思想应运而生。与君士坦丁大帝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基督教学者尤西比乌斯在他的《卅年致辞》(Tricennial Orations)中首先提出了基督教的皇权神授的思想,由于基督教属于一神信仰,这使其无法像多神信仰那样直接地把统治者奉为真神予以顶礼膜拜,于是为了达到神化统治者的目的,只能采用君权神授的解释方法,把统治者的权力说成是由神授予的。例如,尤西比乌斯就采取了 “映像说”的方法神化君士坦丁的统治权。他认为君士坦丁帝国是天国在尘世中的一种映像。由于天国中有且只有一位上帝,故而尘世中也应相应的有且只有一位皇帝。帝王的一切权力都源于上帝。君士坦丁通过神圣之言的逻各斯与上帝保持着特殊的联系。他是上帝的朋友,箴言的阐释者;他转动的双眼能够接受来自天庭的讯息;他能够为臣民升入天堂做足准备并热忱地向一切人等宣达真实、神圣的法律,以此唤醒整个人类接近上帝。*D. M. Nicol, “Byzantine Political Thought,” in J. H. Burn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350-c.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2.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十分注重利用这种皇权神授的思想,例如,他曾下令打造一个金属圆盘,镌刻有上帝亲自为君士坦丁加冕的塑像,以此向他的基督教臣民们宣示,他是应上帝的召唤统治帝国的。*George Ostrogorsky, “The Byzantine Emperor and the Hierarchical World Order,”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35, No.84(Dec.1956), p.2.
尤西比乌斯认为既然罗马皇帝的权力是由上帝授予的,那么他在人类事务的管理方面就应该享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故而,作为一个由上帝所主宰的国度——罗马帝国理应统治整个世界,以符合天国中只有一位上帝的映像。尤西比乌斯在《卅年致辞》(Tricennial Orations)中写道:
“罗马帝国此时已确立了君主制度,而原本仅仅从唯一基点出发的基督训诫为了赢得一切人众的欢迎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故而,这两大权力得以并行发展并兴旺发达。由于凭依我主的力量,多元化的魔鬼和多神教的神祇均遭毁灭,这预示着一个由上帝主宰的国度的到来,这一国度便是罗马帝国。它君临希腊人、蛮族人及所有民族之上,甚至包括了那些在世界上最为遥远地区生活的民族,既然政府林立的原因已被消除,那么罗马帝国就应该兼并那些可以看到的政府,以此把整个人类民族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和谐体。罗马帝国已经把诸多民族中的大部分并入,它注定会把那些尚未被并入的民族一一合并,直至人类所居住世界的最为遥远的地区。”*H. A. Drake,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A Historical Study and New Translation of Eusebius’Tricennial Orations,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20.
尤西比乌斯君权神授的思想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政治思想的基础,自此之后,由于帝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在近东古老文明神化君主传统的影响下,拜占庭帝国也走上了神化皇帝的道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基督教一神信仰的传统。例如,在拜占庭皇帝的宫廷生活中,皇帝的穿着和排场处处体现其为上帝代理人的特殊身份,皇帝在重大场合一般头戴皇冠、足踏紫色御鞋、身着紫色且镶缀黄金的丝绸御袍。按照君士坦丁·波菲罗根尼蒂斯的说法,皇冠与御袍并不是由人工制成的,而是天使奉上帝之命,送给君士坦丁大帝的。*George Ostrogorsky, “The Byzantine Emperor and the Hierarchical World Order,” pp.3-4.在教会庆典中,拜占庭皇帝时常模仿耶稣基督,重现他在尘世生活的情景。如皇帝在圣诞节会邀请十二位宾客共进晚餐,重现耶稣与十二使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故事;在圣枝主日(on Palm Sunday),皇帝模仿耶稣前赴耶路撒冷的样子行进于游行队伍中,而军事长官(the magisters)和贵族(patricians)则扮演使徒;在濯足星期四(on Maundy Thursday),皇帝效仿曾为门徒洗脚的耶稣,也为帝国的十二位穷人洗脚。*George Ostrogorsky, “The Byzantine Emperor and the Hierarchical World Order,” p.4.由于拜占庭皇帝自命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所以在对外交往上,总是以宗主对待属臣的姿态对待别国君主。拜占庭君臣的这种傲慢态度甚至到了不考虑敌我双方实际力量对比,罔顾国家安全的地步。5世纪初,被誉为 “上帝之鞭”的匈人首领阿提拉一度纵横欧洲大陆,对东、西罗马帝国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被迫向其输银纳款。尽管如此,拜占庭方面仍旧坚持其皇帝享有不可企及的至高地位。当拜占庭使节与匈人使节宴饮之时,匈人使节吹嘘其首领阿提拉的实际地位已盖过了拜占庭皇帝,拜占庭使节威吉列(Wigilia)抗言答道: “把凡人与神相提并论是荒谬的;阿提拉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狄奥多西皇帝则是一位神。” 威吉列的回话触怒了这位匈人使节,尽管为了化解矛盾,拜占庭使节们向其馈赠了许多礼品以示抚慰,但在立场方面却丝毫不肯让步。*Fritz Kern, 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 I.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and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I. Law and Constitution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S. B. Chrimes, New Jerse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5, p.63.
476年之后,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原西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一系列由日耳曼人军事首领实际统治的蛮族王国,拜占庭皇帝有效统治的区域仅限于东部地中海世界。尽管拜占庭皇帝统治地中海世界的权力因蛮族的入侵而动摇,但在历史继承和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下,拜占庭皇帝仍然不肯放弃对西部地中海世界的统治主权。例如,“拜占庭皇帝芝诺曾以‘以蛮治蛮’的策略, 邀请东哥特人首领提奥多利克进军意大利, 为帝国收复西部失地。结果, 事实并未如其所愿, 提奥多利克反而独霸意大利, 造成了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第二次冲击。”*王晋新:《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6世纪中叶前后, 一代枭雄查士丁尼遣派大军反攻。无论就其本身意愿而言还是从客观的实际效果上看, 这场查士丁尼战争都体现出了罗马帝国对帝国失地的收复以及恢复地中海统一世界的强烈意愿。”*王晋新:《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他在敕令中把自己称为阿勒曼尼人、哥特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安提阿人、阿兰人、汪达尔人、阿非利加人的凯撒弗拉维斯查士丁尼(Caesar Flavius Justinian the Alamannicus, Gothicus, Francicus,Germanicus, Anticus, Alanicus, Vandalicus, Africanus),以此表明自己是泛地中海世界的罗马皇帝。拜占庭皇帝还通过赐予蛮族国家首领“贵族”、“执政官”头衔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统治主权,最典型的一例是阿纳斯塔修斯皇帝赐予克洛维执政官的头衔。
值得注意的是,奥多微克、提奥多利克、克洛维等蛮族首领对于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大多采取承认的态度,他们的承认似乎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尤西比乌斯的说教——拜占庭皇帝的权力是由上帝授予的,理应统治整个世界。因为除了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蛮族首领大多信奉阿里乌斯派,在宗教上与拜占庭皇帝存有分歧。把西部正统教徒从阿里乌斯异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查士丁尼征讨汪达尔、东哥特、西哥特等蛮族王国的一个动机和口号。例如,查士丁尼发动汪达尔战争的借口是因为汪达尔人拒绝了他的一个要求——使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国王盖利默(Gelimer)退位,使亲罗马、亲正统教会的希尔德里克复位。蛮族首领承认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似乎更多是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以及对于罗马-拜占庭先进文明的仰慕。在蛮族大迁徙的过程中,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蛮族人口在数量上远远少于罗马当地人,尽管我们无法从史料文献中找到各个蛮族人口数量的确切数据,但从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对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数量的记载,可以推知各个蛮族人数的稀少,据其记载,闯入北非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战士仅有5万人。*参见普洛科皮乌斯著:《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2 页。于是,为了缓和罗马当地人的不满情绪以稳固统治,蛮族首领需要借用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名义实行统治。譬如东哥特国王提奥多利克以拉文纳为首都,充当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副王(sub-emperor)统治意大利,提奥多利克完好地保留了罗马元老院并在拜占庭皇帝的准允下,每年都任命罗马贵族执政官(consul)。这样东哥特王国实行了一种双重统治制度,东哥特人首领提奥多利克统治王国中的东哥特人,而罗马贵族(magistrate)统治王国中的罗马人。罗马-拜占庭的先进文明似乎也是促使蛮族首领承认或者默认拜占庭皇帝宗主权的一个历史动因。例如,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对罗马-拜占庭文化仰慕不已,他模仿诗人塞杜里乌斯的诗作撰写了两首韵律诗,还撰写了若干赞美诗以及吟诵弥撒的歌谣。另外,在生活上,希尔佩里克处处模仿拜占庭皇帝,对拜占庭皇帝赠与的礼物爱不释手,格雷戈里在他的《法兰克人史》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希尔佩里克国王非常自豪地向他展示拜占庭皇帝赠与的礼物。格雷戈里写道:
“我去诺让的王室领地见国王,他把各有一磅重的金块展示给我们看,这是皇帝送给他的,金块的一面有皇帝的像,镌有“永垂不朽的提贝里乌斯·君士坦丁·奥古斯都”的铭文,反面是一辆架着四匹马的马车和御者,镌有“罗马人的光荣”的铭文。他同时展示了使臣们带来的许多其他贵重物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O. M.道尔顿英译,寿纪瑜、戚国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90—291页。
希尔佩里克国王的这一举动恐怕并不仅仅是因为拜占庭皇帝所赠物品的贵重,更可能是因为他对罗马-拜占庭文明的仰慕以及对于拜占庭皇帝宗主权的充分认可,使他对拜占庭皇帝的垂青欢心不已,因而热衷于向他人宣示以表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也似乎能够解释他为何遵照拜占庭皇帝的指令强迫辖域内的犹太人受洗。*Bernhard Jussen, Spiritual Kingship as Social Practice: Godparenthood and Adopt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nd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2000, p.174.
当然,在这段历史时期,也有某些蛮族国王不肯承认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如7世纪20—30年代的西哥特国王苏安提拉(Suinthila),他在西哥特人的心目中,是驱逐拜占庭人,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英雄。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曾在《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国王史》(Historia de regibus Gothorum, Vandalorum et Suevorum)中把他称作第一位统治全西班牙(totius Spaniae)的国王。*http://en.wikipedia.org/wiki/Suintila.在6世纪50年代,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派遣大军进攻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占领了半岛东南沿海地区并建立了拜占庭的西班牙行省。西哥特国王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无力抵抗拜占庭人的进攻,被迫承认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但625年,苏安提拉国王打败了拜占庭人,完全收复了失地。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颂扬苏安提拉:“乃是第一位高踞海峡的全西班牙王国的君主(monarchiam),此前的历代统治者从未取得过这一功绩。”*David Rojinsky, Companion to Empire: A Genealogy of the Written Word in Spain and New Spain, New York: Amsterdam, 2010, p.51.依照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辞源》(Etymologiae)对于“monarchiam”的释义,“monarchiam”是指那些掌握无可置疑权威的人,如统治希腊人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罗马人的朱利乌斯·凯撒。*Isidore of Seville,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 trans. by Stephen A. Barney, et al.,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1.可见,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称苏安提拉为“君主”(“monarchiam”),是对拜占庭皇帝宗主权的公然挑战。不过,在476年—800年,尽管蛮族王国中也存在着不承认拜占庭皇帝宗主权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的侧重点在于强调蛮族王国自身的独立性,而并非强调蛮族王国具有与拜占庭帝国同等的政治地位,是又一个志在统合地中海世界且与拜占庭帝国并驾齐驱的“罗马帝国”。
476年—800年,拜占庭皇帝的世界宗主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承认。这一时期的罗马教皇与拜占庭皇帝在神学信仰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芝诺、阿纳斯塔修斯、希拉克略等拜占庭皇帝从争取帝国一信论信徒的支持,巩固帝国统治的立场出发,主张调和与基督一性论的矛盾,从而与恪守卡尔西顿信经,主张“基督神人两性”的罗马教皇产生了严重的宗教分歧,二者碰撞最为激烈的一幕是654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对于教皇马丁一世的迫害。马丁一世因为无视君士坦斯二世禁止宗教争论的敕令,继续批驳调和正统派与一性派矛盾的一志论而被君士坦斯二世派人拘捕,押解至君士坦丁堡刑讯后,流放至克里米亚半岛并客死于该地。尽管在神学信仰方面,罗马教皇没有对拜占庭皇帝唯命是从,教皇格拉西乌斯一世更是提出了教皇掌握最高宗教权力、皇帝掌握最高世俗权力的“双剑论”,但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教皇对于皇帝的抗命,还是他所提出的抬升自身权威的诉求都仅仅局限于宗教神学领域。在世俗政治领域,教皇远远无法与皇帝相抗衡,他们仍以拜占庭皇帝统治下的属臣自居,据《历代教皇传之哈德里安一世传》的记载,直至“丕平献土”之际,“哈德里安教皇才开始索取和行使(世俗)的最高统治权。”*Anonymous, The Lives of the Eighth-Century Popes,The Ancient Biographies of the Popes from AD 715-AD 817 trans. by Raymond Dav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2.772年—781年教皇哈德里安一世开始在公文上使用自己的在位年次纪年,而在此之前都是使用拜占庭皇帝的在位年次纪年。此外,对于世俗政治格局中存在的拜占庭皇帝高于蛮族国王的政治地位差异,教皇也深表认同,譬如,大格雷戈里在致信拜占庭皇帝时,把他们称为“伟大的皇帝”(Lord emperor),而在致信西方诸王时则把他们称为“最亲爱的儿子们”(dearest sons)。*Henri J. M. Claessen,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 New York: E. J. Brill, 1996, p.230.
三、拉丁西方与拜占庭之间的政治疏离
中世纪拜占庭皇帝的世界宗主权承袭自古罗马帝国,又因基督教会神化皇帝的做法而强化。由于拜占庭皇帝既是古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又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因而享有了凌驾于诸国之上的宗主权。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800年查理曼加冕,在这一阶段里,地中海西部世界的政教首脑大多遵奉拜占庭皇帝为名义上的宗主,尽管蛮族王国中也存在着不承认拜占庭皇帝宗主权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的侧重点在于强调蛮族王国自身的独立性,而并非强调蛮族王国具有与拜占庭帝国同等的政治地位,是又一个志在统合地中海世界且与拜占庭帝国并驾齐驱的“罗马帝国”。而拜占庭帝国也把“西向进取”,恢复古罗马帝国旧日疆界作为自己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点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行。在476年—800年,尽管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和西部存在着促使双方分离的种种历史因素,如拜占庭皇帝与西方蛮族首领之间的敌对、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代表的东西方基督教会内部的争论,但东西地中海世界仍然存在着一个维系和联结双方的重要历史因素——拜占庭皇帝的世界宗主权。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因素的长期存在,使得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世界之间长期存在着某种源自历史的一体化连接。
然而,查理曼加冕推动了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世界在政治上的疏离,它实现了古罗马帝国传统与西方蛮族王权的有机结合,使法兰克-加洛林国王成为了一个与拜占庭皇帝平起平坐的 “罗马皇帝”,自此之后,西欧教俗封建主对于拜占庭帝国及皇帝的态度从之前的仰视转变为平视、甚至鄙视。在与拜占庭皇帝的外交往来中,西方的帝王一般使用表示地域性的限定名词“希腊”,而不是表示世界性的限定名词“罗马”称呼拜占庭皇帝,如12世纪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把拜占庭尼西亚帝国时期的皇帝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泽斯(John III Vatatzes)称为“希腊人最杰出的皇帝约翰”(John, the most illustrious Emperor of the Greeks),言外之意,弗里德里克二世认为他自己是古罗马皇帝的唯一后嗣,否认拜占庭方面任何有关罗马后嗣的宣称。*Dimitri Korobeinibov, Byzantium and the Turk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4.由于加冕后的查理曼已不再单纯是日耳曼蛮族国家的国王,而是上帝认定的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的使命也不仅限于管理日耳曼国家的世俗事务,包括宗教事务在内的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都受他的管理。因此,加洛林帝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连远在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阿勒·拉什德也与查理曼通好并承认了后者基督教世界领袖的地位。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记载,797年—807年间,查理曼曾派遣两位使者前往巴格达,而哈里发哈伦也派遣了两位使节对其进行了回访。阿拉伯使臣所携带的礼品中包括了一座钟表和一顶精美的帐篷。*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87.耶路撒冷大主教还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圣城钥匙转让给了查理曼。*Anonymous and Nithard,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p.78.据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的记载,“查理曼派遣使臣带着祭献物品来到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墓地和他的复活地祭拜,当时这块圣地已归属波斯国王……然而波斯国王却把这块圣地算作了法兰克国王领地的一部分”,*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20页。此处的波斯国王实为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阿勒·拉什德,当时的法兰克人误把阿拉伯人当作波斯人,故而,无论是《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还是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都把哈里发哈伦·阿勒·拉什德记载为波斯国王。这些举动均象征了遥远异域的君主、宗教领袖对于查理曼基督教世界领袖地位的承认。查理曼逝世后,有关他的神话传说越来越多,诸如“耶路撒冷圣城保卫者”的荣誉光环也加到了他的头上,结舌者诺特克据此在他的《查理曼事迹》中写道哈里发哈伦·阿勒·拉什德为查理曼的赫赫威名所折服,心甘情愿地担当查理曼的代表,替他代管圣地。*诺特克写道:“我愿把这片土地(指圣地耶路撒冷)至于他(查理曼)的权力之下,我作为他的代表来统治这块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高兴,或者是有适当的机会,他派遣使节到我这里来,他将发现我是这一省份的税收的忠实管理者。”见:爱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81—82页。考虑到《查理曼事迹》这一史册据有把历史事实过度放大并予以神话的特点,诺特克的说法似乎不足采信,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查理曼超越以往蛮族首领的业绩,使得法兰克-加洛林帝国得以与更多、更为遥远的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并赢得了他国某种程度的尊重。查理曼加冕提高了西方世俗封建帝王的政治地位,初步开创了中世纪西欧皇权与教权两大权力系统相互依存的历史,此后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幻,双方的实力互有消长并形成了皇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这与拜占庭文明皇权控制教权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普罗卡奇曾以 “中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两大黑幕”*普罗卡奇:《意大利人民的历史》(日文版)第1卷,第33页。来形容中世纪西方文明的这一独特特征。
其次,查理曼加冕也促使拜占庭帝国的经略重点发生了彻底的转向,尽管800年西方皇帝的出现并未彻底改变拜占庭皇帝在与西方帝王交往时的傲慢态度,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一事件促使拜占庭皇帝彻底放弃了查士丁尼曾经为之奋斗的收复西方失地的梦想,转而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等近东地区作为自己经营关照的重点,集中力量抵御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并积极支持君士坦丁堡教会向东南欧异教信仰地区传教。864年,在拜占庭皇帝米凯尔三世的军事威胁下,保加利亚可汗鲍里斯接受了拜占庭所遣使节为之施行的洗礼,皈依了东部教会,拜占庭皇帝米凯尔三世成为了鲍里斯的教父。尽管鲍里斯一度摇摆于东、西方两大政教势力之间,但最终还是顶住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成为了东部教会的一员。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也向保加利亚北部的大摩拉维亚公国派遣了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他们二人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了最早的斯拉夫文字母并在大摩拉维亚公国建立了从属于东方教会的斯拉夫教会。但在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摩拉维亚公国由于被东法兰克王国占领,在日耳曼封建主和罗马教皇的胁迫下,大摩拉维亚从此倒向了西部教会。988年,新兴的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迎娶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并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接受了洗礼,基辅罗斯公国从此皈依了东部教会。由于拜占庭帝国不再把“西向进取”,恢复古罗马帝国旧日疆界作为自己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点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行,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帝国逐渐形成了对等的政治外交关系。
结 语
通过对中世纪拜占庭皇帝世界宗主权历史的长时段追踪与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拜占庭皇帝的世界宗主权承袭自古罗马帝国,又因基督教会神化皇帝的做法而强化。由于拜占庭皇帝既是古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又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因而享有了凌驾于诸国之上的宗主权。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800年查理曼加冕这一阶段,地中海西部世界的政教首脑大多遵奉拜占庭皇帝为名义上的宗主,尽管蛮族王国中也存在着不承认拜占庭皇帝宗主权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的侧重点在于强调蛮族王国自身的独立性,而并非强调蛮族王国具有与拜占庭帝国同等的政治地位,是又一个志在统合地中海世界且与拜占庭帝国并驾齐驱的“罗马帝国”。而拜占庭帝国也把“西向进取”,恢复古罗马帝国旧日疆界作为自己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点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行。然而,800年查理曼的加冕,从形式上彻底摧毁了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长期存在的“一个罗马皇帝、一个罗马帝国”的古典文明政治空间,使得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世界之间长期存在的某种源自历史的一体化连接彻底裂解,拉丁西方世界与拜占庭世界实现了政治疏离,从而逐渐形成了对等的政治外交关系。
2017-06-0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加洛林王朝史学编纂与王室宫廷互动关系研究”(编号:15CSS007)。
朱君杙(1983-),男,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A
1674-6201(2017)03-0066-12
(责任编辑:郭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