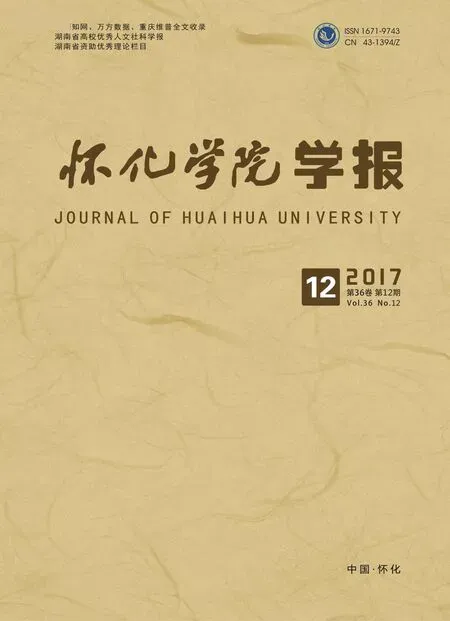何休公羊学“条例”研究综述
2017-03-10张振
张 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公羊学作为春秋学的一支、经学的一种兴于两汉,也盛于两汉。而两汉公羊学者著作相对完整留存于世的,只有西汉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东汉末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下称《解诂》)。《解诂》被视为“春秋公羊学两百年发展的总结”,是“汉代公羊学的最后成果”。何休是春秋公羊学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其公羊学则被认为是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因为何休著作以及相关文献的缺失,现今绝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中的“条例”。
“例”也就是所谓的“书法义例”,指的是《春秋》中一件事的文字记录方式以及记录其中所蕴含的大义。“例”是解读《春秋》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对于“例”,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有,或以为无,但无疑何休承认《春秋》中存在“例”,更讲究公羊的“例”。戴维认为何休《解诂》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义例的总结与发挥”[1]108。何休的“例”有很多。清人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十卷三十章梳理了“例”二十六,“表”四。梁启超讲:“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2]75郑任钊讲:“每‘例’皆先罗列举证《春秋》经传及何休解诂条文,最后以‘释’来阐发该‘例’之主旨要义。‘表’则是‘例’的一种变形,通过纵横比对相关内容来使义例清晰,而阐述主旨之文字则移於‘表’首,以序的形式出现。”[3]3也有学者对刘逢禄所总结的“例”作了补充及讨论,如王磊的《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主书例”探微》[4]79。
何休《解诂·序》中讲:“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5]9据徐彦《春秋公羊疏》,“何氏作《文谥例》”[5]5。《隋书·经籍志》载何休撰《春秋公羊谥例》[6]931。徐彦《疏》中引“《文谥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5]5《文谥例》就是整部《解诂》的提纲[7]351,而“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就是“何休以例说经的大纲”[8]165。
一、“三科九旨”
关于“三科九旨”,徐彦《疏》中有“何氏之意”和“宋氏之注”两种说法。“何氏(何休)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5]5学者认为“三科九旨”是何休“例”的主旨[9]136。黄开国认为“‘三科九旨’的发明权并不属于何休,而是出于纬书”[7]372。吕绍纲则认为“三科九旨”是何休同左氏家论战的产物,其中有何休的“创造”。并且吕绍纲认为何休所概括的“三科九旨”抓住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根本问题,比之前辈后人都要“高明”[10]77-78。黄朴民基本认同吕绍纲的观点,但说法相对谨慎保守[11]92-93。黄开国对比“何氏”与“宋氏”的说法则认为“宋氏”的提法“较何休更为经典、更为明晰”[7]375,但黄开国同时认为这并不能说宋氏在春秋公羊学上的造诣高于何休。
(一)第一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何休第一科被认为是宋氏所谓的“存三统”,或董仲舒的“通三统”。顾颉刚认为“三统说”出于“三正说”[12]124,黄朴民也认为“通三统”就是所谓“存三正”[11]189。而黄开国认为“通三统”与“存三正”之间存在诸多龃龉与矛盾,“何休实际上并不重视‘通三统’。他不仅对‘通三统’论说极少,而且实际上有着与‘通三统’不同的观念”[7]379。赵伯雄认为何休《解诂》中对“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内容的解释都可以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看到,但像何休用以作为解释《春秋》的书法,“却是在《繁露》中不曾见到的”[8]166。黄开国也认为何休的“三统说”的具体内容继承自董仲舒,但黄开国讲“新王、周、夏为‘三统’”[7]377,“夏”恐怕是“商”的笔误。黄朴民认为第一科“是何休对今文经学家‘三统说’的重新解释,即以司马迁、董仲舒的观点为素材,加以彻底改造,注入全新的含义”[11]168。
吕绍纲认为何休“第一科”是何休提炼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黜周王鲁,这是《春秋》和《公羊传》中所没有,是“何休强加给《春秋》和《公羊传》的”[10]78。黄开国认为“通三统”作为一种历史观,在东汉已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理论。“应该注意的是他(何休)的‘王鲁’说与‘孔子为汉制’说”[7]380。章权才认为“王鲁”是何休政治思想中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其目的“一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关系;一是调整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13]237。吴从祥区分了“新王说”与“王鲁说”[14]51,他认为“新王说”是一种历史学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王鲁说”则是一种春秋笔法,突出的是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而曲利丽则认为何休发挥“王鲁”意在神化孔子[15]132。但因为“王鲁”只见于何休的《解诂》,而且与儒学尊崇维护政治秩序的主张相悖。所以历来反对者众多,或直接从对经文的解读上加以否定,或间接从对孔子的理解上加以否定[16]56-65。吴从祥就认为“王鲁说”没有坚实的材料基础,“多经不起推敲和反驳”[14]54。
(二)第二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休第二科被认为是宋氏所谓的“张三世”。公羊学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董仲舒据“君子之所见”“之所闻”“之所传闻”,分哀、定、昭三世为所见世,计六十一年;襄、成、宣、文四世为所闻世,计八十五年;僖、闵、庄、桓、隐五世为所传闻世,计九十六年[5]9-11。何休同意董仲舒对三世的划分。但颜安乐以孔子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 生,且《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昭公二十七年“二文不异”,所以划定襄公为所见世[5]4。何休驳颜安乐“以为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以为见,孔子始生,未能识别,宁得谓之所见乎?”[5]5因此,邱锋认为在三世的分期问题上,何休“采取了与统治太学的家法师说相对立的观点,依据纬书回归到公羊先师董仲舒那里”[17]132。当然,何休“三世说”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浦伟忠从一个社会历史宏观角度作了四点思考[18]28;邱锋则从何休本人生活的历史视野范围作了两点解读[19]280。
为什么是三世?何休认为:“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5]38邱锋认为这是何休以“《孝经纬》将《春秋》之义统一于孝道的论调”[17]132。黄开国认为三年之丧属伦理观念,三世之分则属历史观念,何休两相附会,“是难以服人的”[7]396。浦伟忠则认为何休的分期依据同董仲舒比起来,是“过而不及”,“企求以礼来解说,三世说的分期依据变得模糊起来”[18]27。他认为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何休三世递进的历史哲学。而张汝伦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何休三世说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系统化的历史哲学理论’,而在于他明确把‘立爱自亲始’的道德理论变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彰显了伦理与政治的连续性”[20]61。学者一般都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去解读“三世说”。汪高鑫认为在《公羊传》抑或《春秋繁露》中,“三世说”已经“蕴含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21]22。但浦伟忠则认为《公羊传》或《春秋繁露》中的“三世说”还只是一种历史分期的理论[18]26,“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一直到何休才正式形成”[22]130。何休受纬书的影响[17]132,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与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相对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衰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就使‘三世异辞’说由以往的书法意义为主,转变成了一种历史观”[7]402。
作为一种历史观或历史哲学,陈其泰认为“三世说”是“描述历史变易进化的哲理”,强调的是“变”[7]169。赵伯雄则认为何休的“三世说”有“历史进化论的性质”[8]166-167。浦伟忠认为“何休的三世说,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18]25。而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王化’是贯彻这三个发展阶段的主线”[18]28。黄开国认为何休的三世说是进化的历史观,但是一种渐进的历史观[7]403。而杨向奎则认为这是一种机械的和带有循环色彩的发展史观,但“它不是以古代为黄金世界的复古派,也免去向后看齐的倒退的政治理论”[23]164。刘家和等则强调何休的“三世说”是对“历史循环论”的突破[24]135。黄朴民认为何休的“三世说”并不同于泥古的复古史观[11]173。李建军也认为虽然何休“善复古”,但何休所谓“古”并不是真的“古”,而是假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构建一套理想制度。所以这种以进化为目的,复古为手段的复古史观也是一种进化史观[25]106。许雪涛则认为三世渐进的真正原因在于“复古”,所以“三世渐进非但没有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含义,相反却是对理想古制能成就大一统的说明”[26]94。而张汝伦不认为“三世说”是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他认为“三世说”讲的“是一个文明扩展的横向过程,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纵向过程”[20]61。许雪涛认为何休基于宗法文明的伦理政治意义的“三世说”,虽然强调三世渐进,但“只是针对春秋242年而发,后人加以‘历史哲学’的解读则有过度诠释之嫌”[27]28。
也有学者从“辞”的角度去理解“三世说”。如郜积意、陈绪波认为“三世异辞说”中含微辞、托辞例,这也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28]45。“三世说”可谓何休《解诂》中最为贯彻的一条书法义例,因为“何休几乎把《春秋》的所有书法原则全都纳入“三世说”的框架之中加以说明。”[11]170汪高鑫强调何休对公羊“三世说”的阐发是在“三科九旨”这一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中进行的[21]24。但何休的“三世说”并没有局限于“三科九旨”。像吴从祥就认为将《春秋》中诸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春秋制等书法也纳入到三世中[29]88。
何休在“三世说”中详细介绍了“太平世”,在描绘“太平世”时则更详细介绍了“井田之法”。冯友兰认为何休“在井田制度里边,对于农民的衣、食、住、保卫、教育、养老等都作了他认为是适当的安排,对于农业、林业、畜牧、储粮、备荒,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30]866。冯友兰认为这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出现的战国以来的井田思潮的一种复兴,“太平”这个理念则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的一个理想。但井田制只是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编造的幻想[30]867。而陈其泰认为“太平世”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何休思想中的人民性与民主性内涵[31]43。黄朴民认为何休的太平思想虽然有空想的性质,“但却多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11]230。“三世说”对历史的评论也与对应的历史并不相符[24]134,何休用“文致太平”来解释这个矛盾。许雪涛也从“书法”的角度作了说明,认为“三世说”“代表着一种完美的书写和传达理想的方法。”解经者借助经典的表述来说明某种在经典中并没有被明确说明的理念,即“曲的方法”[27]28。蒋庆认为何休太平大同的理想世界是为生活在乱世的人们提供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只是一种信仰,即历史中的信仰,而不是逻辑的推理,即不是理性的认识”[32]44。
(三)第三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何休第三科被认为是宋氏所谓的“异内外”。黄开国认为何休“异内外”存在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书法之义,也就是从内外的角度讲‘三世异辞’;第二是在“三世”的不同阶段,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原则规定;第三是讨论从衰乱到太平发展的路径,即如何实现‘张三世’归宿的太平世的问题。”[7]405黄朴民认为何休的民族思想是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以及“张三世”的历史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1]155。赵伯雄则认为第三科的意义在于说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王化”的推行范围有所不同:从空间上讲,从王化以鲁国为中心,进而扩展到诸夏,再由诸夏扩展到四夷的途径;从时间上说,是由据乱世进而发展到升平世,再由升平世发展到太平世。这个过程中,诸夏与夷狄“内外”的界限不同,相应的地位也不同[8]167。
第三科关注的对象是诸夏与夷狄,换言之,处理的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华夷之辩”是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华夏与夷狄其区别不在种族的差异,也不在地理的区别,而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同,也就是文化上的区别。如黄朴民就认为何休是以文明发展的程度作为区分夷夏性质的标准[11]147。而浦伟忠则认为在何休的公羊学中“礼、信、义、尊王,是诸夏区别于夷的重要标志”[22]143。杨向奎认为公羊学中的“中国”或“夷”“夏”“不是种族或民族概念而是政治或者伦理上的概念”[23]95。但是华夏夷狄之间的文明区别并不是固定的、永恒的。黄朴民梳理了何休之前的夷夏观,认为何休并没有继承《孟子》 《盐铁论》 《白虎通义》中狭隘落后的民族思想,而是继承了孔子、董仲舒开放进步的民族思想。何休在严夷夏大防的同时,也会进夷狄于华夏,退华夏于夷狄。何休的民族思想具有双重的性质,“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11]148。但何休肯定夷狄的生存与进化的权利,为实现民族融合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性,是进步的学说。李光迪基本接受黄朴民的论述,但并不同意黄朴民关于何休夷狄思想的结论,认为“夸大了何氏‘进夷狄’理念中的积极成分”[33]84,没有看到何休思想中“华夏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康宇凤则认为何休面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世族崛起以及分裂倾向,继承了公羊学“大一统”的观念,“尊王”“攘夷”,反对分裂,致力于总结与弘扬“大一统”民族思想[34]14。
二、“五始”与“大一统”
据徐彦《疏》讲:“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5]6《公羊传》讲:“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5]6-9学者多将“五始”与“大一统”联系起来一同论述。像赵伯雄认为“五始说”表达的是何休的天人观与政治观[8]165。而黄朴民则认为何休的“大一统”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际之学,是着眼于社会政治“大一统”的现实政治哲学”[11]109。赵伯雄认为何休的“五始说”“与董仲舒的学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8]165。黄开国认为何休“五始说”明显受到了东汉谶纬神学的影响[7]353,比董仲舒的说法更为精密。
陈其泰认为何休“五始说”描绘了一个由“元气”、“天”、“王”、“天子政事”、“诸侯治国”构成五位一体的“世界图式”[35]71-72。黄开国则认为“五始说”是“将从世界本原到一国境内之治的宇宙秩序,分为五个层次”[7]353,元属气,春、王属天,正月、公即位属人,何休又以分为气、天、人三个层次。蒋庆认为“大一统”或者说“五始说”解决的是政治秩序合法性及其在历史中表现的问题,也就是要论证的是“大一统”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蒋庆认为“元年春”说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必须建立在超越形上的价值本源上”,“王正月”则说明“超越形上的价值本源必须在历史中的特定政治形态—王政—中表现出来”[32]277。黄朴民接受陈其泰与蒋庆的看法[11]108。但刘家和等则认为何休的“大一统”理论强调历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统一,换言之,何休不仅强调在政治上天下统一于天子,“它还有在‘中国’文化、文明这种先进文化、文明方面达成统一的含义。”[24]133张汝伦则认为汉儒理解的“大一统”并非政治上的“大一统”,不是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而是强调“始”,“强调政教创制要有一根本的原则出发点”[20]59。
当然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黄朴民就认为从政治角度讲,何休“站在极端专制的立场,将君臣关系完全绝对化,斥了早期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合理因素”[11]116;从书法角度讲,何休的思想中也存在背离“大一统”原则的内容。
三、“二类”
据徐彦《疏》讲:“二类者,人事与灾异是也。”[5]6赵伯雄认为何休继承了西汉董仲舒讲灾异的传统。黄开国也认为“从思想本质而论,何休的灾异说不过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新东西”[7]364。但何休进一步将灾异附会人事,从神秘主义方向发展了春秋公羊学。赵伯雄讲:“何休说灾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每一项灾异都要推寻其致变之由,说明灾异究竟是应在哪一桩人事上”[8]168。何休的灾异论与董仲舒也有不同,如吴从祥认为在何休的论述中“异无害于人物而灾有害于人物;灾的威力大于异,但异的意义大于灾”[36]183。何休的“灾异说”也受到了东汉谶纬的影响。鲍有为等特别指出了何休对灾异的公式化阐释就与京房关系密切[37]53。黄开国认为在东汉已经有王充以元气来解释自然现象,并对天人感应作出了实证式的批判的情况下,何休广引谶纬鼓吹灾异的做法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7]365。汪高鑫则认为何休恰恰是透过对“气”的解读为“灾异”与“人事”的感应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38]98。
蒋庆认为公羊学这种天人感应说的功能就是对政治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纯假灾异对统治者进行恐吓,而是揭示出统治者行为与灾异之间具有某种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而使统治者见天戒而悔过自新。建立良好的政治。”[32]216吴从祥也认为何休的“灾异说”一方面试图维护大一统的政权;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民生的关注以及对民声的重视[39]51。黄开国认为何休的这一附会之说,针对结合东汉末年的政治动乱,将天灾归于人祸,这无疑具有批判社会黑暗的现实意义,而且借这种天人感应之说批判社会现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积淀”[7]365。
四、“六辅”、“七等”、“七缺”
据徐彦《疏》讲:“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5]6这部分内容学者论述少。黄开国认为“六辅”与“七等”是何休对公羊学理想社会结构制度的义例的归纳。“六辅”讲的是君臣等级制的政治结构以及地方与中央的社会组织,但却只有下级辅助上级、地方辅助中央,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下对上单向的“辅”。而且黄开国认为“六辅说”“实质上是与大一统相通的,或者说‘六辅’是大一统的制度保证”[7]366。至于“七等说”黄开国则认为是孔子重名思想的发挥。康宇凤认为“七等说”中体现了华夏中心主义,“反映了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倾向”[34]21。“七缺”是何休总结在《春秋》的记载中礼制上的七个缺失。黄开国认为“七缺”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的总体缺失,“主要是从三纲高度,来批评春秋时期的政治缺失。反映了人们对礼的认识的时代变化”[7]366。“七缺”与“二类”同属何休批评政治缺失的义例。但也有学者认为“七缺”并非由何休总结,而是出自《春秋说》,所以学者认为“七缺”是何休之说,“是读书不细而致误”[40]74。
小结
对于何休“例”的来源,学者的意见大同小异。杨向奎认为像“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这些理论中有何休继承的传统学说,也有何休自己的理解与创造[41]98。赵伯雄则认为何休的义例来源,有总结和继承传统公羊学派的种种义例,也有一批自创的新例[8]169。章权才认为《解诂》中的“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承袭先师的;一类是加以畅通的;一类是何休自设的”[42]95。而赵友林认为何休对“例”“简略者充实之,未备者补足之,无有者创建之”,有“回护、弥缝”,也有“修正、扩充”。而且他认为何休据“三科九旨”“赋予了书法时间、内外、大小三个变化向度,从而使书法的变化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发展进程”[43]14。
对于何休“条例”的性质或主旨。黄开国认为“三科九旨”是何休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五始”是何休关于“正本贵始”的说明;“二类”与“七缺”是何休关于政治缺失与灾异的内容;“六辅”与“七等”则是何休对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7]351。杨向奎认为何休的“例”既是历史学理论,也是政治理论[41]98。章权才也认为“例”使得《春秋》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经学”[42]95,何休“衰世救失”的政治企图就是以“例”的形式或明或晦地表达了出来。黄朴民认同章权才的观点,他也认为何休诸如“五始”、“七等”、“六辅”等义例,“就是为了‘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是直接服务于‘尊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的”[11]92。
近代以来对何休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经学到哲学的转换,现今对何休的研究不再集中于何休对公羊学文本意义上的整顿,而是集中于何休对公羊学的发展,也就是完成了从考察何休的师承与文本到讨论何休的思想与影响的转变。虽然也有文章也着眼于何休的时代环境对其作论述,但现今对何休的研究中更多是有关书法义例的讨论。围绕何休的“例”,尤其是“三科九旨”形成了不少的论文。但局限于文献的缺失,有关何休的研究多是追溯何休思想的渊源,或董仲舒作比较,或讨论留存的谶纬材料。这部分讨论在何休的研究中占大部分。多数文章只是选择某一主题从理论的角度讨论何休公羊学的主旨,论述何休公羊学后世影响的多。少有文章去具体分析何休公羊学的主张,更缺乏对何休思想逻辑及历史的整体论述。
[1]戴维.春秋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2]梁启超.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清]刘逢禄.郑任钊校点.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王磊.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主书例”探微[J].孔子研究,2016(05).
[5][汉]董仲舒.[清]苏舆义证.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第 4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赵伯雄.春秋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9]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10]吕绍纲.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J].人文杂志,1986(02).
[11]黄朴民.何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3]章权才.两汉经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14]吴从祥.论何休《春秋》王鲁说[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
[15]曲利丽.何休与董仲舒《公羊》学比较[J].文艺评论,2012(02).
[16]刘伟.王鲁例:刘逢禄对经学诠释范式的新创立[D].苏州大学,2008.
[17]邱锋.何休“公羊三世说”与谶纬之关系辨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2(04).
[18]浦伟忠.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J].史学史研究,1993(01).
[19]邱锋.何休“公羊三世说”二题[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00).[20]张汝伦.以阐释为创造: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一个特点——以何休为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21]汪高鑫.何休对公羊“三世”说的理论构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
[22]浦卫忠.春秋三传综合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23]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4]刘家和,李景明,蒋重跃.论何休《公羊解诂》的历史哲学[J].江海学刊,2005(03).
[25]李建军.进化与复古的双重变奏:何休“三世说”辨析[J].管子学刊,2007(01).
[26]许雪涛.公羊学三科九旨及其内在逻辑[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04).
[27]许雪涛.何休公羊三世说及其解经方法[J].学术研究,2011(04).
[28]郜积意,陈绪波.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J].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
[29]吴从祥.何休“三世说”浅议[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03).
[3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7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1]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2]蒋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33]李光迪.“天下归一”:公羊学视角下的何休“进夷狄”思想[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6(02).
[34]康宇凤.何休对春秋公羊学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D].内蒙古大学,2008.
[35]陈其泰.论何休对儒学发展的贡献[J].东岳论丛,1995(60).
[36]吴从祥.何休灾异说浅议[J].齐鲁文化研究,2007(06).
[37]鲍有为,王承略.汉代京氏易学与何休公羊灾异论[J].周易研究,2015(05).
[38]汪高鑫.何休“人事与灾异”“二类”说论略[J].中州学刊,2004(02).
[39]吴从祥.论何休灾异说[J].绥化学院学报,2008(03).
[40]葛志毅.《春秋》例论[J].管子学刊,2006(03).
[41]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42]章权才.何休《公羊解诂》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1984,(01).
[43]赵友林.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