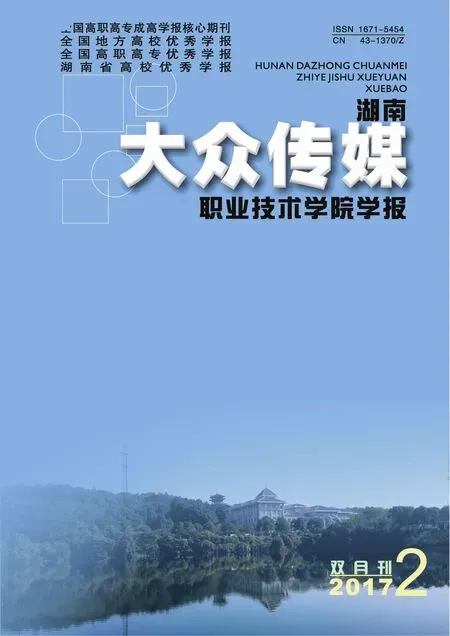试论传播学“二元对立”的历史由来与学术意识形态
2017-03-10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试论传播学“二元对立”的历史由来与学术意识形态
黄经纬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传播学“二元对立”是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史学家为解决传播学危机,基于历史上法兰克福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段既“合作”又“对立”的恩怨,而建构出的一种学科史的自我叙述。这种自我叙述体现了主流传播学术共同体既焦虑又期盼、既想解决危机又不愿放弃霸权地位的学术意识形态。这种学术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二元结构,既造成后来传播学内部的撕裂,更无助于主流传播学危机的解决。
传播学;批判学派;二元对立;学术意识形态
传播学的“二元对立”,通常被认为源于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但有趣的是,施拉姆在创建传播学时,并没有将法兰克福学派纳入学科建制。我们不禁追问,传播学何以会被描述成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的建构反映了当时传播学怎样的学术意识形态?这种学术意识形态又对传播学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
一、“二元对立”的解构:被建构的“批判学派”
在回答“为何二元对立”的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检视“二元对立”结构本身,尤其要追问:作为二元对立其中一极的“批判学派”,其内涵究竟为何?
“批判”一词是霍克海默从马克思的理论派生而出的,霍克海默及其同志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者,他们将自身“否定性”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因而很喜欢被人称作批判的理论家。而“批判学派”,按罗杰斯的说法,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及后世受其影响的一批学者所组成的理论团体。然而,尽管现今我们仍然延用“批判学派”这个名称,但是必须“承认无论是今天的批判学派,还是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都不能代表一个统一的理论事业”。[1]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内部诸君的理论来源多元且取向迥异。马丁☒杰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谈到,30年代的理论家们并不试图建立某种学术派系,成立社会研究所是为了抵抗当时僵化的德国大学体制,以保有自己跨学科的兴趣和研究的独立性。正是这种对独立性和跨学科的强调,造成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这两种反差极大的理论在研究所奇妙并存的景况。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系谱的“批判理论”随时间推移不断流变,甚至出现“理论变异”。兰德尔☒柯林斯指出:“1970年代至1980年代,哈贝马斯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建立了他自己关于社会的普遍理论。”[2]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血统到哈贝马斯那里已经变为“批判”外衣包裹下的“结构功能主义”。
仅从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流变情况来看,“批判理论”这一松散的团体不能被称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而晚近传播学话语中的“批判学派”更囊括了脉络差别极大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等研究传统,面貌变得更为复杂。那么,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何以会被化约为“批判学派”这一符号,并以与“经验学派”分庭抗礼的姿态出现在传播学的话语体系中?
二、“二元对立”的历史由来:学科危机的召唤和历史事实的裁剪
早在1959年,贝雷尔森就指出传播学研究缺乏新思想,将面临“枯萎”的危机。20世纪50至70年代,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让传播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也导致传播研究的“科学主义”拜物教。赖特☒米尔斯曾批判道,作为社会科学共同尺度的“科学”之含义早已变异,“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成为‘科学主义’,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问题。”[3]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将个人或事件置于“社会-历史”的维度中形成一种“同构”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对人或事件的真正探索。但传播实证研究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正好与此相反,“实证研究方法往往只能做到同一时间维度下的空间取向而无法兼顾研究的时间取向和历史脉络,因此它的研究必然与传播现象中的历史因素相脱节而无法回应事物的时间变迁。”[4]正是由于“科学主义”拜物教,定量方法成为传播研究的霸权取向,而传播学变成“方法先行”的学科,研究视野越发局限于米尔斯所说的“学术剩余物”,学科危机也就接踵而至。
另一方面,美国遭遇意识形态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新左派运动”为代表的左翼思潮、7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和美军在越战的种种作为,极大动摇了美国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相应地在社会科学界,为主流意识形态出谋划策的行政取向的实证研究受到美国知识分子的批判。
当“科学主义”和“行政研究”受到批判,传播学面临危机时,传播学者不得不反思传播学界定和传播学边界的问题,不得不回到传播研究的历史中去寻找“治病”的“药方”。而正是在这场西方意识形态危机中,主流传播学者看到了当代欧洲思想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存在引导着传播学史学家发现了曾被无视的法兰克福学派。而历史上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一段恩怨,为“二元对立”的建立提供了可被书写的“历史材料”。
193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被纳粹政权关闭,批判学者开始在美国与欧洲的流亡生涯。1934年,在拉扎斯菲尔德和林德的帮助下,社会研究所从纳粹魔爪下逃出生天,并于哥伦比亚大学重建。从进入美国到返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有过多次合作,但多数以失败而告终。其中,阿多诺参与纽瓦克广播研究项目的合作失败,被罗杰斯记入了《传播学史》“批判学派的历史大事记”。从“大事记”可以看出,1938年这次失败的合作被书写成两个学派从亲密到分离的转折点。尽管马丁☒杰指出这次失败与阿多诺本人乖张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研究风格有莫大的关系,但它仍被视作两个学派“二元对立”的重要证据。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与思辩的研究方法与哥伦比亚学派经验的研究方法有明显区别。这是“二元对立”结构的“学理”来源,也是“二元对立”最具迷惑与混乱性的“灰色地带”。事实上,这种区别是由于两方的研究并不在同一层次上,前者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统摄的整个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后者则致力于对中观或微观社会结构的研究, 因此方法论上的“对立”并不成立。但这种方法上的区别,却被建构成各种“对立”,如“经验研究”与“反经验研究”的对立,“实证研究”与“反实证研究”的对立。再次,批判学者对行政研究的批判被认为是“二元对立”的另一重要证据。阿多诺曾公开表示对行政研究的不满,他认为行政研究的实证主义“把文化和可测数据完全等同是大众文化物化特性的典型体现”,[5]而对文化物化的批判正是批判学者的重要立场。最后,二战过程中批判学者在美国战时新闻局和保密情报局的渐渐消失,以及战后哥伦比亚学派和耶鲁学派合流,并与法兰克福学派分道扬镳的事实,为史学家建构“二元对立”提供了结果上的“论证”。
除了“对立”的历史证据,我们还应看到两方成功“合作”的历史事实,因为史学家发掘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是为找到传播学“第二春”的可能。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单独列出《权威人格》并重点论述的做法令人深思。《权威人格》是阿多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取得的重要成果。史学家认为,也许能够从此次成功的合作中得到解救传播学的启示。除此之外,罗杰斯在“批判学派和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学派”这一部分中专门提到洛文塔尔,洛文塔尔曾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大众文化,并且得到默顿高度赞扬。显然,洛文塔尔也被追认为批判研究和实证研究成功结合的典范。正是因为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有着这样既“合作”又“对立”的“历史事实”,史学家才得以开始“二元对立”的书写。
三、“二元对立”的学术意识形态:主流传播学术共同体的焦虑与期盼
主流传播学者发掘法兰克福学派是为解决学科危机,然而被遗忘的传播研究谱系除法兰克福学派外,还有芝加哥学派和北美技术学派。为何史学家要选择“二元对立”而不是“一超多强”或者更为多元的结构开始历史书写?这种结构反映了主流传播学术共同体怎样的学术意识形态?这种学术意识形态又对传播学的发展造成了何种影响?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将意识形态分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总体性的意识形态”。特定的意识形态是指当现实的本真性不符合该团体的利益时,其对真相的部分意义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掩饰或扭曲的一种观念体系。而学术意识形态,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共同体”对“学术现实本真性”进行改造的“特定意识形态”。
对主流传播学来说,其学术意识形态就体现在学科历史的自我叙述中。自我叙述是一套符号体系,“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是该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两个符号。结构主义认为,“符号”的意义产生于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运作。处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其意义就产生于二者的差异性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符号在二元结构中被同等看待。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指出,对立的两项总处于不对称的关系,结构和认知更复杂的那一项往往被视作“标出项”,即“异项”,指“他者”;余下的一项为“非标出项”,又称“正项”。“批判学派”就是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异项”,其存在就是为区别于作为正项的“经验学派”。而“二元对立”结构所暗含的学术意识形态存在于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中。
首先,70年代“二元对立”结构的建立,意味着对除“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之外的其他所有范式的排斥。这种排斥背后,是主流传播学术共同体面临学科危机时,对是否打开学科边界、多大程度上打开边界的怀疑与忧虑。打开学科边界,意味着在学科体制化之后的研究成果会遭遇挑战,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会遭质疑,这是罗杰斯和詹姆斯☒凯瑞等人所害怕见到的。但是,学科的危机不允许传播学者固步自封。在这种矛盾下,他们有三个可能“解决危机”的选择: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技术学派。芝加哥学派在凯瑞的建构下,代替哥伦比亚学派成为主流传播学的新起点;而同时代的技术学派过于天马行空,因此未得重视。更重要的是,这两大源流都无法与60年代最活跃的左翼思想家产生历史关联。所以,史学家选择了与主流传播学不论是时间还是学术实践上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呼应当代的批判理论家,期盼以建构起的“二元对立”结构来拯救学科危机。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传播学话语中的“批判学派”所涵盖的理论谱系越发复杂。史学家将所有不同于批判实证取向的理论统统归进“批判学派”。更夸张的是,90年代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中,将英美文化研究传统、美国本土社会批判传统、女性主义传统甚至是麦克卢汉的技术传统通通划归到“批判学派”。面对层出不穷的“批判性”理论,史学家被迫不断地重释“批判学派”内涵和“二元对立”结构,传播学边界一次又一次被解构和重构。
将所有异己理论都划归“批判学派”的做法体现了“二元对立”更为重要的一种学术意识形态,即经验学派依然想维护自己的“学术霸权”。“批判学派”是一个被“标出”的“异项”,始终被视作与“经验学派”相区隔的“后来者”。而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所有“后来”的理论传统都被视作传播学的“移民”,被安置于“批判学派”这个“社区”,以维持两大学派界线的泾渭分明。以经验学派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牢牢掌握着“批判学派”的“命名权”,它以这种给后来者命名的方式,宣示自身在传播学中的话语霸权,维护“二元对立”的合法性。
正是由于主流传播学这种既焦虑又期盼、既想寻求危机解决又不愿放弃霸权地位的学术意识形态,造成后来传播学极其矛盾的一种状况:看似学科版图不断扩张,但传播学一直处于“撕裂”的状态。不得不承认,这种“撕裂”有其客观原因。尽管各种证明“二元对立”的证据颇有问题,但两个学派的确存在着一种“对立”,即“研究取向”的对立。胡翼青将这种“对立”概括为美国社会科学体制化背景下,坚持批判立场、学术独立的“知识分子”与作为政治与权力顾问的“专家”的对立。这种价值立场上的“撕裂”使得两大学派难有融合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这种“撕裂”同时也是主流传播学在其学术意识形态支配下,从“话语逻辑”上对各种理论取向拒绝的结果。
依照文化符号的观点,对立的文化范畴中除了“正项”与“异项”之外还有一个“中项”。中项是一种无法自我界定而必须依靠正项来表达自身的项。赵毅衡指出:“任何两元对立的文化范畴,都落在正项/异项/中项三个范畴之间的动力性关系中。”[6]具体来说,在二元结构中,中项只有依靠正项才能不被标出为异项,而正项只有争夺到中项携带的意义权力,才能真正确立自己在二元结构中的支配地位。然而在传播学“二元结构”中,作为“正项”的“经验学派”,将后来不断出现的“中项”(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等各种所谓“批判性”理论传统)“标出”为“异项”,使作为“异项”的“批判学派”的话语力量越来越强,自身在传播研究领域却日渐“失语”,甚至出现“标出性历史翻转”的倾向,即“异项”变成新“正项”,传播研究江湖易主的趋势。这不仅加剧了“二元对立”两极之间的撕裂,更使得“经验学派”自身越来越封闭。尽管在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护佑下,实证研究仍大有市场,但随着来自“批判理论”阵营的批评越来越多,其欲维持的霸权地位已渐趋瓦解。
正是由于这种“焦虑又期盼”的学术意识形态,批判的传播研究始终没有真正为主流传播学所汇通,只是作为一个新添的知识版图被牢牢地钉在主流传播研究的边缘位置。对主流传播学而言,“批判研究”仿佛被建构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救赎彼岸”,两大学派之间被划出一道不可撼动的楚河汉界。“二元对立”结构无助于传播学危机的解决,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主流传播学者再次寻求新的革新之时,“二元对立”结构反而成为学科范式革命的阻碍,不断遭受质疑和批判。
(责任编辑 陶新艳)
[1] 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11.
[2] 兰德尔·柯林斯, 迈克尔·马尔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6:446.
[3]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2.
[4]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211.
[5]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辩证的想象(1923-1950)[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254.
[6]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86.
G206
A
1671-5454(2017)02-0031-04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7.02.007
2017-03-13
黄经纬(1992-),男,湖南武冈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传播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