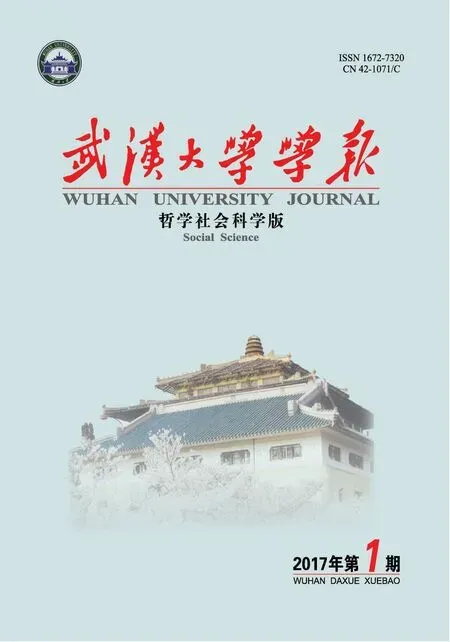惊变①与重组:维尔达夫斯基的政治文化研究*
2017-03-09杨绘荣
杨绘荣

惊变①与重组:维尔达夫斯基的政治文化研究*
杨绘荣
政治文化时常被视为一个静止的、缺乏活力的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它偏好“稳定性”,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变化。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另辟蹊径,尝试突破前辈学者过多关注政治文化静态层面的局限性,挖掘出其动态机制,力图将政治文化与政治变化统一起来。根据维尔达夫斯基的研究,可以找到政治文化变化的两条常见路径——“惊变”与文化重组。
惊变; 文化重组; 维尔达夫斯基; 政治文化变化
一、 政治文化如何变化?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那些必然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且不易改变的有关政治生活的习惯,即经由“社会化”这一遗传机制而形成的一整套政治态度、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观念等,它常常被视作维系政治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和政治变化的对立面。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曾详述过“渐进社会化”(cumulative socialization)的内涵,认为人们的早期学习对后期学习起到了“滤纸”般的作用,早期习得的东西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内心且不易改变,它有助于人们将各式各样的学习片段整合成一个更宏观的连贯模式,从而形成稳定的文化倾向(Eckstein,1988:790-791)。也正因为文化承载了许多惯性的东西,艾克斯坦认为难以迅速转变人们的文化倾向(Eckstein,1988:796)。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主要表现为一定的共同体人群的共享性、延续性和继承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稳定性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变动而言,常常用于解释不同共同体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变动的差异性,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然而,若要解释一国(或共同体)政治变化的话,这种强调社会化和惯性的传统政治文化理论恐怕难当此任。但英格尔哈特指出,若非通过文化,人们是如何认知到自身的利益与偏好的,尤其是在面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时(Inglehart,1988:1229)?
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的学者大多译为威尔达夫斯基,而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如丛日云、王乐理等大多译为维尔达夫斯基,本文主要参考后者的译法。的文化模式理论似乎能够提供一条可行的分析路径。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他基本沿袭了阿尔蒙德的研究传统,关注人们的政治偏好。沿着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网格—团体”(grid-group)*在道格拉斯看来,“团体”是指个人与具有严格界限的单元体结合的程度。这种结合力越强,个人的选择就越服从于团体的决策。“网格”是指个人生活受到外在社会规定性约束的程度。社会规定性的范围越广泛,就越具有强制力,个人之间进行协商的空间就越小。类型学的研究轨迹,维尔达夫斯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文化偏好、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机制,概况出五种基本的文化模式,即等级主义(高团体、高网格)、平等主义(高团体、低网格)、个人主义(低团体、低网格)、宿命论(低团体、高网格)和隐士的生活方式*文中的“文化模式”、“政治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均指同一概念。(或自主的生活方式),形成其文化模式理论,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代表。文化模式理论为政治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解释框架,摒弃了等级制与个人主义的“两分法”以及过分强调民族性的研究取向,为理解政治文化的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维尔达夫斯基尝试打破前辈学者关注政治文化静态层面的局限,挖掘出政治文化的动态机制。在政治文化解释力方面,他反对将文化与变化对立起来,认为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地一代接一代往下流传,而是随着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变动。文化模式理论批判“静态文化观”,试图阐明政治观念体系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致力于将文化与变化统一起来。维尔达夫斯基不仅关注早期学习对于塑造公民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还更加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即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文化模式理论在解释政治文化变化方面遵循特定的模式与规律,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 “惊变”与文化重组:政治文化变化的主要路径
既然政治文化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态物,那么,政治文化的稳定性也不再是一种终极的、没有任何活力的状态。如维尔达夫斯基所言,稳定性也需要不断注入活力,各种变化或运动也只是为了保持各种生活方式原来所处的社会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变化是稳定性的“永久伴随物”(Thompson,Ellis & Wildavsky,1990:66)。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变化的理论,它验证了变化对于维系文化模式的稳定性而言不可或缺。从该理论出发,可以找到政治文化变化的两条常见路径。
(一) 惊变
与强调“社会化”和早期学习的文化理论不同,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强调终生的学习过程。道格拉斯曾经指出,社会化不仅出现在孩童时代,而且还贯穿整个人生,她还特别强调说,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孩童时代养成的习惯与民族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这显然低估了“人类的适应能力”,该理论视角“在面对变化时表现得无能为力”(Douglas,1982:185)。文化模式理论坚持认为,人类并非带着一系列偏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其偏好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是制度背景和社会关系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通过将社会关系和制度背景融合到文化之中,便可预见并理解政治文化的变化。
维尔达夫斯基强调政治文化与实践经验密不可分,认为文化如同一层“滤纸”,通过这层滤纸人们便可感知整个经验世界,同时社会实践经验又反过来塑造着人们的政治文化偏好。正是经由文化偏好与社会经验这种相互作用,人们将自身归为五种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个人主义、等级主义、平等主义、宿命论和隐士的生活方式,且每种文化类型均持有与自身文化偏好相符的自然观、人性观及政治价值观。有些文化类型在观念上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某种文化模式所谓的理性行为,在其他文化模式看来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在自然观上,个人主义者坚信自然是仁慈的(Nature Benign),认为自然非常宽容,不管人们对自然界施加何种外力,也不会带来严重后果。与之截然相反,平等主义者持有自然短暂说(Nature Ephemeral),坚称自然十分苛刻,哪怕极小的举动也可能使自然界遭受致命破坏。等级主义者比较中庸,信奉自然刚愎∕宽容说(Nature Perverse/Tolerant),认为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宽容的,可以容许人类在一定程度上的开发利用,但一旦过度使用,便会带来巨大灾难。宿命论者坚持自然多变说(Nature Capricious),断定外在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反应是随机的,认为生活总是如同买彩票一般,给人们提供资源的往往是运气而不是个人努力。隐士们笃信自然弹性说(Nature Resilient),批判其他文化模式只是抓住了自然的部分属性,认为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因而采取避而远之的策略。
再如,在人性观上,个人主义者相信人性利己,认为没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阻止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共同体的利益,他们信奉竞争性的体制。相反,平等主义者深信人类生而“善”,只不过被邪恶的制度环境所腐化,若构建一个平等主义环境,人性也能被塑造得非常“善”,他们反对可能导致结果不平等的竞争。等级主义者相信人生而有罪,但可以通过良善的制度赎罪——即遵守等级秩序,大家各就各位,他们相信掌握权威信息的专家。对于宿命论者而言,人性是难以预测的,他们往往任凭命运摆布,从来不会期望从别人那里获取什么东西,因而一般都不相信其同伴。隐士们时而认为人性善,时而认为人性恶,意欲逃离任何社会关系的束缚。
既然每种文化模式都有各自坚守的观念体系,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失去或赢得拥护者的呢?对此,维尔达夫斯基引入“惊变”这一概念描述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用以预测政治文化变化的方向和方式。当现实偏离人们的预期时,“惊变”就会发生,紧接着便是不断地怀疑、猜测甚至背叛。倘若现实世界持续令人感到意外和惊讶,人们可能会转而寻找一种与现实相符的政治文化模式,最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偏好,完全改变其原有的文化模式。以个人主义者为例,假设有一位具备“理性人”典型特征的生意人,作为一个期待获取最大利益的个人主义者,他崇尚自由竞争,生意也一直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试想有一天,因政策变动或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无论他如何努力,不仅难以维持原来的盈利状态,反而每况愈下,甚至破产。届时,他可能会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世界并未按照其预期在运转。倘若令人失望的结果持续发生,他便很可能改变其坚守的世界观、价值观,寻求一套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观念体系,从而转化为另一种政治文化模式(如宿命论或等级主义)的支持者。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变化在美国1929年那场经济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当时的环境下,个人的努力与收获之间难成正比,由此导致人们崇尚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信念遭受破坏,支持其他政治文化模式的倾向日渐突出。曾经将贫穷和失败归因于个人懒惰和运气不佳的个人主义者开始意识到,由“大萧条”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状况才是真正推手,而这些都并非个人主义者所能掌控的。在经受了一次次“惊变”的打击后,他们原有的个人主义信念开始动摇,最后选择“背叛”,转而支持罗斯福新政,即肯定政府干预对于振兴经济的作用,成为等级制的支持者。当然,其他文化模式*这里“其他文化模式”不包括隐士的生活方式,因为隐士们几乎脱离了社会关系,过着类似于“出世的” 生活,维尔达夫斯基在分析问题时一般忽略该文化模式,据此亦可将其他四种文化模式称为“入世的”。的拥护者也会遭遇类似的“惊变”,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发现自身所处的环境是富饶的,便逐渐调整其观念模式,由此导致平等主义文化停滞不前。同样地,若宿命论者发现其所处的环境资源短缺,便可能会逐渐意识到,为了维系生存,他们需要与同伴共享有限的物质资源,而不是静待命运的安排。等级主义者可能发觉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随机的、不受掌控的环境中,其信任的专家在勘探和分配资源等问题上,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最终导致他们不再信任专家,转而投向宿命论,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个随机的世界。
维尔达夫斯基提出,在所有可能的文化变化*维尔达夫斯基以四种“入世的”文化模式为基础,指出每种模式都有可能朝着三个方向变化,于是便有六组、共计十二种转变类型,即宿命论者到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到宿命论者;等级主义者到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到等级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到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到平等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到宿命论者、宿命论者到平等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到宿命论者、宿命论者到等级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到等级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到平等主义者。中均能发现相似的案例。比如,从宿命论者到个人主义者是“乞丐到富翁”故事的文化基础;个人主义者可以通过官僚化的过程逐渐演变成等级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又可能通过内部分裂的方式变成平等主义者;若平等主义者被体制抛弃,却未获得其应有的平等地位,则很可能转变为宿命论者(Thompson,Ellis & Wildavsky,1990:75-78)。这些政治文化变化类型在我国也能找到对应的案例。譬如,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农村推行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民大多持有平等主义和宿命论的文化偏好。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广大农民惊讶地发现,个人的努力与收获是成正比的,多劳多得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生产积极性也得到极大提高,于是他们转而信奉个人主义文化。再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对比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城市人相对优越的身份,不少原先信奉个人主义文化的农民工在城乡二元体制的现实面前渐渐转向“宿命论者”,无能力感不断加强。这些案例可以证明政治文化的变化无处不在。文化模式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系统地规范这些变化类型,预测政治文化变化的方向,同时提供多种替代性的政治文化模式,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有利于缓解文化冲突,维系社会稳定。
(二) 文化重组
在维尔达夫斯基看来,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模式的统一体,在各种文化联盟之间摇摆不定,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个人主义者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并非霸权地位,为了适应时代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个人主义者不断寻求与其它文化模式结盟,时而与平等主义者,时而与等级主义者。正如维尔达夫斯基的观点:“网格—团体”类型学通过确定构成文化同盟基础的不同文化间相吸和相斥的因素,能够合理地解释政治变化(Thompson,Ellis & Wildavsky,1990:86-96)。维尔达夫斯基指出,每一种文化模式必然有其内在的缺陷,没有一个能够独自生存,每种生活方式都离不开其竞争者,或者为了弥补自身不足,或者为了加以利用(Thompson,Ellis & Wildavsky,1990:4)。此外,每种文化模式均与其竞争者共享某些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在“网格”维度处于低值,它们都注重个体自主性,反对等级权威。正是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为文化结盟提供了基础。但是也必须看到,每种文化在某些核心价值观上与其竞争者是相异甚至完全相反的,在表面的同盟体之下实际上一直都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因此,从长远来看,文化结盟注定只是暂时性的。
在美国殖民地时期,英国颁布的强化殖民统治的规定引起美国个人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偏好自由竞争的他们最终选择联合平等主义者,共同抵制英国的殖民体制。这显然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共同组合而成的反等级权威同盟,该同盟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维尔达夫斯基指出,这场由“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同盟担当的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辉煌胜利,是因为等级主义在美国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平等主义者将等级制的中央政府视为不平等的根源;至于个人主义者,他们倡导机会平等,坚信一个弱小的中央政府意味着较少的规制和较低的税款(Wildavsky,1991:34)。因此,在早期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追求结果平等的平等主义与追求机会的个人主义能够相互兼容。
然而该文化同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二者都期望个体行动受到较少的约束,但二者对待权威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偏好最低限度的权威,后者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威。个人主义者热衷于物质资源的获取,逐渐开始赞成通过广泛的国家权力达成这一目标,就这一点而言,个人主义者更接近于等级主义者,而不是平等主义者。与此同时,在革命爆发后的几年时间里,平等主义者不断通过立法机关抨击财产权,与个人主义者渐行渐远,为个人主义者转而与等级主义者结盟提供了契机。维尔达夫斯基认为,1787年的宪政传统正好表明了个人主义者试图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古弗尼尔·莫里斯:以执笔撰写美国宪法序言著称于世,他机智善辩,独具慧眼,为自由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些等级主义者结盟的意向(Ellis & Wildavsky,1989:24-31)。这个阶段形成的联邦主义者同盟创立了一个更为集权、更为强大的联邦政府。只可惜,该联邦主义者同盟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联邦党人过分强调中央权威,令个人主义者倍感失落,他们开始重新考虑与平等主义者结盟。
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美国的平等主义力量与日俱增,最终演化为激进平等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同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激进平等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要求重新分配资源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任何差异性的文化观念。他们大力宣扬结果平等,显然已将矛头对准支持社会分层的个人主义者。在维尔达夫斯基看来,正是这股强大的激进平等主义力量,最终完全粉碎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同盟,迫使个人主义者不得不转而与倡导差异性的等级主义者再次合作,重新强化能够有效保护个人财产安全的联邦制,结成“个人主义—等级制”文化同盟。
可见,在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政治文化模式的结盟、解盟和再结盟随时势而变动。具体而言,作为个人主义者,他们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免受威胁,他们会合适宜地选择与不同的文化模式结盟。当英帝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管制时,个人主义者便与平等主义者结盟以保护自治型政府;当平等主义者开始威胁到个人财产权时,他们便选择与等级主义者合作,创立了可以有效保护个人财产权的联邦制;当等级主义者坚持强化中央权威时,他们又重新与支持人类平等的平等主义者结成文化同盟;当平等主义日益发展为一股激进的力量时,他们又不得不转而与等级制再次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激进平等主义者钟爱的结果平等。
根据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结合美国转换文化同盟的过程可以看出,在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重组是有诱发机制可循的。以俄罗斯为例,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时期,其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色彩,即强调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按照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分类,这是典型的等级制文化。由于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欧亚两洲,除了受到亚洲等级制传统的影响,也深受欧洲个人主义文化的熏陶,即以个人及其自由、自然权利为中心。同时,平等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发挥很大作用,当然也存在大量宿命论者,如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布尔什维克一直致力于塑造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治文化,他们联合平等主义者(也有部分宿命论者),共同打压个人主义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转型,其政治文化也发生巨大变化。以领导人叶利钦为代表的西化派在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坚持走西化的道路,这显然是个人主义文化偏好。为了排除传统势力的干扰,西化派的个人主义者与平等主义力量结盟(也有部分宿命论者),联手对抗等级主义者。随着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参与加强,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的冲突、对抗甚至分裂,漫无节制的游行抗议活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混乱,这一状况直到普京上台才得以缓解。普京重新整合了国家政治资源,实行联邦大区制度,建立起垂直权力体系,全力弘扬俄罗斯传统文化,重新返回到“国家主义”思想,逐步树立中央权威,这显然是以普京为首的等级主义者联合其他文化模式的拥护者,共同对抗个人主义力量的结果。由此可见,文化同盟的转换没有终点,它与不同文化模式的力量和政治偏好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当然,维尔达夫斯基是基于美国多元文化的特殊国情,强调其混合型政治文化偏好,通过文化重组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变迁进行了纵向分析。这种思路对于多元文化国家(或共同体)的政治变迁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对于一元或二元文化的国家(或共同体)解释力有限,因此并不具有普适性。即便如此,文化模式理论仍然为我们理解政治文化的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三、 简短结语:政治文化变化的基本条件
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变化的问题上,因多数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连贯性的现象,人们往往认为“政治文化”最不能被用于解释政治变化。而政治文化的变化是维尔达夫斯基文化模式理论的研究主题,他批判传统的“静态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地一代接一代地往下流传,提出用“惊变”这一概念解释政治文化的剧变,将文化与变化统一起来。然而作为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体系,政治文化一般很少发生彻底改变,如果文化偏好上的剧变频繁发生,那么文化解释的价值恐怕会广遭质疑。对此,维尔达夫斯基在梳理美国政治文化变迁历史的基础上,还提及了政治文化变化的另一路径——文化重组,强调混合型文化偏好,再加上一些导火索(如出现某些突发事件),有利于促使不同文化模式之间频繁地结盟、解盟和再结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从而维系自身的生存。
简言之,从文化模式理论的视角来看,若要实现政治文化的平稳变迁,应该满足如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存在混合型政治文化偏好,即多元的文化模式,并用统一的维度将其划分为有限的几种文化类型;二是不同文化模式之间要共享某些价值观或具有互补性,以便结成文化同盟;三是要有一些令人感到意外和惊讶的突发事件作为契机,为新的文化同盟构建新的制度体系提供合理性,同时还应在新的制度框架下,进一步培育新的观念体系,强调制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而非孰先孰后。
[1] Mary Douglas (1982).Cultural Bias.Mary Douglas.IntheActiveVoi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2] Harry Eckstein (1988).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82(3).
[3] Richard Ellis & Aaron Wildavsky (1989).DilemmasofPresidentialLeadership:FromWashingtonThroughLincoln.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
[4] Ronald Inglehart (1988).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82(4).
[5] Michael Thompson,Richard Ellis & Aaron Wildavsky (1990).Cultural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
[6] Aaron Wildavsky (1991).TheRiseofRadicalEgalitarianism.Washington,D.C.: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叶娟丽
Surprise and Restructuring: Wildavsky’s Study on Political Culture
YangHuirong
(Shanxi University)
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the paths of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was deeply studied by Wildavsky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s of political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As we know, most scholars consider political culture as the safety net of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as the antithesis of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think that political culture is a se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political habits and political beliefs which is formed by the mechanism of “socialization”, and emphasize that it prefers stability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use “political culture” to explain lots of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real world. Thus we could inevitably say that it is a static concept without vigor.
10.14086/j.cnki.wujss.2017.01.014
D0
A
1672-7320(2017)01-0126-06
2016-03-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Z040);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5225)
*“惊变”一词在维尔达夫斯基的论著里原文为“surprise”,笔者之前发表的论文将其译为“惊奇”,后与相关学者探讨后,认为将其译为“惊变”更为合适。
Of course, this kind of “stability” is compared with great changes or shifts in the field of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people often use this concept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hifts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or communities), and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However, if we want to explain political changes in only one country (or community), it may become a very hard thing for thos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political culture which focused on “stability”.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Wildavsky’s Culture Theory found a new way to attempt to break through pre-scholars’ studies whi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atic state of culture, tried to illustrat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beliefs and social system, explored political culture’s dynamic mechanisms,and finally advanced th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s.
According to Wildavsky’s study, we could find two common paths that how political culture changed: “surprise” and culture restructuring. Firstly, when the reality deviated from people’s expectations all the time, then “surprise” would occur, and in the end people might turn to find another political culture pattern (or way of life) which fits with the present world more neatly. At that time, there would be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Secondly, in the countries (or communities) such as America, whose political culture is diverse or plural,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acclimatized to the new surroundings, different political culture patterns (or ways of life) would frequently ally with other ways of life, or break their alliance and even choose to ally again-that is to say culture restructuring which could be properly used to explain the political shifts in a country (or community)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Thus we can see that Wildavsky’s Culture Theory follows particular patterns and rules in interpreting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is theory’s strong points are obvious. The more important is that we could find corresponding cases in our country or others for these two paths of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as mentioned before, and that would give us much more valuable enlightenment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t combed through Wildavsky’s study on the paths that how political culture changed, and at the same time illuminated its extensible significance combined with some exampl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very few similar studies on this matter in our China presently. Key words:surprise; culture restructuring; Wildavsky; changes in political culture
■作者地址:杨绘荣,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Email:yhr198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