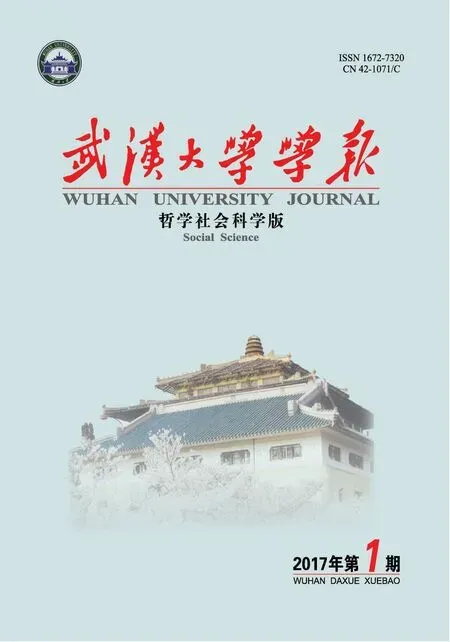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
2017-03-09何艳玲
何艳玲 李 妮

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
何艳玲 李 妮
改革以来,中央政府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锦标赛”设计,激发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上的激烈竞争。在围绕“增长”的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不断寻求地区GDP最大化。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以及中央政府政策的调整,地方政府的竞争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增长”竞争为地方政府获取经济收益的空间正日益缩小,为获取相对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开始为“社会创新”而竞争。为“社会创新”竞争,源于结构变迁、制度压力与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围绕创新的竞争或许能够促进地方政府转向基于公共利益的竞争,迈入为善治而竞争的轨道。
地方政府竞争; 社会创新; 增长
关于政府创新的实践与讨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烈。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等三家民间学术机构联合发起。已举办七届,申报项目超过1800余项,至2010年有1500多个省、市、县、乡镇等各级地方政府申报奖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至2013年,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项目超过1800余项,入围项目达到139项。仅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例,近年来,南京、深圳、海口等多地试点社会组织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制度改革;自2000年上海率先提出并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南京、无锡、深圳、浙江、天津、北京等地相继推出各种类型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项目;自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建设大会上推出《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上海、天津、A省相继开展枢纽型社会组织试点工作,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社会组织(彭善民,2012;冯志明,2011);各地“模式”辈出,各类“经验”涌现。
作为“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无论是作为“扶持之手”,以政府企业家的角色经营企业,发展地方经济;还是作为“掠夺之手”,攫取各类税费,增加地方财政,都在围绕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地方GDP而积极行动。何以当下的地方政府对社会创新如此充满热情?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极力争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又为何频繁推出似乎是削减自身利益的创新举措?同样是“经济人”思维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创建枢纽型组织,扶助社会组织,将财政支出投入到更多的是花钱而不是赚钱的社会项目、民生项目(某些地方政府的民生支出已占公共支出的六成至七成)?为什么地方政府要你追我赶地投身于似乎风险大过收益的社会创新呢?
学者们对政府创新动因的研究(俞可平,2012;陈国权、黄振威,2010;李景鹏,2007;吴建南等,2007)一直是政府创新领域的热点。就社会管理创新动力而言,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以及与其不匹配的治理结构造成了多发的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李路路,2012;何艳玲,2013),社会结构基础的变迁和重构提出了再适应性的新功能载体建构的要求(李志强、王庆华,2014),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去搭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才能重新形成,政府才能真正回归到法律的执行者、秩序的维护者角色(蔡禾,2012)。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面对此起彼伏的维权上访与群体性事件,“维稳”的巨大压力也促成了“危机—人事变动—创新”的创新“运动”模式(杨雪冬,2008)。
闫健(2014)认为上述研究均支持“压力驱动论”,不过尽管压力驱动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并不享有解释上的“排他性”,需要引入行为体层次的解释因素,关注“主要党政官员”的微观动机。作为地方治理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能力素质等决定了地方的政治运行和治理绩效(杨雪冬等,2013);许多地方改革在行动者的社会责任感(李景鹏,2007)或其某种道德情怀(朱光喜,2013)的作用下发起;Zhu & Xiao(2015:1-17)的研究也突出了“政治企业家”在社会政策创新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然而,“政治能人说”也难以成为社会创新如此普遍、覆盖面如此之广(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均出现诸多创新案例)的唯一理由。
区别于强调结构因素的结构化视角与强调特定个体的个体化视角,本文提供中间层次的机制研究视角,运用案例分析探讨因果机制及其过程。实际上,政府间竞争一直是政府行为最有力的解释框架之一。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驱动机制,政府竞争推动整个政治系统趋向均衡,并位于政治模型的中心(Breton,1996)。竞争机制不仅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也是本文要给出的回答。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官员治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依据“政绩-晋升”的逻辑,“社会创新”正在成为新的政绩竞争标的。
一、 为增长而竞争
20世纪90年代,何梦笔、冯兴元等人引入布雷顿提出的“竞争性政府”的分析范式,为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许多研究试图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有学者强调,“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张军,2005:16),而许多实证分析也提出,地方政府竞争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正是因为行政分权与财政包干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Qian & Weingast,1996)的竞争前提,加上政治激励(Li &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的竞争动力,地方政府纷纷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竞争行为(徐现祥、王贤彬,2010)。
就竞争动力而言,周黎安(2007)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是地方政府不遗余力促进经济增长行为的最为基本和长期的动力源泉。也即,这种中央政府设计的“政治锦标赛”,以“政绩—晋升”作为激励机制。在为“增长”的竞争中,地方政府的竞争目标设定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益。地方政府行为体现为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郁建兴、高翔,2012)。
在此目标下,竞争策略体现为:其一,经营。作为企业家的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财税的增长,通过各种行政手段介入企业运作。戴穆珍(Oi,1992)用“地方国家法团主义”描述90年代中期的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在当时的财政结构下,地方政府把促进工商业发展作为重点,像董事会一样管理辖区内的工商企业;魏昂德(Walder,1995)直接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而这一时期的“村镇政府即公司”(Peng,2001),显现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 的特征(张静,2000;杨善华、苏红,2002)。2002年分税制改革,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变为共享税种,地方政府从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获取收入的空间显著缩小,同时转移本地企业收入避免中央集中的做法也难以为继,地方政府不得不全力开拓财源——经营土地。陶然等(2009)考察了90年代中期后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策略,即在商、住用地上最大化出让金收入,在工业用地上提供低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甚至放松劳工、环境保护标准吸引制造业。“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滚动增长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不但塑造了东部地区繁荣的工业化和城市景象,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周飞舟,2010:80)随着1990年代末兴起的城市化浪潮与1994年开始推行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经营土地发展到经营城市,此时的地方政府行为被指为“城市企业主义”、“增长联盟”或“增长机器”。其二,争夺。地方政府间为体现为GDP增速的经济增长,就各类稀缺资源进行竞争,如资本、人才、中央政府的项目支持与政策倾斜等等,招商引资成为“增长”竞争中最常提及的竞争手段。地方政府采取超国民待遇政策、制度外财政行为等降低本地相对实际税负的税收竞争策略,吸引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本辖区流入(杨瑞龙,1998;郭庆旺、贾俊雪,2006;李涛等,2011)。一些研究发现此种竞争降低了地方政府环境管制的努力(章泉,2008),在区际与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趋向于放松对本地企业的进入控制,甚至与企业合谋突破管制性壁垒(汪伟、史晋川,2005)。而地方保护也从中兴起,通过“红头文件”、“办公纪要”、“打招呼”、“设卡”等行政管制行为,限制外地资源进入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造成市场分割(冯兴元,2001)。其三,建设。在相对的经济发展绩效排名激励下,各地区投身于见效快的行业或产业投资中,重复建设,同质竞争。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选择干预和资本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偏爱基础设施建设,大建“政绩工程”(Qian & Weingast,1996;靳涛,2006;张军等,2007),导致地方重经济建设支出,轻社会性支出,公共支出结构“偏向”(傅勇、张晏,2007;平新乔、白洁,2006)。
这轮指向增长的竞争,使得各地GDP迅速拉升,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日报晒中国经济成就:33年GDP年均增长9.8%,载网易新闻网,http://news.163.com/13/1121/09/9E6Q6ER900014JB6.html。。与此同时,“增长”竞争的负面效应也一直受到研究关注。
二、 社会创新的地方实践
30年过去,竞争格局显然发生了变化。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维护社会稳定”;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9年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也把社会管理创新列为三大重点工作之一;而2011年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意见更为密集,是年3月,“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7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简言之,中央为下级政府下达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任务。许多学者强调GDP已经不再是政府竞争的唯一目标,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社会管理体制更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领域(李培林,2005;俞可平,2007;何增科,2011)。“社会创新园”、“创新中心”等社会管理平台的创新也以极快速度得以扩散。
如果地方官员正是在追求政绩和政绩竞争的驱动下开展政府创新(陈家喜、汪永成,2013),那么围绕“社会创新”的地方政府竞争何以可能?其体现了怎样的竞争特点,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呢?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基于社会创新处于全国前沿的A省L县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L县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创造了经济先发地区的“L县模式”;90年代,L县率先推进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先导、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综合改革;2006年时,L县成为首个GDP突破千亿元的县;2007年,L县居民人均GDP已超过93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L县在经济“增长”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
但在近年来,L县发展路径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L县依靠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竞争优势不再。L县产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改革开放后L县逐步确立起家电、家具、机械、五金等为主的制造业,以花卉、养殖等为主的农业,以房地产、饮食、旅游等为主的服务业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经受经济危机后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再加上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等,一系列环境因素都造成制造业成本的节节攀升,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出口驱动型产业经济优势不再,GDP增速放缓,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自90年代以来,L县依次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现代化试点、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相较同级政府,L县官员思想更为开放,对改革的认可度相当高,阻力相对较小。L县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先后推进了大部门体制改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和省直管县改革,并被列为全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批县(市、区)级试点。实际上,L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该县2009年大部制机构改革框架下的延伸和补充。也就是说,作为改革试点的地方政府,已经付出了高昂的初始成本,当下的社会创新,正是前期改革框架下的延伸、补充或纠正。不创新少创新反而是对现有制度与政策资源的浪费。
“在后强人政治时代,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确立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式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郑永年、翁翠芳,2012:67)。L县开始调整竞争策略, 其多个政府工作计划、总结以及地方发展战略的官方文本,开始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以体制创新、社会改革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为选择:“寻求新的体制竞争力”,“增创科学发展体制新优势”,“打造L县发展核心竞争力”。2011年,L县被确定为A省社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不断尝试社会创新项目。
(一) 竞争标的:从GDP到“不仅仅是GDP”
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为了完成某些重要任务,就会将它们确定为“政治任务”,要求下级政府以及职能部门全力完成,并相应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激励和惩罚(杨雪冬,2012)。前述,近年来的一个新兴任务即为社会创新,地方政府在重重压力下要实现政治责任的承担必须进行各种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当“社会创新”成为新一轮的政治中心任务,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回应无疑是全力配置与调整资源,最快最好地完成。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L县被赋予了“创新”的政治使命,全方位推进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2011年,A省专门成立社工委这一统筹、协调、推进本辖区社会建设的机构,也是这一年,L县被确定为A省社会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区,并且在大部制的政府架构下,整合相关社改职能部门,成立区社工委;2011年,A省出台加强社会建设的“1+7”文件,L县也随之出台社会工作发展“1+6”文件、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办法等政策性文件30多份,制定了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和群众生活类等4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细则,培育社会组织,成立法定机构,开展“社区营造”,推行参与式预算试点;2013年L县又按照省社工委文件指示组建民情志愿服务队等等*摘自L县2013年社会建设总结和2014年工作计划。。
与此同时,政府评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2013年,A省全面清理各种考核检查,撤并率达88%,但新增了社会建设综合考核项目。考核指标体系分为社会事业、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参与4个维度,包括37项二级指标。从2014开始,每年对各地社会建设的基础情况、进步情况和综合情况进行考核,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分别排名,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各级领导班子和官员政绩、年度考核和任用的重要依据*A省明年起正式启动社会建设综合考核,载广东新闻网,http://www.gd.chinanews.com/2013/2013-11-26/2/286284.shtml,2013-11-26。。换言之,从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到提倡社会创新,政府之间的较量,已经不仅是GDP的竞争。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实施目标责任制,当社会创新成为地方政府要实现的行政目标本身,就会通过绩效考核体系由上自下确定并传递创新任务。各乡镇均通过不同的表述或形式把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列为重点工作目标,以回应县级的考核与政治施压。或者可以认为各镇街为吸引以改革为政绩取向的县级政府关注,开始了基于“创新”的竞争。
(二) 竞争策略:求差异、多改造、重扩散、争试点
求新求异。地方政府在创新的学习模仿中,非常强调同中求异。就国内各地相继推广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而言,一是在购买领域求异,从居家养老、市政设施养护、水资源监测、社区建设、社会矫正、残障康复等越铺越广;二是在购买形式上求异,如推出相关职能部门的先监督评议再付费、合同外包、项目委托等多种形式。L县的“两社三工”管理创新即体现了在创新竞争中的差异化策略。与L县相邻的Z市在青少年服务、特困服务中运用“社工+义工”的联动模式,H市则开展了“双工一社”联动运作模式(“社工+义工+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项目;L县在这些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设计了“两社三工”管理方式。两社,指社区、社团;三工,指社工、义工和优秀异地务工人员。也就是说,L县并非完全采纳以上两市的创新管理方式,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特点做增减与调整。2012年11月,此项目被确定为“A省社会创新试点项目”。在“创新”竞争中,求新求异是提升同级政府间竞争力的必需,如果某项“创新”举措不是由该地方政府最早提出,那么必然要在类似的创新举措上有所突破和改变。
学习改造。L县因其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及乡土民情的贴近,其最具特色的三项创新举措“建立党代表工作室、设立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与试点法定机构”,就是在学习香港与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模仿与改造而来。在有限理性下,模仿同辈(peers)的成功行为是组织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而学习域外成功经验,可以更大可能地提高创新行为的成功率。2012年8月20日,L县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经审议通过的《法定机构管理规定》和4个法定机构的具体管理规定,首批法定机构——社会创新中心、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产业服务创新中心正式诞生。作为法定机构之一的“社会创新中心”,在“社工委”的指导下进行各种“实验”。
内部扩散。求差异的同时,L县在辖区内重视创新经验的扩散,综合运用多种类型的创新扩散策略:2010年10月,L县党代表工作室成立;2011年年底,全县各层级建立党代表工作室231个,这是典型的从上至下的扩散。与之相反的是自下而上的扩散。2010年1月,L县G街率先成立全县首个公共决策和事务咨询委员会,这也是全国镇(街)首个决咨委。2010年9月,L县率先成立“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至2012年11月,全县共有各类决策咨询机构37家。迅速扩散是组织迅速保持与同行相等水准的行为,L县的社会创新迅速获得较大社会反响。
争取试点。“试点”是上级政府给予下级政府有限突破和创新的重要手段,一旦成为上级授权的实验场,就会获得相应的资源与支持。一次又一次试点或示范区的获得,将为该地方政府贴上“创新”的标签,扩大地方知名度,发挥品牌效应。据不完全统计,L县2010年以来获批和申报国家级、省级试验区、示范区达25项*内部资料统计。。社会创新集中在近两年:2012年,L县“两社三工”社区管理服务模式被正式确定为“省社会创新试点”12个项目之一,是L县所属F市唯一入选的项目;L县同时被授予“A省社会创新实验基地”称号,其后2013年被赋予创建全省社会建设与治理创新示范区的重任。一位官员在访谈中所言:“L县干部队伍的积极性是很强的,工作氛围也好,一直都是改革试点,从经济改革开始,所以会把这个社会创新的试点给到我们,支持我们。”*资料来源于访谈记录(20140113)。中国试点是“由点到面”的“分级制政策试验”(韩博天,2010),L县的诸多社会创新项目,就是以“相马赛马”的方式进行,即在下级政府挑选试点进行社会创新的实验,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如在S村开展“社区营造”实验,选择三个社区作为“社区创新观察点”等。也就是说,争取试点既可以带来创新所需要的上级信任,也是L县开展“创新”运用的策略本身。
(三) 竞争结果:从经济增长到社会稳定
市场化改革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在相应的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信任、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不稳定这三大困境(何艳玲,2013)。只有当国家建设把目光投向社会,致力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才有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建设为重新塑造国家与民众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探索新的治理机制提供了契机(周雪光,2013),也为地方政府带来了社会“稳定”的实际收益,缓解了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与此同时,民生工程与治理的改善赢得普通民众的认可,而地方政府以此收获的声望与美誉恰恰积聚为“政绩”,并成就其获取晋升的政治资本之一。
L县也出现了各种社会不“稳定”现象:地块纠纷、租赁纠纷、村务纠纷,维稳任务艰巨。虽然经济发达,社会结构仍处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状态,公共服务与居民收入的差距显著。L县要改变“经济腿长、社会腿短”的现状,必须以社会治理方式的突破换取社会矛盾的解决。党代表工作室制度实行以来,全县247个党代表工作室,从2013年1月至8月,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700多条,办结率89%;区镇(街)两级38个各类决策咨询机构,吸纳了1000多名各界精英义务担任咨询委员;截至2013年10月,L县共登记成立社会组织共989个,其中社工机构达到16家。2013年上半年,全县110警情(刑事及治安)同比下降38.3%,“三两”警情下降36.7%,八类暴力案件下降23.9%,民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有所提升。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各种再分配难题和市场负外部效应,使“稳定”成为重要的政治要求,并进一步转换成科层组织的组织任务(何艳玲、汪广龙,2012)。在此背景下,社会结构变迁使社会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三、 社会创新作为新的地方竞争机制
前述,地方政府的竞争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争资源,要政策,促发展,体现为“发展型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创新型”政府则体现了不同的竞争内容、竞争方式与竞争策略。为“社会创新”而竞争,让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创新”的竞赛标的变换,而是地方政府在变化的制度环境和任务情境中主动适应环境、调整组织目标的一种自主选择。
(一) “为创新而竞争”的动力机制
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们总是通过思考、计划和分析,寻找与动态环境相匹配的竞争优势获取机制。“为创新而竞争”的形成,来自结构、制度与机制多层次的推动。其一,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开始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孙立平等,1994)。然而,面对迅猛变迁的经济结构,社会系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系统,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成为启动社会创新的最大动因。其二,压力型体制体现为各级政府普遍实施的目标责任制,当改革创新成为地方政府要实现的目标本身,它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改革创新一般由上级党政系统确定目标、制定方案,对下级政府下达改革任务。社会“创新”是顺应中央与上级要求的举动,体现下对上的政治忠诚。其三,对官员考核指标的变化,标示着“社会创新”已然成为官员晋升竞争的明确标的。
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所以制度创新的一般动因在于可以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成本(唐丽萍,2011)。地方领导在“向上问责制”的体系下,容易在“政绩”之间做出选择,以达成较易达臻的“政绩”,并尽量夸大其表现(蔡文轩,2010),即地方精英在干部任期与有限资源的限制下将结合执政地区的初始条件,倾向选择最能显示政治忠诚且较易达到的政绩目标,同时尽可能政绩最大化,展开政绩竞争。而在新常态下,廉价劳动力、大量土地供应、容忍环境破坏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退。“增长”竞争为地方政府获取经济收益的空间正日益缩小,付出的成本却日益增高;而改革“创新”的路径依赖正处于报酬递增与成本下降阶段,传统“增长”竞争优势不再,L县处在“政绩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加上官员任期制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社会创新”的竞争中。
30多年的改革,成功激发了经济活力,也使“改革”成为政府应对一切治理问题的首选方略,“改革”逐渐演变为一种变革、创新、进步的符号。在不断推进行政体系理性化的过程当中,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政府积极作为的象征,地方政府进入“改革”的路径依赖。社会创新,本质上就是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模仿学习的社会创新,具有低成本与高收益的特征,不但有助于收获社会稳定的政绩,也同时收获了市民的认同。而最近的研究也显示,成功的政策创新也可以作为官员升迁的政治资本(Heilmann,et al,2013)。即社会创新的结果是一种高附加值的绩效产出。进入官僚效用函数的变量包括工资、津贴、公众声誉、权力、资金、官僚机构的产出、变革的难易程度等(尼斯坎南,2004),在官员“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下,围绕“社会创新”的竞争正是有限理性下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社会创新”从最初的少数事件逐渐成为作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
(二) “为创新而竞争”的运作机制
GDP导向的政绩观刺激了地方政府经营企业、经营土地等政府企业家行为,当创新政绩被地方政府视作新的竞争标的,地方政府开始指向创新政绩的经营。创新政绩没有增长政绩可量化的指标,身为政绩竞争者的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差异性、影响力等软指标突显成绩。
实际上,组织追求“差异化”战略并不新鲜,企业总是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将“第一”、“首个”、“首次”、“最先”等设为关键绩效指标,追求创新的项目的新颖性,这种新颖性要么通过概念性生产获得,要么通过最“早”采纳域外制度安排实现,总之,地方政府更希望启动专属的创新项目而非完全模仿其他同层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Zhu,2014:117-139)。就创新扩散而言,形式上的模仿远比实质性改革来得容易,由于政治体制不同,许多域外创新制度的移植仅取其形,在融进当地的制度框架的过程中,实现本土化改造。换言之,在社会领域进行制度移植时,地方政府通常策略性回避体制障碍,以形式上的模仿、名义上的创新引进境外或港澳先进做法;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同级政府的成功经验,但并不积极移植,而是在内容或形式上有所调整,冠以新的项目名称运用于自己辖区。这样的运作方式,体现了决策者降低决策风险的考虑,既维持现有权力格局,不涉及根本的制度变革,将创新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进取与差异。实际上,对照完整形态的法定机构,上文所言的法定机构制度与理想形态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大多数要作结构性调整。
与“增长”竞争的变通行为不同的是,地方政府的社会创新通常是在自上而下的宣传与意见指令的发动下开展,而其实现的最主要方式即争取试点。地方改革试点是中央推动创新的代表性手段(杨雪冬,2008),可以说社会创新的竞争首先就是争取创新试点的竞争。试点可以获得上级和中央的重视,获取资源与政策,也放大了地方改革的效应。这意味着更有可能加深上级政府对该地的创新印象,印象管理不仅用于试点的争取中,还用于创新在地方政府辖区内部的迅速扩散。区别于域外经验的改造实施,地方政府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辖区内推行成功项目,扩大该项目的影响力,博得上级的注意力。此外,试点亦或实验,更是经过多年实践的以“稳定”为前提的政策出台策略。“创新”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风险, “试点”、“实验区”、“观察点”的设立,都是创新项目的试水,地方主政者更强调建立在“稳定”之上的“创新”。
就创新的积极功能而言,创新促进了组织学习。当目标指向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显然需要更多的组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亚洲的香港政府、新加坡政府,都成为地方政府学习的标杆。模仿与改造域外经验、制度和理念成为创新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实际上,通过组织学习进行的社会创新,是一种相对低成本与潜在高收益的理性选择。同时,环境动态性的变化加强了组织学习对于组织竞争的作用,组织学习带来的组织创新提升了组织的竞争优势(Hurley & Hult,1998)。可见,指向创新的竞争促进了地方政府“学习型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提高了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这种适应能力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尤为重要。毕竟,创新手段并非都是首创,而是考察和学习其他地区经验和做法的结果(吴建南等,2007),组织学习会提升组织绩效已为不少研究所证实。
政绩竞争中的“创新”尽管存在追求形式创新、概念创新的负面作用,但本文所述的创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财政结构发生了转变,社会发展投入在整个预算中的比重加大,而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也向着与民间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转变,并且在社会管理决策科学化问题上引入了更多决策听证、公示与责任追究的制度,最为关键的是,政府职能在社会管理领域开始逐步退出并重新定位(周红云,2013)。因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也被认为是提高民主化水平、政府绩效与政治合法性和推动社会善治与政治进步的重要动力源和突破口(陈家喜、汪永成,2013)。
四、 结语:促进为创新而竞争的制度化
改革开放让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众对生活改善的迫切需求与GDP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促成了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30年的地方经济竞争忽视了社会领域的需要,带来了转型阵痛。中央密集出台引领社会创新的政策,地方直接遭遇社会治理的挑战,传统的“政府企业家”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纷纷谋求社会创新。增长竞争无法解释地方政府诸多社会工程的行为,因此,我们提出“为创新而竞争”的解释框架以解读地方政府行为的这些新趋向。
“为创新而竞争”,可以解释地方政府从追逐经济增长到注重社会创新的行为局部变化。虽然创新行为的研究很难得到跨越组织类型的普适性结论,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丰富了政府间竞争理论微观层面的探讨,提供了不同于“为增长而竞争”的解释框架。这一努力还将在理论上丰富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内容与范畴。蒂伯特模型指出,居民“用脚投票”给辖区政府带来硬约束,促使各辖区政府展开竞争,从而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公共服务(Tiebout,1956)。与民选国家地方政府竞争有所不同的是,集权体制下的官员并非“用脚投票”产生,更多地凭借上级的考核与任命,这样的竞争指向的更可能是前文所述的“晋升”。围绕“社会创新”晋升竞争其产生和渐成趋势,实际上将促进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向“用脚投票”的基于公共利益竞争的转向,同时说明中央政府与执政者在提拔官员思路上的转变与激励策略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因此,如何使得这种“创新”竞争走向可持续,走向制度化,以防止“创新”举措“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央政府应该为这样的“社会创新”竞争创造良好的激励环境,给予相应的制度安排,明确竞争考核指标,提供相应的晋升渠道,即促使“为创新而竞争”的制度化。当然,创新行为与晋升的关联还需要经验数据的验证,但我们的企图在于分析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应对变化环境时的策略调整与预期的发展方向,展现地方政府行为的多样性。
[1] 蔡 禾(2012).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学研究,4.
[2] 蔡文轩(2010).解释中国大陆省级的政治改革:“政绩/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科学论丛,44.
[3] 陈国权、黄振威(2010).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热点主题与理论前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
[4] 陈家喜、汪永成(2013).政绩驱动: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分析.政治学研究,4.
[5] 冯兴元(2001).论辖区政府间的制度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6.
[6] 冯志明(2011).共青团“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浅探.北京城市学院学报,5.
[7] 傅 勇、张 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3.
[8] 郭庆旺、贾俊雪(2006).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5.
[9] 韩博天(2010).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3.
[10] 何艳玲(2013).“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开放时代,3.
[11] 何艳玲、汪广龙(2012).不可退出的谈判:对中国科层组织“有效治理”现象的一种解释.管理世界,12.
[12] 何增科(2011).以治理和善治为方向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学会,12.
[13] 汪 伟、史晋川(2005).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管理世界,4.
[14] 靳 涛(2006).资本倚重、投资竞争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9.
[15] 李景鹏(2007).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3.
[16] 李路路(2012).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2.
[17] 李培林(2005).重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人民论坛,10.
[18] 李涛等(2011).税收、税收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世界经济,4.
[19] 李志强、王庆华(2014).“结构—功能”互适性理论:转型农村创新社会管理研究新解释框架——基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维度.南京农业大学学报,5.
[20] 威廉姆·A.尼斯坎南(2004).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王浦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1] 彭善民(2012).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自主管理创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1.
[22] 平新乔、白 洁(2006).中国财政分权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财贸经济,2.
[23] 孙立平等(1994).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
[24] 唐丽萍(2011).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制度创新及异化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
[25] 陶 然等(2009).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7.
[26] 吴建南等(2007).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多案例文本分析.管理世界,8.
[27] 徐现祥、王贤彬(2010).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世界经济,2.
[28] 闫 健(2014).“父爱式政府创新”现象、特征与本质——以岚皋县“新农合镇办卫生院住院起付线外全报销制度”为例.公共管理学报,3.
[29] 杨瑞龙(1998).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
[30] 杨善华、苏 红(2002).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社会学研究,1.
[31] 杨雪冬(2008).简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个问题.公共管理学报,1.
[32] 杨雪冬(2012).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11.
[33] 杨雪冬等(2013).地方政治的能动者:一个比较地方治理的分析路径.东南学术,4.
[34] 郁建兴、高 翔(2012).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5.
[35] 俞可平(2007).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学习时报,2007-04-23.
[36] 俞可平(2012) .中美两国“政府创新”之比较——基于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分析.学术月刊,3.
[37] 张 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38] 张 军(2005).为增长而竞争:中国之谜的一个解读.东岳论丛,4.
[39] 张 军等(2007).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3.
[40] 章 泉(2008).财政分权、公众偏好和环境污染——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41] 郑永年、翁翠芬(2012).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地方? .文化纵横,2.
[42] 周飞舟(2010).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3.
[43] 周红云(2013).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现状、创新与展望.载周红云主编.社会管理创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4]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7.
[45] 周黎安等(2005).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经济学报,1.
[46] 周雪光(2013).社会建设之我见:趋势、挑战与契机.社会,3.
[47] 朱光喜(2013).“嵌入型”富裕地区政策创新:空间限制与行动策略——以神木“免费医疗”政策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
[48] Albert Breton(1996).CompetitiveGovernments:anEconomicTheoryofPoliticsandPublicFina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9] Sebastian Heilmann,et al(2013).National Planning and Local Technology Zones:Experi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s Torch Programm.ChinaQuarterly,216(4).
[50] R.Hurley & G.Hult(1998).Innovation,Market Orientation,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An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JournalofMarketing,62 (3).
[51] Hongbin Li & Li-An Zhou (2005).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
[52] Jean Oi(1992).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 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Politics,45.[53] Yusheng Peng(2001).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Ownership,Governance,and Competition.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6(5).
[54] Yingyi Qian & Barry R.Weingast (1996).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ofPolicyReform,1(2).
[55] C.Tiebout (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4(5).
[56] Andrew G.Walder (1995).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2).
[57] Xufeng Zhu (2014).Mandate versus Championship:Verti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in Authoritarian China.PublicManagementReview,16(1).
[58] Yapeng Zhu & Diwen Xiao(2015).Policy Entrepreneur and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 in China.TheJournalofChineseSociology,2(1).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lies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tournament” to motivate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compete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t is GDP-oriented view of achievements and “achievement-promotion” incentive model that can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local governments are interested i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and why they manipulate the land and urbanization to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it is hard to explain wh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eager to become reform pilot and why they frequently take initiative to reforms and consequently cut their own interests. It can’t explain why would local governments spend more money rather than put money into livelihood projects (accounted for 60%-70% of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And why local governments actively carry out risky social innovation.
If the “achievement-promotion” logic is unchanged, the only explanation is that “achievements” changed. Preliminary analysis shows,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With the further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through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those brought by economic reform, “reform” evolved from means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to policies “target” itself; with gover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ce narrowing, cost increases. The advantage of GDP-oriented competition mechanism reduced greatly.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find a new point of “achievements” growth, “social innovation”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as key tasks,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keen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is research selected an official social innovation sector of a county in L district which is one of the reform pilo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obtain experience data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lso collect official policy texts and relative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What has changed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ing objectives and restrictive condition? How “innovation” competitive mechanism happened? What innovative strategies taken and what the type of innovation? What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behind innovation behavior? What is the impact o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public policy is likely to bring?
It is reasonably expected in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llected facts and data: to form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social innovation”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hrough the “championship” desig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imulated competition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e competition around the “growth”, the local government serves as a “political entrepreneur”, and constantly seeks to maximize the regional GDP. With the adjustment of changes in national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c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greatly changed. “Growth” competi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get economic benefits of space is increasingly narrow.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el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local government began to compete for “social innovation”. The cho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s due to the structure change, and the system pressure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changes. Around the “Innovation” competition may be able to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has turned to the competition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enter a good governance and competitive track.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mechanism; government behavior; soci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 logic
■责任编辑:叶娟丽
Competition for Innovation: A New Competitive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s
HeYanling&LiNi(Sun Yat-sen University)Abstract: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soci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new competitive mechanism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10.14086/j.cnki.wujss.2017.01.010
D035
A
1672-7320(2017)01-0087-10
2016-06-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041);广州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作者地址:何艳玲,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Email:2006hyl@163.com。 李 妮,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