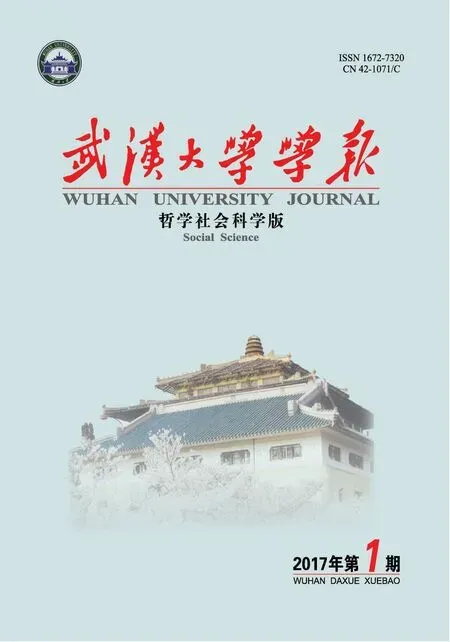罗森茨威格的“新思”与古今中西之争
2017-03-09高山奎
高山奎

罗森茨威格的“新思”与古今中西之争
高山奎
罗森茨威格在《救赎之星》中提出了“新思”观念。这一思想的提出受到罗森茨威格一战参战经验的激发、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个体信仰经验的支撑。在哲学前提和对“启示”理解两方面,新思与旧思之间存在根本性不同:旧思的起点是存在和有,新思则从先于理性的存在(知识之无)出发;旧思崇尚“一”与不变,试图用观念的“全”来统摄一切,新思则从时间性的生存体验出发,肯定了多样性和生成变化的真实;旧思把上帝视为远离人的生存经验的观念他者,新思则把上帝视为在人的灵魂里与人相遇、不断启示更新并引人走向救赎的永恒的你。尽管罗氏的新思带有浓厚的黑格尔式旧思烙印,它所希冀重返的犹太正统亦是受到启蒙思潮修正了的“犹太正统”,但是,廓清罗氏复返犹太正统的哲学努力,对我们当下复返中国传统、重思古今中西之争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罗森茨威格; 救赎之星; 新思维; 旧思维; 海德格尔
弗兰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堪称20世纪宗教哲学领域最具原创性的犹太哲人之一*Amos Funkelstein认为德国犹太哲学“始于门德尔松的《耶路撒冷》,终于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也就是说,从门德尔松到罗森茨威格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和连续性(Funkelstein,1993:257)。尽管二者在思想根基(回返现代启蒙意义上的正统神学)和问题意识(关注“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上存在重要的家族相似,但在是否接受同化以及回返理性神学(旧思)还是体验神学(新思)的问题上,二者具有显见的差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罗森茨威格修正甚至翻转了门德尔松的哲学努力,因而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犹太哲人。。他的思想巨著《救赎之星》(完成于1919年,首版于1921年)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巴特的《〈罗马书〉释义》(1919)、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等著作一道被认为“共同反映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和人心”(张汝伦,2014:引言1-2)。在启蒙自反、理性主义毁灭的大幕乍起之时,他充分汲取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给养,倡“新思”弃“旧思”,“将犹太神学从沉睡中唤醒”(施特劳斯,2008:270),为现代犹太神学“带来了无疑最重要的转变”(格林,2010:324),被誉为“德国犹太人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施特劳斯,2013:17)。作为以复返犹太传统信仰为志业的犹太人,他毅然放弃了可以给自己带来良好声名和处境的大学教职,全身心投入到犹太思想研究、希伯来圣经(以对抗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和哈列维作品的德译以及犹太教学术研究院(Akademie für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Myers,1992:107-144)的创办之中,有力地激励和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的德裔犹太智识精英(如布伯、施特劳斯和肖勒姆),成为影响北美犹太人宗教思想的精神导师(Himmelfarb,1966:72;郑文龙,2011:130-131)。罗森茨威格对犹太传统的复返和捍卫不仅对复兴犹太教信仰意义非常,而且对我们重思启蒙观念,尤其是省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关联(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在现代性危机和神学复兴的背景下理解和评价罗森茨威格的“新思维”,算是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 “新思”之基:沐火重生的体验之思
在《救赎之星》中,罗森茨威格将自己的思想定性为“新思维”(The New Thinking,以下简称新思),藉此与以往的理性主义“旧思维”(The Old Thinking,以下简称旧思)划清界限。为了更好地理解新思的理论要旨、恰切地评估它的原创意义,我们有必要对罗森茨威格为何以及如何提出新思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背景加以廓清。具体而言,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思的提出与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的参战经历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罗森茨威格号称“战壕里的犹太思想家”,这不仅由于《救赎之星》的逾一半手稿是以明信片或书信形式在炮火纷飞的战壕里草就(Glatzer,1999:87-88),更重要的是,战争中的创伤经历和生死体验使罗森茨威格获得了灵感,进而从旧思的桎梏中破茧而出。众所周知,一战的爆发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祛魅意义:民族国家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和相互屠戮,彻底颠覆了启蒙哲人所期许的美好图景,让理性哲学神圣化国家的所有努力变得苍白无力。战争中最突出的事件是死亡,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血肉横飞、生死两隔,那些为家国而战、为正义献身的神圣呼召瞬间褪去光环,变成了裹着蜜饯外壳的“动听谎言”。虽然早年的罗森茨威格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吸引,甚至将《黑格尔与国家》(HegelundderStaat,完成于1914年,首版于1920年)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但血腥惨烈的战争实践让他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了幻灭*郑文龙认为罗森茨威格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的1910年就开始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失望(郑文龙,2011:156-157),笔者对此并不完全认同。纵然我们承认导致罗森茨威格远离黑格尔的因素复杂且并非一蹴而就,如罗森斯托克向前者提出的非此即彼的选项: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信守犹太教,已表明黑格尔的理论无法为罗森茨威格提供一个绝对的理论支点(1913);罗森茨威格的博士论文中显露出受到狄尔泰生命哲学影响的痕迹;晚期谢林的启示哲学对罗森茨威格冲破黑格尔的体系提供了重要参照(1914),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消减罗森茨威格对黑格尔的热情:前者依旧以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在博士毕业后到莱比锡大学继续进行黑格尔思想的研究。概言之,如果没有1913年仲秋的犹太转向及其之后的柯亨影响,尤其是1914年爆发的一战及其参战经历,罗森茨威格艰苦卓绝的理论摸索将难以冲破黑格尔浓重阴霾的体系雾障,瞥见令其眼界洞开的新思曙光。因此,郑文龙先生仅从理论(动机及其渊源)视角评价,忽略战争(实践)对罗森茨威格突破旧思(黑格尔)的重要意义,显然失之偏颇。,并最终得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国家在根本上绝非客观价值的正义化身,而是赤裸裸的 “战争与革命”*在罗森茨威格看来,民族国家有着个体般的永恒追求,但与个体诉诸祷告等形式来祈求永恒不同,国家通过将民族精神上升为普遍精神,通过保证法律“高悬在更迭之上”来保证自身的稳固和永恒。然而,这受到生命变动不居的有力挑战:繁忙的生命“向前疾驰,将僵死的、固定的法典抛在身后”。 为了保持自身,“在每一个瞬间,国家都以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保存与更新、旧法律与新法律之间的矛盾”,因此,绝非永恒而正义的客观精神,而是“战争与革命成了国家唯一熟悉的内容”(罗森茨威格,2013:314-315)。。对罗森茨威格而言,那种将个体的人视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永恒价值的承载者”的教导,不过是理性主义哲学“关于尘世的全的观念的蓝色迷雾”,是毫无根基的虚假承诺(罗森茨威格,2013:4)。死亡始终是个体的事件,是最真实的深渊体验。个体根本无法通过融入永恒的全之观念来消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人抛不掉尘世的恐惧,他继续存在于死的恐惧之中。”(罗森茨威格,2013:4)一言蔽之,正是血腥残酷的战争经历和生死体验,让罗森茨威格最终放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封闭体系和逻辑论证,返身投入爱与死的宗教—价值体验,并以此为根基,开启了他独特的哲学新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救赎之星》这部哲学巨著*施特劳斯通过古今对照来为《救赎之星》的哲学属性定调。他强调指出,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首先不是一部哲学著作,而是一部犹太教著作”,与之相对,“罗森茨威歌德《救赎之星》则首先不是一部犹太教著作,而是‘一套哲学体系’”(施特劳斯,2013:24)。的独特开篇才变得可以理解:它一反正统理性哲学的致思路向:既不探讨世界由所从来的始基或本原(本有论),也不探讨认识得以可能的前提和机理(认识论),而是把个体性的经验之死,把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这一个体此在的本质性事件作为其哲学致思的起点。
其次,新思的提出不仅受到战争经历的触发,也有着哲学上的学理渊源。我们知道,罗森茨威格出生在一个富有且高度同化的犹太家庭,从童年时代起,他便接触到很多非犹太的文学艺术思潮,尤其受到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哲学(罗森茨威格称之为“新哲学”)和歌德著作的影响。尽管学徒期的罗森茨威格仍把当时主流的学院派哲学(如黑格尔哲学和新康德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战争中的生死体验愈发使他感到非理性主义哲学所强调的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性和真理性。因此,在《救赎之星》中,罗森茨威格强调,“叔本华是第一位不探究世界的本质,而探究其价值的伟大思想家”,他“从哲学的棺木中倒出了它的千年秘密,即,死亡应是它的自己指导者”。这一思想的巨大影响在于,“人感觉到——实际上这才是实情——站在体系的开始的是人。这个人不再被哲学史的背景所哲学化或作为其受托人了,也不是作为其问题的任何可能的当下状况的承担者了,而是‘把反映生命的任务担在自己身上’,因为‘生命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罗森茨威格,2013:5、7、8)。然而,叔本华的贡献只是打开了从旧思向新思、从“全”之观念向个体价值迈进的一个缺口。真正为罗森茨威格新思奠定阿基米德支点的是克尔凯郭尔,后者找到一个“在认识的全之外‘立足的地方’”,并从“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出发与把启示纳入全的黑格尔式的综合展开了争论。这个支点是出于克尔凯郭尔自身的,有关他自己的罪和救赎的特殊的意识或恰巧是他的名和姓的任何东西”。简言之,这个新思的支点就是个体的自我,“这个‘自己的’正是最重要的”(罗森茨威格,2013:7)。不过,叔本华的转向、克尔凯郭尔的阿基米德支点,只有到了尼采那里才真正获得了新思的内容:诗人、圣徒与哲学家实现了个体化的统一,即“灵魂与心灵的统一,人与思想家的统一”。至此,哲学“走出了只承认其自身的世界,走出了哲学的全”,对于罗森茨威格而言,这种新哲学的影响“至今仍未结束”,而他自己的新思就是这种新哲学在哲学、尤其是启示信仰方面的某种拓进和思考(罗森茨威格,2013:9-10、7、19)。可见,除了个体历史经验上的触发之外,非理性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和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存在主义为罗森茨威格新思的创立提供了学理上的准备和养料来源。
最后,罗森茨威格的新思与他犹太教信仰的实践体验紧密相关。罗氏的新思首先是一种哲学之思:它脱胎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又受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新思又是一种直接关涉犹太教启示信仰的学说,是源自犹太人宗教体验、关切犹太人安身立命,同时受到犹太思想资源深刻影响的著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救赎之星》的灵感来自罗森茨威格异常关注的启示概念。1917年11月,在致友人鲁道夫·艾伦伯格的信中,罗森茨威格谈到了自己对于启示概念的一些独特感悟。9个月后,他决定将这一想法落笔成书,这就是后来的《救赎之星》(Glatzer,1953:63;傅有德等,1999:88)。其次,尽管在心性偏好上与赫尔曼·柯亨差别显著*柯亨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领袖,其思想倾向于调和启蒙理性主义与犹太宗教,而罗森茨威格则注重个人信仰的宗教体验,重视个体性的独特价值和爱与死的灵性体验。因此,二者可以分别看作是20世纪犹太神学复兴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但柯亨对犹太教信仰的忠诚以及他作为敏锐深刻的哲学家而非“钢丝上跳舞”的哲学教授的学问气象深深地影响了罗森茨威格。毫不夸张地讲,正是柯亨对康德先验幻象(认识之无)“可以作为源头的、有产生能力的东西”的发微和创造性解读,为罗森茨威格创作新思打开了理论通道和进阶支点,从而开启了从知识之无(Noughts)到知识之是(Aught)的哲思之旅(傅有德等,2008:482;罗森茨威格,2013:19、22)。最后,罗森茨威格新思的提出还与他参加犹太宗教活动的经历体验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作为一个高度同化的犹太人,罗森茨威格青年时代曾一度决定皈依基督教,然而,1913年10月11日的一次参加犹太会堂赎罪日活动的神秘宗教体验,让罗森茨威格戏剧般地“迷途知返”。在给母亲的信中,罗森茨威格强调,犹太教并非基督教会所批判的那样是死亡的宗教,恰恰相反,犹太教信仰绝非外在于生命的象征符号,而是走向救赎无其右者的永恒生活方式(Glatzer,1953:26-27)。自那时起,罗森茨威格便把犹太启示信仰的复兴作为余生的志业,从而有了这部犹太思想史上熠熠闪光的新思巨著——《救赎之星》。
综上所述,罗森茨威格的新思是以个体性的生存体验为基底,以非理性主义哲学为给养,以犹太教(但并不排斥基督教)的启示信仰为鹄的的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宗教哲学之思。如果说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发起的思想变革主要彰显在哲学领域,那么,卡尔·巴特、罗森茨威格则分别代表了基督教和犹太教领域的神学复兴或回返。这种回返,尤其是罗森茨威格的回返,不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原教旨主义回归,而是在充分浸染、吸纳理性主义旧思的基础上的反思和扬弃。因此,在清理了新思提出的个体经历、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之后,我们接下来在与旧思的对堪中廓清罗森茨威格新思的思想要义。具体来说,这主要包括哲学和启示信仰两个层面,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二、 “碗的隐喻”与哲学原点上的“新—旧”分歧
在《病态的理智与健全的理智》一书中,罗森茨威格通过“碗喻”来申明自己的新思与传统旧思在哲学方面的本质不同:世界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世界观(在罗森茨威格那里,观即看,世界观就是世界被“看到”)则如同一个碗,“这只碗可以被浸到河流之中,并被随意地从水中舀起”。观察者观世时,他把这只碗浸入世界之流当中,然后“以专注而惊异之情盯着这只碗”,凝思碗中孤立静止的水,却全然忘却了碗外川流不息的河流(世界本身)(罗森茨威格,2006:319)。这个譬喻生动地刻画了新、旧思的两个根本分歧:首先,如果世界真的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那么,它本质上就是运动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动。变化寓于时间之中,意味着事物无法在时间中保持自身,故而无法实现永恒。在巴门尼德看来,运动不是存在(is)的属性,事物生灭流转,无法自持,何以自存(being)。因此,真正的存在应当静止不动,但我们无法在感官经验中把捉这种“变中的不变”,因为感官经验中只有生生不息的赫拉克利特之流。绝对的不变只能存在于理智观念中,即存在于逻辑性的语词is(是、存在)中。其次,如果世界是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那么它就是多而不是一。譬如,我们可以在万物之流中随意舀起一碗,然后命其名曰树木、石头、飞鸟,抑或野兽,等等。对于传统旧思而言,感官知觉中世界万物的多样性只是真正存在的表象或幻象。因为,唯当存在是一,才能化一为多,创生万物;如果存在是多,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追问,这个由诸多个体聚合而成的多中,哪一个最为根本,哪一个才是化育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可见,碗喻形象地揭示了旧思所具有的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渴望超逾时间的不变和永恒,以此摆脱对生灭变化的恐惧;二是试图祛除多样性的感观表象(幻象),获得观念性的整全和唯一。在罗森茨威格看来,旧思的这两个特征恰恰表明它是一种病态的思维而非健全的理智。
首先,旧思试图通过诉诸统一、普遍的“全”来摆脱死亡(变化)的恐惧是一种十足的自我蒙蔽。正如碗的隐喻所表明的,我们至多只能熟悉世界的某些片段,“这些片断仅仅与数量有限的事物、人和事件相关”。然而,旧思全然无视自己舀起的只是一碗水,只是世界之流中的一个孤立、静止的片段。它把目光聚焦在这碗水上,然后开始思量“它是什么”“它在本质上为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罗森茨威格,2006:323、319-320)。它太过于投入,以至于把片段视为全体,最终忽略了碗旁那永不停歇、奔涌向前的河流才是真实的世界(存在)本身。对罗森茨威格而言,“世界的存在不是一个无限静止的本质”(罗森茨威格,2013:40),“有关世界的令人不安的是事实是,它毕竟不是精神。其中仍存在着其他东西,常新的、紧迫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它的子宫在不知足地孕育,在无穷无尽地生产。”(罗森茨威格,2013:42)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不是永恒静止、而是永不停歇的生成和变化。因此,旧思苦心孤诣地编织的不过是“关于尘世的全的观念的蓝色迷雾”,它“在这个‘应该’的问题上欺骗”自己(罗森茨威格,2013:4),却全然未觉人之理性的有限本性与根底虚空。与之相反,新思“通过采取打开水闸并允许它自己就是其中一部分的那条河流将其淹没的方式”(罗森茨威格,2006:326)来获取自身,它并不把理性能力或自我意识预设为认识世界的前提,进而用知性演绎的因果之网来滤除世界的偶性和杂多,而是从身体性的生存体验出发,凭靠时间性的主体经验去体知世界之河的生生不息。
其次,罗森茨威格也不赞同旧思对整全观念的热衷和膜拜。在罗森茨威格看来,传统理性哲学对绝对的一的痴迷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露天的画廊”:在画廊中,墙和画是不同的个体,它们之间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却是画廊的统一性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或环节。没有了画与墙的内在统一,画廊就丧失了其应有的意义,反之亦然。罗森茨威格并不否认墙所具有的统一性:一面不挂东西的墙是空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无,而是一个赤裸裸的统一。若没有这面墙,挂一幅画是不可能的。但对于新思而言,墙(全)的内在统一性却无法统摄画(个体)的多样性。罗森茨威格强调,“墙内在地是个统一,画内在地是一个无限的多样性,外在地是排他性的整体。无论如何,这不意味着统一,只意味着个体——‘一幅’画……无论如何,统一不在世界的墙之内,只在世界的墙之外。”(罗森茨威格,2013:13)简言之,世界这面墙之内拥有的只是诸多个体(一幅幅画作),世界本质上“是多,在其自身内根本没有一。只有在推理中才有世界的存在。同时,推理是作为一个具有许多分支的个体的思维系统而进入世界的。因此,逻辑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作为世界的本质是后来的”(傅有德等,1999:100)。对罗森茨威格而言,旧思以认知逻辑的视角“观看”世界,不仅在顺序上是后来的,而且在根基上也不牢靠。个体存在是涌动的生命之流,因果认知逻辑仅仅是为了解释生命之流而中途突入的一种理观或反思活动。然而,旧思却舍本逐末,把源自生命之流的认知观念视为人之根本,最终遮蔽甚至遗忘了由所从出的生命事实本身。与之相反,新思则从更加本源和真实的个体生存体验出发,将世界、上帝和人视为独立实存和涌动贯通的内在统一,就像“大卫之星”,它们在静态本质与动态互动中连缀成一个星体,给当下祈祷救赎的生命个体以不可或缺的光芒和指引。因此,与旧思作为一种“没有神的神学”相比,新思不仅是哲学上的某种运思或范式转换,更是启示信仰上关于圣灵降临的叙事。
三、 “观念的他者”到“对话的你”:新—旧思在启示观上的根本分歧
与门德尔松身处的时代不同,罗森茨威格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启蒙之光的普照。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拿破仑的铁蹄打破了德意志王国的封建割据与思想保守。犹太人走出了隔离区,获得了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和教育权利*这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达到顶峰,因为其所施行的自由民主制是“第一个既承认犹太人有权保持犹太身份,同时又享有完全公民权和平等权利的政治制度”(Smith,2006:75)。。与同时代的许多犹太青年一样,罗森茨威格自幼便受到非犹太的欧洲哲学与文学思潮的影响和熏陶,甚至曾一度试图改宗皈依基督教(Glatzer & Rosenzweig,1953:24-25)。然而,1913年的一个赎罪日活动,让罗森茨威格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在“自我折磨和冥思苦想近三个月后”,罗森茨威格终于做出了一生中的重大抉择:回返犹太正统,以复兴犹太教启示信仰为余生志业。然而,抉择的非此即彼并不像删除电脑文件那样可以轻易抹除记忆中的思想印痕。换言之,仅仅确定方向是不够的,传统理性哲学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克尔凯廓尔式的“信心(信仰)的一跃”无法让罗森茨威格感到满意,因此,如何从哲学(而非从信仰)上把握启示便成了他必须跨越的“卡夫丁峡谷”。为了攻克这一难关,罗森茨威格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努力。在沉潜蛰伏4年零10个月之后(1918年8月),罗森茨威格终于下定决心,将自己对启示的感悟和对犹太信仰的忠诚以哲学化的方式付诸笔端。这就解释了《救赎之星》的开篇为何以“向哲学开战”为标题,并以新(健全)思维—旧(病态)思维的二元区分作为其论述的初始基点:对于罗森茨威格而言,没有哲学范式的转换就无法获得启示信仰的全新理解。新思的提出是为了解答启示的现代困境,唯有完成旧思的新思转换,才能让人(不只包括犹太人)获得活生生的生存(信仰)体验,从而最终确立起个体与上帝之间“普遍的爱的交流(对话)关系”*正因如此,尽管罗森茨威格把启示作为自己哲思的阿基米德点和最终指向,但他仍强调(《救赎之星》)并非是一部面向犹太人的传教之作,而是一部对所有人言说的哲学著作(Rosenzweig,2000:110).。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新思如何超逾旧思,从而实现哲学上对启示的开放?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罗氏启示的具体所指。在罗森茨威格看来,启示并非一个抽象的观念或范畴,而是“上帝和人类之间活生生的事件”,是“隐蔽的唯一者”的自我显现和人—神对话(罗森茨威格,2013:181、160、151)。具体而言,罗森茨威格在以下三个方面超逾了理性宗教的启示观念,对启示做出了独特的生存论解读。首先,在创造和启示的关系上,罗森茨威格认为“创造本身就已经是第一个启示”。创世即让世界显现,在《旧约·创世纪》中,通过六重肯定,上帝不仅创生了世界,而且彰显了他的良善、智慧和力量,从而确证了他自身的存在。正因如此,罗森茨威格强调,创造是“启示的创造和历史性的启示”(罗森茨威格,2013:155、180)。然而,创造的启示性质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混为一谈,因为,相对于启示经验的当下性而言,创造更多表现为历史性的一个事件,“过去的创造是由现在的活生生的启示来确证的”,“当启示的表达在此时此地出现……事物才能从实体性的过去进入生机勃勃的现在”(罗森茨威格,2013:175、155)。其次,与传统的先知观不同,罗森茨威格认为“先知并非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他的目标不是启示的接受和传递。毋宁说,上帝的声音是直接从他那里发出的,上帝说话时就像他自身的‘我’直接说话一样”(罗森茨威格,2013:171)。在罗森茨威格看来,启示不仅是《旧约》中记载的某个遥远的“神圣历史事件”,亦是当下甚或未来发生的神迹,因为“启示的基本的奇迹发生在过去,而它的完全实现则需要一个未曾发生过的未来的奇迹”(罗森茨威格,2013:177)。因此对于信众而言,沉溺于过往并不足够,重要的是要把握当下,凭借祈祷——它是对上帝的最高和最彻底的信任的表露——的呼喊、叹息和请求,在“‘我’与‘你’由以涌出的”启示土壤上为上帝的临在敞开地平(罗森茨威格,2013:177-179)。最后,在思维的表现形式上,罗森茨威格强调启示并非隐蔽唯一者的独白,而是人与上帝在当下时刻发生的活生生的我—你对话。思想的表现形式是独白,逻辑的运思具有超逾时间的永恒特质,而对话则是面对面的推心置腹,它受时间滋养、并受制于时间的当下性。与传统旧思将理性范畴作为思维的原点不同,罗森茨威格把新思的起点设定为处于生命之流中的具体个人,这一起点显然与独白的表现形式无法兼容:自我个体的当下性和流变性很难用超时间的独白来加以固定和展现,只有“完成了独白到真正的对话的转变之后,它才变成了我们刚刚为可听闻的‘否’所要求的那个‘我’。独白中的‘我’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我’”(罗森茨威格,2013:168)。综上可见,罗森茨威格的启示是上帝与人之间发生的活生生的“我—你”对话。上帝首先进行爱的创造,然后启示自身,人接受了启示,然后在牢固而持久的信仰中肯定了爱者瞬间性的爱。上帝在经验性和当下性的启示中获得了存在,在与人的对话当中显现了自身,并通过立约和颁布戒律的方式赋予启示以内容。而人则在与上帝的临在和对话中蒙受了神恩,获得了救赎,走向了永恒的道路和永恒的生活。
罗森茨威格这种生存论的启示理解与理性宗教概念化的启示观念之间存在着无法融通的紧张和对立。传统旧思是一种概念逻辑思维,它试图用逻辑之网来统摄一切,最终建构起一个封闭自洽的整全体系。旧思之所以误入歧途,源于它根基的偏狭以及由此而生的恐惧:它对一的热衷和对数—理逻辑的膜拜,使其不敢相信内心体验的真实性,从而无力肯定生命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躲避在观念编织的避风港内,通过划定边界,将经验排斥在外;它为自己筑就囚笼,最终断绝了与上帝、世界和他人直面的可能性,因而无法对上帝产生一种真切而直接的体会。因此,旧思对启示的封闭性,注定了它在创造的神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神学)方面面临失败:它“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喂养了神学,就像一个保姆可以拿一个抚慰的东西放进孩子的嘴里使他不哭一样。这种源远流长的欺骗随着康德和黑格尔达到了双重的终点”(罗森茨威格,2013:17)。然而,对于创造神学而言,上帝却有着“先于一切存在和思维的统一的生存”(罗森茨威格,2013:17)。因此,与旧思把上帝看作一个观念的他者不同,新思通过将上帝视为一个“同人交往着的、不断创造和启示着并带人走向救赎的活生生的‘永恒的你’”(傅有德等,2008:472)而对启示敞开了大门。新思并不耽溺于一与多、变与不变的观念之争,相反它把目光从理性的观念世界和自我中心下解放出来,试图从时间性的当下体验出发,大胆而自信地走入生命、走进生活。新思信任经验,肯定生命的意义,它把自己置身于世界之流的跌宕起伏中,通过启示搭建的人神之桥,发自内心地向上帝发出亚当式的请求:“您在哪里”,或在上帝的召唤面前做出亚伯拉罕式的回应“我在这里”。正是在这种活生生的邀请—应答中,当下的个体自我获得了时间性而非终末性的救赎,最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并获得了自己的真实(本真)之在。
四、 复返的究竟是何种正统?:罗森茨威格新思评价
在20世纪犹太哲学史上,罗森茨威格哲学的范式建构意义毋庸置疑。无论是双重立约论所包含的对基督教信仰的罕有宽容,还是存在主义新思对哲学反思的颠覆性符码意义;无论是对理性宗教之根基的生存论批判,还是我—你对话的启示理解所开启的犹太信仰复返之路……无不彰显了罗森茨威格存在论犹太神学的思想力度和现实影响。无怪乎在一次“评论研讨会”(1965)上,罗森茨威格被与会学者公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犹太思想家”(张志刚:2007:66)。然而,思想威名并不表明其理论思考的完美无缺。相反,仔细审查罗森茨威格除旧布新、复返犹太正统的理论思考,我们发现其新思并不像他所坚信的那么纯粹彻底。这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罗森茨威格的新思真的超出旧思阈限了吗?与此相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罗森茨威格复返的正统到底是何种正统。
毋庸置疑,罗森茨威格翻转了传统理性哲学的初始基点:从“存在和有”转向“先于理性的赤裸裸的存在”(无)。对于传统理性哲学而言,前理性的存在“大致可以等于‘无’,在它称为思维的存在以前是不可能被理解的”(罗森茨威格,2013:19)。然而,这个看来“同纯存在一样贫乏”的无只是旧思意义上的知识之无,但在个体的生存体验上,这个无却是真实的有和在场。问题是,罗森茨威格并不自满于生存体验上的真实,他的旨趣在于从这个“知识之无”前进到“知识上的是”。在《救赎之星》开篇导言中,罗森茨威格强调,传统旧思的道路“是从现成的是引向无……我们不走这条路,而是一条相反的从无到是的路”,即“从知识的‘无’(Noughts)前进到知识的‘是’(Aught)”(罗森茨威格,2013:23、19)。关键在于,用概念的方式描述知识之无不仅受到传统哲学术语的干扰*这在海德格尔“此在”到“在”,从述谓表述到诗性语言的艰难转向中便可管窥。,也需要找到与此任务相称的方法论原则。在这后一点上,海德格尔幸运地找到了现象学方法,罗森茨威格倚重的却是他一直批判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只不过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他对概念式的否定辩证法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和创造性的发挥。罗森茨威格强调,有“两条道路引导我们从‘无’走向‘是’,肯定的道路和否定的道路。肯定是例示的肯定,是非无;否定是对所与的否定,是‘无’”。在《救赎之星》中,罗森茨威格强调否定是概念运动发展的内在源泉和根本动力。在运用肯定的道路对三个不可化约的实在:上帝、世界和人做了静态的本质分析后,他紧接着运用否定的道路,对上帝的自由、世界的无和人的自由意志做出了动态的关联描述。通过肯定与否定这两个相互对立方面的交替铺陈,上帝、世界和人的独特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得以展现。可见,尽管多样性的真实受到个体生存体验的证实,但罗森茨威格对上帝、世界和人的动—静描述却抛开了个体生存经验的原初起点,运用一种类似黑格尔式辩证法的理论推演方式加以展开。更为重要的是,当论述救赎这一观念时,罗森茨威格甚至重拾起了他在开始时一再批判的“整合一切的一元论倾向”,强调上帝、世界和人最终在救赎的履约、赋灵和获救中走向了完满和统一:“只有在救赎中,上帝才变成了一(One)和全(All)。……我们曾刻意打破了哲学家们的‘全’(All)。在此,在完美的救赎的令人眩目的光照下,它最终与那个一(the One)合为一体。”(Rosenzweig,1971:238;罗森茨威格,2013:230;张志刚,2007:64)综上所述,罗森茨威格在概念的理论建构形式、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和统一性的救赎观念等方面都烙刻着黑格尔式概念思维的痕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批判罗森茨威格的“新思维反对旧思维,但它仍然是旧思维的后裔”(施特劳斯,2013:24)。他的思想臆想表面上“以‘经验’为出发点,实际上却以‘教义’为出发点”(格林,2010:325)。
罗森茨威格不仅在哲学之思上具有明显的旧思烙印,而且在新思的终极目标——复返犹太正统上也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施特劳斯敏锐地洞察到,罗森茨威格“所回归的犹太教并不等同于门德尔松时代之前的犹太教”。因为,前现代的犹太正统“从上帝的律法出发,即从《托拉》出发……来理解犹太民族”,而罗森茨威格则是从“犹太经验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出发”,即从律法的前提条件“犹太民族及其选民特性出发”,“以‘社会学的’方式展开讨论”(施特劳斯,2013:24、25)*罗森茨威格强调,犹太信仰的非律法性体现在“犹太人的信仰不是证言的内容,而是再生的产物。犹太人……依靠连续不断地生育出犹太人而证明其信仰。他的信仰不是信某种东西。他本身就是信仰,他是用一种直接性去信仰……犹太教的信仰不太在意教条的确定性:它存在着,这比言辞更有价值” (罗森茨威格,2013:323、327)。。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说明,罗森茨威格对前现代犹太信仰中的神秘主义态度如何。或许因为神秘主义是施特劳斯的理论盲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对这个问题既无兴趣,又缺少相应的理论储备,因此也就不便贸然做出评论*1935年10月2日致肖勒姆的一封信中,施特劳斯直陈自己是神秘主义的“地道的门外汉”(施特劳斯等,2006:255)。。但仔细缕析《救赎之星》 的相关表述,不难发现罗森茨威格对犹太神秘主义的批判指摘:“既是整体又是一切的‘全’,既不能被诚实无欺地认出,也不能被清楚明白地经验到。唯有唯心主义的不诚实的认知,或者神秘主义的不清楚的体验,才自欺欺人地认为已经认识到它。” (罗森茨威格,2013:358)可以看出,罗森茨威格复返的犹太正统,既不是中古犹太律法主义,亦非前现代犹太神秘主义思潮,而是受到启蒙思潮修正了的“犹太正统”。作为被启蒙之光照亮的犹太人,罗森茨威格将拣选的原则“交给每一犹太人都拥有的‘一种力量’来决定,这无异于承认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前提’”(格林,2010:325)。这种对个人自由的潜意识认同,与前现代正统对律法(义务)绝对服从的呼召之间扞格难通;而且,中古犹太律法主义视域下僵硬而严苛的上帝—立法者形象,与罗森茨威格试图将尼采的生命概念接入犹太启示信仰的旨趣之间也水火难容,这些都成为罗氏无法复返中古犹太律法主义正统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罗森茨威格试图以非理性的方式重建犹太启示信仰的致思之旅并没有让他走向不可言说的犹太神秘主义,而是在其论述中处处散发着黑格尔式理性建构和辩证推演的气息。概而言之,《救赎之星》向我们展现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交叠杂糅的罗森茨威格面相:从理性自明的追求上看,罗氏的新思实际上并没有摆脱门德尔松—斯宾诺莎启蒙旧思*罗森茨威格对启蒙思维的依赖尤其表现在对基督教信仰的罕有宽容上,他把后者视为永恒的道路,通过双重立约论方式将其与犹太信仰的永恒生活等量齐观,因主题和篇幅所限,此不展开(罗森茨威格,2013:318-380)。的影响;而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来看,他身上又流淌着尼采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扼杀个体生命价值的反感。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救赎之星》的用意和客观效果上看,该著或可看作是对柯亨《理性宗教》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宗教观的某种直接反动。众所周知,柯亨改造犹太教倚重的资源是康德的道德学说,后者强调的可普遍化的道德律令。但在罗森茨威格看来,上帝的爱的命令要高于理性自治的道德律命令,因为:一方面,康德的道德律令是缺乏内容的“空洞的形式主义”,而唯有上帝的爱的命令才能为康德的道德律令提供实在内容(质料);另一方面,康德对可普遍化的理性形式的强调使得“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即神圣变得不可理解,而神圣只有上帝之爱的协助下才有可能”(Smith,2006:35)。但吊诡的是,罗森茨威格否弃了柯亨调和启示和理性的努力,自己却栖身于理性哲学的另一种形式,即黑格尔的辨证理性来为启示做论证。虽然其意旨最终是要和黑格尔辩证理性哲学的旧思划清界限,但形而上学的反面仍是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认为罗森茨威格对犹太教的重构并不令人信服。在施氏看来,罗森茨威格致力于神学复兴的专著是一套哲学体系(而不是一部“犹太人的著作”),这充分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依赖于自己努力要取代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罗森茨威格并不相信传统律法中的很多训诫,相反,他将自由尊奉为犹太教的中心,这种对现代启蒙(自由)原则的无批判接受和默认,充分彰显了罗氏对前现代犹太教正统律法的核心要义的根本背离*施特劳斯从罗森茨威格那里获益良多,例如,在罗氏的影响下,施特劳斯逐渐认识到犹太问题具有超历史的永恒性,因而远离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但罗森茨威格与海德格尔一样强调非理性个体的存在体验,而施特劳斯则热衷于中古迈蒙尼德式理性主义,他们对理性的不同态度,最终导致二者学术理路渐行渐远(Smith,2006:35,79)。。
可见,罗森茨威格的新思是一种带有旧思烙印、半截子的犹太正统复返之路。当然,在犹太传统信仰的复返上,我们不应怀疑罗氏动机的坦荡真诚。对于那些深陷神学政治困境之中的犹太青年,新思维为其提供了“一个激进的和可敬的解决办法:它召唤犹太人个体抛弃自己的困恼和困惑,返回犹太共同体的怀抱当中,这个共同体的基础是信仰和犹太生活方式”(唐格维,2011:192)。但我们也应看到罗森茨威格回返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对于前启蒙的犹太正统而言,上帝临在的启示之言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永恒性,根本“无需考虑个人主观的和随意的偏好”,然而罗氏用时间性的生命体验瓦解了神圣诫命的这种永恒真理性。永恒真理让位于个体当下化的纯粹任意和主观抉择,成为具有某种历史情境性和主观相对性的姑且言之。正是这种真理相对化的历史主义和(默认)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倾向让施特劳斯对罗森茨威格敬而远之,这恐怕也是施特劳斯虽然对柯亨不乏严苛批判,却始终近后者而远罗森茨威格的原因之所在。另外还需强调的是,在罗森茨威格的新思描述中,较之世界的被造性和人的受启示性而言,上帝作为永恒之你的形象“既不是想象的产物,也不是理性的产物,‘你’只是以其激进的他者性出现在人们面前”(唐格维,2011:199)。比较而言,上帝作为对话之你的大他者性,在海德格尔那里仍是作为某种存在者或者说是需要解构祛蔽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罗森茨威格虽然在启示信仰方面的洞幽察微上远优于海德格尔,但在哲学根底的解构和清理上,尤其对现代启蒙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洞察上,却远不及后者来的深刻和纯粹。
五、 罗森茨威格的新思与古今中西之争
理智上的真诚无畏并不意味着具有可倡导的现实指导意义,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海德格尔对传统解构的彻底纯粹具有深远的思想史意义,却抽空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道德生活的根基。施特劳斯很早就意识到这种虚无主义对现实造成的恶劣影响,它间接为纳粹极权主义的崛起扫清了思想障碍(施特劳斯,2008:101-130)。悖谬的是,高度关注城—哲紧张和隐微写作的施特劳斯,半个世纪后竟缺席卷入意识形态的口水仗中,受到美国自由派学人和主流媒体的讨伐和攻击(德鲁里,2006:2-4)。对于一个严肃的学者而言,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义传统的生存论解构,施特劳斯对古典理性主义的柏拉图式辩护,不应放在意识形态层面简单粗暴地加以对错评判,当然这不是本文处理的论题。可以肯定地讲,与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的针锋相对和非此即彼相比,罗森茨威格“中庸式”的犹太正统复返对我们直面古今中西之争更具启发意义。上面我们论及罗氏新思中的交叠杂糅和不彻底只能表明其理论上的局限。在实践上,诸如犹太人应如何宽容地看待异己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处理个体自由抉择与神圣律法服从的关系、如何获得犹太信仰的当下性和直观性体验等方面,却具有重要的现实可指导性。在启蒙之光普照、平等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让那些业已融入宗主国的犹太人抹去根深蒂固的自由平等观念,回返前现代封闭隔绝的犹太信仰生活,既无可能,也不必要。
事实上,我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时也遭遇到同样的困境。毫无疑问,在以救亡图存为使命的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中—西之争尚有彻底回返前现代德性生活的可能。然而,在知识分子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底层民众层面(文化大革命)的双重解构之下,传统文化观念和道德习俗在学理和文教政制层面已完全失语,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也已深入人心。因此,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实践生活层面几无可能回返到施特劳斯倡导的前现代德性生活;另一方面,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失语,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弥漫风行,让每一个有良知的学人也难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追随海德格尔一味地施展解构之能事。与之相反,罗森茨威格那种对现代西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博观约取,对基督教信仰的罕有宽容,以及为复兴犹太传统信仰进行的艰苦卓绝且极具可操作性的生存论思考,为我们如何复兴中华传统提供了颇具可行性的参照路径。
概括而言,这种启发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文明传承的视角看,复兴传统、重倡国学,唤醒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下出场、在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然而,传统的复兴不应当拒绝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现代文明的成果是启蒙的直接产物,如果对启蒙的理性传统、自由权利观念、政制理念及其实践视而不见,而是一味地在非此即彼的知性逻辑上叫嚷着复返传统、回到过去,这充其量是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表现。罗森茨威格对犹太教的复兴,是在深刻理解消化了西方启蒙精神、康德—黑格尔理性哲学和尼采—克尔凯郭尔非理性哲学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创新,尽管他的方案在理论上不够纯粹和彻底,但因其具有厚重的理论深度和深刻把捉现实的实践感,故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导引性意义。这向我们表明,唯有深刻消化理解西学文明的基础内核及其逻辑演进,将其内化为复兴传统的组成要素和内在环节,才能让中华传统的复兴站在坚不可摧的夯实地基上。其次,从当下国人的生存经验看,无论是天赋权利的自由观念,还是资本化的市场经济,正转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新常态。这种数量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吞噬着中华传统道德的质的边界,在个体权利意识和数量同质化的双重攻击下,传统道德的防线不断后撤,一些优良的价值观念正在失语和退场。因此,简单重复地宣讲、记诵古代经典语录,不仅与现代人的生存经验隔膜难通,而且无益于人们日常决断。换言之,让经典出场,让传统复活,取决于对传统经典进行创造性的重新解读,这种诠释和解读要符合现代人的经验感受,不仅有理论上的说服力,而且具有实践上的亲近感。罗森茨威格重释犹太传统的启示观念,对其进行了与西方启蒙自由观念相容的生存论阐释,让犹太传统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给我们提供了可资效行的样板,并且向我们表明:唯有从人们当下生存体验出发,充分消化理解西方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通过重新阐释传统来复兴传统,才能真正焕发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最后,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看,罗森茨威格对犹太教的复活,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危机及其现代理性主义覆灭的深刻批判的基础上的。启蒙运动试图借助大写的理性在尘世构建宗教允诺的彼岸天堂,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崛起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启蒙理想进行了自我否定。罗森茨威格的犹太教复兴,一方面从非理性主义那里借助理论资源,一方面倚助犹太教启示信仰来填补理性主义覆灭之后的空场,其理论自觉和敏锐洞察可谓顺天命而为。这提醒我们,当下对传统的复兴应当立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五四启蒙时期,我们批判中国传统,引进西方启蒙的德先生、赛先生和费小姐,全因对中国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认识;而今,我们之所以重返传统,也是充分意识到现代性并不是万能良药,并不能端赖其促成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例如,环境污染、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物欲横行等现代病既由现代化所伴生,就不能希求全盘西化和现代化的方式来加以克服。与之相反,具有望闻问切和整体洞察功夫的中华传统文化或可成为诊疗现代病的一个有效资源。由是观之,现代性批判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契机和最佳视角,面对现代化衍生出的种种问题,我们不应只顾埋头向前,更要学会向传统发问,从传统中求取资源。
综上可见,罗森茨威格的犹太复兴,对我们审思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启示意义。这一成功样板启示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汉语学人一方面不应关起门来搞儒学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充分汲取西学,以西为镜,化西为中,打造具有担当意识和中国关怀的融贯中西的学术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唯西是从,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有尊重和文化自信。对于一个伦理本位而非宗教信仰维系的差序格局社会,传统道德文化是我们赖以呼吸的根本,中断文明传承便意味着自断血脉。丧失安身立命之本,又何谈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有思想担当的汉语学人,应如罗森茨威格,在汲取西学的基础上躬身回返民族传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继承传统的教育实践。这样,我们的传统复兴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所依托。
[1] 德鲁里(2006).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刘华等译.刘擎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傅有德等(1999).现代犹太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3] 傅有德等(2008).犹太哲学史: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格 林(2010).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施特劳斯.游斌译.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 唐格维(2011).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林国荣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 罗森茨威格(2006).罗森茨威格论世界、人和上帝.吴树博译.孙向晨校.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7] 罗森茨威格(2013).救赎之星.孙增霖、傅有德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8]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2010).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 施特劳斯等(2006).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0] 施特劳斯(2008).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1] 施特劳斯(2013).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2] 张志刚(2007).20世纪宗教观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3] 郑文龙(2011).罗森茨威格非政治的神学与“犹太人问题”:按法理学“例外状态论”进行的类比分析.“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 Amos Funkelstein(1993).PerceptionsofJewish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 Nahum N.Glatzer(1953).FranzRosenzweig:HisLifeandThought.New York:Schocken Books.
[16] Milton Himmelfarb(1966).Introduction to the Commentary Symposium—The Condition of Jewish Belief.Commentary, 42(2).
[17] Jewish Historicism(1992).The Evolution of the Akademie für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1919-1934).HebrewUnionCollegeAnnual,58.
[18] Franz Rosenzweig(1971).TheStarofRedemption.Translated by William W.Hallo.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
[19] Franz Rosenzweig(2000).PhilosophicalandTheologicalWritings.Translated and Edited,with Notes and Commentary,by Paul W.Franks and Michael L.Morgan.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
[20] Steven B.Smith(2006).ReadingLeoStrauss:Politics,Philosophy,Juda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责任编辑:叶娟丽
Franz Rosenzweig’ s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Quarrel of “Ancient-Modern and Chinese-Western”
GaoShankui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Western philosophy has more than one source. The first one emphasizes the tradition of consistency among changes that comes from Parmenides, is further developed and advanced by Plato, Aristotle, Spinoza, Kant, and Hegel. The second one emphasizes the tradition of life and its growth that starts from Heraclitus, and has its revival in Nietzsche and Heidegger. Although Rosenzweig’s thought is based on Hegel’s philosophy, but he puts forward the new thinking against the old thinking by virtue of Jewish faith exper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and Nietzsche. Therefore, fundamentally, Rosenzweig’s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ould be hailed as “the question of the Heidegger” in the field of faith.
10.14086/j.cnki.wujss.2017.01.013
D0
A
1672-7320(2017)01-0115-11
2016-03-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X061);第5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6M591610)
Considering the content, there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ces between Rosenzweig’s new thought and the old thought. Firstly, the start point of the old thought is Being and the start point of the new thought is nothingness of knowledge which is prior to ration. Secondly, the basis of the old thought is “the One” and immutability, and the new thought affirms the diversity and changes in terms of timeliness existence experience. Thirdly, God is conceptually “the Other” far away from people’s life experience in the old thought, but God is a You of revelation and salvation to meet us in our soul in the new thought. However, Rosenzweig’s new thought has limitation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For example, it‘s methodology is Hegel’s concept of dialectics, and it feeds on atomized individual as the premise of his thought, and he tries to gain a rivival of Jewish orthodox that is impressed by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s. In this sense, Strauss thinks that Rosenzweig new thinking is the seed of old thinking.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return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 vs. the modern and the Chinese vs. the western” from Rosenzweig’s new thinking, e.g., t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hould fully learn from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 Chinese. At last we have to understand deeply to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while we revival Chinese tradition. Key words:Franz Rosenzweig;TheStarofRedemption; The New Thinking; The Old Thinking; Martin Heidegger
■作者地址:高山奎,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徐州 221116。Email:gaoshankui@163.com,gaoshankui@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