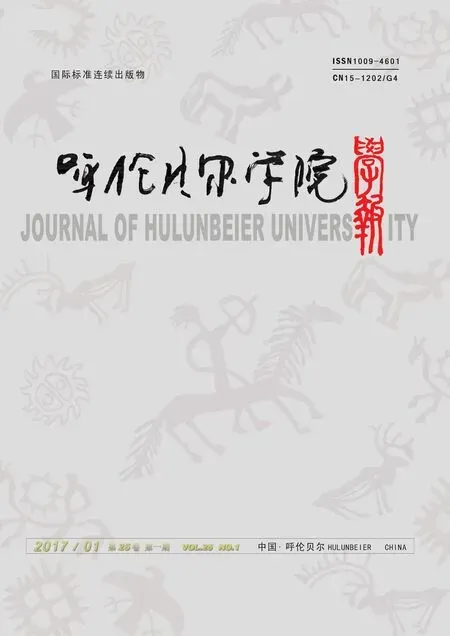新时期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生态小说书写中的文化忧思
2017-03-08郭秀琴
郭秀琴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呼伦贝尔的大兴安岭林区繁衍生息着诸多古老民族,其中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因在全国人口最少被称为“三少”民族。“三少”民族历史上一直生活在草深林密的森林中。他们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森林,狩猎生产方式也是依托于山林,森林是其生存与生活的摇篮。由于“三少”民族在历史上邻近居住、交往密切,在狩猎生产、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有着相似的特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相近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以及文化结构。
如果说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那么良好的文化生态同样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必备条件。“所谓文化生态,指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出来并身处其中的历史传统、社会伦理、科学知识、宗教信仰、文艺活动、民间习俗等,是人类文明在一定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1}文化生态不可嫁接、复制,更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作为民族兴衰存亡标志的民族民间文化,是人类健康存在的“精神植被”,人类应该像保护自然植被一样去保护她。新时期以来,面对现代文明冲击下日渐模糊的民族文化身影,“三少”民族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不约而同地传达出文化消隐后的哀痛心态与身份迷失后的彷徨意识。
一、民族习俗的逐渐消逝
在内蒙古东北茫茫的林海雪原上,“狩猎”成为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也连接着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三少”民族的社会形态,开始由原始、封闭走向现代、开放,传统的生活习俗随之而发生改变。新时期以来,很多“三少”民族作家把民族传统习俗的遗失作为民族文化衰落的重要表征之一来进行书写。
(一)居住文化的变迁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居住生活方式。居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民族物质文明的显在承载,也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投射与物化,综合反映出一定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民族心态。
“斜仁柱”(又称“仙人柱”)是鄂伦春人居住的房子,意思是用木杆建造的房屋,汉语又称之为“撮罗子”。 “斜仁柱”是一种圆锥形建筑,建造方法简单:不用钉不用绳,先用几根粗壮、结实、带杈的松树杆交叉咬合搭成锥形的主架,然后用20多跟粗细相当的木杆均匀地搭在主架中间,形成伞状骨架。然后上面再覆盖上桦树皮或兽皮,一架夏可防雨、冬能御寒的“斜人柱”就建成了。“斜人柱”搭盖迅速 、拆卸容易。搭建和搬迁过程中不挖坑,不筑墙,不用一锹土和一块砖,不破坏草地,对周边的自然环境干扰极小,具有了难得的环保居室的特点。从用料上来讲,所用的料全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而且材料可以多次重复使用,最大化的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体现出鄂温克族节俭简约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斜仁柱”的设计和建造熔铸了鄂伦春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智慧,是集适应、简约、环保为一体的生态型建筑。而如今“斜仁柱”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正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敖蓉的《桦树叶上的童话》写到了鄂伦春人响应政府生态移民政策告别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又难舍难分的复杂心态。母亲对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斜仁柱”有着无限的眷恋,尤其担心她的宝贝驯鹿的侍养问题,她说:“驯鹿又不是牛马,怎么能圈养,天鹅是草地上养大的吗?”“斜仁柱”是鄂伦春人的居所,也是他们的精神栖息的地方。
达斡尔族建房的程序在女作家映岚在《霍日里河啊,霍日里山》里有着极其详尽的、不厌其烦的叙述,寄寓着对祖祖辈辈传统居住方式的留恋与不舍。从粘土奠基到挖坑夯石,从柱子的包皮上油防蛀到檩木搭建弃用钉子而巧妙进行凹凸型槽咬合,从对苫房草选料的精细到铺草的讲究,一一细细道来,如数家珍。“苫房草也不是一般的草,是一种空心坚硬、光滑,土黄色的不易压碎,吸收水分又不易腐烛的草。”铺草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体力活,它包含着相当的技术含量:“草根向上,草梢向内,一层一层平铺上去。铺一层抹一层在草梢上。一直铺到屋顶,房脊会合了,再用梓成的八字草编,一个挨一个扣全房脊。这样,再大的风也不会乱飞草了。”可以说,房屋建成过程的每一步都凝聚着达斡尔族人的心血与智慧。最后还有一道工序还要以雕有精美花纹的白色木板来保护房两边人字坡沿上的苫房草,实用而美观。那些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风雨的老屋,正是达斡尔族历史文化的形象载体,传递的是岁月流年的厚重记忆。作品通过一对老夫妻无奈搬离故土时复杂心理的描绘,来呈现出文化交锋过程中,弱势文化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剧命运。定居的达幹尔族与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的作别实际意味着他们要与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告别,怀旧悲哀却又没有别的选择。对他们而言,房屋不仅仅是居住的处所,更是民族历史文化的形象记忆,在居所的背后绵延着神话般悠远的岁月,让人想起那“紫貂野鹿满山窜,稷子燕麦处处长,棒打獐子瓢舀鱼,锦鸡飞到锅台上”的曾经自由自在、富足无忧的生活。
达斡尔人突然要离别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祖屋,进入一个未知全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失根的痛苦。他们告别的不仅是传统的屋子,更是离开了民族文化的温暖怀抱,离幵了“家“也就意味着精神的流离失所。正如文中的老人所言: “一辈子深根于土地的感觉,前所未有地动摇了。脚下的土地在动,草木在动,远处的山脉也在飘摇。一直不服气自己的桑榆暮景的心理,也升出没有远照的馁气了。我徒然成了无家可归、无所凭依的流浪汉了。”
(二)传统生活方式的远去
传统的狩猎生活方式、森林经济形态逐渐被慢慢遗弃,狩猎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解体。对于森林民族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异无异于是掘根之举,时代的变化带给他们的是灵肉分离的痛苦。
乌热尔图的小说《沃克和泌利格》中,鄂温克部落的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村里早已没了萨满先知的存在,唯一的一流猎手和造船能手泌利格也死在了沃克的枪下。在青年人的眼中,狩猎规矩中的平均主义早已成为过去的黄历,甚至很多人在外来文明诱惑下对狩猎的生活方式开始嗤之以鼻:“现在扔下猎枪,干点儿别的什么,照样活得痛快”。而《雪》则反映了鄂温克人面对传统生活裂变的彷徨和痛苦。世代以打猎为生的鄂温克人,居然要像蒙古族养牛养马那样养起了鹿,就连有名的猎人伦布列也肩负起了到围场撵鹿的重任。在传统的鄂温克人的眼中,只有夹着尾巴的狼才会用这种法子捕鹿。《灰色驯鹿皮的夜晚》通过巴莎老人在幻觉的趋使下光着脚丫在大雪降落的夜晚梦幻地驱赶驯鹿最后被冻死的故事,折射出了老人对森林对狩猎生活的眷恋和痴迷,这种间接的描述,更能深刻反映出当事人内宇宙发生着的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老人身上发生的一切在被一个梦游者见识了,那个梦游者其实就是“我”,尽管“我”对老人死亡的过程视而不见, 但“我”无时不在心怀自然,可是面对现实的变迁,“我”只能选择无奈和哀伤,聊以慰藉的是通过梦里在森林游荡而去追忆失落的一切。小说的故事委婉含蓄,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狩猎经济的解体不是一种激烈的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过程,而是经济变革和现代进程的冲击下的自行解体,这样的过程所产生的冲突不是一种外在动作的冲突,而是一种内在宇宙的冲突,是内在价值的冲突,文化心理的冲突。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萨满、驯鹿、猎场、营地,面临的是被吃掉、被毒死,或消失的命运……赖以依托的生存环境没有了,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失去了生存的根。乌热尔图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淋漓尽致地书写了自己对于民族命运深刻的思考和对生活的理解。他在小说中把这一阶段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向彻底地定格了,人们对曾有的原始文化模式的触摸也只有通过记忆找回。作者通过对一个文化群体所承受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创伤的生动展示,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狩猎经济的最终解体”的过程。正如雷达所言,这一过程是“涌现前所未有的痛苦、苏醒和诗情”[2]。
鄂温克作家杜梅的《木垛上的童话》讲述了鄂温克儿童的心灵变迁故事。打猎能手阿爸曾是他们的骄傲,可随着猎人一次次地空手而归,猎枪的地位开始下降,渐渐地,城里的玩具枪取代了猎枪曾有的辉煌。作品从一个儿童的视角,描述了在外来文明冲击下,鄂温克人对原始生产生活方式的质疑和迷茫,也包含了作家对民族未来发展状况的深深担忧。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昔日固守着原始狩猎方式的猎人怀着深深的纠结与痛苦,无奈地搬迁到城里。类似的主题在杜梅后期的作品中仍然延续着。《那尼汗的后裔》中,哈拉大叔把挑女婿与挑选民族文化优秀传承者合二为一,在他看来,只有把呼烈(最优秀的猎犬后代)驯服的人,才可以做他的女婿。然而,那个符合条件的佳婿那丹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因为没能在山里狩到猎物,那丹到城里卖了猎枪和猎犬呼烈,用换回的四千块钱回家开店做起了生意。那丹的行为,隐喻着鄂温克族狩猎文化输给了商品经济。哈拉大叔和年老的阿拉嘎却始终守望在山岗上,一心企盼着呼烈的归来,梦想着再做山林的主人。作品深刻反映了那些坚守原始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鄂温克人既然无奈又逃避的心理。
(三)丧葬仪式的更改
丧葬也是民族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民族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 “三少”民族的丧葬习俗,有天葬、野葬、火葬、树葬、水葬等等。虽然草原民族丧葬风俗各有特色,但总体来讲他们历来是重生轻葬的,追求死后回归自然、回报自然,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原始的丧葬仪式有的被改变,有的甚至无法存续了,这些变化反映出民族文化难以存续的危机所在。达斡尔族作家萨娜在《达勒玛的神树》中,描述了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达勒玛,她多么希望自己死后可以体面地被送上高高的风葬架,安静地躺在阳光下,灵魂顺着阳光的指点,漂游在蓝色的安格林河流。随着这条清澈而古老的河流, 她就可以升到天堂了。然而伐木工人的到来彻底改写了达勒玛安详的晚年生活。森林中象样的树都被一棵棵伐倒了,找到一幅好的风葬架已经成为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她希望在死后风葬的夙愿已化为泡影,最终老人只能蜷缩在树洞中凄然离世。达勒玛老人一生与人为善,却对伐木工人充满了敌意,缘由便在于现代工业行为对传统民俗的破坏及对民族心理的伤害。工业化进程在发展了经济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改变了民族习俗。作品中充满了理性思考,表达了对民族文化渐趋消亡的深深忧思。
与达勒玛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乌热尔图小说《你让我顺水漂流 》的卡道布老人。老人是部落里最后一个萨满,是“一个智慧得见过自己的生、摸过自己的死的萨满”,却因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林子风葬自己或者说找不到一个宁静的存身之地,只好让生命终结在族人的枪口下,让灵魂顺水漂流。因而小说的标题包含着失传的鄂温克文化可能随水飘逝的未来命运的深刻寓意。
在外来环境的干扰下,民族传统习俗正在面临着渐渐消失或被遗忘的命运,坚守传统的人们精神上正在遭受着进退失据的痛苦,达勒玛老人和卡道布老人都在深重的心理煎熬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作家们对笔下人物“死无葬身之所”悲剧的命运安排有意预示了民族文化失传的可怕结果——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去向何方。
二、宗教信仰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隐退
随着现代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在现代科技与理性精神烛照下,自然内在的神秘性和魔力遭到放逐,人类的主体性意识不断高扬、膨胀。滚滚的现代化洪流,更加膨胀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人们从内到外的一切指向,就是对物欲的控制和利益的攫取。自然神性世界的消隐不仅使得宗教信仰的生态理念逐渐淡出人类的意识,同时也使得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摇摇欲坠了。
居住在大兴安岭的“三少”民族普遍信奉的萨满教的衰落与困境在作家乌热尔图的笔下也有着真切的表现。在鄂温克文化中,萨满是沟通人神鬼三界的使者,是本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因为他们深信萨满是始祖女神“舍卧刻” (sewenki)的附体,是神的旨意的传达者,因而萨满在鄂温克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威望。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严重动摇了萨满的崇高地位,使他们面临着尴尬境地,有的甚至陷入了悲惨的际遇。因为萨满承载了特殊的文化内涵,他们的没落也预示着部落文化陷入了的艰难的境地。
在《萨满,我们的萨满》和《你让我顺水漂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萨满命运及其精神状况的描绘。《萨满,我们的萨满》中,那个深谙部族传说和习俗的达老非萨满,在鄂温克人看来,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可以说他代表了整个族群的灵魂。因为他和 “整个部族的命运纽结在一起,江河一样存在了千百年”。可千百年神圣的传承又如何呢?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萨满”在人们的口中仿佛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甚至“萨满”这个曾经神圣的称呼,现在居然成了新的禁忌。昔日辉煌的达老非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去过隐居无言的生活。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揭开了古老民族神秘的面纱,民族文化被游客视为猎奇的对象,曾经风光的“萨满”老人重新闪亮登场了,当他披着满是虫蛀和鼠粪的萨满神袍再次出现时却不再是被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是被当做能够代表萨满文化的“活化石”,成了人们进行拍照留念的展示品。“达老非萨满被紧紧地挤在那些人中间,一双又一双手在他的肩、在他的背、在他的胸、在他的肘,拍着摸着捏着。”“达到高潮的那一天,人群来了一拨又一拨,像早春回游的鱼群,让你数不清一百还是五百。”而老人为自己争取空间的唯一有效方法居然是把一脬臭屎拉在裤裆里。在这里作者彻底幽默了一把,说这是达老非萨满“绝无仅有的最富有智慧性的成功反抗”。而这种反抗的背后包含了多少无奈与心酸啊!神圣民族文化竟然成了无聊游客们娱乐消费的对象。特别是他在乡长的压力下披上神袍用母语宣布自己是熊时 ,其承受了怎样的精神凌辱!这部力透纸背的小说不仅反映出商品经济条件下民族文化受到的强烈冲击,在被物化的同时更面临着被侵蚀和改造的命运,作者的焦虑忧患之情在此尽览无余。在《你让我顺水漂流》中,卡道布老爹的萨满神袍竟然被被偷走并廉价卖给了城里的博物馆。此一情节的设计暗示着萨满文化成为博物馆的文明,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以狩猎为生,郁郁葱葱的大兴安岭森林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也信仰萨满教,敬畏自然万物、珍爱一草一木。现代化的大规模开发不仅使他们的衣食之源受到破坏,更严重的是对自然敬畏意识的消失使得他们失去了灵魂和生命的诉说对象。动物遭到猎杀、树木惨遭砍伐,水源受到污染,与山林相伴世代的猎人们正在体会着失去灵魂归宿的痛苦。鄂伦春女作家空特勒作品中有这样的描述:“世世代代生活在林子里的鄂伦春人,依靠他们的生态知识和传统文化保住了这一片自然圣境,而现在,鄂伦春人定居五十年的时间,仅仅五十年,不仅是传统文化失落,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夜夜都能听到这些树木在哭泣……”[3]一个生活在植被覆盖率近百分百的原始森林中的古老民族,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因外来文明的冲击、自然崇拜意识的丧失,就变成了无根一族。
而在达斡尔作家萨娜的眼中,这种依托于少数民族与自然之间亲缘关系的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倒不如说是对自然万物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崇拜,人只有在主动回归自然的基础上才能走上回归自我心灵的旅程。《天光》是一曲关于达斡尔历史文化信仰的挽歌:达斡尔族民族信仰的流失造成的民族心理空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灾难。作品具有强烈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文中出现的哑巴女人隐喻着无言的历史,那个浑身长满瘤子的男孩其实是“智者”的化身,历史记录着过去,而“智者”只能静静地客观冷静地注视着发生的一切,注视着人们糊糊涂涂、浑浑噩噩的的生活。面对这样的群体时,“智者”的努力不但没有任何效果,甚至因此而丧生,相应的村民也因自己的愚昧无知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萨娜要痛心疾首地指出民族融合过程意味着民族文化裂变与重新整合。盲目的遗弃历史和祖先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是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浮躁地抛弃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必然会遭致民族精神萎缩退化的恶果。信仰的衰弱和丧失,极有可能会使得一个民族渐渐走向衰微。
三、民族精神的萎缩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动力源泉,指的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和理念。这种精神就像血液流淌在民族的血脉中一样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从而主宰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路向。
内蒙古东部的 “三少”民族作家注意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对鄂温克民族精神特质所产生的破坏作用。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真诚无私等优秀民族品质渐渐消失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乌热尔图在短篇小说《越过克波河》中通过蒙克和卡布坎出猎中的冲突矛盾,为鄂温克民族传统美德的流逝献上了一曲挽歌。60多岁的老猎手卡布坎秉承着鄂温克民族的传统美德,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懂得谦让。他主动放弃了选择好猎场的机会给年轻人蒙克,出猎带新手是毫无保留的培养。而年富力强的蒙克却自私狡诈、心胸狭窄。无视尊老爱幼的民族,接受原本属于人的猎场而忘却感恩,抢占徒弟的猎物而毫无愧疚,破坏了鄂温克的传统规矩,越界狩猎,最终落得被误伤的因果报应,这似乎也是蒙克“把鄂温克的规矩踩在脚下”而遭受的报应。面对鄂温克人遵循了几百年的规矩逐渐被丢弃的现实,作家的心情正如老猎人卡布坎“眼神中隐约闪过一丝哀愁”,充满了悲哀和无奈。如乌热尔图所言:“人类精神的偏执、破碎,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失衡、断裂;而地球生态的恶化,则又加剧了人类精神的病变。”[4]
在鄂温克作家的笔下,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原璞世界在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异。传统的鄂温克狩猎规矩(如一只松鸡的战利品也要共享的)早已被人们所不屑或鄙弃。鄂温克作家涂志勇《黎明时的枪声》中,日常的狩猎活动已经演变为不择手段的争夺。为了显示个人狩猎的战绩,开丰田车的小伙子竟然不顾受伤的同伴驱车追赶黄羊。优秀民族品质的流失意味着鄂温克人与传统的文化轨道已经越来越远了。
来自于内蒙古西部的蒙古族作家阿云嘎曾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如日中天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前,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那轮正在下沉的落日和那面正在逐渐暗淡的晚霞。但别以为凡‘过时’和行将‘消失’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我的家乡在鄂尔多斯西部的荒漠草原。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里的牧民出门几乎都不锁门。一顶顶毡包或者一座座房子就那么永远地为路人敞开着。还有,草原牧民之间很少发生买卖关系,‘自己缺什么,别人会给你。看到别人缺什么你也得给人家送过去’,这是老人们常说的一话……”[5]民族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对于内蒙古东部的“三少”民族作家而言,也恰如“落日”和“晚霞”给予的启示,也是一种深刻的悲剧。
注释:
[1]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2003(01).
[2]雷达.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J].文学评论,1984(04).
[3]空特勒.自然之约[J].民族文学,2007(09).
[4]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
[5]阿云嘎.有关落日与晚霞的话题[J].民族文学,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