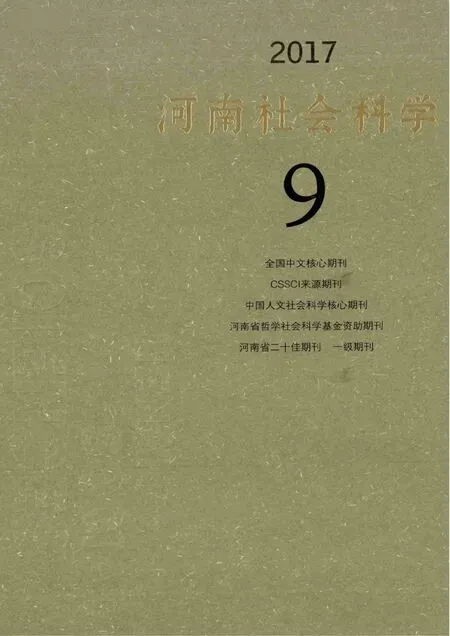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最新刑事立法的衔接
2017-03-07刘霜,吕行
刘 霜,吕 行
(1.河南大学 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最新刑事立法的衔接
刘 霜1,吕 行2
(1.河南大学 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近年,我国政府惩治腐败取得明显成效,刑事立法也及时跟进,具体表现为: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规定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的终身监禁制度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不仅需要国内立法的及时调整,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和成功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惩治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国际法律文件。研究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衔接问题,对我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审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适度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构建公职人员廉洁信息和情报监督制度,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
贪污贿赂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终身监禁;立法衔接
近年,党和政府惩治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我国刑事立法也及时跟进,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最新的立法修正。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不仅需要国内立法的调整,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和成功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社会惩治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关于腐败犯罪规定之全、调整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使国际社会反腐败的法律合作出现多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我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该《公约》,研究《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衔接问题,对我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我国刑事立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最新修改
(一)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指出,单纯以“数额”作为标准难以判断具体个案的社会危害性,难以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公正判决①。《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以“数额”定罪的模式,代之以“数额+情节”的双重定罪模式②。但修正案未明确规定三个档次“数额”的标准,也未明确规定哪些情节属于“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2016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通过《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充分论证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具体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败政策要求,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明确规定③。这样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贪污贿赂案件做到同案同判,以更好地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增设罚金刑
行贿罪属于受贿罪的源头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受贿罪,对其不能过于宽宥。国外刑事立法中,行贿与受贿不仅罪名相同,且受到同等处罚。以意大利为例,根据该国《刑法》第318条④、第321条的规定⑤,处罚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的罪名都是“贿赂罪”(Corruzione),刑罚也完全一样。
我国立法者及时修改刑事立法,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从宽处罚由“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改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外,严格限缩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条件设置,只有对于实行了较轻犯罪,且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到关键作用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行贿人员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罚。
《刑法修正案(九)》还对各类行贿犯罪增设罚金刑。行贿罪属于贪利性犯罪,判定行为人缴纳罚金,使其受到财产刑的惩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此类犯罪的再次发生。考察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刑法,如法国、德国等普遍规定对行贿罪适用罚金刑。据调查,欧美国家行贿罪的罚金刑适用率将近80%⑥。《刑法修正案(九)》还将“行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时直接并处没收财产”合理变更为“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不仅完善了行贿罪的刑罚配置,使附加刑与自由刑实现更好的互补,而且使行贿罪的刑罚适用更加有序合理,从而达到更好的刑罚效果。
(三)严密刑事犯罪法网,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⑦,不仅严密了刑事法网,将“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而且与《公约》第18条的规定相衔接,从而更好地履行了《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
(四)规定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的终身监禁制度
《刑法修正案(九)》中一项引人注目的修改就是增设终身监禁制度。在此之前许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重特大贪腐犯罪人利用减刑、保外就医等方式提前“出狱”,其实际执行刑期过短,民众对此强烈不满。增设终身监禁制度不仅强化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力度,也是立法者对于民众呼声的回应,更为将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做了立法铺垫⑧。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对于犯贪污罪或受贿罪的犯罪人,如果符合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缓二年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适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人采取终身监禁,有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出现此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造成服刑期过短的不当现象,更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⑨。终身监禁不是独立刑种,而是对被判处死缓的贪污受贿罪犯适用的特殊刑罚措施。终身监禁的设立加大了自由刑的惩罚力度,限缩了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惩罚空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终身监禁的立法进程较为仓促,修法过程中持反对意见者或质疑者不在少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时尚未包含终身监禁的内容,但在进入三审时,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中第一次建议加入关于终身监禁的规定⑩。进入三审五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包含终身监禁内容的《刑法修正案(九)》。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⑪,仅仅经过一次立法审议就表决通过终身监禁制度,立法过程确实显得仓促。而且,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⑫,对于这种争议性比较大的条款,可以单独予以表决,但仅仅经过一次审议就表决通过不甚妥当。
笔者认为,对于重特大贪腐犯罪行为人适用终身监禁,反映了我国强势反腐的高压政策,回应了民间提出的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人通过减刑等方式导致其在监狱服刑刑期过短的质疑,也为将来我国在刑事立法层面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做了铺垫。但是,单独对于贪污腐败犯罪规定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这种立法有急功近利的嫌疑,而且也与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不相符。笔者对终身监禁的适用效果持保留态度,并提出如下质疑:
其一,终身监禁仅仅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适用是否范围过窄?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部分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可以“限制减刑”。但是对于本质上属于贪利性犯罪的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却适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在同一部刑法典内法律规定是否协调?如果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是重大立功行为,能否变更终身监禁的适用?
其二,终身监禁的适用能否体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开除公职,因而行为人根本就无再犯同类犯罪的可能性。而且,适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不仅无法激励罪犯教育改造的积极性,更可能彻底堵死其悔改并回归社会的出路⑬,这样如何体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
其三,不能因为少数具体个案就彻底否定减刑制度。司法实践中确实出现少数贪污贿赂罪犯通过减刑方式造成实际服刑刑期过短的现象,民众对此怨声载道。减刑制度设立的宗旨就在于鼓励罪犯知罪悔改并通过劳动改造的方式回归社会、走上正途,不能因为实践中出现的个别不当减刑案例就否定减刑制度的积极意义,而是应当加强对减刑案件的管理控制,以《刑法》第四百零一条规定的“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对不当减刑行为进行规制。只要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就有通过减刑、假释提前出狱的权利。不能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人单独规定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这样显然违反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
根据第55届联合国大会55/61号决议,诸多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维也纳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完成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起草工作。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⑭。我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该《公约》。
(一)缔约目的
《公约》序言明确规定了缔约目的。腐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安全,也会破坏现有的民主体制和法治秩序。腐败不只存在于部分地区,不只影响部分领域,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跨国现象,需要采用综合性、多学科的方法加强国际反腐败斗争。
《公约》设立的宗旨包括:第一,促进和加强各项措施,以便更加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第二,促进、便利、支持预防和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包括资产追回;第三,提倡廉正、问责制,对公共事务和公共财产妥善管理⑮。
(二)《公约》对腐败犯罪主体的规定
1.公职人员
《公约》第2条第1项规定,所谓“公职人员”是指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⑯。至于公职人员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是计酬的还是不计酬的,是有编制的还是没有编制的在所不问,只要其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就可以被认定为公职人员。
2.外国公职人员
《公约》第2条第2项规定,“外国公职人员”是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⑰。
3.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公约》规定,“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国际公共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⑱。这里只限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或者经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人员,而非所有工作人员。
(三)《公约》规定的反腐败机制
1.预防机制
《公约》对于反腐败预防机制的规定包括以下几点:一是预防性反腐败机构的设置(第6条)。该机构负责制订和执行协调有效的反腐败政策,定期对相关法律、措施进行评估,以确定反腐败政策是否切实有效。二是建立公共采购制度。该制度的作用在于维持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的公开、透明(第9条)。三是简化行政程序,建立公众与国家机关的联系通道(第10条)。四是制定私营机构廉洁的标准和程序,防止私营部门的腐败,形成良好的商业惯例(第12条)。五是促进社会参与,开展打击腐败的公共宣传活动,在大中小学开展公共宣传教育活动(第13条)。六是制定预防洗钱措施,打击洗钱活动,查明账户所有人的身份,监控可疑账户等(第14条)⑲。
2.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
《公约》规定的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包括:一是刑事定罪方面,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和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影响力交易等行为确定为犯罪(第15—18条);二是惩治腐败犯罪方面,除刑事定罪外,还包括取消任职资格以及冻结、扣押和没收犯罪所得等制裁措施(第30、31条);三是保护措施方面,《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举报人、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包括为证人和鉴定人的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有效保护,对因腐败而受到损害的人员或实体予以赔偿或补偿等(第32、33、35条)⑳。
3.国际合作机制
《公约》各缔约国应当进行国际合作,包括引渡、司法协助、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等(第43、44、45、46、48、49条)。《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的国际合作义务,并详细阐明国际合作的领域和方法(第43条)。
4.资产追回机制
《公约》第5章规定“资产的追回”。返还资产是《公约》的一项基本原则,缔约国应当进行最广泛的合作和协助(第51条)。资产追回机制包括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财产、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等(第52—57条)。
5.履约实施和监督机制
《公约》第6章规定“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具体包括培训和技术援助,有关腐败资料的收集、交流和分析以及缔约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等内容(第60—62条)。
《公约》第7章规定“实施机制”。《公约》规定应当设立缔约国会议,“以增进缔约国的能力和加强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从而实现本公约所列目标并促进和审查本公约的实施”(第63条)。
三、我国刑事立法与《公约》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
储槐植教授提出刑法的合理立法模式是“严而不厉”。“严”是指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是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㉑。我国刑事立法关于腐败犯罪的规定被有些学者概括为“不严而厉”,即“法网不严密,惩罚过于苛重”。一方面,对于腐败犯罪的规定法网不严密,入罪门槛太高,没有将一部分应该规定为腐败犯罪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另一方面,过于看重死刑在惩治腐败犯罪中的作用,可能会有失公正和人道㉒。笔者认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立法进程经历了“法网逐渐严密,刑罚日益苛责”的过程。
(一)反腐理念层面:我国“重刑反腐”刑事政策与《公约》对于腐败犯罪的“零容忍”基本一致
不能否认的是,近年我国的反腐力度空前,效果显著。然而,从法律角度审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其一,过于强调刑事手段反腐,配套制度的构建却势轻力微,难以从本源上防止腐败;其二,反腐过程中扩张刑罚权,可能会导致有限司法资源对腐败犯罪治理的低效配置;其三,过分迷信刑法功能,可能会导致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其四,某些刑事立法规定过于仓促,实际适用效果存疑。王岐山书记曾经说过,要把坚决惩治腐败、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工作目标,采用多种措施使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㉓。笔者认为,对于腐败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最为有效的方法是构建全方位的预防性制度。
相比较而言,《公约》对于腐败犯罪持“零容忍”的态度,没有具体规定构成腐败犯罪的具体数额和具体情节,入罪门槛很低。例如《公约》第17条㉔关于公职人员涉及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的规定中并无具体数额和情节的要求。可见,在理念层面上,我国与《公约》的反腐败态度基本一致。
(二)犯罪构成层面:《公约》的规定更为细致严密
首先,我国对于贿赂犯罪的主体规定不如《公约》严密。以受贿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㉕。《公约》则规定贿赂犯罪的主体包括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相比较而言,我国刑事立法对于贿赂犯罪的主体没有《公约》规定的范围广泛。
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范围比《公约》规定的范围狭窄。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的范围是“财物”,包括有形的财物和无形的财产性利益。《司法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则是指能够用货币衡量的物质利益或者需要用货币支付的其他利益。而根据《公约》第15条、第16条和第21条的规定,贿赂的范围是“不正当好处”。“不正当好处”是个范围广泛的概念,既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例如性贿赂、安排子女就业等。可见,《公约》对于贿赂范围的规定要广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
再次,就受贿罪而言,《公约》对受贿罪的处罚门槛更低。《公约》规定本国公职人员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贿赂,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㉖。虽然《司法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了扩大解释,但仍然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限制条件。
(三)犯罪预防层面:我国刑事立法缺乏《公约》关于预防性措施的规定
我国刑事立法对于腐败犯罪规定了具体的犯罪构成及量刑标准,缺乏《公约》对于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规定。例如,《公约》规定建立专门的预防腐败机构;建立透明、竞争、客观的公共采购制度;建立公众与国家机关的联系通道;制定私营机构廉洁的标准和程序;开展反腐败的公共宣传活动;打击洗钱活动,监控可疑账户;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刑事立法所欠缺的。
四、完善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建议
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颁布,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开始施行,我国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逐渐完善。笔者认为,对于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还有必要提出一些完善建议以供刑法学界同仁探讨。
(一)审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笔者不赞同对贪污贿赂犯罪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虽然政府强势反腐的势头不减,但就贪污贿赂犯罪的本质而言,其仍然属于贪利性犯罪。犯罪人的生命权益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之间具有不对等性,对贪污贿赂犯罪人适用死刑违背了法益对等原则。这方面的相关论文著述较多,在此不再赘述。
(二)适度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
关于终身监禁的设立意义和价值,笔者赞同赵秉志教授的观点,终身监禁一方面有助于消解民众对严重腐败犯罪适用死刑的渴望,另一方面可以防止轻纵严重的腐败犯罪者,是融宽严于一体的新举措㉗。笔者主张,终身监禁不应当局限于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对于严重暴力犯罪和非致命性暴力犯罪也可适用,其严重程度介于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之间。笔者认为,终身监禁制度应当以立法列明方式在刑法总则中进行专门规定,不赞同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规定。这样可以弥补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的“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问题,也可以减少和限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三)构建公职人员廉洁信息和情报监督制度
笔者认为,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才是预防腐败的根本之道。应当建立公职人员廉洁信息和情报监督制度,加大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具体包括:(1)应当明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范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应仅限于公职人员本人及配偶,还应当包括其近亲属,防止其利用子女出国留学或其他近亲属做生意等进行变相洗钱或转移非法财产。(2)应当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对其公务外活动进行限制。现在我国已经有类似措施实施,例如对于领导干部出国等公务活动进行时间和行程的限制等,这类措施已经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3)应当完善预防性措施和综合治理方式。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公民在打击腐败犯罪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控告、举报和申诉的宪法权利,充分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有效打击腐败犯罪。
(四)注重《公约》规定,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
腐败犯罪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常见性犯罪,为有效打击腐败犯罪,许多国际组织都做出了积极努力。例如透明国际,这是个非政府机构、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此外,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都积极支持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活动。我国应当加强与这些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开展国际协作,例如情报交流、人员协助遣返、资产查封及追回等,及时了解国际反腐败的动态,最大限度地打击腐败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维护公平正义。
注释:
①《两高:对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合法合规》,http://news.workercn.cn/610/201604/18/1604 18132608998.shtml,2017年6月3日访问。
②数额分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档次;情节分为“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三个层次。
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将这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5000元调整至3万元,“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300万元以上。该《司法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条件,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④LUIGI ALIBRANDI,Codice penale e di procedura penale e leggi complementari,op.cit.,p.207,Casa Editrice La Tribuna,Piacenza,2015.
⑤LUIGI ALIBRANDI,Codice penale e di procedura penale e leggi complementari,op.cit.,p.210—211,Casa Editrice La Tribuna,Piacenza,2015.
⑥杨尚文、吴凤:《〈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的立法完善》,《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日,第6版。
⑦参见《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⑧⑬刘霜:《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研究》,《西部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
⑨《“终身监禁”入刑扎牢反腐制度“笼子”》,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5-08/26/content_1944447.htm,2016年5月11日访问。
⑩即“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⑪《立法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⑫《立法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⑭蔡晓:《〈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本情况以及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影响》,《党建》2005年第12期。
⑮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against Corruption,Article 1.
⑯根据《公约》第2条第1项的规定,公职人员包括:(1)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是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
⑰⑱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Article 2.
⑲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against Corruption,Article 6,9,10,12,13 and 14.
⑳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Article 15—18,Article 30—35.
㉑储槐植:《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㉒贾凌、张勇:《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衔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㉓《王岐山“三不腐”彰显反腐信心和决心》,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1018/c241220-23251857.html,2016年5月16日访问。
㉔《公约》第17条规定:“公职人员为其本人的利益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的利益,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其因职务而受托的任何财产、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公共证券、私人证券或者其他任何贵重物品,构成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罪。”
㉕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受上述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㉖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629页。
㉗赵秉志:《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
On the Legisl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and China’s Criminal Legislation
Liu Shuang,Lü Xing
In recent years,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o punish corruption,and the relevant criminal provisions of corruption are revised timely.The specific legislative chang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contents:perfecting 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for corruption and bribery;increasing the punishment of bribery;adding“the Crime of Offering Bribery to Influential Persons”and setting up life imprisonment system(without commutation and parole)for the criminals of serious corruption and bribery who are sentenced to death penalty with reprieve of two years.The punishment against crimes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amendment,but also needs to learn from foreign mature legal experience.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legal document for punishment against corruption in the world.The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ve connection between UNCAC and China’s criminal legislation will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 sound system to punish and prevent corruption.The four contents include:applying death penalty cautiously,exp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imprisonment(without commutation and parole)properly,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public officials’integrity information.
Corruption and Bribery;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Life Imprisonment(without Commutation and Parole);the Legislative Connection
D9
A
1007-905X(2017)09-0066-06
2017-05-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FX056);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FX017);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180JCZD-003)
1.刘霜,女,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河南大学欧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意刑法学双博士;2.吕行,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编辑 潭 影 王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