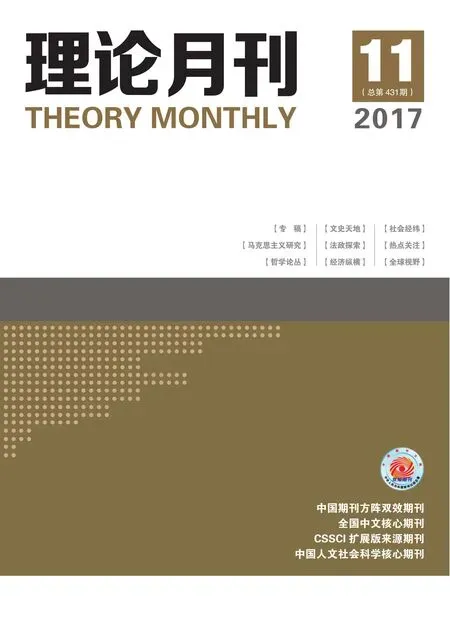利益变化中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形态变迁、影响机制与发展路径
2017-03-07桑建泉
□桑建泉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利益变化中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形态变迁、影响机制与发展路径
□桑建泉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是利益关系变化、协调与重构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先后历经动员式参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主动式参与、渐趋理性化参与等三种不同发展形态。利益变化是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生基础与发展动力,其通过影响基层民众参与心理、基层民众参与模式、基层参与制度、基层管理组织、基层参与文化等机制作用于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发展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须顺应利益变化促成基层参与式民主发生、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完善有利于民众利益实现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度、丰富有利于民众利益维护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形式、规范基层民众逐利而为的参与行为、构建参与型基层政治文化。
当代中国;利益变化;基层参与式民主
民主的发展是利益关系协调与重构的过程。作为民主重要形式的一种,参与式民主的成长与发展也不例外。参与式民主更多地强调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现实参与,然而多数国家疆域庞大、人口众多的现实又注定了其无法全面施行的“宿命”。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小、统辖人口少的特质为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在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是利益关系变化、协调与重构的过程。利益关系变化通过影响民众的参与动机和参与行为直接推动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发展参与式民主为当代中国基层的繁荣输入新鲜养分。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充分发展基层参与式民主,并从顶层设计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制度建设和路径构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呈现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与良好的发展态势。
1 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形态变迁
在当代中国,尽管基层参与式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利益关系变化始终在其形态变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层参与式民主先后历经动员式参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主动式参与、渐趋理性化参与等三种不同的发展形态。
1.1 动员式参与
动员式参与是指具有权威力量的组织和个人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经济目标而动员普通民众进行参与的一种政治模式,它“以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运动为参与的基本形式。”[2]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当代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员式参与时期。共和国成立之初,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动员式特点,镇压反革命、三反运动、五反运动、一化三改、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都是这一时期动员式参与的典型表现。国家“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骤,获得了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3],具备了资源调配、利益协调等方面的巨大能量。基层社会对国家产生了高度依附,基层民众则处于一个个内部功能齐全、外部边界明晰的蜂窝状单位中。革命战争时期的动员力量、动员机构、动员经验在动员式参与时期得以保留,并继续对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2 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主动式参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系列决议终止了新中国成立后官方一直倡导的动员式参与形态。之后,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进入调整恢复和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村民自治、社区自治、职工代表大会的迅速发展成为标志性事件。经济领域的改革顺应了人民群众期待,为主动式参与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不同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整体社会环境更加民主活泼。农业产量的增加,既为农民提供了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物质实惠,也使得广大农民于对比中意识到政治口号的空洞性。在城市,企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在逐步展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现代化改革已成为势在必行之举。众多单位在日常管理与生产中不断采取“放权让利”措施,责任制、承包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司化改革浪潮即在此种背景下具体推进。毋庸讳言,伴随着经济领域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实施,基层民众的自主意识、利益意识、参与意识空前高涨。
1.3 渐趋理性化参与
到党的十六大时期,我们党和政府能够以更加理性及务实的态度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均衡,参与式民主的渐趋理性化时期自然也如约而至。一方面,基层民众更广泛地通过选举、加入政党、同基层官员直接接触等形式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党中央不断加强对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制度设计。党的十六大强调“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十八大更是有针对性地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发展基层参与式民主的方向与途径。此外,党中央还相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的现代化理念,为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健康持续发展指明了价值引领。
2 利益变化对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影响机制
利益变化是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生基础与发展动力,其通过影响基层民众参与心理、基层民众参与模式、基层参与制度、基层管理组织、基层参与文化等机制作用于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
2.1 利益变化对基层民众参与心理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等级森严的异化剥削制度被全面废除,公平、平等的社会制度得以建立。政治层面,民众之间相互平等,享有相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层面,农民分得土地,城市居民得以在新单位、新工厂参加工作。依靠新制度和政策的强大说服力,基层民众体会到了旧时代遥不可及的“平等”社会氛围,在心理上产生对党和政府的极高信赖(regime-based trust[4])。计划经济末期,由于长期感受不到辛勤付出的收获感,基层民众对动员式参与逐渐失去信心。改革开放以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广大基层民众产生追求、保障自身利益的心理。与利益均平时期人民对利益避而不谈的情况截然相反,利益分化时期追求并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潮流。一切行为的背后,总有个人的这种利益[5]。基层民众越发积极地参与到政治发展进程中,而利益追求及利益差别所产生的驱动则成为促进基层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源动力。
2.2 利益变化对基层民众参与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式参与模式依靠自身的独特功能,适应了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巩固,动员式参与民主逐渐失去成长和发育的土壤,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主动参与模式成为主流。利益多元化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是公众和社会的参与需求,特别是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之中[6]。此后,利益驱动下的非理性化参与导致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在发展过程中,民众逐步意识到利益追求并不是公共生活参与的唯一目标,而良善社会的构建、自由和解放的达成才是民主参与的最终目标追求。利益均平时期,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模式是动员式;利益分化时期,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模式是主动参与式;利益整合时期,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模式则更加成熟与理性。实际上,基层民众越来越愿意以成熟、理性的态度融入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实践,在有序参与中实现预期的利益诉求与合理目标。与此同时,基层民众对结社权日益珍视,他们以结社的方式维护自身及群体的利益,通过增量民主的形式活跃基层民主参与的力量组成。
2.3 利益变化对基层参与制度的影响
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国家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民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当时的实际基层政治生态中,乡、村两级组织之间是上下级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依靠严密组织制度的运行,国家能够控制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对基层的过度干预限制了基层活力的发挥、挤压了基层社会的自主发育空间,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又使得实际情况不同的基层地方在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基层利益关系的现实变化,基层民众不断表达自我管理的政治需求,而通过制度化方式保障并持续维护基层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也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基层民众政治参与的自治性质,为基层民众行使参与权利、规范参与行为提供了制度规范与指导。近年来,部分基层地区更是创新并确立了“公推直选”的参与制度①四川省步云乡由乡镇居民直接投票选举乡镇长,大鹏镇和卓理镇则分别采取“三票制”(村民、干部村民代表和镇人大代表分别投票)和“两票制”(干部村民代表和镇人大代表分别投票)选举镇长,并要求乡镇长候选人进行选举宣传和竞选演说。。
2.4 利益变化对基层管理组织的影响
在基层组织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主要依赖人民公社。与此相应,城市主要依赖单位、街道和居委会的互相结合。人民公社是一个复杂程度很高的组织体,其不仅具有行政管理职能,还具备日常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其它职能。在城市,国家利用党政军机构和事业单位以及工厂对居民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身处此类单位之外的其他居民则由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共同进行管理。一些规模较大的单位拥有家属院、学校、医院,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基层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分化,“全能型”基层管理组织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以人民公社为例,其“缺乏激励机制”[7]的弊端不断暴露。伴随市场地位与规律的不断强调与尊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在当代中国拉开序幕。从依附型向自主型的社会转型,由整体型向流动型的社会转向对基层组织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村委会、社区等机构在基层管理实践中不断发挥出自身的特有优势。
2.5 利益变化对基层参与文化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宣扬“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将政治神秘化,强调民众要“忠”于君主和国家,从而生产了“臣民”政治文化。由于封建等级制的存在,普通民众自由谈论政治尚不可能,更没有机会亲自参与政治进而影响政治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一跃成为国家的主人,经济基础变更带来的利益变化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政治文化滋生的土壤。原来存在于旧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彻底废除,“臣民”政治文化的消失与“公民”政治文化的培育建构成为发展必然。同“臣民”政治文化相比,“公民”政治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公民”政治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的平等关系,强调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双向义务。对当代中国的基层民众而言,“参与是参与式民主的逻辑起点”[8]。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和维护自身合理利益,培育并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已成为基层民众重要的公共生活方式。
3 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路径
发展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须顺应利益变化促成基层参与式民主发生、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完善有利于民众利益实现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度、丰富有利于民众利益维护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形式、规范基层民众逐利而为的参与行为、构建参与型基层政治文化。
3.1 顺应利益变化促成基层参与式民主发生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要实现发展,需不断调试自身内部结构与模式,主动顺应利益关系变化的要求和趋势。第一,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要能够适应参与主体的利益需求。参与主体是参与式民主发展过程中的能动因素,其直接参与和推动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利益关系变化的情况也会在参与主体身上得到现实和客观的反映。参与式民主要得到健康发展,参与主体正当的利益诉求不应被压制和忽视。相反,在参与式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应得到重视和保障。当基层民众意识到参与紧密关联着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介入公共生活,“充分地将自身的利益要求表达出来”[10]。第二,参与式民主自身制度体系中应有与利益关系变化相适应的内容。参与制度作为参与式民主静态构成中的关键部分,是参与式民主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参与制度的内容构成又是参与式民主实践在静态上的直接反映,对参与式民主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因此,参与式民主中的制度部分要与利益关系变化相契合。第三,参与式民主要能够及时消化与吸纳利益关系的新变化。利益关系变化因为直接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渐变性、复杂性等特点。针对不断出现的利益关系变化细节,参与式民主要能够主动反映并消化之,在发展完善中与利益关系变化保持动态平衡。适应利益关系的变化,是参与式民主能够发展的基本前提。
3.2 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
回顾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利益关系得到较好协调的时期就是参与式民主健康发展的时期,利益关系的失衡总是为政治参与的无序与混乱提供温床。协调利益关系涉及的影响范围广、关涉的民众数量大,对参与式民主良性发展意义重大。首先,健全利益分配制度。利益分配制度作为政策层面的“调节器”,直接规定具体的利益分配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利益分配政策的调整经历“利益均平”“利益分化”“利益整合”三个时期。实践证明,利益关系调整要在适应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以激发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其次,拓宽利益分配参与渠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一次次地刷新了政治文明的新高度。参与利益分配过程进而享有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红利,是民众极为重要的权利。构建并拓宽由基层民众直接参与的利益分配渠道,是参与式民主精神在分配领域的重要体现。正如达尔所说:“你想防止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受侵害,你就只有充分参与到政府行动的决定当中去”[11]。基层治理机构要树立现代化治理理念,充分认识民众参与利益分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基层治理者还需提高治理能力,发挥参与渠道能够容纳基层民众利益诉求的功能,及时输出相应的利益分配政策。再次,做好利益协调配套工作。利益分配制度的运行、利益政策的执行,利益呼声的整合输入与消化输出,皆需要具体个人去执行和操作。利益政策的实施对相应群体的素质与能力提出很高要求,执行者既要在原则问题上坚守底线,又要在具体问题上灵活创新,切实保障基层民众的现实利益。
3.3 完善有利于民众利益实现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度
作为现代化治理制度的一种,参与式民主在事实上影响着利益关系的调整。现代化治理的目标是民众幸福获得与利益获取的实现,以参与式民主制度引导并规范民众的参与行为是基层趋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公民个人以及共同体的利益”[12],完善有利于实现民众正当利益的基层参与民主制度,需要把参与精神“内嵌”到民主制度运转的全过程。一是要健全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权利法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法律为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提供依据和保障,可以有效维护民众的参与权、监督权等。二是要逐步完善基层直接选举制度。在充分发挥现有基层选举制度功能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基层直接选举的范围,丰富和创新基层党委书记(支部书记)、人大代表、政府官员的产生方式,让实现和保障民众正当利益成为候选人出任职位的决定性因素。三是要加强民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监督权。“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13]。民众监督权的加强,能够有效制约基层治理机构在运行中出现的权力 “任性”与权力“扩张”弊病。此外,监督权的行使还能防止基层治理机构偏离维护民众利益的“轨道”。伴随以村务公开为基础的基层公共事务公开、财务预算及财务收入支出公示、以及民主问询权、罢免权、举报权等工作的逐步加强,基层民众监督权的行使日益常态化。四是要完善事后矫正制度。参与式民主能广泛汲取集体智慧,最大限度避免相关制度与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的可能损失。现代社会的高度异质性、社会转型期的危险随机性等不确定因素给基层参与式民主带来大量潜在风险。因此,加快和完善参与式民主制度的事后矫正制度建设显得必要且迫切。
3.4 丰富有利于民众利益维护的基层参与式民主形式
民主形式是民主精神的外在体现。尽管民主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即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决定自己的事务[14]。不同于民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民主形式在符合民主精神、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自我革新。完善参与式民主形式,一方面要顶层加强设计,另一方面要锻炼并提高基层民众的实际参与能力。一是,稳定并创新基层自治的民主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实行居民自治的治理模式,即通过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的自主权,让基层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有学者在总结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微观自治的模式,即“将自治范围不断下移让自治内容更具体化,使自治方式趋于细化;赋予自治主体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功能,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治水平与创新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5]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基层自治实现了其调动民众积极性、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可以预见,基层自治在今后的基层治理中仍将发挥关键作用。二是,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功能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逐步发挥,基层社会在利益关系领域出现了主体多元化趋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个体与企业之间、集体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非常敏感。尤其是城镇化的推进,拆迁、征地、市政建设等措施的施行,使得原本就特殊的利益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协商民主通过事前的谈判与协商,能均衡各方利益需求与缓解各方紧张利益关系,有效地减轻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三是,创新发挥电子民主的优势。“互联网时代”给基层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便捷,也给参与式民主的形式创新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可以提高公民政治认同的程度;而提高公民政治认同的程度,就可以保证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16]。如何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化工具有效地组织并调动民众积极性,发挥其汇聚民意、汲取民众建议的功能是摆在基层治理机构面前的重大课题。网上办事大厅、政务微博、政府公共微信号的设立反映出政府在互联网时代主动适应发展趋势的努力。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理念、经费等原因的掣肘,电子民主远没有发展起来。运用好互联网的中介载体优势,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与利益关系协调意义重大。
3.5 规范基层民众逐利而为的参与行为
利益关系变化对参与式民主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民众对正当利益的追求符合人性规律,但对利益的过于关注和投入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唯利益论容易引发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甚至酿成“参与分裂”。可见逐利而为的参与行为危害极大,必须有意识地加以规范和引导。首先,发挥价值规范对民众逐利行为的引导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事事谈价钱”“只认钱不认人”等广为诟病的风气在社会上出现并逐步蔓延。要改变这一局面,需充分发挥价值规范的作用,引导基层民众客观理性地看待利益,“社会主义不是不讲利益,而是不讲绝对个人主义的利益或片面的社会利益,强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17]不可否认,利益追求在社会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精神追求在丰满人生、促进人全面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样巨大。其次,加强法律对民众逐利参与行为的规范作用。利益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发人的谋私心理,政治参与过程中因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需要运用法律进行规范。此外,对利益获取过程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法律也要作出相应规定进行保障。再次,培育民众现代化的参与理念。利益追求固然是民众民主参与的基础,但此种追求并不是盲目妄为,而是现代化理念引领下的理性政治行为。基层民众通过有序参与才能在公共生活中获取参与满足感,收获参与快乐。民主是“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18],基层民众的公共生活参与行为同样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3.6 构建参与型基层政治文化
构建参与型基层政治文化,首先,要增强基层民众的参与意识。参与行为具有明确目的性,产生于参与意识的驱动。参与行为并非先天自然形成,只有“学得民主的规范和政治游戏规则”[19]并将其内化为有序参与意识,基层民众才能养成现代参与的行为习惯。其次,加强现代参与理念的宣传。应充分利用学校、基层会议、图书室等公共平台对现代参与理念进行宣讲和阐释,让现代参与理念深入基层民众内心。再次,建构科学的参与制度。没有制度保障,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就会过多依赖主观性、偶然性因素。制度化的参与式民主将有序合法的政治参与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基层民众的参与“‘扩大’与‘有序’相统一,扩而不乱,大而有序”[20]。最后,创造有利于建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外部环境。和谐利益关系为基层民众的参与提供经济基础,《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为基层民众的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党的领导为基层民众的参与提供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参与型基层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良好政治生态。
4 结语
利益变化与参与式民主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关联,利益关系变化对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影响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以利益变化之维构建促进基层参与式民主发展的路径策略,不仅有利于科学、合理地调整利益关系,更有助于深入地理解民主真谛,化解民主形式与实质间的困境,促进当代中国基层参与式民主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 ”[21]
[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02).
[2]梁军峰.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研 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107.
[3]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8.
[4]TIANJIAN SHI.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266.
[5]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3.
[6]郭道久.民意表达与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机制创新[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26.
[7]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3):37.
[8]李波,于水.参与式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J].理论与改革,2016(6):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10]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9.
[11]达尔.论民主[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5.
[12]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65.
[13]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14]林尚立.民主与民生: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19.
[15]赵秀玲.“微自治”与中国基层民主治理[J].政治学研究,2014(5):53.
[16]郝丽,崔永刚.网络政治参与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和对策研究[J].新视野,2014(4):62.
[17]刘世明.树立正确的利益观[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
[18]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8.
[19]梅萍.论公民的主体意识与现代公民教育机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98.
[20]崔浩.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及其实践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8):66.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04.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1.026
D638
A
1004-0544(2017)11-0154-5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5AKS003)。
桑建泉(1989-),男,河南浚县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