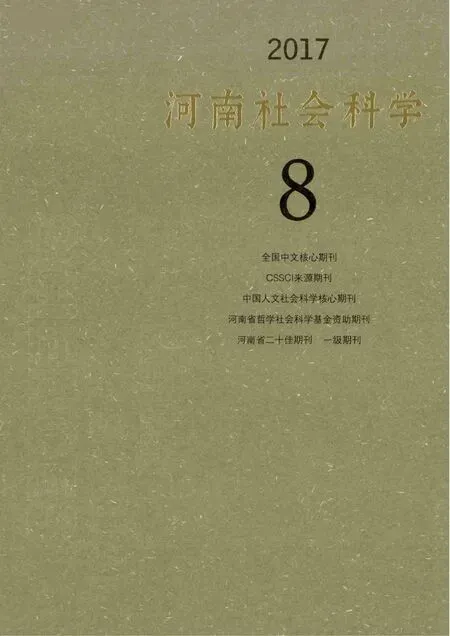人民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的机制研究
2017-03-07张丙宣
张丙宣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人民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的机制研究
张丙宣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如何通过精准介入基层协商,有前瞻性地引领基层社会的变革,巩固基层政权,是当前人民政协面临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但是,长期以来,政协协商往往表现为合法性有余而有效性不足,也就是说,政协协商不能有效地应对转型社会的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它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介入协商的方法与机制。近年,合作治理理论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民政协精准介入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技术。精准介入是在近年跨部门合作、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经由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的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开发的一种新型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该模式为探讨人民政协履行职能,解决转型社会的突出问题,巩固基层政权,提供了新思路。
在人民政协介入基层协商的问题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基层协商民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认为,我国基层协商具有内生性、民主价值取向和发展实践取向的特征。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协商民主用于调控对话性政治和工具性政治之间的张力,其重心从投票选举转至公共领域治理①。研究认为,政协协商内生于中国社会②。它拓宽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领域③,让基层治理运转起来,成为推动基层社会发展的实践形式④。其次,人民政协工作创新的研究。近年,人民政协创新的研究从理论转向实践,从高层政治延伸到基层治理,从提案延伸到建立协商平台。譬如,北京市创新省际政协联合⑤;杭州市建立政治协商“两个纳入”制度,健全政治协商的督办落实制度,建立民主议事会制度、议事协商制度和政协委员担任村务顾问制度;各地还建立基层委员工作室、委员联络室、委员网上工作室,建立民情对话、民情问政等网络议政平台;湖北宜昌政协搭建的“两进两问”载体、建立的“四请两公开”制度⑥。
这些研究表明,人民政协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的实现模式、条件和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尤其是需要研究人民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的技术与手段。为此,本文在反思政协基层协商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合作治理理论深入挖掘和整合人民政协、党政部门、民主党派、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内生的组织和制度资源,探索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的模式、实现条件和实现机制。
二、政协协商的基层实践与反思
近年,在中共中央不断强调政协应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背景下,各级政协逐步将政协组织和服务延伸到基层社会。然而,政协协商的基层实践具有显著的碎片化特征。碎片化介入造成政协协商效果不佳。
(一)政协介入基层协商的方式
人民政协通过延伸机构、促进界别合作、创新履职载体以及强化政协监督等方式,不断介入基层治理。
1.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
将组织延伸到基层社会,是政协介入基层协商的基础。虽然,政协建立之初只是中央层面的爱国统一战线,但是,政协不断向下延伸。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县级政协组织陆续在乡镇设立政协联络处或政协工委。2003年5月,天津市河西区正式在街道设立政协委员活动组,并在社区建立政协委员社区联络站,形成区、街、社区三级政协组织网络。2011年江苏的苏州、无锡、南京、扬州等市,在乡镇(街道)成立政协联络委员会或政协工作委员会。浙江的嘉兴、杭州、宁波、湖州等在此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工作室主任配备上,有的地方配备专职主任,有的则由党工委副书记兼任,也有些地方由纪委书记或其他党委委员兼任。
2.促进界别合作
目前,政协主要通过促进界别合作、整合政协内部资源的方式开展基层协商。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强化专委会的纽带功能。譬如,浙江省岱山县政协通过强化专委会的功能,使每个专委会联络2~3个界别。5个专委会把各个界别工作整合起来,在年初安排工作时把界别活动纳入专委会活动计划,推动各界别联合开展视察、调研,形成“三联系、三服务”的社会服务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界别集体提案或建议。二是推动界别合作。譬如,嘉兴市秀洲区政协把特色相近的界别组织起来,围绕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活动,建立“界别专题约谈会”制度,促进界别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2010年到2013年6月,区政协围绕农村无害化改厕、农村食品安全、教师队伍建设、安全生产、水环境治理、学前教育、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四边”绿化等主题开展了10余次“界别专题约谈会”,为促进民生问题解决建言献策。
3.创新介入方式
近年,各地政协积极创新基层协商的新载体和新平台。譬如,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建立了“政协委员工作室”,集中政协委员的力量倾听基层民意、收集社情民意、组织专题协商,通过调研整理社情民意、提案上报党委政府。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小营小组自发建立“委员进社区,协商365”的工作机制,将35个政协委员分到12个社区,扎根基层,将委员负责的专业领域与社区居民的诉求相匹配,推动委员与居民的互动。创立协商平台,建立“动迁圆桌会”,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动迁各方协商,化解拆迁矛盾。创新委员服务群众的新机制,建立“周末有约”“公益众筹会”,建立“南星委员e家”网上履职新平台,将政协履职由线下拓展至线上。线上平台关注民生和环保,线下成立两处委员履职的“e家驻点”。委员每个季度都与居民进行面对面对话,收集社情民意。近年,委员网络工作室在沟通民意、参政议政以及民主监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各地政协广泛采用。
应该指出,一定程度上,人民政协积极创新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的制度,有助于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然而,政协协商的基层实践仍然以传统粗放的碎片化方式为主。这种方式既不能充分整合政协内部各行各业的资源,也不能跨界整合人大、社会等资源展开精准介入,只能进一步强化碎片化的介入模式。
(二)碎片化介入的制度分析
人民政协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的碎片化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多年来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未能取得大的突破和进展。与此同时,政协委员履职方式缺乏严格清晰的专业规范和责任清单。政协委员的职能与履职方式相互混淆,导致政协委员履职的过程中产生诸如这样的疑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多少?由政协委员来做还是政府职能部门去做,还是由党委去做?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人民政协的碎片化介入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处于弱激励下的政协委员介入基层协商的动力不足;不同平台的主管部门之间协调的困难;党委、政府的运动式治理也带动了政协的运动式介入。
1.弱激励与政协委员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政协委员的弱激励机制导致了他们采取碎片化方式介入基层协商的行为。周雪光等人指出,弱激励行为具有完成任务逻辑、激励逻辑和政治联盟逻辑的特征。直接介入基层协商的政协组织主要是县级政协。县级政协介入的弱激励表现为:一是完成任务逻辑。政协对专委会和委员考核的性质是政治性的,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县级政协对政协委员考核的首要目标是完成党委和上级政协交办的各项任务,必须帮助专委会和政协委员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二是激励逻辑。县级政协对专委会和政协委员的考核,强调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要体现差距,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三是政治联盟逻辑。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政协发挥着联系群众、团结各界的纽带作用,政协与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精英形成政治联盟。因此,具有弱激励特征的政协分散介入基层协商的行为,与具有强激励的政府经济部门的行为形成互补,保证了权力行使的灵活性。
2.不同平台协调的困难
虽然基层社会并不缺乏沟通协商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隶属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各主管部门开展协商时各自为政。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协的协商平台多,但是缺乏整合。几乎每个界别、专委会都有单独的协商平台,有些是界别内部、专委会内部的平台。有些是跨界别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联合开展协商的情况并不多见。二是由基层政府主管的平台聚集了多个部门的力量。有些平台不仅仅是政协收集社情民意的平台,也可能是人大、街道、区民政局收集民意、化解纠纷的平台。这些平台是多部门多层级党委、政府以及政协开展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综合性平台。这类平台不太可能与其他平台整合。三是尽管多个协商平台之间也有零星的合作,但是在基层协商中,这样的自发性合作并不多见。基层协商平台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整合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基层协商平台的专业化容易造成碎片化;二是平台越小越容易开展互动,平台越大开展集体活动的难度越大,搭便车的心理越强,欲合作则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行政化。
3.政协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有助于打破既有制度安排,在短时间内通过政治动员集中跨组织跨部门的资源迅速实现某一特定目标任务⑦,它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的常态治理行动。近年,政协的运动式治理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介入基层协商,主要表现为:一是服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而开展的运动式服务。为了顾大局,政协主动融入当地党委、政府的全局工作中,围绕诸如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环境整治等阶段性和迫切的任务,进行短期的集中的协商、调研、建言献策。二是组织政协委员集中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县级政协往往开展“界别活动周”“政协服务周”等活动,在短期内集中多个界别几乎全部的委员走上街头,深入村(居)、企业、学校,开展送科技、送法律、送医药、送教育、送文化、送温暖、捐资助学等活动。政协开展运动式服务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协的运动式服务直接受到党委、政府的运动式治理的影响;二是多个职能部门专业分工,增加了组织协调的难度,运动式治理则是应对这种危机的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各级政协碎片化介入并未提高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并未有效地促进政协履行协商民主、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功能,并未能完全满足党委对政协的期待和要求,进而导致介入的效果不佳甚至是“脱靶”。因此,必须变革人民政协的介入方式,实现从分散的碎片化介入向多元协同合作的精准介入转变。
三、精准介入:一种基层协商类型
精准介入既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公共管理方式,还是一种治理体制。人民政协的精准介入是政协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技术工具,也是政协参与公共治理的方式和治理体制。与党政部门相比,政协的精准介入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协的精准介入是精准地发现问题、精准地诊断问题、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不是直接精准地解决问题。政协有发挥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智力优势和超脱的政治地位。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政协有条件开展跨界跨部门的合作。这些因素使政协具备精准地发现、诊断问题和提出精准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但是,人民政协既不是领导机构,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执行机构。因此,政协的精准介入不是直接高效地解决问题,而是为高效地解决问题提供精准的信息和备选方案等。
其次,政协的精准介入不是无条件的。政协的介入既可以由一个或几个委员直接单独介入,也可以在多个界别开展合作介入,还可以与党政部门相互嵌入。然而,要达到精准的效果,任何形式的介入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党委、政府不反对政协介入,或者对政协参与基层治理感兴趣,向政协赋权,并让渡部分决策权,而且信守承诺;政协委员对基层治理感兴趣并有良好的动机和广泛的个人影响;政协通过介入基层有助于促成党委、政府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再次,在基层治理中政协扮演催化剂的作用。与党委、政府不同,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该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即有充分的时间、资源和技能把利益相关方结合起来,推动多方以合作的精神参与协商。政协可以设置明确的合作规则、聚焦于推动和维护合作,并对整个合作过程进行管理。为确保合作,政协有权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可信的和有说服力的决定。政协的催化作用还表现为促成居民与党政机关的良性互动,以促成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受益者的衔接,拓宽居民与政府沟通的渠道,提高党委、政府的响应性和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简言之,政协的精准介入是精准地把握和诊断问题,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精准地决策和解决问题。政协的精准介入需要党委、政府的授权,政协在介入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
四、人民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的模式
碎片化介入导致人民政协既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也不能为党委、政府提供精准的解决方案。为此,在政协介入基层协商的空间和边界内⑧,必须创新介入方式,提高介入的精准度。根据介入主体的规模和方式的不同,即一个主体的直接介入,多数主体的松散介入,多数主体之间紧密嵌入,可以简单地把人民政协介入基层治理和基层协商分为直接介入、松散合作介入和紧密嵌入三种模式。
(一)直接介入模式
针对传统政府责任体系和集中供给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由政协或政协委员直接介入基层治理,开展基层协商,被认为能够巩固民主政体,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本质上,政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是参与式治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参与式治理中,人民政协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
直接介入模式依托于政协延伸到基层的组织——政协委员工作室或政协委员网络工作室。县级政协在乡镇(街道)或社区建立政协委员工作室或者政协委员网络工作室。通过该平台,委员能够常规性地深入基层,掌握和反映社群民意,主动发现问题,并向党委和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当然,委员工作室既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也不是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政协的直接精准介入是政协委员主动自愿自主履职的行为。这种介入主要是单个委员或多个委员轮流到工作室,或者进入社区或村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群众代表座谈会;越来越多的委员运用“互联网+”委员履职的方法,建立委员网络工作室。把网上工作室、视频对话与网下实体工作室。面对面对话对接,延伸和拓展介入的空间,精准地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
单个或多个委员直接介入基层治理能否达到精准的效果,与很多因素相关。这些因素至少分为三类:一是政协委员个人意愿与技能。政协委员个人必须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民服务的良好意愿和长期坚守、耐心与主动服务的热情;掌握相关的政策法规,熟练运用与居民打交道的技能和处理基层社会棘手问题的方法;在本地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威望。二是社会资本的大小。一个地方的社会组织的规模、组织之间的关联性程度、人们之间的信任以及互惠规则的自发运行的情况等社会资本,直接影响普通居民与政协委员直接沟通的意愿与能力,而且社会资本的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协直接介入达到精准的可能性越大。三是党政部门的态度。政协委员的介入受到基层党政部门态度的影响。如果基层党政部门不支持政协委员的工作,那么,毫无疑问政协委员直接介入达不到任何效果。相反,如果基层党委、政府积极支持政协委员介入基层治理,考虑委员以提案、信息、调研报告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或者积极参与政协委员与居民代表面对面对话,接受政协的监督,那么,政协的直接介入的精准程度就会很高。
政协委员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增加了党委、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纽带,被认为能够使制度变得更具有回应性,进而提高体制的合法性。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政协直接介入的模式,可以应用于乡镇(街道)、村庄(社区)层面的民生问题、矛盾纠纷解决以及突发性事件应对。
(二)松散合作介入模式
在政协委员个人意愿不强、能力不足以及地方社会资本有限的条件下,直接介入模式应用范围就非常有限,也十分脆弱。如果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主体,政协协商无法奏效的时候,最普遍的精准介入方式有两类:松散合作的介入模式和紧密嵌入的介入模式。
松散合作强调政策和服务通过多个相互依赖的行为者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由单一行为者决定。在理论上,松散合作是网络化治理(networking governance)或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形态。松散合作的介入模式是“一种治理安排,在这个安排中有一个或多个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或个人一起,直接参与到非正式的、一致取向的集体协商过程中,旨在影响政策制定、执行或公共管理等”⑨。在松散合作的介入模式中,合作者之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等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松散合作是取代管理主义失败和多元主义对抗的替代模式。它的目的是求同存异,而且在实现共同目标上,它既不采取行政化、内部化方式,也竭力避免合作对象之间的对抗。
松散合作介入模式的制度安排是松散的、开放的、包容的。近年,地方各级政协纷纷创新合作方式。其中,与媒体合作建立电视直播的协商平台被各地政协广泛采用。这种方式又称为网上议事厅。譬如,温州市政协的“政情民意中间站”,每周定期举行;每期邀请3~6名党政领导、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代表,围绕共同的热点话题,研讨政情、表达民意、形成共识。这种合作根据协商的话题来挑选党政相关部门的官员、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通过这个平台整合政协、党政和各界别的力量,并在党政、群众和社会各界建立新的沟通桥梁,实现政情下达和民情上传,为委员、社会各界和居民直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供了载体。
松散合作模式能否达到精准介入的效果,也与多种因素直接相关。一是合作的激励。政协与媒体都有合作的激励,政协缺乏有效监督的载体,导致监督薄弱,影响政协职能的履行;新闻舆论监督有较强的影响力,但是它们缺乏政治资源和信息资源的依托。二者通过合作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然而,其他参与者,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是否有参与的动机?受到政策影响的弱势群体是否有参与的能力和动机?如果利益相关者有实现他们目标的替代方案,那么,他们还愿意参与协商吗?因此,松散合作要达到精准介入,必须考虑和动员不为人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替代方案没有吸引力的时候,参与者才可能认真参与到集体协商中⑩。二是合作过程的管理。合作通常依赖于在沟通、信任、承诺、理解和结果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尤其是相互敌视的合作者之间如何建立信任并达成共识。而且,松散合作的管理完全不同于传统组织内部的垂直管理。
松散合作介入模式有广泛的应用领域。政协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合作,与行业、社区等领域的基层协商平台合作。譬如在社区层面,基层政协可以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辖区单位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和“和事佬”、“老娘舅”、律师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社区的民主议事、民主协商的治理平台。
(三)紧密嵌入模式
紧密嵌入模式与松散合作介入模式有诸多共同的特征。譬如,存在多元治理主体及其相互依赖关系、多个平台、介入技术的普遍使用等。但是,与松散合作介入模式不同,紧密嵌入模式则强调整合合作平台和应用行政手段,甚至是内部化,以期达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合作的目的。
在制度设计上,紧密嵌入模式更趋于封闭、等级化和内部化。在运作过程中,紧密嵌入模式除了采取非正式的措施,还建立了常规化的合作规则和约束机制,打破界别之间、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功能分割的状况,高效地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变事后协商和事后监管为事前协商和事前监管,使目标和手段之间相互强化,强调预防性、整合性、效率取向的整体目标。而且,紧密嵌入模式强调打破多元主体之间的功能边界,以建立在政治和行政方面强而有力的等级制组织来实现预期的结果。
紧密嵌入的方式很多,既有政协内部各界别、专委会之间的相互嵌入,整合他们各自的协商平台;也有多类协商平台的相互嵌入,进而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协商平台。这两类协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地方政协的实践中。譬如上海市青浦区政协从内容、形式和主体等方面整合政协内部的各类协商。在协商内容上,把内容相似、相同或相近的协商整合为一个大的协商议题,把多个部门集中起来开展协商;在形式上,把提案办理协商与其他类型的协商合并进行;在主体上,将两个或多个界别活动组召集起来,围绕一个议题与党政领导面对面讨论,开展联组协商议政⑪。另一类是多个协商平台相互嵌入形成一个超级综合的协商平台。譬如杭州市上城区的湖滨晴雨工作室,既是区政府、街道、社区三级观测民意的平台,也是社区民众公共问题的协商平台,还是党委、人大、政协开展各类协商的平台。然而,在多重力量相互嵌入组合而成的超级综合平台上,政协的作用并不明显。它无非是平台的参与者之一,平台则由政府通过行政化的方式建立和运营。
紧密嵌入模式要达到精准介入的效果,除了需要松散合作介入模式的条件外,还依赖行政的持续干预。行政部门的干预体现为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的直接进入、主导和整合协商平台;与党政职能部门对接,能够促成协商结果向公共政策转化。持续的行政干预有助于协商平台完成政府的目标任务,但是干预也容易造成协商平台行政职能的超载,造成党政协商之外的社会组织协商、政协协商功能的边缘化。需要指出的是,紧密嵌入模式与其说是党政部门有意设计,不如说是缺乏社会自生能力的平台自发演进的结果。因为对这些平台而言,保持“碎片化与整合性、个性化和共同身份、生存压力与文化整合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危机管理、食品安全管理、城市政府间的协调以及城市公共设施的利用等方面。
五、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与基层治理的机制
在上述三种介入模式的基础上,人民政协可以从问题的发现与诊断、方案的提出与资源的整合以及介入与退出时机的选择等方面,优化介入方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
(一)精准地发现问题
对政协而言,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精准地发现问题:一是精心设计协商议题。政协要围绕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和当年的重大议题,利用专家集聚和专门协商平台的优势,组织委员加强与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沟通,通过决策前协商、问政协商、项目调研协商、咨询协商、调解协商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协商,全面精准地把握中心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二是有前瞻性地从基层社会发现新问题。政协和政协委员要积极主动地联系基层群众,收集社情民意。在建立政协联络室或政协工作室的基础上,定期进入农村、社区和企业,服务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发现新问题。三是政协委员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开展政协工作,继续巩固和拓展委员网上工作室,创新与群众沟通的新形式,全天候收集社情民意。通过这三种方式,政协能够实现对社会问题进行精准定位。
(二)精准地诊断问题
不仅要精准地发现问题,政协还要从试错诊断向精准诊断转变。为实现精准地诊断问题,首先,基层政协委员要在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社会服务的基础上,每年对下辖的乡镇(街道)做全方位的调研,以村(社区)为单位,通过参与或组织基层协商会议,弄清问题的边界和来龙去脉,着重从问题的发生机制、资源约束、能力约束等方面着手进行动态分析。其次,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政协要与媒体、党政各职能部门合作,借助它们掌握的大数据及其处理技术,实时精准地分析不同类型的人群、不同村社遇到的不同问题和演变的态势。再次,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问题诊断机制。减少政协运动式调研和运动式服务,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用常规化、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方式精准地诊断问题的根源。
(三)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
在精准定位和诊断问题的基础上,政协欲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启动界别协商,精准把握解决方案。在精准定位和诊断问题的基础上,人民政协已经搞清楚了利益各方的意图与底线,譬如民众的意愿、政府的计划、企业的难处,以及各方面问题集中的焦点。围绕焦点问题,政协启动协商程序,促成各方协商对话,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听取对方的意见。在面对面的对话互动中,缩小各方心理预期差距,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二是分类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是复杂的,应该坚持分类解决的原则,凡是在政协职责范围内能够通过对话解决的问题,政协直接介入解决;有些问题在政协职能范围内,但暂时无法解决,选择最容易解决的部分,制定备选方案,将备选方案提交给党政部门。由党政部门牵头,采取行政化手段或松散联合介入或紧密嵌入方式解决。
(四)资源整合机制
为有效地介入基层协商,履行职能,政协应该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碎片化的资源。对基层政协而言,介入基层协商的资源整合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促成政协协商与其他形式协商的有效衔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开展的政协协商与其他渠道的协商均有交集,政协参与基层自治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的协商,采取松散的合作方式整合多种协商平台。其次,加强政协资源与基层民主力量的整合。我国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代表的基层民主体系。基层协商民主的开展,需要依托基层民主政治体系,结合基层自治,发挥自身优势,统筹推进。再次,政协协商与基层其他创新做法相结合。基层协商民主要服务基层,需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实践,与基层协商民主衔接起来。
(五)把控介入的时机
人民政协介入基层治理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在人民政协职能范围内、在人民政协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和边界范围内积极主动介入,而不是越界越权介入。在介入基层社会治理中,尤其要把握好介入的时机。政协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时机与问题的类型和介入方式相关。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一般问题上,人民政协应该早介入,采取松散合作介入模式能够动员和整合更多的资源去精准定位和诊断这些问题;二是在突发性事件初期的应对上,政协应该积极单独直接地介入,在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建立缓冲带,将突发性事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三是针对基层社会中错综复杂的问题,政协应该进行有限度的介入,以具体问题为切入口,在党委、政府、群众等各界均无法有效应对的时候,是政协介入的最佳时机。需要指出,政协介入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巧借时机、主动把握时机,使得政协的介入能够精准解决问题,提高政协的履职能力。
(六)适时的退出机制
人民政协仅仅一味地介入基层社会治理是不够的,还必须适时地退出。否则,如果介入面宽事多,势必增加基层政协委员的压力,降低对重要和前瞻性问题的敏感度。实践证明,一味地介入而不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也有违基层治理的初衷。人民政协介入基层协商;应该是促进基层民主和基层自治。为此,人民政协适时地退出尤为重要。人民政协从基层退出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特定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演变到不属于人民政协的职责范围;问题虽没有解决,但是社会组织或基层自治组织完全有能力有意愿自己着手解决;政协提出方案,党委、政府已经着手解决;问题虽没解决,但是党委、政府已经接手不需要政协的介入;等等。具备了这些条件后,政协应该及时地从该问题中退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适时退出并不意味着人民政协从基层协商中退出,而是从基层社会治理的某个问题中退出。退出是为了优化资源的配置,是为了更好地介入、更好地推动和促进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
六、结语
政协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然而,人民政协如何从粗放的碎片化介入向精准介入,推动基层协商,巩固基层政权,是各级政协面临的新问题。在介入基层协商和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各级政协的碎片化介入方式不利于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因此,必须开展精准介入。在介入过程中,政协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精准地发现问题、精准地诊断问题、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精准地决策和解决问题。政协精准介入基层协商主要存在直接介入、松散合作介入和紧密嵌入三种模式。这些模式若要达到精准治理的效果,必须满足诸多条件,尤其是党委、政府的授权。为此,政协必须创新机制,做到精准地发现和诊断问题、提出精准的解决方案和整合各界资源、把握介入和退出的时机。未来,在人民政协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上,还需要深化技术与协商民主、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
注释:
①John S.Dryze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1.
② Jonathan Unger, Anita Chan, Him Chung.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China’s Grass Roots:Case Studies of a Hidden Phenomenon,Politics&Society,2014,42(4):513—535.
③韩福国:《作为嵌入性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6—164页。
④闵学勤:《联合协商:城市基层治理的范式变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53—59页。
⑤周清:《政协委员履职活动方式的创新》,《新视野》2013年第4期,第52—54页。
⑥刘学军:《人民政协介入基层协商问题研究》,《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第41—46页。
⑦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第73—97页。
⑧张丙宣、张磊:《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与边界》,《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4—17页。
⑨ Chris Ansell,Alison Gash.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18(4):543—571.
⑩Archon Fung,Erik Olin Wright.Deepening de⁃mocracy: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Politics&Society,2001,29(1):5—42.
⑪应名勇:《“协商+”推动 政协协商新实践》,《人民政协报》2016年2月3日,第8版。
Monographic Study on China’s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heor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intaining that the cor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t the primary level is the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the grassroots unit builds consensus on how to balance public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The Practical Path and Prospect of Primary-leve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summarizes recent experienc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construction at primary level in three aspects:platform building,system design and procedure establishment and proposes the direction and the path of improving the primary-level consultative democracy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mining the mass line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The Configuration and Nature of Public Opinion Technology—The Technic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ss Line and the Consultative Democracy maintains that there are both high compatibility and important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etween them.The essay underscores that integration and win-win outcome of the two could be achieved by taking i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ith the mass line and expanding the mass line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democracy.
A Study on Mechanism of Accurate Interven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CPPCC)in Primary-level Consultation maintains that fragmentation feature of CPPCC’s present intervention in primary-level consultation has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low efficiency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but also does little help to institutional level of political consultative work.The essay proposes themechanism of accurate interven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CPPCC)in primary-level consultation and probes into its modes,conditions and mechanisms,maintaining that it can optimize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in the discovery and diagnosis of problems,program proposal,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the timing of intervention and exit.
Consultative Democracy;Democratic Governance;Democratic Politics;Mass Line
2017-05-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ZZ039);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ZD201510)
张丙宣,男,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主要从事公共行政理论、地方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研究。
编辑 王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