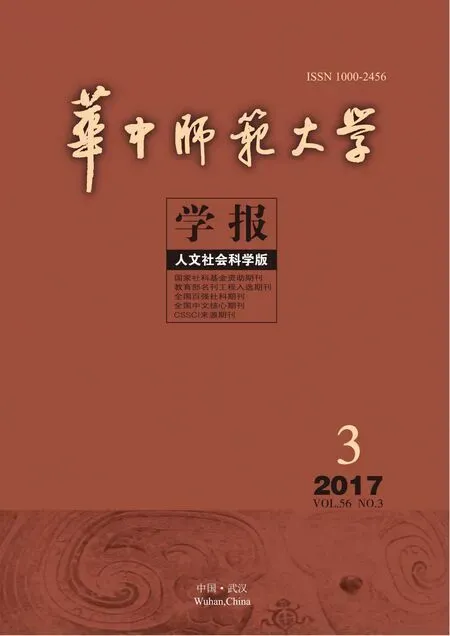城市转型时期的空间改造与文化重构
——京味话剧中的当代胡同市民形象解读
2017-02-27何明敏
何明敏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城市转型时期的空间改造与文化重构
——京味话剧中的当代胡同市民形象解读
何明敏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在京味话剧的舞台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胡同市民或是固步自封地坚守胡同-四合院的城市空间及其所承载的老北京文化,或是转而谋求经济利益,却由于长期浸染于安逸的胡同文化,其商业意识、竞争能力、文化资本等不足以适应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生活。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之下,胡同市民的文化心理仍处于重构之中。他们的现代转型亦滞后于城市的空间改造。在市场经济时代,胡同-四合院的居住空间既是一种生产对象,也是一件可供交易的商品,而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主导的城市改造实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空间生产。面对北京旧城的更新改造,胡同市民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只能被迫迁往城市的郊区,新的有钱阶层则取而代之地入驻城市的中心。可见城市的空间改造也是一种阶层分布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这其中的变化和落差将直接导致胡同市民的身份危机和城市认同感的缺失。
胡同; 四合院; 京味话剧; 市民形象; 城市空间
一、引言:被遮蔽的当代胡同市民
诚如凯文·林奇所言:“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①书写一座城市的历史,或是探讨一座城市的文化,最为值得关注的应该是生活于其中的市民群体。多样化的市民群体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城市文化更为错综复杂。如果说阅读文本是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那么文本所提供的市民形象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城市的认识。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老舍笔下胡同、四合院的市民。一般而言,人们提及北京市民多是指居住于北京旧城区内大小胡同里的“土著”。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之下,寥落的胡同、颓败的四合院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其中的本土市民,逐渐为这座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及其快速的生活节奏所遮蔽。
其实,进入1949年以后,北京的市民构成及其文化主体已然发生改变。土生土长的胡同市民在当代北京面临着较为尴尬的文化境遇。正如杨东平所指出的:“曾经作为老北京城市文化载体的胡同、四合院及其所孕育出的京味文化,正像在地理空间上一样,退缩到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衬托强劲的新北京文化的模糊北京。大院以及生活于其间、以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北京人,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能量,登上舞台中心,成为当代北京社会和城市文化的真正主角。”②的确,“大院子弟”们③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动物凶猛”和80年代的“顽主”时光之后,于90年代重又回归主流社会,并跻身为城市的精英阶层。“大院子弟”的形象也在崔健、王朔、姜文、冯小刚等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之下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而当年“大院子弟”口中的“胡同串子”似乎从不引人注意。如果说于新北京的文化建构而言,他们在“大院子弟”的对照之下相形见绌;于老北京的文化展示而言,他们又不足以代言“京味”。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变迁和社会转型催生了人们的怀旧心理,那个记忆中的老北京被反复言说。京味小说的审美趣味即在于以胡同杂院为依托的旧京市井风情。随着北京城的变迁,京味文化在当代的展示多有倚赖老派的北京市民形象。京味小说的书写自然聚焦于胡同杂院里那些言谈举止间尽显京味风韵的北京老人。可以看到,就当代的文学书写而言,胡同青年多为“大院子弟”或北京老人的陪衬而存在。城市化进程之下,年轻一代胡同市民的切身境遇却较少被提及。然而这座城市的一切正是与他们息息相关。城市的变迁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他们也最为真切地感受着城市的变迁。“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④当我们转而探寻一个城市化进程之下的北京城时,须通过一个更为贴近城市日常生活的市民群体,而当代的胡同市民恰恰是认识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形象之一。
据统计,北京旧城区的胡同1949年为3073条,1980年尚有2290条,至2005年却仅存1353条⑤。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正在重构胡同的空间形态。胡同市民的生活必然随之受到极大的冲击。亨利·列斐伏尔曾经提醒,空间看似是一种客观的、中性的对象,其实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⑥。城市空间既可以是一种政治工具,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城市的规划、建设和改造实则受政治权力和资本力量的支配。当权力和资本干预其中,胡同市民的日常生活则很可能会被忽略。在亨利·列斐伏尔的启发之下,大卫·哈维将19世纪中期的巴黎城市改造视作一种“空间的生产”。他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新的空间生产可以产生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关系、阶层区隔和情感结构等。这也就意味着伴随城市空间的改变,市民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等都将重新调整⑦。同样是面对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哈维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北京旧城改造及城市现代化之下的胡同市民不失为一种借鉴和参照。
“当文学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⑧以此方法论为基础,通过探讨文学文本中的当代胡同市民及其日常生活,也有助于认识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城。面对城市的快速现代化,执着于故都遗韵的京味小说毕竟后继乏力,京味话剧的创作者却在怀旧之余不乏现实关怀。他们将城市化进程之下的胡同市民及其日常生活呈置于观众眼前,为深入探讨一个处于变迁中的当代北京城提供了生动而又丰富的文本。本文选择以京味话剧所塑造的胡同市民形象为考察对象,分别从纵向的代际更迭和横向的地域差异两种维度出发,将之置于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轴上加以审视。与此同时,借鉴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和大卫·哈维的城市研究,结合北京现代化的发展现实,通过解读城市转型过程中的胡同市民形象及其变迁,探讨城市的空间改造与市民文化心理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文化传承与空间生产:四合院的父子冲突
自老舍的《龙须沟》以来,表现市民日常生活的京味话剧常以四合院(大杂院)作为主要戏剧场景。“所谓四合院,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⑨,其布局与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讲究,通常坐北朝南的北房为正房,是一家之长的居所。对称的东西厢房地位低于正房,一般东房为长子所有,其他儿子则住西厢房,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以东为贵。“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一种含义”⑩。可见,作为北京传统的居民建筑,四合院充分体现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长久以来,四合院的居住空间及其所体现的家庭伦理已然内化为北京人的行为准则。然而,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京味话剧,四合院内的家庭生活却多涉及父子冲突。中国的传统家庭历来以父子而非夫妇关系为主轴。自“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父子冲突多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舞台上四合院内的父子冲突,一方面是构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戏剧张力,另一方面也从家庭内部矛盾折射出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通过京味话剧中父子关系的解读以及两代人形象的比较,可以看到胡同—四合院所孕育的市民文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生存状态,也有助于认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角力如何影响并改变着这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及其文化心理。
在京味话剧的舞台上,四合院家庭的父亲形象,诸如《北京大爷》里的德仁贵,《北街南院》里的老杨头,《全家福》里的王满堂,《卤煮》里的何掌柜,《建家小业》里的李臣等,多隶属于京味小说里常见的那一类北京老人。他们是胡同出生的市井百姓,平日里多以提笼架鸟或是票戏下棋为乐,为人处事注重体面,人际往来讲究礼仪。总体而言,这些北京老人,从出身到爱好,从言谈到做派,保留了老舍笔下老派北京市民的气度和风雅。京味小说致力于营造一个宁静祥和、悠然自得的老人世界,而舞台上的胡同老人却不得不被城市现代化的风暴卷入其中。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人生的晚年,却未曾料到原本自得其乐的胡同生活却为城市的现代化所打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95年推出的《北京大爷》一剧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该剧以此为切入点,探讨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之下北京市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击。剧中的主人公德仁贵一家居住在祖上留下来的一座标准四合院内。舞台上,四合院的格局、院落的布置一目了然地呈现于观众眼前。院落正对观众,中心是一张久经岁月磨损的石板圆桌,左后方种着一棵枣树,右前方是自来水池,另有几个花盆和几张石凳点缀其中。左侧是一家之长德仁贵夫妇所住的北房,正面的东厢房住着长子德文高夫妇,右侧的南厢房归属离异的次女德文珠,西厢房则以假想的形式作为舞台的第四堵墙而存在。其中尚未成家的三子德文满,跟随父母住在北屋的西边两间房。可见,这是一户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人家。戏剧的开场,退休在家的北京老人德仁贵,高坐于院内小阁楼“观世台”,悠然自得地喝茶、听戏、逗鸟,偶尔俯瞰院外大街上忙忙碌碌的男男女女,自有一番大隐隐于市的做派。然而,收音机里那苍劲有力的京戏老生唱腔,却一再被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自行车铃声、汽车声、火车鸣笛声、建筑施工机械声等噪音盖过。敲敲打打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已然包围了德仁贵家这座古旧的四合院。
进入90年代以后,北京市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推进“危旧房改造”。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大量拆除。房地产市场随之迅速兴起,现代化公寓、办公大楼进驻旧城,于是危改逐渐演变成对北京旧城的大规模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对于房地产商而言,旧城的胡同四合院既是一件商品,也是一种生产对象,可通过买卖交易或空间的生产谋取经济利益。德仁贵家的这一座四合院就是房地产市场上一件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商品。因此常有不速之客上门询问房产交易事宜。这座四合院将何去何从,其命运成为贯穿全剧的戏剧线索。身为这四合院内的一家之长,德仁贵秉承的是老北京人的财产观念。犹如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在他们看来,“自己必须住着自己的房子,才能根深蒂固,永远住在北京”。对于“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的德仁贵而言,四合院的“一砖一瓦一撮土,都是心肝上的肉”,“对它的情义太深了,深不见底”。何况,讲究体面的老派市民对于市侩气有着天然的嫌恶。老人寄托于这座祖屋的更有一份源自宗法社会的祖先崇拜。然而,这一份老北京人的心气却在现实利益面前败下阵来。长子德文高原先是个工程师,不谙经营之道,却眼高手低地承包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工厂;三子德文满虽是个建筑工人,却长期称病在家,整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随着剧情的展开,先是德文高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后是德文满在牌局上欠下一身赌债。与此同时,南来的广东商人、上海小姐为了租房先后潜入这一院落,准备伺机而动。戏剧冲突由是聚焦于作为百年家业的四合院。德文高拿房产作为抵押申请贷款;德文满倾向于将房屋高价出租,转而入住“煤气、暖气、热水、卫生间”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公寓;作为一个务实的生意人,女儿德文珠意识到市场经济大潮之下四合院拆迁乃是大势所趋。可见对于胡同的子一代而言,他们居住的四合院首先是作为一件商品而存在。他们所追求的是四合院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类似的戏剧冲突也发生于舞台上的另一些四合院家庭。在《全家福》《建家小业》《玩家》《卤煮》等京味剧目中,一面砖雕影壁,一套古董家具,一件元青花梅瓶,甚至是一门卤煮手艺,均如同《北京大爷》里的四合院一般,既作为贯穿全剧的戏剧线索,也是父子冲突的焦点所在,又为戏剧平添一份“京味”。于老一辈的胡同市民而言,以四合院为代表的家传之物集个人的情义、祖上的荣耀和子孙后代的保障等多重意义于一身,而新一代的胡同子民看到的只是它们作为商品所附着的交换价值。可以看到,“五四”以后,新文学中的父子冲突多由家庭、婚姻等问题引起,而京味话剧里的父子冲突多源于经济上的分歧。深受胡同文化熏陶的北京老人德仁贵所秉持的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非分之想莫有,不义之财莫取,站在高处活得自在”的生活态度。像德仁贵这般的老北京人历来轻商,却在20世纪90年代被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的“败家子”则主动与外来的资本力量合谋,不仅败落了祖传的家业,也打碎了老人的那股北京人的“心气”和“精气神”。可见,改革开放之后,在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之下,属于胡同的那一种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已然不合时宜。编剧中杰英曾经表示,《北京大爷》是他对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现实的思考,“在改革开放的商品大潮中,人们的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而相当多的人却处于不适应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其中‘北京人’就是较典型的代表。面对南方经济大潮的涌进和许多以往未曾碰到过的问题,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道德与价值的冲突,事实与愿望的相悖,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历史裂变的漩涡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如果说德仁贵这般的胡同老人试图在市场经济之下延续旧有的居住空间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而德文满兄弟作为胡同的子一代显然已不满足于这一切。京味话剧更为现实地剖露了城市转型时期胡同的空间形态、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所面临的冲击。城市的快速发展越来越难以容纳胡同市民那份知足常乐、安时处顺的文化心态。德仁贵长期处于这个封闭的环境之内,习以为常,对四合院的颓败现状竟无所察觉。四合院的家庭生活及其文化原本呈现相对较为封闭自足的状态,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被逐步瓦解,而这股现代化的力量首先是通过子一代得以渗入传统家庭的内部。如果说建国后的旧城改造和政治运动尚未动摇胡同文化的根基,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现代化则必将打破进而摧毁胡同-四合院那种前现代的生活秩序和文化心理。借用卡林内斯库的话来说,就是“市场并不只是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机制,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表现,一种文化现实的表现”。舞台上所呈现的四合院家庭冲突正是源于由经济变化引起的精神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对于胡同的子一代而言,四合院的物质属性显然重于其文化属性。当胡同-四合院的城市空间被作为一种生产对象而加以改造,它所承载的文化也将随之面临断裂的危机。不过,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城市变迁,外在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或许一朝一夕即可改变,而旧有空间形态所孕育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等,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之下可能比想象的更为根深蒂固。
三、文化拘囿与空间转移:胡同市民的身份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京味话剧塑造了一系列类型化的当代胡同青年形象:《北京大爷》的德文满,《全家福》的王国梁,《北街南院》的杨子,《建家小业》的李为民,《东房西屋》的强哥,《枣树》的关磊,等等。他们出生于六七十年代,自小长在胡同,中小学毕业即踏入社会,职业多是工人、个体户和出租车司机等,或是待业在家。“闲时潇洒,优哉游哉,透着几分傲俱,几分随和,几分热忱,几分仗义,几分贫嘴,几分痞气,几分大大咧咧,几分气定神闲”,这是编剧王俭对于他笔下胡同市民强哥的定位,也大致契合舞台上这一代的胡同市民形象。类型化的文学形象映照出的是某种社会共性,而类型化的胡同市民形象所体现的是城市转型时期这一市民群体较为共通的文化心理。
《北京大爷》里的另一位胡同老人申绍山曾经提及:“这京城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享清福的,历朝历代天子脚下一等国民,挣钱的事用不着操那份心!您瞧我,退休下来多少人来请也绝不下海,落个逍遥自在,玩个小古董小字画,图个小小的个人爱好,有点小快乐小自在。这才叫高雅的人生,美好的享受呢。你呀,甭瞅着街边卖馄饨的眼熟,那是下三流干的活;也别瞅着五个星的大旅馆运气,那是奸商为富不仁挣的昧心钱!”这番典型的“老北京”心态投射到同剧的胡同青年身上,恰如德文高那般心高气傲却缺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也说明德文满的好吃懒做、享乐主义自有传统之因袭。另一方面,却正如赵园所言:“商品经济的发展,胡同居民间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利欲由人性禁锢中的释放,无情地瓦解着市民精神传统,颠覆着他们的宁静世界。”20世纪90年代,德文满、王国梁、靳二鹏们身陷市场经济大潮,“几乎十分相似地热衷于挣大钱,不屑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之类的为商之道”。讲体面、图安逸、好享受、惧竞争等诸种老北京的文化心理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法则。苏叔阳也曾经指出,“这种囿于历史的沉积,而缺乏锐进、冒险、开拓的精神,使北京人在改革中往往落在别人后面,甚至对于任何新事物都采取‘泡’的态度,因而大大缺乏时代精神”。可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胡同市民的金钱欲望有所觉醒,但由于长期浸染于安逸的胡同文化,他们的现代商业意识仍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作为首都,以其经济力量和发展优势吸引了大批流动人口。对比这些改革开放之后涌进京城的外省人,胡同市民身上的诸多老北京文化特性显得愈加清晰。《北京大爷》中广东商人欧日华是“北京大爷”们眼里“偷奸耍滑的南蛮子”。他身为合资公司的经理,佯装生意失败,尔后勤勤恳恳地为德文珠打工,以便打入德家四合院的内部,暗中探查德家的现实处境,目的在于为房屋交易寻求一个双方互惠的合作方案。此时的德文高,生意失败,债台高筑,仍自恃承包的是国有工厂,指望上级领导的救助。对比德文高的眼高手低、自以为是以及德文满的游手好闲、贫嘴无赖,编剧中杰英充分肯定了南方商人欧日华身上更为现代的商业意识、商业道德和商业能力,对于同代的胡同市民则有一份怒其不争的痛惜。
不过,到了黔驴技穷之时,胡同市民或许仍可以借助于祖上留下的房产。在2007年的小剧场话剧《东房西屋》中,主人公强哥四十余岁,却赋闲在家,全赖出租祖上留下的大杂院以为生计。平日里,他养着一只鹩哥,闲来教它说话、唱歌,偶尔扎个风筝,唱上几句京戏,俨然过上了胡同老人的生活。进入21世纪,在这个致力于跻身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城,强哥这般的胡同市民却在尽力维持“北京大爷”的做派。作为当代北京的“吃瓦片”一族,强哥的几间小屋专门出租给“北漂”。如果说“大院子弟”相较“胡同串子”有着强烈的身份优越感,胡同市民则在与外来者的对比之中寻找优越感。常以“北京爷们”自诩的强哥,为人热情正直,讲哥们义气,深受周围“北漂”们的敬重。身为土生土长的胡同市民,面对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外地房客,他虽终日无所事事,却仍出于北京人的身份而自视高人一等。相较之下,剧中所有的“北漂”青年都在为着各自的梦想而努力打拼。他们正像是伯曼所谓身处现代世界的男男女女,允许自己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自己和世界。这个现代世界却正在摧毁着胡同的居住空间及其市民曾经所拥有的一切。
身为土生土长的胡同市民,强哥原本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认同感。但在胡同文化及其生活秩序的规约之下,他从来是被动的生活于这座城市。面对北京城的变迁,旁观外来者的努力,对比自身的故步自封,危机感在强哥的内心悄然滋生。正如剧中人耿田所言:“不管是河南人、安徽人,还是香港人、台湾人;只要有本事,就能进入北京这个大熔炉里来,一搅和,再倒出来,统统成了新北京人!”为了进一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京先后出台一系列户籍改革政策,为各类人才办理进京户口。户籍政策改革,大量外来人口落户北京,进一步消解了胡同市民那份“天子脚下,皇城子民”的身份优越感。强哥的现实处境为京妞一语道破,“不就是靠着一张北京户口外加几间破房子才当了个爷吗?”。而他所驯养的笼中鸟正是他自身处境的一种隐喻。以“东房西屋”为代表的胡同—四合院则正是那一只困住他的鸟笼。耿田曾直白地向强哥指出,唯有失去了这“东房西屋”,他才能“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禁锢他的并不仅仅是有形的生活空间,更是无形的文化积习。“北京人”的优越感迫使他生活在自我伪装的体面之下。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他以“比上不足,比漂有余”的自我安慰强撑起“北京人”的自尊。他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过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他所表现出的淡定从容、知足常乐,仅仅是佯装一种“老北京”的姿态。强哥最终无奈地坦白,“其实我才是最可怜的!我没有多大能耐,还死要那个面子。”身为一个城市化进程之下的胡同市民,强哥身上的那番“北京大爷”的做派只是徒有其表。当胡同被作为一种生产对象来对待,或是作为一件商品而存在,胡同文化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底蕴。
当推土机的轰鸣声响起,无数像强哥一样的胡同市民终将被连根拔起,从此告别他们自小熟悉的院落、胡同和街坊邻里。新的空间一旦生产出来,胡同社会的礼仪文明、人情世故、道德秩序等都将无所依附。在《北京大爷》《玩家》《全家福》《建家小业》等剧目中,已初步显现出现代社会的金钱法则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东房西屋》则更为鲜明地揭示了大都会的资本罪恶。剧中强哥所对抗的房地产开发商牛总,其人虽不曾露面却于无形之中操控着他人的生活。他偷梁换柱地将经济适用房的规划项目改为建设高档公寓楼,以“低价征地,高价卖楼”谋取暴利。这种行为形象地阐释了列斐伏尔所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空间生产。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的牛总则隐喻着大都市的非人性质。可以想象,不久以后,强哥的“东房西屋”乃至整片胡同将在这座城市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一幢幢高档公寓,入住其中的则是城市中产以上的市民。作为低收入人群的强哥们则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将胡同改造成高档住宅区,改变的不仅仅是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意味着原本自居天子脚下的皇城子民将被驱赶至城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有钱阶层。强哥不禁犹疑,“到那时,就要迁到五环外的高楼里了。离什刹海好几十里,离地面好几十米,我还算个北京人吗?”从《东房西屋》《旮旯胡同》《海棠胡同》《玩家》等剧目中可以看到,土生土长的胡同市民随着城市空间的更新而被迫迁移至郊区。作为城市的中下层市民,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的中心之外,最终疏离于自己的城市。在都市社会的资本运作下,胡同的空间形态将被重新规划和改造,胡同市民基于房产、户籍和历史文化的身份优越感将就此被彻底消解。列斐伏尔曾经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工人阶级和移民被逐渐排挤到城市边缘,从而失去进入城市的权力。城市化进程之下,北京的胡同市民未尝不会重蹈覆辙。当胡同、四合院被大量拆迁,他们的归属感又何处依附。身处城市现代化的漩涡之中,以强哥为代表的胡同市民难免会因为“痛失前现代的胡同乐园”而感伤、失落和怀旧。
四、结语
一般而言,城市的现代化要求居住其中的市民告别过去。然而,舞台上的胡同市民却背负着太多过往,以至于一度被甩出现代化的前进轨迹。在《枣树》《建家小业》《北街南院》等剧目中,有着相似的戏剧场景——共话过往的胡同-四合院生活:院落里的枣树,一起嬉戏打闹的儿时伙伴,邻居大妈的炸酱面……胡同-四合院的城市空间承载着一种生活方式、一份集体记忆、一个文化传统和情感共同体。然而,胡同市民曾经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将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而烟消云散。在这座城市,看得见的舞台上,看不见的角落里,感伤、失落与怀旧的情绪四处弥漫。就北京这座城市而言,现代化的阵痛或将更为剧烈、持久。在京味话剧的舞台上,胡同市民仍深感“丧失家园之痛”,似乎分外留恋往日胡同-四合院的生活。从舞台上的胡同市民形象可见,当代北京的胡同市民仍处于一个内心地理世界的重构之中。大卫·哈维指出:“无论被移置者的失落感或‘丧失家园之痛’有多大,集体记忆实际维持的时间往往出乎意外地短暂,而人类的调适速度也相当快。”事实上,相较于拥挤、破败的四合院生活,现实中更多的胡同市民倾向于选择现代化的居住空间。胡同市民的怀旧其实并不意在重返过去,而是源于城市主体地位的失落。
在市场经济时代,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房地产开发商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其中胡同市民所在的北京旧城区作为城市中心,必然是各种资本力量角逐和瓜分的空间对象。胡同—四合院的市民本就多为中产及以下人士,尤其大杂院市民,经济条件十分有限。以强哥为代表的当代胡同市民,他们自小长于传统的四合院家庭,却于80年代受到改革开放的冲击,90年代又手足无措地应对着市场经济大潮,进入21世纪之后则成为胡同、四合院最后的留守者。他们中的一些如德文满一般,在踏入社会之后为城市的灯红酒绿所吸引,于是从狭窄的胡同游荡至繁华的大街;另一些人则像强哥一样,固守“北京大爷”的做派,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抵抗现代化进程之下城市的空间生产。总体而言,他们既游离于都市生活之外,又无法重返过往的家园,从而或是执迷于追求现代都市的物质享受,或是沉湎于回忆昔日的胡同岁月。可见,在城市转型期间,乡土北京的文化积习依旧附着于这一代胡同市民,甚至成为他们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历史阻力。
面对充满竞争的城市生活,就京味话剧所呈现的胡同市民形象而言,当代北京的胡同市民缺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也尚未形成积极进取的现代意识。其原本所身处的居住空间、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在走向瓦解,而他们又一时难以适应大都市的生活节奏和生存法则。在胡同空间及其文化的规约之下,胡同市民的现代化转型显然滞后于城市的空间改造,其商业意识、竞争能力、文化资本等不足以适应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生活。因此,当城市空间从属于物质和资本的时候,胡同市民显然无力招架。城市的现代化摧毁了胡同—四合院的城市空间,代之以现代化的高楼公寓。然而,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原本居住于旧城区的胡同市民无法入住新建的高楼,只能被迫迁往城市的郊区。正如调查显示,“从1990年到1997年,仅西城区旧拆迁安置居民25000户,共8万多人,其中除少量回迁外,大部分都迁往远郊区县。”与此同时,原先的外来人口却凭借财富和权力,取而代之地入驻城市的中心。可见,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更新也是一种阶层分布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这其中的变化和落差将直接导致市民的身份危机和城市认同感的缺失。
注释
①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大院”特指1949年建国之后出现的军队、国家机关、科学、艺术、文教单位等集工作场所与生活区域于一体的空间(主要集中于北京)。参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第172-178页。
④⑧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第3页。
⑤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旧城胡同实录》,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⑥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陈志梧译,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⑨马炳坚:《北京四合院建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⑩刘心武:《钟鼓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责任编辑 梅莉
Space Reform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eriod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Hutong Citizens in Beijing-style Drama
He Mingmin
(Urb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In the market economy era, the living space of Hutong-Quadrangle can be used as a kind of production object or merchandise. In fact, the city reconstruction is a kind of profit-making production of space dominated by property develope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Beijing, Hutong citizens have to move to the suburbs because of the limited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Meanwhile,the wealthy people move to urban center instead of them. It means that the space reformation in city is also the reconstruction of class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which cause the identity crisis of Hutong citizens.
Hutong; Quadrangle; Beijing-style drama; image of citizens; urban space
2016-10-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城市叙事研究(1949-2015)”(16CZW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