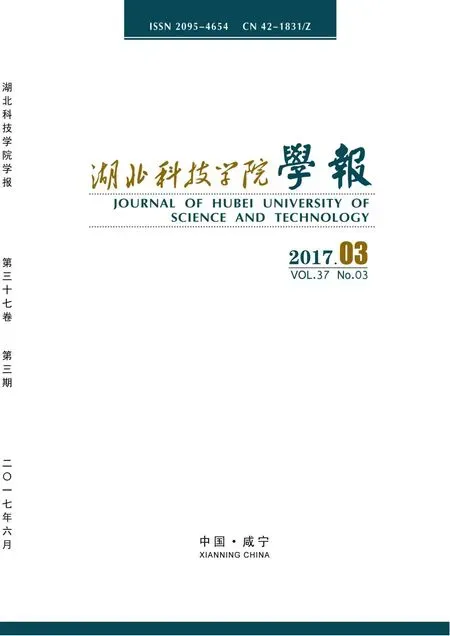苏童的时代呓语
——论《城北地带》中少年的成长之痛
2017-02-25章立群
章立群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研处,福建 福州 350108)
苏童的时代呓语
——论《城北地带》中少年的成长之痛
章立群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研处,福建 福州 350108)
文革十年的时代印记、年幼病痛的独有个体感受,成了苏童很多小说的背景色,《城北地带》尤其如此。作品中的少年几乎都是作者的真实童年印象。由于时代原因——父母缺位、教育缺失、社会失序,这些少年几乎是野蛮生长,他们迷恋暴力,处处挑衅权威,冷漠自私,又渴望长大。乱象时代带给一代人的身体与心理伤痛,是极为沉重的。莫让少年沉沦于时代,《城北地带》意义启发都在此。
少年;成长;环境
谈起苏童,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著名导演张艺谋早期拍过的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的。他凭借着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甚至还一度被贴上“女性作家”的标签。虽然,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面世让苏童的好运接踵而至,但是,在苏童心中,更为在意的却是那组活跃在香椿树街的南方少年成长的故事。苏童曾在《米》自序中提到“《城北地带》是我的长篇新作。在我寥寥无几的几部长篇作品中,它是尤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真实生活中童年记忆闪闪烁烁的那一群,我小说中的香椿树街在这里是最长最嘈杂的一段,而借小说语言温习童年生活对我一直是美好的经验,我之所以执着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1]。
有着三只大烟囱、化工厂、河流、弄堂的城北地带实际上就是苏童故乡苏州家门口的那条大街,达生、叙德、红旗、小拐,这几个成日游荡在香椿树街头的旧城少年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处处挑衅大人的权威却又渴望长大成人,成长是他们共同的目标,然而,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他们在受尽伤痛之后却仍然无法走到路的尽头。少年达生想要凭借暴力成为香椿树街的英雄人物,可最终在一场暴力行动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红旗浑身江湖义气,却因一时冲动将自己的大好青春葬送给了监狱;自以为长大成人的叙德能不负责任地将命运放诸于一枚硬币身上;身体赢弱的小拐成功地击败他的伙伴们成为了模范人物,然而在带上大红花的那一刻迎接他的却是质疑、不屑的眼神。特殊的环境让这些少年偏离了正常的成长轨道,虽然他们性格各异却仍有着相通之处。
一、崇尚暴力——时乱世乱少年乱
暴力因子似乎早已在“香椿树街”的每一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家里、学校、街上、亦或是代表着正义的警察局暴力无处不在。在这里,它是权利、地位和尊严的象征,是每个少年所向往的。作为父亲对母亲性暴力下的产物的少年达生来说更是如此,畸形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对暴力有着执着追求,母亲腾凤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自己的父亲滕文章以200元钱卖给了丈夫李修业,面对着长相猥琐举止粗暴的丈夫以及这个陌生的新家她无时无刻都想要逃跑。而在父亲看来在自己花了八年的积蓄将母亲买下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是自己的所有物了,所以,对于母亲的多次出逃这样触犯他权威的挑衅只有以一次又一次的毒打来解决。而自己虽然厌恶父亲,不想受皮肉之苦,但身体上不占据任何优势的他在自己强大到把父亲打倒之前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所以,他才会那么在意武师的存在、注意锻炼身体、迫切想要加入帮派。
小拐的父亲和达生的父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嗜酒成瘾、粗俗不堪,虽然在外面过得并不十分如意,但是,在家里却又极力维护自己属于大家长该有的尊严。暴力在这条街上已经不是什么寻常的事了,在王基德家更是如此,孩子们惧怕的眼神让他喜欢用极端的的方式来驯服自己的子女,稍有不如意之处,便将恶气撒在他们的身上。身体上的缺陷使得小拐很难在自己的心理上找到一个平衡点,造成了偏激、阴鸷的性格,而父亲从小的棍棒教育令全家人瑟瑟发抖,这让他对暴力有着近乎变态似的渴望。母亲的早逝使得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引导者位置的空白,他无法分清是与非,他只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体会到的一切。所以他常常将用父亲对付自己的招数原封不动地施加到姐姐们的身上,因为自己与冼铁匠的仇恨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的狗杀死。
在家里以外的香椿树街上,各帮派间的暴力行为此起彼伏,跟好人好事相比,这些帮派少年间出其不意的打架闹事更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什么野猪帮、斧头帮、大刀帮这类的帮派名称早已替代各类典型建筑成了城北城南城东城西四个地带的标志,光听名号就早已让人闻风丧胆,而帮派成员更别提有多威风了。这些都是让少年们所羡慕而渴望的。红旗的两个远房表哥是大刀帮的成员,而他也碍于这层关系而获得让同龄人尊重的资本,受他们的影响使得他对加入帮派无比地渴望,虽然还不具备入派资格,但他在平日的一言一行中事事用帮派里的条条框框来束缚着自己和他人,讲究规矩。在一场帮派行动中表哥东风的脑壳被打碎了,被抓进了警察局,但是他却成了街上的英雄,为人所敬佩。就连曾经侮辱过达生的警察也对他们束手无策的,这也成了红旗他们迫切想要加入帮派的另一个原因。
就连承担着教书育人职责的学校,也是暴力行为的聚集地,少年们所就读的东风中学一直都是杀人放火无所畏惧的象征。学校时常有学生辱骂殴打老师的事情发生,在这里老师和学生似乎是不相容的,学生厌恶老师,老师厌恶学生,冷暴力是老师们对待像达生这类的问题少年惯用的手段,更别提什么和谐的师生关系了,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话的语气总是带着怒气,有时甚至还会恶言相向,在他们眼中这群学生的存在对学校来说就是一种耻辱。小拐在课堂上指出了政治老师李胖上课随意体罚学生的事实,愤怒之下竟然当场将小拐赶出教室,并且在众人面前用小拐偷盗的恶习和他腿脚不便的缺陷来攻击他,甚至还以辞职来要挟学校领导将小拐赶出学校。在学校门口遭到学生报复的政治老师李胖在交代事情的原委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学校和学生的:“教师?人民教师?教他娘个X。现在这些孩子哪里要教师?哪里要学校?我看把东风中学改成少年监狱还差不多。”[2]而对于他的这种说辞竟然也能让在场的几个教师拍手称快,在他们心中早已将这群孩子和监狱中的罪犯分为了一类,无药可救了,相对于学校而言监狱的管束更加地适合他们。除了老师外街上的每个人对这群少年也是持同样的看法。虽然老康认为这一切并不都是孩子的错,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在他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甚至遭到了教师李胖的拳打脚踢,他的挨打不仅仅因为他作为四类分子的身份,更是由于他的观点并非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排斥。
二、渴望成长——长大了才有力量
十几岁,本应该是天真活泼的花样年华,可“香椿树街”的少年们却并不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凭借武力来获取主动权成了这群少年们惯用的方式,而在此期间不断崛起的少年帮派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后的产物,刺青、大刀、斧头这一类象征物更是成了一种标志。在这里弱小者没有说话权利,只能够备受欺凌和嘲讽,尴尬的处境让他们对成长更加渴望,他们不愿意自己被别人当成是小孩子看待,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与成人看齐,出口成脏、用自己不理解的形容词来谈论男女之事、挑衅权威、不服从管教等等,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与众不同。
整篇小说在一个举止粗鄙的男人喋喋不休的骂声中拉开了序幕:“我的自行车呢?X他娘的,谁把我的自行车偷走了?”[3]他就是达生的父亲,而令他如此生气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儿子骑走了自己的自行车。作为儿子的达生,虽然明知道自己偷骑自行车所要承受的后果,可他却为了能早日练习双手撒把的车技一意孤行。母亲腾凤是一个成天只知怨天尤人的家庭妇女,丈夫加诸于自己身上的痛苦让她对家里的一切充满怨言,就连唯一的儿子也不例外,向周围的人倾诉自己的不幸以及对丈夫的实施恶毒的诅咒和谩骂是她每天必做的事情。父母间特殊的相处模式并没有给他的童年带来丝毫温暖和关爱,面对自己鄙视却又不得不忍受其毒打的父亲、歇斯底里的母亲以及被贴上弱者标签的自己,他都竭力想要摆脱。所以自懂事起他便执着于一条寻找武师之路,在他看来获得武师的力量不仅能帮助自己早日完成称霸香椿树街的梦想,而且还是自己实现从少年到成人华丽蜕变的关键所在。可他这一路却走得异常艰辛,和叙德骑车到三十里以外所寻找的那个绰号叫和尚的武师是别人凭空杜撰的,被人传得云里雾里的十步街的严三郎实际上是个卧病在床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一连串的真相给他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可他却没有气馁,即使在寻访武师的业余时间里,也不忘在家里打沙袋锻炼身体,以十倍百倍的精神等待拜师那一刻的到来。周围的一切他可以漠不关心,可对待自己的梦想却近乎执拗。这样的性格使得他最后走上了不归路成了毫无悬念的一件事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烂屎,他在遭受到众人的拒绝后孤身迎战,就连在弥留之际心里想的也是怎么让先前看不起自己的十步街少年和户籍警小马付出代价,他用自己最崇敬的方式结束了平凡的一生,轰动了整条香椿树街街,可付出的却是血的代价。
叙德作为和达生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少年,虽然同样渴望成长,但他选择的方式却与别人截然相反。或许是弱懦无能的父亲和过渡宠溺自己的母亲,让他的肆无忌惮有了充分的理由,母亲素梅在儿子残忍的拒绝自己搬椅子的要求时,除了私底下诅咒儿子几句外,更多的便是将过错归咎于这条街上的不良风气。儿子将情人金兰带回家被自己撞了个正着,面对儿子破口大骂,甚至恶狠狠地扬言要杀自己时,她所做的仅仅是用一种绝望的眼光看着儿子后,便又迅速地将攻击的目标转向了金兰。在她看来儿子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荒唐行为完全是出于女方的勾引。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形象,而她的爱最终却使叙德养成了同她的期望截然相反的性格,当然在孩子的教育上除了母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父亲,俗话说得好:“养不教,父之过”[4],父亲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所肩负的作用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可是叙德的父亲沈庭方却空有父亲的虚名,只有在无法再推脱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的时候才勉强说上几句话,能对儿子的嘲笑辱骂一笑而过,这样懦弱父亲形象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叙德来说是打心底里看不起的,就连面对自己暴力父亲也是表现出一副唯唯诺诺、哭哭啼啼的嘴脸,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置于同父母同等的位置上在叙德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除了外表格格不入之外,自己的行为早已与成人无异了,所以,他更注重外表上的成人化,明明是十几岁的孩子,却学着别人蓄起了胡子、故作成熟地嘲笑达生他们幼稚的行为、同女人偷情。
除了家人的管制外,学校是他们摆脱现状的另一个突破口,虽然在学校里他们有着各自的小团体,但碍于学校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无法施展拳脚,可是外头的少年帮派却能够为所欲为,这让他们羡慕也是自己同别人的区别。所以,他们处处挑战老师的权威,视接受学校的教育、服从老师的管制为一件丢脸的事情,以打架闹事、逃课旷课、争上白板等偏激的方式来展现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需要寻找试点学生来应付上级检查的教导主任,为了请求自己重新上学而在家里展示出的低姿态让小拐颇为得意,他便乘机向教导主任提出更换老师的要求来作为自己回校的条件,在他看来,既然老师有选择学生的权利那么学生也是一样。虽然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地回了学校,但这是屈服于父亲强权之下的无奈举动,对于他厌恶的一切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面对着自己鄙夷的政治老师,他选择用言语和行动上的挑衅来宣泄自己的不满,甚至在离校的最后一刻做出向政治老师扔屎包的行为来为自己的学校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三、亲情淡漠——人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倒了
帮派情结或许让少年们热血沸腾,但他们内心的冰山并没有因此而融化,达生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可对于自己的父母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母亲成天的怨天尤人、诅咒谩骂让他无比厌烦,而自己和父亲最好的交流方式便是暴力,其言行举止让他除了憎恨之外就没有其他感情了。父亲的死亡或多或少和自己有一些关系,可是在他的身上却看不到丝毫的愧疚和难过,也很不理解母亲对自己诸如此类的责怪,“达生觉得母亲的逻辑是荒谬的,父亲受害于那辆装载水泥的卡车,她应该去找那辆卡车算账。拉不出屎怪茅坑,他有时候想到这句粗俗的民谚,一个人就捂着嘴嗤笑一声。”[5]他心里更多的是为父亲再也不能随意打骂自己的事实和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自行车而暗暗窃喜着,甚至在父亲死后第一次在梦中相见的场景也是自己用暴力完成了同父亲的对抗。
同达生的悲惨遭遇相比叙德的童年可以算得上是幸福的了,身为党员干部的父亲是香椿树街上那些举止粗鄙、观念陈旧的工人所无法比拟的,而母亲素梅更是将他当成是宝对待,有求必应。可恰恰是这样一份特殊的爱才让他养成了如今这温软自私的性格。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他都报之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朋友红旗被捕入狱了,他跟随达生他们到草蓝街去探望之举无疑是看好戏的时候居多,也因为他的恶作剧让达生摔断了腿,可他对自己的过错却没有丝毫愧疚之心。在家人和朋友们面前处处标榜金兰是自己的女人,可是当金兰真正出事向他寻求帮助时,他却不管不顾。而他现今的性格的养成也并不是没有理由,在文章中曾多次描绘出父亲沈庭方的画面,但同儿子私底下的交流却寥寥无几,身为一家之主的他并没有表现出该有的样子,家里的大小事情全部都由妻子做主,就连教育孩子这样的大事上,在他看来这些事都比不上下棋重要。更荒唐的竟是,在明知金兰是自己儿子的情人的情况下仍与她纠缠不休,这样的父亲形象是无法被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所接受的,虽然他在叙德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做些什么,但是有些影响确实不知不觉就渗透血液当中的,所以叙德才会凡事只想到自己,一到关键之处便打退堂鼓。虽然母亲在这一过程中都在试图想做些什么,但是却用错了方法,以至于叙德在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之后愈加的肆无忌惮。
除了家庭的关系外,几个少年们还成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根据素梅的回忆,“她记得红旗跟叙德都是大炼钢铁那年生的,当时她和孙玉珠都挺着大肚子在城墙下运煤。”[6]照此看来少年们从小就生活在文革后期那个无序的社会环境中。在这里,邻里之间的关系被一条隐形的线捆绑着,一旦这条线断了也意味着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达生的母亲腾凤和叙德的母亲素梅先前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可是却为了几颗鸡蛋而吵得面红耳赤,翻脸之后先前的闺房密语便堂而皇之地成了彼此伤害的武器了。毫无立场、爱看热闹、缺少人情味是这条街上的人们所共有的,出了事情时,获取新鲜的新闻似乎比帮助邻居更加地重要。沈庭方因一时的冲动用剪子剪断了自己的生殖器,最后闹到了不得不上医院的地步,邻居们知道他们家的异常后,全部都聚集到他们家周围看好戏,更有甚者爬上了他们家的窗台一探究竟。能打着要帮忙的旗号借机查看他的伤势好证实自己的猜想,能趁着他们全家人上医院的空档偷走培育已久的名花虞美人,就连身为儿子的叙德在从达生嘴里听说父亲的丑闻之后,第一件事竟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同伴一起嘲笑自己的父亲。少女锦红在反抗的途中被蝴蝶帮少年错手杀死,可是在人们知道了她的死因后的反应并不是为这条年轻的生命惋惜,而是为锦红誓死也要维护贞洁的行为而拍手叫好。而这些恰恰就是生活在这条街上的每个人的相处之道,他们的感情可以因时因地而随意转移,或许我们觉得这群叛逆的少年面目可憎、无药可救,可这些又何尝不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所赋予他们特殊的礼物,对于暴力行为并不是他们一早所渴望的,而是当这种行为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时候所做出的必然反映,他们成日游离在街头巷尾的各个角落无非是想要寻找他们存在的价值,但无论是在家里、学校还是其他地方,他们所见到的都是口出秽言的人以及打架闹事的场面,胜者意气风发,而败者只能落得个灰头土脸的下场。那些敬佩畏惧的目光恰恰都是他们想要拥有的,他们虽然讨厌欺辱他们的人,但只有获得和这些人同样的力量才能扭转局势,于是小小的他们身上无一不表现出对成长的渴望。
四、城北之痛——莫让少年沉沦于时代
三字经中有一句朗朗上口的话:“人之初,性本善。”[7]本应善良的他们却成长成了如今的不良少年,可见环境这一外部力量的重要性。良好的成长环境对孩子们健康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恶劣的环境除了让孩子们身心受创外,甚至还会将他们引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古人对于这一情况早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才会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对于达生、叙德、小拐和红旗来说,正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所以小拐养成了偷盗的坏习惯,红旗会为了那股不知名的冲动而走上了强奸美琪的违法犯罪的道路,甚至是达生也因自己的好勇斗狠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混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变异的学校环境直接造成少年之殇。
在这失序的时代背景中,个体成长最后的避风港——家庭,却也因外在的因素,父母集体失语,多数家庭甚至成为压榨个体的暴力阵地。至此,这个时代少年成长,失却了人性中向上向善的美好意志,在时代河流中沉沦。
生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少年在不断的涌现,而每一代人又都是承上启下的。此时的少年,彼时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此时的时代弱者,彼时的时代中坚力量;失序的时代,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苏童的《城北地带》让我们再次正视生命的成长问题。时代有序,世风祥和,个体的家庭才真可能幸福安康,也才能承担起少年成长的重任。
[1] 苏童.少年血[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 苏童.香椿树街故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张文.论苏童小说中的少年成长叙事[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4] 高承新.“熟悉的陌生人”苏童小说人物析论[D].南昌:南昌大学,2006.
[5] 吴雪丽.从晦暗到澄明:论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J].东方论坛,2009,(5).
[6] 郭颖杰.论苏童小说的童年意绪[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7.
[7] 叶珮琪.论苏童小说创作中“南方世界”的意蕴[D].杭州:浙江大学,2009.
责任编辑:余朝晖
2017-02-21
2095-4654(2017)03-0078-04
I2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