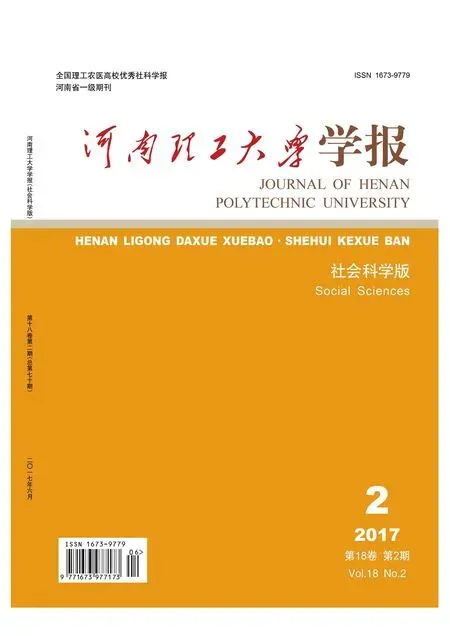部族战争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兼论大禹时期国家的形成
2017-02-25陈建魁
陈建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部族战争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兼论大禹时期国家的形成
陈建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氏族社会,是经常发生战争的社会,这种战争或可称“古代部族战争”“古代部落战争”。大禹时期,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大禹不断扩张其实力,为将政权传给其子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而夏启能够平稳接任其父大禹,并正式建立夏朝,说明大禹既是氏族社会最后一个部落首领,又是国家的缔造者,还是中国阶级社会的第一任帝王。
部族战争;大禹治水;公共权力;文明起源
氏族社会,是经常发生战争的社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阶级对立,首先是通过战争手段产生出来的。就其性质来说,这种战争或可称“古代部族战争”“古代部落战争”。
一
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划分上,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逐步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其标志就是农耕和畜牧的出现,即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因此,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代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在考古学上,这一阶段大致是从伏羲时代开始的。而伏羲时代,也是中国古史上所称的“世系”开始阶段。
关于伏羲时期的帝王,《庄子·胠箧篇》在谈到上古“至德之世”时提到不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若此之时,则至治已。”[1]书成于战国时期的《六韬》等轶书遗文也有提及:“昔柏皇氏、栗陆氏、骊连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此皆古之善为政者也。至于伏羲氏、神农氏,教化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古之不变者,有苗有之,尧化而取之;尧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2]皇甫谧《帝王世纪》亦有记载:“大皞帝包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于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长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取牺牲以充包厨,故号曰包胥氏。后世音谬,或谓之伏牺,或谓之虙牺,一号皇雄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为女皇,亦凤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黄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3]李昉《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曰:“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五气异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羲之号。”[4]郑樵《通志》记载:“女娲之后有大庭氏,有柏皇氏,有中央氏,有栗陆氏,有骊连氏,有赫胥氏,有尊卢氏,有混沌氏,有昊英氏,有朱襄氏,有葛天氏,有陰康氏,有无怀氏,据女娲氏,天子也,自大庭之后十三氏,皆臣于伏羲。”[5]摩尔根指出:“氏族组织则是一种波动的个人集合体,多少是分散的,不能在一个地方的界限内成为永久性的定居。”[6]373
伴随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再加上氏族活动地域的不断扩展,致使氏族成员的职业身份不断变化,原先的氏族也就不断地分化成若干个新的氏族。而原先由母系计算的血缘关系,也就慢慢地发展到以父系来计算血缘关系了。如此,一个姓也就分成了若干个分支,这一个个分支就是氏。因此,氏最早出现的时候,不过是表示氏族和部落支系的居住地而已。伏羲、女娲为风姓,而伏羲序列的其他帝王亦应是风姓,但他们以氏称,应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部落或部族首领。这些部族各自有其活动区域,并在伏羲时代相继而起,成为整个伏羲部落的首领。从伏羲氏十几个部族的活动范围(如葛天氏活动于河南长葛,朱襄氏活动于河南柘城,共工氏活动于河南辉县,等等)可以看出,伏羲部落或部落联盟主要是在中原一带。
结合史载伏羲事迹、伏羲遗迹及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伏羲时代已开始逐步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已基本上进入定居农业时代,当时的氏族组织也正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史载伏羲的各种主要贡献中,并没有伏羲时代已经进入定居农业社会的信息。摩尔根认为:“在我们设想氏族改为以人命名之后的长时期内,其命名的祖先也改换他人,前一位祖先的事迹逐渐模糊了,消失在迷茫的历史印象中,于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出的名人便取而代之。”[7]344由于神农炎帝是代伏羲而起的中国古代部族首领,故而把伏羲的部分功绩归于神农也是很有可能的。中国最初进入定居农业时代的文化范围颇为广泛,包括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甘肃和陕西的大地湾文化等,这些文化大体上与伏羲氏所留遗迹的范围相当,因而这些文化(有学者称为前仰韶文化)应属于伏羲文化的范畴。据与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对照,当时的氏族生活有的似乎仍以渔猎经济为主,但已有了原始的农牧业,有的则已开始定居农业。从发展水平看,裴李岗文化年代稍早,发展水平也略高于磁山文化,尤其是甘陕一带的大地湾文化。
裴李岗文化大约延续了近两千年,从河南新郑、舞阳贾湖等裴李岗文化遗址来看,当时人们对于居住地址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在河曲的台地上,这是原始人从山洞出来以后,经过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慢慢总结出来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方便生产和生活。而他们得以来到河曲台地生活的条件之一便是半穴居建筑技术的发明。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等,三足钵、三足壶、小口双耳壶等各种陶器则是当时主要的生活用具。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当时已有公共墓地,从随葬品看,男性墓多随葬有石斧、石铲,女姓墓多随葬有石磨盘、石磨棒,这反映出当时的男女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可见,裴李岗文化的居民已经过着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了。
新郑沙窝李遗址中还发现了粟的炭化颗粒,这说明裴李岗文化的农业是以粟为主要作物的。长葛石固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各种形式的骨器,其中有两件管形骨器十分引人注目,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的乐器。舞阳贾湖文化遗址的年代,经碳14测定并经过树轮校正,应在距今8500年至7500年之间。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随葬的龟甲、兽骨和石器上,发现有契刻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另外,还发现了16支七孔骨笛,经鉴定和测试,确知其已经具备音阶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贾湖之所在与柏皇氏活动的中心地带——河南西平,距离很近。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狗、猪、鸡、牛的骨骼,说明当时人们已饲养有家畜和家禽。发现的鱼镖、骨镞,说明当时的居民还从事一定的渔猎活动。贾湖遗址有的墓葬随葬有龟甲,说明墓主人生前可能是巫师(古时的巫师往往是居民的管理者)。从磁山文化出土的纺轮、骨针、骨梭来看,当时的居民已经能够纺织和缝制衣服。这些发现都可与古籍中所载的伏羲事迹与发明相互参照。贾湖遗址的墓葬中,第344号墓十分特殊,墓主为壮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有石器、骨器、牙器及龟甲等30多件。骨器包括有2件骨笛,应是巫师举行祭祀活动的乐器,而龟甲则是巫师手中占筮的灵物。这是当时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有力证据。
《论衡》载:“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知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陵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八卦以治之。”[8]因此,伏羲时代应该已经开始进入野蛮社会的中级乃至高级阶段。贾湖遗址面积约55 000平方米,但“只发掘了2 300多平方米,就发现各类灰坑300余座,发现了30余座房址,清理300多座墓葬”[9]。据推算,这里应是一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的遗址。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化的趣向,这种倾向显然有碍于蒙昧人和野蛮人部落的进步……人们在地域上相互分离之后,到了相当时间就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至于各自独立。这不是一个短时期的事情,这是几百年、最后累至数千年的事情[7]103。伏羲氏之裔的15世,虽在地域上可能互不通属,但“各领风骚数百年”,共同创造了伏羲时代3000年的辉煌史。其时,当为野蛮时代中级的最后阶段,即将进入野蛮社会的高级阶段。
二
从生物学的角度说,没有一种高等生物像人类那样,自发的相互敌视、相互杀害。马克思在谈到氏族社会的战争时说:“一个共同体(指部落组织——引者)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10]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在蒙昧时代,“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11]20。他还说,由于氏族制度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故而“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和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11]110。
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古代的部落战争逐渐转化为阶级社会的战争,成为少数特权者手中政治暴力的工具了。恩格斯说:“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12]中国历史上,伏羲时代大概属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晚期,神农时代则属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黄帝时代则进入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在这几个时段,战争是愈演愈烈。《庄子·胠箧篇》载,伏羲与神农时代,“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1]112。大概是伏羲时代战争较少,给庄子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使之把伏羲时代作为自己推崇的治世典范了。
到黄帝时代,战争便多了起来。《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13]3共工氏是存在于中国上古时期数千年的一个部族,从共工氏与其他部族的战争记载中可看出当时战争的频繁性。相传共工为水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所处的年代,《礼记·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郑玄注曰:“共工氏无禄而王谓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间。”《国语·鲁语》韦昭注:“共工氏……在戏(牺)、农(神农)之间。”《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牺,神农者也。”《列子》张湛注亦说:“共工氏兴霸于伏牺、神农之间。”实际上,从古史材料来看,共工之事迹与许多上古帝王都有交集。
(1)共工与女娲的交集。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载:“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路史·后纪·卷之二·女皇氏》载:“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乱,振滔洪水,以祸天下,隳天纲,绝地纪,覆中冀,人不堪命。女娲氏役其神力,以与共工较,灭共工氏而迁之。然后四极正,冀州宁,地平天成,万物复生。”
(2)共工与颛顼的交集。《淮南子·兵略训》载:“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史记·律书》载:“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太平御览》卷908引《古文项语》载郑子产说:“昔共工之卿日浮游,自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尝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王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
(3)共工与帝喾的交集。《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共工与高辛争为帝。”《史记·楚世家》记载:“共工氏作乱,帝窖使重黎诛之而不尽。”《淮南子·兵略》载:“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
(4)共工与帝尧的交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5)共工与帝舜的交集。《淮南子·本经训》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民皆上丘陵,赴树木。”《韩非子·五蠢》记载说舜帝时有“共工之战”。战争的结果,舜帝取得了胜利。《尚书·舜帝》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拯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曰:“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
(6)共工与禹的交集。《荀子·议兵》载:“是以尧伐壤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荀子·成相》载:“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除共工。”《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禹攻共工国山。”《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共工臣,名曰相栗系……禹湮洪水,杀相哥栗系。”
共工时代从伏羲到大禹,持续数千年,可知共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称谓,而且还是一个部族的名称。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这样认为,作为上古氏族、部落和部落盟首领的伏羲,他的名号既代表个体(也代表氏族群体),又代表被其文化泽及的其他氏族和部落群体。当然,不唯共工,其他部族间的战争也是非常频繁的。
古往今来,因为人类自己的战争,使得无数人死于非命。但是,人类这个种族,却没有因为种族内的相互争斗而使得数量减少。相反,人类却因为战争的关系,使得社会进步、历史延续、文明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是文明的催化剂。
三
大禹为五帝之一,但《史记》所载大禹的事迹多在《夏本纪》中,说明在司马迁看来,大禹时代与以前是不同的,应列入夏之范畴。
《史记·夏本纪》所载大禹的功绩,主要在于治水。花大力气治水,说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安土重迁。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大禹扩大了实力,攫取了财富,权力也逐渐膨胀起来,为大禹传子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正如摩尔根所指出:“远较为可能的,世袭继承制的最早的出现,与其说是由于人民的自由许可,毋宁说是用暴力所树立。”[6]247
一般认为,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或“文明的要素”主要为国家的形成、文字的产生、都城的出现和青铜器的发明。其中,权力的强化及其结果——国家的出现,是最基本的特征或最基本的标准。恩格斯曾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2]172的著名论断。国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有了政治生活,从而把人类从野蛮的漫漫长夜中带到了文明时代。在治理水害过程中,各个方国都参与其中。由于大禹领导正确、方法得当,才将水害治愈,大禹也因此得到了各个方国的拥护和爱载。《史记·夏本纪》载:“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13]81正是大家都拥护他,统一的政治集团才得以建立。
《左传》昭公六年曰:“夏后氏官百。”说明大禹时期的官僚机构已经形成并有了分工。大禹在帝舜时期担任司空,主要负责平治水土,并兼任总领联盟内各项具体事务的“百揆”。大禹接受治水的任务后,首先“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13]51,即命令各部族首领、公职人员及其所属民众,都必须参加平治水土的役事。这样,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治水队伍。其次,访求贤者和专门人才。《吕氏春秋·求人》云,禹“忧其黔首”,走遍四方物色人才,“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相助。其中,陶即皋陶,东夷部族首领之一,后皋陶担任司法官。化益即益,善治山泽,长于畜牧,原名大费,秦国之先祖,《史记·秦本纪》说“大费为辅”即指此事。《史记·殷本纪》还载殷之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担任掌管教化的司徒。周族的先祖后稷,也佐禹治水有功,担任了农官。共工之从孙四岳不但辅佐大禹治水,而且还为其建立了官员考核机制。
史载,禹都阳城,而登封王城岗遗址也逐渐被公认为当年大禹所都之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堑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11]181大禹去世后,其子继位为王,所以大禹既是氏族社会最后一个首领,也是国家的缔造者,还是中国阶级社会的第一任帝王。
[1] 王先谦.《庄子》集解本[M].方勇,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14.
[2] 房立中.兵书观止:第1卷[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253.
[3] 王弼.周易正义: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401.
[4] 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22.
[5] 郑樵.通志·三皇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8:31.
[6] 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蒪,张栗原,冯汉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7] 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纯,马雍,马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8]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90.
[9] 许顺湛.史前各阶段对文明的贡献[G]//许顺湛.许顺湛考古论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98-114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5.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2.
[1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杨玉东]
Clan war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country in Dayu period
CHEN Jiankui
(HistoryandArchaeologyResearchCenter,HenanAcademyofSocialScience,Zhengzhou450002,Henan,China)
Wars happened frequently in clan society, this kind of war are called as ancient clan war or tribal war. In Dayu period, Dayu expanded his force gradually in the process of flood control and the battles or wars between tribes to mak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assing the regime to his son. The fact that Xiaqi could take over his father’s regime successfully and found Xia dynasty shows that Dayu was the last clan chef in clan society, the creator of country and the first king of Chinese class society.
clan war; Dayu’s flood control; public regime;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7.02.015
2016-11-25
陈建魁(1965—),男,河南荥阳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研究。
E-mail:hnskycjk@126.com
K21
A
1673-9779(2017)02-0092-05
陈建魁.部族战争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兼论大禹时期国家的形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092-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