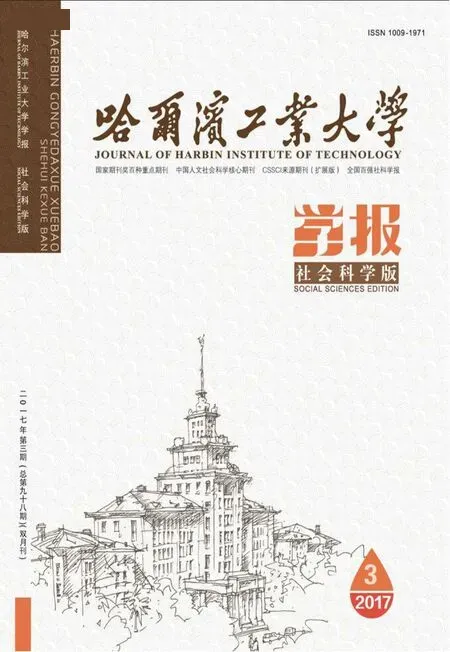“监管中心主义”语境下的社区矫正权责失衡问题
——以浙江省J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监管工作为例
2017-02-24章安邦
章安邦
(吉林大学a.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b.法学院;c.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监管中心主义”语境下的社区矫正权责失衡问题
——以浙江省J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监管工作为例
章安邦a,b,c
(吉林大学a.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b.法学院;c.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通过对浙江省J县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发现社区矫正仍然处于"监管中心主义"的实践状态下。目前社区矫正重中之重的监管工作却存在着"权力小、责任大"的权责失衡困境。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监管中承担了风险极高的脱管责任,却缺少采取强制羁押措施的权力和追捕权等必要的监管权力。同时,监管主体在人力资源上存在着执法人员数量配备不足、特定岗位的司法警察配置缺失等问题。在理论上,从契约论的拟制视角与科层制下的权责观念这两个角度对监管权力的正当性来源进行初步探讨,把社区矫正拟制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签订的约束双方行为的契约,社区矫正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契约义务,监管权力作为在契约一方国家的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理论上追究违约责任、保证契约目的实现的权力;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当中,责任与权力须保持一致,责任的承担需要相应的权力配置。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工作;社区矫正;权责失衡;监管中心主义;契约论;科层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目标,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于进一步完善体现人权保障理念的社区矫正制度的高度重视。该《决定》中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在社区矫正的基层实践中,“权责失衡”的困境与问题凸显。“权责统一”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基本原则。对于权责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本框架下,对国家权力进行“恶”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开展,批判“权力大、责任小”或者“有权无责”等权力问题[1],属于控权论的研究范式。学者很少关注在国家权力体系当中,某些公权力在实践当中却可能面临着“权力小、责任大”甚至是“有责无权”的尴尬困境。这样的权责配置也违背了法治精神,权力主体承担了与其权力不相匹配的责任与风险,因此成为权力体系中的“弱势群体”。本文采取的是“权责一致”的研究范式。
笔者在浙江省J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浙江省J县司法局在2016年共接收社区矫正人员629人,目前在矫人员稳定在册352人左右。笔者与社区矫正管理科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社区矫正执法活动,对社区矫正对象和执法人员进行了访谈,搜集了相关典型案例。笔者发现,社区矫正的权责失衡问题贯穿于社区矫正的全过程。本文对当下社区矫正最为核心的监管环节中的权责失衡问题展开探讨。
一、社区矫正仍处于“监管中心主义”状态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以恢复性司法为理念,旨在帮助服刑人员更好地适应、回归社会,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区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刑罚执行活动。对于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而言,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和矫正方案的具体实施。在实践层面上,监管是当下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环节。实施矫正的前提是得到严格、有效的监管。虽然社区矫正不同于监狱矫正,其具体的执行不是在福柯所描述的全景式监控的“圆形监狱”当中按照严格的纪律、时间表等要求进行[2],但实施矫正的前置性条件就是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监管当中出现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乃至重新犯罪的情况,执法人员在绩效考核中就会承担十分不利的后果,甚至可能会被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发生一次脱管、漏管就可能在绩效考核中让矫正过程中取得的成果都付诸东流。以激励理论看,这样的绩效考核方式缺乏正向激励而以负向激励为主要激励机制,人们在行动中就自然以首先满足负向激励机制作为行为动机[3]。因此,在社区矫正中将监管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是目前绩效考核制度下的最优行为选择。综上所述,目前的社区矫正执法处于“监管中心主义”状态。
二、社区矫正监管当中的权责失衡困境
(一)监管责任的沉重:社区矫正人员脱管的风险与责任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是主持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的主体,负责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管和实施矫正。监管是矫正的前提与基础。由于社区矫正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开放性的特点,给予社区矫正对象比较自由的空间,无法对其进行全天候的监管,无法对其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事前控制。社区矫正人员可能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导致脱管或者重新犯罪行为。所谓“脱管”,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主要是指两类行为:一是未按规定时间报到或者接受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超过1个月的;二是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居住的市、县(旗),或者拒不报告行踪,脱离监管的。“未按规定时间报到”是有客观评价标准的,只需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接收报到和档案管理。“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居住的市、县(旗)”的情况却让司法行政机关难以直接、及时地进行监管。
其原因在于:首先,社区矫正对象除了按照要求定期报到、汇报思想、集中学习、公益劳动之外,处于人身自由状态。社区矫正人员因为游玩、务工、经商等原因擅自离开居住地,执法人员根本不可能准确及时地了解情况。其次,社区矫正人员的服刑意识普遍较弱,尤其是被判处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没有经历过监狱当中全封闭式、高强度劳动的矫正方式,不懂得珍惜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所给予的自由。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大多数被判处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都认为缓刑就是完全赋予其人身自由而不应当再受到任何机关的管理和拘束,其只要消极地不再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外出打工、经商谋生是合理合法的,无视“未经请假禁止离开居住地”的监管规定,外出经商务工,造成脱管,其脱管行为被司法行政机关发现后接到通知或者警告还经常以各种理由拒不及时回归到居住地。笔者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脱管案例,社区矫正人员韦某(开设赌场罪)在缓刑执行期间,其外出尚未得到批准,就擅自与其丈夫外出至广西北海一带养虾,直到几个月后被发现脱管。但是,其投放的虾苗长势良好,预计能够在两个月内收获,因此希望能够继续在广西养虾以谋取生计,韦某对于继续外出养虾的愿望十分强烈。根据《实施办法》,社区矫正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如果继续让其外出养虾直到收获,执法人员就是渎职,毋宁说韦某在广西养虾过程中再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养虾属于高投入、高风险的养殖业,如果不允许其在外继续养虾,其必然遭受重大损失,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成为日后再次犯罪的根源,也无法达到对其进行社区矫正而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的目的,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宗旨。因此,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骑虎难下中承担了实际上的风险与责任。
(二)法定权力的缺位
社区矫正监管活动中一旦出现脱管的情况,就需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状态。根据《实施办法》,司法行政机关只能对其进行通知和警告,并没有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追捕的权力以及采取强制羁押措施的权力。《实施办法》对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当中的职责也仅仅是规定了其对“重新实施了治安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仅仅脱离监管并不符合“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及时依法处理”所包含的处理方式也显得十分模糊。比如,社区矫正人员邹某,未经请假擅自外出,期间还有威胁、恐吓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J县司法局与镇派出所一名民警一起前往L地将其接回,查出其有吸食毒品的行为,由公安机关对其行政拘留。之所以是“接”回J县,是因为J县司法行政机关没有法定的对其进行强制拘捕归案的权力。邹某被查出有吸食毒品的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其行政拘留从而限制其人身自由,至少为司法行政机关下一步向人民法院提起收监建议提供了可能性。否则,即使将其“接”回当地,该县司法局既没有对其羁押控制的场所,更没有被法律赋予对社区矫正人员采取羁押控制的权力,只能将其放回家里,再做进一步处理。在法院裁定收监之前,邹某依然是可以自由行动的,其甚至可以继续外出逃避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一旦邹某意识到其可能被收监执行,就可能在没有实际人身自由限制的情况下逃跑,届时就需要公安机关采取通缉追捕。由此可见,强制羁押的权力与追捕权在社区矫正执法中是缺失的。
1.采取强制羁押措施的权力缺失
社区矫正是在对社区矫正人员做出一定限制的前提下进行矫正,而不是完全地、无条件地将犯罪分子放回社会中。一定自由的限制是实施具体矫正方案的基础。基于脱管等原因符合收监执行的情形并正在向法院提起收监建议的司法程序中,有必要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乃至全面控制。
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定强制方法。《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根据《实施办法》,社区矫正机构就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方面,公安机关拥有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事拘留的权力,检察机关具有决定刑事拘留和批准逮捕的权力,人民法院也具有决定逮捕的权力,监狱机关作为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机关其基本的职能就是严格限制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取保候审制度给予了犯罪嫌疑人相对的自由,与社区矫正制度共享着现代刑事司法轻缓化的基本价值。一旦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符合特定的条件就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对其实施逮捕或者先行拘留。这是对取保候审的必要保障。社区矫正中,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却无法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采取任何限制其自由的措施。所以,有必要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相应的采取强制羁押措施的权力,以保障社区矫正开展。
2.追捕权力的缺失
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无法对发生脱管的社区矫正人员开展追捕,而只能将其“接”回。当下立法没有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追捕权力,也没有明确其他机关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追捕权力。侦查阶段追捕权力的行使目的是为了迫使犯罪嫌疑人归案,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社区矫正中的追捕权是为了在出现脱管、违反监管规定等特定情况下保证刑罚顺利执行,是在特定情况下行使的补救性权力,是为了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进一步的教育、改造和帮扶,恢复社区关系和社会秩序。《实施办法》第19条第2款规定:社区矫正人员脱离监管的,司法所应当及时报告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追查。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追查”是指“根据事故发生的经过进行调查”。因此,司法行政机关仅有组织调查权力而非强制的追捕权力。“追查”的具体方式也未明确。由此可见,司法行政机关缺少追捕权的赋权。
追捕权的赋予是实现社区矫正目的的重要条件。在社区矫正人员脱管后,人民法院裁定收监执行之前,司法行政机关仍需组织追查让其回归到居住地开展进一步调查。根据《实施办法》第23条至第26条,即使是违反规定外出也是需要三次警告并且仍不改正的情况下才可能由人民法院裁定收监执行。在这期间,为了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管、教育、帮扶,防止其在外地重新犯罪,有必要将其追捕回居住地。社区矫正本身就是为了避免监禁刑执行所带来的脱离社会等弊端,让“悔罪态度良好、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分子通过社区矫正恢复被其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区关系与社会秩序。通过社会力量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回归社会,而不是为了让其接受监禁的惩戒。收监的具体规定和社区矫正执法的理念,都以保障社区矫正而非收监为目的。如果符合收监条件,那就意味着其行为已经证明其完全不宜进行社区矫正,必须对其收监执行。
我国的刑罚执行体系中,监禁刑的执行主要由监狱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则主要由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两者所面对的刑罚执行对象都是犯罪分子,而且其对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社区矫正人员当中的一部分便是从监狱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人员也可能因符合法定情形而被收监执行。监禁刑和社区矫正的区别是不同的刑罚执行对象、执行地点、执行方式。两者共同组成我国自由刑的刑罚执行,目的都在于惩罚犯罪、矫正罪犯、预防犯罪。监禁刑执行中,服刑人员有可能通过越狱、行贿等手段逃脱监狱的管理。《监狱法》第42条规定:监狱发现在押罪犯脱逃,应当即时将其抓获,不能即时抓获的,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监狱密切配合。赋予了监狱机关一定限度内的追捕权,即在能够“即时抓获”的情况下行使“抓获”的权力,而追捕就是抓获的具体方式。同时规定在监狱机关不能即时抓获时,可以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实现对逃脱人员抓捕归案的目的。作为全国社区矫正执法依据的《实施办法》,既没有将追捕权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也没有赋予公安机关,存在权力真空地带。
马克思曾言:“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4]现代社会的法律以保护公民自由为目标,国家权力配置、法律制度设计都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社区矫正是国家充分保证公民自由的制度设计,体现国家权力在公民人身自由方面的谦抑。罪犯人身自由的限度伴随着刑罚理念进步而逐步扩大。在当代,刑法规定可以对某些犯罪分子在监狱之外社区当中进行矫正,赋予了公民更多的自由。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的实现要与法的秩序价值协调一致。任何社会都需要建构、维持一定的秩序从而使其良好运转,自由是在一定秩序下的自由,而秩序的核心是安全。“在外面的社会中,成年人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5]197霍布豪斯曾言:“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6]因此,现代刑事司法赋予了社区矫正人员一定程度的自由,也意味着存在一个前提和假设:社区矫正人员能够遵守相关规定,其自由的实现不会危及秩序价值,更不会危及秩序的核心——安全。一旦社区矫正人员出现违反监管规定的情形,就有可能破坏刑事司法的秩序以及社会秩序,对社会安全造成危害。这两种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就有必要为了秩序,亦即社会的整体自由,对违反监管的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自由进行剥夺。所以,从法的价值论来说,社区矫正制度在实践中包含了自由与秩序这一对矛盾体的冲突与协调[7]。由此可见,确有必要对滥用自由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追捕并采取强制措施,维系刑事司法秩序以及社会的安全秩序。
(三)监管主体人力资源配置不足
1.执法人员数量上的配备不足
随着社区矫正的不断试点和推进,人力资源配置上的不足问题显露[8]。笔者调研的J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共有4位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的业务领域内负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监督管理(有必要时直接参与)、接收每一名入矫人员的报到、创建社区矫正人员电子档案、指导管理整体的社区矫正工作以及组织相关的学习教育活动。J县司法局直属的6个司法所共有26名工作人员,司法所的工作除了社区矫正之外包括普法宣传、安置帮教、指导人民调解以及参与乡镇党委政府的相关工作。据某司法所所长介绍,其司法所已将60%左右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社区矫正当中。实践中,岗位职能仅是公务人员工作的一部分,许多精力还要消耗在应付考核、参加会议等。在农村,根据《实施办法》,村双委需组织建立社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小组,调动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矫正当中。根据调研的情况,村一级的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小组,除了定期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签字、盖章之外,不会履行监管职能。因此,社区矫正监管工作的执法主体和参与者实际上就是司法局以及直属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目前J县社区矫正执法人数与监管对象的比例是1∶24,比例严重失衡。由此可见,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只能以监管作为中心工作,无法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全面的教育和矫正,其矫正效果无法达到理想状态。
2.司法警察的配置缺失
社区矫正监管当中的人力资源不足,还表现在缺乏专业的社区矫正警察配置上,公安机关也不参与社区矫正的监管活动,警察的缺位直接影响社区矫正的执法效果。因此,在社区矫正中为基层司法行政机关配置司法警察,使其拥有一定的警察权力,既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也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立法上的可操作性。从中外警察制度发展历史过程来看,新警种的出现往往是执政者积极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实反映,与当时新事物、新情况的出现有密切关联[9]。当下社区矫正监管职能的现实需要呼唤司法警察的配置。
首先,在法律规范上,《人民警察法》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人民警察法》第6条中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的职责。然而,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就不再规定由“公安机关”对判处管制、缓刑和假释的犯罪分子实施社区矫正,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社区矫正的权力由社区矫正机构行使。《实施办法》则明确了社区矫正的执法机构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因此,通过逻辑分析看出,除了“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的刑罚仍然由公安机关执行之外,其余的几类刑罚都应当由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在试点初期仍然由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拥有警察权力,反映了警察权力参与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实施办法》成为执法主体后,社区矫正执法活动的程序更加严格,内容更加复杂。由此可见,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理应获得警察权力,增加警察岗位,作为社区矫正的基本保障。
其次,社区矫正当中配置司法警察是刑罚执行活动的必然要求。刑罚执行是国家司法权最终实现的载体,体现了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虽然相对于监狱矫正具有较高的社会性、开放性,但社区矫正本质上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方式。在刑罚执行中,司法警察的配置也是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安全保障的需要。社区矫正对象都是曾经从事过违法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部分监管对象仍然具备人身危险性,许多犯罪行为甚至是由其性格上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社区矫正是在开放的空间内,社区矫正对象不戴任何戒具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与监管对象在没有任何隔离措施条件下进行直接接触,人身安全存在潜在威胁。在因违反监管规定进行的教育警告的谈话中,社区矫正人员的情绪可能因为对其进行警告和教育而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极度波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J县司法局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没有接受过关于如何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自卫措施和制服犯罪分子的警务培训,一旦犯罪分子对其实施犯罪行为,执法人员甚至很难保护自身安全。J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女性)也反映,在矫正过程中,在单独面对暴力型犯罪分子时,强烈感觉到个人安全无法保障。因此,给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警察编制,让司法警察参与矫正过程,既能保障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也可以提高社区矫正的执法效率。
再次,配置司法警察是对违反监管的社区矫正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的必要保障。社区矫正给予了犯罪分子在社区服刑的相对自由,但其仍需遵守监管规定。根据违反监管规定的情形,社区矫正执法机关有必要及时动用警察权力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为惩罚其违反监管行为创造条件,这些执法活动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司法警察参与。
最后,配置司法警察可以通过警察的符号意义促进社区矫正的有效监管。在布迪厄看来,符号权力是“一种不可见的权力,只有在那些不愿承认自己被它支配甚至运用它的人都屈从于它的时候,它才会生效”[10]。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警察都是使人们趋于服从国家权力的暴力符号。“身着制服的警察,佩戴着随身武器、警棍、徽章、手铐、传讯单以及其他警械,是政府权力流动的象征。”[11]在中国,乡镇公安派出所目前基本上都配备相当数量身着警服的警察,拥有带有明显警务标志的独立用房,并且装备了刷着警徽、顶着警灯的警务用车,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和警示,是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权力的宣示。相较之下,目前乡镇司法所基本都没有自身的独立用房,大部分都“寄居”在乡镇党政机关用房中,基本都不会悬挂司法行政机关有标志性的徽章而仅有一个办公室的门牌,每个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对较少,在日常工作中并未身着特殊制服,一般也不会配有供司法所工作使用的警务用车。社区矫正人员刘某因脱管受到警告后甚至宣称:“我不去司法所报到,司法所也拿我没有办法,他们又不是公安。”虽然在法律规范层面,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对不服从监管的社区矫正人员收监执行,但是就社区矫正的目的而言仍然是尽量通过适当监管和矫正最大限度地实现矫正目的,收监执行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因此,司法警察具有的身份符号学意义在日常监管中可以改变社区矫正人员基本的认知与态度,不再认为“司法所也拿他们没办法”,保障社区矫正的顺利开展。
三、司法行政机关监管权力正当性来源的理论初探
(一)契约论的拟制视角
社区矫正的监管权在传统理论中是国家对公民强制实施的公权力。但是,现代契约理论为理解社区矫正这个区别于传统刑罚理念的现代刑罚制度提供了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的视角。契约精神是现代法治的灵魂。正如梅因在《古代法》中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契约”的本质是意思自治,现代法治用契约作为设定权利义务的手段[13],权力来自民众的授权。刑事司法中,随着诉讼谦抑观与成本控制观的刑事诉讼理念更新,契约精神逐步导入刑事诉讼的程序当中,比如辩诉交易、刑事和解等制度[14]。根据契约论,社区矫正的实质是在作为契约一方的犯罪分子承诺履行相关义务(即遵守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国家作为契约相对人给予其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是双方意思合致的格式化契约。但是,在契约订立、履行过程中,社区矫正人员有可能“违约”(即违反了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在社区矫正人员“不适当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违反了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但不符合收监执行的条件),国家需要强制要求其继续履行契约中的义务;在根本违约(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无法实现社区矫正的契约目的)的情况下,需要强制解除契约,追究其违约责任。无论是继续履行还是解除契约的责任承担方式,都需要作为契约中平等主体的国家行使一定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演化为国家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权力。监管权作为在契约一方国家的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论上的追究违约责任、保证契约目的实现的权力,只不过依然保留着公权力的强制色彩。既然是强制性的公权力,就需要创造和满足其能够强制行使的充分条件。根据《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基层司法机关在社区矫正中就是国家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和代表者,因此在社区矫正监管中,有必要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有效的监管权力。
(二)科层制下的权责观念
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科层结构导致了两种权力的分配方式:一是根据行政权力的不同层次而形成的纵向垂直的划分;二是根据行政权力所指向的不同功能而进行的横向权力配置,即按照具体岗位的职能配置权力。在官僚制的组织结构中,人是与具体岗位联系在一起的,岗位的任务也就是他的任务,岗位的功能也就是他的功能……他只要把岗位的任务、岗位的功能转化为他个人的责任就可以了。所以说,官僚制组织对于其中的个人而言,就是一个纯粹的责任体系,而且是一种单向的、定点的责任体系。官员只要承担了这个岗位上的责任,也就做到了对这个官僚体系负责,他也就是一个绝对合格的官员[15]。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都以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为基本形式,我国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现代官僚制度当中的部分,其岗位责任的履行也需要纵向和横向权力的合理配置,但其目前仍然处于“有责任无权力”的尴尬境地,这种权力与责任的配置方式,违背了现代社会科层制结构中权力分配的基本原理。
权责一致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并且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16]。但是,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一定程度的赋权。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也需要遵循自由与必然统一的原则。该归责原则要求人们在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时要以行为者的自由度为依据[5]137。对于受到高度警惕和限制的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尤其是追捕权、强制羁押权力等有可能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需要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才能授权。因此,在目前“实践先行、立法滞后”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相关义务的基本权力自由,缺乏相应的权力配置,却要承担脱管造成后果的责任,缺乏法理上基本的正当性。
结 语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费用昂贵的过程。社区矫正制度的试点、建立和健全的过程也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责任重新分配和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费用昂贵”就突出体现在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监管中面临的“权力小、责任大”的权责失衡问题。监管当中的权责失衡问题是社区矫正权责失衡问题的集中反映。权责问题是建构现代治理体系过程中必须审慎处理的关键问题,而权责统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奉行监管中心主义的社区矫正实践中,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实际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与责任,而与之相匹配的强制羁押权力和追捕权却缺失,客观上面临着执法人员数量的严重不足与司法警察配置的缺失等。《社区矫正法》正在立法调研当中,期待本研究能为其提供实证材料基础上的理论资源。
[1]秦晖.公共权力、公共责任与限权问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9-13.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夏亮,丁建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问题[J].中国人力资源管理,2004,(6):33-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6.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
[7]谢望原.作为刑罚价值的自由[J].法学研究,1998,(4):36-53.
[8]李端卫,管言明.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人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2):84-87.
[9]董纯朴.建立中国社区矫正警察制度的构想[J].公安研究,2013,(2):53-60.
[10][法]皮埃尔·布迪厄.论符号权力[G]//吴飞,译.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165.
[11][美]罗伯特·兰沃西,劳伦斯·特拉维斯Ⅲ.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M].尤小文,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239.
[12][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7.
[13]邱本,董进宇,郑成良.从身份到契约——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G]//法制现代化研究:第5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詹建红.论契约精神在刑事诉讼中的引入[J].中外法学,2010,(6):913-927.
[15]张康之.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79-85.
[16]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64,222.
Imbalance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Supervision Center Doctrine”—Taking the Supervis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the Bureau of Justice in J County,Zhejiang Province as Example
ZHANG An⁃banga,b,c
(a.Judicial Civiliz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b.Law School;c.Theoretical Law Research Center,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Through the one-month“fieldwork”in Community Correction Management Division of Bureau of Justice in J County,Zhejiang Province,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present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te of the practice of the“supervision center doctrine”.There still exists“small power,more re⁃sponsibility”imbalance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supervision work as the top priority of community correc⁃tion.Grassroots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take high risk responsibility in the supervis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without necessary regulatory powers such as the power of adopting enforcement measures and the power of pursuitfor its supervision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members.Atthe same time,in the human resource ofthe supervision body exists the problem of the insufficient amount of officers and the missing of judicial police in the particular position of role configuration,which leads to the grassroots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incapa⁃ble of fully exercising the supervisory powers.In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ctual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bureaucracy,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and sets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as a contract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itizen.Behavior of the contract and community corrections should bear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ctualobligations.The power ofsupervision in essence is a power in the contracting party to pur⁃su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contractand to ensure the purpose ofthe contract.In the Weber sense ofmodern Bu⁃reaucracy,responsibility and power must be consistent,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mitment needs the corresponding power allocation.
grassroots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supervision work;community correction;imbal⁃ance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supervision center doctrine;theory of contract;bureaucracy system
D926.8
A
1009-1971(2017)03-0032-07
[责任编辑:张莲英]
2017-02-15
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司法权地方化问题研究”(2016055)
章安邦(1989—),男,浙江缙云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法社会学、司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