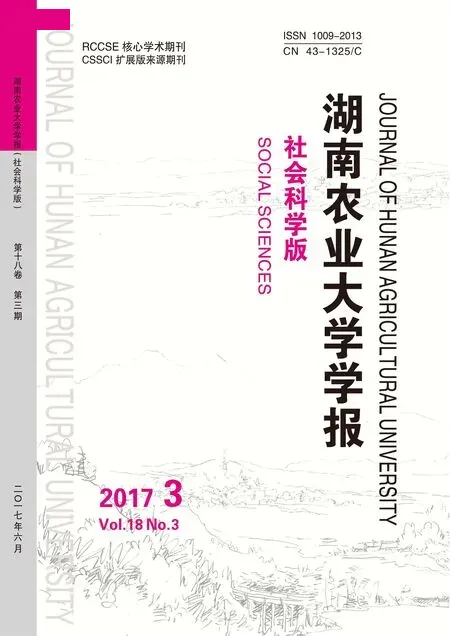新中国城镇化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基于城乡关系视角的考察
2017-02-24左雯敏樊仁敬迟孟昕
左雯敏,樊仁敬,迟孟昕
新中国城镇化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基于城乡关系视角的考察
左雯敏,樊仁敬,迟孟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建国以来的城镇化演进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阶段有其不同特征。1949—1978年为城乡二元结构时期,以统购统销制和生产生活资料配给制为主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封闭和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建国三十年极其缓慢的城镇化进程。1979—1994年为工业城镇化时期,以发展工业为动力,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较快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1995—2013年为土地城镇化时期,以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为动力,形成了“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进程日益加速。2014年以来为“以人为本”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时期,试图矫正工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时期形成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难和农村衰败的历史遗留问题。
新型城镇化;城乡关系;以人为本;城乡统筹
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作了细致阐释,明确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任务,新型城镇化取得良好进展。针对新型城镇化所存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2016年2月,国务院又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城市改造、提升城市功能、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新农村等工作做了更加具体的指导。
与此同时,学界也在积极探讨新型城镇化的相关议题。仇保兴[1]、张占斌[2]、姚士谋等[3]侧重于解析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并针对城镇化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与上述视角不同,笔者拟以城乡关系史为轴,通过梳理新中国城镇化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不同特征,以此考察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以及“新”“旧”之差别,以更好地理解城镇化的历史沿革和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与实践。
一、1949—1978年城乡二元结构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在破坏一个“旧中国”后,中央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当时最主要的是解决“立国”问题,城镇化不仅没有作为重点工作有意加以推进,反而因为行政体制及若干人为因素阻滞而进展缓慢。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城乡二元结构时期,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以及封闭僵化的城乡关系、工业结构和工业化水平等决定了这一时期城镇化率不高,城镇化率仅从1949年的10.64%增加到1978年的17.92%。
新中国初期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非常脆弱,中央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4],试图通过发挥中国农业优势自力更生地完成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土地改革已经将农村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严重影响原始积累的速度。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为满足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现实需要,集体化改革应运而生。国家权力一改“皇权不下县”的历史样态,第一次全面而正式地进入农村,并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分配制度等行政性手段高度控制了农村社会。这一时期城市工业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生产机械化为主,只能吸纳一部分劳动力,呈现出“资本增密,排斥劳动”[5]的格局。城市发展工业和农村发展农业,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块,城乡关系被行政切割,并通过户籍制度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固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与包产到户以后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市场主导型的不同,这一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行政主导型的,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6]。
城乡二元结构是改造小农经济、减少消费、增加积累、优先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的产物。在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下,人口、资源等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要素的城乡流动主要通过国家主导的计划手段来实现,其中最主要的制度安排是统购统销制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配给制。城乡二元结构使农业人口滞留农村,捆绑和聚集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效率日益低下,农业经济逐渐“过密化”。到70年代末期,传统集体经济与体制终于难以为继。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小城镇也开始衰落。根据费孝通对吴江县小城镇的调查研究,从农村方面说,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形态,使农民不再有富余的农副产品可以拿到小城镇去交易以互通有无,于是小城镇就失去其作为农产品集散中心的地位。从城镇方面说,以生产为主的城镇,实行的是国营化经营方式,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垄断在国营部门手中的统购统销几乎是城乡和工农间唯一的流通渠道,使得个人无法在城镇谋生,只能离开城镇,留不住物也留不住人的城镇自然而然就日益萧条。
纵观建国初期三十年,封闭僵化的城乡二元体制妨碍了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大地阻滞了新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城镇化并不是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城镇化率过低、城乡分割制度化,客观上造成日后城镇化建设起点低、包袱重、制度环境复杂的局面。
二、1979—1994年工业城镇化时期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这是新中国城镇化演进的重要阶段。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工业城镇化是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及其要素流动的根本特征。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工业化,特别是乡镇企业快速崛起并带动了小城镇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乡镇企业成为此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引擎。这是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波城镇化浪潮。城镇化率从1979年的18.96%增加到1994年的28.5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裹挟下的纯粹计划经济逐渐显现出其资源配置上的力不从心,工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关系封闭僵化,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弊端都成为改革的重要背景。鉴于农民土地的重要性,包产到户成为首要的改革举措[7]。包产到户并没有使农村土地权属一夜回到解放前,而是土地权属分层设置的土地制度创新:土地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和收益权归农户所有;农户与集体的关系本质是一个租佃关系。这一制度安排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照顾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同一个村庄的分化程度较小,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
1984年中央鼓励乡镇企业四个轮子(镇办、村办、户办,连户办)一起转,乡镇企业正大光明地迎来了春天。乡镇企业的前身是集体时期的社队工业,是为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服务的附属机构,并不作为市场主体而出现。社队工业在改革开放前被界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需要被割掉的“尾巴”,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从客观功能上看,乡镇企业发展是解决当时城乡关键问题的一把钥匙。它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农民家庭收入得到提高;乡镇企业生产的轻工业产品改善了工业结构,提供了多样化的消费品;乡镇企业的税收和利润同时还为城镇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一度在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二”,为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提供了产业基础。
在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制的刺激下,地方政府放水养鱼培植税源,兴办乡镇企业,几乎村村冒烟户户上班,中国掀起了一场工业化的浪潮。其中,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公社时期的集体积累,温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劳务输出形成的国内市场网络,珠三角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香港资本和工资低价差;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8]。乡镇企业的兴盛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在自身传统优势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开始复苏,其中苏南小城镇比较典型。根据《小城镇大问题》,震泽镇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中心,盛泽镇作为丝织工业中心,同里镇作为文化休闲产业中心,平望镇作为水路交通枢纽,这些不同类型的小城镇都依靠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城镇经济的复苏而兴起。小城镇各式各样,但它们都是一定区域内各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9]。这些拱卫小城镇的农村被称为“乡脚”,费孝通的原话是“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乡脚”这一概念形象地说明城乡关系中乡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城乡一体俱荣俱损的特征。
捆绑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力在大包干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得到释放,僵化的城乡关系开始激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产生了一部分自由流动的资源,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开始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社会精英的流向也多样化,不少体制内的工人和干部向体制外流动。单位也不再作为国家的“部件”和全能的保姆,而开始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市场主体,活跃在新的历史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央政府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实行双轨制,开始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各种要素的城乡流动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逐渐被打破。相关的调控手段和利益主体发育也日益多样化。总之,中国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进入到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新阶段[10]。
工业城镇化时期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表面上看,小城镇是城乡联结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模式是统筹城乡关系的优良模式,但也造成了“镇强城弱”的城镇结构问题。“镇强城弱”的格局由于缺少中心城市的主导和辐射作用,进一步制约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从农村方面来说,包产到户使土地过分细碎,农业经营无法达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业逐渐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三、1995—2013年土地城镇化时期
如果说,工业城镇化是以经营工业为先导的城镇化,那么土地城镇化则是以经营土地为先导的城镇化。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既改变了中央地方关系,也改变了政企关系,中央征收增值税的75%,地方征收25%,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的“蛋糕”被中央切走了一大块,地方政府失去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动力,乡镇企业不再成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动力。面对财政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又寻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土地或土地指标为核心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开启了一轮经营土地以经营城市的“造城运动”,掀起了新中国城镇化的第二波浪潮。这一时期的城镇化主要围绕土地问题展开,因而可以概括为土地城镇化时期,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04%增加到2013年的53.7%。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纷纷倒闭或转制,仅1995—1997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就减少了上千万。乡镇企业不再成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动力。农民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大中城市或东南沿海寻找务工机会,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支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大军,构成了中国农民工迁移流动的波澜壮阔的图景。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加大了从基层汲取资源的力度,造成农民负担增加[11]。21世纪初,中央政府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5年,农民不再交纳“皇粮国税”,负担大大减轻。基层政府几乎不用再跟农民打交道,其赖以运转的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政府或地方富人的借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疏远表现为基层政权的“悬浮”状态。
分税制改革同时也启动了一场经营土地以经营城市的造城锦标赛[11]。城镇住房制度开始市场化改革,人口离土又离乡地流入城镇与城镇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房地产发展的历史契机。不久之后,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土地被征用纳入城市建设中来,进城建筑人员和进厂务工的年轻人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为将农村土地转变成城市建设用地提供了法律依据,大兴土木的城镇化浪潮逐渐兴起,形成了以土地财政为中心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用、开发、出让,一方面获得国有建设用地用于城市建设,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并在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下,从银行获得土地抵押款用于城市建设,构成了由土地、财政、金融三个要素组成的循环机制,不断将土地和资金吸纳进来,造就了日新月异的繁荣城市[12]。以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为基础的城镇化,构筑了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城镇化的模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13]。
以土地财政为中心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以土地、财政、金融三要素为基础形成一个封闭的城镇化系统,只要能够满足土地指标的要求,这一封闭系统就会进入自我循环。这种城镇化模式以土地而非产业和人口为中心,因此不以工业化为前提,也不以人口城市化为必要条件。在这种局面下,农村劳动力虽然从农村涌入城市,但仍是没有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家庭成员仍然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土地城市化不仅造就了收入差别巨大、社会地位悬殊的城市二元社会群体(城市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产生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也割裂了这些流动人口的家庭。也因此,这样的造城运动极容易制造出如同鄂尔多斯一样的鬼城。
与之同时,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历史境遇,“东部城市不能落地,中西部城市不能养家”[14]。工业城镇化把人口吸引到城镇,可是在土地财政推高的高额房价面前,却无法在城镇落地并实现全家团圆安居乐业的梦想,因而高频度的人口流动仍在继续。结合农业转移人口的代际差异,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庭都出现“一个家庭分散在不同省份打工”的窘境。年迈的父母逐渐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淘汰回到老家,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则加入到进城劳务大军,体现出非常鲜明的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另一方面,东部城市的高房价让农业转移人口有心无力,望“城”兴叹,他们往往集全家之力回到老家的城镇买房生活,并且在买房的地理位置选择上呈现出一定的梯度。原来居住在村里的可能到乡镇或县城买房,原来在乡镇的可能到县城或地市买房。这一梯度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浪花倒卷”回流到中西部地区而形成了一个梯度城镇化的特点[15]。以“一个家庭分散在不同省份打工”为代价,这些农业转移人口最终实现了城镇化梦想,尽管是以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在土地城镇化的浪潮之后,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是如何在城市聚集“人气”,将硬件与软件配合起来,将人口、产业和城镇配合起来,形成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城为本或以地为本的城镇化思路与实践。
四、2014年至今的新型城镇化时期
新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城乡二元结构时期、工业城镇化时期和土地城镇化时期,遗留下不少历史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较低、制度环境复杂、城镇结构不合理、农业转移人口落地困难、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产业配套不合理、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乡村凋敝、区域差异大等问题。
2014年3月,中央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一条有别于工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试图解决早期城镇化演进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并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总体而论,新型城镇化主要解决的是“人”和“城”两个问题,一个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一个是城乡统筹的问题。其中属于以人为本的政策主要包括放宽户籍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大的落户可能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创业、养老、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完善城镇发展体制机制,包括人口、土地、资金、住宅、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的水平等。属于城乡统筹的政策主要包括优化城镇化布局,增加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形成一个完善合理的城市群;积极统筹推动城乡一体化,重点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型城镇化政策出台之后,城镇化率从2014年的54.77%到了2016年的57.35%,年均增长约为1.3%。不仅城镇化率保持了高速增长,而且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缩小城乡之间差异来看,也取得了不少成效。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推动城乡统筹,实现人与城的融合,除了“人就城”,还可以“城就人”,主要体现在“农民上楼”和资本下乡两种模式。“农民上楼”是新型城镇化时期由政府主导、资本介入推动农民就近集中居住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农民上楼”的城镇化新形态之所以出现,既与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的需求有关,也与土地政策有关,它可以通过增减挂钩[16]政策为城市建设提供用地指标。中央政府严格控制耕地,农民宅基地通过土地整理可以置换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仅城郊土地或政府规划的交通线附近的土地可以置换,而且在成渝等地的城乡统筹改革试点中,偏远地区农民的土地也通过“地票”运作的方式,“漂移”到城里参与城市建设[17]。
与“农民上楼”相伴随的是资本下乡。资本下乡主要从事的是农村房产开发、土地整理和承包经营。关于资本下乡对村庄治理的后果,学界形成了两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资本下乡造成了农业经营的“去社区化”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下乡之后并没有跟农村社区进行融合,而是形成了一个“悬浮型”的资本下乡格局,进而主张重构以农村社区为本位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18]。另外一种观点是,资本下乡在政府的扶持之下,村庄依附于公司,公司成为了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村庄公司化意味着政府在经营城市之后,开启了政企联合经营村庄的模式。资本下乡是政企联合经营城市之后又渗透到广大乡村地区开始经营乡村的历史新现象[19]。资本下乡通过项目制获取了大量资金,是有利于企业获益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资本下乡与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在发生且需要深入观察的重要议题,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资本下乡流转土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使部分农民对自身的土地权属产生了质疑。为安定人心,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并统筹城乡发展,2014年国家开始实施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所有,经营权归经营者所有,实质上是土地权属分层设置的延续,其目的是凸显农户的承包权,既安定了人心,又给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在城镇化更大幅度且较为稳定地调整人地关系之前,这样的产权安排虽然给城乡要素流动增加了一些交易成本,但具有稳定农村的重要作用。
新型城镇化的思路和实践正是试图矫正工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时期的弊端和历史遗留问题。要言之,新型城镇化应当一方面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地生根聚集“人气”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统筹城乡发展,以实现人口、产业和土地相互匹配、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并助力中国经济的发展。着眼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而言,如果梯度城镇化和“浪花倒卷”的“曲线救国”这两个特征具有普遍性,那么在城镇化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基础性工作应该是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和地方产业,积极完善公共服务,使得返乡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一段迂回曲折的打工经历之后回到家乡,并能够全家团圆、安居乐业。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家庭为视角来完整看待农民的城镇化和市民化选择,并制定“因家制宜”的城镇化和市民化政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城镇化史的必然选择,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毕竟,农村和农民都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 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11-18.
[2] 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48-54.
[3] 姚士谋,张平宇,余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6):641-647.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 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J].北方经济,2003(8):12-16.
[6]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J].北方经济,2003(8):12-16.
[8]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9]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0]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47-62.
[11]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100-115.
[12] 周飞舟.以利为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3] 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1):66-83.
[14] 王绍琛,周飞舟.打工家庭与城镇化——一项内蒙古赤峰市的实地研究[J].学术研究,2016(1):69-76.
[15] 周飞舟.就地就近城镇化战略思路与地方经验——地方产业和就地就近城镇化[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6(2):95-97.
[16] 谭明智.严控与激励并存: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脉络及地方实施[J].中国社会科学,2014(7):125-142.
[17] 曹亚鹏.“指标漂移”的社会过程——一个基于重庆“地票”制度的实证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4(2):55-91.
[18] 孙新华.农业规模经营的去社区化及其动力——以皖南河镇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 2016(9):16-24.
[19] 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6(1):49-52.
责任编辑:曾凡盛
Four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evolution in new China: Based o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ZUO Wenmin, FAN Renjing, CHI Meng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each stag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period (1949—1978), the institutions such as state monopoly of the purchase and marketing and allotment system of production goods and consumption goods, made urban-rural and industrial-agricultural separation by administrative means, forming a closed and inflexibl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resulting in a slow urbanization process for three decades. During the industrial urbanization period (1979—1994), urbanization was driven by industrialization, especially depend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small towns. During the land urbanization period (1995—2013), urbanization focused on land and city, forming a trinity with“land, finance, banking” urbanization model. These three stages of urbanization left some historical problems, and the slow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ural area are particularly salient problems.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new urbanization (since 2014), which is human-oriented and tries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to correct the drawbacks and historical problems of industrial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human-oriented; overal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10.13331/j.cnki.jhau(ss).2017.03.008
F299.21
A
1009–2013(2017)03–0044–06
2017-04-28
左雯敏(1990—),男,江西宜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