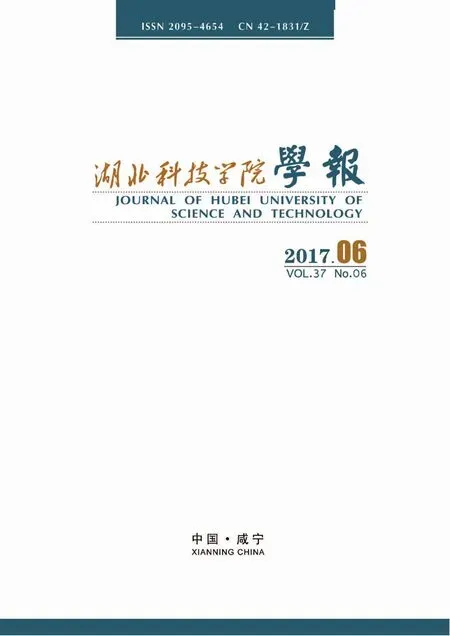民间性与现代性:晓苏乡村小说叙事的两侧
2017-02-24周文慧
周文慧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 430034)
民间性与现代性:晓苏乡村小说叙事的两侧
周文慧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 430034)
晓苏的乡村小说通过混合的民间思想、传统的民间伦理和丰富的民间叙事策略体现民间性特点。同时,他通过对民间传统、风俗的质疑与反思,以生命伦理至上的民间伦理体系的重新建构以及对民间的现代性多元叙事体现出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晓苏;乡村小说;民间性;现代性
晓苏出生在湖北省西北部的山区乡村,他的乡村小说以故乡“油菜坡”为中心构建起一爿精神栖息的家园。在晓苏的乡村小说中,他将根植于心的民间观念通过油菜坡的民间生活状态及民间生活的审美趣味展示出来。同时,他又超越了平面化的民间叙事,既对油菜坡的传统民俗进行了现代性反思,又在城乡文化对峙、传统与现代思想交锋中进行了社会现代性的反思。
一、根植于乡村大地的民间性叙事
晓苏的乡村小说以亲情为纽带、以乡情为依托叙述了“油菜坡”乡民的生活状态,在丰富的情感交织中展示“油菜坡”民间生活的多元色彩。“油菜坡”成为晓苏民间精神的滥觞与文学创作的源头,他得心应手地展示油菜坡的风土人情,在民间性特质的表达上显得游刃有余,正如贺绍俊所言其小说体现“精致的民间文学风格” 。
(一)混合的民间思想
晓苏乡村小说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油菜坡”的乡村村民,崇山峻岭的阻隔使他们聚居于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民间生活形态,较好地保留着原始而朴素的民间思想。其乡村小说流露出混合着家族观念和实用信仰等内涵丰富的民间思想。
晓苏小说通过宽泛的血缘观念、礼俗观念和个人依附于家族获得的认同感和尊严感来表达浓郁的家族观念。父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婆媳关系、叔侄关系等共同构成了晓苏小说的人物关系图谱,并通过宽泛的血缘关系形成传统的、稳定、封闭的家族结构。作者通过不同血缘关系的横切面叙事反映出血缘关系笼罩下的多层次民间生活状态。同时,在强烈的家族观念的影响下,晓苏在多篇小说中设置了家族关系维系者和家族观念守护者形象——“我”。《侄儿请客》中保留淳厚家族观念、回乡为大哥上坟的“我”,《农家饭》《我的三个堂兄》中留恋家族亲情、资助兄弟表嫂的“我”,《我们应该感谢谁》中带有家长风范、悉心呵护家庭与乡亲关系的“我”,都是心灵皈依于家族传统的家族观念守护者形象。在价值观念日益丰富的油菜坡,“我”在处理各种家庭事件中即使被他人日益淡化的家族观念所伤、被繁琐庸常的家庭琐事所累,但仍将家族的血脉关系置于复杂人际关系的顶端,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价值体系的中心,并把家族的延续与发展作为个人精神追求的内核。
礼俗活动既是家庭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强化家族观念、增进家族成员间情感的常见方式。在晓苏的乡土小说中,过生日是最集中表现其礼俗观念的叙事内容。《生日歌》《土妈的土黄瓜》《甘草》《给丈母祝寿》《挽救豌豆》等小说叙述了在民间传统孝道的影响下,油菜坡保留着原始的尊老传统:在长辈生日时,晚辈即使相隔千里、经济困窘也要尽其所能、专程前往表示庆贺。这一礼俗活动背后隐藏的是对长幼有序民间传统的尊崇和对家族血缘关系的维护。而《松油灯》《劝姨妹复婚》《姓孔的老头》《回忆一双绣花鞋》《日白佬》等则以过生日这一礼俗活动传递平辈之间的关怀与问候,以改善或增进情感的交流。此外,晓苏还通过其他的礼俗活动突出家族观念。《人情账本》《坐下席的人》《住在坡上的表哥》写家族重大节日、活动时亲戚间请客吃饭及人情往来,《侄儿请客》《我们应该感谢谁》《等冯欠欠离婚》《矿难者》《桠杈打兔》等小说通过新年为死去的亲人上坟烧纸钱,孝子为死者圆坟,给死去的亲人过百日、周年,为死者撒五谷等丰富的富有仪式感的葬礼活动表达对死去亲人的祭奠、敬畏之情。
个人在家族中获得的认同感和尊严感是保持家族稳定的内在条件。晓苏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这种认同感和尊严感在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成员的归属感方面的积极作用。《村里出了个打字员》叙述在家庭认同感的关照下,万福一家虽然经济困顿,但彼此精神的相通让他们共同享受着富有诗意的生活。《麦芽糖》中父亲在儿子每天为他抓背这样温馨而简单的家庭生活中体味着儿子对他的尊重与顺从,享受由家长尊严带来的简单而快乐的获得感;儿子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有出息,但他对父亲在家庭中权威身份的认同感让他为父亲发自内心地尽孝。而《土妈的土黄瓜》《坐下席的人》《住在坡上的表哥》等小说表达了土妈和表哥们对家族成员心中认同感的呼唤和尊严感的捍卫,从而肯定了认同感和尊严感对家族稳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晓苏小说还表现深藏民间的实用信仰,这种信仰与家族观念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晓苏乡村小说丰富的民间思想形态。晓苏一方面通过不同的民俗活动表现早已化为文化基因在鄂西油菜坡传承的实用信仰:在婚嫁生养的民间风俗中,通过撒花生以求早生贵子;在丧葬风俗中,请阴阳先生选择祖辈埋葬的风水宝地以求泽被后世;为死去的亲人烧纸钱、撒五谷以求其在另一个世界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种混合着实用信仰的民间思想既是当地乡民集体的精神寄托,也是各种宗教杂糅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作家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刻画反映油菜坡村民务求实用的价值追求。《金米》中九女的儿子鉴于金米产量低、收入少而烟叶产量高、收入多的实际情况,果断地放弃了金米的种植而改种烟叶;《老板还乡》中面对落魄而归的老板朱由,朱原、朱因和村民立马意识到无法从朱由身上得到实际的好处而纷纷躲避他;《糖水》中“我”和表妹喜鹊青梅竹马,以前每次去姨妈家有糖水喝,而后来姨妈知道因为近亲关系“我”不能和表妹结婚,“我”就从此没有了喝糖水的待遇;《麦子黄了》中村里的光棍们听说姬得宝得了癌症后觊觎他的老婆徐瓜,主动上门帮忙她割麦,但当傻子金盆戳穿姬得宝的阴谋后,光棍们马上都不再来帮忙了。这种实用信仰源于相对狭隘的个人价值追求和务实的人生态度,作家通过实用信仰写出了油菜坡村民相对简单的生活目标和明晰的价值取向。
(二)传统的民间伦理
民间伦理是产生于民间、且游离于国家伦理之外的,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呈现民众共同情感欲望和道德取向的伦理观念。在表现形态上,“民间伦理则是不定型的、由普通民众在其实际生活中自发形成、在话语表达上居于主流之外的价值观念,它广泛地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非理论化的现实状态之中。” 晓苏的乡土小说通过对善恶相报、孝悌之道、重礼贵和等伦理思想的诠释,延续和发展传统道德伦理思想。
善恶相报是民间传统的伦理思想,它在规劝民众向善、惩恶方面起到了引导和教化的功能。在晓苏的乡村小说中,他多次诠释了这一民间伦理。在《黑木耳》中,石丁、石棉、百合都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处处为对方考虑得很多,所以获得了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圆满结局。《母猪桥》中白天鹅般的医生甘露在杨桩生殖器受伤严重时,出于职业道德挽救了他,此后虽然经历了因为村民的封建思想和丈夫的狭隘心胸影响而导致的离婚、孩子流产等一系列不幸的事情,但最终因为杨问柳的感恩,并与她结婚生子,开启了幸福的生活。《麦子黄了》中傻头傻脑的金盆出于人性的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地帮助徐瓜,最后,徐瓜以温柔的亲吻和深情的拥抱回报金盆的帮助,满足了金盆饥渴的性欲。晓苏认同民间伦理中善有善报的思想,用人性的善在底层叙事中苦难的底色上增添了明亮的色彩。同时,他也以恶者遭殃直接表达了对恶有恶报民间伦理思想的赞同。在《天坑》中张百善用钢钉射死了杨开泰并推至天坑,而当他在得知勘测队要进入天坑勘测地形时,害怕暴露真相又主动跳进了天坑。张百善用自杀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罪行,并希望以此得以灵魂的解脱。《挖坑的女人》中的赵腊梅先后三次跟别人结婚不久就在高速公路工地上挖坑的时候推石头砸死“丈夫”,以骗取赔偿金。她最后也因为蓄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小说中,这些作恶之人或因为深藏于潜意识里的善恶相报的伦理思想的影响,或因为社会法律的规制,都承担了因作恶而带来的惩戒后果。
在民间伦理中,父子关系提倡以孝为纲,甚至百善孝为先;兄弟之间应该彼此关爱:兄长爱护弟妹,弟妹也应尊重兄长。晓苏的乡土小说通过以孝为经、以悌为纬的乡村伦理社会的建构表达他对传统孝悌民间伦理的认可与吸收。一方面,小说多处呈现他对民间伦理中孝道的赞美与推崇。在《村里出了个打字员》中赞扬万水理解父亲生活的艰辛,用写诗的稿费买药医治母亲的重病的行为;《生日歌》中塑造的易怒而敏感的邱金形象,虽然两次因伤害他人而获刑,但他的初衷都是为了给父亲过生日以尽孝道;《油渣飘香》中的姚学本对父母孝顺,甚至以更高的境界把孝道延伸到对干妈的感恩中,把本打算给父母换彩电的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用来翻修干妈破败的房子;《麦芽糖》中的“我”对父亲的陪伴是最温暖而幸福的尽孝方式。另一方面,小说也展示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心与爱护。《你们的大哥》中的“大哥”在弟弟们成长的道路上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名誉、金钱甚至青春,用无私的爱帮助弟弟。《人住牛栏》《姑嫂树》则写出了乡村女性以微薄的力量对弟弟妹妹给予人性的关怀;《姓孔的老头》《住在坡上的表哥》通过年过半百的老孔每年惦记着给表妹王香过生日和经济贫困的表哥竭尽所能地迎接表弟写出了兄长对弟妹的爱护与尊重。而《我的三个堂兄》《农家饭》以原乡者“我”的形象写出了弟弟对兄嫂的尊重与帮助;《矿难者》《桃花桥》《钟点房》《松油灯》通过小斗、妹妹和表弟对哥哥压抑性欲痛苦的理解、并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化解他们的苦闷的叙事深层次地体现了弟妹对兄长的尊重与帮助。可贵的是,晓苏在小说叙事中没有简单地以道德的标准去表现孝悌之道,他往往把叙事的着力点放置在人性的高度,从人性的关怀表现美好的家庭孝悌伦理关系。
(三)丰富的民间叙事语言
晓苏是一位有鲜明民间叙事意识的作家,其小说在叙事语言和叙事资源的选择等叙事策略上体现了鲜明的民间化特色。
晓苏的乡村小说通过方言、粗俗语言和狂欢化的叙事语言体现民间叙事的语言特点。“独特的方言,对于优秀的地域文化小说,绝不仅仅是某种点缀,某种类似于调味品或舞台道具的东西。事实上,它们对于营造小说的氛围、塑造人物的特性、传达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常常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晓苏乡村小说通过鄂西北方言的穿插使用展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也体现了丰富的民间特色。具体而言,在小说中,多次用到“娃子”作为名词词缀以表示对某人的亲热、喜爱,例如“媳妇娃子”、“媳娃子”,用“子”放在名词后表示指称,例如“月母子”、“水管子”、“邪子”、“胯子”、“唢呐班子”、“手颈子”等。也多处使用叠音词,例如“黑黢黢”、“凉飕飕”、“白花花”、“酸溜溜”、“蓝莹莹”等。在方言词汇的使用上,晓苏偏爱选取具有地方特殊意义的词汇凸显民间语言的特质,例如“花被窝”、“打皮绊”、“桠杈打兔”、“日白佬”等。他通过方言将对故乡的原始记忆移植到文学作品中,借此显示其文学的地域性和民间性。同时,晓苏也在狂欢化的叙事语言中体现其民间性特点。通过粗俗语言的使用,他一方面暗示小说人物的身份和反映人物的心态;另一方面创设富有民间趣味的语义场,在较原生态的语言环境中推动叙事。例如,《酒疯子》整篇小说多处用“球”附着在动词或形容词词尾,如“别看球了”、“死球了”、“饿憋球了”、“喝聋球了”等等,这种粗俗语言的使用展现了乡民调侃生活苦难的幽默、举重如轻的从容心态和发泄愤懑不满情绪的宣泄方式,反映了农民文化的民间趣味和幽默精神。其实,晓苏已很早就认识到“粗俗语言是民间化叙事的三大语言法宝之一”“地方语言和口头语言,它们和粗鄙语言一起共同构成了民间化叙事的三大语言支撑。” 所以,晓苏在乡土小说语言的选择上,已以自觉的意识利用和展示民间语言,从语言层面丰富作品的民间特质。
二、超越平面的民间现代性叙事
晓苏乡村小说以混合的民间思想、传统的民间伦理和丰富的民间叙事策略体现了浓郁的民间性。同时,我们看到,作家的乡村小说不是囿于对民间、乡土的反复吟唱,他超越了平面的民间叙事,在民间叙事中进行了深入的现代性反思,体现了鲜明的现代性特质。
(一)对民间传统、风俗的质疑与反思
在晓苏的乡土小说中,他多处写到带有强烈实用信仰的民间思想。作者在肯定实用信仰在调整社会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将它们放置于道德、情感的天平上,试图称量出其在道德和亲情伦理构建的体系中的分量。例如,《老板还乡》中作者突出表现金钱的实用性对农村价值导向的影响:有钱就是爷,就可以得到尊重,得到万众瞩目;而当没钱的时候,人们就会远离,也得不到尊重,从而批判了农村人缺乏道德感的实用信仰的消极影响。《你们的大哥》中的大哥虽然有恩于几个弟弟,但大哥的出狱对几个弟弟而言,既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职位升迁的问题,也不能化解邻里矛盾的问题,所以几个弟弟断然拒绝了去接回出狱的大哥。作者通过强烈的对比反映出狭义的实用信仰在民间往往带来道德沦丧和亲情淡漠。此外,《替姐姐告状》《农家饭》《乡村车祸》《侄儿请客》等多篇小说也对实用信仰在民间思想中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多方位的反思,进一步指出隐藏在农村道德滑坡、亲情疏远背后的民间思想正是农民的实用信仰:狭隘的实用信仰导致了农村价值体系的重利性、现实性,遮盖了道德和情感在人伦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对缺少道德感的实用信仰进行激烈的批判。
晓苏的多篇小说写到了孝道,并在《村里出了个打字员》《麦芽糖》中肯定了守孝道这一优良道德传统。但作者并没有在此止步,他对孝道进行了更深入的现代性反思: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尽孝道才是真正的尽孝?是不是所有的孝道都应该无条件地遵循?例如,在小说《金银花》《土妈的土黄瓜》《我们应该感谢谁》等小说中都塑造了对长辈尊重、守孝的儿孙形象,他们会在长辈过生日的时候回乡陪伴、会给予生活上经济的资助等,但作家却对他们形式上的守孝道持有更理性的认识:儿孙由于缺乏对长辈心理的关心,忽视长辈的心理需求,尤其忽略长辈被认可、被理解的渴望,因而造成了孝道表现的形式化问题。例如,《土妈的土黄瓜》中土妈为儿孙种的土黄瓜被儿孙抛弃的情节深深刺痛了年迈的土妈的内心,这种痛远不是过生日的时候儿孙回家看望能够消除的,这是对人自尊心的损伤、对老年人脆弱内心的巨大伤害。从更深层次看,晓苏对孝道的反思还在继续,例如《光棍村》《桃花桥》《皮影戏》等小说提出了某些孝道的合理性问题,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例如,《光棍村》中范虎对妻子刘文秀宠爱有加,他给老婆洗内裤被母亲发现后产生了矛盾,母亲坚决不准他给老婆洗内裤。范虎对母亲意见的遵循体现了他对孝道的坚守,但这却导致了他婚姻关系的破裂。《桃花桥》中本准备结婚的妹妹红袖因为母亲临终遗言——必须让哥哥结婚了才能结婚而不得不解除婚约,陪着光棍哥哥无法出嫁,因此兄妹俩都忍受着性压抑与性苦闷的煎熬。作家在此提出了孝道的合理性问题和该如何遵循孝道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孝道提倡对父母长辈的无条件尊重与服从,这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显现出需要修正和完善的地方。一味地、缺乏辩证思想地全盘接受孝道容易导致愚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戕害。晓苏提出的孝道继承的问题显然从更深的层面思考了民间传统思想的现代性问题。
在晓苏乡村小说中,有诸多民俗、风俗的叙述,它有时作为小说的题材任由作家驾驭,有时作为小说的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有时还作为小说创作的背景以供作家展示。例如,《你们的大哥》中的婚礼撒花生风俗、《人情账本》中过生日送人情风俗、《糖水》中拜年冲糖水风俗、《侄儿请客》中正月初一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的风俗、《坦白书》中没结婚的儿子是不能分家的风俗、《松油灯》中油菜坡村民隆重庆祝三十六岁生日的风俗、《村里哪口井最深》中投井要投仇人家的井的风俗等等。作家通过婚嫁、丧礼、请客、庆生等风俗的描写展示了油菜坡绚丽的风俗画卷。他在积极描绘风俗图景时,也对有些风俗的合理性进行了现代性反思。比较典型的如小说《娘家风俗》。小说叙述了油菜坡的风俗:女儿回到娘家是绝对不能和女婿同房的,否则就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我”和新婚妻子雨花回到她的娘家,按照当地风俗,就只能分房而睡。新婚夫妇无法排解这种煎熬,只好选择在外开旅馆,却又被邻居钱书借此诈取封口费。看似幽默的小说情节以荒谬的方式引起了读者对风俗的合理性问题产生思考:有些风俗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吸收风俗,而应该与时俱进地批判性地传承风俗,否则容易导致人性的压抑。
(二)建立以生命伦理至上的民间伦理体系
晓苏在传统的、合乎理性的民间伦理叙事之外,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入洞察,写出了强化生命伦理、弱化传统婚姻道德伦理、渲染自由奔放生活气息、超越传统伦理禁锢的活泼的民间伦理形态,甚至试图通过失范的伦理秩序表达对传统伦理的挑战与突破。他还以感性的笔触歌颂民间生命力的勃发和消解某些传统伦理的正当性,深入挖掘了深藏于民间的、反传统的民间伦理,体现了对传统民间伦理的超越性。
晓苏通过对特殊的底层群体——光棍儿和空窗女性的着力叙述表达了生命伦理至上的民间伦理。晓苏在多篇小说中写到光棍男青年或因为家庭经济的贫穷、或因为自身生理的缺陷、或因为适婚女性人口的迁出等社会因素造成无法正常结婚的窘状。《光棍村》中为了缓解压抑的性苦闷,范虎顾不上嫌弃怀孕在身的刘文秀,并且小心而窝囊地维持着脆弱的婚姻;《为光棍说话》中四十多岁还没碰过女人的杨喜只能悄悄爬树,偷看邻居邱巾洗澡以缓解性饥渴;《坦白书》《麦子黄了》和《人住牛栏》中因为身材、长相和智力等问题一直单身的刘贵、金盆和苕长期处于情感的空白和性欲的荒漠之中;各种因素影响了光棍正常性欲的释放,因而他们有的为了缓解性压抑不得不委曲求全、有的借偷窥以缓解身体的饥渴、有的通过出于本能的释放以宣泄压抑已久的性苦闷。同时,晓苏还把眼光聚焦于处于性压抑状态的农村女性身上,《误诊》《养驴的女人》中的白果和朱碧红因为丈夫的身体原因陷入了生理的空窗状态,《我们的隐私》《花被窝》《寡妇年》《劝姨妹复婚》《传染记》中的留守女性在打工大潮的影响下经历夫妻分离的煎熬和性的压抑,她们在生理欲望的指引下击碎现实世界中坚固的道德壁垒,绽放生命的绚丽花朵。“当这些生命的景象得到了公正的、富有同情心的书写,真实的个体就出现了:张扬文学叙事中的个体伦理,就是要让个体的生命发出声音,并被倾听;个体的痛苦得到尊重,并被抱慰。” 在晓苏的创作中,这种超越世俗道德判断的人性光辉折射出作者对生命的敬畏与对人性的歌唱。晓苏体察并同情生命的残缺,理解并宽容底层的性苦难,同时回避消费主义思潮下对欲望无节制的渲染,从生命的本能出发关照底层生命的坚韧,把生命的欲望置于伦理的中心,化繁为简地表达了生命至上的民间伦理。
婚姻伦理的失范、叔嫂关系的失范甚至兄妹伦理关系的失范都是晓苏乡土小说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花被窝》《坦白书》《我们的隐私》都写到了妻子出轨或者夫妻双双出轨。《嫂子改嫁》中嫂子跨越伦理与道德的边界,一直暗恋小叔子杨文;《嫂子调》里嫂子推倒了横在叔嫂之间的道德屏障,直接充当了小叔子的性启蒙者。《挽救豌豆》中弟媳豌豆对表哥杨聪充满了崇拜,甚至主动要求与表哥发生关系;《劝姨妹复婚》中胡雪与妹夫杨栓、“我”与姨妹杨栓分别点燃了身体的欲望;《人住牛栏》《松油灯》中弟弟和哥哥的光棍儿窘态让姐姐和妹妹怜惜而无奈,甚至发生了姐姐和弟弟、妹妹和哥哥的乱伦关系。晓苏有意回避用道德伦理的尺度去评价他们的过失及追究他们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是以非道德逻辑回应了民间底层对欲望的呼号、并表示了足够的宽容,在油菜坡的民间大地上尽情地张扬隐匿于人性最深处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其实,各种家庭伦理关系失范的根源是他们试图不断挣脱传统道德羁绊的自由精神。晓苏一方面基于对人性的尊重与宽容理解民间乱伦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对民间自在的生存逻辑和伦理法则保持认可与接纳。他“从民间的价值立场来说,就是理解、尊重、承认民间的完整、自足,并依据民间固有的价值原则去理解民间的生命与生活” 。晓苏自己也认为“民间文化的核心是自由,它游离于政治意志和精英意识之外,独享着自己的民间意趣,自主、自在,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法自然,尊人性”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作品通过生命伦理至上的民间伦理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三)对民间的现代性多元表现形态
晓苏在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着力表现乡村小说的民间性特点,同时,他也尝试以现代性书写方式反映乡村生活中的偶然性、荒谬性等。
晓苏在小说中写出乡村生活中的偶然性。《三座坟》中的李有福在一年内连续死了三个亲人:妈、儿子和老婆。媳妇偶然发泄对卧床母亲的不满导致了母亲的自杀,接连发生了儿子的自杀和媳妇的自杀。《击鼓传花》中的田福是个好人,本来和“我”能力相当,在县文化局招人时,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展示个人才能,但田福运气不好,没有机会展示才能,所以不得不留在了农村;当兵招兵时,因为体检前一天砍柴时眼睛被野蜂咬了,体检未通过,又不得不留在农村。《卖卤菜的李学乖》中喝醉酒的岁岁在李学乖的搀扶下回到理发店。刚上阁楼时,裤子垮了,露出了大腿和内裤,正巧,男朋友棒头这时回来看到了这一幕,这一偶然的事件引发了棒头与李学乖之间的矛盾与误会,导致了岁岁看清了两人的本质,并重新做出选择:去派出所汇报实情。最后李学乖免责,竟成为了岁岁的男友,还阴差阳错地结束了单身生活。晓苏通过写人生中的偶然性,写出了底层人命运的无常、脆弱与不可捉摸,也写出了底层生活中充满希望和阳光的一面。
晓苏在小说中也写出了乡村生活中的荒谬性。《侯已的汇款单》中在河南煤矿打工的侯已为了安全保险,就在打工地从邮局汇回老家、寄给自己的积蓄——500元。但他儿媳领走了汇款单,当他经历了种种方式借钱以疏通邮局关系取到钱时,除了还掉为取钱而找剃头铺老板、药店老板、杂货铺老板借的钱之外,还被儿媳索要了200多块钱,最后自己一分钱也不剩。侯已本来怕钱被偷才采用邮寄的方式寄钱回家,结果事实上钱仍然被“偷”了,自己仍然一无所获。《我们应该感谢谁》中住在城里的兄妹三人为了感谢帮助照顾父亲的乡亲,先后感谢了村长尤神、村民钱春早,最后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应该感谢的人,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不会说话的哑巴。《陪周立根寻妻》中周立根几经周转找到在矿上打工的妻子,通过温情的告白、亲情的倾诉试图劝回妻子,但在即将离开矿区的时候,妻子安小环还是下了车,因为她无法继续接受周立根家贫困而乏味的生活。《挽救豌豆》中本来以劝说者身份出现的表哥,不但没有成功劝说弟媳豌豆放弃进城务工的想法,相反,他的出现更激发了豌豆对城市和生命更强烈的欲望,加速了弟弟弟媳婚姻的瓦解。晓苏通过荒谬性书写底层的苦难,也窥视了苦难底层中人性的恶、放大了底层中人性的善。他通过小说提供给读者的预设结局与实际结局的强烈反差,增强荒谬感,写出了现实的残酷、人性的复杂。
晓苏还在小说中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乡村。《侄儿请客》中“我”回乡给大哥上坟,侄儿说第二天请我吃饭,我翘首期盼,但侄儿根本不记得跟“我”说过请客的事情。《住在坡上的表哥》中住在坡上的表哥精心准备招待从城里回来的表弟,但“我”只是图个方便,在坡下表弟家就吃饭了,完全忘记了表哥请“我”去吃饭的事情。《农家饭》中“我”为了帮助金嫂、银嫂和铜嫂,先后资助她们开农家乐饭店,但最后却没能在她们任何一家饭馆吃上一顿饭,并被她们用不同的方式下了逐客令。《村口哪口井最深》中陈仁打算投井,儿子陈义、支书尚元宝、包工头周大本这三个有负于他的人都担心陈仁会投向自家的井,但陈仁而是用石头栓在自己的脖子上投入了自家的井。《剪彩》中吴满升无奈之下偷了修理厂的车变卖换钱以资助村里修公路,当通车剪彩时,无所作为的县交通局领导刘亨作为嘉宾剪彩,而真正的英雄吴满升却因为想见到这一激动的场面而悄悄潜回村,并被公安抓走了。《桠杈打兔》中没有领到养老金的毛洞生本来苦闷,但因拿了养老金,喝酒驾摩托撞死的姜广财的命运又让毛洞生庆幸自己没有拿到钱,否则同行也会丧命。晓苏以诙谐的笔调叙述了乡村底层的复杂性:既写出了底层在贫富悬殊环境下内心的自卑与自尊心理,也深刻批判了深藏的农民的精神劣根性;写出底层既有超越苦难的大慈悲,又有追求名利的小心思。
晓苏的乡村小说是一个兼容民间性与现代性的复合体,一方面呈现了丰富而驳杂的民间世界;另一方面也吸引我们对乡村大地进行更深入的现代性思考。晓苏的乡村小说创作在丰富当代乡村小说叙事内容的同时,也进一步挖掘了这一题材表现的深度,带来了更多的叙事可能性。
[1] 贺绍俊.花被窝·序,花被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2] 贺宾.关注民间: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J].唐都学刊,2006,(1):40.
[3] 樊星.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2.
[4] 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218,238.
[5] 谢有顺.小说叙事的伦理问题[J].小说评论,2012,(5):29.
[6] 王光东.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4.
2095-4654(2017)06-0045-06
2017-08-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晓苏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研究”(16Y147);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鄂西北作家作品中的方言文化研究”(2015FYY003)
I207.42
A
余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