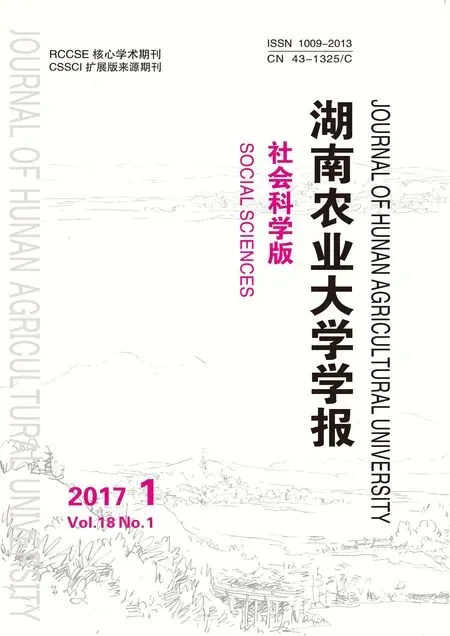村规民约的当代形态及其乡村治理功能
2017-02-24周铁涛
周铁涛
(1.益阳市委党校,湖南 益阳 413000;2. 益阳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村规民约的当代形态及其乡村治理功能
周铁涛1,2
(1.益阳市委党校,湖南 益阳 413000;2. 益阳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农村治理基本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政权直达基层,乡规民约被废弃。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体制下,传统村规民约得以复苏并呈现出两种形态,即部分村规民约被改造后虚化为一种形式化的文本,形同虚设;部分村规民约则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重获新生。在当下的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仍具有推进村民自治、整合农民利益、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等重要功能。对于被严重虚化的形式化的村规民约,应当坚持紧密结合村域实际、坚守国家法律“底线”的原则,使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村规民约;历史嬗变;当代形态;乡村治理;功能
一、问题的提出
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乡规民约是农村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最基本社会规范。现代村规民约则是沿袭传统规约,迎合农村市场化改革趋势,回应村民政治期待、利益获取和社会秩序维护等诉求,逐步发展完善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规则,是村民与集体之间的契约,是民间法,也是国家法律的地方化。作为一种契约式规范,由于村规民约源于乡土社会,更贴近群众生活实际,在讨论制定过程中又融入了协商民主理念,能获得村民普遍认可,能较大程度地通过村民的共信、共行得以实施,缓解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基层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冲突和矛盾,在基层法治化治理进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功能和价值。
既有的关于村规民约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从“法律多元”出发,将村规民约纳入民间法视野予以考察,探讨其与国家法的关系。在性质界定方面,梁治平认为,“村规民约既不是国家正式法律的对立物,也不是其简单的延伸”[1],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为规则,“不论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家的认可,它们都不是国家授权的产物”[2]。刘笃才认为,民间规约具有民间性、乡土性、自治性、成文性等特点,和国家法律、私人契约之间既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野,也从来不是分庭抗礼的关系[3]。在价值功能方面,苏力认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4]在与国家法的互动方面,田成有认为,村规民约的订立应该属于私法范畴,是集体成员的一种意思自治,只要村规民约不违反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冲突,法律就应当确认并保障这种约定[5]。吴冬梅认为,乡规民约的法治化功效在于其实施效率高于国家法律,能促进国家法律的实施,具有国家法律的补充作用;在法治化背景下,应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实现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6]。张明新认为,由国家政权机关自上而下引入的村民自治章程体现了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治理原则,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更加趋近[7]。
二是从“村庄治权”出发,将村规民约纳入基层治理规范范畴,探讨其对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的影响。张静认为乡规民约具有特定的治理原则及管辖范围,其体现的村庄治权与国家治权有联系又很不同;国家治权面临的困境,实质“在于两个性质上非常相似的管制规范竞争其各自的管辖地位和范围,力图加强或扩张自己治权的行动,一直没有寻得制度化的解决方法”[8]。张广修、张景峰的《村规民约论》则试图建立村规民约的基本理论框架与体系,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进程。谢晖认为,乡规民约是官方借民间力量管理乡民社会的方式,不得不随着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改变、削弱甚至隐退自身[9]。姜裕富认为,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传统的乡规民约也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村规民约的转型[10]。在个案研究方面,主要有徐晓光、吴大华、周相卿、李向玉等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和周世中等对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法的研究。
尽管不少研究者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对村规民约的性质界定、价值定位、现实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多是对村规民约的相对静态化的研究,对其在现代法治化背景下如何走出传统,融入现代治理,进行动态化的转型研究,则稍显薄弱。为此,笔者拟对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进行梳理以把握其发展大势,剖析其呈现出的当代形态,并阐述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功能。
二、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
中国的村规民约积淀了几千年,是“乡土性”抑或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传统,农村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因此,探讨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梳理“乡土社会”的各种规约、传统、习惯,有利于把握其发展趋势,有利于国家权力对村规民约的现实改造。
乡约是中国古代介于国法与家规之间的生活规则[12]。古代中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是乡里组织,有组织即有规则,最初的乡规民约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不成文的地方习俗。成文乡约的产生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1076年,即北宋神宗熙宁九年陕西蓝田吕氏兄弟创制的《吕氏乡约》。其对民众的约束以“入约”为前提,约规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带有明显的契约性和乡村自治性。由于乡约产生于乡土社会,通俗易懂,又伴随有族权的维护,其实施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明清时期,乡规民约受到统治阶层高度重视。明朝时,明成祖朱棣时期一度以国法的形式颁布乡规条例,赋予乡规民约以法律地位。在清代高度集权的政治背景下,乡约完全沦为国家控制农村基层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乡民自治内涵。吴理财的研究显示,“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务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13]表面上看,国家权力的终端是州县,事实上,农业社会时代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农村的统治,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没有农村社会源源不断地向上层社会输送资源,政权将失去立足之基。这一时期,地方官员对农村的控制一般是借助乡绅阶层实行间接控制,只有当农民起义或造反致使乡绅阶层无力控制局面时,国家权力才会强势介入。在长期的乡绅治理中,地主贵族们借助乡规民约使农村社会得以安定,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历史上的乡规民约表面上源于乡土,在实际制定过程中却并无底层农民的实质参与,都是在地方精英(地主士绅)的主持下,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维护封建宗法礼教的伦理纲常为目的所制定。尽管如此,乡规民约的内容仍然以淳朴民风、发展生产、维护治安、稳固秩序为主体,是古代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规范。
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乡规民约退出集权治理范畴,回归乡土自治本位,出现了短暂的复兴。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人们普遍认同的农村“破产”为基础,以知识界投身到救济农村的各种尝试为表征。尽管各种团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形式不同,但目的却完全一致。在江宁自治和镇平自治的尝试中,一个通过政府的力量推动乡村自治,一个通过发动农民群众推动乡村自治,都出现了乡规民约治理功能的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快速延伸至农村最基层,取代传统乡绅势力行使农村社会管理职能。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国家法律和政策直接传递到生产队,彻底打破了“皇权不下县”的惯例。在农村管理方面,人民公社对社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包揽一切、无所不能,乡规民约不再有存在的价值。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开展的“倒儒反孔”运动,更从思想和政治高度把村规民约视为反动、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产物[14]。这一阶段,传统的乡规民约基本被废弃。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广大农村建立乡(镇)人民政府,行政权退至乡镇,形成乡政村治格局,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对土地拥有了自主生产经营权,政府干预减少,村庄逐步脱离政府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进入村民自治阶段,甚至乡村治安的维护等公共服务也需要自身供给,为村规民约的再生和发展创造了契机。1979年,广西宜州合寨生产大队尚十分贫困,由于分田到户,国家的管制逐步放松,原有利益格局被打破,“政社合一”的管理被弱化,出现了无人管事的状况,农村社会秩序受到冲击,社会治安迅速恶化,偷盗成风,赌博成风。果地屯的三名老党员在聊及“村民耕牛经常被盗”的问题时,萌发了通过村庄内部力量管理治安的念头。经过充分酝酿,果地屯召集全屯160多户户主开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了村内治安的“带头人”。1980年1月20日,治安“带头人”主持召开全村村民会议,通过了村规民约,人人按手印以示共同遵守,果地村委会成为首个利用村规民约进行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村委会[15]。1998年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村规民约在农村治理中的合法地位。越来越多的村民自治组织通过恢复、制定或修改村规民约,推进农村治理。
从中国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来看,不管哪个时期,不管国家政权如何强盛,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总存在程度不同的分离,不得不借助来自宗族或士绅阶层的非官方势力维持乡村秩序。即使在军阀割据、外敌入侵的战乱时期,除了外部扶持的地方治理傀儡外,也还存在与之抗衡的民间势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秩序维护中,封闭的环境、落后的文化以及上层可能存在的愚民思想,使得村民无法更多地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代代相沿的习惯、乡俗或由基层精英主导制定的成文村规民约,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试图建立起直达农村最基层的管理体系,最终亦未能持续,基层社会仍需“自治”。笔者由此认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对农村基层社会而言,更多的是价值导向和底线守护,作为村域内部权威的载体,村规民约始终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只不过它可能会因国家治理理念的更新而不得不应时转型。
三、村规民约的当代形态
一直以来,村规民约都是在维护国家主流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既有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良好社会风俗的传承与弘扬,也有对森严等级的维护与对“违德”行为的惩处,呈现乡村自治的特征。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通过“送法下乡”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农村输送法律资源,农民对村规民约中一些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惩处,提出了种种质疑。尤其从进入后税费时代开始,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征地拆迁带来了村集体利益的剧增,原有的关于村民身份确认和集体利益分配的村规民约与在籍村民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以出嫁女参与集体利益分配的诉求表达为主要标志的对村规民约的责难不断见诸媒体。由此,国家开始关注村规民约中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当代村规民约开始逐渐转型,并呈现出以下两种典型形态。
(1)虚化为一种形式上的文本。一些村在村委会主持下,按照基层政府下发的“范本”,重新修订和颁布依法治村章程和相关规约,被誉为“最完备的村规民约”的村民自治章程,在村规民约的被动转型过程中虚化为一种形式上的文本。笔者走访调查发现,湖南某镇于2006年按照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印发的《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和市、县的要求进行了一场由基层政府主导的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集中清理、修订活动,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镇主要领导牵头,以民政所、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体快速完成了清理、修订工作。在这场清理“运动”中,村委会的工作完全按照镇政府规划的流程进行,《依法治村章程》或《村民自治章程》挂上了村公布栏。就内容而言,《村民自治章程》包括总则、村级组织、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公益事业、社会管理、附则七章,而《依法治村章程》则只将第二章改成了“组织形式”,其它六章完全相同。在基层政府看来,《章程》界定了村民自治的性质,确认了村民权利,规范了村民自治机构的设置、职能和村权运行规则,是村民自治中的“小宪法”。事实上,《章程》的内容全部来自于《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汇总和罗列,没有任何创新,更没有结合各村实际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详细规定。当各村的《章程》制定或修订完成后,包括村干部在内,几乎没有村民会关注其实施。这种内容虚化的《章程》,仅仅只是纯粹的形式化的文本,没有任何实效,成为了挂在墙上的摆设,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各级领导的检查和各部门的考核中能“有据可查”。
另外,基层政府对村规民约的清理,总在试图通过统一的格式化的版本废除原有规约中超越法律之上的惩罚性规则,但同时也弱化了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传统权威,使部分村规民约虚化为一种形式化的文本,从而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功能。某村1994年12月印发的“村规民约”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尽快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为目的,总共设置52条内容,其中有43条设定了5~200元不等的罚款,2条涉及收费(外籍人员来本村土葬的占地费和纠纷调解费),1条涉及对检举、揭发和见义勇为的奖励,涉及到了村民生活中大至计划生育、公益建设,小至锄挖田垄、开塘不关的方方面面事宜。后几经修订,目前该村的村规民约仅12条,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倡议性条文,已粘贴到各家各户的墙上。就实效而言,新的村规规约抹去了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性和传承性,弱化了村干部们的矛盾纠纷调处权威,演变为基层政府的“倡议书”。正因如此,村民对规约越来越生分,视若无物。而缺乏民众关注的村规民约,也就失去了原初的价值和功能,形同虚设。
(2)转化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尽管部分村规民约被虚化为一种形式化的文本,但也有一些村规民约逐渐转型为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既在宏观上契合了国家政策、法律,又在微观上保持了自身的乡土特色和自治特色。
村规民约一般是依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结合村域实际,就村级治理中的一些日常规则或重大问题而制定,是要求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越来越多的村规民约是在村级组织的主持下,由全体村民共同讨论制定,由全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从起草到修改的全过程都有村民代表的广泛参与,村民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因此,村规民约具有村民契约的性质。一些村打破了原来系统化的、百科全书式的村规民约框架,用多个涉及不同事项的村规民约来管理村内各种事务。比如湖南桃江县一些乡村为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就单独制定了农村清洁工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村规民约。益阳市赫山区沧水铺镇的香炉山村,为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净化社会风气,专门针对操办红白喜事中的攀比行为发起倡议,并形成相关村规民约。这些规约既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规定,也考虑到了村庄的实际,迎合了社会发展的新潮流,自然具有生命力。
还有一些村庄在政府主导的村规民约的清理中,将原有的惩罚性制裁作出了不违反“硬法”的变通。比如对不支持村内公益事业的村民,原来的惩处是罚款,现在变成了点名批评、有偿使用公共设施;有的村还规定严重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不得向政府申请低保、救助等。对于盗伐林木的,某村规民约原来规定除赔偿损失外,还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因行政处罚权属于公安或林业部门,现已修改为责令赔偿损失并按所盗林木数量的10倍栽种新苗。一些村甚至将原来村规民约中通过惩罚得以实施的事务转型为通过奖励来治理。比如通过评比活动表彰贤、孝,通过村委资助奖励升学等。
由于这些村规民约以乡情、村情、民情为基础,紧密联系当地实际情况,立足于解决村级治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制定的措施具体明确,通过详细条款精确而明了地告之村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因此容易被群众所接受,从而成为国家法律政策的地方化版本。作为这些乡村介乎国家法律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准法”,村规民约不再只是道德规范,不再只以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为目的,而是涉及到了包括社会公德建设、经济科学发展、地方秩序维护、集体利益分配等在内的诸多内容,将国家法律、政策在村域范围内具体化。
四、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功能及其完善
尽管随着城乡一体化,乡规民约的效用有所下降,但在很多偏远乡村,村规民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乡村治理功能。在这些村庄,村规民约以村民自我管理为基础,由村民相互协议而产生,是村民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有效地推进了村民自治。村规民约也不再只是简单地维护生产生活秩序,而是逐渐转化为农民与集体、他人之间利益调整的重要依据,对村民利益的整合功不可没。而且,村规民约并没有局限于只维护原来村内精英的治理权威,而是以民主、法治为基础,推动了文明乡风建设。
(1)推进村民自治。村规民约普遍基于大多数村民的同意而设立,因而对村民约束力比较大,并能通过村民的相互督促和自我管理保证其有效实施。村民自治章程作为“最完备的村规民约”,主要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制度层面就村民自治机构的设置、职能的确定以及村级公共权力运行规则等问题订出规约,而其他的专项性村规民约侧重于就村民自治范围内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护、村民行为的规范、具体事务的处理等作出约定和规范。作为村域内的自治性规范,村规民约发源于村内,作用于村民,体现了村民的共同意志,是村级民主治理的重要载体,是村民通过“契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自治准则,与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发展紧密相连,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治理改革的需要。在当代社会,村规民约与时俱进,纳入了国家法律、政策的诸多内容,逐步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接轨,将村域“个性”与国家“共性”、村民的个体诉求与村域整体发展利益融合在一起,对于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保障村民民主权力具有重要作用。
(2)整合农民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传统农村的封闭性被打破,人员流动性增强,农民不再只是简单地从事农业生产,其生活、工作的地域也不再局限于农村。尤其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的发展,传统农民职业从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变,农民群体逐步分化成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前的农村基本只有村组干部、手艺农民、耕种农民、农民商人和少数半农半工的智能型农民(如部分农村教师、医生、工人),现在的农村除了普通农业劳动者外,还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农村社会管理者、农村服务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智能型职业者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和机制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而村规民约正是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达成的共识,能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其整合农民利益诉求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村规民约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对整合机制需求的契约性规范[16]。村规民约相当于村域内部的“习惯法”,农村社会各群体据此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诉求。就民主程序而言,村规民约的制定就是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村社会各群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通过村规民约这一制度化的规定可以均衡各群体利益。另一方面,村规民约作为一种介乎国家法律和村民个体诉求之间的利益调整机制,融历史沿袭的乡土性与由外部植入的现代性为一体,不失为当代农村社会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与协调制度安排。当代形态的村规民约,形式上是民众契约,实则是国家法律的地方化,规约中的诸多内容大都是法律的细化,只有个别带有明显村域特色的内容才是原初意义上的村规民约。在实际操作中,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一般都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处理诸如承包地、自留山、宅基地、征地补偿等事务。当村民对村组的决定不服时,一般只能选择提起诉讼,也有的直接上访。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也基本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来进行,只有当村规民约与法律、政策相抵触或侵犯村民权利时,方依据法律维护村民权益,否则不会否决其效力。
(3)促进文明乡风建设。村规民约是国家法律、政策的有效延伸。从中国历史的视角审视,在传统乡土社会里,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后盾”的象征意义而存在的,或者说国家法律在传统农村基本上是疏离的,农民更多的是生活在自在秩序的民间法中,由民间法调控和解决一切[17]。在沿袭熟人伦理的农村社会,法律不可能触及农村生活的细枝末节,更不可能是“万能”的。作为维护底线伦理的法律很难解决道德层面的一些现实问题。在现有的农村政治资源环境下,政府权力也被限定在法律明确授权的范围内,对法律之外的违德行为无力调控。而村规民约结合村域实际将国家法律地方化,成为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能够依据国家法律政策的原则、精神或者基本伦理,就社会公德、家庭伦理、乡风民俗、邻里关系、农村秩序等作出规定,制定村庄道德规范,促进文明乡风建设,实现乡村治理的有序化。
作为介乎国家法律与乡风民俗之间的村内规范,村规民约既具有规范性的一面,也带有契约性的成分,依靠乡村公共权威得以实施,是协调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之间冲突的缓冲地带。在一些村庄,村规民约被虚化为一种形式化的文本,有的甚至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政策,限制了其乡村治理功能的发挥,笔者认为,应基于以下原则进行完善。
一是紧密结合村域实际。紧密结合村域实际是村规民约发展的生命力所在。村规民约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其乡土性,尽管适用范围相对狭小,由于其与地方风俗、农民习惯、传统规则紧密相连,群众认可度高,遵守的自觉性强,对基层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觑。在一些带有地方习俗的个案处理中,村规民约甚至有国家法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比如相邻关系的处理,尽管《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有相应规定,却言之不详,由于各地风俗习惯不同,相同的行为可能在不同地域对相邻方的影响截然相反,国家法不可能周延,这时村规民约的作用自然显现。村规民约紧密结合村域实际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简单地以地方化的方式将国家法律、党委政府决策进行细化,贯彻落实;二是对本村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处理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形成村规民约,共同遵守。一方面,村规民约应承担诠释国家法律、政策的作用,承担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用适合于当地普遍文化水平的语言文字告诉村民什么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不能为,倡导文明新风,可以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贬抑、惩处违法违德行为,规范村民行为。另一方面,村规民约是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要紧密结合村域实际,着力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对不具有普遍性,带有明显村域特色,国家法律政策尚未予以规范的领域,要通过村民协商,形成村规民约,实现有效治理。
二是坚守国家法律“底线”。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最大的差别是不具有普适性,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它往往只针对特定地域内的事务制定,由村域内的特定权力保障实施。表面上看,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施行与国法无关,事实并非如此,当村规民约的实施侵犯到宪法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时,农民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由此,可能出现国家权力对地方规则的裁决。因此,村规民约应自觉接受地方政府的指导与备案,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只有在合法的基础上,村规民约方可得到全面实施。
村规民约的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应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由村民会议制定和修改村规民约,制定和修改的主体是村民会议,而村民会议的召开本身又应该具有合法性,在参会人数上,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户代表参加,没有达到法定参加人数所召开的村民会议是不合法的,其表决通过的村规民约当然无效。二是村规民约内容的合法化。就国家治理层面而言,村规民约不应是“独立王国”内的“小宪法”,而应是国家法律的地方化。传统村规民约与纲常伦理密不可分,强化了特定身份背景下的服从意识,一味强调集体(乡村集体或家族集体)权威,处罚多于倡导。其所规定的惩处,就国家立法而言,是村民委员会超越职权对村民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不具有合法性,应该对其违法内容进行清理和删除。如出嫁女分红的问题,村委的决策可能依据了村规民约,也有可能在具体实施时还通过会议表决的方式获得了绝大多数村民的同意,整个过程中,出嫁女始终只是少数,既无力阻止村规民约通过,也无力通过自己的反对票否定会议决定。国家法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无论什么样的契约,即使村民签字同意,只要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有可能基于合法权利的保护而在司法裁决中被撤销或宣告无效。
村规民约在经历现代转型后,逐渐演变为衔接国家法律政策和乡土风俗民情的基层治理规范。农村居民囿于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获取途径的有限性,对法律、政策不太了解,而对通俗化、地方化了村规民约,因其结合了每个村不同的村情民意,也考虑到了当地习俗,由村民起草、讨论、表决,更贴近生活,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村规民约通过契约化的约束机制,把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相关内容乡土化、具体化,可以起到法律无法企及的作用,因而更具操作性。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地方治理功能,必将有利于缓解农村法治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缓和基层政府与农村居民的矛盾,推进乡村民主化、法治化治理。
[1]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C]//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5-488.
[2]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法律与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4.
[3] 刘笃才.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J].法学研究,2006(1):135-147.
[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0.
[5] 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0.
[6] 吴冬梅.乡规民约的合理性及其与国家法律的协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4-60.
[7] 张明新.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6(4):169-175.
[8] 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J].北大法律评论,1999(2):4-48.
[9] 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J].东岳论丛,2004(4):49-56.
[10] 姜裕富.村规民约的效力:道德压制,抑或法律威慑[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2-66.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6.
[12] 易舜.《吕氏乡约》: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01-18.
[13] 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1999(4):75-79.
[14] 王晓慧,翟印理.村规民约略论[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6(4):127-131.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宜州市合寨村[DB/OL].http://www.gxzf.gov. cn/zjgx/gxzz/lszz/201104/t20110422_315708.htm,2016. 02.03.
[16] 杨建华,赵佳维.村规民约:农村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J].宁夏社会科学,2005(5):63-66.
[17] 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5.
责任编辑:曾凡盛
Contemporary forms of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ir fun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ZHOU Tietao
(1.Yiya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Yiyang 413000, China; 2.Yiya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 Yiyang 413000, China)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originated in the rural society have always been a basic standard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a period of 1949—1978, state power was utilized directly to the grassroots and village regulations were abandoned. Under the system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renewed and present regulations appeared in two forms: parts of the regulations being virtualized into a superficial text and existing in the name only, the other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law and localized policy and regaining a new state. In the current rural governance, the village regul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tegrating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and promoting the civilized country custo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have the virtualized regulations play a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we should insist the principle of connecting it with the village actual situation and insisting the bottom line of national law.
village regulations; historic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forms; rural governance; function
C912.82
A
1009-2013(2017)01-0049-07
10.13331/j.cnki.jhau(ss).2017.01.008
2016-12-20
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4YBA382)
周铁涛(1976—),男,湖南益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法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