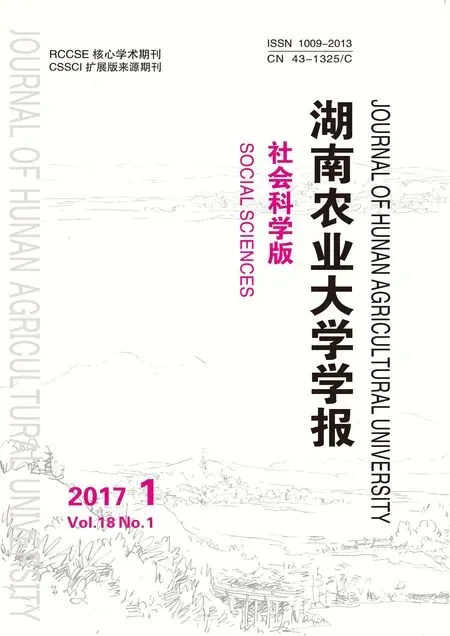产业扶贫项目主体行为及其运行机制的优化
——基于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的考察
2017-02-24黄文宇
黄文宇
(湖南省广播电视微波总站,湖南 长沙 410003)
产业扶贫项目主体行为及其运行机制的优化
——基于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的考察
黄文宇
(湖南省广播电视微波总站,湖南 长沙 410003)
基于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的考察表明:项目绩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偏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农户(贫困农户)等项目主体基于各自的动机与利益诉求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产业扶贫项目运行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缺乏约束;参与企业自身利益和社会责任难以兼顾;贫困农户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优化产业扶贫项目运行机制必须增强各参与主体的协调沟通,形成风险共担和利益分享机制;加强部门间合作和工作人员培训;进一步下放项目权利,增强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户的主体性。
产业扶贫项目;主体行为;运行机制
在中国现阶段贫困治理体系中, 项目的地位日益重要。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专项”、“项目”等方式对贫困地区进行扶持,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在一般语境下内涵丰富。本研究所说的“扶贫项目制”或 “扶贫项目”,是指在分税制的大背景下,在收入越来越集中的体制下,扶贫资金的分配采取“条线”体制单独运行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财政资金通过项目制的形式在行政科层体制外运作的机制[1]。
学界对扶贫项目制进行了大量研究。渠敬东等认为“项目制”包含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要素,“是一种能够促进体制顺畅运行的机制”。项目制的推行催生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双轨制”,在科层制内形成了条条权力的新输送路径,同时在科层制以外形成了有竞争性的市场路径[2]。折晓叶、陈婴婴通过对东部及中部较发达地区乡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并基于若干村庄项目的运作实践,对参与项目相关主体的行为选择和制度背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3]。周雪光等则分析了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据“国家视角”向基层输入项目的优缺点[4]。陈家建认为项目制在基层政府的实行重新构架了科层体系,政府内部动员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行政资源的配置也转变为以项目为核心[5]。初步文献梳理表明,学界基于产业化扶贫项目的主体行为分析还不多见,鉴此,笔者拟基于湖南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的考察,分析参与项目的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社等经济实体,以及农户等项目主体的行为特征,并针对各主体在产业化扶贫项目协同与合作中存在的若干核心问题提出有关机制的改进策略。
一、“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的实施
P县位于罗霄山脉北段,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新阶段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之一。该县辖24个乡镇778个村,总人口9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8万。2015年全县农村贫困人口17.1万人,贫困村542个。P县的茶叶产业近年来受到上级高度重视,先后被列为全国茶叶生产百强县、全国首批标准茶园创建示范县、湖南省十大良种茶基地大县、湖南省人民政府2013年新确定的全省33个茶叶优势区域县之一。因此,茶叶产业被P县列为六大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由县级领导负责对接乡镇,县高山茶产业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全县茶叶产业化基地建设的领导、规划和资金协调工作;实行县委书记、县长联络员制度,县直各单位按照分派的工作完成自身任务。为推动茶叶产业化基地建设进度,县委县政府在三大山区的七个重点乡镇召开了动员会,每周监督质量标准和工作进展,坚持一周一通报。在政策方面,为了加强农户对项目的预期,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建设P县茶叶良种繁育基地的意见》、《关于加快P县茶叶基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育苗品种、组织领导和补贴政策,大力推动项目的落实。2014、2015年在全县海拔800米以上的FB山区、FSS山区,以国、省定贫困村为中心,以现有高山林场和茶场为样板,向周边辐射,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扶持JSZ、BY、RD等3家企业和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海拔800米以上的19个贫困村新建约733公顷高山有机茶基地和3个高标准精细加工厂,规范3~5个初加工厂。项目建设初步惠及2 300多户,7 000多贫困农民。也许是项目实施没有很好地与村组织及其农户实际需求契合,农户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以致当地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户对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项目绩效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
二、项目有关主体的行为特征
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参与主体包括县、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大户”和“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农户,这些主体在项目的实施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行为特征。笔者现主要就参与P县“万亩有机茶园”的政府(县乡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企业(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社)、农户(担任村干部的农户、贫困农户)的动机和行为予以简要分析。
1.政府的行为特征
2013年国家开始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提出“要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促进各项扶贫资源的合理分配,做到扶贫到村到户,逐渐建立起一套扶贫工作长期稳定的制度,从而达成扶贫到村到户的总体目标。”①而由于贫困群体对风险的回避和政府产业扶贫项目的逐利性,贫困群体并不那么容易为项目“吸纳”和覆盖[6]。因此,要实现精准扶贫,切实提高扶贫的有效性,实现项目预期的“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目标”,动员贫困农民参与项目就成了这一产业扶贫项目工作的重点之一。作为这一产业扶贫项目的主要参与主体P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其参与“万亩有机茶园”扶贫项目的重要动机和使命就是既要激励有关企业、合作社参与其中,更要动员尽可能多的贫困农户尽量参与项目,并通过有机茶的生产脱贫。随着基层政府动员能力的减弱和农户(贫困农户)利益的分化,传统的政府动员手段越发难以发挥作用。于是,P县政府力图在做好整村推进产业项目的确定和农户补助标准后致力于项目的协调与服务工作,让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主体更好地发挥作用。
“由市场主体在扶贫中发挥龙头作用有很多好处。首先,市场主体掌握的消息多,来源广。像FSS镇XW农村合作社对YY市、省城的市场信息掌握得很准,能够灵活地调整策略。其次,他们收农户的茶叶一般都签订合同,有个保护价,保护农户的利益,降低了风险。还有就是技术上的帮助,包括优良的种子、茶苗,用什么化肥农药,种的技术和标准等等。”(20150810县扶贫办主任访谈)
“政府通过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动员村民搞有机茶,他(村民)还不高兴。觉得是给你政府或企业面子,帮你完成任务。我就这么点田土,不能种太多。还有村民会质疑:为什么要我种这么多?那个谁为什么种的比我少?为什么给某人扶持多而给我扶持少。由企业、农民合作社等给的政策补贴或扶持经费常引起干群矛盾或者群众之间的矛盾。”(20150810县扶贫办主任访谈)
对于参与项目的企业的在激励措施,主要是P县政府(扶贫办)实行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扶贫贴息贷款等扶持激励政策,对于带动农户脱贫效果好的市场主体还运用购买服务等手段进行支持和鼓励。
“企业和合作社是可以申请扶贫贴息贷款的。另外,有些涉及农户多、带动面广的还有别的扶持方式,比如给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作为奖励。像FSS镇XW茶叶合作社的基地没有一条直通的路,交通不便。政府就拨了4万元,加上他们自己出的4万元,路很快就修通了。去年政府还拿出80万元由XW茶叶合作社牵头对70家位于基地的贫困农户的危房进行了改造。”(20150810县扶贫办主任访谈)
因为市场主体很多,囿于资金的压力,P县政府不是“撒胡椒面”式地进行扶持,而是有针对性地扶持带动贫困农户多、实力相对强的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同时设置“门槛”排除一些动机不纯的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其中。
“FSS镇的合作社虽然有20多个,但实事求是地说有很多是为了套项目而不是搞产业。因为我县前两年的政策是成立专业合作社就有国家2万的直接扶持资金。有些就是想套这个钱成立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限的资金和项目给自己知根知底、带动农户多的企业比较有效。”(20150810FSS镇镇长访谈)
也许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意愿没有很好地与村组织及其农户实际需求相契合,农户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以致对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导致项目绩效不理想。
2.企业的行为特征
P县“万亩有机茶园”是典型的扶贫贴息贷款项目。这类项目是国家为支持贫困地区及其企业发展,并发挥企业在产业扶贫中的能动作用,促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贫困户增收的重要项目安排。P县 “万亩有机茶园” 项目的参与企业主要是若干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显然,项目健康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的积极参与和协同合作。
2008年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全面改革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项目贷款应由项目实施单位签订扶贫责任书。在“万亩有机茶园”项目实践中,参与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要获得扶贫贷款就必须与P县扶贫办签订“扶贫责任承诺书”。承诺书包括带动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数量、项目参与农户收入增加幅度、农资价格和收购保护价的承诺、给予农户一定的技术指导、兴办公益事业等一系列具体指标。凡参与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要享受税收、贷款方面的优惠、补贴等都要受到P县扶贫办制订的“项目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约束。原则上只有较好地履行了规定的扶贫责任的企业才能得到上述“利好”。
S茶叶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与P县政府有关部门就签订了扶贫责任承诺书,承诺帮扶2个村,带动1 200户农户,扶持520户贫困户生产有机茶,使参与项目贫困农户纯收入增长3 000元以上;对口帮助一定数量贫困户和贫困学生;安排10个以上贫困户的劳动力在企业就业,扶持1项公益事业。
S企业认真履行承诺,先后举办3期茶叶种植技术培训, 培训400多户茶农;建成高山有机茶园400公顷,其中标准化高山有机茶示范园1 00公顷;采用预先签约的方式,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保护价收购茶农的产品;吸纳本县贫困户劳动力40人在公司工作。在P县扶贫办核实履行了扶贫责任承诺后,S企业获得了年利率为8.358%的240万元贷款的利息补贴(7万元)。虽然扶贫贴息贷款项目对参与企业的激励有限,但如果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贫困治理就有机会获得多笔扶贫贴息贷款。这无疑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履行扶贫责任。
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资金相对充足、产品多元化,因而抵御市场及自然风险的能力比普通农户要强很多。农户尤其贫困农户和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地位不平等,市场风险常常被市场主体转给了农户。因此在产业扶贫项目中,政府一般要求企业在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中以市场保护价收购农户产品,从而承担了大部分的市场风险,使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
“我们茶叶合作社目前的发展势头还比较好,主要原因就是跟农户签订了保护性收购价格。农户的产品销售有了基本保障,种茶就没有太多顾忌了。农户今年种茶赚了钱,明年就会适当扩种,如果收入还可以就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甚至租了别人的田地来种茶。碰到市场行情差,我们也不得不收。比如有一年我们给XS村订的合同价是每公斤200元保底,超过200元就根据市场行情往上涨。XS村以前种茶不多,你不给出保护性收购价格,农民不愿意也不敢搞。结果那年包括运费、包装费在内,我们在XS村的收购业务就亏了不少。我们要把合作社做得长久就必须跟农民讲信用啊,亏了也没办法”。(P县FSS镇XW茶叶合作社法人代表H访谈)
企业和农民合作社承诺按照市场保护价收购农户尤其贫困户的茶叶,既体现了政府组织产业扶贫项目的初衷,即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和早日脱贫致富,同时也是维护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企业和非贫困农户利益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稳定并扩展当地有机茶生产,对企业和合作社等市场主体自身的长远发展有益。当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业还可以运用“训诫”、“惩罚”等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如XW茶叶合作社要求包括贫困农户在内的有机茶种植户遵循标准化的生产规范以保证产品的质量数量,如果不按照XW茶叶合作社的规定要求种植,他们就可以拒绝收购其茶叶。
3.农户的行为特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张庞大复杂的关系网,越是在基层社会,个人情感和关系在治理中的作用就越大。产业扶贫项目的有效实施需要农户的理解与配合,尤其离不开担任村委、村党支部委员的两委干部的骨干性农户,以及广大贫困农户的大力配合、支持。
在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实施中,许多担任村干部的农户承受政府下达的目标的压力,尽量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运用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和资源做好项目工作。如R村村主任带头卖掉耕牛,将自家的田土全部改种有机茶。在他的示范带动下,R村有机茶种植面积达到32公顷,占全村耕地面积的八成左右。又如B村村支书,为了推动选址在B村的“千亩有机茶基地”建设和本村农户积极种植有机茶,自掏腰包杀了两头猪,请村民来他家吃饭。乡村干部以此为契机宣讲“万亩有机茶园”产业化扶贫项目及其有关扶贫政策。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宴席宣传,再加上村干部带头领种,该村有关项目工作取得良好效果,B村千亩茶园基地建设顺利启动,九成以上农户种植了有机茶。
贫困农户对于政府主导的有机茶产业扶贫项目有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贫困农户对国家的扶贫政策非常欢迎,但另一方面,对通过发展有机茶产业脱贫致富没有信心,因而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在P县高山有机茶园项目实施中,虽然政府通过有关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免费或优惠提供苗木和肥料,但田地不多、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仍容易边缘化。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出发点是给贫困线下的群众提供生活保障,为了完成项目安排的各种任务,有的村干部便运用相关优惠政策和自己掌握的建议权,将有机茶种植和贫困农户享受“低保”待遇等关联起来。如H村,种有机茶的农户可以得到相应的种茶补贴(每公顷2.25万元),过去没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户在种茶后还可以优先获得“低保资格”。而原来享有“低保”的农户要是不开展有机茶种植,也就可能既享受不到相关的补贴资金,就连“低保”也有失去的风险。
“现在扶贫资金因为和上面给县里的其他资金打包使用,扶贫的功能体现得不太明显。家里条件好的农户得到这笔资金自己额外再投入点是可以搞好的。贫困户本来就基础差,县里给的这点钱很难对他们发展有机茶生产有大的帮助。结果往往是基础好的做成了,基础不行的不敢搞或者搞不下去。”(20150809县扶贫办主任访谈)
在与H村几家贫困农户的交流中,笔者明显感到他们对在当地发展有机茶来摆脱贫困的信心不足:
“我们村2004年按照县里的指示种早熟梨,大部分耕地农户都不种庄稼而是改栽了梨树苗,但是2006年早熟梨滞销,大部分家庭都亏了。后来因为镇里看到旁边乡镇的农户种植白术效益好,就要求改种白术。收成好的时候,一公顷耕地大概可以获得6万元收入。后来白术的市场价格下降,大家又赚不到钱,现在村里种白术的很少了。政府这些年都在想办法让我们脱贫致富,但一直没看到什么成效,所以也不敢再试了。”(20150811DP乡H村村民访谈)
可以看出,近年该村在政府推动下尝试发展过一些产业,但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周边靠农业脱贫致富的例子也少,所以农户对这种国家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充满疑虑也很正常。
“我也想利用政府的帮扶政策来脱贫致富,但你讲的通过发展有机茶生产脱贫不太靠谱,而且种茶太辛苦,我们没有精力也不敢搞。现在我爱人、儿子和媳妇都在外面打工,还是在外面挣钱比较靠得住些。”(20150811DP乡H村村民访谈)。
对种茶积极性不高的贫困农户只会在保证自己基本口粮的情况下才会种茶。在政府动员种茶而没有人手和时间的情况下农户的行为选择是不公开违反政府的政策,只进行一些开挖、栽种等工序敷衍了事,导致定植后成活率低。DP乡的12个村在新扩茶园土地中套种烟叶900亩,在不影响原有烤烟种植的情况下完成了县里的指标。
农户的这种行为特征是长期与强势政府博弈的理性选择。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农户面对政府只能使用弱者的“韧武器”——非对抗性抵制[7]。作为高山有机茶产业扶贫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民通过表面参与减少压力,避免显性冲突带来无法预期的风险,同时非对抗性抵制政府强加的任务[8]。贫困农户清楚农业产业的风险,出于追求风险最小化、利益稳定化的考虑,大多选择消极对待政府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规划和任务。
三、产业化扶贫项目运行机制的优化
产业扶贫项目主体基于利益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行为选择,从P县“万亩有机茶园”项目的实际运行结果来看,项目绩效与预期存在较大偏差,其根本原因在于项目运行机制仍存在缺陷,以致各主体的行为没有实现有效耦合。笔者认为项目运行机制存在缺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缺乏约束。为了实现贫困农户精准脱贫的总体目标,理想的产业扶贫项目运行机制应该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农户与政府形成平等的互动合作关系,各主体以项目为依托平等博弈,各自利益诉求在项目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等项目实施过程得到充分体现。通过对P县产业扶贫项目的调查来看,虽然多元主体参与相比以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扶贫运作模式有很大进步,但政府的全能主义倾向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巨大惯性仍然主导着当前的产业扶贫。地方政府作为核心主体的主导地位依旧十分稳固,在产业扶贫项目化运作中垄断了关键的扶贫资源分配权。参与农业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市场主体资金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对不足,只能在政府主导下被动参与,各主体互动博弈的情境很难实现。在政府居于产业项目扶贫核心地位的情况下,地方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产业规划普遍时间跨度较大,缺乏明确的阶段性要求和有约束力的时间表,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随意性较大。另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产业规划的重点在于项目的启动,项目落实之后的后续监管和可持续发展则往往遭到忽视。产业化扶贫项目对于地区贫困治理的实际效用主要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验收,缺乏目标人群的反馈和第三方的评测。
(2)企业自身利益和社会责任难以兼顾。使贫困农户脱贫致富是产业化扶贫项目实施的首要目标。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困农户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禀赋不足,在没有外界资源输入情况下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因此,作为产业化扶贫项目实施主体的企业就要在市场开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方面着力,让农户的有机茶生产更好地与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对接。然而这种理想的企业直接引领农户的模式在产业扶贫项目运作中还是较难实现。企业作为营利性的经济主体,企业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选择的首要出发点,其主要诉求是盈利而非扶贫,盈利和扶贫存在一定冲突。而实施产业扶贫项目的根本目标是使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因此,这一社会责任对于参与项目的企业而言,与其经济利益具有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从P县茶叶产业扶贫项目的个案可以看出,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往往出现两类矛盾。首先,企业的行为选择是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场,追逐利润加快发展的企业目标往往背离给贫困农户提供帮助服务的社会目标。企业更多地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无视农户的利益和诉求,很难使得农户满意。其次,企业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纽带,拥有市场、信息、资本等优势条件,这使其在这对合作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理论上的平等合作实际上蜕变成了不对称关系,产业扶贫项目“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中“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理想情境很难实现。市场波动、气候不利等不利情况发生时,合同违约率很高,“厂家压价”或相互违约的情况十分普遍。
(3)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在项目实施中仍缺乏足够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扶贫开发作为一项旨在使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的系统工程,他们的参与是这项惠民工程成功的关键。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一般来说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当前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农户还是被动参与到由当地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中。通过P县高山有机茶园项目的实施可以看出,贫困农户对于项目的参与度低,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农户尤其贫困农户长期处于贫困亚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教育程度较低,且与外界交流少,思想观念相对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浓厚,缺乏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有时甚至目光短浅,在生产经营中注重短期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基层政府、参与产业化扶贫项目的企业、农村合作社等没有尊重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认为大部分贫困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必要的素质和能力,以致当地政府、有关企业、合作社对于项目资源的分配、项目具体执行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决策过程中虽然有征求农户意见的程序,但贫困农户意见很难真正被采纳落实,从而降低了贫困农户的参与积极性。
产业扶贫项目化运作机制的完善直接影响贫困地区农户的利益和扶贫项目的功效。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化运作机制优化应重点增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的同时,重视目标对象群体的主体性。
第一,增强项目各主体的协调沟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的一种形式必须要符合市场规律,因此,龙头企业需要建立与产业扶贫对应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产业扶贫项目使目标人群脱贫增收的重点是项目的效益。连片种植、规模化种植的丰收只是供给侧的成功,只有产品适销对路农户才能真正从中受益。因此政府在进行产业规划时,首先必须考虑市场和销售。做好市场需求调研的同时要考虑自身的基础和现有资源,风险和前期投入相对小的项目比较适合贫困地区农户。基层政府对于农户与市场连接的帮助不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社等主体共担产业项目的市场风险。分散的贫困农户没有能力构建这样的产业扶贫风险防范机制,这就对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出了要求。因而扶贫办等部门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引导培育一批实力强、信用足的经济主体加入产业扶贫项目中。
第二,推进部门间的合作和工作人员培训。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项目仍然通过传统基层政府主导推进的[9]。部门协作的效率和基层人员的能力素质就越发显得重要。产业扶贫在国家战略中的愈发重要意味着参与的部门、单位数量的增加和相互之间合作的增多,现有各级政府的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级别和职能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要,一个专职协调各部门的专门机构的设立势在必行。这个机构旨在清晰定位各参与产业扶贫部门的职能,减少各部门单位之间的内耗和不作为。各市县、乡镇应该选拔和培训一批专业人员,提升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以应对基层扶贫工作事务繁杂、人手不足的问题。另外,通过完善目标责任机制、考核激励机制以及人员管理机制来加强组织领导,在制度上保障产业扶贫工作。
第三,进一步下放项目实施权利,增强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户的主体性。按照目前的管理程序,产业扶贫项目审批之后即要依据方案逐项落实。虽然在产业扶贫项目化运作中,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主要是指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就乡镇政府而言,其产业扶贫工作权限明显不够。乡镇政府和村干部虽然对当地真实状况掌握得更准,但是在推进项目落实和应对事先没有预计的问题时灵活调整方案的权限极为有限。部分项目原定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推进中问题不断,然而由于乡镇政府不具有即时解决甚至停止项目的权限,上级批复的程序冗长繁复,往往造成错失最好解决问题的时机以致项目不成功。适度下放权限使乡镇政府能够依据当地农户的真正需要和具体情况、项目实施中的突发状况即时修正,在确保项目经费高效利用的同时使项目应有的功效得以实现。给乡镇政府进一步下放权限本质上是为了促进农户对项目的参与,提升农户对项目的获得感,维持项目输入地社区的稳定。运作农村产业扶贫工程的成本压力消减了基层政府对这项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上级财政相应的工作经费匹配至关重要。上级给乡镇政府下放一部分财权事权后,项目运作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增强可以避免传统压力型体制的不足。乡镇政府和村干部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农民群体的具体要求对项目进行调整可以减少长官意志主导项目忽视当地社区发展和农户切实利益的现象,尤其是目前农村贫困治理中相当普遍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注释:
① 参阅国务院扶贫办:《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2014年。
[1] 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J].社会,2012(1):1-37.
[2]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113-130.
[3]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6-148.
[4] 周雪光.通往集体债务之路:政府组织、社会制度与乡村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J].公共行政评论,2012(1):46-77,180.
[5] 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13(2):64-79,205.
[6] 杨小柳,谭宗慧.良美村的蚕桑种养业:基于微观家庭生计的人类学分析[C]//陆德泉.反思参与式发展——发展人类学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 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J].社会学研究,2008(3):1-28.
[8] 张兆署.生存伦理还是生存理性?——对一个农民行为论题的实地检验[J].东南学术,2004(5):104-112.
[9] 马良灿.项目制背景下农村扶贫工作及其限度[J].社会科学战线,2013(4):211-217.
责任编辑:曾凡盛
Behavior of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alpine organic tea industrialization of P county, Hunan Province
HUANG Wenyu
(Hunan Radio and TV Microwave Station, Changsha 410003, China)
The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of alpine organic tea industrialization in P county demonstrates: the project performance is not so satisfying as expected;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ment and departments concerned, enterprises and farmer cooperatives, poor peasant households are diverse due to respective motives and interest claims; the major deficiency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s the lack of restrai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participating enterprise to take both self-interes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account; poor peasant households are in inferior position. To improv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the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a risk/benefit-sharing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departments should be enhanced; superior governments should decentralize and devolve power to township governments, farmer cooperatives and poor peasant household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subject behavior;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C912.82
A
1009-2013(2017)01-0056-06
10.13331/j.cnki.jhau(ss).2017.01.009
2016-12-28
黄文宇(1988—),男,湖南长沙人,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