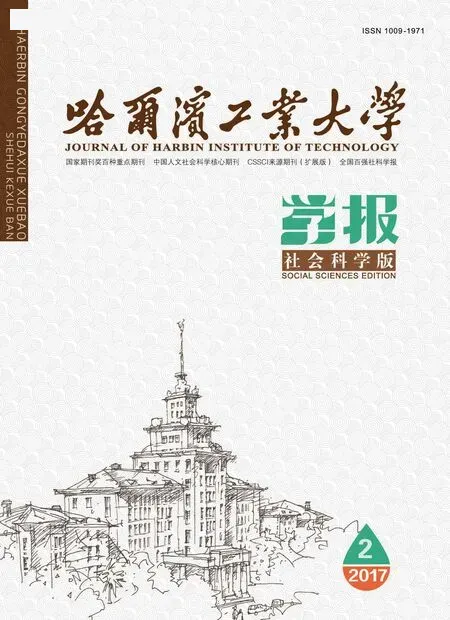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多元文化烙印
2017-02-24孙薇薇
孙薇薇
·文学与文化研究·
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多元文化烙印
孙薇薇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25)
加拿大文学根植于多元文化,并衍生出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女性意识。从殖民地时期受印第安多元文化影响而萌发,到加拿大联邦成立初期在女权主义滋养下的成长,再到建国百年时由少数群体文化和女权主义文化的双重教导下走向成熟,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深深打下了多元文化的烙印。然而,在多元文化进入发展瓶颈时,加拿大文学的女性意识完成了向生态女性主义的嬗变,在跨越自我的同时又为多元文化发展指引了道路,实现了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反哺”。随着少数族裔文化的崛起,少数族裔作家将用本民族文化对加拿大社会中女性的生活状态进行不同解读,未来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多元文化烙印也会更加绚丽多彩。
加拿大文学;女性意识;多元文化
从17世纪起,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人移居于此,不同文化在这片大地上碰撞、交融,逐渐从二元文化结构演绎成了加拿大特有的多元文化体系。而根植于多元文化沃土的加拿大文学之树,不仅茁壮成长,而且衍生出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加拿大文学女性意识。从殖民地时期受印第安婚姻文化影响而萌发,到加拿大建国百年时在少数族裔文化和女权主义文化的双重教导下步入成熟,不论思想内涵如何变迁,加拿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都深深打下了多元文化的烙印。
一、萌发:欧洲大陆文化与北美土著文化的“邂逅”
加拿大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时的加拿大只是法国的海外殖民省,耶稣会教士每年给法国教会的报告及军队官员的一些游记已经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但女性文学还无从谈起。到18世纪中期,加拿大文学仍然以见闻和游记为主,但这片土地上英国、法国以及土著文化之间的碰撞,为加拿大营造出了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文化氛围,也为文学家的创作积累了知识和素材。
1769年,弗朗西斯·布鲁克夫人以当时魁北克地区英国驻军的生活为背景所写的《艾米丽·蒙塔古小传》,是加拿大乃至北美洲的第一部小说。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艾米丽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了不喜欢的克莱顿,但最后在好友阿拉贝拉的影响下,最终解除原婚约,与心仪的里夫斯上校结婚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虽是艾米丽,阿拉贝拉却更像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她热情开朗,聪明活泼,有敏锐的观察力,羡慕印第安妻子可以不受丈夫干扰、无拘无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68。在女权意识没有那么鲜明的18世纪,小说里强调女性爱情与婚姻自由的女性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与布鲁克夫人受到加拿大印第安土著迥异于欧洲大陆的婚姻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布鲁克夫人也因此成为了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启蒙者。殖民地时期,欧洲大陆传统文化与加拿大土著文化的一次浪漫“邂逅”,便孕育出了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萌芽。
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加拿大还属于英法二元文化社会,欧洲大陆传统文和宗教文化对其影响依旧深刻,男权主义还是其文化核心。布鲁克夫人的“灵光乍现”,也仅停留在了“嫁个好男人”的女儿心思里。即使这种“小富即安”的女性意识,在加拿大文学中也似乎只是波光一闪。在布鲁克夫人之后,加拿大也曾出现过茱莉亚·哈特、伊莉莎·库辛、罗萨娜·乐普罗温等女性作家,可她们的文学作品要么是传奇故事,要么流于说教,明显受到了男权主义和宗教文化的影响[2]。在殖民地时期,加拿大文学女性意识中的文化烙印依然带有浓重的男权主义文化色彩。
二、成长:二元文化结构中女权主义文化带来的“叛逆”
19世纪末,拿加大这个新生的二元文化国家受席卷欧美以平权为主要目标的“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加拿大女性对其在社会中被压迫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加拿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也在女权主义的滋养下再次焕发出生机。如果说殖民地时期加拿大文学中才刚萌发的女性意识主要是唤起社会对女性境遇的关注和同情,那么联邦成立初期的加拿大文学表现出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强独立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女权主义文化给加拿大二元文化系统带来的“青春期叛逆”。
1904年,加拿大小镇文学的开创者——萨拉·邓肯,出版她这一生最著名的小说《帝制支持者》。这不是一部以女性意识为主题的小说,不过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作者透过姐姐艾德维拉表达出了对妇女独立、平等自由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关心,这是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另一种觉醒[3]58。在《帝制支持者》出版四年后,“20世纪初最受关注的加拿大明星作家”露西·蒙哥马利出版了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故事用动人的情节描述了女主角安妮·雪莉是如何以积极乐观追寻希望的生活态度获得了家人和社会的认可[4]。作者在安妮身上映射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女性意识也不再拘泥于爱情故事,而是安妮用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与殖民地时期加拿大文学中“只为爱情顾”的女性意识相比,安妮这种不拘泥于爱情,追求在家庭和社会中体现人生价值的女性主义思想,微妙却具有革命意义,意味着加拿大文学的女性意识进入了成长期。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作为英联邦成员,约有大量适龄男性踏上了欧洲战场,加拿大女性适时添补了劳动力空缺。由此,加拿大女性社会地位获得提高,社会责任感也越来越强,加拿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描写愈加深刻。辛克莱·罗斯的《至于我和我家》、玛莎·奥斯腾索的《野鹅》,女主角在家庭中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对男权主义社会的格局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反抗意识[1]138。
随着新移民数量增加,加拿大女性文学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女性意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东欧移民女诗人多萝西·利夫赛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在二战前后创作了大量以政治为主题的诗歌;英裔女性移民作家艾琳·贝尔德的都市小说,更加关注城市中底层人民的疾苦,尖锐地反映了社会问题,政治气氛强烈;冰岛移民女作家萨尔富森的长篇小说《勇敢的心》以冰岛移民经历为背景,刻画了一位务实求真、勇于奉献、有理想、有追求的加拿大女性代表,而小说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写,反映了加拿大人民祈盼和平和愿意为和平牺牲的精神[3]117。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多元文化的烙印也在这时变得多彩了起来。
尽管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文学作品,加拿大女性意识都在迅速成长,但二元文化下的加拿大仍然是一个男权为主的社会,仍然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仍然顽固地把女性的社会角色固化在家庭里,这种“叛逆”并不为整个社会所接受。这点在战后加拿大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的1951年的戏剧《在我心灵深处》可见一斑,作品选取特雷尔夫人、苏珊娜·穆迪和弗朗西斯·斯图亚特这三位加拿大历史上才华横溢的女性为主要人物,她们都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理想和丈夫来到了加拿大拓荒,而魔鬼却煽动她们去追寻自己的理想[5]。这部带有宗教色彩的剧作中,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女性追求人生理想的行为则是受到了邪恶魔鬼的蛊惑,女权主义文化依旧受到了男权主义和宗教文化的排斥。
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又是不可阻挡的,埃塞尔·威尔逊194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天真的旅行者》。女主人公托帕斯天真淳朴,按自己的意愿快乐生活,不去承担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在旅行中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从侧面表现出二战后家庭已经不再是加拿大女性生活的中心。1954年,埃塞尔·威尔逊又出版了小说《沼泽天使》,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姬的在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之中,不断探索和反思,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6]。1959年,希拉·沃森创作的“加拿大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双钩》出版,小说通过引借《圣经》、希腊神话和印第安神话等多种文化元素,以詹姆斯逃离家乡,又回归故土的过程,对加拿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人的命运并非注定不变的,人的爱心与觉悟必能引导人前进[7]222。《沼泽天使》中经历了家庭种种不幸的玛姬的自我反思,以及《双钩》中作者通过詹姆斯对社会的反思都标志着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成熟:多元文化体系下的“反思”
二战后,加拿大非西欧裔移民比例大幅增加,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也同时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族裔认同”行动的传入加拿大,少数群体(原住民民族、亚裔、非洲裔和东欧裔)渴望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渴望获得社会话语权,渴望打破二元社会结构。1971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了《双语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长期在二元文化夹缝中挣扎的少数族裔文化获得了生机,加拿大开始进入强调个性、独立和平等的多元文化发展时期。与此同时,追求性别差异性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思潮”再次在欧美兴起。在少数群体文化和女权主义文化的双重教导下,加拿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已经不像“青春期”时单一强调“叛逆”和“反抗”,而是如一个成年人一样,开始对女性在社会中生存的意义和女性如何实现人生价值进行“反思”。
1964年,加拿大“小说三大家”之一玛格丽特·劳伦斯和她的马纳瓦卡系列小说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在十年的时间里,劳伦斯创作了《石头天使》(1964)、《上帝的玩笑》(1966)、《住在火里的人》(1970)、《关在屋里的鸟》(1970)和《占卜者》(1974)共五部马纳瓦卡小说。在五部小说中,主人公从欧洲移民变换成了原住民梅蒂斯人,再到欧洲移民和梅蒂斯人的双线交错;故事背景从马纳瓦卡小镇延伸到了温哥华,又在繁华都市和小镇间穿插跳跃。马纳瓦卡系列小说的演绎正好印证了加拿大从二元文化向英语文化、法语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化多元共生过渡的发展轨迹。在这多元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中,苏格兰后裔《石头天使》夏甲在临终前爱心觉醒,完成了自我认识;小镇女教师蕾切尔因为《上帝的玩笑》而母性复苏,检讨人生,获取了新生的力量,开始学习适合的生存方式;《住在火里的人》斯泰茜在大都市温哥华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在彷徨、孤独和恐惧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心灵归于平静,直面人生和现实;小镇少女瓦妮莎观察到,在社会的屋里,女性好似《关在屋里的鸟》,要摆脱现状只有努力奋斗,如果放弃挣扎,只能如《潜鸟》梅蒂斯人皮格特一样,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最终消亡;女作家莫拉格在回忆与梅蒂斯男友朱尔斯的往事的过程中,感悟人生,成为了一个用写作探索人生意义的《占卜者》[8]。在劳伦斯的小说中,女性意识已经不仅仅是反抗男权意识的压迫,而是打破传统观念、家庭、社会和环境给女性的种种束缚,反思自身性格给女性带来的困惑与烦恼,并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是在精神独立和自由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妥协和回归。在劳伦斯的笔下,加拿大文学的女性意识真正意义地成熟了起来,多元文化的烙印也更加明显。因此,马纳瓦卡系列小说也奠定了劳伦斯近二十年的加拿大文坛领袖地位。
在这一时期,蜚声世界的“当代女契诃夫”加拿大小说家艾莉丝·门罗出版了《快乐精灵之舞》(1968),已至暮年的马萨丽丝毕生致力于少儿音乐教育,在面对学生及其家长前讽后赞时宠辱不惊、心地空明,表现出的“弱者不弱”的可贵精神已经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意识。而在姊妹小说集《姑娘们和女人们的生活》(1971)和《你以为你是谁?》(1978)中,女主人公都意识到了男女的差异性,也认识到了女性在社会上生存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但作品并没有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社会,而是直面存在于新女性自身的问题,思考人生的实质,表达出仅有事业成功而没有家庭幸福的女性也是“强者不强”的失意者[9]。在“强弱”转换之间,女性只有能掌握自身命运,人生才有积极意义。加拿大文学的女性意识也因为门罗愈发的成熟和丰满,散发着无尽魅力。
不仅是女性作家,加拿大男性作家也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开始关注女性问题。1970年,加拿大剧作家乔治·里加在代表作《丽塔·乔的狂喜》中讲述了丽塔·乔从一个天真善良的印第安少女沦落为一名妓女的过程。在剧中表现出的丽塔·乔土著人身份受到的歧视,政府部门对其遭遇的漠不关心,以及丽塔·乔的无辜和无助,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整个社会,认为社会应认真反思丽塔·乔的不幸[7]366。剧作在描写少数族裔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之外,也关注到了加拿大女性在社会中困境。这说明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加拿大,男权社会已经不再是主流,加拿大女性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萌发于殖民地时期的女性意识,在经过二元文化结构时的“叛逆期”后,终于在加拿大建国百年的时候走向成熟,并获得了的全面认可,而与生俱来的多元文化烙印,也成为了她身上最宝贵和不可或缺的装饰。
四、超越:生态女性主义的“反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日趋成熟。1988年,加拿大通过《多元文化法》,进一步阐明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和实施方法。加拿大的执政者希望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加拿大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事非所愿,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发展陷入了“与之前双语制度的矛盾”“各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缺失”“少数群体的政治民主无法保证”和“种族歧视”等种种困境。但加拿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并未因此停止前进,而是在吸收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的基因后,为自己打开了向更高层次进化的通道。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为“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主宰之间有着重要联系”。生态女性主义者批判“逻恪斯中心主义”思想,认为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理论,导致自然和女性都处于弱势地位,受到人类和男性的剥削。1985年,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小说《使女的故事》。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的女儿,阿特伍德对女性问题、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把女性与自然联系了起来。在《使女的故事》中,由男性组成的决策层肆意破坏自然环境,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形象地描绘了女性和自然都遭受到了男权中心主义思想的迫害,它们同处于相似的从属、被动、受害地位。小说揭示出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人类之间隐秘的压迫、统治与支配关系,揭示了女性与自然同时受到男性迫害或破坏,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统治同人类对自然的践踏、蹂躏对应起来[10]。从解构主义视角分析,很多早期加拿大女性文学中都可以看到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子,直到《使女的故事》才是加拿大作家第一次有意识地应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的创作。小说同时对两性和谐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进行探讨,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在《使女的故事》之后,阿特伍德又陆续出版了《猫眼》(1989)、《强盗新娘》(1993)、《盲刺客》(2000年)、《羚羊与秧鸡》(2003)、《好骨头》(2010)等长篇小说。这些小说表达出了作者对自然环境遭到人类破坏后的强烈危机意识,以及对女性被男权主义压迫的深深关注。阿特伍德也因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写作技巧成为玛格丽特·劳伦斯之后,新一代的“加拿大文学女皇”。
如果说阿特伍德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表达出女性遭受男权主义戕害与自然环境遭到人类破坏之间的关联,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莉丝·门罗则用其“看似平淡,实则老辣”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对加拿大文学中的女性生态主义给予了另一种诠释。以门罗200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逃离》为例,卡拉、朱丽叶、格蕾斯等小镇女性处在逃离家庭、逃离两性、逃离自我的渴望中,却最终都无奈地放弃。从表面看,作者似乎是在通过她们的悲惨命运控诉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迫害。而作者则用小说中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暗示读者,社会好像一个生态圈,生活在这个圈中的无论男性女性其价值并没有差别[11]。社会对不同性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期待。温顺的女性并不必须是弱者,强壮的男性也不理所应当站在统治地位,正所谓“弱者不弱,强者不强”。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按照准则行事,无论哪方想打破这个生态平衡,最终都将走向灭亡。门罗用她深刻犀利的眼光、朴素细腻的文字,借由一个个平凡但颇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为读者展现了男女之间难以解释的生态关系,表达了一种两性平等、和谐共存的生态女性主义理想。
门罗的这种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仅让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对自己的社会价值有了新认知,而且对加拿大其他少数群体也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在施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加拿大,每一个维度的文化互相对抗又互相依存,它们共同组成了加拿大社会的多元文化生态圈。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过渡强调文化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必将导致各个社会群体走向了封闭,排斥外来文化,最终使多元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只有用生态主义的思想,打破文化间的壁垒,努力构建能包容所有文化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圈,才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说从17世纪起,加拿大文学的女性意识一直是在多元文化的滋养下萌发、成长并成熟起来的,那么到20世纪末期,进入生态女性主义层次的加拿大文学女性意识不仅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而且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发展指引了新的出路,形成了对多元文化的“反哺”。
结语:少数族裔引领的未来
完成了生态主义嬗变之后,加拿大文学女性意识似乎已经进入了圆满状态,但与生俱来的多元文化烙印赋予了它无尽的可能。在二元文化结构时期,少数族裔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即使偶有“发声”也仅停留在对本民族人民生活艰辛的描写和被剥削迫害的控诉中,女性意识根本无从谈起。直到加拿大进入了多元文化时期,少数族裔尤其是华裔的女性作家开始崛起。1990年,华裔女性作家李群英出版了长篇小说《残月楼》,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处于文化边缘的华裔女性在加拿大的生活状态。在李群英之后,在20多年的发展中,又先后涌现出了如张翎、李彦、陈和等一批成就斐然的华裔女性作家,给加拿大女性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12]。与英法裔女性作家不同,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会用本民族文化对社会中女性加拿大社会的生存状态进行不同解读,而且其作品中具备对少数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双重关注的传统。虽然,目前加拿大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中还没有出现阿特伍德或门罗那样的旗帜,但乘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春风,一个由少数族裔引领的加拿大女性文学也许就在不远的未来,而加拿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多元文化烙印也将因此而愈发绚烂多彩。
[1]傅俊.加拿大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赵慧珍.19世纪加拿大英语妇女文学及其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133-138.
[3]郭继德.加拿大文学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陈秀君.《绿山墙的安妮》生存主题的女性主义解读[D].宁波: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35.
[5]郭继德.当代加拿大文学的一位缔造者——罗伯逊·戴维斯[J].当代外国文学,2003,(2):91-95.
[6]耿力平.从《沼泽天使》看女性的自然属性[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3):55-58.
[7]逢珍.加拿大英语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8]郑莉.文学与历史的互动[J].安徽文学,2009,(10):224-225.
[9]书玉.艾丽丝·门罗:短篇中的人生[J].书城,2013,(12):100-108.
[10]张冬梅,傅俊.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8,(5):145-152.
[11]邓远亮.追寻女性的精神“桃源”——评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J].中国教育学刊,2014,(5):113-114.
[12]赵慧珍.论加拿大的移民女作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4):87-92.
On the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SUN Wei⁃wei
(School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Canadian literature is rooted in its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feminist culture full of regional features gradually formed.It germinated under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dia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Then,the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literature developed at the nourishment of feminism move⁃men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onfederation.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eminine culture,this kind of conscious⁃ness ushered in its maturation stage.And the multi-cultural identity in Canadian literatu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asy to recognize.However,when the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came across its bottleneck,its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went through its ecofeminism transmutation in which self-transcending and literary guiding came into being.That is what we called regurgitation-feeding in literature.Finally,it's a predication that the ethnic writers are bound to analyze the female life for the rising of its ethnic culture in the future.Therefore,the multi-cultural identity will be more diverse in Canadian literature.
canadian literature;feminist consciousness;multi-culture
I106.4
:A
:1009-1971(2017)02-0088-05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6-12-10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加拿大现实主义区域小说研究”(1254126)
孙薇薇(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从事加拿大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