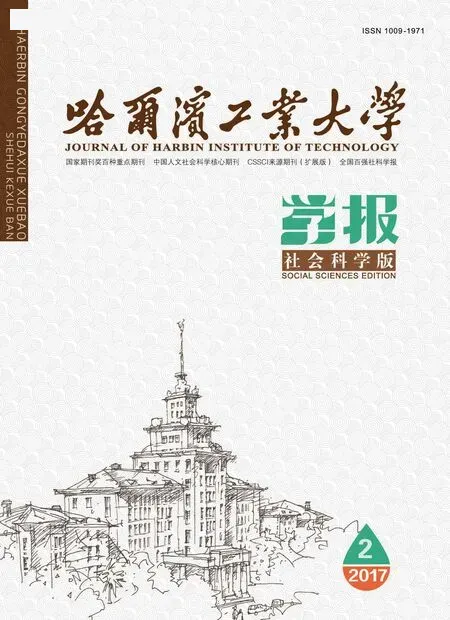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自治困境与优化路径
——来自上海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
2017-02-24曹锦清
马 立,曹锦清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自治困境与优化路径
——来自上海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
马 立1,2,曹锦清1
(1.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237;2.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上海200233)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要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和自治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社会组织还面临着资金来源不稳定、经营性项目不规范、运作过程不独立等困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一方面,政府要改变传统的“分类控制”思路,转为通过政策、资金“嵌入引导”的方式,扩大社会组织的自治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要从对政府的“绝对依赖”转向“最小化依赖”,不断提高自身的自治能力。这种双向的改变有可能推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从“依附式合作”转向“协商式合作”,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自治;政社合作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1]。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对于国家治理方式的更新、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文化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和水平,急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找到活力与秩序之间的最佳平衡点,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前和未来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2]。如何打破社会组织发展的桎梏,有效释放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已成为一个急需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字之差体现了治国理念的重要变化,要实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建设目标,就必须从以往单一的政府权力主体,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力体系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协商共治的横向权力网络。社会组织既能够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有效达到特定目标、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化的共同活动群体。它是在法律规定或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相对于政党、政府、市场组织等传统组织形态,以社会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具有民间性、公益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类型多种多样,涵盖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他们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有创意的项目吸引了公众的热情参与,有的社会组织已经开始参与环保、教育、扶贫、志愿服务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还有一些社会组织由专业人士发起和运作。比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就是由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发起和运作的。这个社会组织在公益领域全方位引入商业化管理模式,倡导“非牺牲”的公益精神,不仅具备较高的透明度(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慈善基金榜”榜首,被誉为“中国最透明的基金会”)和较强的筹资能力,而且具备较强的公信力和较高的运作效率,以推动贫困地区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梦想课程”已覆盖230万左右的学生,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就是要彰显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社会力量和公益的积极性,构筑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作用、形成合力的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对于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
(一)协调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和矛盾的凸显期,各个阶层的利益都面临着分化、重组与分配,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如果长期积累,不能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有效释放,就容易引发社会冲突。
首先,社会组织是连结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和纽带。公众多元化、多层次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及时地向上传递,影响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比如:上海杨浦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一家法律类社会组织——“天一市民诉求调解中心”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创立了“政府——社会组织——信访人”的三元矛盾化解机制,通过“律师尽职调查、拟定化解方案、进行内部审核、组织外部论证、报请领导审批、化解方案落地”等六个环节,使杨浦区的信访矛盾量一落千丈。“天一市民诉求调解中心”作为社会组织,具备独立、中立的第三方身份,更加容易被有利益诉求的公众所接受,也便于政府与公众更好地沟通。这个组织以专业化的技术和社会化的运作参与协调利益矛盾,与政府合作实现了矛盾解决主体的多元化。同时,这个组织还尝试配合政府信访部门建立“公众诉求信息管理平台”,在化解矛盾的范围和深度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更加有助于政府及时准确地把握公众诉求,科学决策。
其次,“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连结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不仅能够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作用,将基层社会组织的呼声、诉求与政府发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有效对接,而且能够协调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有序竞争。“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经市政府授权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市级联合性社会组织。①《北京市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08年9月,这是“枢纽型”社会组织首次面世于官方文件。比如:上海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就是一个“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个组织通过“1+5+X”的架构(即1个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5个基层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若干个某领域社会组织联合会,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宽至“1+14+X”),跨越了社团、社会服务机构(即“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界限,有效整合了各类社会组织的资源,为政社合作、社社合作搭建了平台,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指导、引领、管理、服务、协调的重要作用。
(二)扩大公民参与,推动社会自治
公民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治理如果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那就不是真正的“治理”。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自下而上,由公民自主发起、自愿成立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公民通过加入社会组织或者参加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参与社会治理。久而久之,公民就会养成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自治习惯,社会的自我运转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从知识可视化和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辩证关系中可以发现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与知识可视化的结合新视角,二者的辩证关系启示人们应该把知识可视化作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告诉人们具有网络媒介素养的受众能够对知识进行更好的可视化表征,因此,必须探讨知识可视化与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融合的策略(图3)。
上海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三村原是一个拆迁户居民区,具有房屋出租多、垃圾多、困难人群多、两劳人员多、癌症家庭多、居民利益诉求多等特点,社会治理的难度很大,街道、居委会力不从心。2012年,梅陇三村居委会培育出社会组织“绿主妇环境保护指导中心”(简称“绿主妇”),抓住“绿色低碳环保”这一广受居民欢迎的主题,聚焦“垃圾减量”这一和居民关系密切的关键利益点,不断设计创新各种契合居民追求、贴近居民需求、吸引居民眼球的项目以及激发居民参与热情的激励机制。比如: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并定期统一回收,发放垃圾分类回收积分卡,居民凭积分可以换取环保工艺品或日用品等;鼓励居民捐赠废旧毛衣,组织“爱心编结社”的退休阿姨对毛衣拆洗、消毒、重新编织并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倡导居民充分利用自家阳台开发“一平米菜园”,利用墙壁开辟“墙上微绿地”,种植豆芽等绿色蔬菜,并教授居民将厨余垃圾发酵制成绿色蔬菜的肥料的做法。这些项目不仅吸引了居民,而且还吸引了北京万通基金会、北京地球村等十多家公益组织,他们与“绿主妇”合作,带来了资金、技术、设备、专家等,帮助“绿主妇”成长壮大。“绿主妇”这一社会组织有效弥补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功能缺位,在动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提高居民自治能力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三)承接公共服务,推进职能转变
基于无限扩张的政府职能会导致政府管理效力的衰减以及社会自我管理功能的萎缩等问题的共识,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型”、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成为可能,“小政府、大社会”成为努力的目标。现代治理理论强调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以及各类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把作为社会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推到了前台。一方面,社会组织要不断发展壮大,为更好地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政府在转变职能时不能有截留利益的思想,即对自己有利的职能就以社会组织没有能力承接为由而不交给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变须与对社会组织的“赋权”同时进行。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面对社区结构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基层政府感到原有的以街居体系为基本依托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系已不适应多样化、个性化的群众需求。于是,街道一方面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街道辖区内建成了上海市第一个“公益社会组织示范基地”——“浦东公益示范基地”,即浦东公益服务园、浦东基金会服务园、塘桥社区公益服务园和浦东公益街,这“三园一街”集中了几十家社会组织,包括了基金资助、研究培训、法律支持、一线服务、监督评估等各种社会组织类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组织生态链,号称“公益硅谷”;另一方面,街道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积极引入社会组织设计和完善公共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改进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并通过“一意见三目录”(即《塘桥街道关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施意见》、《塘桥街道政府职能转变目录》、《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资质目录》、《塘桥街道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目录》)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对转变政府职能和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加以明确,调动了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推动了政社合作与多元共治。
总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社会治理中相对于政府的独特作用是不容小视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运作活力和自治能力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
二、社会组织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
市场经济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需求资源的有效释放催生了社会组织,但在资金来源、经营性项目、运作过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却制约了社会组织的活力和自治空间。
(一)资金来源不稳定
目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仍然是为数较多的社会组织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虽然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做法已日渐普遍并日趋规范,但从全国来看,很多地方无论从政府角度还是从公众角度,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文化心理层面,还不习惯于从既有的公共服务政府供给模式转向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即便是已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做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从适用全国的统一性法律来看,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相关的法律仅有基础性的《招标投标法》及《政府采购法》[3]。而且这两个法律中,也并未明确规定公共服务是政府可以采购的产品,这就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缺乏全国性的法律依据。虽然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法规、条例及指导性意见,但它们大多过于原则化,缺乏必要的细则,可操作性不强。其次,由于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购买方和承接方,在谈判和协商地位上尚不能做到对等,两者之间的合作随意性较大,购买程序不太规范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多时候,购买方对于购买服务的类别、项目、数量、标准、价格、评估办法等没有深入细致的考虑,缺乏科学、专业的设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作为服务承接方的社会组织,由于对政府存在政策依赖和资金依赖,社会资源的募集能力还比较薄弱,因此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基本上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在价格上缺乏足够的谈判能力。最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为购买服务而购买服务”,没有遵循中央“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的要求,而是偏向于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或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甚至以“政社分开”为名,暗示一些职能机构尽快成立社会组织,以便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利益截留和转移。这一方面可能会造成政府有限的资金给了并不专业或社会不太需要的组织而造成浪费,另一方面可能会使那些真正需要政府资金支持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组织面临经济困境。
(二)经营性项目不规范
社会组织的生长、自治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对于大多数的社会组织而言,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资金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组织通过开展经营性项目来提高组织自身的收入,弥补公益性支出。一些项目虽然没有太多的利润,但是却可以减少组织对政府和社会的资金依赖,使自身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和稳定。经营性项目是不少社会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然而,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社会服务机构(即“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营利化趋向”。不少社会服务机构注册为一个社会组织的目的就是打着“非营利”的旗号进行“避税”。一方面,一些社会服务机构从事着貌似公益的社会性行为,但背后却有着强烈的营利性动机;另一方面,公众似乎没有感受到社会服务机构有很强的公益性,相反,对营利性却感受较多。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服务机构应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非营利性应是其必须坚守的本质属性。社会组织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可以通过经营性项目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获取合理的利润,但是,过分逐利的行为可能会使组织偏离非营利性的本质,损害组织的公益形象,影响组织的公信力,甚至会受到公众的排斥和抵制。因此,对于很多社会组织而言,经营性项目对于组织的自治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自我造血的能力不强,组织很可能由于运转资金不足而使发展不可持续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但如果经营性项目牵扯了组织大量的精力,也可能使组织偏离非营利目标,甚至改变组织的性质。
(三)运作过程不独立
由于大多数社会组织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比较有限,因此,对于政府购买服务存在单方面过度依赖,这些组织不是专注于调查、倾听社会需求,回应各种社会问题,而是主要迎合政府的意图和需要,以这个为出发点来设计项目,从而导致公众满意度不高,服务项目可持续性不强,甚至有些社会组织“积极争取”与政府职能部门、在职或退休官员、官员亲属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具有“官方背景”,以便在资金支持、政策扶持、运作网络、公信度方面获得倾斜,但同时,这些组织也往往要以牺牲部分独立性和自治性为代价。政府部门往往拥有对社会资源进行垄断性分配的权力,难以割舍既得利益,一些政府部门没有将社会组织看作平等的法律主体,为了达到获利或扩张权力的目的,还是采用“控制”而不是“合作”的思路,有意无意地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错误地理解为政府可以干涉社会组织的内部事务,从而使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不独立,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以及在社会治理中独特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社会组织的活力,也延缓了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的进程。
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能力的优化路径
目前社会组织面临着法律法规不健全、获取资金不稳定、自营项目不规范、运作过程不独立等自治困境,政府要改变传统的“分类控制”思路,从“分类控制”转向“嵌入引导”,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更多的社会组织纳入与政府合作共治的制度框架中。社会组织也要从“绝对依赖”转向“最小化依赖”,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构建一种从“依附式合作”转向“协商式合作”的伙伴关系,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自治的制约因素迫使我们要深入研究其自治能力的强化路径。
(一)政府:从“分类控制”转向“嵌入引导”
康晓光、韩恒通过对八类典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实证调研,认为:“从整体上来看,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手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即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我们把这种‘多元化的管理策略’称为‘分类控制’。”[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正在探索新的思路和模式。
正如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资本、组织关系等环境因素对组织运行逻辑和发展态势都有植入性影响一样,掌握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政府,也可以将特定的机制与策略嵌入社会组织的管理中,从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干预,并促进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
1.制度引导
没有大量自立、自强、自治的社会组织,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就是一句空话。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三个目标: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归根结底都需要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随着《慈善法》草案的出台,很多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其外部活动和内部治理都得到了相应的引导和规范。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三个专项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相继出台,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的自治结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的范围,逐步走向民政部门的单一管理。降低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门槛,逐步建立“备案登记、法人登记、公益法人登记”的三级准入制度,将大量社会组织放在阳光下,纳入法律法规监管的体系中。此外,将社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政府依法行政、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政府依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机结合,将政策资源嵌入社会组织的管理中,正确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
2.资金引导
大多数的社会组织都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因此,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杠杆,通过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流程,通过对完成项目社会效果好、影响大的社会组织实行资金奖励或优先续签合约等方式,加强对社会组织自治的资金引导。其次,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与资质审查,建立相应的许可和准入制度,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记录在册。政府可以通过向困难居民发放社会组织服务现金抵用券的方式,一方面使困难居民能够免费或者以较低的成本享受有资质的社会组织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向有资质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现金抵用券的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资金引导。再次,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激励和引导,为社会组织建立提供服务的质量标准,避免欺诈行为的发生,并通过指导或限制提供服务的费用,对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不是指定某个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而是居民拿着社会组织服务现金抵用券,自由选择服务的提供者,这就可以促进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质优价廉的社会服务。最后,对于没有实现或无法实现财政可持续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慈善类组织,政府提供补贴是维持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于那些宗旨性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正向功能明显、在居民中口碑较好的社会组织,即便没有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也可以对机构或项目提供补贴,用于机构的员工工资、场地租金、办公经费等,使这些社会组织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从而发挥资金的嵌入引导作用。
(二)社会组织:从“绝对依赖”转向“最小化依赖”
萨拉蒙认为,社会组织应学会巧妙地与政府合作,在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的同时,保持相对的自主权和独立性[5]。对于大多数的社会组织而言,外部资源的获取是不确定的,组织对外部资源存在依赖关系,这里的外部资源主要是指政府、社会所提供的制度性资源和经济性资源。一方面,社会组织要使自身的结构、行为的模式和行动的策略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双重认同,以获取组织需要的制度性资源和经济性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还要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成效、增加透明度、提升公信力、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等保持自身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组织自身对于政府所提供的资源的依赖程度最小化。
但是,从“绝对依赖”到“最小化依赖”[6]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过程,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须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熟以及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相伴随。就目前来看,我国社会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期,虽然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形成了初步的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双方的地位实际上很难做到对等,因为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是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源,而社会组织的资源尚不能对政府构成约束,因此,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制度资源和资金资源仍然会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绝对依赖”,但是,从“绝对依赖”走向“最小化依赖”是方向也是必然。
(三)政社关系:从“依附式合作”转向“协商式合作”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是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在这个需要多元合作的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完全独立,为了维持其生存,组织必须引进、吸收、转换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来自环境中的其他组织[7]。虽然“小政府、大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由于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引导和资金引导的方式对社会组织施加影响,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经济性资源存在非对称性的“绝对依赖”,因此,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还是一种“依附式合作”关系,即在政社合作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为了获取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可能更多地会从政府的意图出发设计公共服务产品和项目,从而对政府形成一种“依附式合作”关系。在社会组织发展的初期,这种形式的合作可能还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
实际上,政社关系的理想模式应是逐步减弱“依附式合作”,走向一种相对平等的“协商式合作”关系,双方应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基于目标的一致性、相互信任、资源与功能互补而形成一种组织间互相协商、互动、合作的关系,切实把政府从“社会之上的政府”转变为“社会之中的政府”[8]。这个过程并不是削弱政府的权力,而是权力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随着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协商沟通的制度化,政府通过国家的基础性结构,经由社会而实现的基础性权力会不断增强,政府能够越来越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能够更多地借助社会组织实现政府目标[9]。
结 语
在现代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与政府管理和自治不同,多元共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和合作机制的共同治理,合作机制是多元共治的核心机制,合作是多元主体集体行动的前提和基础。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对待社会组织有五种政策选择:防范、无视、收编、利用、合作[10]。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是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对于公共价值的共享以及在公共话题领域中的共同行动是两者合作的基础。在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架构下,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政府要改变“分类控制”思路,在体制上为社会组织松绑,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拓展更大的空间,为社会组织的自治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嵌入式政策引导、资金引导等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要利用其民间性和专业性特点,发挥政策倡导功能,并通过社会组织负责人加入各级政协、人大及党代会,或通过联席会议等政策咨询机制,积极建言献策,协商议政,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社会组织也要有意识地通过内部结构优化与外部项目拓展,为社会提供更为高效和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强自身获取和吸纳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步弱化对政府的依赖和依附,尽力保持自身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与政府协商互动,有效合作[11],在社会治理中体现更为重要的价值。
[1]李立国.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激发和释放社会发展活力[J].求是,2014,(10):48-50.
[2]关信平.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4,(3):83-89.
[3]周芹,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面临的难点及对策[J].中国政府采购,2013,(4):36-37.
[4]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73-89.
[5]萨拉蒙,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0:27.
[6][美]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4.
[7]RICHARD H HALL.Organization:Structure,Process and Outcomes[M].New York:Jersey Prentice Hall,1991:278.
[8]史云贵,欧晴.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J].社会科学,2013,(4):25-32.
[9]汪锦军.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J].政治学研究,2015,(4):98-105.
[10][美]朱莉·费希尔.非政府组织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8.
[11]杨君,徐永祥,徐选国.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95-105.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Autonomous Dilemma and Optimized Path—The Experienc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Shanghai
MA Li1,2,CAO Jin⁃qing1
(1.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2.Department of Sociology,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anghai 200233,China)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and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social governance.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we must mak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Under the goal and require⁃ment of“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and“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the developing space and the capacity of self-governa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How⁃ever,recently,social organizations still fac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at the source of funds is not stable,the oper⁃ation of projects is not normative,the process of project operation is not independent and so on,which makes us rethink the path of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On one hand,the government should change the traditional“classification control”ideas,use“embedded guide”ways by policies and funds,expand the autonomous space fo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On the other hand,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also change from absolutely depending on the government to“minimum dependence”,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autonomous ability.This kind of bidirectional changes is likely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from“dependent cooperation”to“deliberative cooperation”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governance;autonomous;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913
:A
:1009-1971(2017)02-0001-07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6-12-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15ZDC028);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性重构研究”(16CSH06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0326);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WE1524302)
马立(1976—),女,江苏镇江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从事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曹锦清(1949—),男,浙江兰溪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转型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及三农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