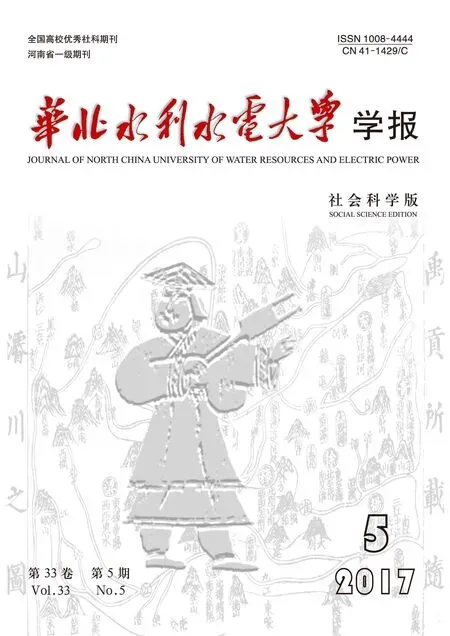文学地域主义视阈下文学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建构
——以薇拉·凯瑟的小说为例
2017-02-23张文娟
张文娟
(太原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12)
文学地域主义视阈下文学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建构
——以薇拉·凯瑟的小说为例
张文娟
(太原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12)
地域文学观在薇拉·凯瑟的创作过程中影响着其小说中人物身份的建构。凯瑟以地域文学创作观念,即地域的丧失、欧洲传统文化的坚守、地域主义女性文学观、印第安文化的认同等,构建了一个个多重复杂的文学地域身份,如女性拓荒者、移民“民族”身份、印弟安文化身份等,以更加细致、变通和辩证的态度阐释文学创作和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
薇拉·凯瑟;文学地域主义;地域;身份建构
薇拉·凯瑟是20世纪初杰出的小说家,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对美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具美国西部地域色彩,清新的作品风格独具特色[1]。凯瑟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能够摆脱传统创作思维的约束,致力于艺术形式、思想内容二者的有机融合,因此得以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和传播,对研究凯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学者在多维角度下开展研究工作,重新将凯瑟的小说带入到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浪潮中,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凯瑟这位出色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借助凯瑟小说在叙事结构、情节、主题等层面所体现的不确定意义、复杂性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读者喜爱凯瑟小说的重要原因是其对土地所持有的真挚情感。到目前为止,各国研究凯瑟的专著约为70部,包括20多部传记,论文数量繁多。针对凯瑟进行的研究,涵盖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同性恋论、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读者反应批评、人类学等视角。然而,在凯瑟小说的文学范畴归类方面,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Susan J.Rosowski和Demaree C.Peck将凯瑟视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2]21;艾米·阿赫恩、约翰·莫菲两位学者在研究中探究了自然主义与凯瑟之间的关系[3]。
当前,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社会中的个体身份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对地域文化产生了极大挑战,人类基于地域的民族归属感也在不断淡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开始主动、积极地探索自我,期望能够探寻根源。本研究主要从文学地域主义的视角出发,借助传记批评法、新历史主义批评法及文本分析法等多种方法,深入研究凯瑟的文学作品,对其文学作品中角色的构建进行剖析,探究其小说所表达的地域文学创作理念及多样化的文学地域身份,全面了解其小说创作中地域文学观的重要性。同时,研究作家凯瑟同其生活地区的关系,详细分析地域诗学特征,运用全新的文学视角来研究凯瑟小说,将凯瑟基于美国西部地区所创作的地域文学作品进行深刻分析,充分挖掘凯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意义。
一、凯瑟的地域文学观
早期美国的原属州——弗吉尼亚造就了帕特里克·亨利、华盛顿和李将军等众多历史名人,该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联系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关键所在。从属于弗吉尼亚州的后溪谷就是作家薇拉·凯瑟的故乡。薇拉·凯瑟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摆脱了传统理念和制度的约束,着手研究历史文化。薇拉·凯瑟拥有的大量家族资料信息,通过其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充分地体现出来,弗吉尼亚即凯瑟小说的原始背景。凯瑟的南方生活为期较短,然而却深深影响着其生活和创作。美国西进运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欧洲移民、美国人纷纷向西部转移。由于凯瑟家的谷仓被烧掉,所以才远离家乡,在内布拉斯加的分水岭定居。童年的记忆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凯瑟在年龄较小时就有了背井离乡的生活经验,位于中西部的分水岭成为凯瑟新的生活环境。凯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感受到陌生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内心不安,以至于之后在对凯瑟的采访过程中,采访者也可以感受当时凯瑟的心理阴影,荒凉的内布拉斯加扎根在凯瑟心中。由此可以看出,地域丧失是导致文化、社会关系及生活家园丧失的根源。通常人类都会通过怀念及悲伤的情绪来体现对遗失事物的惋惜,凯瑟则不同,其将注意力转向文学创作,通过全新的方式抒发内心情感,使心中的爱得以在新地域表达出来。分析凯瑟的小说作品,可以发现,对于遗弃过往、家乡及亲朋好友的人来说,生活中笼罩着悲伤的情绪,但是凯瑟会将新生活地区的环境描述得更加优美。
1911年底,凯瑟辞去《麦克卢尔杂志》的主编职位,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她接受了朱厄特的建议,选择了自己最熟悉和最亲切的西部作为创作素材。早期丰富的文学积累与广泛的阅历深化了凯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使其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当她开始反思过去的生活时,对创作有了更深的感悟,能够分清“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她所欣赏所崇拜的东西”,并且不再局限于自己所喜爱的、与自己观念相契合的环境与人物,能够以更加全面客观的态度,将更广阔的社会景象纳入创作视野中。将西部置于历史的大坐标中审视,将体验内化后输出,凯瑟分别对照分析了东部与西部、旧世界与新大陆、草原与城镇,描绘出宽广的地域,同时还体现出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感,追溯了精神源泉。
凯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回忆与纪念。她的作品都是她自己与身边所认识的人的经历,但是又经过了她的内化加工,她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赋予其笔下的人物,使他们带有凯瑟的个人标记。“她所做的就是进入一个房间,与你谈论一些她曾经认识并喜爱的人。她没有创造而是重新排列她的记忆。”凯瑟在创作草原三部曲时己经30多岁,虽然她写的是回忆中的故乡,但是这个故乡却是经过了她的加工,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受融合进去的故乡。因此,它不只是对历史的重现,更是凯瑟自身经历的呈现。她写的不只是西部,更是西部处在社会巨变中的人,西部的生活变化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变化的浓缩;因此,其作品就有了更加丰富的涵义与厚重的历史感。
在1913年至1918年间,凯瑟陆续以西部为背景创作出了《啊,拓荒者!》(1913年)、《云雀之歌》(1915年)、《我的安东尼娅》(1918年)三部小说,在评论界与读者中都大受欢迎,取得了极大成功[4]。这三部小说讲述了19世纪末拓荒晚期内布拉斯加草原上移民们的生活。凯瑟在移民的生活中展示了他们所继承的欧洲传统文化与西侵的美国现代物质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在冲突中现代文化强势地占领着传统文化的地盘,西部乡村慢慢被同化,物质欲望战胜了精神追求。对此,凯瑟感到愤慨与痛心,并努力探寻一条出路,创造出新型的拓荒者形象,体现出她自己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
美国政治、文化及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均受到20世纪60年代新思潮的影响,在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多种全新理论,包括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及新社会历史主义等,促进了美国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广大学者在分析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过程中,由于1970年重新提倡地域主义研究,所以地域主义文学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在女权主义批评者看来,女性作者基于地域主义文学视角,创作空间更加广阔,为母性及哺育价值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地域文学作品内的女性角色体现出来。其中,最具特色的女性地域作家就是凯瑟。通常人们都将女性作者、地域作家分离开来,认为这些女性作家在地域主义领域中对女性世界进行了分析,她们在新时期需要对自身性别地图进行构建。在女权主义批评者的视角下,作为特殊工具,地域文本能够对不同经济体、阶级、种族及性别的人进行分析,从而构建等级制度,不会在现代层面来区分地域主义,能够针对广大女性构建起自身领域,确保男、女领域能够在地域意识及构建方面达成一致,打造区别于男性的特殊叙事风格。由此可以说,女性文学、地域主义文学非主流,二者在女权主义批评者眼中占据着相同的地位。加兰德的思想理论同女权主义批评者的观点相似,认为批判美国政治及社会为地域主义的本质所在。但是,就女权主义批评者所创作的地域文学作品来看,其并没有意识到实际存在的地域,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纯文本,评判女性文学的角度不够全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注重性别的同时没有正确地看待周围环境、地区的影响力,对地域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凯瑟这一阶段创作的小说有《教授之屋》《一个迷途的女人》《我的死敌》,作品中的主人公同之前塑造的乐观形象完全不同,均在社会生活环境下失去希望和发展方向,从而做出错误判断和决定[5]。其中,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推崇消费和金钱的同时,圣·彼得教授仍然坚持内心的信仰,安静、沉稳地面临即将来临的死亡;而玛丽恩·福瑞斯特太太由于生活所迫,投靠投机商而不断沉沦;米娅·汉舍尔受到金钱及权力的诱惑,导致身心俱疲,不堪忍受痛苦而悲惨死亡。凯瑟在该时期所创作的小说均以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且将科罗拉多的方山、西部小镇及伊利诺伊小镇作为故事的地理环境,不再以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为主,转变了地域风格。所以,很多人也将该时期凯瑟所创作的作品命名为危机、迷失小说。
作为凯瑟的著名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备受读者的关注,这部小说还被改编为电影,凯瑟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对文学界的影响力也较为深远[6]。以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许多作家深受薇拉·凯瑟的影响,其创作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写作风格,同凯瑟的经典之作——《一个迷途的女人》存在很多相同点[7]。
作家凯瑟面对文化认同危机也同样会迷茫,无法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无法在实际生活中探索出走向,常常怀念过往的事,以期通过怀念过去的方式对迷失自我的缘由进行探究,从而探索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凯瑟开始认同和接受传统印第安文化,因其拥有西南部探险的经历,所以凯瑟在幼年时期就对印第安文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无法正确地看待印第安文化,认为其存在一种神秘感,象征着原始野蛮力量,缺少正确的认知理念。由于凯瑟后期的生活经历,她逐步加深了对印第安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感受到印第安文化独特的魅力。该文化蕴含着深厚的自然观,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注重追求艺术化的生活,这些都深深感染着凯瑟。再加上一战的影响,凯瑟本身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这就便于其更快、更自然地接受印第安文化。
凯瑟在19世纪初期多次到西南部旅游,在亚利桑那州游历大峡谷、穴居遗址后,产生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促使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也安抚了其内心的动荡,使其能够以一种平和、稳定的心态面对今后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凯瑟在探究过程中发现了悠久的美国发展史,印第安土著人文化更新了其对美国历史的看法,促使其不断深入地分析土著民族文化历史。凯瑟的小说作品总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其对印第安文化的看法,其对印第安文化的认同感呈现出逐步加深的趋势。
二、地域文学观下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塑造
在小说《啊,拓荒者!》中,凯瑟利用自身的创作素材,在作品中将故事情节、角色形象构建在地域元素的基础上。乐观向上是中西部乡村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影响凯瑟的一种重要文化,由此使生活于内布拉斯加的凯瑟能够对作品中人物身份及其主体性进行创建。凯瑟与其他地域作家存在很大的区别,其在创作《啊,拓荒者!》这一小说的过程中,摆脱了原有男性拓荒者的人物身份,重新建立了女性拓荒者这一形象,凸显了女性的英雄形象。凯瑟借助笔下所创造的亚历山德拉这一拓荒者角色,实现了文化认同感的转移,其并不是一味地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生活状况进行描写,而是从全新的角度阐释拓荒者角色,将女性元素融入到地域叙事领域。
亚历山德拉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具有勇敢、忍耐力强的性格特征,不再受传统社会女性地位低下落后思想的约束,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和奋斗来保障今后生活。作品在对亚历山德拉这一人物形象进行描写的过程中,将男性元素赋予其性格、外表上,由此也可以看出男权制在当时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而凯瑟也对此表现出一定的认同感。小说最初针对亚历山德拉的服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人物性格的塑造奠定了基础。主人公身穿男性外套,亚历山德拉似乎本身就非常满意和适应这种打扮。这就表明亚历山德拉并不介意自身的男性气息,而是以此为傲,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内心情绪的变化。亚历山德拉深受父亲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像父亲那样生活,而她也没有将自己的热情全部投入到这块土地中,所以不会主动参与到家庭活动中,仅仅想要借助土地来获得金钱。亚历山德拉和一般的女性不同,和母亲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并不具有抵抗父权的意识,不再受传统女性理念的束缚,更加认同和肯定男权主义。所以,在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亚历山德拉刻意地隐藏内心的柔弱性格,抵抗心理情绪的释放和发泄。
正是因为亚历山德拉的思想行为,才使其备受父亲的青睐,在整个家庭中的位置相对较高。父亲在生病后对亚历山德拉寄予很大的希望,要求家庭其他成员要跟随亚历山德拉对土地进行保护,不要产生内部纷争,要积极拥护亚历山德拉。这表明父亲非常肯定和赞赏亚历山德拉,也导致亚历山德拉产生非常明显的男权思想倾向。
正由于拥有在内布拉斯加荒原生活的经历,凯瑟能够在小说中对移民生活进行详细的描写,童年时期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其能够积极地投身艺术追求,移民文化对其有着很大的影响,也使其对欧洲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不同地域中感受着不同的文化,帮助其形成包容的文化态度,能够正确地接纳多元文化。凯瑟意识到移民生活经历多是通过口头形式传播的,欧洲历史存在于很多古老传说中,其在小说《我的安东妮亚》内,结合故事大概情节和背景,通过构建的多个人物形象,对众多欧洲故事、传说进行组合[8]10-12。美国西部地域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发生的,这些故事来源于大量的移民生活和地域故事。
在小说《我的安东尼娅》中,作者就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欧洲移民、美国人进行了描述,包括瑞典人、波西米亚人等,并对内布拉斯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在罗西看来,该作品赞扬了人类精神,并分析和研究了新、旧世界间的张力。凯瑟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承着这一观念,旧世界象征对历史的传承,人类要想更好地迎接新世界,就必须抛弃传统,在对新世界进行适应的过程中,对旧世界予以怀念,才能真正认同自身的美国身份。在该部作品中,主人公吉姆来到内布拉斯加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短时间内无法融入到新生活环境中。之后,其在祖母的菜园中感受到自然的魅力,从而产生了转换思想观念的想法,不再沉迷于过去,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身份归属感。家庭社区是吉姆的主要生活场所,有祖父母、雇佣者等,他也参与到跳舞棚及哈林家族中,成为城市精英人群。吉姆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由最初的草原逐步转移到小镇、大城市。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凯瑟对文化传播和空间迁移进行了描述,并明确了对故乡的眷恋情感和寻找美国民族身份认同感的创作主线。威廉·汉利认为,由于内布拉斯加大分水岭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区域既包含了西部文化的经典,又融合着东部文化的精髓,对凯瑟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孩提时代,她经常来到此处,而这里移民们的生活和女拓荒移民身上那种独特的、坚毅的人格魅力更是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种子。所以凯瑟才会非常热衷草原文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不断思索和探寻内心深处对于移民身份归属的感悟。
印第安文化很早就在凯瑟的作品中出现了,但是在早期作品中,作为个体的印第安人却无处可寻。在《云雀之歌》与《教授的房子》中,以印第安穴居遗址为代表的悠久灿烂的印第安文明是主人公灵魂的休憩之所和艺术生命再生之地,而在《死神来迎大主教》中,凯瑟走出了博物馆和文化遗址,走进了印第安人的村落和草屋,走进了实实在在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中[9]。而存在于真实生活中的鲜活的印第安文化向凯瑟展示了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与融合力,身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剧烈冲突导致的危机中,印第安文化逐渐得到了凯瑟的认同。文本中,拉都主教满怀激情地进行着传教工作,使教区渐渐变得有序而安定。他撤换了不合格的本地神父,将天主教的正确教义教给教民们,改变生活中的一些陈规陋习,还在凶恶残忍的美国人巴克·斯开厄斯手中解救出墨西哥女人马格达莉娜,重新给予她自由。主教正直而无私的行为受到了教众的欢迎,传教工作有序地开展着。但是,主教也发现了印第安人对传统宗教的信仰是天主教怎么都无法改变的。
与印第安文化的冲突碰撞,还使拉都主教领悟了自己所信仰的天主教的真谛。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随着对教众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的深入了解,拉都主教的内心产生了矛盾。在这片复杂的土地上,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或者说是天主教的贫乏与无力,感到了传教的可笑。“一种失败感揪着他的心……他的灵魂成了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他的内心空虚,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他的教士或教民们。他的工作似乎很肤浅,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屋宇。他那辽阔的主教管区仍然是一个异教地区。印第安人走着他们恐惧和黑暗的老路,带着不祥之兆和古代的阴影同别人打仗。墨西哥人则是玩着宗教游戏的孩子。”[9]与这些根深蒂固、古老的传统相比,宗教似乎显得非常浅薄。这里的人们实际上有着自己明确的信念,不需要再塞给他们另外一个需要膜拜的神明,这种工作是不必要也是无用的。他所肩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这种疑虑深深困扰着他,让他感到痛苦,思考传教的真正意义。而随后在教堂里遇到墨西哥老婆婆并给予她帮助后,他领悟了宗教的真谛——怜悯、给予、支持、宽恕。“他从未像那个夜晚对宗教所给予的神圣的欢乐体会得如此深切。跪在她身边,他能体会到祭坛上的东西对她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是多么的珍贵,他又体验到他年轻时代体验过的那种神圣的奥秘。认识到天上毕竟存在着一位大慈大悲的女子,虽然地上有那样残酷凶恶的人们,他也似乎能感觉到这种认识对她的全部意义。温情,只有一位女子,天上的圣母,能够懂得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一切苦难。”
在与印第安传统信仰的碰撞中,拉都主教体会到了印第安文化的古老与强大,正是那种文化造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而在此过程中,他也得以透彻地领悟天主教的真谛,摆脱了困扰他多年的疑虑,思想得到了升华,意识到这种交流的益处,改变了初始宣扬天主教、改造所有人的想法,对印第安文化给予了尊重与理解。
三、结论
凯瑟的地域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笔者在对凯瑟的地域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地域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及不同的分析方法,使地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化,弥补了传统分析方法的弊端,能够将地域诗学特征有效体现出来,迎合了多元化文学价值、文化意义的基本规律。优雅、简练是凯瑟小说的独特风格特点,其在小说中对传统叙事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将地域描绘得极具艺术气息,使地域文学作品更具艺术创新性,备受学者的关注。通过凯瑟的作品,能够发现其在不断提升和创新创作技巧。凯瑟借助多种不同的创作技巧,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突出了作品的互文性,让文本、读者进行充分的互动。此外,她还运用破碎的叙事形式、变换的时间及开放的结尾,使作品的结构框架更加丰富多样,展现出凯瑟的高超文学创作能力。
[1] 孙宏.美国文学对地域之情的关注[J].外国文学评论,2001(4):78-84.
[2] 孙晓青. 文学印象主义与薇拉·凯瑟的美学追求[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孙宏.薇拉·凯瑟作品中的生物共同体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 2009(2):71-80.
[4] 邹德芳.解析《啊,拓荒者!》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J].芒种,2014(3):70-71.
[5] 欧阳玲.女性和她们的环境:薇拉·凯瑟的三部小说:《哦 拓荒者!》《我的安东尼亚》《一个迷途的女人》中女性角色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6] 陈妙玲,吴非祺,李频.《一个迷途的女人》的生态批评[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6(2):66-69.
[7] 赵伟,罗绮伦.路就是全部:谈薇拉·凯瑟“迁移”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J]. 作家,2011(2):46-47.
[8] 陈蕾.《我的安东妮亚》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9] 马玉华.威拉·凯瑟文化身份认同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ConstructionofIdentityinLiteraryWorksfromthePerspectiveofLiteraryRegionalism— Taking the Novel of Willa Cather as an Example
ZHANG Wenju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College, Taiyuan 030012, China)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literature influ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s in Vera Kaiser’s novels.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literature creation that is, the loss of the region, the persistence of Europea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feminist literary view of regionalism, the identity of Indian culture and so on. She u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ple complex literary regional identity, such as female pioneers, immigrants “national” identity, the Indian brothers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to more detailed, the flexible and dialectical attitude to expla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reation and geography.
Willa Cather; literary regionalism; region;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2017-05-24
张文娟(1978—),女,山西古交人,太原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I106.4
A
1008—4444(2017)05—0149—05
(责任编辑:王菊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