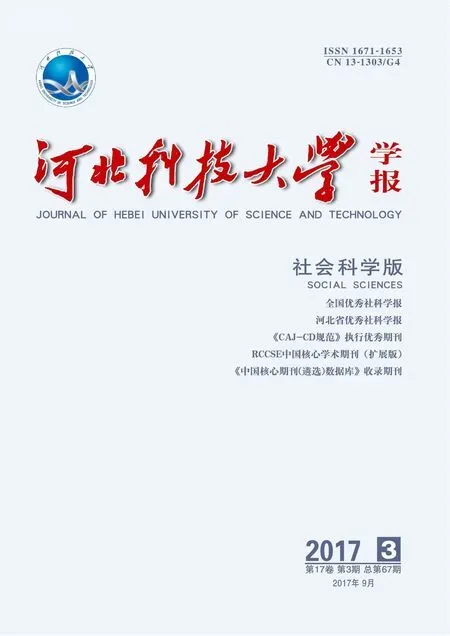民俗事象与哈代小说叙事
2017-02-23陈珍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民俗事象与哈代小说叙事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哈代小说与民俗有不解之缘,民俗事象构成哈代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情节,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的命运轨迹,在时间上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民俗事象也是作者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此外,民俗事象还构成小说细节,深入到小说肌理,发挥润滑链接的作用。民俗化叙事是哈代小说鲜明的艺术风格,民俗文化内涵是哈代小说重要的艺术审美。
哈代小说;民俗事象;叙事艺术
民谣专家古默里(Gummere)在《通俗民谣》中称哈代为“威塞克斯农民习俗的权威”[1](P248)。哈代以其厚重的民俗文化底蕴,在小说中展示了一副盛大的 “民俗风情画”[2](P354),是英伦民族风习的集大成者。民俗事象①构成了哈代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情节,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的命运轨迹,许多人物都在民俗活动中走过了人生的历程。民俗事象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因此,民俗活动也是作者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民俗事象除充当主干情节外,还构成小说细节,深入到小说肌理,发挥衔接过渡的作用,成为哈代小说民俗化叙事不可或缺的成分。此外,哈代还运用民俗题材来烘托地方氛围,渲染乡土色彩,拓展深化主题,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地方文化魅力。R.L.史蒂文森(Stevenson)把小说艺术归纳为叙事艺术,哈代的小说艺术就是基于民俗事象的叙事艺术,民俗事象构成哈代小说的重要内涵,是哈代小说的叙事范式。本文将从文本叙事的角度梳理民俗事象与哈代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发现民俗文化在小说中的文本意义。
一、民俗事象与叙事结构
哈代素以地方色彩和乡土书写闻名,其小说多以乡村为背景,以农民为主要人物,乡村是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主要空间,民俗是最贴近农民这个群体的文化现象,因此,民俗文化在哈代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俗文化是营造哈代小说乡土气息不可或缺的因素,哈代充分利用民俗文化进行小说叙事。纵观哈代的主要小说,民俗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民俗事象构成了哈代小说的主要情节,这在“性格与环境小说”《还乡》《远离尘嚣》《卡斯特桥市长》和《苔丝》中表现尤为显著。整个小说都由相关民俗事象串联而成,在各种民俗事象构成的链条上,在各种民俗事象的演进过程中,故事情节得到了拓展,人物命运发生了变化。民俗事象作为小说的叙事核心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小说中有几个大的民俗事象就有几个主要情节,如《还乡》中的“祝火”、“幕面剧”、“抓彩会”、“吉卜赛舞会”、“五朔节”;《远离尘嚣》中的“雇工集市”、“圣瓦伦丁节”、“洗羊”—“剪羊毛”—“剪羊毛的晚餐”、“丰收晚宴”、“格林山羊集”、“圣诞晚宴”;《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羊市卖妻”、“民间娱乐”、“地方庭审”、“讦奸游行”;《苔丝》中的“妇女游乐会”、“蔡斯伯勒饮乐会”、“圣母领报节”等,这些民俗活动分别构成了各小说的关键环节。哈代以民俗活动为核心情节和人物活动场域,在民俗语境中发展情节、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叙事手法与川端康成《古都》的叙事手法相契合。
民俗事象在哈代小说中除充当主干情节外,还构成了小说的细节,深入到小说的肌理,发挥着微妙的作用,成为哈代小说民俗叙事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这些细节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虽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发挥了衔接过渡的功能,收到了润物无声的效果,比如《还乡》中,婚前张贴布告、结婚扔便鞋讨吉利、送喜糕、切喜糕、礼拜日理发、针扎巫婆放血解魔法、火烧蜡像施巫蛊、用蝮蛇脂油治蝮蛇咬伤、给新婚夫妇唱祝愿歌和送鹅毛褥子等;亨察德找巫师预测天气;琼·德北用《算命大全》测算命运;芭丝谢芭用圣经和钥匙预知婚姻等等。如果说集体性大型民俗事象作为主干情节建构小说骨架,那么小型民俗事象则作为细节充当小说血肉。另外,哈代在小说中还适时穿插了民谣、民间故事、谚语、俗语、俚语为主的语言民俗事象,或刻画人物性格,或预示人物命运,或点化文本主题,或铺设情节背景,或营造故事氛围,或渲染乡土色彩,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乡土文化魅力。因此,民俗文化为哈代提供了创作素材和艺术灵感,民俗认同是哈代小说创作的心理基础,哈代小说就是各类民俗事象以民俗叙事艺术串联起来的乡村故事。在民俗化叙事过程中,哈代没有对现实民俗进行机械复制,而是根据故事需求做了必要的艺术加工,倾注了自己的艺术匠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哈代小说是现实民俗艺术化的产物。
哈代的民俗叙事形成了一种规律,各类民俗事象在小说中按开场—拓展—转折—收场的基本叙事顺序出现,故事沿着民俗事象构建的主干情节的变化演进并逐渐走向高潮落幕,因此,民俗事象规定了哈代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每一个主要情节都与相应的民俗事象息息相关,跟民俗事象同步发展并形成呼应。哈代秉承了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传统,以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依次安排情节并逐步完成文本叙事,带有传奇风格,常以情节制胜,在文学叙事学上属缪尔(Muir)所谓的“行动小说”或福斯特(Forster)所谓的“情节小说”[3](P174~175),每一个情节由富有巧合和离奇特质的人物行动构成,每一次重要的行动都被设定在一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民俗活动上,这样民俗活动出现的时间直接制约着情节推进的时间,民俗事象的节奏就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民俗事象形成了小说的有机结构,构成了故事情节的主要链条,故事在这个链条上以一种逐步向前推进的节奏发生、发展、高潮、落幕。故事往往在民俗活动中拉开序幕,在民俗活动中情节得到拓展,并且在民俗活动中实现转折,最终在民俗活动中落下帷幕,形成“起、承、转、合”式的叙事模式。
二、民俗事象与叙事脉络
哈代小说基本呈现出以社会民俗②事象“开场、拓展、转折、收场”为顺序的叙事范式。《还乡》以爱敦荒原的祝火节展开了小说叙事,通过祝火狂欢描述了故事发生的环境及背景,祝火节是纪念1605年福克斯火药案成功告破的节庆活动,但民间祝火节却带有原始宗教督伊德教的痕迹;[4](P32~33)紧接着通过圣诞节欢迎克林返乡的幕面剧(Mumming)来拓展小说。幕面剧是英国一种古老的类似情节剧的民间戏剧,是19世纪英国广泛流行的节庆活动之一,有搏斗英雄剧或圣乔治、剑舞剧、耕作剧或求爱剧三类。[5](P41)《圣乔治》的演出为克林和游苔莎的会面提供了绝佳场所和机会,二者的相爱使韦狄断了游苔莎的念头,转而跟朵荪结婚,这一环节成为人物关系和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对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幕面剧在小说叙事上发挥了链接和拓展故事的功能,主人公“归客”克林的登场正式拉开了《还乡》的序幕,抓彩会和吉普赛舞会在故事的不断演进中起了实现情节转折的作用。抓彩会为中心的民俗事象制造了婆媳间的矛盾,加剧了人物关系危机,为下一个情节“姚伯夫人之死”做了铺垫,从此故事迅速朝着悲剧的方向发展。“吉卜赛舞会促成韦狄和游苔莎自我毁灭的情节是小说的叙事要点”[6](P100),它复活了男女主人公潜意识中的“异教精神”[7](P381),冲散了他们淡薄的道德意识,使他们走上了“不受羁勒的旧路”[7](P385),吉普赛舞会给二人提供了重逢的机会并让他们燃起了逃离荒原的希望之火,他们此后的幽会间接造成了姚伯夫人之死,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了“雨夜悲剧”。哈代把小说的收尾设置在来年的五朔节上,五朔节也叫贝尔坦节,是欧洲民间具有异教性质的节日之一,旨在祈求五谷丰登、人畜旺盛,五朔节那天,青年男女在村中竖起点缀着鲜花的五月柱,并围着花柱纵情歌舞,同时还跳篝火以驱邪除病。小说通过五朔节舞会后文恩捡到朵荪手套的插曲用象征手法表现了文恩失而复得的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哈代小说的核心情节一般都需要重要民俗活动来支撑,《还乡》的5个关键情节就是5个比较重要的民俗节日,在传统民俗节日中故事情节得到了拓展,人物命运得到了发展。
《远离尘嚣》也是一部主要由民俗事象串联起来的乡村题材小说,遵循了同样的演进范式。故事开始于卡斯特桥市镇一年一度的雇工集市,民间集市属商贸民俗,主人公奥克在集市登场,几经辗转和芭斯谢芭相遇并构成了雇工和雇主的关系。在圣瓦伦丁节③故事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西方情人节有给意中人送贺卡的习俗,芭斯谢芭的贺卡使一向冷漠的博尔伍德卷入了一场爱情纷争,使奥克和博尔伍德成为情敌,从而使人物关系复杂化。“洗羊”、“剪羊毛”和“剪羊毛的晚餐”是韦特伯里牧场“生产过程习俗”[8](P44)构成的关键情节,博尔伍德向芭斯谢芭的两次求婚都与这一系列民俗密切相关。丰收晚宴,也叫“丰收家宴”,属于“农业娱乐民俗”[8](P46),它是欧洲乡村庆祝收割或粮食收仓的重要民俗节日,哈代在1849~1850年间参加过当地的一次丰收家宴[9](P20~21),《远离尘嚣》中的丰收晚宴也许就是这次记忆的文学再现。根据《英国民俗词典》,这天农场主通常准备宴席来款待雇工及其家人,这个晚宴也是雇工领取劳动报酬的时候,晚宴上还有一整套歌曲和游戏以此增加晚宴的趣味性和娱乐性。[10](P168)《远离尘嚣》中的丰收晚宴既是粮食收仓的庆祝,也是特洛伊和芭斯谢芭的后补婚宴,丰收晚宴后特洛伊和妻子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间的情感开始出现裂痕。南威塞克斯一年一度的格林山羊集上四位主人公的巧遇加快了故事走向悲剧的节奏,圣诞晚宴上特洛伊的出现终于把矛盾推向了高潮,博尔伍德开枪打死了特洛伊,这个“一度破坏过他的幸福、折磨过他的心灵、夺走了他的欢乐的人”[11](P448)。纵观《远离尘嚣》的故事结构,民俗事象构成了这则复杂爱情故事的主干情节和最精彩的片段,三位男主人公都在民俗活动中出场并卷入恋爱漩涡,同样在民俗活动中结束了这场漫长的爱情纷争。
《卡斯特桥市长》中4个民俗事象构成了小说的主干情节,主人公亨察德在这些民俗事象的陪伴下走完了人生路程。《托马斯·哈代的事实笔记》中记载了3起卖妻事件,格林斯莱德认为《卡斯特桥市长》的框架借鉴了这类故事,收于《英国民间故事和传奇》的“鞋匠卖妻”[12](P289~290)的故事内容跟《哈代的事实笔记》中的3则故事大致相同。1888年版的《现代街头民谣》的第一首就是“卖妻传”[13](P1~3), 民谣版和哈代版之间存在诸多契合点,卖妻者和亨察德一样贪杯,交易均发生在醉酒状态,买主都是水手,两对夫妻感情都不和睦,因此,交易后女方都毫不犹豫地跟了买主,故事发生的干草市场跟亨察德打草工的职业也很吻合,哈代以民间传说为原型,结合现实、虚构和想象创造了以卖妻为母题的文学佳作。卡斯特桥民间娱乐会集中展示了具有多塞特地区特色的民间游艺习俗,这一细节从故事情节上来说固然并不重要,但在故事的整体脉络上起到了一定的过渡衔接作用,自此法夫瑞日渐强势而亨察德日趋颓势。在地方法庭上卖粥妇揭发亨察德卖妻丑闻的戏剧性情节是后者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身败名裂,开始踏上了悲剧之路,丑闻还导致露塞塔和亨察德之间的情感危机。多塞特地区轻罪审判的法律民俗事象为卖粥妇和亨察德创造了对簿公堂的机会,也为人物命运的转折和情节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亨察德的悲剧铺平了道路。讦奸游行为小说掀起了又一个高潮,讦奸游行是英国古老的民俗之一,也叫司奇米特(Skimmington Ride),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惩治背离道德规范的行为的一种民俗事象,具有相当大的社会约束力,目的在于揭露奸情,暴露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败坏当事人在地方上的名声。[10](P301)讦奸游行造成的露塞塔之死促成了伊丽莎白和法夫瑞的结合,而亨察德最终遭遇了事业、家庭、爱情的三重抛弃。
《苔丝》也有3个民俗事象构成的重要情节。“哈代试图在民俗中揭示出人类的一个核心认识——一个时代盛行的仪式不可能彻底枯萎”[14](P313~327)。马勒特村的遗风余韵是最好的佐证,历时数百年的妇女游乐会是纪念谷物女神德墨忒耳(Demeter)的五朔节的遗留,这种异教风习常与性放纵联系在一起,诺曼·培基(Norman Page)认为游乐会上妇女手拿的柳枝很可能是阳具象征,是原始生殖崇拜的符号。[15](P94)苔丝和克莱尔先后在这个乡间游乐会上登场,决定苔丝命运的两次“堕落”也与民俗事象有关,第一次“堕落”起源于蔡斯伯乐游乐会,第二次“堕落”发生在履行契约的圣母领报节上,圣烛节签订的雇工合同在圣母领报节兑现,这样苔丝的两次堕落都借助于民俗事象来实现。除了以民俗事象充当核心情节之外,为了使情节顺利过渡,故事按节奏演进,哈代还常依赖于大量的偶然巧合,例如,游苔莎和韦狄在吉普赛舞会上的巧遇,格林山羊集上表演马戏绝活的正好是流浪回国的特洛伊,苔丝和亚力克在圣母领报节上的不期而遇等等,这种“无巧不成书”的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逻辑合理性,往往使故事有牵强之嫌,从而遭到了许多评论家的发难。另外,哈代因过分注重情节而削弱了人物的主体性,人物常常受到情节的牵制,因此,有些人物显得被动僵化,这也常常遭到诟病,福斯特对此就颇有微词,当然也有批评家认为福斯特的结论有失偏颇,比如缪尔对哈代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创造力大加赞赏,沃顿(Wharton)对苔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苔丝是能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萨克雷的佩基·夏普、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相媲美的具有强烈“现实感”[16](P177)的文学典范人物。
三、民俗事象与人物塑造
人物是小说艺术的灵魂,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小说的成败,亚里士多德在《诗艺》中就强调了性格和形象,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也剖析了人物的重要性。民俗事象在哈代小说中除规定情节发展方向和人物命运轨迹外,在一定范围内限定了人物活动的空间,成为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景,因此,民俗活动也是作者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段。哈代利用民间集体活动的特殊性,借助民俗事象的宏大场面为小说人物搭建了共同活动的平台,在民间活态文化场域成功塑造了众多形象灵动传神、性格鲜活饱满的艺术人物。哈代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开场形成呼应,主要人物常常在开篇的民俗活动中出场与读者见面,形成了人物程式化的出场范式,另外还通过乡民间的对话介绍人物关系。民俗事象与小说人物息息相关,充当他们的人生舞台,从民俗舞台上走近读者,同样在民俗场域告别读者,以下是哈代核心人物第一次出场与民俗事象之间的配伍关系:游苔莎—祝火节,克林—幕面剧,苔丝—妇女游乐会,亨察德—羊市卖妻,奥克—雇工集市。《还乡》中哈代让大部分人在祝火节一起登场,借助民间节日欢闹的场面生动刻画了乐观爽朗的阚特大爷、萎缩扭捏的克锐、泼辣放浪的苏珊·南色、幽默风趣的费韦等人物形象。《苔丝》中蔡斯伯勒镇饮酒行乐会上,特兰岭村民都变成了酒神的门徒,喧闹洒脱,野浪不羁,这种粗放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乡民们质朴憨直的性格、乐观豪爽的生活态度和豁达平和的心态。哈代没有用语言来评述人物性格而是让人物在民俗活动中通过自身行动来传达信息,像戏剧一样,靠人物的行为动作来自我表露,让读者亲自去捕捉感悟,从而提高了人物的动态感和真实感。
哈代还通过人物在民俗事象中的特殊表现来突出人物的“另类”性格并暗示人物的异常命运,《还乡》通过文恩的视角描述了那个飘荡在雨塚上的神秘人影,凸显了女主人公“夜的女王”游苔莎的神秘和在荒原语境的“另类”身份,参加祝火节的人挑着柴火从左面上了雨塚,但她却两手空空从右面下了雨塚,上下左右虚实,她跟荒原人的节奏正好相反,她首先是以晃动的影子出现在文恩的视线中,而村民们却是以具体的人的形状登场的,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巧妙地暗示了游苔莎与荒原格格不入的现实。她的与众不同与苔丝的标新立异在手法上相契合,游苔莎表现在行动,而苔丝表现在装束,作者以相同的手法暗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未来命运。马勒特村的妇女游乐会上,妇女皆一身缟素,手执白花,唯有苔丝与众不同,哈代以苔丝头上的红绸带来暗示其异教特质和凶险的人生命运,因为在基督文化中红色带有不祥的寓意,巫婆标志性的颜色即为红色。哈代还通过该民俗节日上的一些细节描写,预示人物的命运轨迹,男女主人公克莱尔和苔丝先后在妇女游乐会上登场,遗憾的是两人并没有跳舞,克莱尔离开时双方不无遗憾地目视了一下对方,作者以这种方式预示了二者“有缘无分”的爱情。幕面剧演出是突显游苔莎“另类”形象的又一个民俗事象,幕面剧通常在圣诞节和新年演出,场所一般在家里、酒馆或露天,演员均为男性。[10](P252~253)游苔莎为了见到克林竟然女扮男装,在剧中扮演一个土耳其武士,与她在小说开始时“与众不同”的出场遥相呼应,进一步展现了她的“他者”形象和“另类”身份,同时还表现了游苔莎敢于挑战传统的勇气与不受成规羁绊的叛逆精神。
哈代在描述抓彩会这个民俗事象时还穿插了“胎膜”俗信④和“后来者幸运”的俗谚⑤及三个赌博赢钱的民间故事来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哈代通过抓彩会及之后韦狄、克锐和文恩围绕100个基尼的赌博游戏进一步刻画了人物性格,突出了韦狄的“精”、克锐的“傻”、文恩的“智”和费韦等村民的“乐观豁达”和对生命的“坦然淡定”。《远离尘嚣》中的丰收晚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特洛伊的享乐主义和奥克的责任意识,特洛伊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形象和奥克的勤劳质朴的劳动者形象跃然纸上,从此芭斯谢芭对特洛伊开始感到失望,对奥克倍加敬重的同时又增添了复杂的情愫。在剪羊毛的晚餐上,通过唱歌娱乐刻画了普格拉斯的“害羞扭捏”,芭斯谢芭的民谣《在阿兰河两岸》隐射了特洛伊对爱情的不专一。《林地居民》中的仲夏节到森林预知婚姻的风习展示了费兹皮尔斯的“老练精明”、贾尔斯的“敦厚憨直”、格蕾丝的“文雅矜持”、玛蒂的“善良温婉”和苏克的“轻佻浮浪”。《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通过羊市卖妻透视了亨察德的“鲁莽执拗”、卖粥妇的“圆滑诡秘”、苏珊的“温良顺从”;通过讦奸游行的策划实施着力刻画了赵普的“阴险狡猾”、治安警察塔斯伯德的“猥琐懦弱”,赵普的小人形象更加清晰,后者的小丑形象更加鲜明。
民俗事象叙事手法是哈代小说的典型范式,民俗事象一方面充当规定故事发展方向和决定人物命运的主干情节,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细节的形式渗透到小说的肌理,起了润滑过渡的作用。民俗事象在时间上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民俗事象也是哈代进行人物塑造、性格刻画的艺术手段,民俗事象还有助于烘托地方氛围,渲染乡土色彩,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地方文化魅力。哈代小说就是各种民俗事象串联起来的结构更加复杂、内容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刻的乡村“民俗故事”,透视出作者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深切的民俗文化认同。
注释:
①民俗事象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指与生产、生活、文娱、信仰、制度等相关的各类民俗活动或民俗现象。
②鉴于哈代小说所涉及的民俗成分包罗万象,形式多样,数量庞大,为了文章论述的条理性,本文主要从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四分法所界定的社会民俗为基点来分析哈代小说的民俗叙事策略,以期使文章从宏观上呈现出一条完整明晰的脉络。
③西方情人节从古罗马牧神节演变而来, 是对即将来临的春天的庆祝,后来基督教会把这个节日同殉教者圣瓦伦丁主教联系起来。
④“后来者幸运”的说法可能跟“最后的有运气,脏土里捡便士” (Last has luck, found a penny in the muck.)这个谚语有关。
⑤英国民间认为,出生时有胎膜的人能免于溺水、玩牌抓彩很走运,这种俗信源于原始信仰。
[1]Gummere, Francis B.. The Popular Ballads[M].Boston and New York: The Riverside Press, 1907.
[2]张中载.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3]申 丹,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Hardwick, Charles. Tradition, Superstitions and Folklore[M].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72.
[5]Chamber, E.K..The English Folk-Play[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3.
[6]Daleski, Hillel M.. Thomas Hardy and Paradoxes of Love[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7]哈 代.张谷若,译.还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9]Hardy, F. E.. Life of Thomas Hardy[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7.
[10]Simpson, Jacqueline, Roud, Steve.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Folklor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哈 代. 傅徇宁,佟天翎,等,译.远离尘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Briggs, Katharine. British Folk-Tales and Legend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3]Ashton, John. Modern Street Ballad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888.
[14]Radford, Andrew. Dethroning the High Priest of Nature in Woodlanders[A]. Keith Wilson. A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M].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09.
[15]Page, Norman. Thomas Hardy:The Novels[M]. London: Palgrave, 2001.
[16]Wharton, Edith. Permanent Values in Fiction[A]. Frederick Wegener. Edith Wharton: The Uncollected Critical Writings[M]. Chechis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6.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FolkloreandtheNarrativeArtofHardy'sNovel
CHEN Zhe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Folklore items matter much as the decisive plots in Hardy's novel, defi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story and the fate track of the characters, and creating the space for their actions. Thus they also help the author a lot in characterization. Besides the frame plots, folklore items are woven into the tissues of the novel as the delicate constituents which function in plot transition. Such a narrative art is known as the typical paradigm of Hardy's novel and folklore proves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aestheticism in Hardy's novel.
Hardy's novel; folklore items; narrative art
I106.4
ADOI10.3969/j.issn.1671-1653.2017.03.012
1671-1653(2017)03-0078-06
2017-07-16
陈 珍(1967-),男,青海湟中人,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