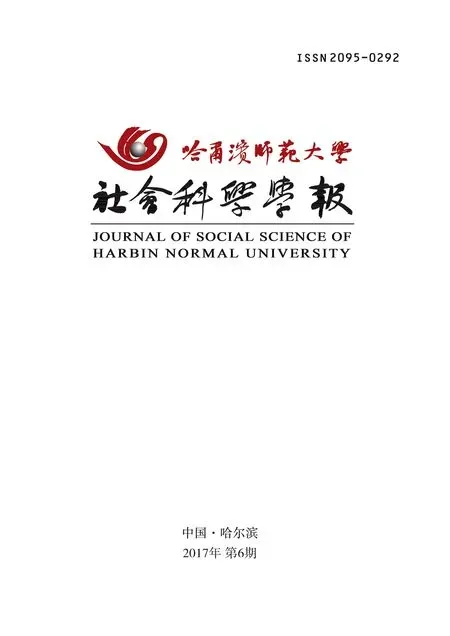相近的乡思与不同的构思
——《故乡的野菜》《藕与莼菜》之比较
2017-02-23李慧军
李慧军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读周作人和叶圣陶两位的散文,有一种亲切、快意与踏实的感觉。放下书卷,略加回想,就不知不觉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们共同的取材倾向: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写了自己故乡的物产,一个写野菜,一个写时蔬,虽然在故乡都是平常物事,但是在异地他乡却都成为他们萦绕难舍的牵挂与想念,在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同时,也成为有味儿的载体。
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在文中声称自己对于“故乡”并不特别固执或留恋:
周作人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
叶圣陶说:“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追慕平淡自然的境界,较少在文中透露情感倾向和褒贬判断,尤其在单一篇章中更是如此,如上所引他对于“故乡”的定义就表现了这种特点。虽是如此宣称,我却发现他是那么自然而然地把笔墨洒向自己的故园生活与记忆,一句“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引出的却是有关家乡的三种野菜的叙写与回忆,可谓浮想联翩,举一反三了。这样活跃的生活记忆、丰富的情境展现与文献征引,基本只有在他写到浙东故乡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来,甚至让你觉得由“絮语”转成“絮叨”。比如,在这一篇短文里,他就反复引述典籍、童谣、扫墓风俗与乡人的饮食习惯来介绍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这三种野菜,不厌其烦,更自得其乐。若把他的小品散文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出他对故乡绍兴的特殊感情,他对故乡的人事、风景与民俗的种种记述更多流露的还是欣赏与眷恋,他在古都北京的诗意栖居大半也源于他葆有着这份乡土之思。
但另一方面,身处民国甫成、军阀混战的政治中心,“淡然”其实只是周作人小品散文的形态或姿态,内隐的忧和苦才是他观照、传诉的人生本相,他的小品文写作只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是对周遭暗淡、痛苦的生活现实的逃避、遮蔽或注意转移,是以这种淡然的人生体味达到对人生的粗鄙或痛苦的平衡乃至于救赎。能做到这样一种辩证的考察,方可领略周氏小品散文的风采和真味而又不出现误解与偏差。
比较而言,叶圣陶的《藕与莼菜》就写得质直坦率、褒贬鲜明。他由在上海吃藕自然联想到家乡清晨农民在集市上卖藕,联想到农夫农妇健硕和美丽的身姿,带着欣赏的语调赞美他们的劳作成果,更表达了在自己所寄身的都市上海藕的难吃与难得,表达了对于都市贫富分化和乏味生活的不满。而本来没有味道的莼菜则以鲜绿的颜色和丰富的诗意让作者恋念难忘,上海也还是难得吃到这种应时的美味。最后作者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升华为一种哲理:“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虽然两位作者都选择了家乡的物产来传诉他们的思乡之情,但是具体写法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叶圣陶主要是捕捉了萦绕于唇舌之间的味觉,通过对比故乡与上海两地不同的味觉体验,来表达对于故乡的恋念和对于上海的不满。局部也用情境描绘廓大场景细节,如细致描绘清晨农夫农妇在市集上卖藕,以强化和美化故乡人与故乡生活的风致。结构方法是先分写后总括,最后一段就是上面引述的“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一句话,独立成段,提炼出作者对于故乡的独特界定,同时也是对于全篇的收束和升华,非常警策有力。然而,也有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收尾为累赘的,不然可以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味。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也不必去争辩的。
周作人的结构方法则恰恰相反,他是先端出自己对于“故乡”一词的界定,他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于是,作者就有了绍兴、南京、东京和北京等四个故乡。继而由妻子寻常的一句话引出对于故乡绍兴三种野菜的记述与回忆。关于三种野菜的段落是各自独立和并列的,或写挖掘野菜的情景,记述相关歌谣与风雅的传说,或以标准的植物学式的语言介绍某种野菜的植物特点,介绍民间习俗里的习惯用途或不同国度、不同城市的食用方法,或者状写某种野菜生长于田野间的美丽画面,介绍它的药用价值等。其间穿插着各地的童(歌)谣、典籍记述和风俗志一类的文字,既使有关几种野菜的介绍精确翔实,又取得了活泼生动有趣的效果,文字富有流动性和多种风致。文章最后止于对紫云英这种野菜的风俗志一样的介绍,最后一句是:“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文章到此戛然而止,没一句多余的话。在一般的文章写法上,应该有一个段落对整篇文章的内容做一个收束,或回应前面关于“故乡”一词的独特理解,或就本篇写到的几种野菜加以小结,都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周作人恰恰有意排除了这种习惯写法,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同时是不是也能取得一种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的自然通脱的效果呢,不拘一格,没有架子,有些类似于魏晋人物与文章的风致。
在我看来,把周氏和叶氏两篇散文放在一起来讨论,还可以引申出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思乡主题和家园意识的话题。叶圣陶在写《藕与莼菜》的时候,正是他第三度离开家乡苏州去上海谋生并最终决定定居于此的时候。初到上海,他很不适应这座大城市的生活,这里的民居过于低矮拥挤,里弄的居住环境更是有似丛墓;而让他感到不胜其扰的还有清晨就扰攘不息的使人心烦意乱的苍蝇的飞鸣声和噼噼啪啪昼夜不停的摔击麻将牌声;更有各种贫富悬殊、洋场乱象的潮水般冲击。对比之下,叶圣陶就自然而然地会有一种客居上海的心绪,而没有办法让自己全身心地融入这个东方大都会。在这个背景上,我看《藕与莼菜》就不仅是表达思乡之情了,还隐含着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主题,表现着叶圣陶复杂的思想文化意识:一方面追求着“五四”以来的有别于传统封建文化的民主科学进步的现代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又近乎本能地在直接触及这种文明载体——现代都市的初期感到慌乱和不适,从而引发某种不自觉的精神收缩和传统乡愁。这又说明现代知识分子走向现代的思想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在这个意义上看,不管他们的思乡感情和家园意识在审美的视域中被表达得多么动人,我觉得作为读者和评论者都有必要保持一份审视和警醒,而不是随着这股审美的激流回退或者彷徨无主。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整体上正是从审美的起点上开始走了一条回退之路的。在“五四”时期,他还能够在“绅士”和“叛徒”这两种身份上进行区分,有意发挥着作为“叛徒”的战斗作用,甚至成为引领那一时期进步思想的先驱。但是,他始终没有前驱到领袖这个层次上,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的身份矛盾所制衡,另一方面,决定于他的性格特点,他不是那种愿意负责任的和权力欲很强的人,但同时又对优裕的物质生活不是没有要求,甚至把这种要求打扮成一种富于文化色彩和绅士风度的艺术理论,并发展成自成体系又引领潮流的小品散文一脉文章传统。沿着这条道路,周作人在自己的朋友、弟子之间互为号召和推动,越走越远。我能够理解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和蕴含其中的某些苦衷,具有传统知识分子身处乱世的全身远祸和独善其身的色彩,有他的不得已,他的思想观念和文章路数之所以能够发生巨大影响也在于他的处境与抉择与很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相近之处。但是,从理论到创作,乃至于一般社会生活的应对,他的选择之中都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具有颓废倾向的享乐思想和怀疑主义的彷徨无主。在这个意义上看他的小品文,尤其是那些写故乡绍兴的文字,或介绍野菜,或叙乌篷船,或谈喝酒,都不再只是一种审美表达,同时又具有一种人生观与社会意识的投射,后面是隐藏着他后半生人生走向的必然逻辑的。
中国文学的思乡主题特别突出,家园意识十分浓厚,二者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的,在文学史中的发源与表达都可谓源远流长。这与中国地处内陆,农业文明发达,国人安土重迁、耕织持家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自《诗经》开始就有一个思乡恋土的文学主题流淌于中国文学的血脉之中,学者们或以精神分析学的“情结”理论阐发其深层心理机制,或从表达方式上归纳它的抒情模式,或历时性地总结它的流变轨迹,或从哲学层面阐述它的形上根据,等等。这个强大的文学传统一直延伸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在各种体式的作品中,譬如,冰心对海的思念,鲁迅对故乡瓜果的思念,沈从文对湘西的思念,萧红对呼兰河的思念等,这些都成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性表达。我把现代文学的思乡主题和家园意识与传统文学相区别,将其作为一种现代性来看待,是因为现代文学的表达已经有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背景和视野,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结构中,现代文学的思乡表达具有一种虚构性,现代知识者心目中的家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存在的,现实的家园已经难以回归或者再认同了。这种难以回归或重新认同的经验,鲁迅曾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这样表达过:“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表达产生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社会的现代化是以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弱化和解体为前提的,它同时产生多种后果:一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二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三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变成了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脱离了农耕文化所建构的文化价值观,改变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主动拥抱现代文明。所有这些变化在文学上形成的表达之一就是现代文学出现了大量离家出走,或出走之后又牵绊着故园之思的作品,家园是对他们的束缚,所以必须弃绝,以此作为他们对传统思想意识的叛离和新的人生道路的开始。但是,这种叛离与寻找都不是简单和一蹴而就的,离开乡村的知识分子有他们的迷茫和对新的城市环境与生活的不适应,新的人生道路不是自然而然在他们离家出走时就摆在眼前的,他们带着茫然和面对未知的恐惧一点点摸索着、试探着前行。所以,又难免对故乡的眷恋和反顾。但不管怎样,被他们留在身后的乡土和家园都是无法再回去的,他们在情感选择上的牵挂与在行为选择上的弃绝构成了十分强烈的内在张力和审美意义。家园成为他们念兹在兹又徘徊犹疑的形上寄托,这种寄托在想象中比在现实的接触中具有更为感人的意义和色彩。
[1]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M].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叶圣陶.叶圣陶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3]王一川.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J].甘肃社会科学,2002(1).
[4]卢建红.“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