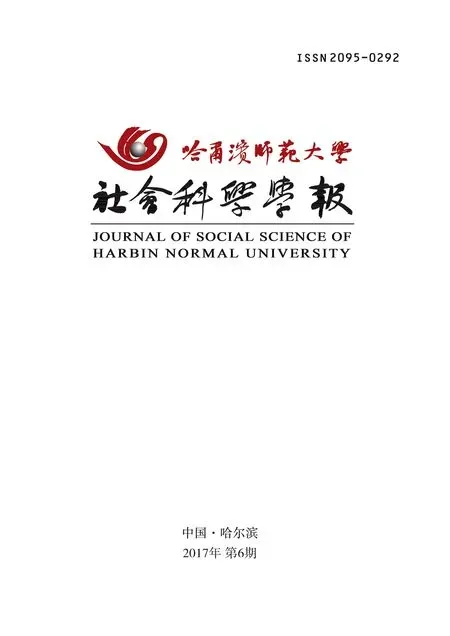在真实与虚假之间
——评孔广钊小说中身份焦虑问题
2017-02-23郭永洁
郭永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身份焦虑问题是20世纪以后不断出现的问题,它也作为一种理论难题不断被讨论与解答,与古希腊哲学的“我是谁?”的问题不同,这种身份认同危机是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现代化扩大了个体的社会生存空间,因此不同的文化土壤间的人口迁徙变得十分常见,原有的文化认同机制不再稳定,这也使得迁移的个体既呈现着旧有的文化体系的特点,又沾染了异国文化的习俗,只凭外在表征难以确认他究竟归属于哪一个文化体制,个体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孔广钊小说中的身份焦虑问题不再局限于地区迁移层面,更关注时代发展层面上每个人身份的错位和失落,现代化不仅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节奏,还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原有阶级既可能因此辉煌,也可能因此失落,就如孔广钊创作的小说《太平,太平》就以哈尔滨现代化进程为整个小说的背景,写个人的经历遭遇,时代的种种转折在历史书只有寥寥几笔,但在生活其中的普通人那里却有真实的无奈和血泪。个体的身份随社会语境发生偏移,而自我如果不以时代、符号、国籍、金钱、权力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将外在符号视为虚假,自我又要怎样去确定其真实的身份?
一、现代化浪潮中的身份焦虑
不同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而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王晓明称之为“新意识形态”[1](P78),这是以追求利为首要目标的社会价值体系,只有在市场化浪潮所带来的功利逻辑里,自私自利者才能左右逢源,心怀革命热情的工人则失掉了自己位置,强调奉献自我的社会主义理想逐渐退场。《太平,太平》里高哥故事的背景就处在这样的世纪之交(由小说里高哥被枪决时作者十二岁推测),在这个时间段里国有企业开始衰落,人心开始动摇,“人心的天平开始倾斜,一切都是根据眼前的利益来结算”。文中开头里一幕:当美丽的庞丽香出现时,工人们一阵骚动,男工人一改粗俗的吃相,老工人嘿嘿怪笑,女工人们一脸不屑。种种心态的描写表明这是一个充斥着私人欲望的空间,而不是如“十七年文学”里那样贯穿着革命的热情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世界。然而文中的主人公高哥自己仍天真地怀揣着革命理想,并将其写进求爱的情书里,以此作为爱的告白,“我会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把我火热的青春投入到祖国建设的洪流中去;我会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一颗闪闪发亮的螺丝钉”,而对方回信打开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些“革命宣言”的背面都画满了蛤蟆。这就构成了一重虚假与真实的对比,信的正面“革命宣言”是假,背面的嘲弄之意却是真的,流行的价值观念里貌似宣扬无私奉献,实则谋求私人利益。
求爱失败是一个转折点,高哥终于明白了现实的虚假,或者说此前他一直明白,却始终选择不愿相信,宁愿奉行更高尚的价值观念。当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情时,才终于对自己的工人之子的身份产生困惑——高哥失踪了,庞丽香最后在安息桥附近找到他,高哥说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意味着他将要杀死了过去的自己,重新选择或者说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出生在工厂的高哥并不是工人的长子,而是一次权色交易的意外,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所付出的代价。高哥于是不再困惑,变得极度自私自利,只为私欲而活。
安息桥是个有隐喻的地方,高哥与王立臣都在此处迷失了自己的身份,王立臣是一个任劳任怨的警察,辛苦工作一辈子还是没有升迁,他的处世逻辑不符合上位者的逻辑,因此他选择退休当和尚,却又六根未净,斩不断欲念。不论国家体制还是佛家圣地,无论哪一个体系王立臣都找不到他的位置,于是他开始出走,走出寺庙,走过太平桥,走得越来越远,却又不知道去往何处,只能“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高哥与王立臣的悲剧是现代人都会遇到的身份失落的问题,怀有革命热情、无私奉献精神的人无法在社会中得到他应得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我们告别了革命、投身资本积累的浪潮,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兴起,财富才是个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人不再是阶级的人、文学的人、活着奉献的人,另外的所谓“强者”符号取而代之,被现实碾压的普通人剩下无尽的彷徨和焦虑。
《隐形书写》对此的批评更为透彻,“‘告别革命’间或成为90年代一种深刻而可悲的社会共识。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革命、社会平等的理想及其实践,被简单地等同于谎言、灾难,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作为90年代中国的社会奇观之一,是除却作为有名无实的官样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批判的立场,不仅事实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公敌’。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经济规律’、‘公平竞争’、‘呼唤强者’、‘社会进步’。因此,在1993-1995年间,陡然迸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不仅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而且在对激增的欲望指数、生存压力的表达中混杂着的无名的敌意与仇恨”[2]。在这样的社会变迁里,高哥、王立臣都成为不合时宜的人,高哥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偷铜饼不至于枪决;或者革命热情高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也许他的理想会被理解和尊重,但他偏偏生在时代的折角处,只能在时代的错位里隐没了身影。
二、在逃避虚假中确认真实
小说《和我一起荡秋千》[3]试图通过三段爱情的描述来确认个体真实的身份,虚假符号已经包围了他们生活的空间,无论是学业、欲望、地位或者现代化都在时刻异化他们的生存空间,六个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真相和自我身份:蒙克坚守爱情,王翠翠则选择遗忘;孙坚在写作中寻找意义,肖娅逃避意义;艾苇寻找过去的记忆,倪霞像晚霞一样很快消失在夜色里。六个人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像不同方向的列车轨道偶尔交汇,又很快分道扬镳,他们对现实永不满意,不愿像大部分人一样麻木而安稳地生活,为生活中鸡毛蒜皮耗费生命。在他们看来,平凡生活的底部还隐藏着人生真正的意义。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启蒙的欺骗》[4]一书中写到了文化身份的虚假,而相似的情景总在发生。银幕上总能看到明星是如何一步一步从普通大众变为商业宠儿的。而实际上明星是被文化工业体系塑造出来的一个符号,明星和常人的不同,并不在于本人特殊的品质或能力,而是位置使然,时代的机遇成就了明星这一职业,这是整个文化工业体系外在的加持才确立了这样的位置。不止文化工业,平凡生活中的意义也总是为外在符号所加持,“我是谁”并不是由他自身可以决定的,成绩、名次、三好学生奖杯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好坏。小说里的蒙克等人显然不愿为符号所绑架,旷课逃学就是他们反抗的仪式,在他们看来迎合外界符号框定好的意义就是虚假,遵从内心向往才是真实,也就是孙坚在母校演讲时所说的“爱”,是追求和构筑爱的过程,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就是幸福,以“爱”作为答案依然过于抽象,在这里爱、真实、身份认同、心灵满足都是同义词。以其行为本身解释“爱”或许更容易理解,六个人终其一生都在逃避主流价值观框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是“让他人看的符号”,他人觉得拥有这些形式就是幸福,但却难以收服蒙克等人。
蒙克他们知道何谓虚假,因此去逃避;却不知道何谓真实,对建构真实茫然无措。真实是情绪上的快乐吗?但快乐转瞬即逝。真实是个体的成功吗?但成功也是一种为他人的描述,也是虚假。孙坚所说的“爱”只是一个暂时的称呼、一个能指符号,没有具体所指,称呼是可以更换,所谓真实既可以称为“恨”,也可以称为“怨”。所以行为个体所能把握的只有行为本身,蒙克等人所能把握的只有逃避本身,就如蒙克休学一年为与王翠翠一起高考,刺死欺骗王翠翠的政治老师,他将他“所谓”的坚守当作超越男女之情、体认自我身份的一种途径,而当他真正接近王翠翠内心只有内疚和恐惧,他无法忘记过真正建构一种“爱”。追求真实到了极致,任何话语也都是虚假,孙坚因此选择失语,只要事件一经描述,就变成完全陌生的东西,当事人也不得不在后来的叙述中认识发生的事实,被动地接受编织的意义代码和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获得了哲学层面上对真实的探讨。
小说中蒙克的老师尊重了他休学的选择,但是也不难想象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学者能够得到多少理解和认可呢?世俗价值体系紧紧包围着生活,违反意味着被边缘化,意味着个体强烈的焦虑感,蒙克等人无论走到哪个城市都被当作陌生人,始终无法融入世俗环境中。他们越逃避,“爱”越是遥不可及,只能不断拾起破碎的情感去追寻,在追寻的过程中又支离破碎。最终自我在社会上的位置还是由自我一厢情愿确认,社会标准依然稳定地设立在那里,与之抗争的结果是自我像秋千一样被迫在风中摆动,蒙克等人只能在真实和虚假之间游离。
三、在动态合力中确认身份
在现代化的视野下考察个体身份,会明白这种身份完全是由所谓时代“强者”书写的,“强者”的生活方式成为标准的生活方式,高消费、小资情调等也变成社会流行风尚。在这样弱肉强食的资本游戏里能跻身食物链顶端的只有少部分人,而占据社会多数的普通人产生普遍的挫败感,在“强者”树立的标准面前,对自我产生深深的怀疑和焦虑,像《太平,太平》中的王立臣一样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不知道如何是好。
以“爱与自由”逃避虚假,确认自我身份,则不免陷入另外一种虚假之中,从来不存在绝对的“爱”和“自我”,以个人来说身份问题似乎不太严谨,因为它的提出始终与群体文化认同相关联,古代哲学从诞生起就在思考自我主体性问题,它所讨论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而非单个的人,每个人的文化身份相对稳定。到了20世纪以后身份焦虑问题成为人文科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现代文明不断放大每个人的生活空间,个人在不同文化空间里的穿梭,生活在美国的华裔要思考自己究竟是美国人还是华人,这种身份界限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孔广钊小说里的身份焦虑更多不是生活空间变化引起的,而是由现代化带来的,表面看来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对自我有一种理想的想象,以心灵美好和充实程度为标准,而现实生活以外在的符号为标准,要事业有成、要婚姻美满,房、车就成为判断的依据,二者标准不同,但“自我”身份只能和外在的社会标准冲突吗?
回到“爱与自由”的角度,所谓真实不是先验的目标,它只存在于逃避虚假的过程中,而个体身份也是在多重力量的博弈中不断变化的。正如拉美裔的斯图亚特·霍尔所说,身份并非恒定不变的:“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的身份,再也不以统一的自我为中心了,它们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5](P208-212)社会各个方向的力量都会影响自我的身份建构,隔绝不同声音,一味地追求纯粹爱的真理往往会变成一厢情愿,我们总是要不断回应周围的环境,所以真实虚假并不是泾渭分明,二者的界限不断变动、需要不断划分,那么划分的底线又在哪里?顺应资本逻辑变为成功的商人还是守住本心不染世故,无论哪一个都不完美。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仿真文化的年代身份变得更加混乱,我们只能像肖娅一样在寻找的路途上“去而复返,返而复去”地找到模糊的答案。
身份焦虑是时代种群体性的焦虑,小说的书写本身也在时代中成为一种难题。《和我一起荡秋千》写成于2000年,探讨存在和本质,延续了先锋时期的哲学思潮,在作者自己的叙述里也将它视为对先锋文学的一种总结[6](P106-112),它得益于作者对当时先锋潮流的接受和反思。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普遍追求自由与个性,“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种哲学问题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就是个人化、市场化,承认私有制、承认完全私人的空间。南帆在《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7]里总结这一时期,认为:“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阶级革命话语的通道。”也就是说先前的阶级、革命主流话语成为先锋文学批判的立脚点,虽然它反乌托邦,但其形式本身仍是乌托邦的。
时过境迁,在个人化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流话语之后,先锋文学失掉了它的对立面,反对僵化的形式主义的前提是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形式被我们远远地抛开,先锋产生影响力的基础也就被消解了,蒙克等人在此时追求“爱”和“真实”就会显得不真实,个人的幽微之处不再有反叛的意义,那幽微之处存在的依托又在哪里呢?小说内部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社会外在符号和自我价值体认的冲突中,摆动在虚假和真实的两端。这种书写本身也成为一种症候,折射了先锋文学在当前的身份困惑,它失掉了它批判的对立面,又面临当前的市场化浪潮,不得不反思自我在文学中的位置,而“位置”本身是否存在,先锋文学能否在文化工业现实中产生意义又成为新的时代性难题。回到现实,先锋已经不再是流行话语,甚至文学也显得已经落伍了,文学本身位置已经毫无依托。个人化、市场化产生新的异化符号,个体还是被框定在符号枷锁里,自我要时刻面对异化的可能,个人欲望也是虚假的一种。先锋文学不得不像高哥、王立臣一样去面对现代化带给他们的困境。
[1]王晓明.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J]. 当代作家评论,2001(1).
[2] 戴锦华.隐形书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孔广钊.和我一起荡秋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4][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乔焕江,等. 通往世界幽微的叙述之舟——孔广钊小说的叙事艺术[J].小说林,2017(1).
[7]孔广钊.太平,太平[J].北方文学,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