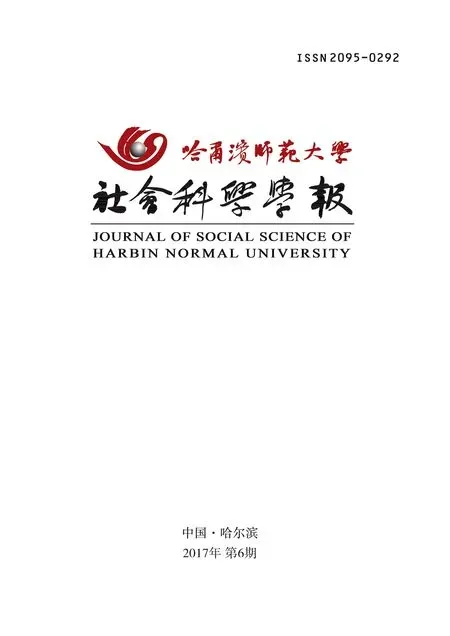从柄谷行人的解读看索绪尔的语言观
2017-02-23林佳信
林佳信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1992年)和后来的《民族—国家和语言学》*两篇文章分别收录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和《民族与美学》。,柄谷行人重新解读索绪尔的理论,企图将索绪尔解读成现代语言学的深刻批评者,从中发现语言学与民族主义互动的历史。这是一种解构主义的阅读方式,又是一种政治批评。与一般的索绪尔研究不同,柄谷行人将《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搁置一边,另选一些边缘文本(以《日内瓦大学就职演说》为代表)来进行分析,从而建构一个与“结构主义的鼻祖”这一形象相分离的新的“索绪尔”。但这种处理方式有其偏颇之处,《教程》一书和索绪尔的关系早有定论;而索绪尔的思想具有延续性,《教程》和他的其他文本有着相互观照的联系。笔者将回到索绪尔的文本中,在批判柄谷行人的思路基础上,继续探讨语言学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
一、现代语言学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的时间重合。在柄谷行人看来,以历史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学研究,充当了同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柄谷行人一般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来表示,以与一般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相区别,但在本文中不做这一区分。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意识形态。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的形成,民族国家从古老帝国的边缘脱离出来而形成*对于这个过程,柄谷行人习惯通过分析“资本—民族—国家”等三者的关系来呈现,兹不赘述。。这时,民族语言也从原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群方言俗语,转变成民族国家的官方语言(“民族语言”)。对民族国家来说,其内部是同质化的,或者是,其国民是均质性,共同体由一门共同的语言来维持。因而,在典型的意义上,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有一门民族语言。
和诸多社会科学一样,现代语言学肇始于19世纪,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代表。这门新兴学科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并梳理出欧洲各国语言演变的历史和前历史,最终创建了“印欧语系”的家族谱。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年轻时代便师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家,21岁时他写出了《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正如柄谷行人所说,这种语言学“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要对各种语言从语系上进行历史性的统合。”
“经过这种语言系统的分类,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相互缠绕的复杂历史便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实际是将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合理化的目的论的历史。并非语言学家本身做出了什么政治举动,仅仅是将语言学的认识奉为科学,就发挥了无上的政治性功能。例如,印欧语系这种说法就给反犹主义提供了‘客观的’依据。”[1](P135-137)
并不是由于文化接近或是文字相似,只是在语音系统的层面,语言学家“发现”了欧洲各国语言的某种历史演变规律,并找到了它们共同的祖先——梵语。无论是印度还是西欧各国,都有着不同的传统,或者说是异质的存在。但是“语音”成为主导因素,至于其他一切复杂因素,都要被统合在“语音”规律下。正是这种科学的语音研究,为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兴起提供某种客观依据。
正如上文所说,语言学的研究压抑了诸多复杂因素,“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相互缠绕的复杂历史”。比如,萨米尔·阿明在《欧洲中心主义》中对古希腊至今一以贯之的历史叙事质疑。他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不仅压抑了没有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就没有近代欧洲*希腊哲学曾一度传播到阿拉伯地区,由阿拉伯文明继承发展,到了中世纪后期才传回欧洲。可以说,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为后来欧洲文艺复兴保存了古希腊的遗产。这一事实,还压抑了作为其起源的古希腊是埃及的边陲岛国这一事实。历史比较语言学确定的“印欧语系”,实际上以自然科学的方式,为这种高度简化的欧洲历史叙事提供了支持。历史叙事大体就变成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西方现代化。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似乎可以追溯到那个“早熟的”希腊文明,而这个文明的存在似乎也注定了西方的现代化。其他的文明在“西方的目光下”,实际上要么变成科学研究的客体,要么变成浪漫的美学化的存在,直到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研究,才将其“文明与野蛮”的逻辑完整而深入地披露出来。在这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中,现代语言学作为“科学”出现,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
在柄谷行人看来,索绪尔以他的方式(包括数十年在学术上的“沉默”)批评着这种带来某种政治效果的语言学研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强调语音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文字作为表现工具却又“凌驾于口语形式”,“篡夺”了主要作用[2](P35)。柄谷行人认为,索绪尔无意强调语音高于文字,否定文字的重要性,而是要确认语音和文字的差别。批评当时语言学“把文字作为仅仅是记录声音的东西来看待”。这当然是一种较为激进的解读。正是从针对索绪尔关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论述开始,柄谷行人有意塑造一个新的、更具备政治性的“索绪尔”。
二、语音与文字的政治内涵
索绪尔在《教程》中严格区分文字和以语音为代表的语言,认为语言才是语言学研究的唯一对象。我们在其中能看到那些经典的表述,关于文字和语音之间的关系: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2](P35)
作为语言的主要部分,语音(“口说的词”)起着“主要的作用”,文字(“书写的词”)只是语音的代表,但却篡夺了原本属于语音的位置,成为文字的代表。这段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种理解认为文字本来应该隶属于语音,最后以其“威望”“凌驾于口语形式”,这也是《教程》的表述,总之,文字属于第二级,而语音属于第一级。第二种则仅仅认为文字和语音分属两个同级别的符号系统,彼此之间没有主要次要的依存关系。第二种理解则是柄谷行人所坚持的,可能因为《教程》中出现了“文字表现语言”“文字凌驾于口语形式”“篡夺”“僭越”这样有着感情色彩的说法,致使他放弃这些文本,选择其他文本进行分析,如下面的引文:
“语言和文字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有必要对它们作根本性的区分。只有语言才是语言学的对象。面向时间的语言学的分类只不过是因为语言被记录了下来才成为可能。这么说不是要否认文字的重要性。实际上,只有刻上了文明的某个阶段以及语言使用程度的某个阶段的印记,书面语和文字对于口头语才不是没有反作用。但混淆书面语和口头语正是早期无数幼稚错误的根源。”(《语言学绪论》)[1](P140)
柄谷行人转引的这段《语言学绪论》中的论述,仅仅强调语言和文字的“根本性的区分”以及语言学研究中混淆书面语和口语的错误。原本等级色彩较浓的“篡夺”说法变成“混淆”一说。但我们也看到,这两种解释都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文字不同于语言(语言),文字不能代表语言。
为什么索绪尔要将文字从语言学研究中剔除呢?在《教程》中,文字最开始确实是要用来表现语音的,甚至他承认“在某种情况下,文字可能延缓语言的变化”,但是,文字逐渐形成“威望”,最终替代了语音成为语言的代表,因此语言学的研究非常混乱。这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考虑的。正因为如此,从索绪尔在给他的学生梅耶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通行的[语言学]术语的绝对谬误,对它们进行改造并为揭示出一般情况下语言是何种研究对象的必要性,不断地来破坏我在历史方面的兴趣,尽管我的最大愿望不是去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语言。”[3](P28)学科建设的需要(“术语的绝对谬误”)迫使索绪尔暂时放下自己“在历史方面的兴趣”(可能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以及方言的调查),转而投入到对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也即是普通语言学——的思考。所以柄谷行人“连‘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都不是他(指索绪尔)所期望的东西”[1](P137)*柄谷行人表示:“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的身后由学生(巴利和薛施蔼)将课堂笔记编集而成的,并非索绪尔自己的意图,甚至连‘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都不是他所期望的东西。从结果来说,他的讲稿给现代语言学乃至现代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这样的野心。”的判断,有偏颇之处。
索绪尔不断地在强调“语言有一种不依赖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2](P35),他认为,“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的”,“有些很细微的语言事实是不依赖任何符号记录的帮助而被保存下来的……即使没有文字的帮助,这个发音上的细微色彩也很准确地流传下来”[2](P36),等等。所以,索绪尔构想出一条脱离文字而自由生长的语言传统。索绪尔甚至以《荷马史诗》来证明这种传统也可以支撑共同体的存在:“共同体是否一定要有文字呢?荷马的诗歌似乎可以证明情况并非如此。这些诗歌虽然是在人们不使用文字或差不多不使用文字的时代产生,它们的语言却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具有文学语言的一切特征。”[2](P237)
而文字是怎样的存在?首先,它是帝国的语言,在帝国的行政官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传达政令的工具。其次,它还是宗教或其他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拉丁文的《圣经》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它还是一些经典文本的载体,比如,贺拉斯的诗歌。可以看到,此时文字是帝国管理的工具。正因为和帝国关系的联系,文字实际上成为语言的“规范”。比起拉丁语,拉丁文更为稳定地规约着帝国境内的诸多方言俗语,尽管这些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自然,这些方言俗语原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可以说,它们原本处于索绪尔所说的“口耳相传的传统”中,现在接受了文字的规约。
民族国家的语言与传统帝国的“标准语”之间有一层微妙关系。以欧洲为例,古罗马帝国以拉丁语为“标准语”,拉丁语有文字,此外,境内各个民族还有各自的方言俗语。这些俗语一开始只有声音,没有形成文字。这些语言无不受到标准语和拉丁文的规范和影响。但丁用俗语写作《神曲》,并不是“记录”当时的口语,而是选择了意大利境内众多方言中的一种,通过翻译拉丁文的方式进行写作。换句话说,但丁利用意大利俗语的内容,模仿拉丁语(文)创造了一门新的书面语(意大利文),这种书面语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规范俗语,最后形成所谓“意大利语”。可以说,意大利语是被翻译、复刻出来的。
因此,在《教程》中“文学语言”这一概念,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还等同于“民族语言”,即“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主要是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这是一种人们通过某种默契从现存的方言中选出来作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2](P272)。索绪尔认为,文学语言(民族语言)增强了文字不该有的重要性。当一种现存的方言“被提升为正式的和共同的语言”之后,这种民族语言是在掺杂了“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也可以说是一种“吸纳”。而在《日内瓦大学就职演说》中则更为直接地用了“屠杀”的字眼:
“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证实。我们不易看清楚这种分化,是因为各种方言中的一种获取了作为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由此,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别的方言则被认为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扭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纳的方言屠杀了众多其他的方言,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日内瓦大学就职演说》)[1](P144-145)
在这种民族语言“屠杀”众多其他方言的同时,民族语言不断地明确自己的边界。这与属于语言自身的规律不相符合:“与两个方言间的情况一样,两种语言之间也没有所谓规律性的界线”,“语言在时间上并不是明确的概念,在空间上也完全是不明确的。”
三、作为意识形态的langue
在《教程》中,索绪尔用langue(语言)来区分langage(言语活动),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确定的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语言是社会的,是整体的原则;而言语活动则属于个人。他提出新的语言学的方案便是:“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她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P16)一般而言,我们对langue的理解便是语言系统,抑或是语言结构。索绪尔同时强调,这种语言本质上是符号,由能指(音响印象)和所指(概念)结合,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别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含的那么重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不必触动意义或声音,一个要素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而改变。”[2](P162)
柄谷行人则反对这样的理解,他认为“langue”应为“连边界也不确定的作为习语(idiome)的多数语言”,这些习语会因为民族语言的出现开始消亡。柄谷行人将索绪尔的思想与系统论、结构主义区别开来,但这里柄谷行人“langue”的解释依旧是没有积极性的东西,仅仅由差异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的“langue”的提出,针对的是明确边界的民族语言。当然,这种不确定边界的语音,其实与《教程》中提到的语言的“不依赖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有某种契合之处。
与柄谷行人不同,罗兰·巴特认为,正是索绪尔提出“语言结构”(langue)引发了认识论的变化:“类比性取代了进化论,模仿性取代了派生法。”[4](P128)可见,langue有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含义,有它在政治上的效果。强调共时状态的语言结构,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格格不入,这种历史主义在语言学的代表自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比如,印欧语系的建立,就有着“起源”和目的论的色彩。语言学家发现梵语这个源头,开始叙述这种语言演变的历史,这种叙事的另一面,是民族国家的起源叙事。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示意着‘根源’概念的退场”[4](P128)。
在《教程》中,索绪尔批评文字作为表现语言的手段,有着“效用、缺点和危险”,甚至他在谈及语言学家葆朴的时候,认为他并没有明确区分字母和语音,掉进了书写形式“这一陷阱”[2](P36)。事实上,语言学家无法直接接触到历史上出现的语言(语音),常常求助于表现语言的文字和字母,这种做法十分可疑。而文字作为规范,是与政治管理结合起来的,并且有明晰的边界。在现代社会,文字还是民族语言的模板。总而言之,文字属于语言的外部因素。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混淆了语言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从一开始就将政治因素纳入语言内部,也就是将外部“内面化”。这就导致一系列政治后果。
柄谷行人对索绪尔的理解,是他“引入‘共时性的体系’”,“为了粉碎历史语言学那种目的论式的进化论”,其实和巴特的结论不谋而合。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他所重新解释的“langue”作为一个没有边界只有差异的存在,以零符号的方式暴露了语言边界的存在,揭示出语言的“外在性的”东西,即政治的、经济的因素。
[1][日]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M]. 薛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
[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M].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历险[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