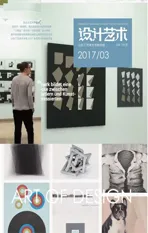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对顾恺之“传神论”的影响
2017-02-13王美琪朱平
王美琪 朱平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对顾恺之“传神论”的影响
王美琪 朱平
顾恺之的“传神论”作为中国绘画美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种绘画思想,不仅影响了人物画的发展而且对其他画科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魏晋时期,玄学风气盛行,加之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依据品行、修养、道德、精神风貌等对人物进行品评成为时代的潮流。当时的朝廷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大环境中把“人物品藻”作为人伦鉴识的重点内容。本文试从对“人物品藻”这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出发,分析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对顾恺之“传神论”思想的影响。
人物品藻;传神论;影响
1.魏晋时期“人物品藻”风尚
“人物品藻”是与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成为一种潮流,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发展变化具有时代性的特征,从对伦理道德上的鉴识逐渐转变为具有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评。“人物品藻”主要是对人物的外貌、品格、道德修养、神态等方面进行的一个评判,它带有审美性质的品评是从具有实用价值的人物品评发展而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1]孔子把人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努力看作是一种评论人格高下的标准。“里仁为美”也把仁义道德作为人格美的一个尺度。后来,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批人物品评的专家,专门负责对人物的神态进行品评。两晋时期,人物的品评又发展为对人的精神状态、内在修养、谈吐举止的评判,在人物画盛行的魏晋时期,画论不免就会受到这种品评标准的影响。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文人已无心参与政治,纷纷转向艺术方面聊以自娱。他们隐居山林过着出世的生活,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进行绘画创作。受当时玄学的影响,“人物品藻”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加之“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对人伦鉴识的要求更加严格。“人物品藻”这种社会现象也由政治上的实用性渐渐地转到了对个人品格的欣赏上。整个社会对人物品评的标准由“形”转到了“神”上,从德行、才能等转到了气质、风度上,从道德关系转到审美关系上。叶朗曾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提到:“在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的影响下,魏晋的人物品藻有一种略形而重神的倾向,像‘神姿’‘神隽’‘神怀’‘神情’‘神明’‘神气’‘神色’‘神采’‘神骏’‘神韵’‘神貌’‘神味’等概念大量出现在人物品藻之中。这种和‘神’有关的概念,并不是指人的道德学问,而是指人的个性和生活情调。人的形体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关乎神明,在人物品藻中受到重视;一部分属于形骸,在人物品藻中则被忽略。”[2]关于神明的这部分就被顾恺之发展到了艺术绘画上,发挥其所具有的审美性质对绘画进行品评。受这种“人物品藻”风尚的影响,顾恺之的绘画思想理论“传神论”出现了。这一思想理论的问世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随着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人物画的发展,“人物品藻”的社会风尚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并将其提高至审美层次,从重形发展到重神。正如汤用彤所言:“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3]这也在说明当时渐渐重神的迹象。玄学、佛学以及庄学的兴起,就使得这种对“神”的重视成为品评人物的主要着眼点,事物自身的形体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关键在“神”的表达。也正是由于这种社会风气,致使许多人为了能够成为士人名流,纷纷服用五石散。殊不知服用这种药物是很痛苦的,但它的确能够使人看起来眼睛明亮有精神,可见神态对当时人们的重要性。当然,这种对人物精神风貌的品评也突出了自我个性的表现。每个人所展现的精神风貌是迥然有异的,那么人们对待审美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从而也促使了绘画中审美观念的发展。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指出,顾恺之的‘形神论’是在‘神’变为一个审美范畴时产生的,他说“这‘神’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精神、生命,而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不同于纯理智的或单纯政治伦理意义的神,而是魏晋所追求的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的某种微妙难言的感情表现。它所强调的是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独特的‘风姿神貌’。”[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的“传神论”的提出,受到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使人们对待绘画的态度从具有鉴戒性质开始转向了带有审美性质的自觉艺术。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开始转变,由“形”到了“神”,这在后世的山水、花鸟画中也有体现。例如,后世的宗炳、王微“写山水之神”就是受到了顾的思想的影响。他们提到的这个“神”实际是指画家个人精神的一种表达,借山水之神来写自我之神。谢赫的“气韵生动”也是对“传神论”的发展,他在顾恺之的基础上又更加全面的强调了传神的内容。由此可见,“人物品藻”这一社会现象对重神的绘画美学思想的影响。
2.“人物品藻”对顾恺之“传神论”思想的影响
“人物品藻”发展到魏晋时已经从带有政治性质的品藻渐渐转变为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藻”,从顾恺之的绘画思想中可见其影响。魏晋之前的绘画作品一般是以劝诫的作用盛行,以图画中所展示的伦理道德的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上。而从顾恺之开始可以看到绘画渐渐摆脱了这种鉴戒的功效,开始涉及一些关于审美性的内容,使艺术进入到了审美自觉的阶段。这种变化与魏晋以来“人物品藻”上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人物品藻”开始从道德伦理上的政治性品评转变为带有审美性的人物品评,主要集中反映在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中。该书以精炼的语言概述了汉至东晋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化,其“人物品藻”的重点转到了对才情、风貌、容姿、气质等精神层面上来,以“神”的表现来品评人物,强调人物个性的表达。如《赞誉》篇中所记“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5],“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6]从中可以看到对太尉王衍的品评就表现在他所具有的神姿风貌上,把他的容姿看像自然中岩石那样清秀挺拔,与尘世的人不同。在赞叹支道林时说“器朗神俊”;《识鉴》篇中提到“神衿可爱”,《巧艺》篇中庾道季在评戴逵画的人像时也有提到“神明太俗”等词,都涉及到了关于“神”的概念。这其中对“神”的概念就已经进入到了审美的范畴。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也涉及了“人物品藻”与“神”的关系问题,在关于“神”应用于“人物品藻”和艺术中时,他有这样的结论:“对‘神’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评论,也就是对美或丑的评论。”[7]由此可以看到“神”的概念是当时人物品评的关键所在。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顾恺之“传神论”思想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受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顾恺之所强调的“传神”、“以形写神”中的“神”就不再仅是指人物的精神面貌,同时还带有审美意味的关乎人内在精神风貌、才情等内容。他开始强调在追寻阔达的境界时找到一种感性情感的表达,突出人物个性。如《世说新语・巧艺》中记载“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有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8]顾恺之为了突出裴公“俊朗”的神貌,特意在画完成后又在其颊上添加三毛,以此来突出裴公独具的精神风貌,让观画者看到这三毛能有“神明”的感觉,以此来展现人物的个性。从他的《论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以“神”为标准的对人物的品评的影响,如他在评《伏羲、神农》这幅画时所说“虽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属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9]认为伏羲、神农虽是神话人物,但在这幅作品中表现出了他们在神情上那种深邃幽远的感觉,的确是侯王所应有的神态和风度,是说画者把人物独具的气质风度给描绘出来了。可见,顾恺之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神”的观念应用在了绘画中,使其与艺术相连。这可谓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上的一大进步。
“人物品藻”是通过人物的外在形体去品评人物内心的个性、才情、才能等内容的,最终的关注点是在形与神的关系上。对这种形神关系的探讨离不开玄学、佛学的影响。王弼的“得意忘象”、嵇康的“形神相亲”的观点都对“人物品藻”中形神问题产生过影响。后来,顾恺之提出的“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也是“人物品藻”中对形神问题的发展。他的“以形写神”思想指出了绘画的本质在于“传神”而不在于写形,写形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传神。他在评论《东王公》这幅画作时说“如小吴神灵。居然为神灵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10]论出了画中所画的东王公像小吴神灵那样带有灵气,不像世中的人,即说画中的东王公给人的感觉是带有神气的,是因为绘画者通过对他形体的描绘把内心的“神明”部分传达出来了,把东王公独具的个性表现出来了,用“形”表现了“神”的内容。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也有涉及形神问题的地方,如“凡生人亡有所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11]指出在摹画时眼睛要专一地注视所描摹的对象,通过对外形的描绘再经过加工以达到传神的目的。如果不对照原作中的形进行摹写的话那么传神的地方就无法表现出来了。由此可见,顾恺之通过对人物摹写要法的表述指出形与神的关系,与“人物品藻”中“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12]这种表述形神关系的观点是相联系的,即认为人物的“神”高于“形”,“神”通过“形”来表现,但同时又不忽视形的作用,希望通过形来展现神的内容。
顾恺之在“传神论”思想中特别强调眼睛的作用,指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13]。通过对能够传达人物精神的眼睛的刻画来展现人物个性,认为眼睛是最能传神的地方,因而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独特的风姿神貌都可以通过眼睛传达出来。而顾恺之的这种品评标准就与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出的“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14]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刘劭在对人物进行品评时认为面貌展现的是人物的精神气质,而眼睛展现的是人物的才情、性格,认为这些才是人物本身最重要的东西。由此可见刘劭也是在强调眼睛的作用,他把“人物品藻”中对伦理道德上善恶的品评转到了通过面貌、眼睛把握人的才情、性格等方面的品评上来。这种转变是“人物品藻”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为之后“人物品藻”中重个性、重才情的风尚做了铺垫。因刘劭生活的年代早于顾恺之,因而我们可在顾恺之品评的一些画作中见其影响。如在《魏晋胜流画赞》中顾恺之认为在摹画时“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15]意思是在对眼睛的刻画上容不得一丁点儿的失误。如果不注意长短、大小、浓薄的变化就会使人物的神气改变,可见他对眼睛传神的重视。而且历史上还有顾恺之画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之说。他认为在绘画中人物的精神风貌、思维、知识修养等内容是从眼神中流露出来的,这不仅是顾恺之对作画过程中技巧、技法的要求之高,最主要的他是回归到了东晋时期“人物品藻”这种社会风尚对“神”的追求上。
“人物品藻”最初与我国古代的相法是相连的,主要是对人物的贫贱、贵富、祸福的评论,而在后世常提到的“骨法”又与相法相联系。“骨法”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中用的比较多,主要以评论人物的精神、风度等内容,在《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如《品藻》篇中提到“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16],《赞誉》篇中提到“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此人”[17],“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18]。可见“骨”字在人物的品评中的运用。顾恺之受这种条件的影响把“骨法”引入到了绘画中。他在评论魏晋时期的人物画时就多次提到“骨法”问题。如在评论《周本纪》一画时说“重叠弥纶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19]。在评论《汉本纪》一画中说“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细美”。评论《孙武》一画中说“大荀首也,骨趣甚奇”[20]。顾恺之所提到的“骨法”“天骨”“奇骨”等词都与人物的外形结构有关,从他“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出发,可以看出这些对“骨法”的表达也与人物的精神气质有关,主要涉及从骨骼形体中展现出来的人物尊卑贵贱的形,这与“人物品藻”中用“骨法”来品评人物的内容是相通的。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下,顾恺之对“骨法”问题的解释最终回归到其“传神论”的绘画思想中,并借用这种“骨法”之形来传神。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风尚不仅表现在重神、重个性、重才情上,还涉及容貌问题。与汉之前对人物仪容的品评有所不同,在汉末之前对人物仪容的品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把人物的容貌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到了魏晋时期才有所转变,对人物的品藻更多的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赋予容貌一种美的意义。而这种对容貌的美又与人物的形有关。这在《世说新语》中有专门的记载,如《容止》篇中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21]就是在说嵇康的风姿洒脱,见到他的人都对他的这种爽朗清秀的容貌发出赞叹之声。“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气”,[22]“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23]等皆是对人物容貌的秀美、俊丽的赞叹,进而展现出人物的形美。正是在这种审美性的“人物品藻”的影响下,顾恺之的绘画思想中虽然重“传神”的内容居多,认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但其实他也并不排斥“形”中对人物的姿和美的表现。如他在评《小列女》中说“然服章与众物既甚奇,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24]。认为虽然没有把人物的“神气”充分的表达出来,但其中的衣服装饰画得已经足够好了,作为女子这样的衣服装饰与她的容貌搭配在一起是可以看出其艳姿的,可见他对人物仪容以及形中美的认同。他在评《北风诗》一画时也有说“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25]这种具有美丽的形体和纤妙的仪态也是被世人所推崇的,亦可见顾恺之对形中美的肯定。从顾恺之的这些绘画思想中足以看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藻”这种社会风尚对他的影响,而他又作为自觉艺术的开端人物,其绘画思想进而影响到了中国绘画的各个领域。
3.结语
顾恺之“传神论”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也与人物品评的社会风尚有关。就如陈传席在《六朝画论研究》中论述顾恺之“传神论”产生的原因时提到了玄学作为人伦鉴识的一部分并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而导致了在品人和绘画中都开始“重神”的内容。在刘劭著的《人物志》中可见对人物“神”的重视:“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26]“物有生形,形有神情,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27]在《世说新语〈容止篇〉》中所记的曹操的故事也与人物的神态有关,可见当时的人伦鉴识之风影响是极大的。但这时期对人伦鉴识更多的是一种政教功能。到了顾恺之时期,庄子美学兴起,文人们才开始谈玄远、幽眇的事物,开始注重审美的发展,把人格美与自然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达到艺术美的统一。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表达出他对“神”的重视。轻形重神的艺术认识,使“传神论”成为重要的艺术财富。他认为眼睛是传神的关键所在,“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28]就是强调了眼睛传神的重要性,而且他画人物常常会数年不点睛。他所强调的“传神”实际传的是人物的“神”,把从外表的形态面貌到内在的气度、修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美”的东西给描绘出来,这就与当时“人物品藻”所要求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人格的美和人性的美。
“传神”成为中国画的第一要义,不仅作为绘画理论影响后世,在绘画创作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开始主要是指人物画的“传神”,发展到后来,在山水、花鸟画绘画中也开始重视“神”的表现。南齐的谢赫就受顾恺之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六法论”,但他的美学理论比顾恺之又更加全面,更加概括。其中“六法”中首屈一指的“气韵生动”就是“传神论”另一种方式的表达,实际还是要求人物画要“重神”。在《古画品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陆探微作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29]被称为一等品。其中的这个“理”就是指人的本质、人的精神、人的个性,强调的就是人物“神”的表现。可见“传神论”的产生有其理论基础,但也与魏晋时期“人物品藻”这种社会风尚有关。
注释:
[1]陈晓芬.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85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5
[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2.40
[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74
[5]刘庆华译注.世说新语[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110
[6]同[5],112
[7]同[4]
[8]同[5],188
[9]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44
[10]同[9],45
[11]同[9],67
[12]同[4],135
[13]同[9],11
[14]同[12]
[15]同[11]
[16]同[5],126
[17]同[5],116
[18]同[5],118
[19]同[9]
[20]同[10]
[21]同[5],155
[22]同[5],156
[23]同[5],157
[24]同[5],44
[25]同[24],45
[26]同[2],40
[27]同[26],227
[28]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11[29]同[28],126
1.陈晓芬.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刘庆华译注.世说新语[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
3.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4.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5.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王美琪 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朱 平 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