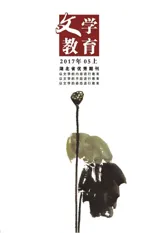钱歌川散文创作起点论
2017-02-12王芳英
王芳英
钱歌川散文创作起点论
王芳英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时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代化”进程使之失去了本土小镇特色而一跃成为兼容万象的国际大都市。1930年到1936年,是钱歌川在上海工作生活创作的六年,上海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的城市,他的文学之路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走远。上海都市现代化从思想到内容层面都影响了钱歌川地文学创作,使其创作也浸染了商业世俗气息;然而,钱歌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又有意无意地想要摆脱商业而让自己的创作提升至雅的层面。钱歌川的散文随笔兼具雅俗,市民性、意识独立之精神聚融其间,消闲中融贯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城市使得钱歌川地创作产生了灵与肉的分割,而钱歌川又以个体创作书写了城市,丰富了“城市性格”,体现城市与人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上海 现代化 钱歌川 市民性 知识分子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伴随着工商化发展,市民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接收对象,大众媒介市场繁荣。钱歌川就从这时开始闯入上海,从这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于是,上海这座城市与钱歌川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特殊的城市与人关系。
一.“鸣”在上海而“名”因北平
新文化运动文学肇始阵地《新青年》在上海创办,而高潮中心却在北京,上海只是作为当时响应运动的一个重镇,属于北京文化中心的附属之地,这就是源于上海当时文化没有深刻内涵。但运动退潮后,北京作家们又纷纷南下,到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文化中心。钱歌川与上海发生联系是在1920年代钱在日本留学期间往返其间,其短篇小说《诞生日》曾经发表在《一般》杂志上。但是他真正进入上海文学界,在上海工作创作是在1930年后,经夏丏尊介绍任中华书局编辑,负责编辑《辞海》。此时,上海已经同时成为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而钱歌川还只是一个初到上海的“海漂”一族,生活与理想最终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他与都市上海共同的记忆。
在《一般》杂志上,钱歌川发表了他“平生第一次的作品”——短篇小说《诞生日》,而由于这一次的助人投稿行为,竟然让钱歌川就着这渊源,奠定了他一生文人基础。钱歌川出版的散文集中,真正创作于其居于上海的只有《北平夜话》、《詹詹集》和《流外集》三部集子。而散文正式成为钱歌川创作体裁选择是在1932年之后,当时,他参加了一个学术团体应邀到北平开会,故而便在朋友陪同下将北平仔仔细细地游览了一番。回到上海后,写成了10篇“夜话”,以“味橄”笔名将“夜话”发表出来。因着此次的创作,让“味橄”这个笔名“一炮而红”,时有人打听“味橄”何许人也?钱歌川也因“味橄”而在上海文学界“一鸣惊人”。从这时候起,他对写随笔小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钱歌川再也没有换过文学体裁,一直坚持散文创作,出版了大量散文集,数量之多仅次于周作人,超过了林语堂和梁实秋[1]。
上海之于钱歌川是文学的起点,而他真正的文学创作却是以“北平夜话”开始,时间已经是1933年了。
二.城与人:知识分子“灵与肉”之割裂
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居于城市中的人,在文学中,“城只有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相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2]。城市与人的契合在城市中一一表现,城市在向着人的意识规划发展,而人在城市中进退都与城紧密相关。上海与北京都与开始进行散文创作的钱歌川关系密切。上海是钱歌川生活所在地,是代表现实的一方,是“柴米油盐”;而北京便是他表现知识分子身份的堡垒,是理想承载者,是“诗和远方”。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们生活在都市,是正在融合,却自身自觉地彰显着与城市的间隙,他们也就是在这样的消融与嫌隙中摇摆不定。在这样地撕扯中,他们进退两难,却坚持独立,因而,他们只能居于都市而仰望自身灵魂之独立。《北平夜话》是钱歌川第一部散文集子,也正是这个集子让他真正进入读者视野,除了身为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编辑写文章为刊物“站台”之外,恐怕还有更为深刻的原由,他要在上海都市能够动弹的自由里徘徊,以知识分子之身份独立其间。
1.身于斯缚于斯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以“海”的开阔胸怀包容着出现或者迁移至此的各种文学现象。这里既有精英文学,也有市民文学;有雅文学,也存在着俗文学;有左翼文学,又有自由主义文学,甚至有反动文学…
因着上海都市包容性和顺应市场规则,投其所好便成为当时上海大众媒介内容选择的准则之一。在1930年代的上海,国共合作已经完全破裂,上海成为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舞台,加上租界为代表殖民政治,生活在上海的市民是最靠近政治的人群;而市民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每日生活求得安稳便好,所以政治仅是他们生活的点缀,对于政治抱有极大期望和参与欲望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城市“现代化”在硬件方面正在满足都市人物质需求,而大众媒介的繁荣则是满足都市人思想的“现代化”;市民需要新媒体(当时的报刊杂志等纸质媒介都算是新媒体)来满足自己了解世界,而精英们则需要通过新媒体来满足自己对市民思想引导而成为“意见领袖”,各取所需,报刊杂志等媒介便成为联系精英与大众的纽带。读者基础意味着市场,在当上海那个以市场作为经济衡量标准的都市来说,拥有庞大的市民读者群了便是拥有庞大的市场了。都市市民每日生活便是柴米油盐,时有些“宏大”话题便是如今政治局势之“各家之言”,顺应市场规则,都市散文频频说说“闲话”,时而伴有些“国家大事”之评说,再以提升气质为目的谈谈艺术。
钱歌川几乎是和南下知识分子们同时来到上海,初到上海的他几乎是和南下作家们一样,对上海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感,他们都带着一腔热血要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却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他们留学国外,接受的知识和思想都可以算是当时属于国际的最前沿,但是回到国内,他们要面对的是尘封已久的中国文化,南下上海之后,对于上海这座“东西合璧”的都市和“亦东亦西”的上海都市文化,他们起初是坚决与之保持距离。所以初来上海并没有积极地融入上海都市文化,而是坚持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骨气”,站在高处俯视着这座都市的平平常常。但是就算是精英知识分子,还不能逃过生活的摆弄,生活永远可以将最顶端变成最卑微,这一时期的作家们都逃不过物质需求而跳脱至纯粹的精神需求。最是能说明例子的是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海居住,因着徐申如对徐志摩迎娶有夫之妇陆小曼而断绝了对徐志摩地经济支助,徐志摩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在北京上海双城之间来回兼职。到了钱歌川任职于中华书局《新中华》杂志,上海出版业已经最大程度地考虑市民需求而出版发行更迎合市民趣味的内容。《新中华》杂志地创刊,本来也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为了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一争高下。为了考虑读者群而出书,钱歌川在《詹詹集·自序》中如此道来:“《北平夜话》发表以后,识与不识,咸来问讯——姓,作者之姓也——并要我多写一点文章,我当然受宠若惊,于是更大胆地写。”“…明知他故意捧我,但他这套话说得我多么心痒,我无法制止我自己不拿去出版。”钱歌川就像是被奖励了糖果的孩子,读者的阅读兴趣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大动力,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消融”于上海都市。
2.独立思想
“士”用来专门指知识分子是从孔子那个时代开始,“孔门弟子”“儒生”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称呼[3]。知识分子其实是古代君王便于统治的工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奴化人心的武器,而北宋重文官也是对君权地进一步巩固。“士”失去了以自己知识和思想为指导的独立性,成为统治阶级的指令执行人。然而,“士”因着知识本身的独立性,即便是在君王压制下,“以天下为己任”之思想犹存,家国责任感从他们灵魂里溢出来。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社会动荡不安,中国的“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他们身上背负着社会转型时期的责任,而此时他们本身的独立性也在时代中熠熠生辉。1930年代大有作为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属于“后五四”代前一批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出生于1895年到1910年之间,他们成长在在“五四”时期,有留学经历,也接受过着传统的知识教育。[4]他们聚集上海,刨去他们为生存而“沉浮”洋场之成分,他们是抱着济世思想来到上海。于是,上海这座城市,也承载着他们的梦想与情怀。
1933年1月《新中华》创刊号文学艺术板块,钱歌川发表了《大战以来的世界文学》一文。他是一个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之思想深入心中。上海时期的钱歌川也积极参与了抗日救国活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钱基博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同一年,6月,他与叶圣陶、赵家璧等署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心中有着对家国的忧患,也有着对于文学的理想主义。
在上海这座都市里谋生,“卖文生活顶苦的事,就在把一个血肉的人,当作一架钢铁的机械来使用。每天加多少马力上去,一定叫他出多少货。人当然没有机械那样结实,做文章也没有造货物那样容易。这是一种绞尽脑汁的工作呀。但是人类是残酷的,甚至于对自己也不肯十分慈悲。”都市里,灵与肉的撕扯让城与人产生了不可复原的间隙,于是,文学创作成为知识分子们对生活无声地抗议。作为《新中华》杂志文艺版主编,钱歌川有发表言论的条件,但生活在上海都市,受着政治和市场地约束,他又需要“隐秘”地倾诉。他用“絮语”与读者闲聊,将自己心之所感心之所悟娓娓道来。
对北平,钱歌川的第一印象是“沉静的,消极的,乐天的,保守的,悠久的,消闲的,封建的。”“从来没有到过一个车站有北平车站那样肃静”;北平人是保守的,但他们却“欧化得厉害”。后来他发现,北平人会享受“闲中滋味”,因着这里到处都是古物,太闲了就会想法子消磨时间,于是,北平人会吃,听戏;在北平城内的人们,也只想着自己方寸之间的事情,这是他们封闭保守的结果。北平虽则有着帝王之气,这里的人们却就着这眼前的古朴过着,“惯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或者东郊民巷一带走动的人,他们是不知道人间有地狱的。”他们是生活在“皇城脚下”,并不懂得人间疾苦。钱歌川游览北平,“拜倒”在帝王气下,却他只是一个游客,像是岸上观鱼人,走不进北平,这其中间隙并不是短短几天游览就可以消融的。在他生活的年代,所受的教育,都尚未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之范围,但因着自己本身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他对北平的态度是既崇敬又鄙夷。他批判北平遗留下的“王室”气息,然而他却不是激进地附和上海都市的外放。对上海都市,钱歌川是客观上融不进主观上也排斥。上海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5]“租界的扩大,当然是表示它的繁荣”,“那一个知名的军阀在上海没有产业呢?”他“认为这都是租界所造成的罪恶,租界当局只顾到租界的繁荣,而不顾居民的生命”,然而,上海浮华也只是表面,一旦“世界不景气的恶浪”,“波及到繁盛的上海来”,“所谓上海繁华”,也势必成为“陈迹”,“洋场有什么可取呀?”上海泡沫经济在经济危机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生活在上海,谋生深受此“恩惠”,然在浮华面前又激起钱歌川作为知识分子之习惯性的鄙夷。一方面,北平的封建残留让它走不到该到的时代面前,依旧是“乡土中国”之传统,这让钱歌川在北平也找不到精神寄托,但是北平可以让他离开上海而去“晓得帝王的尊严”,可以是他逃离上海浮华之参照。另外一方面,上海北平作为1930年代中国的两个对比城市,而整体中国社会又都是封闭为传统,作者写北平游记或许还是有着满足上海市民对北平城的猎奇心理。
北平不是钱歌川“心之所向”,上海同样不是,两座城一个还残留之封建统治气息,一个太过于“现代化”。“城”是他的书写对象,也是他自己,“对象如何对他说来如何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6]。他“居住于同时思考着城,也思考估量着自己与城的关系”,“城才是人的城”。[7]钱歌川在城市中思考的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地冲突,还有他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拼命想要超越传统、脱离现代的独立精神。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关心最多的是知识本身,“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8]”,因而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独立精神极具理想主义,也注定了他们解答不了前辈遗留下来地对于社会和文化价值意义的困惑。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是在“仰望”自己身上的独立精神,“仰望”灵魂生出来的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三.结论
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代化”催生了市民群体,扩展大众媒介的传播范围,文艺创作也在都市化影响下必须参照与市场规则而运行。当时主要进行文艺创作的群体——“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居于城市,不得不顺应市场规则而从事创作;然而他们又是极具独立性的一代知识分子,崇尚知识独立性使得他们不甘于主动屈从于此,于是,在城市中,他们经历着“灵与肉”地割离。钱歌川从进入上海文学界开始就深受着知识分子与城市“若即若离”关系之影响,他的创作也势必逃不开这个规律。上海都市给了他文学舞台,而北平给了他站稳于文学舞台的机会,然而,这两座城市都没能真正地走进他心里。人被困在城里,想逃又逃不了,城也绝离不开人,二者就这样在相互影响中,丰富着彼此。
注释
[1]陈子善,《钱歌川和他的散文》,《书城》[J],1995年第4期。
[2]赵园,《北京:城与人》[M],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3]延涛、林声,《中国古代的“士”·导言》[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许纪霖,《另一种启蒙》[M],第82页,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周斌编,《穆时英短篇小说集·上海的狐步舞》[M],第15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M],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7]赵园,《北京:城与人》[M],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2版。
[8]许纪霖,《在诗意与残忍之间》[M],第8页,重庆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作者介绍:王芳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