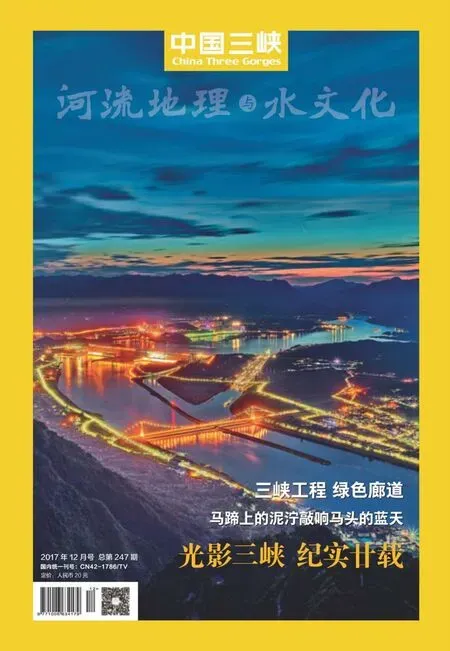游牧:流动的家园
2017-02-05安歌编辑任红
◎ 文 | 安歌 编辑 | 任红
真主以你们的家为你们的安居之所,以牲畜的皮革。
为你们的房屋,你们在启程和住定之日,都感觉其轻便。
他以绵羊毛和山羊毛,供给你们织造家具的暂时的享受。
真主以他所创造的东西做你们的遮阴,以群山做你们的隐匿处……
—— 《古兰经》
迁徙,是哈萨克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甚至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
记得小时候邻居巴依拉夫妻是哈萨克人,他们是妈妈单位的同事。平常上下班什么的,他们和单位的其他人一样,生活规律已完全和我们这些汉族人一样了。由于我们家和他们家没有隔墙,两家的生活完全在彼此眼皮底下,彼此的生活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不时会有不知从哪儿来的哈萨克族人背着袷袢或者带着包袱什么的,打开巴依拉夫妻家的大门。他们家一周起码有客人来往两三次,大多数人的样子也不像是牧民。
家里一来人,巴依拉夫妻就开始忙碌起来了,碗盏碰撞的声音,烧水的声音,人们走动的声音,互相问安道好的声音,飘荡在院子空气里的饭菜香,渐渐被歌声代替:
湖中的黄鸭,
怎么会知道野外的辽阔;
乡村的人们,
怎么会知道勇士的珍爱;
没有经过游牧生活的人,
怎么会知道美丽富饶的大地。
如果来的是牧民,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从巴依拉家的阿姨那里得到酸奶疙瘩,妈妈也许就能得到一小块儿熏肉或者马肠子。
节日或者休息日,巴依拉夫妻有时也会突然消失。他们的院子撒满阳光的寂静,因为没有巴依拉夫妻的影子,院子里的草丛和西红柿苗明亮得空虚且晃眼。我常常问妈妈,巴依拉家的阿姨去了哪里。妈妈笑着说,游牧去了。
他们回来的时候,有时也会给我手里塞几块酸奶疙瘩。在我小小的心里,游牧就是酸奶疙瘩,是酸奶疙瘩又酸又香的味道,咬开,就有草原的味道从唇间游牧开来。那时,我想,游牧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
游牧民族的牧场一般分为夏牧场和冬牧场。游牧,主要是为了给草留一个生长的时间。一年四季,游牧民族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转场中度过的。在过去,哈萨克牧民一般每年转场至少四次,最多的要转十几次。转场的时间主要视气候、水源和草场条件而定,气候、水源和草场条件好,转场的时间可能要推迟一些,反之,转场的时间可能要提前一些。
在转场季节来临之前,草原上不时有人家架起大大的锅,热气腾腾地开始做“包尔沙克”(油炸果子)。妇女们在毡房前围成一团,这些妇女们有来帮忙的邻居,也有自己家的媳妇小姑——小孩子在一旁兴奋地跑来跑去,就是安静的马儿们也仿佛闻到了就要迁徙的味道,不时地打着响鼻。寂静的哈萨克草原上,仿佛过节。
七八月正是转场季节,我跟随牧民转场,从布拉特草原到夏塔温泉,一路的风光异常美丽。
因为整个夏天没有放牧的缘故,牧场的草长得有半人高,野花盛开,不时有泉水从山上涌下来,形成小小的瀑布,晃动着阳光。夏塔河一路响在转场的路上。风过时,野花在草丛中低俯,仿佛成群的小姑娘低眉而笑。风中的花香甜美而温暖,在草原上无边无际地飘荡着,让人无端地怅惘起来。这幸福是在我们就要忘记时记起的,曾经有过的甜美、芬芳、无边无际的容纳。

哈萨克人迁徙时居住的木屋 摄影/李凯江
但转场的哈萨克人却是极辛苦的。随着卡纳提塔森家的转场队伍前行,不时地会看到草丛掩映里的木头房子,空落落地站在阳光里,不只房前屋后,连房顶都长满了禾草,开满了野花,看起来温暖而寂寞。这是秋牧场的哈萨克人住的房子。里面一般都备有一些生火的用具和简单的食物,等着主人回来时取用。这样的房子一般都不上锁,虽然说在这常常空无一人的大山里锁了也没有什么用处,但不上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样的房子随时会为任何一个遇到难处的路人提供遮挡——这或者是一个在路上的民族对在路上的人的理解和关照。一般哈萨克人在没有主人的木屋子过夜后,都会尽自己的能力,为主人补充些柴草和食物。这对长年生活在草原上和迁徙中的哈萨克人来说,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道德。
在草原上和另一家迁徙的人相遇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真正碰到了这种相遇,对转场来说,是件大麻烦事。哈尔森家就在山路上遇到了另一个转场路过夏塔谷地的羊群。羊和羊混在一起,样子又惊慌又快乐,根本不管主人急着要把它们分开的心情;牛似乎要矜持一些;马儿们也像遇到了他乡的故知,打着响鼻往别人家的马群中去叙旧。哈尔森的儿子阔列别克骑着一匹乌黑的烈性马,手拿马鞭,嘴里不停地发出吆喝声。他时而前,时而后;时而爬到山腰,又时而下到深谷。每当遇到汽车通过或与其他羊群遭遇在一起,他都要花上半个乃至一个小时,才能把惊散的羊群集中在一起或把自家的羊群和路遇人家的羊群分开。而这样的情况在迁徙时节的路上又频繁出现,仅五公里的路我们走了近五个小时,阔列别克嗓子都喊哑了,浑身像个土人一样。那个样子很像一个战争后的国王终于收回了自己的国土。
转场中,妇女们的工作也不轻松,这次转场的还有哈尔森的两个儿媳,她们在上路前就要先行备好食物,照顾孩子。在路上,她俩起得最早,先烧水做饭,紧接着就帮助丈夫拆卸毡房,整理物什,并帮忙装驼。
转场是一种长期的家庭生活,又是一种必要的生产形式,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用具都要一应俱全,大到毡房、箱柜、铁炉,小到坛罐、木柴、斧子……还有从夏牧场带回的成袋的奶疙瘩、奶酪以及羊毛、驼毛等,每次摊开摆在地上,都有一个篮球场大小。不要说每天装卸,就是将这些物品捆绑好,集中在一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们一边做着这些,还一边不时哼着歌,周围的阳光荡漾着野花的海,她们在其中安静地弄着食物,挤奶,牵着骆驼,辛苦中有一种静静的光芒。可能路上的人是快乐的,因为有路可走,要走:一路风光变化,便是你不去看,它也会走进行者的目光、身体、血液,在那身体里晃动起活动的泉,晃动出歌声。看着他们,看着这些迁徙着的哈萨克人在草原上移动的身影,我感觉,他们就是草原的血脉,牵动着安静的草原,让草原流动起来。

哈萨克牧民就是草原的血脉,牵动着安静的草原,让草原流动起来。 摄影/李凯江

新疆阿勒泰,千年牧道见证游牧民族——哈萨克族的迁徙。 摄影/视觉中国
如果用摄像机的镜头去看,让诗人来写,那衬着天空的云朵,草地的野花,和其中移动的渺小的人流,都为我们呈现着一种无言的大美。哪怕是艰辛的,这些只有在艰辛时才会有的生命状态在自然中赤裸着,这赤裸和大自然温存或者暴烈的擦痕融为一体,里面有人的努力,普通人的梦想,有的实现,也有的破灭。这一切都在行动者的动作中,在他们的身体里,也在他们的眼神中,化进了自然——在这样巨大的自然中,人再暴烈也是微不足道的,是一个个活动的小小的点,是一个个小小的温和的生命。
有时,我和小李会留在迁徙羊群马背的后面,拍他们转场远去的身影和草原上扬起的淡淡的灰尘。当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融入到阳光、草原和野花之中,我希望时间就这样停下来,时光、草原和自己,都停在这样一个定格的镜头里,不再离开。可我们还是离开了,我离开了自己的童年,离开了卡纳提加阿塔,也离开了卡纳提塔森一家……在某一天早晨,打开秋牧场毡房的布帘门,夏塔温泉的大山那么近,几乎是劈面而来,那青黛的颜色,和我们来时是一样的,但满地的草,却因一场夜晚突降的冰雹,枯黄了许多,远远的伐草人挥舞着大镰伐着半人高的牧草,灿烂的阳光在他们身上变淡,显示着离别。
想起一个深知哈萨克人迁徙之苦的汉族乡村干部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哪天,你们这些诗人对哈萨克人的这种迁徙生活写不出诗来了,哈萨克人都定居了,那么哈萨克人的生活是变好了。”但是他所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说的好,是不是哈萨克人自己所要的那种好呢?如果哈萨克人都定居了,没有了春夏秋冬牧场,没有了驭马立在自己的草场上王者似的哈萨克老牧人,没有了这种节日般的迁徙生活的味道,总之这些山里的味道全没了,那么哈萨克人还是哈萨克人吗?

毡房,哈萨克语之为称“宇”,它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坚固耐用,居住舒适,并具有防寒、防雨、防地震等特点。 摄影/东方IC

转场中的哈萨克牧民。 摄影/视觉中国
面对草原,面对在山路上艰难地聚起羊群的哈萨克人,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无论是我站着的动作,给他们帮忙的动作,和他们交谈的动作甚至和他们一起吃饭的动作,都在提醒我,此刻的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外来者,是一个注定要离开的人,是一个观看者。我的喜好与否,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干系。我所有的由他们的生活引发出来的喜怒哀乐,也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这如同我们看一朵花所激发出来的感情和花无关是一样的。
但有地方可以让人一厢情愿起来,也是放置生命的一种方式,人是需要遥远的。一种遥远的文化,一种遥远的存在,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在我们的想象之外,放牧着我们的想象。就是我站在这片哈萨克草原上,走进他们的生活里,在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也明白,我所面对的,依然是遥远。
一路的风光如果用离别的眼光去看,就带上了回忆的气味,带上了美丽的忧伤。但哈萨克族人却是用 “在”的眼光去看的。他们在转场时的艰辛和劳累让他们无暇顾及一路的美景,而这一路的美景,却因他们的在场,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