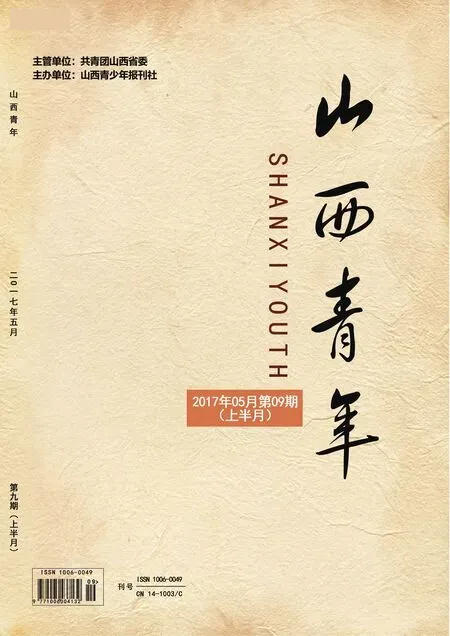《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命运悲剧分析
2017-02-01林杰
林 杰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命运悲剧分析
林 杰*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醒世恒言》是明末冯梦龙纂辑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其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史传和唐、宋小说。内容修饰润色较精,形象鲜明,结构充实完整,描写细腻,不同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市民思想感情。在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刻画了一个多情、忠贞、矢志不渝的痴女形象,她敢爱敢恨,为求真爱,两度身死,虽最终与心上人梦中相聚,却仍逃不出悲剧的轮回桎梏。周胜仙作为反叛者的形象存在于冯梦龙笔下,其对爱情的积极主动与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构成了二律背反,是为当世的统治秩序所不容,其悲剧原因与话本小说的创作来源、作者的价值观念以及文中周胜仙的人物性格特点都有关系。笔者通过文本细读和史料收集,结合先验性的阅读体验,对周胜仙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进行突围分析。
周胜仙;男权;悲剧命运;女性意识;婚恋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也是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女子,可她的一片痴情却并未使她获得梦寐以求的爱情,反而将她推入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困境中,乃至失去生命。
自周胜仙在金明池边与范二郎一见钟情,并借由卖水的两人互报家门后,周胜仙的生命悲剧便拉开了序幕。
一、生命悲剧的层次性体征表现
(一)金明池逢范二郎,归罢已是相思长
周胜仙因在金明池邂逅了范二郎,春心萌动,便对范二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追求。她机智的通过与卖水的争执,借此自报家门。范二郎也对周胜仙有情,以同样的方式答复了周胜仙,使得周胜仙“心里好欢喜”。但在封建礼法制度的制约下,男女之间没有一个可以自由交往的环境,少女心中的异样情愫无法发泄,使得她相思成疾,由“点心也不吃,饭也不吃,觉得身体不快”到了“若还不肯嫁与他,这小娘子病难医”的地步。这就是周胜仙的第一层悲剧,相思成疾,甚至危及到了性命。
(二)不教嫁与范二郎,气绝倒地身冰凉
周胜仙母亲为救其性命,央人去范家说亲,亲事既成,周胜仙的病也不药而愈,心安意乐等着周父回归嫁娶。不料,周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周胜仙在屏风后听见“一口气塞上来,气倒在地”,等周母赶来相救,“却死了”。就这样,周父将大量财物细软放入棺材,将假死状态的周胜仙几近于活埋了,并且这些财物也使得周胜仙遭遇了第三层悲剧——失去贞洁。
(三)贞操失了盗墓贼,伤心被囚无自由
盗墓贼朱真看上了随周胜仙下葬的财物,挖开坟墓,在除女孩儿身上的金银首饰时看见女孩儿身体,“淫心顿起”,将周胜仙奸了,并把周胜仙骗至家中,囚禁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
(四)噩梦却了离朱真,惨死棍棒心上魂
尽管被盗墓贼囚禁,失去自由,但是周胜仙一直在找机会逃走。终于,机会等到了,她逃了出来,找到范二郎,却在范二郎“灭!灭!”声中打死了。至此,便是周胜仙最大的悲剧也是最后的悲剧,真正的失去了生命,为情而死。
二、悲剧命运的叠加与原因洞察
周胜仙死了,我们一开始可能会唏嘘不已,觉得范二郎太冲动了,否则可以成就一段姻缘,认为周胜仙是死于一场失误。事实上,周胜仙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理学家程颖明确表示“女子之义,从于人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义,媒妁之言。男先下之,然后从焉”,而周胜仙一开始在心里思量“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这就与封建伦理纲常背道而驰,周胜仙越是坚持,她的前路便越是荆棘满地,这是最主要且最本质的原因。除此之外,这与话本小说的创作来源、作者的价值观念以及文中周胜仙的人物性格特点都有关系。
(一)传统礼教对交往方式的变态扭曲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并即将达到顶峰,而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繁荣发展,使得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儒家所推崇的“义利观”受到冲击,士农工商无不言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2]便是当时的生动写照,这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由此,在上层士人中刮起一阵振兴儒学之风,大力提倡纲常伦理,其中就以宋明理学为最。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禁欲主义,具有严苛的纲常礼教束缚。虽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天理”和“人欲”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并在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反传统的“逆流”,比如“异端之尤”李贽就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3],“食色性也”等肯定人的正常欲求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封建官吏的迫害之下,这些观点始终是作为一种“逆流”存在的,对正统思想有一定的冲击,却始终被正统思想压制,没有造成革命性颠覆性的影响。比如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与范二郎“四目相视,俱各有情”,但是却不能直接交谈,只能通过与卖水的吵架借机向对方介绍自己。并且,两人回家之后,由于礼教的束缚,无法相见,两人纷纷陷入相思之苦。这里就体现了当时男女虽然具有了一定的反叛意识,但仍旧无法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
1.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的会带上时代的烙印,且宋元小说话本的对象是广大的市民阶层,迎合市民的趣味是叙事者首要关注的。所以,在当时多种价值观念的冲击之下,市民既对婚恋自由这种顺从“人欲”的思想感到向往,同时,这些市民生活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却也无法脱离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婚恋自由,男女平等的观念。体现了一种市民真情意识和封建礼教并存的状态,并且封建礼教占主导。这就是为什么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热烈积极追求爱情的周胜仙既受到叙事者的同情,却又在同情中含有谴责,并给她设置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作者在结尾点评道“情郎情女等情痴,只为情奇事亦奇。若把无情有情比,无情翻似得便宜。”这是对周胜仙痴情的直接赞美和同情。但在这赞美和同情中,我们也可发现叙事者对周胜仙的谴责,比如在周胜仙看似对那卖水的道,实则对范二郎的暗示“你敢随我去?”,范二郎跟着去了,叙事者在点评这一处时,使用的是“惹出一场没头脑官司”。表现出了叙事者将周胜仙主动邀约看做是对范二郎的一场灾难、一种祸害。所以,在市民阶层看来,周胜仙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这是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遵从。同时,我们可以从这发现,叙事者是站在男性角度的立场上看待问题的,是一种男权主导下对女性一定范围内自主意识的认同,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比如周胜仙追求爱情给范二郎带来了灾难,就会受到了谴责。
2.周胜仙的悲剧结局是必然,与当时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首先,周胜仙第一次死去便是由于周父不同意他和范二郎的亲事,她受到父权的桎梏,无法反抗,只能是气倒在地。而从后文来看,周父在其女儿气绝身亡后,也并未感到后悔,周父作为一个冷漠的封建家长,严格按照封建制度那套来要求所有人,甚至是自己的女儿。在他心目中,女儿只是他用以和“大户人家”联姻,增长面子的工具,这种思想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其次,范二郎对周胜仙“欲大于情”,是一种“猎艳”的心理。比如范二郎初次见到周胜仙,想的是“芙蓉帐里作鸾凰,云雨此时何处觅?”直接体现出一种肉欲的追求。并且,在他眼中,周胜仙的容貌是“色色易,迷难拆,隐深闺,藏柳陌。足步金莲,腰肢一捻,嫩脸映桃红,香肌晕玉白。娇姿恨惹狂童,情态愁牵艳客”,带着一种挑逗妖媚的美,不具年轻女孩儿清纯可人的美,充满情色意味。但话本却对这种轻薄亵玩女子的行为予以暗许和赞扬,并不认为这样有何不妥,这种对女性狎昵有余尊重不足的心态就是男权社会下女性无人权的表露。在封建社会,“女子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作为男子的奴隶,一人专有的玩物,摧残自己以悦媚男子的,原来是男尊女卑的结果;习之既久,谓为固然,又变成为一切行动的原因。乃说女子的人生标准,只是柔顺贞静,无非无仪。[4]”所以,周胜仙这种主动追求爱情的行为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为世所不容,所以结局注定是悲剧。
更兼在男权社会下,女子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要求女子从一而终,死心塌地。女子对男子的牺牲奉献被认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无需付出就能得到女性的痴情眷恋,生死相从,这是男性的爱情理想。所以,在话本中,周胜仙对范二郎生死不渝,热情主动,两度死去,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其痴情让神也为之动容,最后给假三天,让周胜仙一了心愿。而与之对应的范二郎,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他的所有作为都是在周胜仙的带动之下,只需做出应承即可,甚至在周胜仙死而复生,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寻他时,他一句话不听,亲手将周胜仙打死。可即便是这样,周胜仙仍对他痴心不改,托梦在狱中与范二郎欢好,为他求情出狱,但是出狱后他竟是欢天喜地回家,最后娶妻生子。那般的无情冷漠,对爱情无所作为,和周胜仙对他付出的感情是完全不对等的,他无法回应周胜仙对爱情的执着,所以周胜仙爱情的悲剧是必然的。
(二)话本故事来源的悲剧性注定
从话本的创作来源看,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改编自廉布《清尊录》中的《大桶张氏》。《大桶张氏》讲了一个“以财雄长京师”的张家少主路经孙家,看到孙家女儿漂亮,便随口许下婚约,以玉条为信物。但是后来张家却娶了别户,孙氏女“去房内蒙被卧,俄顷即死”,下葬之后被盗墓者发棺而起,再去找张家,“曳其衣且哭且骂”,被张家以为鬼,“推仆地,立死”。并且,这个故事衍生了多个版本,有王明清的《玉条脱》,洪迈的《鄂州南市女》,中间情节或有不同,但都是以女子死亡为结局。小说是源于现实且高于现实的,当时应该是确有女子下葬之后死而复生的事发生,并被人误认为鬼打死,所以,文人以此取材进行加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改编据此,周胜仙的悲剧结尾自然会受到原型中悲剧结尾的影响。
(三)时代局限性的藩篱与突围
从编者冯梦龙来看,冯梦龙在辑录这些小说话本时,因为遗漏或是版本不齐,必然会对其进行再加工。冯梦龙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他一方面受到李贽“童心说”、汤显祖“至情说”的影响,强调文学要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比如他在《情史》中明确的表露过观点“天地若有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5]。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总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没有人能完全冲破封建思想礼教的藩篱。所以,冯梦龙既认同正统的儒家观念,也具有个性解放的思潮,他虽然质疑礼法对人感情的压制,具有文人的批判精神和自由心态,但是,人的意识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冯梦龙虽然表达了对周胜仙大胆主动追求爱情的赞美和同情,具有反传统的意识,但是仍没有摆脱男权主义下女性主动追求爱情的命运悲剧。
(四)抗争礼教过程中的妥协
从周胜仙的性格弱点来看,周胜仙有着对爱情的美好追求和反叛意识,但她不能完全走出家庭的影子和自己理性意志的笼罩。她没有《碾玉观音》中璩秀秀的坚决果断,敢于抛开一切的决心和勇气。她虽然成功的用机智赢得了范二郎的心,但是却没有坚持和守卫它的力量,在对爱情的渴望和惧父心理的双重矛盾下,她听到周父不同意她的婚姻,只能气倒身亡,甚至在她真正的死去后,她了却心愿的行为,也是在五道将军的恩准下实现的。所以,她的所有反叛都是在尊重权力的前提下实施的,没有一种决绝的,鱼死网破的态度,这也是她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封建悲剧的客观认证
在商品经济的驱动下,女子的自我意识有一定的觉醒,她们大胆主动,坚定执着的追求爱情,小说话本对这样的女性给与了赞美和同情,表达了当时人们渴望冲破封建樊笼的自由平等意识。对此,我们不能一味拔高这种反封建意识,但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责其中的男权主义、礼教纲常,要正确看待其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1]汤显祖.牡丹亭[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2][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M].中华书局,1985.
[3]李贽.焚书卷1《答邓石阳》[M].中华书局,2011.
[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书店,1984.18.
[5]冯梦龙.情史﹒龙子犹序[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林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I
A
1006-0049-(2017)09-00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