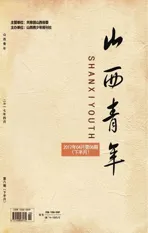“走西口”对绥远地区饮食嬗变的影响
2017-01-31刘超超孟和宝音
刘超超 孟和宝音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走西口”对绥远地区饮食嬗变的影响
刘超超*孟和宝音*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一、走西口移民的来源及其迁入地
清民时期,晋陕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旱灾,且绥远地区和晋、陕两省间虽被城墙相隔,但由于成为一国辖土,原来的城墙失去了固有的作用,同时政府也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灾荒之年开放关口,因此以农为生的最早走西口者,就是那些距离边墙非常近的口内农民,或边军、营兵,他们利用这一优势,首先在口外垦种。
山西偏关、平鲁左云,由于一代的移民大多迁往清水河、和林格尔,如光绪《清水河厅志》说:“清水一郡,所属幅员辽阔,至千余里,原系蒙古草原,所有居民并无土著,大抵皆内地各州县人民流寓,而附近之偏关、平鲁二县人尤多。”[1]大同、阳高、天镇的移民大都迁往凉城、丰镇一带。而离归化土默特地区较远的太原府、大同府、宁武府、汾州府、平定府、朔平府和忻代二州的移民则大部分迁往大青山区。若以府级政区计算,太原府最多,占山西农业移民总户数的27%,代州占26%。[2]其中太原府的阳曲、代州的崞县(今原平市)移民户数最多。
随着清政府对鄂尔多斯蒙古王公防范的降低,黑界地(在此地沿长城边外划定的南北宽50里的禁地,既不许汉人开垦也不许蒙古人放牧)放垦,鄂尔多斯地区的晋陕流动人口增多。至乾隆年间掀起了到河西垦种之高潮,神木县、靖边县、府谷县等陕西近边民众以及山西近边民众在河西地区建立许多伙盘(“民人出口定例春出秋归,暂时伙聚盘居,因以为名”[3]),神木县边外共有8甲32牌350伙盘,垦种地亩1348犋牛半。[3]至道光光绪年间流动人口更多。
河套地区距离晋陕均较远,道光以后由于黄河的改道,以及清末民国的放垦政策,使得移民增多。移民中晋、鲁、陕、直隶之人均有,晋陕之人最多,“如陕西则属榆林、府谷、神木,如山西则河曲、保德”[4]。
大量汉族移民进入绥远地区,多数从事农业。据文献记载:“在贻谷督办垦务的6年多时间内,先后放垦了绥远城八旗牧厂地3700余顷,伊克昭盟各旗土地18800余顷,乌兰察布盟各旗土地7900余顷。在清末新政的10年内,清政府在内蒙古西部新放垦土地共约87000余顷。”[5]除上述的农业移民之外,该地区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移民人口,如旅蒙商移民、军事移民、以及手工业者、教师、医药业、学徒、运输业、矿业移民。此时如此大批量的移民活动极大的促进了迁入地的汉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地的饮食。
二、绥远地区饮食变化
绥远地区是一个泛称,大致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清代,绥远地区在行政区上划分为西二盟和土默特旗。元朝蒙古建国后该地不仅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以及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因而接受一整套汉文化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仅久居汉地的蒙古人受汉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在饮食方面,蒙古人仍以肉乳为主要食物,宫廷饮食亦以羊肉为主。到明朝时期,蒙古人退到的长城以北一带,但是仍留有吃谷物蔬菜的习惯。据1498年王越写的《平贺兰山后报捷疏》写到:“又帐后石垒低墙,载有山果树株并野菜根苗,显是久居巢穴。”[6]可看出游牧名族虽以肉食为主,但食用瓜果蔬菜。
到清朝时,大批内地汉民向蒙古的涌入,并随之发生的大量牧场被开垦,农业和家庭养殖业的迅速发展,食物获取方式日趋多样化。农业区、半牧半农区蒙古人的饮食结构发上很大变化,改变了过去夏季(4-10月)以白食为主、冬季以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多以谷物为主,辅之以蔬菜、肉、蛋和乳制品。食品制作方式也逐渐丰富起来,在吸纳汉族饮食方式的同时也保留了蒙古族的特点。如:用酸奶发酵制作面食,在汤面中加入奶食品,仍用羊肉、奶茶、奶酪和奶酒等待客。察哈尔地区蒙古族日常饮食与汉族基本相同“其食物平常以莜面、小米最为普通,白面荞面次之,副食品以山药为主,至晚秋腌咸菜、烂腌菜,亦与汉人同。”[7]大规模移民之前多饮家庭酿造的牛奶酒或酸马奶。至民国年间,粮食的增产刺激了酿酒业的兴盛,“烧锅”(酒坊)已遍布内蒙古城乡。而且,饮食观念年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饮食逐渐从注重温饱、食物味道向注重饮食营养均衡转变。
三、晋陕移民对迁入地饮食嬗变的影响
随着清民时期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不仅改变了绥远地区的饮食习惯,与饮食相关的其他方面也收到了巨大的影响。如人们的食物器皿、食物种类以及营养价值观、礼俗价值观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给当地的饮食文化增加了许多不利因素。
(一)饮食嬗变的积极影响
食物器皿:游牧迁徙并在马上驰骋颠簸,其饮食器具必须经久耐用,因此蒙古牧人常用铜制品、木制品及皮制品。蒙古族最早用树皮制作碗,后来大量使用椴木碗,而且在游牧或者聚餐时,蒙古人随身携带火莲、刀、碗、筷,但是随着大量汉族移民迁到蒙古地区,现在的蒙古有两种类型的食用器具:游牧地区用具、器皿和过去差不多,多用木器;农业地区和汉族一样,多用瓷器,用木器较少。同时由紫铜、黄铜等制作的鸭咀茶壶、酒壶等器皿减少,瓷器器皿增多。另一方面,制作食物的器具也增多。
食物种类:自古以来蒙古民族食莜面或米还有玉米以及糜子做的蒙古炒米,另外也食荞麦面、小米,后来才有小麦面和大米,但不常食用。他们自古将茶作为食品,早餐吃炒米泡茶(此处的茶对了一定比例的牛奶,又称“奶茶”)。满族建立清朝后将汉族大规模移民蒙古种地,至此蒙古自己有了各种粮豆、蔬菜,因而改变了过去以牛羊肉为主的食物,农业区开始以粮食为主食,且副食多而盛产青菜,白菜、萝卜增多,还有梨、桃等果类。晋陕中部、北部擅做面食,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入,蒙古民族蒸煮炸烤类面食增多,“零食以麻花、饼子等为早晚食品等,粽子、凉糕、月饼等为时节品。”[7]汉人进入蒙古后,蒙古族的酒类由以前的两种变为三种,即奶酒(由牛马羊奶制作的酒或被发酵奶对上酒)粮食酒和外地来的酒。蒙古原来不产烟有了农业之后开始种烟,到了清末民国时期甚至使用肥沃土地大批量的种植鸦片。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常饮食逐渐从注重温饱、食物味道向注重饮食营养均衡转变;节俗饮食逐渐注重肉食向“求吉祥”“避灾祸”转变。
营养价值观:随着农业、家庭养殖业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以肉奶为主食的饮食方式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人民的日常饮食逐步走向多样化,开始以谷物制品等为主食,辅之蛋类、肉类和各种蔬菜水果。谷物作为汉族传统饮食,营养素非常丰富,是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荞麦面富含生物类黄酮、酚类、亚油酸、及钙、镁、铜、铁、锌、硒和丰富的维生素等特殊营养成分,[8]有利于降低“三高”,也有防癌、防心血管疾病、防高血压的作用,同时也是集减肥美容、强身健体于一身的保健食品。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有利于缓解口腔溃疡等由于缺乏维生素引起的疾病。蛋类食品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人们对营养、保健、药用类食品极大需求,粮食、蛋类以及蔬菜类食品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礼俗价值观:蒙古族无论是“办喜事或祭敖包,或过年时,如有待客之事,特别注重肉食”[9]。真正蒙古人的宴席除了“布乎力”(最高礼节的贵重食品,即将牛羊的后半身煮熟)[9]以外,没有其他菜肴。但是随之汉民的迁入,为求吉避祸,许多里礼俗有所变化。为了求吉祥,在冠礼中“亲友送面圈、面系、首饰、襦袴之属…亦曰圆锁。圆锁之俗,于汉满二族最为通行[10]”,此中圆锁之俗又称带锁,在晋中晋北一带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习俗,且源远流长。民国时期绥远地区“换帖之日,男家以食盒盛白米二合,红枣四两,酒一壶,羊一只,银镯,戒指,耳环,各一只,簪一件,喜饼面搭手,各二十四,兔二或四,富者家银锁一盘,单夹棉衣各一袭,饼馓各三十二,舁(共同抬东西)送女家”[10]纳彩中除了给物如换帖之外,还增加了“馒头百枚”,清初规定漠南地区聘礼为,“国初,定蒙古庶人结婚聘礼,给马五、牛五、羊五十,逾数多给者入官。”[11]这个换贴之俗与清初漠南地区聘礼之俗的差异较大,且增加许多晋陕地区象征吉祥喜庆的红枣、喜饼和饼食。
(二)饮食嬗变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汉族饮食文化中的弊端也随之而来。古代蒙族人几乎不抽烟,而山西人自古就有抽旱烟的习惯,直至上个世纪末,许多晋中、北部农民腰上别着烟杆及烟袋,因而有俗语说:“红住腰,红裤带,外穿皮袄敞开怀,腰上别着大腰带”[12]。因而抽旱烟是汉族移民的嗜好之一,蒙古地区有了农业之后开始种烟。到了咸丰年间绥远地区的人民甚至使用肥沃土地大批量的种植鸦片,“遍地皆种鸦片,人民自种自吸,即妇女儿童无不吸食”[13],人民是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主体。这里种植鸦片是由于晋陕特别是晋省内鸦片的种植、吸食泛滥,且移民的文化水平、素质比较低,因而移民为了眼前利益种植鸦片,同时“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晋旅蒙商们在商业往来的过程中将一部分“饮食文化”带到绥远地区。蒙古族自古以来喜爱用美食美酒招待亲朋好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联络感情,汉族与此不同,请客不仅是为了联络感情,有时也带着一定的政治、商业或者其他目的。如汉族的酒桌文化,其实质就是在吃饭喝酒的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达成合作或者表达合作的意向,如商业宴会、政府宴会等大型宴饮以及家长请客、员工请客等一系列小型的宴饮。旅蒙商为了在蒙地获得商业利益,也采用这种方式,如旅蒙商为了获得满蒙封建势力的支持,不仅需要请客,还需“赠送王公礼物,如上好的绸缎衣料和有佛像的哈达等,一般官吏则分送烟、酒、茶和哈达等物品”[14]。
从文中可看出,绥远地区饮食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不考虑人类社会进步所导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饮食习俗变迁,那么绥远饮食习俗这些变迁主要是在汉族移民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中既有有利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部分,也有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部分,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能够在发扬精华的过程中剔除糟粕,那么该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必将再上新台阶。
[1]边衡.晋绥关系及其蒙旗政策[J].蒙藏旬刊,1936(115).
[2]王卫东.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清王致云.神木县志·卷3[M].苏州:凤凰出版社,2007年影印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周晋熙.绥远河套治要·风俗[M].1924.
[5]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赵长海校注.王越集·卷一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7]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下[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8]郭志利.小杂粮利用价值及产业竞争力分析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05.
[9]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M].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10]绥远省政府编.绥远概况(下册)·社会概况[M].绥远省政府印,1933.
[11]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12]李彬.山西民俗大观[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13]呼和浩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六辑·鸦片在归绥[M].呼和浩特文史委,1984.
[14]邢亦尘.诚析旅蒙商止的宏观经营[J].呼和浩特: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
刘超超(1993-),女,汉族,山西吕梁人,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蒙古族历史文化;孟和宝音(1967-),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蒙古族历史文化、中国文化史。
K892.25;C
A
1006-0049-(2017)08-00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