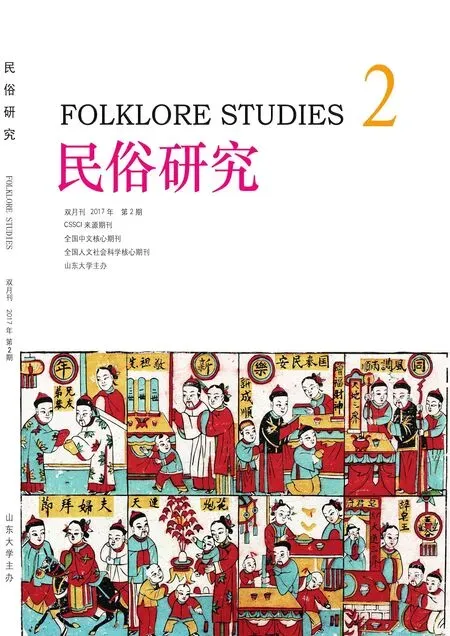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
2017-01-30张志娟
张志娟
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
张志娟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至少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和西方的。综合考虑学科意识及与中国学界之关系,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1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现有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土一线,发掘并建构出这被忽略的第二条线,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学术史的既有认知,亦可从两条线的分离与聚合看中西文化交流,观照本土民俗学的立场,还有助于考察学科内在理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西方汉学;分期
自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民俗的搜集和记录已由传教士先行一步,但直至十九世纪晚期才出现有意识的民俗学探索,即现代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民俗研究。
西人对中国民俗的研究有着与本土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发展脉络,其论著部分为中国学者所知,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直接先导或平行参照。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民俗学史*所谓“现代”乃时间层面和学术范式意义上的双重规定,即同时指向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至少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主线)和西方的。*日本的中国民俗研究大概介于二者之间:理论方法从西方来,相应术语及成果又转译到中国。西方的中国民俗研究发生较早,是欧洲民俗学对神秘东方的远征。起初,作为比较民俗学世界版图中的一块,它采集中式素材补完西式构建,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关联极为有限。但对中国了解愈深入,中国民俗的自足性和独特性愈显明,中国被称作民俗学者的“乐园”或“理想之地”。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开始关注到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对中国民俗的记述,中国歌谣运动的新发展也适时地被译介并刊载——两条线自此有了交集。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后,随着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改革、国际汉学与中国学界往来日增,依托教会大学和部分汉学机构、团体,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研究者和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以及更频繁、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双线并进,彼此交融。
长久以来,中国民俗学者只见主线,而鲜少留意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另一条重要线索: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发掘并勾勒出这被忽略的第二条线,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学术史的既有认知;亦可从两条线的分离与聚合看中西文化交流,观照本土民俗学的立场;还有助于考察学科内在理路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几乎在中国民俗研究的所有领域,西方人都走在本土学者前面,虽然他们带来的影响唯余一小部分有据可查,但即便了无确证,中国学者多年后在某些议题上的主张仍仿佛是对西方先行者遥远的回应。
综合考虑学科意识及与中国学界之关系,笔者将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确立期(1872-1892),延伸期(1893-1923)和交融期(1924-1949)。
一、确立期(1872-1892)
1872年,《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orNotesandQueriesontheFarEast)在香港创刊*一说创刊于上海,误。但《中国评论》确是长期由香港的“德臣印字馆”(“China Mail” Office)、伦敦的“Trübner&Co.”和“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td.)共同出版发行,而别发洋行的总部位于上海。该刊发行范围应该包括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天津等)、东南亚地区、欧美和澳大利亚。参见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46、49-50页。,首期便登载了对广东语词迷信的介绍,并征求中文双关语、笑话及有关鞭春牛习俗起源的解释。*“Notes and Queries”, The China Review, vol. 1, no. 1 (1872), pp. 61-62. 语词迷信(verbal superstitions)即如“棺材”叫“长寿板”、“通胜”代“通书”等。第二期,主编戴尼斯(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刊发了一则题为“中国民俗学”(Chinese Folk-lore)的启事,声称“本刊编辑正在准备一系列关于中国民俗的论文,如若通商口岸的居民能够告知目前出版物中所没有的事实,编辑将十分感激。有关日、月、年的迷信,幸运数字,咒语,巫术,新年仪式,幽灵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的材料最受欢迎。我们对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将表示诚挚的谢意。”*“Chinese Folk-lore”, The China Review, vol. 1, no. 2 (1872), p. 138. 戴尼斯,或译德尼斯、腾尼斯、谭勒等。
搜集结果戴尼斯未作说明,只是陆续登出一些双关语、谜语、谚语、歌谣、婚俗、神话、街头叫卖、民间故事及相关评介。该刊第3到5卷,他以“The Folklore of China”为题分10篇连载了自己研究中国民俗的专题论文。*N. B. Dennys, “The Folklore of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3, no.5 (1875), pp.269-284; vol.3, no.6 (1875), pp.331-342; vol.4, no.1 (1875), pp.1-9; vol.4, no.2 (1875), pp.67-84; vol.4, no.3 (1875), pp.139-152; vol.4, no.4 (1876), pp.213-227; vol.4, no.5 (1876), pp.278-293; vol.4, no.6 (1876), pp.364-375; vol.5, no.1 (1876), pp.41-55; vol.5, no.2 (1876), pp.83-91. 从第2篇起,标题改作“The Folk-lore of China”。杨堃将“Folklore一词之传入中国”追溯至“1874年”“德尼斯”开始在《中国评论》上发表论文*杨堃:《民人学与民族学》,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又见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1874年”误,实为1875年。,大概是没读到更早的启事。
考虑到“folklore”专名的应用、倡导者鲜明的学科立场及活动后续影响,本文将1872年定为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点。
西人对中国民俗的研究兴趣与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本土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戴尼斯,他熟知格林兄弟、缪勒等人的著作,认为“以比较研究为目的的民俗学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在很多国家展开,是时候将中国纳入其中了”*N. B. Dennys, “The Folklore of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 3, no. 5 (1875), p. 272.。而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后,身为学会驻香港的秘书,骆任廷(James Haldane Stewart-Lockhart,或称骆克)再次通过《中国评论》发出号召,想要倚赖欧美所有在华侨民的支持,“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各地特有的民俗资料。每份资料都别具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事实链的一环,或能从中推演出关于中国民俗的总体阐释。”为统一行动以便尽可能完备地获取相关资料,骆任廷借鉴民俗学会的出版物,列出一份分类大纲,将民俗分为四个部分,以下细分若干小类,希望在此纲要的指导下夯实基础,形成中国民俗在事实及特质归纳方面的基本架构。*J. H. Stewart-Lockhart, “Contribution to the Folk-lore of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14, no. 6 (1886), p. 352.为争取更多读者,这份公开信还被译成法语。*Shiona Airlie, Thistle and Bamboo: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 Hong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1.
骆任廷热切期望中国人也能参与搜集工作,因此特别准备了一份中文版的告示:
有民风学博士问于余曰:先生居邻中土,其国之大与物之繁固尽人皆知也,惟始则列藩,继则混一,圣贤代出,骚雅接跡,其间俗之所尚,各有异同。古今仪礼岁时,载籍亦博,等而下者,即童子歌谣、猜谜、戏术、占卜、星推与专论或旁及此等事之书,靡不备具,子其逐一举以相告乎?余即以耳目所及并载此等事之书目陈之,而博士犹以为未足。故于公余之暇,特将其原问之旨分列条目并略注其梗概,以便依样裁答。想诸君子爱我,谅毋金玉其音。泰西骆任廷谨识*J. H. Stewart-Lockhart,“Contribution to the Folk-lore of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15, no. 1 (1886), p. 39.
具体分类为:“一世故:常人故事(平民及六畜等事),豪杰事迹(如郭令公福寿之类),歌谣(如采茶竹枝词、猺歌等类),地方故事(古迹之类);二风俗:各方风俗(如婚丧祝嘏各事),岁时纪(如年节亲朋交际之类),礼仪,戏术(如童子玩弄及戏法之类);三习俗:鬼祟,巫覡(如召亡降神之类),星占,笃信吉凶(如符箓、小儿钳钏、崇祀竹木之类);四俗语:成语(如泾渭宜分、补天浴日之类),古语(如飞不高跌不伤等类),童谣,谜语,混名(如水浒传母夜叉,又鱼头参政之类)。”*J. H. Stewart-Lockhart, “Contribution to the Folk-lore of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15, no. 1 (1886), p. 39.
响应戴尼斯和骆任廷的外国侨民很多,身份遍及传教士、外交官、港府职员、学者、医师等等,国人的反馈则相对有限。《中国评论》为数不多的中国作者中,“Hung Mao-Tsz”“老广东”“毛锡九(Mo Sih Chiu)”和“Wong Fan”分别提供了双关语、习俗、迷信、谚语等方面的材料和说明。*Hung Mao-Tsz, “Chinese Puns”, The China Review, vol. 2, no. 2 (1873), p. 129. 老广东,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Animal being Transmitted to a Human Being”, The China Review, vol. 11, no. 6 (1883), pp. 399-400; “Traces of ‘La Couvade’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Review, vol. 11, no. 6 (1883), pp. 401-402. Mo Sih Chiu, “Spiritualism in Formosa”, The China Review, vol. 15, no. 5 (1887), pp. 304-305. C.M.Ricketts and Wong Fan, “Chinese Proverbial Sayings”, The China Review, vol. 20, no.6 (1893), pp.381-391.而在汉语世界,骆任廷发布告示当年,《申报》登出一篇《述豪杰事迹应泰西骆任廷问世故之一》,作者佚名且文稿不全。*《述豪杰事迹应泰西骆任廷问世故之一》,《申报》第4754号,1886年7月11日。该文实为金石学家叶昌炽所作,完本后收入《缘督庐秘乘》*叶昌炽:《述豪杰事迹应泰西骆任廷问世故》,《缘督庐秘乘》十五种之一,见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30册,巴蜀书社,2000年,第167-176页。,其内容虽近乎忠义传而非民间文学,但泰西骆任廷之影响可见一斑。香港本地的中文日报(ChangNgoiSanPo)同样表现积极,其编辑特设专栏,参照英国民俗学会之列表(骆氏中译)讨论民俗的诸多事象。这些文章后来被骆任廷译成英文发回伦敦,登在学会的《民俗》(Folklore)专刊上。*J. H. Stewart-Lockhart, “Chinese Folk-lore”, Folklore, vol. 1, no. 3 (1890), pp.359-368.骆氏还建议民俗学会在中国增设秘书,加强与地方出版业的合作,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学会提供资料支持,以服务于本国目标的实现。*“Through the local secretaries the press could be approached, and with the aid of both, it must be evident that the Society would be materially strengthened, and more capable of fulfilling the objects at home. ” Ibid., p. 359.
至于戴尼斯1876年由连载论文结集出版的大作“The Folk-lore of China, and It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N. B. Dennys, The Folk-lore of China, and It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 Hong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76.,近半个世纪后还出现在早期中国民俗学者的书桌上。茅盾自承对神话研究的兴味“是被几本英文的讲中国神话的书引起来的”,其中“经得起批评”的两本之一便是“腾尼斯”所著“内有一部分是论中国神话与传说的”《中国民俗学》。茅盾认为它“材料倒很丰富,然可惜太杂,有些地方又太简。我不能恭维这部书。”*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号。赵景深却觉得,同是应用雅科布斯的型式,“谭勒的《中国民俗学》”将民间故事分为八大类、十七式,这种先研究大类的方法比分得过于仔细、“漫无系属”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要好得多。因此收到钟敬文与杨成志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后,赵景深特意撰文向他们介绍了作为“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的“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赵景深:《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英国谭勒研究的结果》,赵景深:《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第1-11页。
遗憾的是,以上未见载任何民俗学史。*《中国评论》的研究者已论及该刊在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如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72-176、219-223页;段怀清、周俐玲编:《〈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6-119页。但他们对部分专业术语及民俗分类的理解有误,且不了解相应著述在本土的反响。
第一阶段以《中国评论》上戴尼斯的启事为起点,但同期甚至稍早的《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也发表过一些民俗学论文,如叶慈(M. T. Yates)的《祖先崇拜与风水》,Sinensis的《中国神话》,又有中国俚语、谜语、谚语之哲学及对广东节日的介绍等。*M. T. Yates, “Ancestral Worship and Fung-shu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1, no. 2 (1868), pp. 23-28; vol. 1, no. 3 (1868), pp. 37-43. F. H. Ewer, “Some Account of Festivals in Canton”, vol. 3, no. 7 (1870), pp. 185-188. Sinensis. “Chinese Mythology”, vol. 3, no. 8 (1871) - vol. 4, no. 8 (1871). A. E. Moule, “Chinese Proverbial Philosophy”, vol. 5, no. 2 (1874), pp. 72-77. 有些虽早于1872年,但未曾提出明确主张或号召,亦无学科意识,故不作起点讨论。期间还有两部影响很大的俗谚专集出版:沙修道(W. Scarborough)的《中国谚语集》(AColletionofChineseProverbs,1875)和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andCommonSayingsfromtheChinese,1888)。
此外,搜录中国民歌的先驱司登得(G. C. Stent)于1874、1878年先后推出歌谣集:《二十四颗玉珠串》(TheJadeChapletinTwenty-FourBeads:aCollectionofSongs,Ballads,etc.,fromtheChinese)和《活埋》(EntombedAlive,andOtherSongsandBallads,etc.,fromtheChinese)。他非常了解欧洲民俗学的进展,在前一本书的序言中列举了许多著名人物,继而表示翻译中国流行歌谣将不无价值——“作为人类家庭重要一员的精神状态的示例”。*“as illustrations of the mental status of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human family.” G. C. Stent, “Preface”, 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Four Beads: a Collection of Songs, Ballads, etc., from the Chinese. London: Trübner&Co., 1874, p. iv.
总的来说,这段时间西人之中国民俗研究并未与中国发生多少关系,顶多在通商口岸造成了一点影响,但影响十分有限,即如戴尼斯的大作也是四五十年后才被本土民俗学者读到。
二、延伸期(1893-1923)
第二阶段始自1893年,这一年,美国传教士菲尔德(Adele Marion Fielde,1839-1916)的《中国夜谭》*初名《中国夜谭》,1912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童话集》。Adele M. Fielde, 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 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Actors in the Romance of the Strayed Arrow. New York; London: G.P. Putnam’s Sons; Knickerbocker Press, 1893. Chinese Fairy Tales: 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12.问世,这是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更早有赫恩(Lafcadio Hearn, 1896年入日本籍后改名小泉八云)的《中国鬼故事》(Some Chinese Ghosts),但他不懂中文,故事大都译自法国汉学家的作品。Lafcadio Hearn, Some Chinese Ghosts. Boston: Roberts Brother, 1887.
菲尔德,有关文献作斐女士或斐姑娘,因病逝的未婚夫姓Chilcot,她也自称“旨先生娘”。1873年2月,斐女士被浸信会派来中国,在潮汕地区服务近15年。她在此开办“明道女学”,培养本地的女传教士和《圣经》教师;1883年出版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潮汕方言词典》(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a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创立了一个潮语的拼音体系。她写过中国亲历记两种,一是1884年在波士顿初版,后多次再版的《塔影:中国生活观察》(PagodaShadows:StudiesfromLifeinChina),1894年在伦敦和纽约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一隅——在中国人之间生活的考察》(ACornerofCathay:StudiesfromLifeamongtheChinese)。两本书名称相近,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书中不少章节关乎民俗,如婚嫁丧葬习俗、儿童游戏、奇妙的人和动物、各种各样的迷信等*Adele M. 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Studies from Life among the Chinese.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作者生平见最新整理本的中文提要,即[美]菲尔德:《中国一隅——在中国人之间生活的考察》,李国庆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部分曾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ScienceMonthly)上连载。*Adele M. Fielde, “Chinese Superstition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ol. 32(1888), pp. 796-799. “Some Chinese Mortuary Custom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ol. 33 (1888), pp. 589-596.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ol. 34 (1888), pp. 241-246. “Farm-Life in China”,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ol. 35 (1889), pp. 323-327. “The Chinese Theory of Evolution”,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ol. 36 (1890), pp. 397-400.
菲尔德声称自己“时不时在外国人从未涉足过的村庄逗留”,她对中国人生活的考察“得益于熟悉当地方言和妇女”:“我从社会各个阶层和男女双方都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所有记录都经过本人充分的观察验证。文中所涉及的题目都跟当地人讨论过,所得结论也都是为大家所接受的、真实的。”*Adele M. Fielde, “Preface”, A Corner of Cathay: Studies from Life among the Chinese. pp. vii-viii. 译文参考[美]菲尔德:《中国一隅——在中国人之间生活的考察》,第4页。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群众基础,菲尔德记录了十七年间(1873-1889)听到的、由不识字的中国人用汕头方言讲述的四十则民间故事,写成《中国夜谭》*Adele M. Fielde, “Preface to Second Edition”, Chinese Fairy Tales: 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p. vii.,并因此得到赵景深对该书民俗学价值的一点赞许。*赵景深:《费尔德的〈中国童话集〉》,赵景深:《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第85页。作者表示“其中没有任何一则曾被译成过欧洲语言,甚至所有中国书上也找不到”;“这些故事展现了在中国流传数百年的观念和风俗”,“显示了种族的特性”。*Adele M. Fielde, “Introduction”, Chinese Fairy Tales: 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pp. vii-viii.
菲尔德有着清晰的民俗学学科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她最初搜集故事只是为了获取汕头方言的口语语料,但不久发现故事如斯丰富且深刻揭示了本土人民的想法,于是后来每得到一个故事线索,就让讲述人单独复述给她听,同时自己迅速用罗马拼音记录下来,以便兼顾意义和词句的保存。*Adele M. Fielde,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Folk-Tal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8, no. 30 (1895), p. 186.
编完《中国夜谭》后,1895年,菲尔德写了一篇《中国民间故事的特质》,发表在《美国民俗研究》上。*Adele M. Fielde,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Folk-Tal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8, no. 30 (1895), pp. 185-191.文中提出,中国地广人众,历史悠久,其文化因隔绝闭锁而自成一体;民众大多没受过教育,却在生活的压力和挣扎中发展出一种高阶的与生俱来的智慧。虽然外来研究者可能遭遇种种困难:方言阻碍、各地风俗有别、难以接近民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家庭内部,女人们的居所)、东西思维差异等,但中国无疑是民俗学者的理想之地(an ideal field for the folk-lorist)。
菲尔德似乎开启了一种修辞,数十年后,翟孟生(Raymond D. Jameson)在其《比较民俗学方法论》一文中再次满怀热情地说道:“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China is the folklorists’ paradise)。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切,吸取了一切,并且什么也没有忘记。几乎没有一种信仰、一个故事或一种习俗不是仍然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某些最遥远的地方。”*R. D. Jameson, “Comparative Folklore Methodological Notes”, The Tsing Hua Weekly (English Supplement), vol. 31, no. 464 (1929), p. 20. 中译参考[美]R. D. 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田小杭、阎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菲尔德或翟孟生那样意识明确、表达直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出自异域人士之手的中国民间文学资料集大量涌现:歌谣方面以1896年韦大列(Baron Guido Vitale)《北京的歌谣》和1900年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的《孺子歌图》声名特著*Baron Guido Vitale, Chinese Folklore. Pekinese Rhymes. Peking: Pei Tang Press, 1896. Isaac Taylor Headland, 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 New York; Chicago;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0.;而故事集多达十余种,如韦大列的《中国笑话集》,戴遂良(Léon Wieger)、皮特曼(Norman Hinsdale Pitman)、亚当(Marion L. Adams)、白朗(Brian Brow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麦嘉湖(John Macgowan)、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等人的中国童话或民间故事集。*Marion L. Adams, Fairy Tales from China. London: Review of Reviews Office, 1900. Mary Hayes Davis and Chow-Leung, Chinese Fables and Folk Stories.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1908. Léon Wieger, Folk-lore Chinois Moderne. Hienhien: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catholique, 1909. Baron Guido Vitale, Chinese Merry Tal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Y. T. Woo.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9. J. Macgowan, Chinese Folk-lore Tal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10. N. H. Pitman, Chinese Fairy Storie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1910. Herbert Allen Giles, Chinese Fairy Tales. London: Gowans & Gray, Ltd.; Boston: Leroy Phillips, 1911. Richaid Wilhelm, Chinesische Märchen, Jena, 1914. Nellie N. Russell, Gleanings from Chinese Folklore. Compiled by Mary H. Porter. New York, Chicago, Toronto, London and Edinburgh: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5. N. H. Pitman, A Chinese Wonder Book.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19. E. T. C. Wer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London; Calcutta; Sydney: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22. Brian Brown, 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s: Stories of Old China. New York: Brentano’s, 1922.适逢本土民俗学运动的勃兴,韦、何二人所编歌谣集成为最早真正影响到中国学界的作品,尤其韦大列关于歌谣与“民族的诗”的说法经《歌谣》周刊发刊词引用,一举奠定了中国歌谣学两大走向之文艺一派的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歌谣征集的成果也被转译到英语世界。文仁亭(E. T. C. Werner)在《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1919年创刊于上海)上写道:“最近,北京公立高校官方报纸的编辑想到了很棒的主意,他请学者们将各自省份或地区目前流行的小调寄送给他。而学者们来自中国各地,他由此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材料。”*E. T. C. Werner, “Chinese Ditties”, The New China Review, vol. 3, no. 4 (1921), p. 259. “Werner”也音译作倭讷、文讷或威纳,这里取用其本人认可的汉文名“文仁亭”,见文氏自传封面。E.T.C.Werner, Autumn Leaves: an autobiography. Shanghai; Hongkong; Singapore: Kelly&Walsh, 1928.《北京大学日刊》从1918年5月末起,揭载刘半农编订的《歌谣选》,共出一百四十八则。*《发刊词》,《歌谣》周刊第1号,1922年12月17日。文氏认为外国读者或许感兴趣,于是翻译了其中一部分,附汉语原文并加注解,以《中国小调》为题,分五期连载于《新中国评论》,不久结集出版。*E. T. C. Werner, “Chinese Ditties”, The New China Review, vol. 3, no. 4 (1921), pp. 259-272; vol. 3, no. 5 (1921), pp. 368-375; vol. 3, no. 6(1921), pp. 442-450; vol. 4, no. 1 (1922), pp. 23-31; vol.4, no.2 (1922), pp. 106-113. E. T. C. Werner, Chinese Ditties. Tientsin: The Tientsin Press, 1922.又有中国学者迅速读到这部“文讷的《中国的俗歌》”,将它与韦大列、何德兰、平泽清七的歌谣集并提,称为四本“研究中国近代歌谣的书”。*《〈台湾的歌谣〉序》,《歌谣》周刊第9号,1923年3月11日。相应绍介转发《歌谣》周刊,为更多读者知晓,后续著录歌谣专书名目时,此书经常被提及,然则真正经眼过的人却寥寥。*如朱自清《中国近世歌谣叙录》收录了此书,却注“未详”“未见”,参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三、交融期(1924-1949)
如果说上阶段,西方和本土的中国民俗研究只是偶然交汇,那么随着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和中国化,随着国际汉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二者开始进一步融合,互相渗透,或协力共谋,或交锋对峙。
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1922)和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席卷全国。这两个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方向:“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人管理的宣传外国教义的学校了……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音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同时教师队伍中,中国人已成多数。*[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之后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校内中国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教会大学角色的变化加速了它的发展。1900年以前,所有基督教大学每年入学总人数不到200人,直到1926年,入学总人数才经常超过3500人。1936年,基督教大学生人数是10年前的两倍,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到1947年,教会大学有学生12000人,数年间,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2-20%。*任利剑:《从“布道者”到“教育家”——教会大学的角色变化及其意义》,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教会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倡导者既有对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感兴趣、以“抢救”式心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传教士,也有被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激发民俗学热情的中国学者。他们成立不同团体,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并发布研究成果,前者如北京辅仁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和《民俗学志》,后者如福建协和大学的福建文化研究会和《福建文化》。*但双方阵营都同时有中、外籍成员。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压力,部分传教士团体逐渐向中国人开放。以成立于华西协和大学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早期这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学术团体,1931年开始修改章程,不限人数,继而鼓励国人入会。随着中国会员势力的发展,杨少荃(S. C. Yang)1936年成为学会第一任中国会长。他主张扩大学会规模,寻求与更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体现更多中国性。*周蜀蓉、王梅:《华西地区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思想演变初探(1922-1950)——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中心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
西方的中国民俗研究者纷纷执教教会大学,与本土知识分子联络更密切。他们的研究由于得到中国籍师生的帮助如虎添翼;其成果、观点也以组织机构、学术刊物和课程讲演为依托,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1915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为例,在之江大学教授宗教比较研究课期间,他发动在读学生、毕业生和朋友们,为本校博物馆收集了两千多张家庭供奉的纸祃(或称“马张”)*Clarence Burton Day,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Shanghai; Hongkong; Singapore: Kelly and Walsh, 1940, p. 5.,其目的既是了解中国人的宗教背景,“也为促使中国学生欣赏他们自己的宗教遗产”。*Clarence Burton Day, “Preface”, 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p. ix.基于这些纸祃样本以及在杭州周边的田野调查,队克勋完成了一部被时人誉为“继高延、禄是遒的鸿篇钜制后,关于中国农民宗教最下苦功的归纳研究”之作。*Clarence H. Hamilton, “Review”,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2, no. 4 (1943), pp. 412-413.
一门学问,一旦走进课堂,编入学科建制,其影响力便远胜从前。教会大学的中、外籍教师通过教学和实践激起更多学生对于民俗学的兴趣。
黄石、李世瑜、李慰祖等人都出身教会学校。黄石就读广州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期间,随校长龚约翰博士(Dr. John S. Kunkle)研究宗教史,据其追忆:“他不但增加我对于宗教的知识,并且把我引入一个神奇美妙的新世界……乃是我们的远祖,靠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神话世界!”黄石的《神话研究》正是在龚氏的支持和帮助下写成。*黄石:《编后》,《神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30-231页。又如禄是遒神父的“中国迷信研究”曾在震旦大学讲授*李天纲:《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二百年》,《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辅仁大学的民族学民俗学课程引导赵卫邦、陈祥春等一批年轻学者亲近民俗研究*张志娟:《北京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民俗学志〉(1942-1948)为中心》,《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类似的例子很多。
除了作为主要受众的中国学生,也有不少西方人在教会大学修习。比如金陵大学华言科便是面向来华传教士。华言科常年邀请教会内外的名人到校演讲,内容关涉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诸问题,像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讲过“中国礼节”,Mechlin的“中国成语”,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主讲“中国人的生活与习俗”等。*“School Calendar 1922-1923,” The Linguist, 1923, pp.71-73. 转引自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吴义雄编:《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0页。又如1913年成立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1925年并入燕京大学后易名“燕京华文学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简称“华文学校”,1928年结束与燕大的合作,1930年改名“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中文名不变。,数以千计的欧美人士在此接受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1924-27年,传教士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全职教授“中国社会习俗”等课程*李孝迁:《北京华文学校述论》,《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30年代何乐益(Lewis Hodous)做过系列演讲,介绍中国文化遗产,很受听众欢迎*Lucius C. Porter, “Lewis Hudous, December 31, 1872-August 9, 1949”,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0, no. 1(1950), p.65.;罗金声(Clifford Henry Plopper)受邀主讲中国谚语*W. B. Pettus, “Preface”, Clifford H. Plopper, Chinese Proverbs: The Relationship of Friends as Brought out by the Proverbs&Economics as Seen through the Proverbs. Peking: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1932, p. 1.,翟孟生的“中国民俗学三讲”也是在这里进行的。*R. D. Jameson, Three Lectures on Chinese Folklore. Peiping, China: The San Yu Press, 1932.
教会大学之间不乏往来,一方面在于人员流动,如毕业于金陵神学院的朱维之,1929年入职福建协和大学,一度出任《福建文化》主编,抗战期间却困守孤岛,在上海沪江大学为国文系二、三年级的学生讲解“民间文学”。*《沪江书院大学部授课时间表》(卅一年秋),见《沪江大学1937-1951课表》,沪江大学档案,现藏上海市档案馆,卷号Q242-1-777。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合作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哈佛燕京学社将争取到的霍尔基金分配给六所中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100万美元,岭南大学70万,金陵大学30万,华西协和大学20万,齐鲁大学15万,福建协和大学5万。*此外还有按年发放的中国文化研究专项资助。大学得到捐款者皆为至少由三个教会合办的基督教新教大学。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75年的汉学贡献》,《文史哲》2004年第3期。这些学校纷纷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机构*根据哈佛资金筹委会1924年向霍尔遗产董事会提交的方案,哈佛燕京学社的工作重点是开展“人文科学”,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东方文明,同时训练和培养东西方各国学者,尤其年轻一代学者,以增强他们对东方文明的认识。Wallace B. Donham, “A Proposed Institute of Ori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 B. Wallace Papers, HYI Archives. 转引自樊书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比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专为此事并入的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都设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新建机构与校内已设的同类组织并行不悖,如金陵大学另有国学研究会和文学院国学研究班,但中国文化研究所又是一班人马。作为该所研究员,贝德士承担了“外人关于中国文化之研究”的题目,编出《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金陵大学秘书处编:《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南京美丰祥印书馆,1933年,第42-43页。福建协和大学受益的则是福建文化研究会(后改名中国文化研究会),该会之所以发展顺遂、成绩显著,霍尔基金的支持功不可没。会刊《福建文化》上发表了许多民俗学论文。
类似刊物还有《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和《齐鲁华西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民俗研究的文章不多,但前者登载了刘咸的《亚洲狗祖传说考》*Chungshee H. Liu, On the Dog-Ancestor Myth in Asia, Studia Serica, vol. 1 (1940-1941), pp. 85-109.和贺登崧《察哈尔省万全县的狐突神》*Willem A. Grootaers, The Hutu God of Wan-ch’üan (Chahar), Studia Serica, vol. 7 (1948), pp. 41-53.,后者有徐益棠《广西象平间傜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徐益棠:《广西象平间傜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齐鲁华西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杨汉先《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杨汉先:《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齐鲁华西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斯维至《殷代风之神话》*斯维至:《殷代风之神话》,《齐鲁华西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8年第8卷。等。
获得基金资助的学校须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研究计划、阶段性报告,接受后者监督和审查。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统筹下,各校中国文化研究协同发展,彼此最新动态的交流也更迅捷。比如燕京大学会收到《华西、福建协和大学、金陵、齐鲁大学国文学系课程纲要》*《华西、福建协和大学、金陵、齐鲁大学国文学系课程纲要》(1932年),燕京大学档案,现藏北京大学档案馆,卷号YJ1932010。、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工作近况等。*《致洪煨莲:关于中国文化研究会1939-1940年工作报告》,燕京大学档案,卷号YJ1940004。福建协和大学向哈佛燕京学社送出年度报告后,时任社长叶绥夫致林景润校长函(1935年12月6日),称赞协大的报告“好极了”,同时也对协大课程及研究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并将其他基督教大学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转给福建协和大学参考。*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中国文化研究热对于教会大学的民俗学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来它将中国民俗研究囊括在内,为后者提供了资金、人员方面的助力;可因为“中国文化”的范围过于宏阔且以经典文史为重,本就身在边缘的民俗学的地位反而更加岌岌可危。如福建文化研究会扩大为中国文化研究会之后,民俗的内容便少得可怜,再不见早期的繁荣了。
无论是个体的教学与实践,还是团体合作,这一阶段,教会大学为中西民俗研究的交流互助提供了最好的平台,而之前西方研究者们的作品此时也接连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比如戴尼斯的《中国民俗学》被发现;西人所编“中国童话集”,赵景深读到五种,并逐一写了评介文章。*赵景深:《皮特曼的中国童话集》,《童话论集》,第77-83页;《费尔德的〈中国童话集〉》,《童话论集》,第85-89页;《马旦氏的中国童话集》,《民间故事研究》,复旦书店,1928年,第31-34页;《亚当氏的中国童话集》,赵景深:《民间故事丛话》,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第1-5页;《白朗的中国童话集》,《民间故事丛话》,第7-13页。
四、互动及影响
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及双边互动远比我们曾经以为的要多,这些互动和影响应该放在国际汉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著名学者个人,且不少出于留学因缘,如冯承钧之于伯希和(Paul Pelliot),杨堃之于葛兰言,郑寿麟之于卫礼贤。但始自1920年代末,大学里陆续开设具有汉学史性质的课程,如1929年辅仁大学史学系的“西文汉学书阅读”*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1930年暨南大学的“近世域外研究中国文学情形”*《国立暨南大学一览》(1930年度),转引自李孝迁:《编校缘起》,《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页。;1931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刘半农讲“欧文所著中国学书选读”等。*《北京大学法文理学院各系课程大纲》(1931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2682期,1931年9月14日。1937年陆侃如说:“‘汉学’现在非常受人的重视,各学校都列入专门的课程,如清华大学考取留美学生时,题中常有几个关于‘汉学’的,如没有看过高本汉(Karlgren)的书,就不能考取留学。北大设有专科,对欧洲或日本的‘汉学’研究皆由专家来讲。一种学问既设了专科,内容一定很复杂,必须对它有基本的常识。”*陆侃如讲,张愍言记:《欧洲“支那学”家》,《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周刊》第244期,1937年5月10日。
于是出现索引式的汉学著作,如金陵大学贝德士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和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日人所写的汉学史也被翻译过来,如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这些都具有文献目录整理的性质,还每每夹带民俗学方面的信息:贝德士的书收入许多篇民俗学论文不说,即以《欧人之汉学研究》为例,书中介绍了马若瑟的《书经以前时代和中国神话研究》,且附录是岩井大慧所著《研究东洋史者必读的欧西书》,其中提到“德兰”(即禄是遒)的“中国迷信之研究”和“华基”(即戴遂良)的“中国的信仰及哲理之变迁”。*[日]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朱滋萃译,中法大学,1934年,第188、292-293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在沦陷区仍有一定发展,如梁绳袆《外国汉学研究概观》*梁绳袆:《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1941年第1期,1942年第2期。、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8期。、唐敬杲《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唐敬杲:《近世纪来西洋人之中国学研究》,《东方文化》1944年第1卷第2期。等。同时法、德等国的汉学家聚集北京,创办研究机构和刊物,与中国学者往来频繁。就民俗学界而言,中法汉学研究所是大家都知道的,杨堃负责其设下的民俗学组。该组在神祃、年画、照像资料之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还曾纂辑风土全志,编制民俗学分类表,并为西洋研究中国宗教信仰的巨著如禄是遒的《中国迷信之研究》和高延的《中国宗教系统》制作通检等。
作为国际汉学的一个分支,西方现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成果藉由国人对汉学的瞩目一并传播,汉学机构或刊物在中国的创设则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人事、学术上的羁绊。
本土和西方,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这两条若即若离的线索时有交集,互为映照。第二条线以及二者间的互动,此前之所以一直被忽视,主要受材料掣肘:文本散见各处,若不专门搜集便很难注意到;且外文居多,又平添了语言的关碍。但其实许多乍看孤立的事件,细细寻来却往往能找出一些牵动周边生态的蛛丝马迹。
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翟孟生的《中国民俗学三讲》为例,这本1932年由北京San Yu Press出版的书,主体内容为翟君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三场民俗学讲座的底稿。钟敬文说“此书,大概当时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理由是日本学者松村武雄三十年代前期曾编纂《中国神话传说集》,《导言》介绍西方学者的中国民俗研究时并未述及;当时住在北京的民俗学者,如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诸位,似乎都没在他们的著作中提过此书;钟敬文本人二三十年代颇留心搜罗同类著作,但对于这部书,却是1949年夏到北京后,才在东安市场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和购得的。*钟敬文:《序言》,[美]R. D. 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田小杭、阎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5页。——据其描述,该书似乎寂寂无名,影响甚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成书当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欧阳采薇作评论推介之,先是分述各篇内容——依次论及中国的“灰姑娘”、狐妻和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末了称“全书文笔流畅,隽永有趣,间复分条疏证,解释详明,每用比较方法,参证西方故事,以研究中国传说。当此盛行比较文学时代,此书亦颇矫矫不群也。……余谓此书行世,不惟西方人士研究汉学者得其裨益,即吾国有志研究古代传说之士得而读之,亦足以汇合中西之文学而欣得异闻也。”*采薇:《中国民间传说三讲》,《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6卷第6号;见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425页。燕京大学李安宅写了英文短评,称赞“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可以激发中国学生对民俗学的兴趣”*Li An-che. “Review”,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51, no. 202 (1938), p. 452.。1942年,他与林语堂多次通信,探讨有关中国灰姑娘问题,可见遗响。西方学者中,萧洛克认为翟著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胡适《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一文的译介*J. K. Shryock, “Revi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52, no. 4 (1932), pp. 399-400.;瓦萨学院的Martha W. Beckwith则指出:翟孟生的发现固然有趣,其比较却流于一般化,没有落到更具体的事件和语境上。*Martha W. Beckwith, “Review”,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47, no. 186 (1934), pp. 396-398.——可见事过留痕,虽有无数人物和文章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也有不少幸存下来,只是深埋故纸堆中,等待被发掘。
建构并书写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便要经历这般探赜钩沉、披沙沥金的漫漫求索。唯有本土与西方的发展线路都得以充分呈现,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史才会如钟敬文所说,是真正意义上“包括本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在内”*钟敬文:《序言》,[美]R.D.詹姆森:《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第14页。的民俗学史。
[责任编辑 刁统菊]
张志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