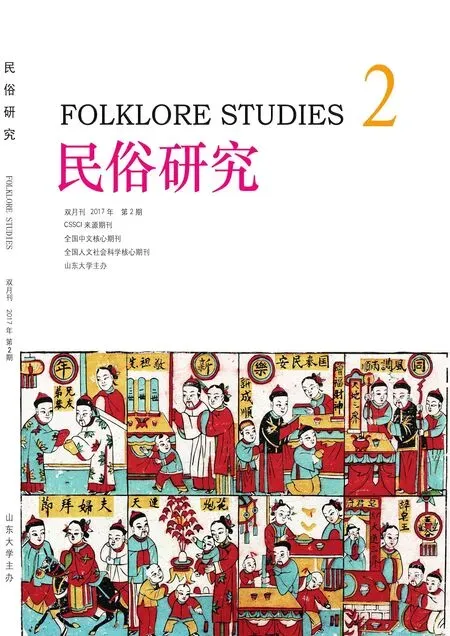十九世纪末中国语境下民俗学汉译及其学术思想史意义
2017-01-30沈梅丽
沈梅丽
十九世纪末中国语境下民俗学汉译及其学术思想史意义
沈梅丽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语境下发生过两次由英国传教士及在华英人主导的民俗学汉语译介活动,相关文献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梳理阐述。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两次民俗学汉语译介成果未能成功介入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历程,是晚清民初中国民族运动背景下民国学者转求日本明治经验的学术选择结果。
十九世纪末期;民俗学汉译;学术思想史;学术选择
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民俗学译介活动的开始一般认为是在民国初期,事实上中国语境中的民俗学汉译活动已有文献支持可上溯至十九世纪末期,即1886年《中国评论》刊载英国民俗学会秘书、时任港英政府辅政司的骆任廷“中国民风学(the Folk-lore of China)”调查征稿*[英]但尼士(N.B.Dennys)、[德]欧德理(E.J.Eitel)等主编:《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第14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35页。,征文以中英文双语系统介绍“民风学(Folk-Lore)”调查的要求、对象和方法等内容。该征文同时期载于《教务杂志》,面向在华传教士宣传进行中国民俗学调查的必要性和意义。骆任廷之前,1885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著《西学略述》列出泰西“风俗学”*[英]艾约瑟:《西学略述》,上海盈记书庄藏版,光绪戊戌八月。一门,因其译介“风俗学”时未援引英文,使得进一步研究存在困难。这两次发在中国境内的、由传教士及英国民俗学会成员所主导的与民俗学相关的译介活动,在二十世纪之交晚清文人西学史述、以及当时大学课程体系建设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和发展,如《西学通考》这类西学概述类书籍中基本都会描述作为西学的风俗学情况,光绪末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课程体系建设计划中陈独秀拟开民俗史等,理应可看成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等理论在华传播与接受的反映。但这两次民俗学汉语译介成果最终并未能成功介入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历程,1920年代现代民俗学初创期学者倾向于接受日本汉字译名“民俗学”及相关理念,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来看,是晚清民初中国民族运动背景下民国学者转求日本明治经验的学术选择结果。
一、作为西学的晚清风俗学及其理论源头考辨
晚清以译介促变法富国的西学热潮中,风俗学作为西学的一支,在晚清文人的表述中并非少见,其与化学、物理学、代数学、工学等并为格致学之属,光绪丁酉(1897年)胡兆鸾《西学通考》西学流别分类亦遵此说,将风俗学和身体学、几何原本学、代数学以及工学、师范学等归为格致学派。*(清)胡兆鸾:《西学通考》(四),光绪丁酉长沙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6月初3日《申报》登载一则售书广告,称选辑者皖江杞忧生“学贯中西,凡天文、舆地、格致、化学、政治、风俗、兵法、制造、商务及一切西学,无不该被”。*《申报》售书广告,光绪二十三年(1897)6月初3日。1902年,于宝轩从变法、介绍西学出发编辑《皇朝蓄艾文编》,其有关风俗学介绍即采录艾约瑟《西学略述》,除“以测定其或为今盛于昔,或为昔盛于今”句,《皇朝蓄艾文编》中“风俗学”条改为“以测定其今昔,盛衰异同之故”*(清)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卷七十“学术二”,上海官书局排印本,清光绪二十九年。,其他内容与《西学略述》无异。此外,《文编》收傅云龙《原学》篇首辨汉宋之学流弊所在,列出多种“致用通经”西方格致学,其中亦列“风俗学”一门。
西学体系中的风俗学观念在晚清期文人群体中有较为广泛的接受,文人接受中也出现因传统学术理念影响而产生新解读的情况。1906年,《国粹学报》第2卷第1期载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顾亭林先生学说》,文中邓实将“天下之学术”分为三种,即君学、国学和群学,他说“先生(顾亭林)之学,则为群学”,而群学乃“其功在天下”,又解释说:“群学,一曰社会学,即风俗学也。”*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顾亭林先生学说·风俗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2卷第1期。群学为1897年严复《群学肄言》翻译斯宾塞《社会学》之Sociology时初用,后来1902年章太炎翻译此书时则译为社会学。*[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邓实将群学、社会学、风俗学三个术语等同为一个概念的现象,表明现代西方学术体系入华初期或因西学文献的缺乏,晚清文人西学概念解读中缺乏一些相应的西学理性思维。
为晚清学界熟知的“风俗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术,因艾约瑟当初译介时未引原有术语、又概述简约,晚清西学译述活动也一直未曾关注到风俗学类著述,于是出现以下情况:1920年代民俗学兴起后研究者很快开始讨论folklore汉译名问题,成为译名之一的风俗学主要源于对传统风俗史观的继承,论者并没有关联到艾约瑟及其《西学略述》,作为晚清时期昭示一门学科的“风俗学”,与我国现代民俗学的确定似乎没有发生联系。艾约瑟所译介之风俗学是否即是folklore,在近年间有研究关注到,有观点认为艾约瑟《西学略述》中风俗学即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兴起的民俗学*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认为,1885年艾约瑟《西学略述》中“风俗学”为英国民俗学(folklore);彭恒礼《“民俗学”入华考——兼谈近代辞典对学科术语的强化作用》(《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泰勒是英国人类学家非民俗学家,艾氏所译“风俗学”非民俗学(folklore),而是指人类学。,然而这却是个不难被文献质疑的观点。
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48年来华传教,1880年被大清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同年艾约瑟开始着手“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汉译工作,共译成十五种西学启蒙读物。《西学略述》是艾约瑟为了向中国人概述西方诸种学术而专门编译*邹振环:《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59页。,书前编者自序的落款时间为“光绪乙酉孟冬”。艾氏将西学按“实学”分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史学、格致、经济、工艺、游览等十卷,第七卷格致学包括风俗学、天文、质学、地学、动物学等二十三种。其中,“风俗学”条内容如下:
风俗一学,乃近泰西格致家所草创。原以备征诸荒岛穷边,其间土人,更无文字书契,莫识其始者,皆可即其风俗,而较定其源流也。此学起于好游之人,或传教之士,深入荒岛,远至穷边,见有人民衣食皆异,兼之言语难通,无缘咨访,似此日记既富,要皆返国印售。格致家取而为之,互参慎选,勒部成书,皆各即其婚食丧祭讳算起居,以测定其或为今盛于昔,或为昔盛于今,如算十位盈数,人所习知,乃竟有以七或五与六为盈数者,然皆宜究其前人有以十为盈数否也。近英人鲁伯格与戴乐耳,皆喜查访此学大著声称。*[英]艾约瑟:《西学略述》,上海盈记书庄藏版,光绪戊戌八月。
艾约瑟从起源来介绍泰西“风俗学”兴于好游之人或传教士所记录的荒岛穷边之地的游记,泰西格致家们将这些游记内容按“婚、食、丧、祭、讳、算、起居”等分门别类加以研究,目的是“以测定其或为今盛于昔,或为昔盛于今”,即测定外方文化发展的进化与否,这种今昔孰“盛”的比较方法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民族志、民俗学等领域并不常用。
艾约瑟1848年来中国,至1905年病逝上海,期间数次短暂回到英国。这个时间段内英国民族志、人类学、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等各种学术先后形成体系,且理论方法日趋完善。英国民俗学会在成立之初(1878年),会刊第一期篇首民俗学会规章中将目标定为:“保存和出版民间传说(Popular Traditions)、民谣(Legendary Ballads)、地方名谚(Local Proverbial Sayings)、迷信(Superstitious)及古老习俗(Old Customs)(英国和外国),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内容。”*Folk-Lore Record (v1), Pubications of the Folk-Lore Society, 1878年。综合十九世纪英国民俗学会刊各期内容来看,比较方法并非常用,早期英国民俗学研究似乎更为注重“遗留”的实际发现,进而试图发现这种遗留文化下的社会形态。不过由于材料多来自于外方传教士搜集所得,因此在比较方法使用中存在体现基督教海外传播中存在的所谓“文明”与“野蛮”的文化优劣比较视角。
此外,从晚明耶稣会士来华直至艾约瑟时期,传教士所著英汉双语文献中与汉语“风俗”(民俗)对应英语词汇多为custom。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普遍热衷于西学输入,其西学东渐的先期准备则是风俗知识传播,如1885年《益闻录》刊载《本馆拟登西学启》中说,该启示陈述为做好性学、地学等西学译入的准备,早在此前四五年就开始在报章“首位”介绍风俗知识:“所谓西学者,以西人先得而名也,其学分门别类,不一而足……本馆存心同善,知无不言,前以地理列报章首位四五年,述俗记风,不惮繁琐。兹将性学、地学、化学、算学以及大同文制造等学逐渐译明,按期登报。”*《本馆拟登西学启》,《益闻录》第500期,1885年。艾约瑟本人著述主要是介绍中国宗教信仰、婚姻习俗以及语言等,此类著作为十九世纪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材料支持。
作为风俗概念内涵的custom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文化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及民俗学(folklore)等学术研究中都是一个重要的被关注对象。而民族志及民俗学常以方法或内容的角色被人类学所涵并,例如1930年代艾尔佛雷德·哈登《人类学史》即设“民俗学”条,哈登在讲述十九世纪欧洲神话、宗教等民俗学研究成果及影响时,描述民俗学“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现在被视为人类学中的无价之宝”*[英]艾尔佛雷德·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由此,艾约瑟的“风俗学”会不会是对泰西(包括英国)民族志、人类学及民俗学等学术普遍关注的风俗(custom)对象的一种高度概述,难以定夺。彭恒礼认为艾约瑟“风俗学”条出现的“戴乐耳”是泰勒(Edward Taylor)*戴乐耳为泰勒(Edward Taylor),据彭恒礼《“民俗学”入华考——兼谈近代辞典对学科术语的强化作用》,《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他认为泰勒是英国人类学家非民俗学家,因此提出艾氏“风俗学”不是民俗学(folklore)而是指人类学。然据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会刊可考: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初,泰勒(Taylor)名列民俗学会十二位委员名单中,1880年泰勒为民俗学会副主席。*见Flok-Lore Record,1878&1882,by Publications of The Folk-Lore Society.在当代英国学界中,也不乏见到将泰勒介绍为“致力于民俗学的人类学家”的情况。而鲁伯格,据笔者所考应为John Lubbock,1872年5月6号《人类学杂志》刊载学会组织成员中John Lubbock为主席,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初Lubbock同在该学会会员之列。可以明确的是艾约瑟所例举的两位英国“风俗学”家“鲁伯格与戴乐耳”,是身兼人类学及民俗学多学科学者身份。
综合而言,无论从“风俗学”译名词还是根据两位英人“格致学家”身份来判断艾约瑟所译“风俗学”是或不是民俗学(folklore),证据应该都不充分。虽然这样的结论未免不符合应该解决具体及实际问题的学术期待,但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到十九世纪后期人类学、民俗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情况,也可以看到在现有文献支撑下对西学身份的“风俗学”研究还需要更细致审慎的考察和判断。
二、骆任廷首译“中国民风学”及民俗学理论框架初立
1886年香港发行的英文报刊《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一篇征文内首次汉语译介folklore,征文发布者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介绍说征集目的是应英国民俗学会要求面向在华西人征求搜集中国民俗资料。这份由近代在港英国人士创办的英文期刊,主要面向英语国家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历史、政治风俗等,这样的期刊定位使得已经走进汉语的folklore及其理论未能像其他西学一样被用心推介给中国学界。这不是《中国评论》第一次刊登有关folklore文章,早在1872年第二期即推介该刊创办者、主编但尼士(N.B.Dennys)从吉日、新年、鬼神及神话等角度研究“中国民俗(学)(Chinese Folk-Lore)”系列文章。但尼士和时任港英政府辅政司的骆任廷同为英国民俗学会会员,后者同时也是英国民俗学会驻中国的负责联络人。
骆任廷号称“洋儒生”,通晓汉语,熟悉中国国情,以英国政府官员身份在香港和青岛等地长达40余年,编《中国引语手册》(A 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 1893)等书。1886年《中国评论》第15卷载骆任廷一篇征集中国民俗材料调查的重要征文,即ContributiontotheFolk-LoreofChina*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Vol.15 No.1(1886),Hongkong: China Mall Office,No.5,Wyndham Street,p37.,这篇征文介绍西方学者的中国“民风学”研究现状、发动中国“民风学”调查的目的、中国“民风学”之于比较“民风学”(comparative Folk-Lore)研究重要的学术价值等,骆任廷除从比较研究角度阐述中国民风学的研究价值外,还认为通过掌握更多中国民俗资料会有可能“成功地探索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和思想”*[英]但尼士(N.B.Dennys)、[德]欧德理(E.J.Eitel)等主编:《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第14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35页。,这种希望通过民俗途径以了解中国人心灵思想的说法,是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以民俗研究促进传教的通常之论,实际上在英国民俗学的实际研究中,外方传教士在提供民俗学研究的基础材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正是这个原因,骆任廷在《中国评论》上登出征文后,同时也给在华传教士教务信息及宣传重镇《教务杂志》写信请求传教士提供中国民俗学材料调查的支持。当时在广州的传教士皮尧士(T.W.Pearce)则从传教角度对这次“中国民风学”调查材料的征稿发表看法,他说根据自己传教经验发现:民间故事、地方传说、谚语、节日和礼仪习俗等,在向异教徒宣讲基督教义时既可提供最好的切入点,亦可提供说明材料。他认为,很少有外国人像传教士这样有便利条件获得中国民俗学知识,而民俗研习对其他群体也不会直接有用。*《教务杂志》,美国长老会宣教出版社,1886年,第362页。
骆任廷的这篇征文,陈述了发动中国民俗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后,根据英国民俗学会所公布的民俗学研究理论方法,将调查对象列为四个主题(中英文对照),即“世故(Traditional Narratives)”,“风俗(Traditional Customs)”,“习俗(Superstitions,Beliefs and Practices)”及“俗语(Folk Sayings)”,每一主题下各列细目,计共十七种。“调查主题(subject of investigation)”的中文版附随于英文征文之后,较之于英文内容,中文部分对每种细目都进一步扩展介绍,例如第一种主题“世故”下的“(b)豪杰事迹(Hero Tales)”,原英文条目下并无说明,但汉译部分增加了“如郭令公福寿之类”内容,骆任廷的解释是“中文版本目的是在中国人中流传”,据其经验显示,中国人了解民风(俗)学的目的和对象后,就会对调查主题有很大兴趣,因此,“每一细目之下,给出事例是为帮助调查”。
从我国民俗学学术史角度出发来看,这篇征文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是在汉译部分开头,骆任廷虚拟了一位英文版本中没有的、且想要了解中土俗尚的“民风学”博士与“余”的问答,博士对中土“仪礼、岁时、童子歌谣、猜谜、戏术、占卜、星推”等各类俗尚比较了解,“余”虽“居邻中土”,但并不能满足博士对此方俗尚知识的需求,因此特于公事之闲暇向“诸君子”征集中国民俗材料,其原文如下:
有民风学博士问于余曰:先生居邻中土,其国之大与物之繁,固尽人皆知也。惟始则列藩,继则混一,贤圣代出,骚雅接迹,其间俗之所尚,各有异同。古今仪礼、岁时载籍,等而下者,即童子歌谣、猜谜、戏术、占卜、星推与专论或旁及此等事之书,靡不备具,子其逐一举以相告乎?余即以耳目所及,并载此等事之书目陈之,而博士犹意味未足,故于公余之暇,特将其原问之旨,分列条目并略注其梗概,以便依样裁答,想诸君子爱我,谅毋金玉其音。
细读征文原文英汉两个版本,汉文版中的“民风学”对应英语即征文通篇主题folklore。相较于1885年艾约瑟译介“风俗学”因无对应源术语词而难定其所据的情况而言,骆任廷则将英文征文翻译成了汉语。只是这在当时未曾引起更多关注,原因之一是骆任廷两次推介folklore都是在英文报刊上,二是征文对象主要是在华传教士或相关来华人士,根本目的是英国民俗学会要求他搜集中国民俗资料以助研究,而并非向中国介绍folklore,虽然他也表明译成中文是为了“在中国人中流传”,但实际上他并未为此做更多工作。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到:对思求务实强国的晚清社会来说,西学译介基本都集中在格物学,如制造、船舶、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以及对晚清政府政体及经济等各方面有改造意义的社会学等方面。与上述西学门类相比,民俗学(folklore)因重视对社会风俗知识、风俗事象的系统化发现与总结,其富国强民、匡时救世之用往往体现在社会风治的长效上,因此虽然1886年骆任廷已汉译其入华,因缺少晚清文人群体的关注和推进,在此后三十多年里,无论是民风学还是艾约瑟的风俗学都不存在发展为一门学科的、更急迫的时代空间,具体到大学亦谈不上设立专门课程,晚清大学学科设置中出现与民俗学能沾上点边的课程,首次是1906年北京大学史学门下设立由陈独秀拟就的“民俗史”课程,然而在随后的学科终审当中即被去掉了。
三、文献审视和学术思想史双重视角下的现代民俗学发生研究
前文梳理十九世纪两次与民俗学相关的汉语译介活动,意图不仅在让一段客观历史进入民俗学学术史研究视野,更重要的是希望探求:已为晚清文人熟知几十年的作为西学的“风俗学”以及已经有较为系统理论译介的“民风学”,未能深刻影响现代民俗学的初创,似乎遭到民国学者的集体漠视,他们最早时分别取道英法及日本等国民俗学,而在folklore译名及相关学术理念上何以舍近求远选择接受日本“民俗学”理念、从而带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建构参与到国家民族运动中?有研究从民初双语辞典编纂、学术名称译介及之于学科形成角度认为,日译名词“民俗学”被学界接受并成为近代汉语学术新词,源于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年)吸收了日本《新译英和辞典》(1902年)folklore日本汉字译名。*彭恒礼:《“民俗学”入华考——兼谈近代辞典对学科术语的强化作用》,《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检阅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年),Folklore与Lore作为正式词条分列于F和L字母组,Folk-lore下译名有“野乘,古谚,俗传,历代相传之事,稗史,逸史,遗事”等七种,Lore下作为例词的Folklore则译为“民俗学”。*颜惠庆:《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第927页、第1365页。按此,则会发现前七种正式译名无一被民国学者接受,作为Lore词条下例词的“民俗学”译名却成为学者之首选,由此若将日译名词“民俗学”被民国学界接受归因于辞典传播显然尚欠说服力。
学术史往往必然体现为思想史,日译名词“民俗学”及其学术研究理念在华接受理应还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因素。如果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回到文献说话。1918年北大成立歌谣征集处征集全国歌谣,至1922年征集活动再起,《歌谣周刊》创,其《发刊词》说明歌谣征集“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其中“文艺的”目的则是希望益于“民族的诗的发展”*《发刊词》出《歌谣》第一号,民国11年。《发刊词》中引意大利卫太尔(Vitale)关于“新的‘民族的诗’”内容出自1896年Vitale《北平歌谣》选译本序。,此处可说明作为民俗学发轫的歌谣征集有着非常具体的民族性诗歌发展诉求,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是在近代民族运动驱使下进行的,讨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离不开对晚清民初时期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关注。*逮耀东:《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序,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民俗学研究重镇的早期倡导研究者多为江浙人士,当年这部分学人多怀国家民族救亡之志赴欧日留学,如果仅从日本影响或有留日求学经历来解释颜惠庆或周作人分别从欧日归国后使用日译名词“民俗学”的原因,显然会流于表象认识。
明治之前的日本和中国同是奉行儒家治世传统的东亚国家,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和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先后向近现代国家转型,有着相同的内外因素。利玛窦来华之前,十六世纪后期已有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登陆日本传教,耶稣会对日本佛教及民俗的批评最终引发日本禁教,江户时天主教转为地下密教,日本进入锁国时期,其时政治及社会秩序维护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起主导作用。*参考戚印平《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及至十九世纪,因新教依靠炮舰及通商重启日本国门,以办报、办学及译介西学等方式辅助基督教传播,传播教义的同时传教士从佛教、民俗批评展开对日本传统思想观念的深入改造,逐渐形成日本社会整体西向的气候。*参考沈梅丽《近代日本基督教传教活动与民俗关注:以明治时期横滨市为考察中心》,《非文字资料研究》(日本神奈川大学)2014.1;横滨基督教史研究会编:《图说横滨基督教文化史》,有隣堂,1992年。明治政权建立后,为了消除欧美列强强加的(半)殖民地化危机,把日本建设成为独立国家或近代国家,明治政权大力推进“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展开“文明开化”政策,部分沿袭幕末时期吸收“洋学”“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模式推进近代化进程。*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页。也正是在明治以来西化潮流下日本社会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各种变化,引起一部分日本文人对被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影响力渐失现象的重视。柳田国男在明治时期土俗研究基础上*[日]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发展小史》,莎日娜译,《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跳出该研究所持十九世纪英国民俗学“遗留”研究立场,将近代西化之前的日本民众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发挥传统文化因素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从明治坪井正五郎、铃木太胜等人的土俗研究到柳田国男为重新发挥日本传统影响力进行的乡土研究,显然对晚清民初时期国弱族危中的中国文人有十分的吸引力。具体到中国民俗学发生来说,相比较于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由歌谣征集开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有着反思传统文化文学、推动强国建设的考虑及诉求于学术研究途径的特征。晚明耶稣会士入华开始及至十九世纪新教,及至民初传教士、在华西人通过传教、西书译介及办报办学等多种途径,向中国社会全面输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期间从未间断过对中国儒家礼俗、佛道宗教及民间风俗信仰长期进行负面批评。数百年间在华西人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性宣释,最终形成晚清在华传教氛围的极度紧张。晚清新兴西学书报媒介中影响传统文化存续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于传教士,但其真正触及到晚清文人思想灵魂的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费正清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指出:
不过就像王韬、容闳一样,传教士的改革主张也只是停留在中国生活的表面,不过是通商口岸地区的产物,对广大农民和缙绅阶层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92页。
费正清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说文明对缙绅阶层“钳制”来谈晚清文人思想状况,他评价早期参与传教士办报活动的王韬“本为封建知识分子”,在西学影响下又是常对清政府提出批评的“爱国主义者”*[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王韬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改良思想则来源于与西方的接触,然而他的改良思想只表现于其政体观念中,并未触及更多关涉中国传统宗教礼俗文化,这从其著述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即便在他所服务之报刊常见关于中国风俗习惯的批评和报导,王韬仍很少会抨击本国传统风俗文化。但到了甲午战后的第三年,梁启超这位曾协助过英国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办报的革新派,1896年撰《论中国之将强》文批评传教士报刊上对中国传统风俗的恶意攻击,他慨说:“西人之侮我甚矣!”随后将西方传教士舆论传教一般形态描述为:“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使其本国之民士,若邻国之民士闻其言也。……斯道也,昔施诸印度,又施诸土耳其,今彼中愤士责士唾骂士之言,且日出而未有止也。(迭见今日《万国公报》、《时务报》)。”*《梁启超全集·论中国之将强》(1896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9页。尽管在面对传教士中国民俗批评时,梁启超指出其舆论过度和不尽合理性,但一定程度上他开始认同传教士关于儒佛道及传统风俗批评,从兴儒教角度指出,“教者,国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托命也。吾党于此世变,与闻微言,当浮海居夷。共昌明之,非通群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书,亦不可不读也。”*《梁启超全集·万木草堂小学学记》(1897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另一方面,他在认同传教士各种民俗批评的基础上,从历史因果角度将传统风俗与国弱颓势联系起来,其《中国积弱溯源论》深入探讨了中国积弱原因,并归于理想、风俗、政术、近事等因素。*《梁启超全集2·中国积弱溯源论》,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1896年在《戒缠足会叙》文中,梁氏将缠足习俗与“中国之积弱”联系起来,叹说“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提出:“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梁启超全集·戒缠足会叙》(1896年),北京出版社,1999,第80页。从强国本所需条件渐次推及“女教”改革,而改革即为以“戒缠足”为重的女性身体解放。象梁启超这样在西学视角下将传统风俗批评与国弱时乖捏合成因果论的,在晚清文人思想里是一种甚为普遍的现象,其源头来自于1840年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从国弱论出发所进行的中国社会风俗批评。*[英]李提摩太:《救世教益》,《中西教会报》1891年卷一、1892年卷一。
十九世纪末传教确实造成了传统文人思想观念的西向倾向,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中国士绅文人阶层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客观造成传教士推销的非实用西艺以外的西学如艾约瑟“风俗学”难以被接受,晚清文人更愿意通过留学途径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选择,但真正促动文人深入反思传统文化并跨出国门以期救国之道的还应是甲午战争。西方以基督教为先行者先后进入汉文化圈的日本和中国,所引发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成为近代东亚中日相同的时代课题。日本的先行一步在近代化国家建设中取得成效,并依靠甲午战争证明其西向转型的成功。这个结果一方面改变了东亚政治秩序,也客观造成晚清中国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危机,战争后的晚清文人奔赴欧美、日本学习现代知识方法的潮流中,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及其学术研究衍生成果“乡土研究”的学术建设成为这群怀抱强国理想的人士的重要选择之一,内外交困的时局则为晚清文人放下传统“复古以革新”及华夷执念取道日本的一个历史性因素。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国势颓弱、思想学术交困于东西传统与现代巷战的大背景中,日译“民俗学”相关理念入华是民国文人学术强国诉求下对有着近代发展相同背景的日本经验的选择,是寻求国家存亡之困在观念方法上的学术改造路径。反观十九世纪由传教士西学“风俗学”及民风学的汉语译介活动,因缺少了契合中国社会亟需的类似日本明治经验的政治与学术背景,以及明治以来土俗及乡土研究的发挥传统作用的思想背景等两种支撑因素,被急于寻求思想与实践方法的晚清民初学者忽视也实合于历史选择。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学发生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清末改良派”*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00页。,虽不清楚钟老这一论述是否指清末改良派从治世强国以御外辱目的之下对传统民风民俗的批评研究活动,若从理论研究视角下考虑民俗学学术发生时间,1880年代艾约瑟风俗学及骆任廷“中国民风学(the Folk-Lore of China)”理论及术语汉译*[英]但尼士(N.B.Dennys)、[德]欧德理(E.J.Eitel)等主编:《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第14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35页。的文献价值是显在的。现代民俗学发生研究中,如何评价十九世纪两次相关译介活动,不仅仅是讨论我国现代民俗学所谓发生的时间问题,更为有意义的是可以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推进现代民俗学学术史的研究深度。
[责任编辑 刁统菊]
沈梅丽,上海工艺美院工艺美术研究中心(上海2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