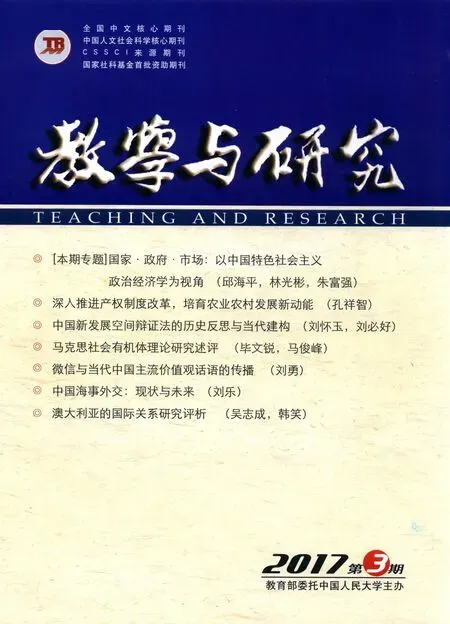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
——兼评张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7-01-30邱海平
邱海平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
——兼评张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邱海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调控
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理论特性和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只有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创建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全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于,坚持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因此,把“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作为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会得到全新的科学说明。
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不仅召开了众多学术研讨会,而且已经出版了一些教科书、专著或论文集*例如,张占斌、周跃辉著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建荣、何芹、汤一用著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宇著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李旭章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洪银兴著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王立胜、裴长洪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仍然需要逐步得到解决,其中包括研究对象问题、学科定位和性质问题、方法论问题、逻辑起点问题、主要范畴和基本理论及其逻辑关系问题、体系的完整性问题,等等。本文集中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解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前一种解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强调了这种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而在后一种解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研究对象。前一种解读是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而后一种解读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观点。这两种解读是存在差异的,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既然我们要创立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那么当然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问题,否则很有可能是南辕北辙,错失重大的理论创新的机遇。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中,是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去人们往往把这部分理论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具有一致性的。
但是仅仅这样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理解很可能是不到位的、不充分的。我们在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同或相通之处的同时,更应该充分认识它们的重大差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特性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那就是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无论哪一种解读,都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解读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可以有国别特色吗?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在许多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正像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一样,世界上也只能有一种经济学,而这个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且它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所谓“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显然,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认为只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不符合社会科学实际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同,历史上德国的经济学就与英国的经济学不同,后来美国的经济学也与英国的经济学不同,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经济学。显然,只有承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多元化,只有承认我们有可能创建一种不同于现有的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种解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仍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线性发展和延伸,而未能充分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理论特性和巨大的创新含义和价值,下面的讨论将会说明这一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解读同样存在需要研究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一个特定的国家,它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没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它是否能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一个特定国家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为对象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东西能不能称之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呢?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还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
初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如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样,是完全不合乎经济学理论常规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以来,还几乎从没有将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作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通行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
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P8)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1](P35)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而不是来源于对所有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各个国家的实际材料的归纳和总结。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很明显,这里涉及国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概括地说,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是关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但是,“社会经济形态”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另一方面更多地是通过理论抽象所得到的范畴,它的实际运动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过程中。因此,从来不存在脱离开以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总是通过对具体的国家经济运动的研究,进而得到关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理论。至少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这一点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也是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客观事实。
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首先第一条,就是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相对于已有的相关认识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或者理论创新。其创新性体现在,这个理论认识和观点非常明确和非常明显地恢复和重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
这里自然涉及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问题。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得以逐步充实和发展。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起源于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表现为一个一个国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现象,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究竟如何对待和处理具体的实践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观点的重大影响,例如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等。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虽然他们都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没有能够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从理论上来说,离开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就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完全囿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理论和规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党第二代领导邓小平同志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升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之后,我党各届领导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假如我们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同过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比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为只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这样的理解,虽然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却淡化甚至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别,从而大大削弱或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独特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的巨大创新价值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在于,这两个范畴或理论体现着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论。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体制,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从而为人们重新思考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实践依据。可以预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最终成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上的巨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因此,急需创建一种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满足这样一种需要。否则,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它无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发展和进一步延伸,而不可能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总之,从理论特性上来说,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它的最重要的理论特性在于,一方面,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决不照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原则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国家、政府、市场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创新性在于,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创造出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坚持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并通过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通过发展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以及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一样,[3](P31)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政治组织,同时也表现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一系列重要特征。把“国家”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作为逻辑起点,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创新性的集中体现,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取得理论上的突破和发展。[4]例如,在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只有把“国家”纳入进来,我们才能得到更加科学的认识。关于这一点,张宇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4章第7节和第6章中第一次进行了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5](P216-256)对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论述。
长期以来,人们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概括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样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特征。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理论概括更多地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不仅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会产生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如上所述,只有把“国家”纳入进来,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特点。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在14-16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来,于是,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直接通过关税保护、颁发经营特许证、建立殖民地、制定法律、海上争霸战争等多种方式,一方面逐渐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使大量小生产者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又完成了货币资本在资本家手中的原始积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近代工场手工业(16-18世纪),从此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以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为起点),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最适合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并最终战胜了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在16世纪中叶-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产阶级国家 “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6](P295)但是,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组织,并不具有特别的经济职能。但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发达国家进入国家干预主义时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和不景气,从而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限制,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理论,除了继续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摇摆或者混合之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得到了空前的表现。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日益要求国家代表整个社会占有生产力,但这一点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又是相冲突的。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只能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进行一定的调节和干预,这种调节和干预主要在于所谓“弥补市场失灵”,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从而这种调节和干预并不能解决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以及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等各种严重问题。
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以“国家”为前提和基础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形态的进一步形成。从此之后,中国的一切发展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并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展开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和管理主要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面的国家计划来实现的。这样一种模式不仅来源于苏联的经验和影响,而且来源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从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新和完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其核心内容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全面私有化和彻底市场化,这正是中国的改革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的本质区别。30多年的发展结果表明,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失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成绩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和巨大的优越性在于,一方面,为了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内在需要,坚持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并通过国有制占有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不断获得快速发展。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形态存在本质性的差别,进而在国家职能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张宇教授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属性”出发,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调控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国家调控的目标、国家调控的组织体系、国家调控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等,[5](P216-256)这就在理论上彻底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调控完全混同于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的流行观点,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也是该书最具理论创新性的部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实际上,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的经济形式,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必然形式和重要内容,而且是国家实现其他方面调控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从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角度出发去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做大做强做优的必然性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可能会开拓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综上所论可见,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理论特性和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只有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创建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全新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坚持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因此,把“国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作为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会得到全新的科学说明。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邱海平. 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J]. 教学与研究,2010,(3).
[5] 张 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陈翔云]
On the Subject of Study of Chines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Also Comment on thePoliticalEconomics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by Zhang Yu
Qiu Ha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ate; regulation of socialist states
Only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we fully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innovation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is to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whole state, and to develop the economy with a variety of ownership, the market economy and soci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state” into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major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newly and scientifically explained.
国家·政府·市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重要论述,而正确处理好国家、政府、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为此本刊特推出专题讨论。邱海平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坚持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并通过国家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因此,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林光彬教授重新阐释了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为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朱富强副教授则基于规模经济与技术差距的分析,讨论了市场开放与保护的限度,从而为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顺序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