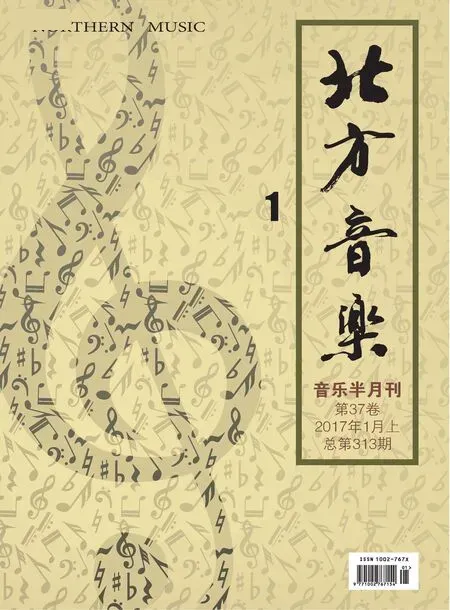从《吕氏春秋》看先秦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2017-01-29张川
张 川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从《吕氏春秋》看先秦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张 川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吕氏春秋》是先秦文献中保存音乐资料最为丰富和完整的一部著作,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八篇,除此之外,《十二纪》每纪之首篇等篇章中也涉及到对音乐的论述。本文力从《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相关部分出发,探索先秦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内在关联。
《吕氏春秋》;先秦时期;音乐与政治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此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主要的观点即主张仁政为主、刑罚为辅,主张无为,反对君主专制,以民为本,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1]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吕氏春秋》是先秦文献中保存音乐资料最为丰富和完整的一部著作,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等八篇,除此之外,《十二纪》每纪之首篇等篇章中也涉及到对音乐的论述。笔者认为不能孤立的去看《吕氏春秋》中的音乐部分,而是应将《吕氏春秋》作为一个整体,从而折射出先秦时期音乐与政治的内在关联。
一、《吕氏春秋》与其他学派的音乐思想
(一)《吕氏春秋》之前的先秦诸音乐理论
先秦诸子的音乐理论,主要有儒、道、墨三派。
儒家主张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不提倡去除欲望,只认为应该节制欲望,主张“与民同乐”。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唱歌、吹笙、弹琴、鼓瑟,还有深厚的音乐理论知识,论语中就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说明了孔子对正确的评价音乐作品提出了要从“美”和“善”两个方面考虑。孔子还主张用礼乐培养和建立个人的高尚品格,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最重要的是孔子认为礼乐与治理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五色”“五声”等东西,“皆生之害也”,[5]他们认为音乐是危害人民的。墨家也对音乐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也认为音乐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是因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子故墨子曰:为乐非也”。[6]
《吕氏春秋》的音乐思想有明显的杂家色彩,其特点就是用阴阳五行的学说统摄儒、道、墨等家的思想,即“兼儒墨,合名法”,是在对先秦时期各流派音乐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挥的,但偏重于道家系统。[7]
(二)《吕氏春秋》的音乐观点
1.音乐的本源
《吕氏春秋·大乐》篇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8]
度量是指管乐和弦乐在一定长度的容量内,所发出的振动频律。《古乐》有记述伶伦制作十二个标准音的经过,“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9]《音律》中则有论述十二律的计算方法,“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10]
《吕氏春秋》关于度量问题的论述,其特色在于它对为何要有一定的度量所作的分析,《适音》篇说:“夫音亦有适。太钜则志荡,以荡听钜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故太钜、大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11]就是说声音太大会使心志动荡,耳朵无法容纳,身心会不舒服。反之则会使心志疑惑,耳朵不充实,内心不满足。因此,音乐的声音不能太大、太小,太清晰、太浑浊,而是要适中。
“太一”是一个抽象复杂的概念。《道德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2]“道”和“太一”内涵一致,都是指事物本源。《吕氏春秋·大乐》把“太一”又称谓“天常”,该篇解释为:“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13]这里的“天常”,是泛指自然界的规律,但是由“太一”生出的“阴阳”已经不是形而上学的凝固观念,而是日月星辰的不断运行,四时寒暑的交替,带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
“太一”“天常”“道”是指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之源泉,而“度量”也是来自于自然、来自于“道”,就是强调“生于度量”与“本于太一”的一致性,更突出了音乐与自然界不可分割的关系。
2.音乐的审美观
《吕氏春秋》主要是围绕“欲”“乐”“理”三个方面来阐述音乐的审美观点。
首先是关于“欲”。《吕氏春秋》既批判道家、墨家等学派“非乐”的观点,肯定了人民对音乐审美的欲求,又反对无节制的欲求,明确提出节制的观点。《情欲》篇有:“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14]这句话就是认为耳之乐声等等,不仅是出于人的天性,而且也是人的生命的必然需求。
其次是关于“乐”。审美愉悦的感觉即是“乐”,《吕氏春秋》认为人都有“欲”,但并非都能从“欲”进而达到“乐”,能否实现对音乐的审美愉悦,要有四个条件:一是音乐本身的“适”“侈”,因为以侈乐为乐不是真正的乐,只有“适音”才是给人愉悦的“乐”;二是社会环境的安危,因为“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而“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15];三是听乐者能不能节欲,不能节欲者则“耳不可瞻,目不可厌,口不可满”,导致“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以致于“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16];四是听乐者心境能否平和,因为“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17]
最后是关于“理”。“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怎么才能使心合适呢?在于“适心之务在于胜理”,即:“夫乐有适,心亦有适……。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18]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吕氏春秋》的音乐思想既重自身的修养,也重视治国的道理,反复探讨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二、《吕氏春秋》音乐思想与政治之关系
《吕氏春秋》中的音乐思想与政治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政治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讨论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就必须讨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即探讨音乐的社会功用。
在音乐的社会功用方面,诸子各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9]在先秦时期,诗是唱出来的,所以这也是孔子在论述音乐的功用,他认为要充分发挥音乐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效果。孔子还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有智慧、勇敢,而且还必须“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20],主张用音乐加强对人自身的修养。老子崇尚自然,认为教化人民不能用仁义善美等标准,而是用“道”来感化,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否定人为而失自然的有声之乐,推崇无为而自然的无声之“道”。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1]
《吕氏春秋》认为音乐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充分顾及和肯定音乐的社会作用与教育意义。如《适音》指出:“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记于音乐以论其教。”[22]《吕氏春秋》主张把音乐当成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用它去感化人。
(一)社会对音乐的影响
《大乐》篇说:“天下太平,万民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务”“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23]。《适音》更指出:“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凤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24]可见,天下政治安定时,音乐能发挥其积极的愉悦作用,当处于乱世之中,音乐则不能发挥这种积极的作用,是一种“悲而哀”的音乐。
《侈乐》篇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古代的圣贤之所以重视音乐,是因为音乐能带来身心的享受;而乱世之音乐,则把音乐当成了一种奢侈的追求,音乐越追求奢侈则民越抑郁,而国则越乱,“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萧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25]在这里则指出了夏桀、殷纣为追求庞大的音乐,以巨大、众多为壮观,追求耳所未闻、目所未见的音乐形式,这种对音乐的奢侈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朝代的灭亡有很大的联系。
(二)音乐对社会的影响
音乐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的政治教化方面。例如《适音》篇:“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26]先王制作礼乐,并不是娱乐耳目、满足口腹,而是教化民心、明辨是非、实行理义。此外,《音初》篇作了深入的论述:“世浊则礼烦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27]世道混浊,礼烦杂而乐淫荡,即所谓的“郑卫之声”“桑间之音”。
《吕氏春秋》继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对一切淫乱的音乐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样的音乐不能对民众产生良好的教化,民乱则政治就会混浊不堪,社会也就动乱。基于这样的看法,《音初》篇进一步指出:“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28]要产生好的音乐,君子必须修养良好的道德,这样的音乐才能教化好民众,政治才会稳定,社会也就不会动乱。
可是《吕氏春秋》夸大了音乐对社会的影响,如《古乐》篇指出:“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29]认为音乐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昌盛和灭亡,这种音乐亡国论则夸大了音乐的作用。《吕氏春秋》以乐教化,以乐治政的音乐观点,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把音乐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提高到一个不适当的高度,则夸大了音乐的社会功用。作为意识形态的音乐,是从属于政治的,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不能混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
三、《吕氏春秋》音乐思想与政治之关系的现实意义
自秦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和“中庸之道”,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相处。在先秦时期,“和谐”的音乐思想就已经出现了,如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中就有:“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同时也指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合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这样音乐的作用就能达到“和合君臣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30]
《吕氏春秋》中也有许多关于和谐的音乐思想,如:“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亦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31]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下太平,万物安宁,都随从着上面的教化,音乐的作用才算完成。制成音乐要有设施,必须节制欲求。嗜欲不邪辟的人才可以从事音乐。从事音乐要有方法,必须从平正出发,平正出于公正,公正出于有道,所以,惟有得道之人可以与其谈音乐。亡国难民也有音乐,但这种音乐不能使人快乐,要淹死的人不是不笑,罪犯也不是不唱歌,发狂的人也不是不手舞足蹈,乱世的音乐就像这样,君臣、父子、夫妇都不能正常相处,人民在痛苦的呻吟,在这种情形下制作音乐是怎么可能呢?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音乐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谐的音乐思想体现了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和谐;不和谐的音乐思想则体现了乱世的景象。当今的政治是太平盛世,我们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要求和谐的音乐应不断出现,而和谐音乐的创造者应是“得道之人”,无道之人则只能是垃圾文化的制造者。
《制乐》篇中也指出:“欲观至乐,必于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32]要欣赏最好的音乐,必定先要有最好的世道。谁施政仁厚,其音乐也因此盛大;谁施政刻薄,其音乐也就单薄。而动乱的世道,就谈不上什么音乐了。《吕氏春秋》在这里告诉我们从音乐的品级中,就可以分辨一个时代的施政是仁厚还是刻薄,是治世还是乱世。
注释:
[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44.
[2]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
[3]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5.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8.
[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2.
[6]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73.
[7]李耀建.《吕氏春秋》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J].高校社会科学,1989(3).
[8]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55.
[9]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84-285.
[10]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25.
[1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73.
[12]司马哲.道德经[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96.
[13]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55.
[14]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85.
[15]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55-256.
[16]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85.
[17]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72.
[18]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72.
[19]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1.
[20]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5.
[21]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3.
[22]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73.
[23]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55-256.
[24]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73.
[25]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65-266.
[26]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73.
[27]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35.
[28]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35-336.
[29]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84.
[30]吉联抗(译注).乐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13+39.
[31]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255-256.
[32]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47.
[1]吉联抗.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2]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M].齐鲁书刊,1987.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5.
[4]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5]王志成.《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J].齐鲁艺苑,2002(2).
[6]罗卉.《吕氏春秋》音乐思想研究的两个问题[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3).
张川(1981—),女,湖北黄石人,讲师,硕士,汉族,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音乐系教师,从事古筝和音乐理论教学工作近13年,研究方向:器乐和中国音乐史学。
本文系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Q245,课题名称:朱载堉《律吕精义》乐器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