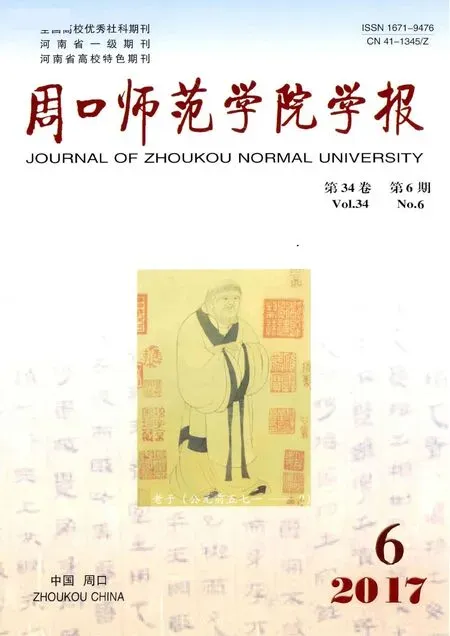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瞬间的惊险一跃
——邵远庆访谈录
2017-01-28邵远庆
付 静,邵远庆
(1.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2.周口市作家协会,河南 周口 466000)
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瞬间的惊险一跃
——邵远庆访谈录
付 静1,邵远庆2
(1.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2.周口市作家协会,河南 周口 466000)
付静:邵老师您好!您一直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是周口作家群里短篇小说的代表。您的作品文字幽默质朴,故事引人入胜,同时又包含着人生的哲理。交谈中,知道您来自于豫东一个民风特别淳朴的小村庄——西华县奉母镇前邵村,这个小村出了3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谈起家乡,您非常有感情,家乡给您的创作带来了什么?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创作经历,让我们对您的创作背景能有一个纵向的、更深入的了解?
邵远庆:在周口这块版图上,我的老家虽说只有指甲盖那么大,颍河的分支鸡爪沟居然也绕着村庄稍微弯曲了一下,或许因弯曲的幅度不够大,或许目前尚未给小村带来太多的神奇和灵性,所以那个名为“前邵”的地方,只能出现几个所谓的作家了。这当然是戏言。前邵村仅是个普通的行政村,却一样有着古老的历史。听长辈说,我们村以前是个寨子,周围有厚厚的围墙作保护,只留下东、西两道城门供人们进出。寨墙以外的地方全是白茫茫的水域,水里有芦苇,岸边有垂柳,一种叫“小白条”的鱼类成群结队地在河面上追逐嬉戏。可惜这种美景早已荡然无存了,“文革”期间寨墙被拆除,河道也跟人一样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干涸。否则的话,我们村现在应该是个不错的旅游景点,至少也能划入“美丽乡村”的范畴。
我们村的姓氏并不复杂,两千多口人当中,除了几户朱姓以外,其余都姓邵,也都是邵雍的后人。邵雍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他根据《易经》中八卦形成的原理并结合道家思想,发明创造出自己的宇宙观和学说体系,后人称之为先天学。著作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渔樵问对》等。正因如此,我把“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嫁接到老家头上觉得并不算过分。
如果说我个人的创作之路是受“浓郁的地域文化”影响未免有些牵强,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家很普通,跟豫东平原上的大多数村庄没有太大的区别。写作只是个人爱好而已,是讲究“随缘”的,也是顺其自然的,不存在丝毫的被动和勉强。同学当中比我有才气的人太多太多,他们的作文水平都比我高,智商也比我发达,只是他们将才气用在别的地方,抑或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迁给埋汰掉了。我从这种侥幸般的机遇中挣扎而出,用老家的一句话说:显出你那一鼻子灰!所以我认为激发我个人创作灵感的应该跟良好的阅读习惯有关,促成我走向写作道路的应该是理想、兴趣和勤奋。
付静:您成长的那个年代,精神生活还比较匮乏,您小的时候是怎么培养起的文学兴趣,是什么让您执着地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
邵远庆:在读初中以前,我的童年时光均是在这个巴掌大的故土里度过的。有句话说得好: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小时候笑着笑着就长大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变老了。儿时的日子虽然贫瘠,却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美好和乐趣的。从产生记忆开始我的职业是捡杨树叶,那时间因为缺烧,必须靠残枝和树叶来补充。母亲把搓好的几根纤细的麻绳交给我,让我到公路旁的杨树下捡树叶。我像穿羊肉串一样把梦想穿成一个长串再兴高采烈地拖回家。——这大抵算是幼时最大的收获了。到小学四、五年级时候又学会“烧炕”。那时间我老家遍地都是烟叶,有烟叶就得有烟炕。白天大人们要下地劳作,烧炕的重任便义不容辞地落在我身上。晚上再交给爷爷和父亲值守,爷爷负责前半夜,父亲负责后半夜。我依稀记得每个繁星满天的晚上,我睡在一棵槐树下的凉席上,开始攀着爷爷为我讲故事。爷爷虽骨瘦如柴,肚子里却装满许许多多的好故事,如《杨香武三盗九龙御杯》《杨家将》《七侠五义》等。但是每次不等爷爷将故事讲完整,我便沉浸在紧张的故事情节中昏沉睡去。一个故事通常要讲几个晚上,才能将它听囫囵。
因为家穷,我只能靠亲戚的周济,才能偶尔买回些连环画津津有味地阅读。但是那些连环画对我来说完全是形式大于内容,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在去一个朋友家玩耍时,无意间发现他爷爷家居住的屋子有个破箱子,里面放了许多书籍,每本都有板砖那么厚。朋友家世代行医,家境自然比常人好出许多。我大喜过望,偷偷拿一本回去阅读。读完再悄悄放回去,换一本揣在腰间。我对文学的偏爱大概也正是在那时间开始的,阅读给我的精神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为我今后的文学创作汲取了相当丰富的营养。
1996年,我在《周口日报》副刊发表第一篇小小说《送匾》。当时我在民政部门下属的一家企业上班。忙完“政务”我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闭门造“说”。后来因行迹败露被领导说成“不务正业”,我只能把写作由公开转为秘密进行。后来接连在《四川文学》《广西文学》《热风》《杂文报》《文学故事报》等报刊发表几十篇作品,也有不少作品被转载,并连续几年入选“年度最佳”选本,个别作品还被选入语文课本和高考试卷。
但是我至今仍不认可自己为专业作家这个称谓。无论从写作水平和发表数量方面来讲,我都觉得我跟那些所谓的专业作家相差甚远。文学这片水域太深,艺无止境嘛,需要我今后不断地努力和提高。所以迄今为止我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爱好者和初习者。
付静:在阅读中,我发现您的很多作品,比如《乡村寓言》《天上有个太阳》《憋尿》《谈婚论嫁》《沿着老路奔跑》等作品,故事和人物都来自于民间,有些应该是您非常熟悉的身边的故事,您通过这些乡邻中的平凡人生,展现了市井生活百态,从中揭示了生活的真谛。从中可以感受到您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块土地上乡民的深厚感情。能谈谈乡村生活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邵远庆:老家地处周口、漯河、许昌三地交界位置,这样的地方在治安方面往往比较混乱。但是老家不同。我几乎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村内的大街两旁,诸如玉米、辣椒等农产品堆积如山,更有小四轮、摩托车、拖斗等农用机械长年累月地随意摆放。而且至今尚未听说过有丢失上述物品的现象发生。所以每每讲及此事,我都会无比自豪地对外人夸赞说: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前邵特色!
家乡人的纯真、质朴、良善和勤劳的本质特征一直令我深有感触,它时常会像喝到体内的酒浆一样引发我内心的抒写欲望和冲动。因为地多,家乡人在经济收入方面仍以传统农作物为主,很少有人举家外出打工,也基本不存在农村当前惯有的“空巢”现象。乡亲们目前唯一的经济支柱是辣椒。辣椒这小东西听起来普通,身子骨却如同婴幼儿一样娇贵,从秧苗到栽种,从管理到收割,再从采摘到销售,足以让人连篇累牍地从初春忙到冬末。后秋本来就是个繁忙季节,我深夜出门游荡时,经常看见一些头戴矿灯的人在堆得如屋脊一般高的辣椒垛上忙碌,我也经常听见小四轮发出的隆隆声在田间的夜幕中飘荡。尽管现在的科技已经相当发达,但是乡亲们真正付出的巨大的体力劳动,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众所周知,这几年农作物价格酷似钱塘江的潮水一般波动很大,一毛钱一斤的蔬菜、瓜果比比皆是,烂在地里无人收拾的尴尬场面时有发生。农民的收入通常得不到有效保护,他们的付出与收入往往是不成正比的。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病态和扭曲现象,对每一位心存良知的写手来说,都应该去积极关注和思考。虽然我们不能身体力行地去促其改变什么,但是对于劳动人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至少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去聆听、去发现、去讴歌。——这恰是作为一名写手最起码的应当承受的责任和担当。
付静:在交谈中,我听到您的创作是从小小说写作开始的。有观点认为小小说属于短篇小说的一个分支;也有人认为它不属于短篇小说的分支,是作为独立的小说品种,与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并列的一种新样式。那么您是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的?
邵远庆:小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个新兴文体,她以短小精悍和触人心灵的快捷方式,给读者迅速带来一种精神享受和感悟。我最初也是以小小说为主从事业余创作的,后来专门出版一本小小说集《容不进半点砂砾》。我认为一篇好的小小说,恰恰好在受其篇幅短小和字数有限的约束下,能以小博大,知微见著,通过一些小细节和情节,实现对一个大的社会背景的刻画,从而引发读者的强烈震撼和深思。而如今的小小说文体概念日渐模糊,通常集故事、杂文和小情调之类的文章于一身,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精品意识,缺少对细节的把握和形象刻画。作品往往偏重于故事和结构,而忽略了语言和叙事技巧。在日前郑州召开的“小小说新论坛:内容创新与载体创新”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小说名家、评论家对小小说进行把脉问诊。《小小说选刊》总编辑任晓燕说:“近年来小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内容上的同质化现象,内容重复、情节雷同、缺乏新意,这是遏制小小说发展的头号杀手。”
无论长、中、短篇还是小小说,我认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叙事方式和技巧,各自有各自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就叙事方式来讲,长篇小说就像拉锯,中篇小说就像拿钝刀砍树,短篇小说像用斧头砍树枝,而小小说则像拿刀切菜。可以根据作者的构思、素材和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去合理选择文体,能长则长,能短则短,是勉强不得的。
我后来之所以涉猎中短篇小说创作是受了张功林的“误导”,他说单纯写小小说没出路,力劝我尝试写中短篇。那时间我俩都在《大河文学》杂志做编辑,季刊的工作量不大,有足够的写作时间,但是我却没能写出与时间和环境成正比的数量和分量的作品来。鲜花插在牛粪上可以继续盛开,一旦插在尿素或化肥上则必死无疑。所以环境和状态对每个人来说很重要!那几年我倒是写了几个中短篇,除了两个短篇分别发在《牡丹》和《雪莲》之外,其他基本都打了水漂。
付静:您认为小小说的创作,周口作家群里大致有三种写法,您的写作更偏向于哲理型、寓言体的,我突然发现您比较偏爱“寓言”,能谈谈您对“寓言”的理解吗?
邵远庆:当时在周口的这方小小说版块上,写得比较成熟的、已经形成个人鲜明风格的作家有几位。孙方友先生以新笔记体方式打造一批传奇色彩的小镇人物系列;程习武先生擅长以闲云野鹤式的手法去刻画人物形象;车中州老兄则以暖情调为叙事方式,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和目的。近年来写小小说的人更多,像红鸟、顾振威、飞鸟、刘艳杰、王伟等,他们大多已经熟练掌握小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方法,距离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也就一步之遥或者已经基本达到。我一直对类似哲理型的小小说比较偏爱,通过一些简单的人和事去表现一种哲理和思想,已成为我在构思和创作当中不经意间形成的固定模式。
寓言是文学作品中一种常见的体裁,采取寄托和隐藏的写作手法,使故事的意义和道理更加深刻,从而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无论采取何种文体写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写出深度和广度。这就需要作家不断地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挖掘生活,不能仅限于和书籍、报纸打交道,如果仅仅依靠阅读经验去写作,文本中肯定会露出苍白和贫血的面容。李敬泽先生针对目前的文学现状曾说过:现在的作家写的底层,除了“小姐”写得比较真实外,其他的都面目可疑。
付静:寓言体小说往往使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使精深的思想和隽永的哲理得以通俗、平易、畅达地表现。您的一篇小说的名字就叫《乡村寓言》,是不是也体现了您对这种形式的一种偏爱呢?
邵远庆:严格来说《乡村寓言》的内容是构不成一个短篇的,她缺乏必要的应用素材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仅仅是把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堆积在一起,组成这篇寓言式小说。但是迄今为止,我个人仍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她能够生动刻画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小人物的善良、执拗、勤劳、俭朴的性格特征。在创作当中,我把一些能用的生活细节通过合理布局穿插在一起,再融入许多虚构的东西,使“寓言”的成分更为明显,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乡村寓言》发在《莽原》杂志的头题,并获得当年的周口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作品的一种偏爱和认可吧。
付静:邵老师,我能问您一个私人性的话题吗?每位作家在写作时可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癖好,您有吗?
邵远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无非是或轻或重、明显与不明显罢了。我的最大嗜好是抽烟,尤其是在写作的时候,基本达到手不离烟、烟不离口的程度。夜晚的写作时间,通常是根据抽烟的进度决定的。一包烟抽完,时间差不多已经夜里11点多钟,只能住手了。
付静:在中国小说界,现代作家们从五四开始就对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进行学习,当代很多的作家都在关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辩证关系,小说的形式有时甚至大于小说的内容,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邵远庆:我做编辑时候,有位老作者拿一篇小说让我看。他自认为这篇作品写得很好,甚至在畅谈中几欲落泪。我读后却认为这篇作品水平很一般,如果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或许能在省级纯文学刊物发头题,但是现在,他的叙事手法已经明显落伍,陈旧得像一盒过期的蛋糕,刚打开就能嗅到一股刺鼻的酸味。——我认为这正是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区别。一篇好作品对“写什么”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关键是怎么写。在怎么写的同时,把写什么的意图和主旨表达出来,这才是一位成熟小说家所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
不仅是文学作品,现在很多影视作品也是如此:把场面和背景设计得无比宏大和唯美,人物着装尤为华丽和上档次,镜头像拍照片似的频繁闪烁。除了形式上走马观花外,从中却看不到任何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艺术是相通的。如何“留白”给读者,是每位艺术家都应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付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生活的经历、文化的背景、生命的体验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如何通过作品把这些经历和体验艺术化地表达出来。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自己作品风格、语言、结构等方面的感受?
邵远庆:受当前社会发展趋势和市场生存法则影响,很多期刊的选稿标准迫使作者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偏向一种误区。很多小说往往只侧重于讲故事,把自己知道的故事以“故事”的方式讲述给不知道的人听。这种作品就像新闻稿件一样,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过后便什么也不是了,很快被读者忘掉。文学作品如果仅限于复制生活,将会永远落后于生活。一篇可以流芳百世的好作品,应该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让人记得住、传得开。
我的创作素材同样来自生活,把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已知的和未知的,哪怕只是一个点或者一个由头,凡是觉得能令我怦然心动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我以艺术加工的方式表达出来。具体能不能高于生活我不敢断定,但至少都与我身边的人和事息息相关。因此我的小说通常都带有浓郁的豫东地方特色,那种近似于土得掉渣的语言,早已深深植入我的血液和骨子里,让我如此坚定、执着、深入地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
小说的结构对一篇作品来说尤为重要,它就像一栋建筑物的主体框架,不仅能凸显出设计者的审美观念,又能准确表现作者扎实的基本功和对作品的驾驭能力。作品风格更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她是作者在写作水平方面日臻成熟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个人觉得,真正能形成自己鲜明和独特创作风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家”。
付静:刚才的谈话中,我发现您其实也在寻找一种突破,短篇小说的创作想要重新整理思路,语言上注意凝练。您近期发表的历史系列小说三题,就是您寻找突破口的新尝试吗?
邵远庆:超越和突破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位写手都应当思考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觉得目前约束我们创作思路的瓶颈,是我们的眼界和思想不够开阔。因为我们自小深受传统教育模式和思想道德观念的禁锢,在出手前的每个字、每一撇一捺都建立在思想道德和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这种无形的约束让我们很少能够像西方作家那样充分展现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这对每位写手来说是相当可怕的。著名评论家何弘先生曾说过,小说创作不只是要讲一个或者一系列故事,而是要通过叙事,传递我们对个人、社会、世界的理解,要有自己精神的建构,要有思想的深度,要对时代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小说是一门叙事艺术。因此,如何通过叙事来完成精神的建构和思想的传达,是小说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历史题材的作品对我来说不算首次尝试,平时我也不会刻意逼迫自己去写。我至今仍对小小说创作的热情不减,生活中凡是有可以利用的素材和线索,都会激发我对小小说创作的冲动。一个点带动一个面。历史小小说同样如此。所以这对我来说应该不算是一种突破。真正需要突破的东西不是题材,而是认识和写作手法。
付静:您下一步有什么创作打算?
邵远庆:今年的写作时间安排得比较紧凑,先写了两个“乡村人物”系列短篇,接着又写一个官场内容的中篇,另一个中篇还在创作当中。文章在于三分写、七分改。所以我并没急于把这些作品撒出去,而是全部存放在电脑里,等沉淀一段时间后,再拿出来重温一下感觉,能达到先让自己满意的程度岂不更好?接下来还要完成一部长篇,一稿在前年差不多已经写完,下半年打算完成二稿。至于何时能够出版,要看机遇了。
付静:期待您的新作品早日问世。以后的创作是不是仍以短篇小说为主?
邵远庆:短篇小说对我来说犹如乡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捞面条”,不但做起来方便,而且吃起来比较可口。短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是最讲究技巧的,很多时候她需要一个成熟而又漫长的酝酿过程,或许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支撑点和爆发点。刘庆邦老师在《短篇小说的种子》中讲道:短篇小说的种子可能是一个题目、一句话、一个细节、一种思想、一种理念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有一个东西,一个故事,可能在我们脑子里存在若干年,觉得可能会写成一个短篇小说,迟迟不能动手写,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种子所在。可能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种子在哪里,就会感觉一下开朗,时候就到了。
短篇小说的魅力在于瞬间的那么惊险一跃。具体能不能“跃”上去,全凭个人造化了。
【责任编辑:曹丽华】
2017-07-30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经典文学阅读现状与对策研究”(2017-ZDJH-269)。
付 静(1977-),女,河南周口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邵远庆(1973-),男,河南西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小说创作。
I206
A
1671-9476(2017)06-0035-04
10.13450/j.cnki.jzknu.2017.06.07